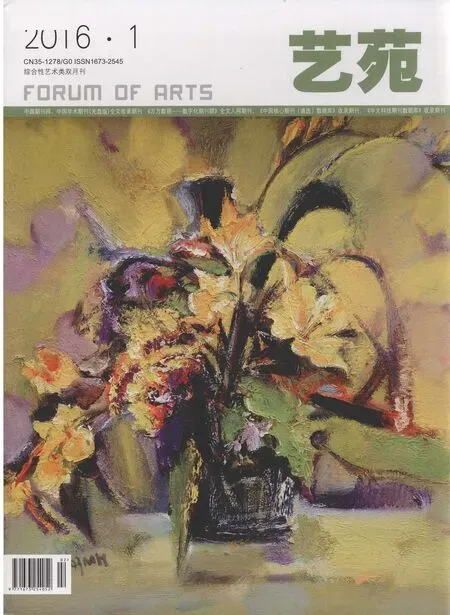《港》:票房與口碑的背離——關于“核心競爭力”與“目標觀眾群
文‖郝朝帥
?
文‖郝朝帥
【摘要】電影《港》的票房與口碑背離較為嚴重,其原因在于主創徐崢放棄了前兩部“戲”取勝的關鍵:以“向下”的價值取向作為“核心競爭力”,以及以年輕人為“目標觀眾群”的投其所好。
【關鍵詞】《 港》;“核心競爭力”;“目標觀眾群
2015年9月下旬開畫的《港囧》,到了第十天票房總量已經攀升至12.8億元,成功刷新了此前創造神話的《泰囧》,而到了10月下旬,這個數據已經被刷新到了16億——再次穩穩站上了華語2D電影的票房巔峰。只是,在第二次迎來這輝煌時刻的時候,徐崢的心里或許爽得并不那么徹底。與上一部《泰囧》不同,《港囧》自從公映之后,基本就被淹沒在吐槽的口水里,線上線下多是差評滔滔——雖然口碑和票房相背而馳對于當下的中國電影市場而言可謂常見,但相對于徐崢背后的付出和信心而言,碰到這種現象還是多少令人有些挫敗與不爽吧。
如果沒有《泰囧》的票房奇跡,人們對《港囧》也不會有這么高的期待,正所謂“成也蕭何敗蕭何”:因為有了前者的超好的市場鋪墊,后者才會有強大的票房號召力,而處處用前者成績來衡量后者的結果是,幾天之后口碑就被票房遠遠地甩在了后面——問題出在哪里呢?缺少了黃渤和王寶強,搞笑鐵三角變成了徐崢獨角戲?包貝爾刻意模仿王寶強,但是人緣不濟成了邯鄲學步?這些說法都似是而非,一部系列電影,只要劇情保持自己的“核心競爭力”,時刻牢記取悅好“目標觀眾群”,上面那些理由都不足以撼動觀眾的口碑。徐克當年導演的《黃飛鴻》系列,甚至男主角都能從李連杰換成趙文卓,一樣還是完美的經典。
而《港囧》真正讓人擔心之處在于,作為“囧”片系列,它似乎在“核心競爭力”和“目標觀眾群”這兩條商業電影的生死命脈上都出現了令人不安的“游離”——而這兩條在前面的《人在囧途》與《泰囧》中則得到了堅定的選擇和貫徹。
一、“向下”的價值取向與“核心競爭力”
雖然導演不同(《人在囧途》為葉偉民,《泰囧》則是徐崢本人),但前兩部“囧戲”的整體故事框架與角色設計可謂一脈相承。徐崢與王寶強,一個是都市中成功人士狀的“老板”,衣冠楚楚、器宇軒昂;一個是城市的邊緣人物——進城打工的牛奶場工人或者油餅師傅。王寶強的形象一直是“傻”而耿直、“笨”且溫暖,他用那顆未曾被商業社會所馴化的質樸、坦誠,在人心惟危的都市中保持著樂觀的天性,既有著頑強的生命力,也有柔軟的內心。他對母親的孝、對朋友的信、對陌生人的善,都使得他活得坦然而且堅定。而作為這些特質對立面的徐崢——貌似在生活中游刃有余的“中產階級”,他們擁有了一定的金錢和地位,但卻是活得緊張焦灼、躲躲閃閃,不敢(或無法)直面自己的生活,生活質量其實比不上前者。這兩種人原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很難形成交集,一旦不得不形影不離的時候,沖突與摩擦必然不斷發生,包袱笑料也在啼笑皆非中一次次生成。而這種種沖突摩擦的結果是,看似更加聰明的徐崢總是顧此失彼、計劃落空,而頭腦一根筋的王寶強卻會歪打正著、愿望達成,并且,影片最終還是草根王寶強的質樸與活力拯救了陷入精神危機之中的中產階級徐崢,讓他更深刻地找回了生活的真諦、幸福的真諦——作為喜劇類型片,前兩部“囧戲”堅定地執行了這樣的敘事立場,王寶強對徐崢的一勝再勝,則是高調張揚了中國的傳統道德觀(或者說仍是今天官方與民眾共同認可的“主流價值觀”)。王寶強角色身上負載著的是“老實人不會吃虧”、“人算不如天算”、“公道自在人心”等等傳統中國所推崇的品質。而兩部“囧戲”也同時構設了一個關于屌絲逆襲的美好故事,顯示了草根階層的巨大力量,給銀幕前“沉默的大多數”提供了有效撫慰。
值得一提的是,這種“向下”的價值取向的主導性,不僅僅體現在今天的各種商業類型片中,比如在韓寒那部充滿文青氣質的《后會無期》中,同樣延用了這種敘事模式:陳柏霖的角色就是一個有文化的王寶強,而馮紹峰的角色則更靠近徐崢。影片中,后者雖然外出闖蕩多年,有一種世故的油滑,待人接物顯得很有經驗,然他更習慣于看到人性的黑暗面,并沒有在外面的世界中磨合出強大的內心,一旦遇到打擊動輒氣急敗壞、束手無策;而前者作為一個海島上的小學教師,雖然沒見過什么世面,但他對身外的世界有著滿滿的善意,在多年的“讀萬卷書”中已然修煉出通達的人生態度,總是氣定神閑地以不變應萬變。于是,經過一番探險之后,二人最終命運是,馮紹峰的角色在故事中徹底消失,不知所終;而陳柏霖的角色則成為人生的贏家,不但功成名就,還成為保存家鄉小島的功臣。
——可以說,這種主導性價值觀的昭示,這種角色力量的反轉,就是兩部“囧戲”的“核心競爭力”。對于以盈利為目標大眾文化產品,這一點絕對不可忽視。可以看到,近些年來,在高速進入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同時,通行在社會生活中的是強者邏輯,贏家通吃,在經濟叢林里爭取進入食物鏈頂端才是普通人追求的終極。而商業電影,作為“造夢”的工廠,從淺處言,必須要有效撫慰那大面積未能(或許完全沒可能)進入食物鏈頂端的觀眾們,這樣才能獲得滿意的市場票房。從深處言,大眾文化畢竟還肩負著引導大眾的“教化”意義,當下社會道德水準的整體下滑也需要以足夠的“正能量”來進行反撥。就像好萊塢大片,越是在生活中美國老百姓的離婚率高,它就越要維護男女主角家庭的完整,哪怕是離了婚的也要讓你破鏡重圓,“第三者”即使再優秀也要安排他(或她)退出,甚至以死掉的方式徹底玩完(遠的不說,近幾年且看從《2012》到《末日崩塌》)。這也算是電影工業的一種“社會責任感”了——不用去嘲笑故事模式的老套、情節的爛俗,有市場也有口碑就是商業片的硬道理。也正是因為這樣的屢試不爽,某種固定的敘事立場才能成為影片的核心競爭力。
于是,回過頭來看《港囧》,難免感覺有些“杯具”了。用包貝爾頂替了王寶強,可除了造型上的盡量靠近外,人物與情節設計都可謂是另辟蹊徑,誤入歧途。徐崢還是徐崢,那位活得不開心的中產階級,可包貝爾卻再也不是純樸的屌絲,正能量滿滿的普羅青年了。他是一個天分不足的二貨文青、富家子弟,或者說,是中產階級的未完成狀態,徐崢未來的繼任者。他的腦筋不足一如既往,但內心也欠缺作為“拯救者”的道德力量。這一次,徐崢只能依靠自己頑強地找回內心,修復青春傷痕,而包貝爾,就只留下制造沖突、完成笑料這一種功能了(他對于“拍紀錄片”的理想堅持或可算作正能量,但也不強于徐崢“證明青春”的信念堅持)。如此一來,影片的敘事立場就發生了可疑(可怕?)的傾斜,整部影片成了中產階級的自我肯定,成功人士的自我歌頌。而上文所說的以草根青年拯救中產人群的“核心競爭力”,則被放逐得無影無蹤。——這種敘事立場的選擇,真可謂是太不高明了,跌入了近年來被人們屢屢詬病的國產片窠臼。什么窠臼?中產階級的自我驕矜,中產生活的高調炫耀。就像前幾年在國內市場一度走紅的、以《非常完美》、《杜拉拉升職記》為發端的“小妞電影”,多是打造了關于“中產階級”的愛情神話與事業神話,但這些看似“勵志”的影片高開低走,在當下的中國影壇日益末路,即便是擁有吳彥祖和古天樂這種絕對男神的《單身男女》系列也無力回天。唯一的反例大概就是那部以小搏大的經典案例《失戀33天》了,而它恰恰是反“中產階級”敘事的:白百何扮演的小職員每天搭地鐵、合租房、生活在沒有高富帥和白富美的空間,但照樣可以理直氣壯地甩臉色給有錢女人,充滿優勢地戲弄有錢男人。這部影片票房口碑雙豐收,背后的人心所向一目了然。養尊處優、衣帶漸寬的中產者的自我追尋、實現、表揚,對于銀幕前更多年輕的、不掌握任何社會資源的年輕人來說,可遠觀而不可親近。——當然或可誅心一點,認定此番徐崢為自己設定的這個角色,是“中國最高票房導演”身處巔峰時自覺不自覺的膨脹所致,自己已經是業界大牛、金牌導演,怎堪再讓一個“傻根”來啟蒙開悟呢?沒有口外羊,一樣吃涮鍋子!(1)
二、銀幕下的逆襲與“目標觀眾群”
同時,也有數據顯示,目前中國電影的觀眾集中在二十出頭的年輕人群中,而中國電影票房增量又主要由二三線城市的“小鎮青年”帶來。同時,“中國大城市的年輕人絕大部分也并非土生土長的‘城里人’,而是真正意義上的‘小鎮青年’,如假包換”(2)。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很好地解釋了,2012年的《泰囧》何以成為(《捉妖記》之前的)國內票房冠軍,獨孤求敗了好幾年。王寶強土里土氣的形象非常容易受到年輕觀眾的認可,他可能就是大家生活中常見的村頭二蛋、街邊阿狗,傻乎乎中透著股可愛的執著,雖未受過高等教育卻有著明確的人生堅持,做事憑良心,靠譜也暖心。更何況,影片最后總是證明,他還是人生真正的贏家呢。這種影片看著絕對是一個舒服。所以,前兩部“囧戲”關于“目標觀眾群體”還是瞄準得妥妥的,投其所好,正中下懷。
而隨著角色設定的轉變,《港囧》的“目標觀眾人群”的問題也就此凸顯。這部由趙薇重點參與的(以戲份而言,很難說這部電影有所謂女主角)的“后青春”影片卻似乎刻意走了趙薇《致青春》的路線,將目標人群對準70后一代,意圖格外明顯。像影片中致敬的無數港片和老歌,多是在1990年代走紅、70后們耳熟能詳的“舊作”。而主角徐崢的初戀發生的時空,更是明確地申明“1994級油畫系”——標準的70后上大學的年份。在復現一個90后時空的飽滿度來說,這部影片比《致青春》更充分到位。只能說,這次徐崢要下定決心為同齡人代言了,縱然是一部中規中矩的商業片,也要包裹著自己的一腔情懷再打包外賣出去。
如果說,銀幕下徐崢和趙薇的同齡人看到這些,心中難免暗潮翻涌,情不自禁地為自己曾經的青春觸動一番、傷懷一把的話,那影片給包貝爾的同齡人(和更年輕的人群)又留下了什么呢?想當初王寶強的角色,是因為正規教育和商業社會都在他生活中的缺位,因此他放大夸張了的傻勁與樸實還顯得真實可信。而包貝爾扮演的這位“山寨版”呢,則是一個莫名其妙的二貨,雖然是學電影的大學生,還背著藝術大家的語錄,可腦子一樣不好使,而且也缺少任何一點讓人感到親切的情懷與溫暖,正能量完全看不到。這樣的角色即便真正的文青同道也很難認可他(想想彭浩翔早年《買兇拍人》里那位同樣做著電影夢的可愛的屌絲青年吧),廣大普通青年更不會去接受這樣衣食無憂、滿身無趣的所謂“藝術青年”。可是,真正支撐起中國電影票房的觀眾,是70后還是90后呢?應該取悅哪個人群更有商業眼光呢,這本不是一個問題。要知道,《致青春》的票房成功不可復制,它更多是依靠趙薇個人的IP,而不是不常看電影的70后人群。
在“目標觀眾人群”問題上,如果對比另一部同期上映的喜劇片《夏洛特煩惱》,更顯得意味深長了。和《港囧》比起來,這部影片在前期造勢上簡直可以忽略不計,“開心麻花”團隊或許有些知名度,但絕大多數的人只知道他們的小品上過幾次春晚,而春晚對于今天的年輕人來說又基本無感。但是,這部電影硬是敢與《港囧》在2015國慶檔期“同臺打擂”,而且是不聲不響地低開高走,依靠良好的口碑一點點地發酵出12億多票房,直至一舉超越了前冠軍《泰囧》。(3)說它與《港囧》分庭抗禮一點也不過分,雖然總體票房上還是略遜一籌,但在投入產出比上,尤其在觀眾口碑上,很顯然《夏洛特煩惱》結結實實地贏了——恰如一場始料未及的屌絲逆襲。
非常有趣,兩部影片其實故事框架還大體相同。都是一位活得不很如意的中年男人,心中念念不忘年少時初戀的女神,為此一把年齡了還要執著地回到往昔,尋找自己青春的存在依據。不同的是,《港囧》中的中產生活者徐來(徐崢)在現實生活中上山入地,經過一番奇遇之后感悟到還是身邊的妻子和生活最值得珍惜;而《夏洛特煩惱》中的屌絲級人物夏洛(沈騰),則是經過一場漫長的黃粱美夢后幡然醒悟,回到妻子身邊。那為什么類似的情節架構口碑卻反差甚遠?顯然不是因為《夏洛特煩惱》的笑點設置更加高明——徐崢在這方面不僅一點也不差,毋寧說,作為一部商業電影,《港囧》顯然在制作品質上,在電影元素的豐滿上,在畫面的精良上,還要勝出很多。一個更有力的解釋應該是,一個屌絲男人的故事——他的煩惱和幸福、情感與傳遞,距離銀幕下年輕觀眾們的生活更近,與年輕觀眾們更投緣,更“接地氣”。尤其是片中那一碗“茴香打鹵面”,讓很多年輕觀眾為之動容:有道是“人間有味是清歡”,作為生活中的大學生、小職員、普通的打工仔打工妹,當影院中的燈光再度亮起時,他們就要回到寄身的學生宿舍、格子間、生產流水線……但他們一樣可以有自己青春而青澀的甜蜜,有物質匱乏而精神豐盛的愛情。《港囧》成功人士的錦衣玉食遙不可及,但這樣一碗妻子為丈夫做的家常打鹵面,也許就是他們生活中的愛情最有體溫的表達。所以,《夏洛特煩惱》雖然說的還是中年人的故事,但夏洛這個低微普通的男人,他的處境和心態更容易和年輕的心發生共鳴。
銀幕里,夏洛是個標準的loser,除了在夢中,他的人生也不會有更多精彩與傳奇,做不到為了彌補那一個青春的初吻而遠赴香港,他的妻子更做不到買下一個法國的畫室向他表達愛意——影片中沒有給人看到奇跡的發生,正如在現實生活中一樣,夏洛這樣的人很難有機會逆襲人生。但是,在銀幕外,得觀眾者得天下,卑微的夏洛在“時光倒流”中完爆了有錢人徐來。如此強大的“群眾基礎”無疑是一筆巨大的無形資產,為“開心麻花”團隊的下一部影片做足了市場鋪墊。一年或幾年之后,如果說《港囧》目前的2D電影票房冠軍被“夏洛”他們的續集給奪去了,那也真的不用大驚小怪。
三、結語
在談到《港囧》的票房新高時,有人扒出了徐崢在準備這部電影時所做的種種前期工作,他的繁密、細致、精確都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的確很少有人能夠比得上他下的功夫。他的各種精益求精,足以顯示他是一個標準意義上的商業片導演。(4)但是,《港囧》票房與口碑的背離,也算給他提了一個醒,對電影市場的研究和潛力發掘,或許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要放下身段,不要自覺背上“偶像包袱”,太把自己當成“神”了。也許這一點對于剛剛開始走上“神壇”的“開心麻花”主創沈騰同樣重要。
注釋:
(1)關于這部戲,王寶強、黃渤和徐崢之間為何“分手”的說法,在各種傳媒上鋪天蓋地,無可證實或證偽。但能夠看到的是,在《港囧》首映日當天,王寶強和黃渤在微博上對此都未作反應,昔日“鐵三角”在感情上的破裂已是不爭的事實。
(2)《小鎮青年撐起中國電影半邊天》,“騰訊娛樂”網頁2013年11月1日。http:// ent.qq.com/zt2013/guiquan/71.htm?pgv_ ref=aio2012&ptlang=2052。文中注明,所謂“小鎮青年”,泛指二三線城市的年輕人。但文章同時提到了,在很多縣城中,今天也有一些現代化的影院陸續開張,縣城中的年輕人“走進影院已經成為一種習慣”。
(3)來自“中國票房網站”1 0月2 3日數據,網址http://www.cbooo.cn/ m/628183?tn=sitebaidu。
(4)《最賣座的三部華語片,憑什么他占倆》,“毒舌電影”微信公眾號,2015年10月16日。
作者簡介:郝朝帥,文學博士,廣東第二師范學院中文系副教授。
[中圖分類號]J90
[文獻標識碼]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