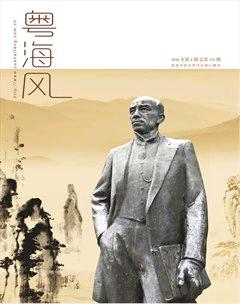《封鎖》的誤會、套話與反諷
余岱宗
如何讓兩位陌生的人物相識,進而相戀,這常常讓小說家頗費思量。兩位戀人,如果相識的介體不過是同學朋友的關系或相親介紹,容易落俗,拉近人物的距離更要藝術家發揮創造力。如果相識的情景過于新奇,那就需要藝術家多多發揮“圓場”的本領,為相識的偶然性周旋出必然性來,否則不近情理。羅曼·波蘭斯基執導的《苦月亮》男女主人公相識在公共汽車上,女主人公逃票,查票的來了,男一號悄悄地將自己的票遞給女一號,“自我犧牲”的他被逐下汽車。男一號是位三流作家,副業是花花公子,他這下可找到事做了,每天都到巴黎的同一個公共汽車站尋找女主人公,那么,他能找到那位逃票女郎嗎?車廂邂逅的關系能發展出什么樣的人物關系呢?韓國電影《我的野蠻女友》的男女主人公的相遇則被安排在地鐵中,鬧劇式的相識很符合整部戲的基調。藝術家似乎都鐘情于從封閉的交通工具中發展出陌生的戀情,加拿大作家門羅的短篇《機緣》的男女主人公亦相識在列車上,他們身份殊異,一位是放寒假的女博士,攻古典文學,另一位是出來旅行的漁民,模樣精明。兩位主人公素昧平生,小說家卻能對人物施加種種擺布力,在極有限的空間里,幾番周轉,不由得讀者不信這對陌生男女有相識的可能。關系發展很快,男女主人公不久便在觀景車廂一塊兒抬頭望天。加拿大的寒夜繁星點點,捕魚的漢子擁有豐富的航海經驗,常以星座導航,于是他告訴年輕女博士天上的星座分布;古典文學女博士諳熟希臘神話,對星座為何如此命名一一道來,天上的故事如數家珍。列車密林間穿行,這一男一女,待在寒冷的觀景車廂,透過玻璃天窗,看星空夢幻般流轉,絮絮叨叨的都是天上的故事,語調傳達的卻是“為你而來”綿綿情愫。《機緣》的結尾,老太太艾麗絲·門羅設置的情節布局竟讓女主人公“跌入”令人難以置信的情感迷思的境地,在學院和家庭環境中從小中規中矩的女博士的叛逆式“逃離”之旅所面臨的情感難局令人咋舌。艾麗絲·門羅的諸多短篇小說中“暗藏”著大量女性的“叛逆”“犯忌”的故事,不過,作為一位具備了高超而冷靜的敘事操縱能力的奶奶級女作家,門羅對女性世界的“泄密”式寫作,無論是從故事層面還是語言層面,往往都是點到為止,甚至有意將種種叛逆故事進行背景化或往事化處理。也許,一位資深的長者作家才擁有足夠的理解力和寬容心,將世情百態都放置在一個既洞徹又寬宥的道德情景中加以觀照。對于同一種故事不斷調整道德校準位置的門羅,她的短篇故事中遍布“樹洞”式的隱秘故事,對于人物心路探索皮相化且缺乏耐心的作家是難以企及門羅式的智慧深度和道德高度。
門羅的《機緣》的故事始于一列長途列車車廂之中,張愛玲的《封鎖》也讓故事發生在一部電車車廂內。當然,這只是表面的相同點,其內在的相似在于,創作《封鎖》之時的張愛玲雖不過二十多歲,其對人性的理解的開闊度與寬容度卻已經達到相當成熟的水準,在這一點上,張愛玲與門羅都顯示出女性作家特有的洞徹力、領悟力與寬容心。當然,門羅的寬容還帶有縱容的意味,她對筆下屢屢“犯規”“犯錯”的女主人公辯護式開脫式的書寫得益于門羅老辣精到的道德情景的不斷變換,而這種道德情景的悄然轉移往往又是在看似無心的隨筆化敘事中獲得漫不經心的多次調整。門羅不提供理論化的辯護,她只是拉開時間的距離或帶出另一個當事人的感受來消解道德沖突的緊張感。至于張愛玲,她對筆下人物的行為的縱容是十分有限的,其人物的“發乎情,止乎禮”的“回歸”是人物最終與環境達成和解的一種常規路徑。無論是《傾城之戀》,還是《紅玫瑰與白玫瑰》,張愛玲主人公的“叛逆性”多是內心戲十足,但外部動作遠不及門羅的主人公那么“離經叛道”。張愛玲的悲憫,相當部分分配給人物“回歸”社會認可的道德規范框架之后的自我抑制乃至自我摧殘。
張愛玲善于嘲弄和挖苦,但張愛玲的小說不會被當做諷刺小說,原因便在于張愛玲在挖苦和嘲諷之后生成出的是對人的種種弱點洞徹之后的寬宥。夏志清推崇張愛玲,格外突出的是張愛玲的悲憫心,以為張愛玲“她能和珍奧斯汀一樣地涉筆成趣,一樣地筆中帶刺;但是刮破她滑稽的表面,我們可以看出她的‘大悲——對于人生熱情的荒謬與無聊的一種非個人的深刻悲哀。張愛玲一方面有喬叟式享受人生樂趣的襟懷,可是在觀察人生處境這方面,她的態度又是老練的,帶有悲劇感的——這兩種性質的混合,使得這位寫《傳奇》的青年作家,成為中國當年文壇上獨一無二的人物。”[1]諷刺中溶解著悲哀,悲哀是被嘲弄之后的理解。張愛玲善于挖苦,是因為她了解“俗人”,她能瞬間辨識出現代都市中各色人等常態下的算計、權衡、計較、愚蠢與怯弱。然而,就是挖苦“俗氣”和“算計”,張愛玲并非只是“露丑”,而是有點欣賞精明的“俗氣”。比如,張愛玲對《傾城之戀》中白流蘇這位“有本領的女人”的婚姻豪賭,多少有些欽佩,盡管張愛玲對于白流蘇和范柳原的兩性對弈不無調侃。展示“俗”的言行之時,張愛玲對“俗人俗事”極盡調侃,但筆調潑辣卻不惡毒,言語犀利卻帶點辯護。
《封鎖》,正是從車廂之中的一群“俗人”只言片語的交談開始。戀愛故事之前是一大段“浮世繪”般的車廂風俗畫,敘述者似乎在享受“偷聽談話的樂趣”,這樂趣來自于聽到背后說同事壞話的兩人對話,夫妻倆關于西褲干洗費的議論。這看似簡單的車廂里“塞滿”了“俗人們”從車外帶進來的種種“閑氣”“閑事”“閑話”,乘客話語飄散出來的,都是各自生活軌跡延伸進來的精神痕跡。張愛玲寫出了他們思想的逼仄,也寫出了一群乘客的自以為是,他們都誤讀了一位醫科大學生所繪的人體骨骼簡圖,卻誤解得振振有詞頭頭是道。這誤解對應這之后兩位男女主人公的一連串的誤會導致的相識相“愛”。張愛玲對于誤會的使用真是爐火純青,誤會才可能讓兩位有點呆板的“正經人”來一場戀愛,誤會還帶來了歪打正著的詼諧性:誤會導致自作多情,誤會的自作多情讓無意者變得自信,自信又推動自作多情者進一步多情。也許,人與人的交流,許多時候誤讀要多于正解,人與人之間不就是在反復誤讀的過程中嘗試著交流。歧義叢生的語言,讓人物間的交流充滿了“美麗的誤會”,宛如女主人公助教吳翠遠讀了男生寫的作文竟然臉紅,僅僅由于這作文的作者是男生,僅僅只是因為文章里寫了些貌似大膽其實大而無當的話,便誤以為男生將自己引為知己。如此善于誤會的女助教,她即將迎來一場情愛誤會便不會被視為不可能。男主人公呂宗楨“搭訕著望了一望她膝上攤著的練習簿,道:‘申光大學……您在申光讀書!他以為她這么年青?她還是一個學生?她笑了,沒做聲。” 如此開心的“笑”,在于如此可愛而自然的誤會比任何贊美都更沁人心脾。一本大學生的練習簿,先后兩個誤會都以此為介體,張愛玲就地取材的本領真是高超。
很難想象,如此沉悶單調的電車車廂,兩位陌生人,即便聊起天,也不見得往戀愛方向走。可是,張愛玲憑著三四種誤會,五六回合應答,竟然讓平時挺拘謹的一男一女談情說愛,還令女助教哭起來,“眼淚唾到他臉上”。讀者可能在回過神后覺得這樣的故事不太可能發生,可是,小說家只要在文本中不斷賦予主人公每一環節的感受變化和情緒波動以合理性,那么,讀者就有可能被敘述者牽引主人公的內心世界。這種感受、情感變化的合理性,《封鎖》中,便是透過大大小小的誤會讓第一眼看上去“整個的人像擠出來的牙膏,沒有款式”的女助教變得“熾熱,快樂”。女助教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形下,在男會計臨時虛構出來的“調情戲”里充當一個角色,女助教沒有認出這是一出“假戲”,由此便順理成章誤讀了男會計的所有的行為。女助教并非不聰穎,被人拉來當演員做道具她不知情,但她還是迅速辨識出會計男絕非那種敢作敢當的男子。可是,晚了,女助教來勁頭了,她要將故事表演下去。門羅的《機緣》是通過一個極端事件讓人物靠近,而《封鎖》則是透過一連串“美麗的誤會”成就一場虛擬戀愛。
誤會鼓舞了女助教,“覺得自己太可愛了的人,是熬不住要笑的”,于是,她成為戀愛中傾聽者和交談者。可是,兩位陌生人,如何才能通過交談戀愛起來呢?光閑談,顯得單調;彼此抒情,容易空洞;放肆調情,不符合人物身份。怎么辦?《封鎖》的辦法是讓女主人公一邊戀愛,一邊審視與自己演對手戲的男子,或者說,女主人公“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她抓住這次被人求愛的機會,嘗嘗自由戀愛的滋味,但她很清楚這樣的戀愛是沒有結果,她只是要“看看”自己是怎么戀愛。女主人公稀罕浪漫,但她沒有被浪漫沖昏了頭,而是計算著浪漫都行進到什么步驟。這就是張愛玲式的浪漫敘事,其主人公哪怕陷入浪漫之中,也少不了對對手的揣度和盤算。張愛玲的特色就在于她很能創造都市男女的浪漫,但她的目光從來未離開浪漫中的博弈性。也許,張愛玲還覺察出一個現代都市男女的戀情原則:沒有無條件的浪漫,浪漫也免不了權衡與計算。《封鎖》中,女助教心理活動往往走在男主人公話語之前,女主人公心里剛剛嘀咕“世上有了太太的男人,似乎都是急切需要別的女人的同情。”男主人公便脫口而出“我太太——一點都不同情我。”男主人公如螃蟹吐泡沫般說出串串戀愛套話,女助教樂得照單全收,享受著戀愛的滋味,評判著套話的價值,掂量著情感的真偽。這位女助教絕不會像翠翠那么單純,她要戀愛,但她又很了解戀愛中的套話程序公式性,這又免不了帶點批判的意味。再從藝術技巧角度看,沒有戀愛套話,缺乏花言巧語,戀愛故事不好進展,但套話式的花言巧語又極容易被讀者識破,怎么辦?干脆就讓女主人公直接評價戀愛套話吧,這就讓套話不那么套話了:情愛套話被女主人公一番挑剔之后,套話的“套話性”多少消解了。張愛玲這一招可謂一箭雙雕,既避免了直接寫套話的“俗”,又刻畫了女主人公的聰明,以及聰明的女人也擺脫不了要人愛她的渴望。聰明的女人還特別懂得套話的價值:“戀愛著的男子向來是喜歡說,戀愛著的女人向來是喜歡聽。戀愛著的女人破例地不大愛說話,因為下意識的她知道:男人徹底地懂得了一個女人之后,是不會愛她的。”男人徹底地懂得一個女人會不會愛她?這很難說。女人愛聽戀愛中的男人的套話、傻話、閑話,卻是容易理解的。因為套話或傻話雖然其中的內容不見得新鮮或經不起推敲,但獻殷勤本身便令人陶醉。再說,就是女助教本人,她也完全明白這偶遇的“愛情”是不會有刻骨銘心的成分的,有的只是對一次“意外愛情”的白日夢似的體驗,就是女助教的“哭”,也是因為她怪男子太認真了,不懂得白日夢的價值,“以后她多半是會嫁人的,可是她的丈夫決不會像一個萍水相逢的人一般的可愛——封鎖中的電車上的人……一切再也不會像這樣自然。再也不會……啊,這個人,這么笨!這么笨!她只要他的生命中的一部分,誰也不希罕的一部分。他白糟蹋了他自己的幸福。那么愚蠢的浪費!她哭了……”這樣眼淚,不是為戀人,而是為自己;這樣流淚,更多是怪罪對方不懂“虛擬情愛”的價值,“萍水相逢”的男人一下就將戀情與實用的婚姻聯系起來,毀敗了“真空狀態”中素昧平生的一對男女的“戀愛幻覺”。所以,眼淚的價值不是真情,而是情感游戲的“不完整”或“不真誠”。
這就是《封鎖》的“幻想之戀”,真誠以不真誠的方式進行,不真誠的戀愛又要求具備真誠的表達特征或程序流程。戀愛的真誠性與浪漫性具有完整的編碼,套話與眼淚一樣具有價值——女助教希冀的,不過是浪漫流程編碼的“完整性”。戀情編碼的可重復性,可復制性,與戀情對象的唯一性,在女助教那兒形成悖論:她預測她未來的丈夫不會具備這位萍水相逢男性的浪漫性,她的婚姻不過是世俗婚姻編碼中再次重復的一次婚姻,但車廂偶遇的男性的唯一性不也“收編”入浪漫編碼的鏈條中嗎?再說,女助教的眼淚,既是對浪漫戀情的悲悼,但悲悼本身不也是浪漫流程中不可或缺的甚至可以說很關鍵的環節嗎?
羅蘭·巴特以《少年維特的煩惱》為藍本,分析了戀情中種種表現程序,闡釋戀情編碼的文化意義,其中“眼淚的功能”一節,是這樣說的:“我讓自己落淚,為了證實我的悲傷并不是幻覺,眼淚是符號跡象而不是表情,借助眼淚,我敘述了個故事,我敷設了一個悲痛的神話,然后便將自己維系其上:我與它俱生,因為通過哭泣,我為自己設立了一個探詢者,得到了‘最真實的信息,身心的,而不是口頭的信息:‘嘴上說的算什么?一滴眼淚要管用得多。”[2]是的,眼淚是戀情的印戳,表明戀情的真誠度乃至某種唯一性。眼淚的符號意義,在于證明女助教的確是經歷過了一次極其短暫但確實存在過的戀情,而不是僅僅只是“幻覺”。應該承認,女助教并不是毫無用心的,她不是福樓拜筆下的魯道爾夫,《包法利夫人》男主人公魯道爾夫的眼淚是造假的淚:“他把信又念了一遍,覺得很不錯。‘可憐的小女人!他帶著幾分同情想道,‘她會認為我的心腸比鐵石還硬;信上應該灑幾滴眼淚才好;可是我哭不出來,這不能怪我。于是魯道爾夫倒了一杯水,用手指蘸了些,讓一顆大水珠從高處落到信紙上,形成一塊淡色的印跡……”[3]這樣的眼淚要與女助教的眼淚完全區別開來。魯道爾夫是利用造假的眼淚來嵌入戀情編碼中,形成具有欺騙性的戀情流程。女助教相反,沒有人強迫她流淚,她也沒有必要做給誰看。女助教的淚是一種自我哀悼,是與她自認為不可能再擁有的浪漫戀情告別之后的悲哀。張愛玲筆下不少女性多具有上海人的精明,但精明不能與欺騙畫等號。精明的女人曉得戀情的程序性,她更明白這種“真空愛情”的幻覺性,她清醒地分析這種幻覺性,但浪漫性本身又要求不宜過多的計算,是需要帶著某種“癡情癡念”去投入的,由此浪漫性便被清醒性所破壞。然而,浪漫性又是女助教所稀罕的,因此她就退而求其次,心想哪怕是臨時性的浪漫或階段性的浪漫也是值得成為未來的記憶的。因此,在小說的結尾,男主人公問她電話號碼
“翠遠飛快地說了一遍道:‘七五三六九。 宗楨道:‘七五三六九?她又不做聲了。宗楨嘴里喃喃重復著:‘七五三六九。伸手在上下的口袋里掏摸自來水筆,越忙越摸不著。翠遠皮包里有紅鉛筆,但是她有意地不拿出來。她的電話號碼,他理該記得。記不得,他是不愛她,他們也就用不著往下談了。”
就連能否記得她的電話號碼,女主人公都如此在意,不用說,女助教是挺挑剔的,但這種挑剔只是對臨時性浪漫的挑剔,她要男主人公配合得好一些,假戲也要像真的那樣有頭有尾地表演好。然而,封鎖一結束,一切都恢復了之前的狀態,浪漫戲也宣告謝幕。浪漫的脆弱,無望的孤獨,戀情的幻覺,人世的悲涼,張愛玲小說美學的諸種特征,都濃縮在這部短篇小說中。
張愛玲極會營造浪漫情節和浪漫的氛圍,但她不沉溺,總有另一種目光在審視這種浪漫。浪漫以及對浪漫的懷疑,再一步,警覺、懷疑之后的寬宥與諒解,才共同構成了張愛玲小說美學對現代都市男女的獨特敘事。這一特點,在《封鎖》中,也是明顯的。
注釋:
[1]《中國現代小說史》,夏志清著,第296頁,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二版。
[2](法)羅蘭·巴特 《戀人絮語——一個解構主義的文本》第174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第一版。
[3](法)福樓拜,《包法利夫人》,第236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