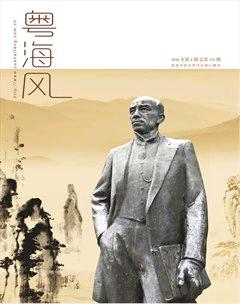王任叔之死
王東梅
王任叔(1901—1972),著名作家、文藝理論家,新中國首任駐印尼大使。浙江奉化人。早年即開始對新文學運動發生興趣,是早期文學研究會會員,創作過大量詩歌和小說,其中小說《疲憊者》被茅盾選入《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他不僅是作家,還是革命戰士,1923年前后即參加過家鄉的社會改革活動。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到廣州任北伐軍總司令部秘書處秘書,當他覺察到蔣介石要背叛革命,馬上離開了蔣。隨后,在寧波被捕。出獄后曾任中學教員并到日本留學。1930年回到上海,加入“左聯”。1931年任海員總工會黨團委員。抗日戰爭爆發后留在上海“孤島”。從事抗日活動和寫作。曾先后編輯《譯報》副刊《爝火》、《大家談》、《申報》副刊《自由談》,還和許廣平共同主持過《魯迅全集》的編輯工作,與此同時。還以巴人、八戒、行者等七八十個筆名寫了大量雜文。有人評論說,他是留在“孤島”的作家中,從事抗日活動最活躍、寫作品最多的一個,也是黨員作家中,團結黨外作家最廣泛、執行黨的統戰政策成績顯著的一個。1941年,“孤島”淪陷,他遠走南洋,協助胡愈之開展華僑抗日文化活動和統戰工作。日本投降后,他在當地從事華僑愛國民主運動,并參加印尼人民的革命斗爭。1947年10月被荷蘭當局驅逐回到香港。不久,即進入解放區,任中共中央統戰部第二處副處長。新中國成立后,于1950年任我國駐印度尼西亞首任全權大使。1954年起,負責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工作。1961年,因1957年發表的一篇雜文《論人情》,而被康生視為“人性論”典型,受到批判。被撤銷職務,調到東南亞研究所編寫印尼史。十年動亂中,他更是受盡折磨。最后被強行遣返原籍農村,精神錯亂,含冤逝世。本文所記述的正是王任叔同志輝煌生命的最后的沉痛旅程。
車爾尼雪夫斯基曾說:“悲劇是人的偉大痛苦,或者是偉大人物的死亡。”任叔曾把他的系列小說命名為《中國的悲劇》,而他自己,也成了悲劇中的人物。
1970年2月,他在痛苦、寒冷和孤寂中,迎來了春節。除夕之夜爆烈的鞭炮聲,艷麗的焰火,飄散在空中的火藥的濃香,喚起了他對自己的親人,特別是上海的克平(他的兒子)和小高高(他的小女兒)的思念。他再也不能帶著高高去胡愈老等老同志家中拜年了。往日的朋友很少有敢登門來看望的,有的甚至走在對面也早立即避開。環繞著他的是無限的寂寞、孤獨與痛苦。他在這痛苦的孤寂中度過了他在北京的最后一個春節。3月18日,終于決定遣送原籍。遣送書中規定:一、不準參加群眾大會,不準參加一切社會活動;二、不準隨意聽收音機(帶回的一架收音機被封存);三、不準出縣外就醫……
火車駛進上海站,看著這熟悉、親切的城市,自己在20年代中到40年代初在這兒參加革命的情景一幕一幕在腦際映出。他多么想下車回上海的家去看看,但,這是不允許的,他是被遣送的戴“罪”之身。克平聞訊帶著自己的兒子匆匆地趕到站臺。王任叔已陷入了痛苦的麻木之中。克平只能是讓父親吃上一碗送行面,以表綿長的孝敬之情。
汽車行駛在通往大堰的叢山峻嶺之中,這蜿蜒陡峭的山路,曾是他幾次奔出又幾次鎩羽而歸的熟悉的家鄉的路。家鄉的親人熱誠地迎接了他。侄兒夢林(王仲隅之子)安排了他的生活。
他仍住在自己幽暗的木屋里。隨帶的器物中,除了一床棉被和一條毛毯之外,主要是一箱印尼史手稿和參考資料。他每天修寫印尼史或查看資料,力作不輟。夢林勸他不要再寫了,以免再遭批判。他說:“人活著為了什么,還不是為革命。過去我的文章被批判是當時的形勢、時代所致,錯了,拿出來批判也可以教育大家嘛。”于是,每每夜靜更深,夢林所看到的,仍是從他窗口上放射出的長夜不息的燈光。這燈光,這不屈的圣潔的生命之光和天上的星光相輝映,伴著門前日夜奔流的溪水聲,譜寫著他的悲壯命運交響曲中的最后樂章。
這最后樂章中的唯一的一個歡樂音符是親屬和鄉鄰們為他舉辦的七十壽辰慶典。夏歷九月初八,人們在盛傳著林彪折戟沉沙的爆炸性消息的喜悅中,慶祝他的壽誕。張福娥老人、夢林和侄孫們以及遠村的親屬,童年時的朋友,歡聚一堂,獻上了帶濃郁鄉情的壽禮,舉杯祝他健康長壽。親情、鄉情給他帶來了一瞬間溫馨的安慰。在此之前,他的精神狀況已經很不好。
他的家鄉四面環山,只有那么大的一塊藍天,收音機又不準聽,他覺得自己與外面的世界隔絕了。談工作,論研究找不到同志和知音。尤其是想到還沒有給他作定案結論時,更覺得整個腦海里,充滿了鉛一樣沉重的不能擺脫的苦悶。他認為,把他遣送回鄉是對他的陷害。他曾多次往原單位寫信,要求返回北京,甚至寧愿去干校。但去的信總是石沉大海。他焦思憂慮,日夜不得入眠,腦血栓、冠心病和嚴重的神經官能癥侵害著他的健康,情緒也越來越壞。夢林是鄉里的干部,從他那里讀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和《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錄》的影印本之后,精神嚴重受挫,逐步發展為精神分裂。曾特別喜歡的煙也不吸了。晚上不睡覺,深夜里常常跑出去,敲打親戚和鄰居家的門,發出驚恐的呼叫。在冰天雪地的日子里,他不穿衣服跑出去,踉踉蹌蹌,倒在外面。他也常常癲狂地沿著溪畔行吟……散亂的滿頭白發,蓬草般的白須,目光呆滯,乞求似的仰望著蒼天……
叱咤國統區,縱橫海內外,躍馬文壇,日試萬言,熱烈、坦誠、敏銳、拙直、睿智、不畏刀劍、嫉惡如仇的王任叔癲瘋了!
只有兒子克平從上海趕來,才能有一點令人欣慰的安定。克平含著淚給老父親修剪著亂蓬蓬的須發。這閉塞的山村,缺醫少藥,夢林看著正遭受精神分裂痛苦的老人,鼓足了勇氣,毅然地向王任叔的原單位寫報告,請組織允許派人來,安排去外地就醫。委派的人來后,經商定,去寧波地區療養院治療。療養院在奉化溪口,這是蔣介石的家鄉。到溪口下車后,經武林門,王任叔看見大門上“武林”二字下有“蔣中正題”的落款,即說:“你們這是耍陰謀,把我送到蔣介石的老巢來了,簡直是陷害,我要回去,我決不住這里。”單位派來的人說:“這是組織的命令!”他說:“別的命令我服從,這個命令我決不服從!不讓我回去,我就跳樓自殺!”吵了一夜,無奈,第二天只得返回大堰。以后病情加重,夢林又兩次寫報告請求治療。單位電告克平,由他找人安排,同意出縣看病。克平經多方聯系,才得以去杭州精神病院治療。住院達半年之久,以為是不治之癥而推手。不得已,又返回大堰。
1972年春,王任叔病情日見加重,大小便亦不能自禁。常不穿衣服在街鄰面前或溪畔癲行。夢林無奈,只得含淚用一條圍巾將他捆綁在坐椅上。他可憐巴巴地叨念說:“我失去自由了,我已被綁架起來了……”病情惡化后,又不得不把他送到奉化醫院。7月25日,逝世于奉化醫院。彌留之際,身邊無一熟人,他孤寂地離開了人間。第二天,夢林與侄媳英風趕到縣醫院。二人置棺托遺體入殮。夢林吃力地拉著平板貨車,與英鳳扶靈走過返歸大堰的蜿蜒陡峭的60里山路。橫山上的蒼松翠竹,伏首沉目,送著這位50年前曾在這橫山上作詩,以鷹鷗自比,要飛出大堰、寧奉而翱翔于蒼茫天海的游子。如今,這位游子魂歸故里了。
故鄉的習俗是停靈三日必須下葬。這時夢林想起了王任叔留在筆記本上的絕筆:“一、我的病什么時候死是可想而知的!二、在我未死之前,希望組織上能給我政治上有一個明確的結論。三、編寫的印尼歷史,是否付印可由組織確定,近代史修改也即將定稿,是否錄用也由組織決定。四、死后安葬,可用一堆干柴放在沙灘上燒掉,把骨灰分成兩半,一半用一把小鋤頭在后門山上挖個洞,葬在后門山上;另一半托人帶到上海撒在黃浦江上……”
在溪灘上火化,他在近半個世紀前所寫的詩歌《余波》中(1923年4月1日《文學旬刊》第69期),就為自己描繪了這樣的身后情景:
床草在灘上燒去,
又不知什么人死了!
聽說又是一個著作家了,
他的妻子,
悲哀他的兩手。
再也不會拿筆抄寫人間的
事情,
把他在平日焦容枯發中所
寫的一堆著作,
與所常寫的禿筆與白紙,
盡行放在他的棺材里:
好似死了兒子的母親,
把孩子生前喜歡的玩具,
放在小棺材里一般.
聊以慰死者的苦心,
哭哭啼啼抬到山上去了!
可憐那不言不語的著作家,
再也不能寫出他最后的
悲哀,
只有震蕩后的死血,
滴滴斑癱透過了著作里!
當地沒有火葬條件,夢林不忍心在度過了他夢幻般的童年的溪灘上焚燒他的遺體。還是用壽材讓叔叔安歇在了故鄉群山的懷抱。一陣陣飄著野花芳香的山風,在撫慰著這顆返歸故里的負著冤情的靈魂;天上飄來的朵朵白云,作為葬衣和墓土,輕覆著這位詩人,這顆文化巨星,更顯出他的圣潔和純凈……
終于,歷史的陰霾被掃除,中國出現了晴朗的天空,王任叔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自1986年至1991年,在短短的五年時間里,由文化、出版、教育、研究各界發起,先后召開了三次全國性學術討論會,來紀念這位卓越的無產階級文化戰士。全國已有十幾家出版社整理出版了王任叔的小說、散文、雜文、文學理論、戲劇、印尼史等著述20余種近500萬字,以繼承和發揚他“以血代墨,死而后已”的不朽的“巴人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