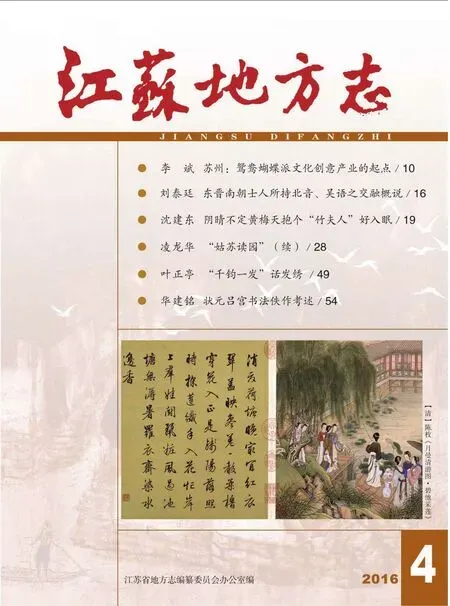蘇南城市規劃中古橋文化遺產的保護模式——以常州古橋遺產保護為例
◎ 嚴 波 張 勇
蘇南城市規劃中古橋文化遺產的保護模式——以常州古橋遺產保護為例
◎ 嚴 波 張 勇
一、引言
蘇南地區是江蘇省南部地區的簡稱,包括南京、鎮江、常州、無錫、蘇州五市,擁有廣袤的太湖平原,長江東西橫貫境內,京杭大運河流經蘇南大部。蘇南地區受地理位置的影響,雨量充沛,氣候濕潤,河網縱橫交錯,是名副其實的水鄉澤國,其中水域面積占21.15%。再加之經濟繁榮發達,創造出豐富的以蘇南古橋為代表的眾多城市文化遺產。蘇南古橋文化遺產是江南“水鄉記憶”的重要符號,是蘇南城市文化建設不可或缺的一環。
近幾十年來,蘇南經濟持續以較快速度增長,城市建設大規模展開。城市發展帶來難得歷史機遇的同時,也在文化遺產保護等城市文化建設方面遇到更為嚴峻的挑戰。如何在城市化加速發展進程中,持續推進城市文化建設和文化遺產保護,成為迫切需要研究解決的現實問題。
二、常州古橋遺產現有的保護模式
古橋文化遺產與現代城市發展的確存在著難以兩全和此消彼長的矛盾關系。怎樣處理好這對矛盾,有待于不斷的探索。近幾十年來在常州城市改造建設中如何保護古橋遺產,歸納起來有八種模式:
1.本善橋模式
本善橋模式是采用“開辟新橋,保護老橋”方式解決陸路交通壓力矛盾的樣板,是一種相對經濟的模式。常州市本善橋位于金壇市金城鎮清培村,橫跨清培河上,是常州地區保存較好的一座宋式單孔石拱橋。本善橋擔負金壇西北鄉村的水陸交通,橋西是聞名遐邇的天荒湖,橋東“過街棚”連接沈瀆、白塔古鎮。所跨的清培河是通向蘇、錫、常地區的黃金水脈,北河通往潭頭古閘和呂坵、莊城、上新河三大古鎮,南河與通濟河相通直達縣城。在“三分天下”水占其“一”的清培,這座古石橋帶來清培集市的繁榮。1995年4月19日,本善橋被公布為江蘇省第四批文物保護單位,也是常州市第一座被列入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的古橋。
本善橋地處清培村村頭,經過全面維修,使古橋重新煥發了生機。為了有效地保護好古橋,已經在本善橋旁新建了一條馬路作為村民出行的通道(圖1),本善橋作為古老的人文歷史文化景觀受到科學的保護,得以休養生息。常州許多古橋遺產就是采用這種方式保護,作為古老村落的象征,即受到村民的呵護,同時還保留了原生態。

圖1 古橋保護模式之一——本善橋
2.寶善橋模式
寶善橋模式是另外一種解決陸路交通壓力的方式,即采用古橋擴建的方式。寶善橋位于常州市新北區孟河鎮小河東街36號東,南北向,橫跨在老孟河上,是一座單孔石梁橋。寶善橋建于清宣統年間,因為時間的流逝這座石橋也變得破損不堪。1983年,當時的武進縣小河公社重新將這座橋進行了擴建,原來這座橋寬只有3米,用三根條石并鋪而成,擴建后增加到8米多(圖2),擴建部分是鋼筋混凝土的雙曲拱橋。橋下原有水閘,現殘存部分構件。至今橋一側的橋柱上還刻有“武進縣小河公社”“一九八三年擴建”字樣。
在一些城鎮道路建設中,如果遇到因道路拓寬涉及到對古橋保護問題,一般的做法是在老橋的旁邊開辟新橋。但如果該橋在所在路段仍在發揮著道路交通的作用,又沒有空間另外建造新橋時,其做法是在保持古橋原有形制不變的前提下,以最大限度保留住古橋的主要構件,在古橋兩側鋪設新的橋梁,讓古橋與新橋并駕齊驅。這樣既保護了古橋的主體結構,同時又可緩解城市交通擁塞。寶善橋模式對原來古橋的歷史風貌有較大的破壞,是某個歷史階段采用的古橋保護模式,現在已不采用。
3.禮嘉雙橋模式
禮嘉雙橋模式是古橋按原貌重新修繕的樣板,這是現在古橋遺產保護采用比較多的方式。禮嘉雙橋位于常州市武進區禮嘉鎮老街,禮嘉雙橋為兩座平板石梁橋,是兩座一橫一豎相毗鄰的石橋,跨興隆河,其中東西走向的叫禮嘉橋,南北走向的叫太原橋。禮嘉雙橋首尾相接,呈“L”形布局的雙橋橋制在常武地區絕無僅有,是常州地區江南水鄉縱橫交匯的特色橋梁代表。2011年1月5日,常州市人民政府公布為第五批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同年禮嘉雙橋被評為常州市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十大新發現之一。
修復之前的禮嘉雙橋為了方便現代交通工具出行,橋面澆筑了鋼筋混凝土,橋欄也改為鐵欄,原橋梁石階幾乎無法辨別,看上去已是改良過的新橋。太原橋雖然保持著原貌,梁石上的“太原橋”三字清晰可辨,但所跨的河道早已填沒,成了一座旱橋。禮嘉雙橋失去了舊時的風貌。2013年7 月,武進區公路管理處組織工程技術人員對禮嘉雙橋進行搶救性加固維修。2014年11月,對禮嘉雙橋本著修舊如故、保存歷史的原則進行修繕。此次修繕根據石板平橋的形制將水泥橫梁換成了石梁。原本埋沒在水泥橋欄中的石橋欄,此次也一一顯現了出來。為原汁原味地展現當年禮嘉雙橋的風采,石橋欄中缺失的部分,施工方用同樣的石材和雕刻方式作了補缺(圖3)。
禮嘉雙橋是禮嘉當地水利工程設施的重要組成部分,屬橋涵碼頭,在歷史上起到了航運、交通等重要作用,為反映禮嘉各個歷史階段的重要發展和歷史變遷提供了重要依據,也為禮嘉漕運文化提供了特殊的見證。禮嘉雙橋的修繕,對于研究禮嘉及常武地區的歷史文化,展示常武地區明清兩代能工巧匠的精湛技藝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時也對禮嘉歷史文化的傳承有著非常重要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圖2 古橋保護模式之2——寶善橋模式

圖3 古橋保護模式之三——禮嘉雙橋模式(修繕前和修繕后對比)
4.烏路橋模式
烏路橋模式解決水路泄洪壓力的樣板。上面兩種模式是緩解了陸路交通的壓力,烏路橋模式則是解決水路排洪的壓力。位于天寧區青龍街道華嚴村丁塘港上的烏路橋,地處水陸交通要沖。烏路橋所跨的丁塘港,連接京杭大運河與北塘河。丁塘港上從北到南依次建有狄墅橋、史家橋、烏路橋、潞城橋、奉先橋和丁堰橋六座古石橋,這些古橋除烏路橋外今已全部拆除或改建成現代橋梁。丁塘港水流湍急,遇到發大水,烏路橋就影響排洪。1982年為有利泄洪,就在拱橋西側將橋堍駁岸開通,向西收縮,并在水中筑兩墩設三孔梁橋,這樣,烏路橋就成為拱梁相接的石橋。拱橋的橋孔高大,供舟船通航,增梁橋孔有助泄洪。改建后的橋梁在陸行、航行、泄洪三方面互補發揮作用。這種改建方法省工省料,因地制宜地把保護古橋與興修水利相結合,成為當地既有泄洪能力又有觀光價值的橋梁(圖3)。

圖4 古橋保護模式之四——烏路橋模式
5.廣濟橋模式
廣濟橋模式是古橋移建的樣板。現代城市的擴建,道路或河流的拓寬,一些橋梁難免會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被拆除或者破壞,類似情況在全國各地都有發生。如果喪失了原地保護的條件,則應當實行遷移保護,這符合《文物法》的精神,也是為了更好地保護這些歷史文化遺產。
廣濟橋位于常州市天寧區東坡公園御碼頭和半月島之間,東西走向,橫跨大運河,是一座三孔薄墩石拱橋,其中孔跨徑是城區古石拱橋中最大的。廣濟橋俗名“西倉橋”,原址位于城西西倉街大倉弄北口和西直街西端的京杭大運河上,連接西圈門和三堡街。西直街曾是一條繁忙熱鬧的街巷,東頭是文亨橋,西頭是廣濟橋,一條大運河沿著西直街綿綿地向東流淌,沿著街巷的兩邊商店林立。

圖5 古橋保護模式之五——廣濟橋模式
1984年春天起,蘇南運河常州市區段拓寬試點全面啟動,先拓寬運河市區東段,即從同濟橋到原白家橋地段,因首當其沖的白家橋沒有能保留下來,后來引起極大的爭議。為此,市有關部門重新審視和規劃僅留存的廣濟橋(西倉橋)和文亨橋(新橋)的移遷工程,廣濟橋成為常州市古橋“喬遷”的第一個“吃螃蟹者”④。1986年這座已達530多高齡、造型精巧的三孔石橋,移建至現東坡公園內。取而代之的是一座能通行自行車的鋼架西倉便橋,現在仍然跨越在運河之上,鋼架油漆成藍色,成為運河一景。惠濟橋因為嚴重阻塞航道的原因,于1990年被拆除,拆除的石料被用于維修材料使用,甚是可惜。
盡管廣濟橋和文亨橋的移建比白家橋和惠濟橋的命運要好,但是古橋移建是迫不得已的辦法,并不值得提倡。保護古橋建筑不僅要保護文物的本體,還要保護其產生和存在的環境,古橋一旦離開了原來的環境,就等于離開了歷史,再也喚不起后人的記憶。有些古橋沒有被列為文保單位或者是大運河遺產點,只是因為不是原地保護,文物的原生態面貌被破壞了,文物遺產價值就大大降低了。這樣的教訓很多,像常州運河上的四大橋③(圖4):惠濟橋、白家橋、文亨橋和廣濟橋當初是因為京杭大運河常州市區段拓寬而消失或移建,而拓寬的運河使用二十年因為再次改道而成為景觀河。如果當初能夠多一點文保意識,運河早規劃改道,古橋就能夠保留下來了。也許常州運河四橋能夠像浙江省湖州市的雙林三橋一樣,成為全國文物保護單位。
6.焦溪古橋模式
焦溪古橋是鄭陸鎮焦溪村從北到南橫跨在龍溪河上的青龍橋、咸安橋、中市橋和三元橋四座古橋組成的古橋群,四座古橋均是常州市文物保護單位。焦溪古橋模式是古橋與周圍環境整體保護的樣板。2013年9月3日,江蘇省政府公布了江蘇省第七批歷史文化名鎮名村,武進區鄭陸鎮焦溪村入選名村目錄。2014年2月19日,鄭陸鎮焦溪村入選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國家文物局公布的第六批中國歷史文化名村名單⑤。
《常州市焦溪歷史文化名村保護規劃》劃定了焦溪村的規劃范圍(39.10公頃)和核心保護范圍(10.09公頃),包括歷史格局(歷史街巷、歷史河道、自然山水)、文物保護單位、歷史建筑、優秀傳統建(構)筑物、歷史環境要素等物質文化遺存和各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內的焦溪村歷史文化遺存保護對象,以“古宅、古街、古巷、古弄、古河、古橋”為載體,確立了焦溪村“一河、四橋、七街、兩巷、十三弄、多圈門”的空間格局(圖5),展示以“黃石半墻”建筑為特色的江南水鄉風貌,將焦溪村建設成為集生活居住、文化展示、休閑旅游等功能為一體的歷史文化名村。在保護村莊的歷史文化遺存真實性和歷史環境整體性的基礎上,形成“有風景、有生活、有文化”的“千年古村.圣賢焦溪”。
焦溪古橋模式優點在于,它是一種最理想的原地和原生態的古橋遺產保護模式,缺點在于需要相當的資金投入。隨著城市經濟實力的強大和文化遺產旅游的興起,應該考慮有更多的古橋通過歷史格局的整體保護得到有效保護,建設決策者們應首選這一模式。
7.上店橋模式
上店橋模式是文物保護單位目錄外古橋遺產保護的樣板。上店橋位于常州市武進區湖塘鎮上店村,是一座縱聯分節并列式單孔花崗巖石拱橋,南北走向橫跨興隆河上。上店橋代表清朝時期江南石拱橋的橋梁特征。上店是座歷史悠久的古鎮,約建于春秋時代。上店自古以來,人杰地靈,名人輩出。明末清初,著名畫家惲南田就誕生在這里,也是我國當代新聞界老前輩。明清時期的上店橋處在古驛道上。南通荊宜(今宜興),北達常郡,往來行李,晨昏不絕⑥。上店橋始建于明朝弘治壬戌年(1502)元月,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重建,1949年曾重修。1988年11月,武進縣(現為武進區)人民政府公布為縣文物保護控制單位。2011年3月,公布為常州市第二批歷史建筑。
歷史建筑,是指經市政府確定公布的具有一定保護價值,能夠反映歷史風貌和地方特色,未公布為文物保護單位,也未登記為不可移動文物的建筑物、構筑物。歷史建筑是體現城市歷史文化發展的生動載體,是城市風貌特色的具體體現,更是不可再生的寶貴文化資源。2008年7月1日,國家出臺了《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條例》,對歷史建筑的申報批準、規劃編制、保護措施、法律責任等方面進行了規定,歷史建筑的保護工作至此有了較為充分的法律依據。近年來,根據《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條例》等法律法規,常州市規劃部門及時制定了《常州市市區歷史建筑認定辦法》《常州市市區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實施辦法》《常州市市區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工作方案》和《常州市區歷史建筑修繕技術規程》,為歷史建筑的保護提供了政策支持與技術支撐。《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條例》規定,任何單位或者個人不得損壞或者擅自遷移、拆除歷史建筑;歷史建筑的所有權人應當按照保護規劃的要求,負責歷史建筑的維護和修繕;周邊規劃也應盡量與歷史建筑相協調。
對于還未能列入文物保護單位的古橋來說,先列入歷史建筑的保護目錄中也是一種途徑。目前常州市公布了三批歷史建筑,分別是2008年的33處、2011年的15處和2013年的178處,其中古橋有列入第二批歷史建筑的上店橋,列入第三批歷史建筑的東富村橋、(陶冶)太平橋、西虹橋、莊基橋、小錢垛橋、陸家橋、西莊橋和吳鐵橋。這些目前沒有被納入文物保護單位目錄,屬于“預備目錄”的古橋,比起沒有被納入目錄的古橋多了一份法律保障,特別有利于這些“目錄外”古橋保護的是:由于“歷史建筑本體及保護范圍劃定規劃”是由規劃部門制定和公布,有利于古橋和周圍環境的前置規劃,一定程度上協調了城市發展和古建筑的和諧共存。

圖6 古橋保護模式之六——焦溪古橋群模式(圖片來之常州規劃網)

圖7 古橋保護模式之七——上店橋模式
目前,上店一帶正在規劃和實施“南田文化城”,主打“文化、休閑、居住”等功能,充分利用和放大片區內的惲南田、胥城寺、上店老街、上店橋(圖6)等豐富的歷史人文資源,進行保護性開發,建設南田文博園、宗博園、胥城遺址公園、武進畫院、非物質文化遺產展覽中心等;并充分利用片區內的興隆河、永安河等水系資源,沿興隆河兩側建設商業古街區、古典園林會所等,這樣上店古橋和與之相關的水系、其他古建筑的歷史風貌都有可能得以延續。
8 .古橋大觀園模式
古橋遺產等不可移動文物的特性是比較分散,不可能所有古橋遺產都能像焦溪古橋群一樣做到原生態整體性開發。許多古橋遺產的周圍環境已面目全非,獨木不成林,可以考慮進行集中移建。這種情況下,可以考慮古橋大觀園模式。這種方式目前在常州還只是初步實施,但可以作為一種常州不可移動遺產保護的未來主流模式。古橋大觀園模式可分為三種:一是整橋移建,就是把農村中廢棄的石橋集中遷建于園中,布置沿河塘路之上,河汊之口,或圓或方,形態各異。二是用古橋構件造“新橋”,利用廢棄古石橋的構件, 用傳統石作工藝拼裝組合。三是眾多古橋構件展示,展示古橋代表性殘存石構件。
我國橋梁專家唐寰澄曾對古橋大觀園有過如此評價:“古越多名橋,然時代進步,不變有礙于與時俱進,今遷而存之,既保護文物,又類聚群分,以清脈絡。子孫永寶,豈不快哉。”古橋大觀園保護模式為各地方古橋等不可移動文化遺產指明了一項有效的措施,這樣就既保護了古橋,又為景點添色。

圖8 古橋保護模式之八——古橋大觀園模式
三、古橋文化遺產保護的發展趨勢
2005年12月發布的《國務院關于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是我國第一次以“文化遺產”為主題詞的政府文件,表明開始了從“文物保護”走向“文化遺產保護”的歷史性轉型①。通過對常州古橋等不可移動文化遺產保護的研究,可以發現古橋文化遺產保護與其它種類的文化遺產一樣,其內涵逐漸深化、范圍也不斷擴大,呈現出若干“從文物保護”走向“文化遺產保護”的新的發展趨勢。
1.古橋文化遺產保護內涵的深化
以往“文物保護”主要由文物保護部門和專業人員進行,而“文化遺產保護”強調全民的參與。橋梁文化的創造、發展和傳承是一個歷史過程。每一代人都既有分享古橋文化遺產的權利,又要承擔保護古橋文化遺產并傳于后世的責任。人類文明就是在世代的文化創造和積累中不斷發展和進步,每一代人都應當為此做出應有的貢獻。與眾多文化遺產一樣,古橋遺產的保護需要注重公眾參與性。古橋文化遺產保護不應僅僅局限于文物保護管理部門和專業人員的范圍,對古橋文化遺產研究、保護和傳播需要不同學科和社會公眾的廣泛參與。因此,必須尊重和維護。常州古橋遺產正是通過“龍城文物保護志愿者”等形式,讓更多的市民積極投入古橋等文化遺產保護之中,使文化遺產保護形成強大的社會意志②。正是通過民間古橋遺產保護組織,拉近了民眾與文化遺產之間的關聯和情感,在保障民眾的知情權、監督權、參與權和受益權的同時,也使古橋等文化遺產煥發出強盛的生命力。
2.古橋文化遺產保護外延的拓展
古橋文化遺產的保護范圍和保護空間不斷擴大。以往“文物保護”重視古橋單一文化要素的保護,而“文化遺產保護”重視由文化要素與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混合遺產”“文化景觀”的保護,從以往重視一座橋、一座塔、一組古建筑群等“點”“面”的文物保護,擴大到空間范圍更加廣闊的“大遺址群”“文化線路”的“大型文化遺產”和“線性文化遺產”的保護。文化遺產的產生和發展與所處自然環境密不可分。我國自古以來崇尚人與自然和諧共處,形成文化與自然遺產相互交融的重要特性。隨著大運河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常州古橋遺產可以作為大運河蘇南段水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納入到中國大運河世界文化遺產整體規劃保護中來。從幾座橋的“點”的保護擴大到世界文化遺產“大遺址群”和“運河文化線路”,成為常州文化遺產旅游的新名片。
3.古橋文化遺產的保護類型不斷擴充
以往“文物保護”重視“靜態遺產”的保護,如今“文化遺產保護”同時重視“動態遺產”和“活態遺產”的保護。古橋文化遺產與大多數文化遺產一樣,她不是靜止不變或死氣沉沉的,而是充滿生活氣息的、與歲月一同發展變化的。例如萬安橋等許多古橋,經過修繕后充滿活力,仍然承擔者日常生活中行人過河的交通功能,與百姓的生活融為一體。
4.古橋文化遺產的保護性質不斷延伸
以往“文物保護”重視大型城市古橋文化遺產的保護,如今“文化遺產保護”還要同時重視反映普通民眾生活方式的“民間文化遺產”式的鄉間古橋遺產的保護。長期以來,處于城市交通要道、體態大型、有地方志記載的古橋遺產才被列入保護范圍,而民間的、小型的、無任何記載的古橋文化遺產常常被認為是普通的、一般的、大眾的而不被重視,而它們卻反映了鄉間社會民眾最真實的生活狀況,具有鮮明的民間樸素色彩,是民間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城市文化的重要補充。近幾年,常州古橋文化遺產消失比較多的主要就是民間鄉村古橋,鄉村古橋遺產作為一種“鄉土建筑”,是文化多樣性的重要表現形式。隨著文化遺產保護的宣傳,越來越多的鄉民認識到不可移動文化遺產的重要性,把它們作為延續鄉土文化的一種符號。
5.古橋文化遺產的保護形態不斷擴展
以往“文物保護”重視“物質要素”的文化遺存保護,如今“文化遺產保護”還要同時重視由“物質要素”與“非物質要素”結合而形成的文化遺產保護。將保護內容由物質的、有形的,伸延到非物質的、無形的,顯示出對于文化遺產認識的進步。古橋遺產是典型的“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結合體,具有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雙重優勢。古橋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古橋營造技術、古橋藝術、古橋美學、古橋民俗等古橋非物質文化形態的遺產。有的古橋雖然已經拆除,但它的非物質文化仍然有可能存在。有關古橋的故事不僅沒有消亡,反而越加引起大家的記憶和懷念。
古橋文化遺產是生活在城市水泥森林中市民曾經的“水鄉記憶”,而文化遺產是共同生活人群的“集體記憶”。古橋文化遺產保護是所有文化遺產保護的一個縮影,文化遺產保護對象和范圍不斷擴大,其蘊藏之豐富、品種之繁多、門類之齊全,必將深刻影響城市文化的發展方向。在現實城市生活中,所有的人都生活在過去城市的“文化積累”之上,有了這樣的共識,就必然引發人們保護文化遺產的渴望與努力。城市在發展過程中應格外珍惜自己的文化遺產,只有保護和建設兩者并重,城市才能獲得真正意義上發展。
(作者聯系地址:嚴波,河海大學地方文化研究所;張勇,常州市文物保護管理中心)
注 釋
① 單霽翔:《關于城市文化建設與文化遺產保護的思考》, [J].中國文化遺產,2012,(3):58~68。
② 張勇:大運河邊的常州古橋保護行動 [J].中國文化遺產,2013,(6):60~67。
③ 常州市人大常委會教科文衛工作委員:《記憶龍城》,[M].北京,中國黨史出版社,2009。
④ 常州市建設委員會:《常州城市建設志》,[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1993。
⑤ 嚴波等:《中吳遺韻》,[M].江蘇:鳳凰出版社,2014。
⑥ 江蘇省武進縣縣志編纂委員會:《武進縣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⑦ 王稼句:《江南石橋》,[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