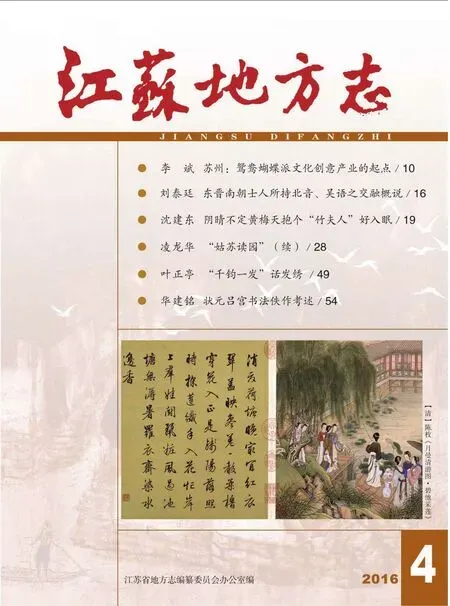“千鈞一發”話發繡----對話發繡藝術家周瑩華
◎葉正亭
“千鈞一發”話發繡----對話發繡藝術家周瑩華
◎葉正亭

周瑩華工作照
葉:周老師最近喬遷之喜,祝賀!
周:謝謝!去年9月,我的工作室從觀前街井巷搬至東環路風華苑。
葉:其實您是雙喜臨門,2016年2月,“明瑩刺繡工作室” 被評為江蘇省非物質文化遺產蘇繡(發繡)保護單位。
周:是的。這是對我這么多年從事發繡藝術創作的一種肯定,更是對蘇州發繡工作前輩們工作的肯定。我非常感恩。
葉:近三十年來,您對發繡藝術做出了不小的貢獻,有目共睹。
周:只能說做了一些工作,主要是將消失多年的發繡在蘇州重新煥發出青春了,并將其形成了蘇州發繡的特點。
蘇州發繡自新中國成立后蘇州刺繡研究所將其恢復后,由于材料、題材等問題又逐漸沒人做了。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我為了實現生父高伯瑜的心愿,開創了自己的發繡工作室,專門從事發繡技藝的傳承。2014年,蘇州市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手工藝與民間藝術之都”時,將蘇州發繡也列入其中申報。
葉:您是如何傳播發繡藝術的?
周:我通過各種展覽,讓大眾了解發繡藝術。2006年,應邀代表中國藝術家赴意大利參加“從長城到奧林匹亞藝術行都靈冬奧之旅——藝術巡展”; 2010年,應邀赴臺灣進行了為期一年的“千縷絲情-周瑩華發繡藝術交流展”(展覽地有臺北、高雄、臺南、嘉義、彰化等地);2011年,宜興大覺寺舉辦“周瑩華發繡藝術展”;2011年,應邀參加由中國傳統工藝研究會在上海舉辦的“中國發繡藝術珍藏品薈展”;2012年,在上海民族、民俗、民間博覽館舉辦“繡苑四絕”大型展覽;2012年12月,在上海徐匯區圖書館舉辦個人刺繡展。
葉:真是不少。有講座嗎?
周:我也開辦過一些講座來傳播。2013年,在上海徐匯區圖書館《發繡藝術欣賞》;2015年,在蘇州中國銀行舉辦了發繡欣賞講座。我還參加了蘇州市文廣新局組織的“走進非遺”活動,讓有興趣的市民走進我們工作室,親身體驗發繡的魅力;和西交利物浦大學、蘇州科技大學合作,組織學生參與發繡這一傳統技藝。
葉 :您的發繡作品得了不少獎項。
周:在全國省級以上的評獎中共獲得了16個金、銀獎項。發繡作品被蘇州工藝美術博物館、臺灣佛光緣美術館和一些私人博物館以及國際名人薩馬蘭奇等收藏。在全國確立了蘇州發繡的地位。
葉:發繡與絲繡有什么不同?發繡的特質是什么?
周:發繡和絲繡最主要的區別在于所使用材料的不同,發繡所使用的是人發,絲繡所使用的是真絲線,在刺繡的針法上基本相同,只是在繡制技巧上有所不同。

發繡《八十七神仙卷》(31×408cm)2008年獲第九屆“百花杯”中國工藝美術精品獎“銀獎”
民國時期的朱啟鈐在《女紅傳徵略》中記載:宋朝孝女周氏,用23年時間繡制成發繡《妙法蓮花經》。主要表現當時人們對佛教的虔誠信仰,將自己的頭發剪下來繡制成佛像、佛經等來朝夕膜拜。這就有了最早的發繡。
葉:中國發繡藝術起源于唐宋,那傳到蘇州呢?
周:發繡是中國工藝美術中一個古老而獨特的品種,歷史上都用來繡制佛像等藝術品,由于它具有“顏色古樸、立體感強、保存時間長”等特點,所以深受人們的喜愛。但由于制作發繡的技術要求高,以及取材的不易,繡制發繡的人很少,到清康熙以后,發繡就逐漸消亡了。清亡后,北洋政府官員朱啟鈐在清點接收宮廷內藏的刺繡品時,絲繡有158幅之多,發繡一幅也沒有見到。現存的幾幅古代發繡作品都在中外博物館收藏。由此可見,發繡的彌足珍貴。
蘇州發繡的歷史,始于明代,清初達到鼎盛時期。明代末年的徐燦,就是其中之一。徐燦,字湘萍,又字明霞,吳縣人。出生于詩書人家,自己也是個才女,詩、書、畫、繡樣樣精通,婚后曾居住在蘇州拙政園內,著有詞集《拙政園詩余》三卷,詩集《拙政園詩集》二卷。她所作的詞被譽為繼李清照之后的又一才華出眾的著名女詞人,同時,她又是一個優秀的刺繡家,晚年專心繡制佛像,她用頭發繡的觀音像,被觀看者認為“工凈有度”,不亞于明末刺繡大家邢慈靜的作品。
清代,蘇州有刺繡家錢蕙,她是吳縣人,能夠以發代繡,繡古佛,被當時人譽為:“繡大士像及宮妝美人,不減龍眠白描”。就是說錢惠所繡的人像,就好像北宋名畫家李公麟的白描畫一樣精彩。
名揚中國刺繡史的還有清代楊卯君和沈關關母女。楊卯君,字云和,清初吳江人,善繡佛像,能以發代線,號為“墨繡”。她的繡藝傳給女兒沈關關。沈關關,字宮音,所繡山水、人物皆有新意。
關于發繡,還有一段趣聞。清代有個才女叫吳慧娟,海虞(今江蘇常熟)人,《梵天盧叢錄》載:吳慧娟,工書畫,尤善刺繡。技藝上遠追盧媚娘,近抗露香園。其夫馮子倩逐酒色樂而忘歸,娟勸之不從,因截自己之發,于白綾之上繡詩二首寄之,子倩得詩大為感動,即歸。并擬文敘其始末,征題詠,成《繡發集》。發繡也成了規勸的浪子回頭手段。
葉:做發繡很難嗎?
周:相對比較難,一般需要具有較高的刺繡水平的人才能勝任。發繡以繡制佛像為主,不比絲繡,大多繡制日用品。所以繡制發繡作品,繡制者本身要有一定的藝術水平,正因為如此,能做好發繡的人很少,發繡的傳世作品更少。我講到的歷史上的幾位發繡大師,都是詩書畫的全才。發繡由于其材料的因素,自從它誕生以來,一直是作為少數刺繡名家的雅興之作,原因主要有幾個,一是作為原材料的頭發的取得不容易,二是發繡的制作難度較高,需要作者有較高的藝術修養,三是發繡的題材有局限,主要用來表現單線條的宗教題材,再就是當時對頭發的加工處理還跟不上要求。所以發繡作品數量很少,而能流傳到現在的更是少之又少。

左:發繡《水月觀音》(78×130cm)2009年獲第十屆“百花杯”中國工藝美術精品獎“銀獎”

中:發繡《羅漢圖》(70×144.5cm)

右:發繡《四仙拱壽圖》(118.5×83cm)
葉:說到蘇州發繡,一定會提到高伯喻。他是您父親嗎?
周:嚴格講,高伯喻是我生父。我出生后,就過繼給舅舅,所以姓了母姓。但我們是大家庭,生活在一起,我自小也受到了生父的教育、影響。高伯喻在蘇州刺繡研究所工作,1954年,他在整理研究蘇繡資料時,發現了“發繡”這一瀕臨失傳的傳統工藝,于是尋找老藝人歸隊,搶救、挖掘了這一傳統工藝,繡制出了新中國第一幅發繡《屈原像》。1959年,發繡《屈原像》在北京展出,受到了朱德委員長的題詞和嘉獎,但由于發繡受到材料、題材、技術等的限制,一直沒有形成規模。“文革”期間,高伯瑜下放到蘇北,應邀到了東臺工藝廠任職。之后,他又推薦了許多蘇繡藝人,如書畫家沈子丞、陳負蒼、王能父、刺繡藝人朱世英、陸素珍、裱畫師殷三元等人到東臺,開拓了中國畫和發繡兩項新業務,將原來以豬鬃、人發、馬鬃為原材料,生產板刷等日用品的“三毛廠”轉型成了以發繡、仿古中國畫為主的工藝廠。他將發繡技藝傳播到了東臺,并使發繡在東臺生根開花,逐漸在東臺形成了規模化生產。東臺工藝廠發繡車間從最初8人發展到100多人,最終發展到今天,成了東臺的一個特色支柱產業。高伯瑜也因此被譽為“發繡播種人”。
葉:您的發繡作品有什么樣的獨特之處?
周:我的發繡作品大都取材于傳統中國古畫,所以在藝術上特別強調詩、書、畫、印的統一。在繡制技藝上,注意用針,依據書畫筆法、要求,提按頓挫之筆意與濃淡枯濕之墨韻皆,得以完美地再現。通過刺繡手法,再現繪畫筆墨意趣,又基于材質和針法所形成的質感、色調、肌理之美,形成了一種筆墨丹青所不能達到的魅力,顯示了蘇州發繡藝術所獨具的“精致、雅潔、柔麗”的美學品格,并逐漸形成了自己的藝術風格。一件表現中國古畫的發繡作品,必須講究詩、書、畫、印的統一,每一個環節都不能忽視,我們看到很多刺繡作品在這些細節上不到位,給整幅作品留下了遺憾。
葉:做一個發繡藝術家,要對中國傳統書畫藝術有較深的理解?
周:是的。中國畫藝術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精髓,中國畫講究的是線條和筆墨,古人將線條分為十八描,也就是十八種勾畫線條的方法,來分別表現各種題材的需求,古人對筆墨講究墨分五色,在運墨的濃淡深淺中表達出自己的情感,最終實現的是一種意境,只有理解了這些,你才能在繡制過程中做到得心應手,所繡制出來的作品才能生動,才有生命力。
葉:聽說您對自己發繡作品的要求很高,近于苛刻了。
周:必須這樣。
曾經有一幅發繡長卷作品《八十七神仙卷》,作品在勾稿、刺繡上都很好,只是在最后裱畫時出了問題,影響到作品的外觀。為了嚴守質量要求,我決定重新繡制,直到自己滿意。有瑕疵的那件至今還躺在倉庫。
葉:您的作品被原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收藏?

發繡《維摩演教圖》(221×41cm)2007年獲第八屆“百花杯”中國工藝美術精品獎“金獎”

發繡《韓熙載夜宴圖》(335.5×28.7cm)2008年上海民族、民俗、民間、博覽會創新類“金獎”第九屆中國(深圳)文博會“銀獎”獎”

發繡《貨郎圖》(162×59cm)2011年獲第十二屆“百花杯”中國工藝美術精品獎“金獎”

發繡《紡車圖》(72×27cm)
周:2000年,我正式創辦了刺繡工作室,在十全街上有一個刺繡門店。有一天,來了一位臺灣客人,看了我的刺繡作品非常喜歡,收藏了我的一幅發繡佛像。在交談過程中,我了解到他是臺灣的國際奧委會委員吳經國先生,祖籍是蘇州,由此結下了一個緣。2005年,我參加了中國收藏文化博覽會并獲得了金獎,又被國家奧組委選上,參加“從長城到奧林匹亞都靈冬奧藝術巡展”,這次活動是由何振梁先生帶隊。在意大利都靈的展覽上,國際奧委會成員都來參觀,其中又見到了吳經國先生。在異國他鄉,又是在這樣的場合相見,大家都異常驚喜。何振梁、吳經國兩位都是國際奧委會的元老,他們同時向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介紹了我的發繡作品。薩馬蘭奇先生看得非常認真,尤其對根據宋代畫家夏珪的原畫繡制的發繡《風雨行舟圖》連連點頭。他收藏了這一幅發繡作品,向我贈送了他親筆簽名的書籍和紀念筆。
葉:您還為星云大師繡過發繡像?
周:2008年,在上海民博會上,來自臺灣佛光緣美術館的妙仲師傅看到了我的發繡作品,很感興趣,尤其是了解到發繡與佛教的淵源以后,熱情邀請我到臺灣各地佛光緣美術館舉辦為期一年的巡回展覽。2010年,我的發繡藝術展首先在臺灣高雄舉辦。在展館中,我看到了油畫家李子健先生創作的星云大師像,非常逼真,由此萌發了為大師繡一幅發繡的想法。回來后,我花了一年的時間,繡制了星云大師像,贈與大師,以表達我對星云大師的敬意。后來在宜興大覺寺,星云大師還特意邀我會面并合影留念。
葉:您作品得獎和被博物館收藏的具體情況。
周:發繡《維摩演教圖》被蘇州工藝美術博物館收藏;發繡《觀音像》被國際奧委會臺灣委員吳經國收藏;發繡《釋迦牟尼佛》《柳枝觀音》《星云大師》被臺灣佛光緣美術館收藏;發繡《水月觀音》被杭州南佛精舍藝術館收藏;發繡《姑蘇繁華圖》長卷被私人博物館收藏;發繡《貨郎圖》被私人博物館收藏。
葉:您目前的職稱與稱謂。
周:我的職稱是研究員級高級工藝美術師。
我獲得了中國刺繡藝術家、江蘇省工藝美術大師、蘇州市非物質文化遺產“蘇繡(發繡)”傳承人稱謂。工作室被授予“蘇州市非物質文化遺產‘蘇繡(發繡)’保護單位”、江蘇省非物質文化遺產“蘇繡(發繡)”保護單位等,這些都是社會對我的鼓勵和鞭策。
我還得到了社會方方面面對我的關愛,2006~2007年度,被蘇州市工藝美術行業協會授予“行業貢獻獎”;2007年,被蘇州市婦聯授予蘇州市“十行百星”優秀女性稱號等。
葉:作為“非遺”傳承人,您在傳承方面做了什么?
周:我的刺繡技藝來自蘇州老一輩刺繡家們,因此我有責任把發繡這一傳統技藝傳承下去,為此,近年來,我重點培養有興趣并有一定美術基礎的學生,這些學生中有中央美院的博士生,南藝、蘇州科技大學的學生,我免費教他們刺繡。我的女兒是大學老師,學的是漢語言文學,但我同樣讓她學習刺繡,每年暑寒假,她都悉心學繡。我也是希望她能多了解并傳承這門中國的傳統文化藝術。
葉:寫詩歌的有句行話,叫“功夫在詩外”,這同樣適合于發繡藝術家吧。

發繡《清明上河圖》(26×668cm)

發繡《赤壁圖》(137×55cm)2008年獲江蘇藝博杯工藝美術精品獎“銀獎”

發繡《盆菊幽賞圖》(87.5×23.5cm)

發繡《悟陽子養性圖》146×47.5cm)
周:刺繡本身只是一種技法,需要通過各種藝術形式才能展示刺繡的魅力。作為一個刺繡工作者,首先要提高自身的藝術素養,才能創作出有生命力的好作品。如繪畫、雕塑、書法、攝影、美學、歷史,你都要有所了解,只有這樣,才能在選材、創作中做到游刃有余。比如我的發繡作品《水月觀音》,就是我在北京法海寺觀看明代壁畫后,根據其中的一幅壁畫改編創作的,將原畫彩色變成更適合發繡的黑白兩色,雖然少了一分雍容華麗的感覺,但多了一些素樸莊嚴的特點,更顯功力。由于運用了自然頭發顏色深淺的不同區分,使整幅發繡的線條層次分明,線條非常精細、勻稱、工整、挺拔。特別是將觀音的披紗表現得惟妙惟肖,披紗上的圖案是六菱花瓣,每一花瓣都有40多根線條組成,發繡運用絲絲白發將披紗“細如蛛絲,薄如蟬翼”的飄逸感表現得活靈活現,感覺水月觀音在輕紗下微微呼吸,更能體現水月觀音的恬靜、優雅之美,
葉:希望您成為德藝雙馨藝術家。在社會公益方面,您做了什么?
周:蘇州“正念養心社”是由100多位女企業家參加的非盈利公益組織,我在社內擔任顧問一職,正念養心社的宗旨是“以公益慈善,扶貧幫困”為主導,帶領社團成員關愛弱勢婦女,扶助弱勢兒童,開展尊老、助老等活動,提高社團成員的公益理念,以“正心、正念、正行”推動城市精神文明建設。每月我們都有定向慈善幫困活動,如慰問養老院我們定點是優康養老院。我個人還通過青海“格桑花教育救助會”定向助學了兩位學生。
葉:您對發繡藝術有什么樣的展望。
周:中國的發繡藝術源遠流長,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了。清中期以前,發繡無論在題材還是在針法上都基本上沒有什么大的變化。新中國成立以后,發繡一直還停留在表現佛像人物和中國傳統繪畫上,題材上有較大的局限。我想,發繡藝術必須在題材上有所創新,而這種突破與創新,帶來的首先是表現手法的跟不上。因此,要在題材上有所創新,首先要解決的是表現手法的創新,要更加豐富多彩,才能滿足發繡藝術題材創新,在這方面,我也一直在思考和嘗試。
葉:期待您有更新、更美的發繡作品問世。
周:謝謝。
(作者聯系地址:蘇州市政協文史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