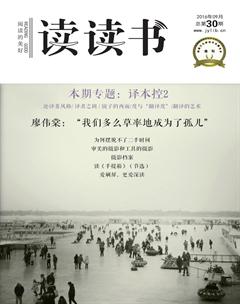譯者之困
思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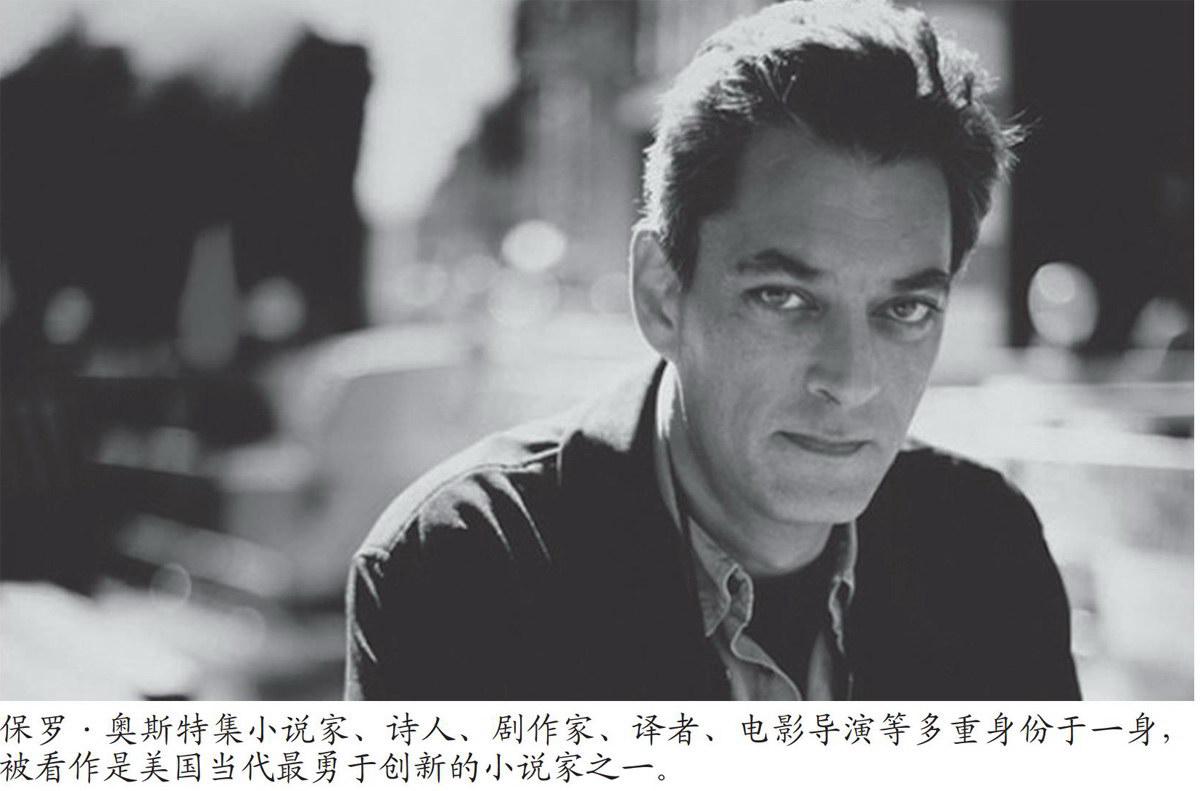

“我們太輕看了翻譯,把翻譯看成了一種技術(shù)工種,一種二手的創(chuàng)作,但是翻譯有沒(méi)有可能是一種原創(chuàng)?一種在每個(gè)時(shí)代都需要的、借助工具性的理解,讓傳統(tǒng)和經(jīng)典重新煥發(fā)生命力,符合我們時(shí)代精神的一種原創(chuàng)?”美國(guó)小說(shuō)家保羅·奧斯特的處女作《孤獨(dú)及其所創(chuàng)造的》中,塑造了一位孤獨(dú)的翻譯家。他讀法語(yǔ)書(shū),翻譯成英語(yǔ),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一個(gè)詞變成了另一個(gè)詞,一樣?xùn)|西變成了另一樣?xùn)|西。以這種方式,他告訴自己,它與記憶以同樣的方式運(yùn)作。他想象在身體里有一座巨大的巴別塔。有一段文本,它把自己翻譯成無(wú)數(shù)種語(yǔ)言。迅速思考時(shí),句子從他腦中涌出,每個(gè)詞來(lái)自一種不同的語(yǔ)言,無(wú)數(shù)語(yǔ)言同時(shí)在他心里大聲呼喊,喧鬧聲回蕩在迷宮似的房間、走廊、樓梯上,有數(shù)百個(gè)故事那樣高。他重復(fù)。在記憶的空間,所有事物既是它自己又是其他事物。”
奧斯特在成名之前,在法國(guó)流浪,以翻譯和撰文為生,書(shū)中的這位孤獨(dú)的翻譯家大概就是他自己青年時(shí)期的寫(xiě)照。但是這段話(huà)涉及到翻譯的很多基本問(wèn)題,比如翻譯是從一種語(yǔ)言到另一種語(yǔ)言,是一種解釋性的移植。需要譯者不單單擅長(zhǎng)雙語(yǔ),而且最重要的是能夠在雙語(yǔ)所代表的兩種相異的文化語(yǔ)境中穿梭自如。翻譯是一種記憶的回響,一種文化的影響力,一種在他者的文化之鏡中尋找自我意識(shí)的探尋之旅。
翻譯是一項(xiàng)出力不討好的工作,很少人愿意以翻譯為生,除了生計(jì)考慮,翻譯費(fèi)用低廉,無(wú)法維持生存,更多的時(shí)候,我們視翻譯為一種二手的創(chuàng)作。翻譯好的是原著的功勞,翻譯差的是譯者背負(fù)罵名,總之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其實(shí)說(shuō)起來(lái)“翻譯家”這個(gè)稱(chēng)呼都透著一股子二手科學(xué)家的范兒,借用喬治-斯坦納的名言,我們可以說(shuō)每位翻譯家身上都有一個(gè)作家夢(mèng)。很多年輕的譯者投身翻譯這項(xiàng)孤獨(dú)的事業(yè),是為了以后的寫(xiě)作積累經(jīng)驗(yàn)。像上文中的奧斯特,對(duì)法國(guó)文學(xué)充滿(mǎn)了景仰,才會(huì)去巴黎漫游,寓居在巴掌大的小旅館中,每個(gè)孤獨(dú)的夜晚就以翻譯為業(yè)。這種理想主義情結(jié)是寄托一個(gè)寫(xiě)作者的作家夢(mèng),翻譯是其中關(guān)鍵的一環(huán)。
翻譯也只有在我們這個(gè)時(shí)代才凸顯出了一種尷尬。這種尷尬很大程度上是因?yàn)榘逊g變成一種職業(yè),而不是人文素養(yǎng)的基礎(chǔ)。當(dāng)翻譯日益被壟斷為一種行業(yè)資源,翻譯事業(yè)只能走向窄門(mén)化。翻譯者的素養(yǎng)一再成為批評(píng)的焦點(diǎn),好像我們只能停留在翻譯的基礎(chǔ)詞匯挑錯(cuò)程度上,無(wú)法做更深度的翻譯批評(píng)和對(duì)話(huà),翻譯的再創(chuàng)造變得高不可攀,這樣的時(shí)代,怎么會(huì)產(chǎn)生經(jīng)典的譯本,所有的爭(zhēng)論都只停留在細(xì)枝末節(jié)上,沒(méi)有人在意真正的翻譯是什么。很多年輕譯者的狂傲程度令人咋舌,翻譯幾本書(shū)就覺(jué)得前輩的翻譯一無(wú)是處,還有比這種翻譯界內(nèi)部的齷齪更令人齒冷的嗎?
前不久,我在微博上發(fā)了一條關(guān)于翻譯理論家喬治·斯坦納的一句翻譯的理論,翻譯永遠(yuǎn)是最基本的了解和呈現(xiàn),翻譯者也總被稱(chēng)為詮釋者,他說(shuō),好的翻譯是“一面鏡子看進(jìn)另一面鏡子里,交換了彼此的光”。這句話(huà)被朋友批評(píng)說(shuō)斯坦納根本不懂翻譯。剝除了上下文的語(yǔ)境,這句話(huà)確實(shí)有些玄妙,但是想來(lái)又覺(jué)得觸及到了翻譯更深層的東西。我們了解到的翻譯只是最基本的從一種語(yǔ)言到另一種語(yǔ)言,從一個(gè)詞匯尋找到另外對(duì)應(yīng)的詞匯而已,但是從更層次說(shuō),任何翻譯都是交流,都是經(jīng)驗(yàn)的積累,都是文化的傳遞,都是文明的塑造,我們的歷史借助于翻譯才得以甄別,我們的古典文學(xué)借助于翻譯才能現(xiàn)代化,我們對(duì)他者的文學(xué)的認(rèn)知只有借助翻譯才能做同情的理解,甚至很多古老的文化符號(hào)只有借助于翻譯才能產(chǎn)生文化的關(guān)聯(lián)。從這個(gè)意義上來(lái)說(shuō),我們的文化即是翻譯。我們太輕看了翻譯,把翻譯看成了一種技術(shù)工種,一種二手的創(chuàng)作,但是翻譯有沒(méi)有可能是一種原創(chuàng)?一種在每個(gè)時(shí)代都需要的、借助工具性的理解,讓傳統(tǒng)和經(jīng)典重新煥發(fā)生命力,符合我們時(shí)代精神的一種原創(chuàng)?
正如斯坦納在他的翻譯理論中所言:“文學(xué)藝術(shù)的存在,一個(gè)社會(huì)歷史的真實(shí)感,有賴(lài)于沒(méi)完沒(méi)了的同一語(yǔ)言?xún)?nèi)部的翻譯,盡管我們往往不能意識(shí)到我們?cè)谶M(jìn)行翻譯。我們之所以能保持我們的文明,就因?yàn)槲覀儗W(xué)會(huì)了翻譯過(guò)去的東西。這樣說(shuō)并非言過(guò)其實(shí)。”
既然提及到斯坦納,不妨對(duì)這位文學(xué)批評(píng)家和翻譯理論家多說(shuō)兩句。斯坦納的父母都成長(zhǎng)于十九世紀(jì)末的維也納,在納粹主義興起之際,父母見(jiàn)微知著,轉(zhuǎn)移到法國(guó),1940年,同樣預(yù)感到了危機(jī),一家人再次離開(kāi)歐洲,前往美國(guó),才得以逃過(guò)法國(guó)淪陷的危機(jī)。斯坦納回憶他早年的家庭生活,說(shuō)他母親終生保持著一種維也納的作風(fēng),常常在講話(huà)時(shí)以某種語(yǔ)言開(kāi)頭,用另一種語(yǔ)言結(jié)束,語(yǔ)言在屋子里流動(dòng),飯廳和客廳都是英語(yǔ)、法語(yǔ)、德語(yǔ)。他經(jīng)常在育兒室聽(tīng)到一句德語(yǔ),下一句在廚房聽(tīng)到的可能就是法語(yǔ)。在這種多語(yǔ)文化的環(huán)境中長(zhǎng)大,所謂母語(yǔ)都變得多余。斯坦納說(shuō),這三種語(yǔ)言對(duì)他來(lái)說(shuō)平等存在,而且彼此保持基本距離,在他使用某種語(yǔ)言的時(shí)候,另外一種語(yǔ)言會(huì)突然蹦出來(lái),就如同說(shuō)母語(yǔ)一樣自然。
茨威格在他的自傳性寫(xiě)作《昨日的世界》中,也提到了那個(gè)太平盛世,人們是如何和平相處,1914年以前,世界是屬于所有人的,人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在哪里待多久就待多久,不需要許可證和簽證,也沒(méi)有刁難,那些國(guó)境線(xiàn)不過(guò)是一些象征性的邊界。隨著一戰(zhàn)、二戰(zhàn),這一切都變了:“后來(lái)我才感覺(jué)到,人的尊嚴(yán)在我們這個(gè)世紀(jì)失掉了多少。我們年輕時(shí)曾虔誠(chéng)地夢(mèng)想過(guò)我們這個(gè)世紀(jì)會(huì)成為自由的世紀(jì),成為世界主義即將到來(lái)的時(shí)代。”隨著尊嚴(yán)喪失掉的還有很多東西,比如各種語(yǔ)言的巴別塔建立了起來(lái),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文化之間的差異日益凸顯,多種語(yǔ)言共存不再是人們生存的常態(tài),語(yǔ)言的意識(shí)形態(tài)屬性變得日益嚴(yán)重。其實(shí)我們都有這樣的經(jīng)驗(yàn),推廣的普通話(huà)讓各地的方言生存的空間縮小到了博物館的陳列位置。像斯坦納這樣的從小三語(yǔ)共存的生存環(huán)境不復(fù)存在。要知道一種語(yǔ)言還是一種文化,擅長(zhǎng)多種語(yǔ)言的人,自然在多元文化的語(yǔ)境中穿梭自如,所謂翻譯就像他說(shuō)話(huà)一樣容易。但是對(duì)我們現(xiàn)在被限制在一種語(yǔ)言和文化環(huán)境中的人而言,翻譯就變成了利用各種工具性的詞典和谷歌,加上各種猜疑性的推測(cè)才能完成的行為。個(gè)中差距,不言而喻。
俄國(guó)詩(shī)人奧西普·曼德?tīng)柺┧罚袼哪切┩?lèi)帕斯捷爾納克、茨維塔耶娃、阿赫瑪托娃一樣,他們都是成長(zhǎng)在一個(gè)多語(yǔ)的文化環(huán)境中,當(dāng)他們被剝奪了寫(xiě)作和發(fā)表詩(shī)歌機(jī)會(huì),就會(huì)借助于翻譯完成一種變形的寫(xiě)作。他們?nèi)绱藢?zhuān)注這項(xiàng)工作,以至于早已將翻譯看作是文學(xué)中最艱難和責(zé)任最重大的工作。在曼德?tīng)柺┧房磥?lái),翻譯基本上是在外來(lái)材料的基礎(chǔ)上創(chuàng)造一個(gè)獨(dú)立的語(yǔ)言系統(tǒng)。所以翻譯,“需要巨大的努力、專(zhuān)注、意志,豐富的創(chuàng)造性、知識(shí)的新鮮性、哲學(xué)的感性、龐大的詞匯鍵盤(pán),以及細(xì)心聆聽(tīng)的節(jié)奏、把握一個(gè)片語(yǔ)的畫(huà)面并把它傳達(dá)出來(lái)的能力;更有甚者,這一切都必須在最嚴(yán)格的自我控制之中完成。否則翻譯只能算是篡改。翻譯的過(guò)程需要龐大的神經(jīng)能源的支出。這種工作耗盡和抽干大腦,甚于其他種類(lèi)的創(chuàng)造性工作”。
對(duì)于他們來(lái)說(shuō),翻譯已經(jīng)不僅是維持生活的手段,還是一種自我拯救,讓他們暫時(shí)忘卻處境的險(xiǎn)惡,這種處境正以無(wú)法遏止的力量把詩(shī)人變成無(wú)足輕重的一粒塵埃。換句話(huà)說(shuō),他們正在用翻譯對(duì)抗一個(gè)帝國(gu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