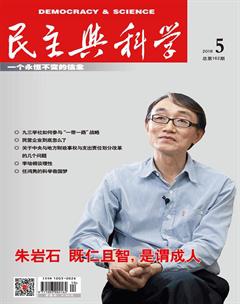追問“什么是科學”的當下意義
吳國盛
就科學而言,中國傳統的優長之處在技術、在博物學(自然志),不在數理科學。如果一味出于面子需要,挖空心思去尋找數理科學方面的世界第一,那是自欺欺人,也不能真正找到傳統文化與當代世界的交匯點。
什么是科學?“科學”是日本學者西周時懋1874年用來翻譯法文science時生造的一個詞。隨著西學東漸,這個詞連同相應的知識、觀念、制度一起傳入中國。在現代漢語語境下,它主要指自然科學。
科學是一個來自西方的泊來品,要理解科學就必須回到西方的語境中。在西方歷史上,科學有兩個前后相繼的形態,第一是希臘科學,第二是近代科學。希臘科學是無功利的、內在的、確定性的知識,源自希臘人對于自由人性的追求。這一科學形態的典型代表是演繹數學、形式邏輯和體系哲學。中國文化以仁愛精神作為人性的最高追求,因此從一開始就與科學精神錯失。
近代科學繼承了希臘科學的確定性理想,但添加了主體性、力量性訴求,成為今天具有顯著的實際用途,從而支配著人類社會發展、決定人類未來命運的主導力量。
近代科學的主要代表是數理實驗科學。它通過實驗取得科學知識的實際效果,通過數學取得科學知識的普遍有效性。數理實驗科學的模式最早在物理學中取得成功,以牛頓力學為標志,后來相繼在化學和生命科學中大展宏圖。從19世紀開始,物理學、化學、生物學陸續轉化為相應的技術、引發相關的產業革命,兌現了數理科學早期的求力理想。當然,大規模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也引發了環境危機、生態危機,這是人類當前面臨的一大難題。為了解決這些難題,有必要關注另一種已經被邊緣化的科學類型,即博物學。
博物學也是來自西方,是日本學者對Natural History一詞的漢譯。它是與希臘以來的自然哲學(Natural Philosophy)傳統相對應的另一種知識(科學)類型,即著眼于事物的具體性(而非抽象概念)、探討事物的直接經驗特征(而非一般本質)的科學。Natural History譯成“自然志”也許更加合適。在人類的諸種文明中,自然志(博物學)比數理科學更為常見。數理科學是希臘人的獨特創造,而每一個古代的文明都有自己的自然志。自然志親近自然、鑒賞自然,比數理實驗科學更少侵略性,可以用來緩解人與自然之間的緊張關系。
中國古代缺少數理實驗科學,但不缺少自然志。作為中國古代科技成就之大成的明末四大名著《農政全書》、《本草綱目》、《天工開物》和《徐霞客游記》均是自然志作品。以自然志(博物學)的眼光重修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史,可以獲得更多的教益和啟示。
追問和思考“什么是科學”的問題,在今天有三方面的重要意義。
首先,中國文化中既缺乏科學的基因,也缺乏科學發展壯大的土壤。中國人從19世紀后期開始接受西方的科學,實則是時代大變故造成的被動、被迫和無奈之舉。驅動我們發展科學的仍然是富國強兵、民族振興這樣的功利主義動機,對真理的追求、對未知的好奇、以求知為樂趣的自由心態遠遠沒有充分激活。中國人要在未來引領世界文明的發展方向、對人類做出較大的貢獻,就不能再滿足于單純功利主義的學習和運用科學,而是要習得居于源頭處的希臘科學精神,改造我們的文化土壤,使科學能夠在中華文化中生根發芽,否則,科學對于我們永遠只是達成其它目的的手段、工具,無法成為有獨立價值、自主發育、自主生長的文化母體。
其次,發源于西方的現代科學在給人類帶來巨大力量的同時,也給人類造成了新的生存危機,這種危機最早被西方人意識到,而且迅速動員了西方文化中的各種思想資源以化解危機;然而,單純作為手段和工具進入中國的科學,如同外來入侵的物種一樣,沒有天敵,沒有制約因素,釀成了嚴重的危機卻不能為國人所意識到,也無法動員自身文化中的資源以克制這種危機。盛行于20世紀中國社會的科學主義意識形態,以及當下愈演愈烈的環境危機,恰恰反映了中國人對現代科學的本質和來源缺乏基本的反思。就此而言,追問什么是科學,實際上具有極其緊迫的現實意義。
最后,正確評價中國傳統文化事關中華文化的未來走向和復興大業。如果我們不能清醒地意識到傳統文化的哪些方面具有現代意義,哪些方面需要發揚光大,我們就不能將傳統與現實進行有機整合。就科學而言,中國傳統的優長之處在技術、在博物學(自然志),不在數理科學。如果一味出于面子需要,挖空心思去尋找數理科學方面的世界第一,那是自欺欺人,也不能真正找到傳統文化與當代世界的交匯點。重寫中國古代科技史,不僅是科學技術史學科發展的需要,也是中國當代科學文化建設的需要。
(作者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