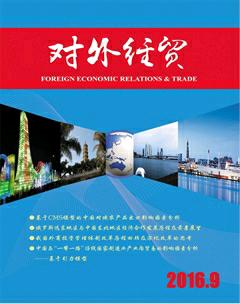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制造業產業內貿易的影響因素分析
摘 要:選取2009—2015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53個國家在SITC30版本中1位數分類標準下第5—8類制成品的貿易數據,采用格魯貝爾-勞埃德指數測算中國與沿線國家的制造業產業內貿易水平。基于改進的引力模型對影響雙邊制造業產業內貿易水平的因素進行分析,實證結果表明,在分析了GDP總量、人口規模、地理距離、貿易開放度、國家規模差異指數、國家接壤情況和區域經濟組織這些因素后,除人口規模和國家接壤情況外,其他變量均對產業內貿易水平有不同程度的影響。為深化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產業內貿易,提出以下對策建議:擴大經濟規模、降低運輸成本、減少貿易的限制性條件、采取制定差異化策略等。
關鍵詞:一帶一路;制造業;產業內貿易;格魯貝爾-勞埃德指數;引力模型
中圖分類號:F74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2095-3283(2016)09-0049-05
[作者簡介]蔣瓊瓊(1991-),女,漢族,河南駐馬店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國際貿易。
[基金項目]甘肅省社科規劃項目“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甘肅省對外貿易空間拓展的研究”(項目編號:14YB032)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一、問題的提出
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涉及了經濟、文化、社會等多個方面。2015年,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和商務部聯合發布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成為我國新時期全面擴大對外開放的綱領性文件。“一帶一路”發展戰略得到了沿線國家的大力支持和積極參與,在當前世界經濟低迷的背景下,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復蘇、推進國內供給側改革的重要引擎。
2013年以來,我國與沿線國家積極規劃“六大經濟走廊”建設,共同推動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產能合作。2015年我國同沿線國家的貿易總量接近1萬億美元,同比增長25%。其中對越南、泰國、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十幾個國家的出口額都超過了100億美元,對越南的出口額則高達660億美元。然而,沿線國家數目眾多,且經濟發展水平尤其是制造業發展狀況差異很大,因此同中國制造業的雙邊貿易額也不盡相同,既有與越南、印度等貿易額高達幾百億美元的國家,也有與馬其頓、阿塞拜疆貿易額只有幾億美元的國家。因此,只有充分了解中國與沿線各國制造業產業內貿易的發展現狀及影響因素,才能更好地提高其發展水平。
二、文獻綜述
國內已有關于產業內貿易的研究文獻大多以中國與其貿易伙伴國或某個區域為對象。周松蘭(2005)通過比較中日韓制造業的產業內貿易指數,強調了中國應把握時機,提高核心競爭力,加強中日韓的產業內合作。鄭昭陽和周昕(2007)采用GL指數測算了東亞經濟體1992—2005年的產業內貿易水平,表明以交通及通訊設備為主的產業內貿易成為了東亞地區主要的貿易方式,并認為產業分工的進一步深化是重要原因。沈國兵(2007)用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和產業內貿易指數衡量了中美雙邊產業內貿易的平衡狀況。陳虹和楊成玉(2015)采用CGE模型模擬了不同自由貿易情境,結果表明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成自由貿易區顯著提高了各國的經貿發展水平。蘇杭(2015)分析了“一帶一路”戰略實施過程中我國制造業海外轉移的現狀和面臨的問題。孟祺(2016)通過計算“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制造業競爭力,總結中國與沿線各國加強制造業產業合作對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馮宗憲等(2016)對中國和中亞五國1996—2013年分行業產業內貿易指數進行測算,得出工業品產業比初級品產業有著更高的產業內貿易水平,且經濟規模差異、人均GDP、FDI、貿易開放和距離等因素對不同行業的產業內貿易有不同影響的結論。然而,現有研究中還沒有針對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制造業產業內貿易水平的系統性分析。本文首先采用GL指數測算了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制造業產業內貿易水平,其次建立改進的引力模型,對雙邊制造業產業內貿易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回歸分析,最后提出通過擴大經濟規模、降低運輸成本、減少貿易的限制性條件和實施差異化的制造業合作策略等對策建議來提高我國與沿線國家的制造業產業內貿易水平。
三、產業內貿易水平的測度
(一)GL指數
產業內貿易水平用于衡量貿易國在同一產業內相互進出口同一類產品的程度,即產業內貿易程度。本文選用目前世界上評價產業內貿易水平時使用最廣泛的格魯貝爾-勞埃德指數(Grubel和Lioyd,1975),即G-L指數來計量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制造業產業內貿易水平。GL指數定義表達式為:
(二)研究維度及數據來源
“一帶一路”戰略因其開放性和包容性而涉及的國家非常廣泛,且惠及的國家還會不斷增加。由于數據缺失等問題,出于統計方便性的考慮,按照已有文獻慣常做法,剔除掉部分國家,選取沿線65個國家中的53個國家作為樣本。因為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往來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開始進入穩定發展時期,時間區間選為2009—2015年。中國對沿線國家的進口和出口數據(Xicjt、Micjt)來源于聯合國貿易商品統計數據庫(UN COMTRADE),為了實現數據的完整性和全面性,本文選取《國際貿易標準分類》中在SITC30版本1位數分類標準下第5~8類制成品的貿易數據。在這種分類標準下,所有商品被分為十大類,選用的第5—8類制成品的貿易數據。
由此,根據(2)式得出全部制成品的G-L指數的表達式:
(三)測度結果分析
基于上述方法及數據,本文測算出2009—2015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53個國家制造業的G-L指數,鑒于本文所選取的樣本國數目較大,限于篇幅,僅列出中國與部分國家制造業產業內貿易的G-L指數數據(見表1)。
由表1可知,從縱向看,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制造業的G-L指數即產業內貿易水平差別很大,從橫向看,中國與同一個國家在不同年份的G-L指數也不盡相同。總體而言,G-L指數小于05的國家數量遠遠大于G-L指數大于05的國家數量,說明中國與沿線國家整體的制造業產業內貿易水平并不高,尚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間。具體來說,差異主要分為三種情況,一是中國與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和以色列四個國家制造業的G-L指數從2009—2015年始終保持在05以上,體現出很高的產業內貿易水平。二是中國與印度尼西亞、緬甸等十個國家制造業的G-L指數在2009—2015年在05左右有不同程度的波動。其中,中國與緬甸、越南、捷克、匈牙利、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這六個國家制造業的G-L指數呈現上升趨勢,表現為從產業間貿易向產業內貿易的轉變;而中國與印度尼西亞和巴林這兩個國家制造業G-L指數呈現下降趨勢,表現為從產業內貿易逐漸轉變為產業間貿易;中國與菲律賓和斯洛伐克這兩個國家制造業的G-L指數都是先降低又升高,表現為從產業內貿易轉為產業間貿易之后又轉為產業內貿易。三是除了上述14個國家之外,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其他國家制造業的G-L指數都處于05以下,即表現為產業間貿易。其中,中國與巴基斯坦、哈薩克斯坦、俄羅斯、波蘭、印度、阿曼和柬埔寨等國的G-L指數都比較接近05,從產業間貿易轉向產業內貿易的可能性很大。而中國與土耳其、約旦、科威特、阿富汗和文萊等接近一半數量國家制造業的G-L指數基本上處在0左右,接近于完全產業間貿易。
三、對產業內貿易水平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
(一)引力模型
引力模型最早由Tinbergen(1962)引入經濟分析中,是當前國際貿易流量實證研究中的基石。引力模型認為雙邊的貿易流量與其經濟規模成正比,而與它們之間的距離成反比,用公式可以表示為:
(二)指標構建及數據來源
其中,被解釋變量Tcjt表示在t時期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制造業產業內貿易值。解釋變量GDPct、GDPjt分別表示中國和沿線各國在t時期的名義國內生產總值,它們代表了中國和沿線各國的經濟規模總量,其數值越大,則雙邊貿易流量越大,制造業產業內貿易值則越大,因此預期其符號為正。解釋變量discj表示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地理距離,其數值越大,意味著運輸成本越高,則越不利于中國與沿線各國制造業產業內貿易發展,因此預期其符號為負。解釋變量Pc、Pj分別表示中國和沿線各國的人口總量,人口的增加一方面可以增加消費,提高貿易流量,另一方面也會深化產業內的國際經濟分工,從而減少制造業的產業內貿易流量,可見其符號具有不確定性。用sdicj表示中國與沿線各國的國家規模差異指數,其數值越大,兩國間制造業的產業內貿易流量越小,因此預期其符號為負。解釋變量openessjt表示j國在t時期的貿易開放度,計算公式為:EXjt+IMjtGDPjt,這里的EXjt、IMjt分別表示j國在t時期的出口和進口總額,貿易開放度越高,中國與j國的制造業產業內貿易水平可能越高,所以預期其符號為正。解釋變量Tigcj是表示中國與沿線各國邊界接壤情況的虛擬變量,這里采用的是海上接壤數據,有共同的邊界取值1,沒有共同邊界取值0,距離越近的國家間運輸成本越低,那么制造業產業內貿易水平可能越高,因此預期其符號為正。解釋變量reocj表示中國與沿線各國是否在相同區域經濟組織的變量,這里選取的區域經濟組織為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和上海合作組織,處在相同區域經濟組織取值1,不在同一經濟組織取值0,在相同區域經濟組織的國家間進行貿易的限制條件較少,制造業產業內貿易量可能會較大,預期其符號為正。μ為隨機誤差項,代表未觀察到的其他其他影響因素
其中,各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單位:美元)和人口(P,單位:人)數據來自世界銀行的“世界發展指標”數據庫,中國到“一帶一路”沿線各國即j國的距離(dis,單位:千米)數據來自網站“wwwmacalesteredu”,中國與j國的邊界接壤數據來自CEPII數據庫,j國在t時期的出口和進口總額(EXjt、IMjt)來自聯合國貿易商品統計數據庫(UN COMTRADE),區域經濟一體化數據來自WTO官方網站。
(三)回歸結果分析
本文采用2009—2015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53個國家制造業產業內貿易的面板數據,共371個樣本,首先對使用混合回歸還是固定效應模型進行檢驗,結果顯示個體虛擬變量的顯著性水平很低,因此可以使用混合最小二乘回歸,并用穩健標準誤予以修正,回歸結果見表2。
從一次回歸結果可以看出,除了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c)、中國的人口(Pc)和兩國的邊界接壤變量(Tig)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外,其他變量都達到了1%的顯著性水平,各變量回歸系數的符號也與預期一致。而且模型的擬合優度高達915%,說明模型整體擬合較好。進一步采用“向后法”對解釋變量進行篩選。在先后剔除變量lnpc和tig進行回歸后,得到表2中的二次回歸結果,所有變量都達到了1%的顯著性水平,且模型整體的擬合優度仍然高達9148%,因此本文采用二次回歸分析的結果。從而可得回歸方程(公式7):
其中,GDPc、GDPj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4423、10275,說明中國和沿線各國的經濟規模總量與制造業的產業內貿易量正相關,且GDPj的促進作用更大。Pj的回歸系數為01121,說明沿線國家的人口所產生的對制成品的消費需求量大于產業內國際分工深化所減少的產業內貿易量,但是Pj的促進作用相對較低,可忽略不計。中國與沿線國家地理距離(discj)的回歸系數為-09173,說明地理距離(discj)產生的運輸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制造業產業內貿易的發展。國家規模差異指數(sdicj)的回歸系數為-28131,說明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國家規模差異(sdicj)越大,對發展其制造業產業內貿易的阻礙作用就越大。openessj和reocj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7232和05525,說明openessj對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制造業產業內的貿易規模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且處在同一個區域經濟組織(reocj)中也會促進中國與該區域國家間制造業產業內貿易的發展,都表明開展貿易的限制性條件越少,制造業產業內貿易量越大。
四、結論與對策建議
自2013年 “一帶一路”戰略提出后,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尤其是制造業產業內貿易得到了快速發展。選取2009—2015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SITC30版本中1位數分類標準下第5—8類制成品的貿易數據,對G-L指數的測算結果表明我國與沿線國家的產業內貿易還處于相對較低的水平,其經濟發展水平和消費結構等與發達國家還有很大差距。本文進一步利用改進的引力模型對影響雙邊制造業產業內貿易水平的因素進行分析。表明,GDPc、GDPj、Pj、discj、sdicj、openessj和reocj對中國與沿線國家制造業的產業內貿易水平有不同程度的影響。有鑒于此,為加快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產業內貿易提出以下對策建議。
(一)擴大經濟規模。第一,加快推動“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提高我國與沿線國家的宏觀經濟水平、降低國家間的規模差異,吸引更多國家積極參與,以促進貿易規模尤其是產業內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第二,加大對我國制造業尤其是優勢制造業的扶植力度,從而提高我國對國際市場的供給能力。擴大對沿線國家高新技術產業制成品的進口,支持其優勢產業的發展。第三,進一步建立我國與沿線各國的經濟協調機制,為雙邊市場規模的擴大提供有力支持,從而推動我國與沿線國家的貿易格局不斷由產業間貿易向產業內貿易轉變。
(二)降低運輸成本。我國應該充分利用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地理位置優勢,進一步構建現代化的信息流、物流和人流交往平臺。要發揮好亞投行和絲路基金的作用,加大對沿線國家尤其是中亞、西亞等落后地區的基礎設施投資力度,加快與沿線國家包括鐵路、港口、航空在內的“設施聯通”建設。從而通過降低運輸成本,深度挖掘我國與沿線國家制造業產業內貿易的發展潛力,擴大制造業產業內貿易規模。
(三)減少貿易的限制性條件。包括充分發揮區域經濟組織的作用和創造條件,促進沿線國家的貿易開放度。本文選取的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和上海合作組織對中國與沿線國家制造業產業內貿易量的促進作用達到了55%,因此既要繼續深化區域經濟一體化合作,打造好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升級版,不斷擴大規模經濟,促進制造業產業內貿易。要認真總結已有區域經濟組織的成功經驗,積極推動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更多國家達成雙邊或多邊的區域經濟合作協議,從而減少開展制造業產業內貿易的限制性條件。密切關注沿線各國的貿易開放政策,把握有利時機,努力創造條件,著重擴大工業制成品的市場準入和貿易自由化,促進沿線國家提高貿易開放度。建設好“一帶一路”這一新型的區域合作機制,為沿線的77個境外合作區提供正確的指導和幫助,可有效促進區域內成員國的制造業產業內貿易發展。
(四)采取制定差異化策略。通過G-L指數測算出的我國與沿線國家制造業的產業內貿易水平存在很大的差異,既有與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水平較高的產業內貿易,也有與阿富汗、文萊等開展完全產業間貿易。因此,中國在努力擴大與沿線國家制造業產業內貿易規模的同時,應根據不同的產業內發展水平及沿線各國不同的資源稟賦和比較優勢,實施差異化的制造業合作策略,有效落實《中國制造2015》戰略。如應努力擴大對印度、孟加拉國等國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投資,而在馬來西亞、泰國等具有一定技術密集型制造業的國家完成我國部分科技含量較高產品的加工,還應充分利用諸如剛果、科威特等資源密集型國家豐富的資源,與我國產業形成優勢互補。
[參考文獻]
[1]陳虹,楊成玉.“一帶一路”國家戰略的國際經濟效應研究——基于CGE模型的分析[J].國際貿易問題,2015,10:4-13.
[2]馮宗憲,王石,王華.中國和中亞五國產業內貿易指數及影響因素研究[J]. 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6, 01:8-16.
[3]孟祺.基于“一帶一路”的制造業全球價值鏈構建[J].財經科學,2016,02:72-81.
[4]盛斌,廖明中.中國的貿易流量與出口潛力:引力模型的研究[J]. 世界經濟,2004,02:3-12.
[5]蘇杭.“一帶一路”戰略下我國制造業海外轉移問題研究[J]. 國際貿易,2015(3):18-21.
[6]沈國兵.顯性比較優勢、產業內貿易與中美雙邊貿易平衡[J]. 管理世界,2007(2):5-16+171.
[7]蘇振東,周瑋慶. 出口貿易結構變遷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非對稱影響效應研究——基于產品技術附加值分布的貿易結構分析法和動態面板數據模型的經驗研究[J]. 世界經濟研究,2009(5):42-47,88.
[8]周松蘭.從產業內貿易指數看中韓日制造業分工變化[J].南京財經大學學報,2005,(1):8-11.
[9]鄭昭陽,周昕.東亞地區產業內貿易的發展狀況——G-L指數及發展原因分析[J].國際貿易問題,2007(9):39-44.
(責任編輯:董博雯 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