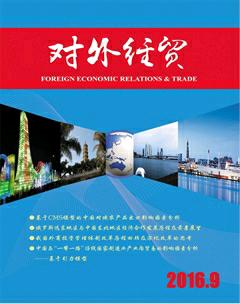西道堂多元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及管理模式探析
摘 要:西道堂商業(yè)經(jīng)濟的發(fā)展壯大,帶動了農(nóng)、林、牧、副等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通過對西道堂經(jīng)濟產(chǎn)業(yè)發(fā)展歷史脈絡(luò)的梳理,探析多元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的形成過程和產(chǎn)業(yè)經(jīng)濟內(nèi)部的關(guān)聯(lián)性,多元的經(jīng)濟產(chǎn)業(yè)使西道堂有了較強的防風(fēng)險能力和盈利能力。其組織內(nèi)部合理的結(jié)構(gòu)設(shè)計和有效的管理模式,組織外部捕獲商機、開發(fā)市場、開拓商道,逐步擴大產(chǎn)業(yè)布局,使西道堂發(fā)展成為一個成功的社會經(jīng)濟團體。
關(guān)鍵詞:西道堂;多元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管理模式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
2095-3283(2016)09-00-02
[作者簡介]丁耀全(1976-),男,回族,甘肅臨潭人,講師,研究方向:民族文化與區(qū)域開發(fā)。
[基金項目]甘肅省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規(guī)劃項目“現(xiàn)代化境域中甘南藏區(qū)回族社區(qū)發(fā)展與變遷研究”(項目編號:YB100)的階段性成果。
清末,馬啟西受伊斯蘭教“烏瑪”思想和儒家大同思想的影響,在臨潭創(chuàng)建了西道堂,“西道堂既是一個宗教團體,又是一個在共同宗教信仰基礎(chǔ)上形成的多民族和睦相處、共同勞動、聯(lián)合經(jīng)營、平等消費的經(jīng)濟共同體”。[1]作為集宗教信仰與世俗生活于一體的西道堂,除宗教外,其經(jīng)濟成就引人注目。西道堂成功的經(jīng)濟活動源于有利區(qū)位、重商傳統(tǒng)和善于經(jīng)營。臨潭舊城是一座歷史悠久的繁華重鎮(zhèn),是通向川、青、藏等地區(qū)的咽喉。早在明代該地就設(shè)置“茶馬互市”,打開了與藏區(qū)貿(mào)易的通道,促進了民族貿(mào)易的發(fā)展,逐步形成臨潭回族“無人不商,無人不農(nóng)”的傳統(tǒng)。西道堂在“宗教至善之心的維系”下,通過統(tǒng)一管理,統(tǒng)一經(jīng)營,分工合作,努力勞動,使它的商、林、農(nóng)、牧、副各業(yè)全面發(fā)展,形成了多元一體的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成為近代成功的經(jīng)濟團體之一。
一、西道堂多元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的形成
商業(yè)的發(fā)展是西道堂經(jīng)濟發(fā)展中最早的產(chǎn)業(yè)之一,也是最成功的產(chǎn)業(yè)。臨潭地處青藏高原的東部邊緣地帶,通向藏區(qū)的條件優(yōu)越,形成了這里重農(nóng)重商的民間傳統(tǒng),這里自古邊境貿(mào)易、民族貿(mào)易發(fā)達(dá)。“據(jù)20世紀(jì)40年代的調(diào)查,當(dāng)時舊城的全部資本為64萬余元白洋,資本在2000元以上的有38家商號,20多個省市的商人來此經(jīng)商。”[2]西道堂自創(chuàng)立以來,受到當(dāng)?shù)刈诮瘫J貏萘蜕處偷膹娏曳磳ΓR啟西為了改變被動局面,號召教生將財產(chǎn)歸入道堂集體經(jīng)營,教生中有人將其財產(chǎn)全部或一半歸入道堂,并移居道堂集體生活,集體經(jīng)營各業(yè),逐漸形成了西道堂“烏瑪”大家庭。西道堂集體生活,集體經(jīng)濟逐漸形成,其集體經(jīng)濟由于管理有方和善于經(jīng)營,適應(yīng)社會發(fā)展的需要而得到快速發(fā)展,西道堂最初的產(chǎn)業(yè)是商業(yè)和農(nóng)業(yè)。
1901年,馬啟西開始號召教生捐獻(xiàn)家產(chǎn)集體經(jīng)商務(wù)農(nóng),開發(fā)洮河上游。設(shè)立“天興隆”總商號,“天興亨”分號,并以此為基礎(chǔ)陸續(xù)開設(shè)店鋪,發(fā)展壯大了坐商。同時,組建多支商隊往返于藏地,逐步形成行商。1910年,西道堂的商隊深入到洮河上游的藏族部落地區(qū)經(jīng)商,由于經(jīng)營得當(dāng),獲得了該地區(qū)藏族勢力的認(rèn)同,成為他們的生意伙伴。同時,在卓尼、迭布等地也打開了市場。后逐漸發(fā)展,范圍遍及甘南、川西和青海玉樹、果洛、海南等安多藏區(qū)。至1914年,形成了以天興隆為總商號,包括諸多天興隆分號和天興泰、天興亨等商號,行商和坐商并舉的大型商業(yè)團體。“由初期教民捐助的10萬兩銀子,累計發(fā)展到百萬家財”,[3]在當(dāng)?shù)匾呀?jīng)是首屈一指。1914年,“五一九”慘案后,西道堂教生全部被趕出家門,財產(chǎn)被洗劫一空。
1919年,馬明仁出任西道堂第三任教長,開始重整經(jīng)濟,“收拾于灰燼之余,萌芽于剝喪之后”。[4]在開始的困難時期,資金短缺,市場被毀,商道受阻,馬明仁派人到甘南、青海、四川的藏區(qū)投奔老朋友處求援。當(dāng)?shù)夭刈孱^人和活佛給予了大力支持,他們給予西道堂財物等支援,這些資金成為振興西道堂商業(yè)的重要資本來源,同時又重新打開了這些地區(qū)的市場,為以后的快速發(fā)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chǔ)。
1919—1929年的十年間,西道堂經(jīng)濟得到了快速發(fā)展,十年中發(fā)展擴建的主要坐商有:在舊城建立了天興隆、天興永、天興泰、永興隆等商號,在新城、太平寨建立了天興亨;在四川建立了阿壩天興隆、松潘天興隆、甘孜天興隆、阿壩天興德;在青海建立了同德天興德、玉樹天興隆、三哦羅天興隆;以及岷縣天興昌和蘭州天興隆等。十年中商隊逐漸擴大,至1929年,西道堂成為包括坐商、行商和聯(lián)合經(jīng)營在內(nèi)財力雄厚的大型經(jīng)濟團體。坐商包括“天興隆”、“天興泰”等諸多商號和15處坐商商鋪;行商主要活動在甘、川、青等安多藏區(qū),擁有固定商隊14對,馱牛1000余頭,馬匹200多匹,流動資金達(dá)10余萬元;同時,西道堂與外界合資經(jīng)營,如臨潭“萬鎰恒”,陜西“恒順昌”,山西“永德全”,北京“公記號”等,使市場觸角伸向內(nèi)地,貨源類型更加豐富、更具特色,可融資規(guī)模進一步擴大,資金總額已達(dá)200余萬銀元。
1929年地方變亂時,西道堂雖然再次遭到浩劫,但多數(shù)行商遠(yuǎn)在藏區(qū)營生,各商隊和開辦在外的商號的資本,基本上全部保存了下來,遷回臨潭后,對原有商業(yè)布局根據(jù)需要作了必要的鞏固與調(diào)整。大部分效益好的坐商商鋪保留了下來,還增加了張家口商棧一處,部分效益較差的商鋪關(guān)閉。行商在原有的基礎(chǔ)上擴建了7個商隊,同時,新建馱騾商隊,有騾30余頭,走四川成都、松潘和漢中貿(mào)易,擴充專往綏遠(yuǎn)、包頭等處經(jīng)商的駱駝60峰。總計行商20多隊,馱牛1700多頭,騎馬二三百匹,流動資金達(dá)20萬余元銀元。至此,西道堂商業(yè)的發(fā)展達(dá)到了鼎盛,坐商店鋪諸多,貨源充裕,品種豐富,行商“西至西藏、南至四川、北至青海北部、東至察哈爾等地,操這一帶的經(jīng)濟大權(quán)”。[5]
商業(yè)的繁榮帶來了豐厚資財,西道堂開始關(guān)注本地優(yōu)勢資源的開發(fā),林業(yè)和牧業(yè)在這樣的背景下得到了開發(fā)。林業(yè)的發(fā)展較早,也最具經(jīng)濟價值,從馬啟西于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購置倉科林,后馬明仁時期逐步發(fā)展并購置森林14處,西道堂單獨成林的林場15座,共計60多處,7萬余公頃。由于資金雄厚,購買的林場面積大,而且都是木材積蓄量好的原始森林,開發(fā)洮河沿岸豐富的森林資源,通過洮河水運銷往省內(nèi)各地木材缺乏地區(qū),收益頗豐。隨著市場規(guī)模和林場面積的擴大。西道堂于1937年在蘭州和馬步芳合辦西北木工廠,和馬步芳的合作保證了戰(zhàn)時市場的暢通和擴大。通過洮河水運到達(dá)黃河上游的蘭州,再從蘭州銷往全國各地,通過水運最遠(yuǎn)到達(dá)包頭。
牧業(yè)的發(fā)展有兩種模式,一種是以西道堂13個農(nóng)莊為依托,以各農(nóng)莊自有土地和草場,蓄養(yǎng)家畜,主要是一些牛、馬和羊等,以備各鄉(xiāng)莊平時出行、耕地、生活時自用和道堂舉行大型活動時統(tǒng)一調(diào)用;另一種是專門經(jīng)營的牧業(yè),草場是自購和在牧區(qū)租借的,西道堂主要有夏河買務(wù)、碌曲拉勒關(guān)和卓尼什路建立的三個大型牧場,主要的家畜有耕牛、奶牛、馬和羊等,三大牧場除了自有的牲畜外,當(dāng)商隊歸來時,大量的馱牛、馬等在此代牧,有一些草場較小的農(nóng)莊的牲口也代牧在大牧場。據(jù)現(xiàn)有資料統(tǒng)計,專門的牧場有三處,草場數(shù)千畝,有耕牛2000余頭,奶牛300余頭,馬400余匹,羊兩三千只,而各農(nóng)莊和商隊代養(yǎng)的牲畜未計,其余各林場也有規(guī)模可觀的家畜。
西道堂農(nóng)業(yè)和副業(yè)是由各農(nóng)莊教民集體生活的生活需要而發(fā)展起來的。西道堂各農(nóng)莊以農(nóng)業(yè)為主兼營牧業(yè)、副業(yè),生產(chǎn)設(shè)專人負(fù)責(zé)管理,組織農(nóng)莊教民集體勞動,各農(nóng)莊勞動力在農(nóng)忙時進行必要的調(diào)配。生產(chǎn)的糧食自給為主,余糧上交道堂集體核算調(diào)用。從1890年西道堂舊城農(nóng)莊成立,到1943年西道堂尕路田農(nóng)莊建立,“共計13個農(nóng)莊和4個農(nóng)業(yè)點,農(nóng)業(yè)人口700多人,耕地771182畝,近500頭耕畜”。[6]西道堂農(nóng)業(yè)從貧瘠的土地上發(fā)展起來,以集體經(jīng)營的方式發(fā)展壯大,年產(chǎn)200多萬斤的糧油收入。這在當(dāng)時是非常巨大的成就。解決了教民的吃飯問題,“因其幾任教長的精明經(jīng)營,居然能夠維持小康水平”[7]
副業(yè)的發(fā)展是為農(nóng)、林、商業(yè)的發(fā)展及教民的生活服務(wù)的,生產(chǎn)在保證自給的情況下,對外銷售,開創(chuàng)了多種經(jīng)營渠道。建水磨15盤,油房6座,磚瓦窯2處,此外,為保證西道堂運作的小廠房很多,如設(shè)醋房、粉房各1處,還有皮匠行、木工行和縫紉行等,其副業(yè)經(jīng)營的盈余也歸西道堂集體所有。
西道堂的經(jīng)濟以商業(yè)發(fā)展為主,進而帶動林、牧、農(nóng)、副各業(yè)的全方位發(fā)展。西道堂經(jīng)濟立足本地發(fā)展產(chǎn)業(yè),開發(fā)洮河上游,最終形成了多業(yè)并舉的多元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各產(chǎn)業(yè)之間聯(lián)系緊密,西道堂經(jīng)濟有“農(nóng)牧兼營、農(nóng)商并重的顯著特點”,[8]以解決生計的農(nóng)牧業(yè)為基礎(chǔ)經(jīng)濟,積極發(fā)展商、林、副等各業(yè)。商業(yè)是本區(qū)的優(yōu)勢,商業(yè)的發(fā)展促進了資本積累和人力資源的提升,推動了林業(yè)的發(fā)展,積累的雄厚資本反過來推動了農(nóng)業(yè)、牧業(yè)、副業(yè)的快速發(fā)展成熟。
這種具有互補性的經(jīng)營策略促進了西道堂多元化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的布局,形成了多業(yè)共生、同步發(fā)展的集體經(jīng)濟,這種多元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比單一的產(chǎn)業(yè)構(gòu)成優(yōu)勢明顯,提高了盈利能力和抗風(fēng)險能力。實際上,經(jīng)濟產(chǎn)業(yè)的多元化經(jīng)營策略,為西道堂經(jīng)濟的發(fā)展與騰飛奠定了重要基礎(chǔ),它使西道堂實現(xiàn)了跨產(chǎn)業(yè)經(jīng)營,在更廣闊的空間里獲得資源和市場,區(qū)域劣勢被最大限度地消減,積累起大量財富,為西道堂文化的發(fā)展打下堅實的物質(zhì)基礎(chǔ)。
二、西道堂經(jīng)濟產(chǎn)業(yè)的管理模式
(一)宗教觀念影響下的科層制
西道堂按照管理工作的需要,將教民劃分成三個層級,教主是最大管理者,但教主不管具體的管理工作,具體的管理工作設(shè)專門的管理機構(gòu),如管理道堂大家庭的大掌柜們,管理商業(yè)經(jīng)營的正副經(jīng)理,管理農(nóng)業(yè)的各農(nóng)莊負(fù)責(zé)人,這是西道堂管理的第二層級,廣大的教民處在第三層級,作為被管理者,他們自覺配合管理者完成任務(wù)。這樣使管理成為一個自上而下的完整運作系統(tǒng),管理工作特別規(guī)范。為保證西道堂這個復(fù)雜的組織整體運作,所有人員都被明確地劃歸到各個部門,這樣各管理者有明確的職責(zé)和權(quán)力,所有個人都有明確的上級領(lǐng)導(dǎo),西道堂建章立制,靠完整合理的制度管理人;強調(diào)制度面前人人平等,西道堂在經(jīng)濟上利用個人對道堂的貢獻(xiàn)和能力大小用人,利于調(diào)動人員積極性。西道堂在宗教至善思想影響下,人們的勞動積極性較高,教民之間的平等使信息的上通下達(dá)的渠道并沒有受到影響,科層制的缺點被消減到了最小。
(二)為公忘私的勞動精神
“管理工作的核心是對人的管理,因為只有人能夠左右其他要素的功效,管理工作只要把人的內(nèi)在潛能發(fā)掘出來,只要能夠使人們在工作中心情愉快、愿意干好并且能夠干好,企業(yè)管理的根本任務(wù)就算完成了。”[9]西道堂在伊斯蘭教的感召下,以“兩世吉慶”為紐帶,鼓勵每個個體在經(jīng)濟生活中努力勞動,“應(yīng)知藏兩世于一身,此生及后生”,“人當(dāng)以為永遠(yuǎn)繼續(xù)的永生而努力,固此生雖是過程,此生毫不虛度”。在具體的勞動中,由于西道堂教民受“大家庭”集體生活的影響,每個人在勞動時只要完成自己的工作,就被認(rèn)為是為集體做了貢獻(xiàn),這樣在精神層面和現(xiàn)實生活中,人們的日常勞動既是為了自己,同時也為了西道堂大家庭,有很強的成就感和歸屬感。每個人都以巨大的熱情投入到勞動中,幾乎沒有人偷懶或怠工,有很強自覺性和主動性,當(dāng)?shù)赜小暗捞迷豪餆o閑人”的美譽。可見人人為集體而努力勞動的場景,這一精神在商業(yè)上稱為“馬鞭子精神”,所謂的“馬鞭子精神”是指跟商隊外出做生意的人,當(dāng)他們滿載財物回到西道堂時,將一切財物,包括座騎全部交給道堂內(nèi)的管理者們。自己只留一根馬鞭,以便下回外出經(jīng)商時備用。這種一心為公、沒有私有的觀念,推動了西道堂各業(yè)興盛,為在近代紛亂的社會中西道堂經(jīng)濟大發(fā)展做出了巨大貢獻(xiàn)
(三)揚長避短,開發(fā)優(yōu)勢資源
自然資源稟賦決定著經(jīng)濟增長的物質(zhì)基礎(chǔ),臨潭所處的甘南草原是全國十大草原之一,飼草豐美,營養(yǎng)價值高,南部洮河流域是省內(nèi)森林資源富集區(qū)。西道堂牧業(yè)、林業(yè)的發(fā)展利用當(dāng)?shù)貎?yōu)勢資源,開發(fā)洮河上游,利用比較優(yōu)勢壯大產(chǎn)業(yè),使資源優(yōu)勢轉(zhuǎn)換成產(chǎn)業(yè)優(yōu)勢。優(yōu)勢資源影響初始產(chǎn)業(yè)布局和結(jié)構(gòu),西道堂因勢利導(dǎo),開發(fā)多元產(chǎn)業(yè),利用豐厚的商業(yè)利潤,立足當(dāng)?shù)亟?jīng)濟發(fā)展,關(guān)注當(dāng)?shù)刭Y源開發(fā),積極布局相關(guān)產(chǎn)業(yè),林業(yè)、牧業(yè)的發(fā)展是西道堂產(chǎn)業(yè)更廣,經(jīng)濟的橫向聯(lián)系性更強。由于立足當(dāng)?shù)兀浣?jīng)濟的安全性也得到了保證,豐裕的自然資源又提高了社會生產(chǎn)率,富集的牧業(yè)、林業(yè)資源,使西道堂林業(yè)、牧業(yè)利潤豐厚,得到了快速發(fā)展
(四)重視公共關(guān)系,統(tǒng)一開發(fā)市場
臨潭自古商業(yè)發(fā)達(dá),但市場主要在路途遙遠(yuǎn)、環(huán)境險峻的藏區(qū),以家庭或家族為單位的小商隊在路途中被劫事件時有發(fā)生。西道堂集體商隊和其他小的商隊相比較表現(xiàn)出極大的優(yōu)越性,在通往藏區(qū)貿(mào)易的安全性方面,西道堂巨大的商隊進過藏區(qū)時,由于商隊大、人數(shù)多,受到的騷擾較少,而且還有護商隊,出于安全考量,當(dāng)?shù)匾恍┬∩剃牫R栏接谖鞯捞蒙剃犕瑫r出入。西道堂通過交朋友、共同經(jīng)商等方式,與當(dāng)?shù)氐拇笮∈最I(lǐng)和寺院喇嘛勢力友好相處,使西道堂商隊在藏區(qū)受到相應(yīng)保護。“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西道堂教主馬明仁先生前往阿壩會晤了買家如土司花兒工成烈,為雙方貿(mào)易事業(yè)進行了友好協(xié)商”。 [10]西道堂在當(dāng)?shù)厥种匾暶褡尻P(guān)系,尤其重視和當(dāng)?shù)貪h、藏各民族的友好往來,儲備了較廣的人脈。“1945年,第十一世班禪在塔爾寺舉行冊封坐床儀式時,西道堂馬明仁教主也被邀請參加慶典”。[11]這種良好的民族交往,增加了友誼,暢通了商道,擴大了市場,推動了西道堂經(jīng)濟的發(fā)展。
(五)公推的選人機制提高了工作效能
西道堂作為集宗教信仰與世俗生活為一體的社會經(jīng)濟團體,其大家庭由于組織結(jié)構(gòu)復(fù)雜,人員龐雜,必須用運有力的管理措施、管理方法,獲得大家大家庭成員的支持,進而團結(jié)教民,推進西道堂事業(yè)的發(fā)展。西道堂從教長,到道堂各業(yè)的負(fù)責(zé)人,都由教民商議推舉,按照自己的能力大小,安排到合適的崗位上。在自己的崗位上作出最大的貢獻(xiàn)。在用人選人上不拘一格、不論資排輩,只按能力大小選人,如卓洛農(nóng)莊后期的農(nóng)業(yè)管理者付拉海曼,原為紅軍傷員,滯留臨潭后加入西道堂,由于吃苦能干,后被推舉為卓洛農(nóng)莊的管理者,商業(yè)的管理者們,自年輕時就跟隨商隊出入,經(jīng)歷練有才能者逐漸選用為管理者。這樣上到教長下到一般的管理者,都經(jīng)過嚴(yán)格的推舉才能成為西道堂的管理者,他們了解西道堂,且有實干精神,更熟悉自己的業(yè)務(wù),這樣保證了道堂事業(yè)的發(fā)展。
西道堂的產(chǎn)業(yè)發(fā)展和管理模式來自于實踐活動。西道堂因地制宜,從事多種產(chǎn)業(yè)開發(fā),通過商業(yè)的發(fā)展,加快資金周轉(zhuǎn),提高資金效率,積累起豐富的資本,從而保證和推動西道堂農(nóng)、林、牧、副等各業(yè)的發(fā)展,這是西道堂經(jīng)濟發(fā)展的脈絡(luò)。由于廣泛參與經(jīng)濟活動,人們開闊了眼界、增長了知識才干、了解了市場需求,為西道堂儲備了大量的經(jīng)營人才。西道堂在經(jīng)濟發(fā)展過程中,權(quán)衡利弊,量力而行,穩(wěn)步實施,它在歷史的風(fēng)潮中幾經(jīng)迭起,毀而復(fù)生。在宗教感召下形成的強大凝聚力和一心為公的思想是西道堂在困難中不斷前進的法寶。西道堂從創(chuàng)教初期集體經(jīng)濟的萌芽狀態(tài),到鼎盛之時經(jīng)濟文化的蒸蒸日上,無不傾注了每一位成員的甘苦和心血,其成功的經(jīng)濟管理模式在今天仍具有現(xiàn)實意義。
[參考文獻(xiàn)]
[1]哈吉·穆罕默德·奴倫丁·敏生光.星月之光[M].甘肅:甘肅民族出版社,2007:3.
[2]哈吉·穆罕默德·奴倫丁·敏生光.中國伊斯蘭教西道堂研究文集(第3卷)[M].甘肅:甘肅民族出版社,2010:150.
[3] [4] [6] [10] [11]青海民族學(xué)院民族研究所、西北民族學(xué)院民族研究所.西道堂史料輯(內(nèi)部資料)[M],1987:24,134,29,53,55.
[5]范長江.中國西北角[M].北京:新華出版社,1980:48.
[7]馬平.我國伊斯蘭教清真寺寺院經(jīng)濟初探[J].中央民族學(xué)院學(xué)報,1989(2).
[8]黨誠恩,陳寶生.甘肅民族貿(mào)易史稿[M].甘肅:甘肅人民出版社,1988:57.
[9]喻曉航,齊善鴻.管理學(xué)原理[M].天津:南開大學(xué)出版社,2004:199.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Xidaotang commercial economic growth,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deputy industry. Through carding of Xidaotang economic industry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ical context, the analysis of diverse economic structure formation process and industrial economy inside the relevance and the multi economic industry with strong anti risk ability and profit ability. Structural design of the organization within a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management mode, external captur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develop the market and develop business, and gradually expand the industrial layout, Xidaotang development become a successful social and economic groups.
Key words: Xidaotang;Multiple economic structure;Management model
(責(zé)任編輯:郭麗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