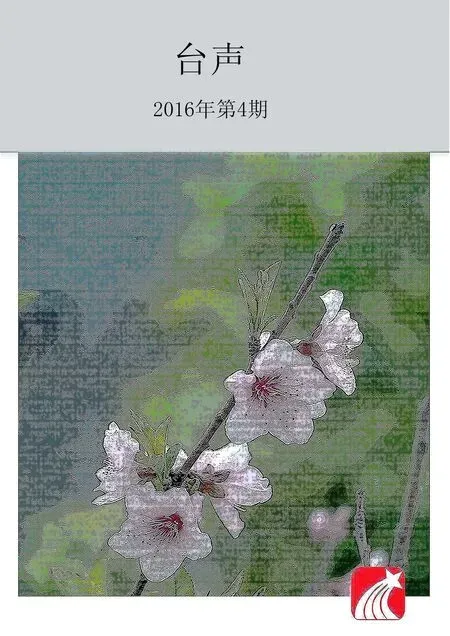教育部語言文字應(yīng)用管理司副司長、大陸代總召集人彭興頎
——將進(jìn)一步完善語言文字交流合作機(jī)制
教育部語言文字應(yīng)用管理司副司長、大陸代總召集人彭興頎
——將進(jìn)一步完善語言文字交流合作機(jī)制
彭興頎,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語言文字應(yīng)用管理司副司長、兩岸合編中華語文工具書大陸代總召集人。
開展10輪會(huì)談和多次分組會(huì)談
兩岸合作編纂中華語文工具書的成果、“中華語文知識庫”網(wǎng)站開通,不啻為兩岸語文學(xué)界獻(xiàn)給中華民族乃至全世界的禮物。這是近年來兩岸加強(qiáng)交流,共同構(gòu)建和諧海峽、繁榮海峽的又一成果。這也預(yù)示著兩岸在經(jīng)貿(mào)往來通暢、興旺、互惠、穩(wěn)定并不斷深化的同時(shí),即將出現(xiàn)文教交流合作的更大熱潮。
彭興頎談道,兩岸有異義的詞匯不勝枚舉,主要包括3大類:“同實(shí)異名”指同一樣事物,但叫法不同,如大陸叫“一次性筷子”,臺灣則稱“免洗筷”;“同名異實(shí)”指同一個(gè)詞語,意思卻不同,如“窩心”,大陸是指“郁悶”,臺灣則指“開心”;一方特有詞匯,如臺灣選舉期間常說“拜票”,意即候選人到處拜訪選民,爭取選票。
一路走來,彭興頎表示過程相當(dāng)不容易,從一開始,兩岸學(xué)者僅在各自使用的漢字如何稱呼,討論起來就相當(dāng)激動(dòng)。2010年初兩岸分別成立小組,啟動(dòng)合作編纂中華語文工具書等工作,開展10輪會(huì)談和多次分組會(huì)談。

彭興頎
深入推進(jìn)合編中華語文工具書工作
彭興頎回顧總結(jié)了5年來兩岸語言文字交流合作取得的豐碩成果。他說,兩岸建立了合編工具書的工作組、工作機(jī)制以及合作成果發(fā)布機(jī)制,出版了中華語文工具書的系列詞典,兩岸以同一名稱命名的“中華語文知識庫”網(wǎng)站互通互聯(lián)、互學(xué)互鑒,兩岸青少年語言文化交流活動(dòng)不斷深化拓展,合編工具書模式產(chǎn)生了廣泛的社會(huì)影響和積極的借鑒意義。
“今后一段時(shí)間,將進(jìn)一步貫徹落實(shí)第五屆、第八屆兩岸經(jīng)貿(mào)文化論壇《共同建議》,充分發(fā)揮進(jìn)一步完善語言文字交流合作機(jī)制,拓展合作空間;深入推進(jìn)兩岸合編中華語文工具書工作,讓兩岸民眾乃至世界人民從中獲益;拓展兩岸青少年語言文字交流合作,增強(qiáng)兩岸青少年共同弘揚(yáng)傳承中華優(yōu)秀文化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彭興頎如實(shí)說。
進(jìn)一步完善語言文字交流合作機(jī)制
近60年來,由于各種原因,海峽兩岸盡管有相同的思想文化傳統(tǒng),使用同一種語言文字,但具體到字詞的形、音、義、語用層面,還存在一定的差異。比如,大陸的計(jì)算機(jī)“軟件”,臺灣稱為“軟體”;同為“脫產(chǎn)”,大陸指脫離生產(chǎn),臺灣指轉(zhuǎn)移出脫財(cái)產(chǎn);“綠色食品”為大陸特有詞,“草莓族”為臺灣特有詞;大陸稱為“等離子體”的科技名詞,臺灣則稱為“電漿”等等。兩岸通過合編詞典,使雙方的語言文字從異中求通到逐步化異為同,對于消除雙方語言文字溝通中的障礙,進(jìn)一步推進(jìn)兩岸經(jīng)貿(mào)文化交流,共擔(dān)傳承弘揚(yáng)中華文化的歷史使命,具有重要而深遠(yuǎn)的意義。
兩岸合編中華語文工具書將為兩岸科學(xué)文化交流起到重要參考作用,也將為增進(jìn)兩岸同胞福祉,促進(jìn)心靈溝通,增強(qiáng)兩岸同胞的民族認(rèn)同、文化認(rèn)同、國家認(rèn)同,共同傳承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建設(shè)共同精神家園發(fā)揮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