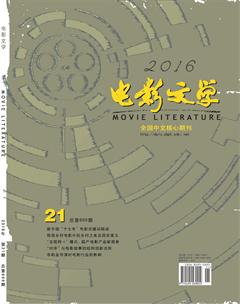《龍蝦》的反烏托邦敘事分析
席曉華
[摘要]《龍蝦》是希臘導(dǎo)演歐格斯·蘭斯莫斯的最新力作。在這部電影中,一個(gè)“理想”的社會(huì)被建構(gòu)出來,婚姻成為社會(huì)中的最高價(jià)值與終極目的,而單身者作為社會(huì)中的異類則必須在一個(gè)酒店中尋找配偶,否則就會(huì)被變成動(dòng)物。影片的主人公配對(duì)失敗逃入森林,卻又陷入單身者的極權(quán)組織中,最終為了愛情努力掙脫牢籠卻只是陷入了新的束縛之中。《龍蝦》的反烏托邦敘事無疑是對(duì)現(xiàn)實(shí)世界的諷刺,影片對(duì)于極權(quán)主義本質(zhì)的思考入木三分,將其對(duì)人性的壓抑、束縛做出了有力的批判。
[關(guān)鍵詞]《龍蝦》;反烏托邦;自由;隱喻
“烏托邦”(utopia)一詞是托馬斯·莫爾在他的著作《烏托邦》中首次使用的術(shù)語,其本意為“烏有之鄉(xiāng)”或“好的地方”,因此烏托邦即指空想的、理想的國(guó)度。與烏托邦理想相對(duì)的“反烏托邦”(DyStopia)則意為“壞的地方”,反烏托邦與烏托邦所依靠的思想原則、社會(huì)構(gòu)建相反,打破了烏托邦不切實(shí)際的空想和過于理想化的未來圖景描繪,眾多反烏托邦題材的小說,如《美麗新世界》《一九八四》等都通過對(duì)黑暗未來的想象來達(dá)到警戒和勸喻的目的。20世紀(jì),隨著反烏托邦文學(xué)和反烏托邦思想的影響力擴(kuò)大,這一主題也逐漸進(jìn)入電影領(lǐng)域。反烏托邦電影尖銳地諷刺了以穩(wěn)定、生存、發(fā)展等理由所建立的新極權(quán)世界。烏托邦的空想世界往往用理性的牢籠或單一的價(jià)值觀限制人性的自由,這樣的“美好”社會(huì)往往需要以自由為代價(jià),因此,反烏托邦電影通常以科學(xué)技術(shù)或集權(quán)主義作為控制人類社會(huì)的最高力量,在無情的摧殘和控制之下讓人類走上反抗之路,試圖沖破既有的牢固的社會(huì)體系。
歐格斯·蘭斯莫斯作為希臘影壇最有影響力的導(dǎo)演之一,善于在自己的電影作品中用極端和新奇的方式展現(xiàn)現(xiàn)代文明的批判與反思。他在2015年的新作《龍蝦》中就構(gòu)想了一個(gè)未來社會(huì)圖景,在這個(gè)社會(huì)中,所有居民的婚戀都受到高層的嚴(yán)格控制,城市中不允許單身者的存在,一旦成為單身者就將被轉(zhuǎn)移到一個(gè)酒店中,限定在45天之內(nèi)找到配偶,否則就會(huì)被轉(zhuǎn)變成一種動(dòng)物流放到森林中。影片的主人公大衛(wèi)在嘗試和一個(gè)女人配對(duì)失敗后逃到了森林中成為孤游者,然而孤游者群體卻遵循一套完全相反的規(guī)則,即所有人都必須保持單身而不可以相愛,正是在這樣極端的條件之下,大衛(wèi)遇到了真心相愛的女游擊隊(duì)員,因此他們必須想方設(shè)法地逃脫組織的掌控。《龍蝦》中存在的社會(huì)組織形態(tài)看似極端,卻是對(duì)現(xiàn)實(shí)極為深刻的隱喻,這一反烏托邦的敘事展現(xiàn)了導(dǎo)演對(duì)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的深刻反思與關(guān)懷。
一、“理想”世界的壓抑與束縛
《龍蝦》的第一個(gè)鏡頭是一個(gè)無對(duì)白的長(zhǎng)鏡頭,一個(gè)面無表情的女人驅(qū)車前往田野之中,走下汽車,鏡頭透過車窗拍攝她射殺了一頭牛,而汽車的雨刷還在機(jī)械地運(yùn)動(dòng)著,將克制與冷靜的風(fēng)格毫無保留地凸顯出來。整部影片伴隨著無感情的女聲旁白和充滿壓抑感的音樂徐徐展開敘事,正如第一個(gè)鏡頭所展示的那樣,在這個(gè)世界中,動(dòng)物雖然是由人變形而成的,但人與動(dòng)物之間有著明顯的等級(jí)差別,這種等級(jí)差異所帶來的壓抑感貫穿了整部影片。
影片的男主人公大衛(wèi)被自己的妻子拋棄后被轉(zhuǎn)移到酒店之中,而這個(gè)酒店就是一個(gè)理想社會(huì)構(gòu)架的縮寫,一切規(guī)則都被嚴(yán)謹(jǐn)?shù)刂贫ú?yán)格地遵守,單身者和情侶的社會(huì)地位不同,其中一個(gè)細(xì)節(jié)就是雙人運(yùn)動(dòng)場(chǎng)地僅供情侶使用,單身者只有權(quán)利使用單人體育設(shè)施,比如壁球或高爾夫球。在酒店之中,任何私人物品都不能擁有,連服裝都是統(tǒng)一的,這種統(tǒng)一所造成的結(jié)果就是僵化,大衛(wèi)甚至無法獲得合腳的半碼皮鞋,而只能穿酒店中配備的整碼鞋。影片用極其平穩(wěn)、克制的敘述進(jìn)程向我們展現(xiàn)這個(gè)微型社會(huì)中的一切規(guī)則,比如每個(gè)進(jìn)入酒店的單身者在轉(zhuǎn)變成動(dòng)物之前只有45天的時(shí)間尋找配偶,他們可以通過捕獲孤游者來延長(zhǎng)居住時(shí)問。剛?cè)胱≈畷r(shí)房客的一只手會(huì)被手銬綁住,其目的只是為了讓他們體會(huì)有伴侶的重要性,在每天起床的時(shí)候機(jī)械的電子女音會(huì)提醒他還剩下多少天,早餐已經(jīng)開始供應(yīng)。而大衛(wèi)在面對(duì)這一切的時(shí)候卻完全沒有反抗,他甚至還沒有從妻子離開的陰影中走出來,只是無奈、疲憊地接受這一切。
在酒店所構(gòu)建的微型社會(huì)圖景之中,價(jià)值觀是單一的,只有一種生活是值得過的,于是人們必須服從,必須去追尋這種所謂的“正確”的生活方式。在這種高度統(tǒng)一的價(jià)值體系之中,任何異己的力量都被貶低到更低一級(jí)的存在,甚至是“非人”的存在,即動(dòng)物。在《龍蝦》中,幸福的價(jià)值完全在于脫離單身,因此單身者的社會(huì)價(jià)值與社會(huì)地位低于情侶,賓館是使得這一套社會(huì)價(jià)值體系生效的社會(huì)機(jī)器,以機(jī)械、無情的方式運(yùn)轉(zhuǎn),將對(duì)錯(cuò)進(jìn)行嚴(yán)格的劃分。凡是錯(cuò)誤的將被毫無保留地剔除,只有符合規(guī)定的所謂正確的東西才會(huì)被執(zhí)行。但悖謬之處在于,這個(gè)社會(huì)中對(duì)于幸福、正確的定義是完全沒有商量的余地的,觀眾可以發(fā)現(xiàn),盡管在我們生活的世界中幸福是值得追尋的,正確的東西是值得堅(jiān)守的,但影片中用這種極端的形式卻恰恰說明并非在任何情況下幸福和正確都是值得追求的,一旦幸福和正確有了唯一的標(biāo)準(zhǔn),那它們就反而會(huì)成為強(qiáng)烈的束縛,并不惜以個(gè)人的自由為犧牲品。
單身者的存在違背了理想社會(huì)的構(gòu)想,因此他們成為異己者,只能努力尋找配偶進(jìn)入正常的社會(huì)或變成動(dòng)物被排除在社會(huì)之外,這意味著異己的存在完全無法被社會(huì)所容忍,只能被消除。在這樣的社會(huì)中,對(duì)單身的歧視不僅毫無理由,而且為了消除單身者,酒店的工作人員會(huì)強(qiáng)迫房客接受伴侶,并對(duì)單身生活進(jìn)行妖魔化的構(gòu)想,比如一個(gè)男人獨(dú)自吃東西就會(huì)被噎死,一個(gè)女人獨(dú)自走路就會(huì)被強(qiáng)奸。另外,人們還會(huì)被組織到森林中射殺單身的孤游者。毫無疑問,影片有力地對(duì)集權(quán)社會(huì)的本質(zhì)進(jìn)行了影射與批判,即任何以幸福為名義的洗腦都是一種對(duì)人性的壓抑與束縛。
二、追尋自由的不可能
大衛(wèi)在酒店中重復(fù)著機(jī)械的生活,但隨著可居住天數(shù)的減少,他和伙伴們都開始想方設(shè)法地尋找配偶,成為配偶的條件是兩個(gè)人必須有某個(gè)真實(shí)的共同點(diǎn),因此當(dāng)他的瘸腿伙伴無法找到瘸腿的伴侶時(shí),就經(jīng)常撞破自己的鼻子,假裝自己常流鼻血,并以此為契機(jī)與酒店中經(jīng)常流鼻血的姑娘靠近,并最終成功配對(duì)。走投無路的大衛(wèi)則只能假裝自己冷酷、殘忍、無情,來和酒店中那個(gè)殘酷無情的女人完成配對(duì)。為了避免變成動(dòng)物被天敵吃掉,或者在森林中成為孤游者忍饑挨餓,大衛(wèi)忍辱負(fù)重,與無情的女人住進(jìn)雙人套房,甚至連她殺了自己變成狗的哥哥也要假裝無所謂。但他難以克制的眼淚還是被識(shí)破了,于是大衛(wèi)只能與對(duì)方?jīng)Q一死戰(zhàn)。他在一個(gè)女服務(wù)員的幫助下殺死了她,逃入了森林,成為孤游者中的一員,被那群制度的反抗者所接受。
可悲的是,這個(gè)群體完全走向了另一個(gè)極端,使得大衛(wèi)尋求新生和自由的希望第一次落空。在孤游者的群體中,所有人必須單身,相愛的人必須接受懲罰,而且每個(gè)人都要事先為自己挖好墳?zāi)埂?shí)際上,大衛(wèi)只是從一個(gè)冷酷的機(jī)器中進(jìn)入了另一個(gè)機(jī)器之中,二者的本質(zhì)沒有區(qū)別,都是以絕對(duì)的價(jià)值觀念要求和束縛人,遵從唯一的標(biāo)準(zhǔn),奉行唯一的準(zhǔn)則。森林中的孤游者群體冷酷無情,以強(qiáng)者為絕對(duì)主宰,當(dāng)他們中的一員被捕獸夾夾住時(shí),女首領(lǐng)完全不去幫助他,只是留下他自己努力掙脫,如果他成功了就繼續(xù)追趕他們的步伐,如果無法掙脫就只能獨(dú)自躺進(jìn)墳?zāi)怪小T谒麄兊挠^念中弱者是可恥的,不值得拯救,想要生存唯一的法則就是強(qiáng)大。當(dāng)這種價(jià)值觀成為主導(dǎo)之時(shí),人性中的善良和信任就完全被消耗殆盡了。當(dāng)大衛(wèi)在森林中遇見前來射殺孤游者的昔日伙伴羅伯特時(shí),他立刻選擇用謊言欺騙他,認(rèn)他做最好的朋友,打動(dòng)他不殺自己,而大衛(wèi)的伙伴則從背后傷害了羅伯特,大衛(wèi)轉(zhuǎn)眼間就毫不留情地剝光了羅伯特的衣服留作自用。
至此,影片的諷刺更深了一層,通過先后展示兩種極端的組織形式,導(dǎo)演否定了任何單一的價(jià)值體系和評(píng)價(jià)標(biāo)準(zhǔn)。影片并沒有將視野局限于對(duì)特定的社會(huì)婚姻制度或?qū)紊碇髁x者的諷刺,而是批判了所有抽象的單一社會(huì)結(jié)構(gòu)。事實(shí)上,只要一個(gè)社會(huì)或團(tuán)體組織存在一套不可懷疑的標(biāo)準(zhǔn),那么它的目的就反而是極為可疑的,當(dāng)中心與邊緣、主流與非主流被確立為區(qū)隔人群的標(biāo)準(zhǔn)之時(shí),那么這個(gè)社會(huì)就存在著潛在的危險(xiǎn),走向壓迫、暴力與極權(quán),正如資本主義發(fā)展初期對(duì)殖民地的控制,二戰(zhàn)中德國(guó)對(duì)猶太種族的屠殺,甚至冷戰(zhàn)中的霸權(quán)思維,強(qiáng)大的一方都會(huì)竭力證明自己統(tǒng)治的合理性和存在的優(yōu)越性,這就是人類歷史上曾真實(shí)上演的悲劇。
原本大衛(wèi)在這個(gè)新的群體中逐漸被轉(zhuǎn)變得冷酷無情,但是另一位女隊(duì)員的出現(xiàn)改變了局面,二人逐漸發(fā)展出的愛情讓大衛(wèi)人性中的溫情重新浮現(xiàn),并獲得勇氣重新追求自由。二人的愛情使得他們成為隊(duì)伍中的異己存在,當(dāng)孤游者的女首領(lǐng)發(fā)現(xiàn)他們相愛的事實(shí)之后,用欺騙的方式弄瞎了女隊(duì)員的眼睛,讓他們?cè)局朴喌奶用撚?jì)劃無法實(shí)施。影片的敘述進(jìn)行至此,沖突聚焦在了女首領(lǐng)與二人之間,因此當(dāng)大衛(wèi)想方設(shè)法殺掉了她之后,仿佛希望的曙光真的出現(xiàn)了,但這一次大衛(wèi)和愛人能夠獲得真正的自由嗎?顯然,《龍蝦》再次給出了否定的答案。
三、反烏托邦的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隱喻
當(dāng)大衛(wèi)殺死了女首領(lǐng),帶著愛人逃出森林進(jìn)入城市之中,卻并沒有迎來預(yù)期的幸福生活,因?yàn)樵诔鞘兄兴麄內(nèi)粝胍院戏ǖ纳矸萆罹捅仨氉袷爻鞘械囊?guī)則,即接受婚姻,而婚姻的前提則是二人必須有真實(shí)的共同之處,唯一的可能就是大衛(wèi)戳瞎雙目和愛人一樣成為瞎子。于是在影片的結(jié)尾處,大衛(wèi)在努力地戳瞎自己,至于他有沒有成功就完全留給觀眾去想象了。這個(gè)看似開放的結(jié)局實(shí)際上并無任何懸念,如果大衛(wèi)沒有戳瞎自己,那么他就會(huì)再次進(jìn)入酒店重復(fù)前面的循環(huán)。從某種程度上講,大衛(wèi)和愛人只是重新接受了社會(huì)的規(guī)訓(xùn),為了生存而犧牲了自由和個(gè)性,這正是影片最深的著力之處。
影片中那個(gè)美好的烏托邦的理想是讓所有人都得到幸福,主宰者的目的是讓所有人都處于和諧穩(wěn)定的婚姻關(guān)系之中,然而《龍蝦》卻通過反烏托邦的敘事揭露了這個(gè)“美好”世界的脆弱之處,正是因?yàn)樾腋J潜欢x的、有條件的東西,因此幸福被僵化成標(biāo)準(zhǔn),原本值得主動(dòng)追求的東西成為人們被迫接受的產(chǎn)物。在這樣的條件之下,獲得幸福的方式只是滿足條件,即尋找真實(shí)的共同之處。因此,孤游者群體摧毀伴侶的方式就是破壞條件,揭露出雙方并不相愛而只是在偽裝的事實(shí)。烏托邦的理想社會(huì)是用極權(quán)的鐵腕實(shí)現(xiàn)的,這一機(jī)械、冷酷的社會(huì)機(jī)器瓦解了人性之中最美好的部分,摧毀了真誠(chéng)、善良的美好品質(zhì),最終只能將人轉(zhuǎn)變成沒有感情的零件,在龐大的機(jī)器中維持自己的運(yùn)轉(zhuǎn),支撐存在的假象。
更令人絕望的是,在這樣的社會(huì)之中,個(gè)體根本沒有反抗的余地,正如大衛(wèi)所經(jīng)歷的,他無法以一己之力推翻這個(gè)穩(wěn)固的社會(huì)組織,最終為了生存只能做出犧牲而成為它的一部分。《龍蝦》反烏托邦的敘事完成了對(duì)于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的深刻隱喻,“酒店”和“森林”兩種看似迥異的社會(huì)組織形態(tài)實(shí)則有著相似的本質(zhì),那就是極權(quán)的壓迫與束縛,無論一個(gè)社會(huì)組織是假以愛的名義還是假以自由的名義,只要它奉行唯一的、至高無上的價(jià)值觀念,不允許任何異己的存在,那么它所宣揚(yáng)的名號(hào)就都是虛假的。人類幾千年的歷史不斷證明,宗教、國(guó)家、民族主義都有可能成為這樣的極端力量,以冠冕堂皇的理由來清除異己,不斷為自己的霸權(quán)確立合理性,但究其本質(zhì)則不過是奴役與壓迫。
《龍蝦》用一個(gè)看似荒誕的寓言讓我們反思何謂真正的自由,何謂人之為人的本質(zhì)。顯然,在極權(quán)社會(huì)的控制下,不可能存在真正的自由和完整的人格,在如今看似多元平等的社會(huì)表象之下,人類必須對(duì)任何可能出現(xiàn)的奴役與壓迫提高警惕,無論它以什么樣的面貌偽裝自己。從這個(gè)角度看,《龍蝦》這部電影對(duì)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的反思無疑是十分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