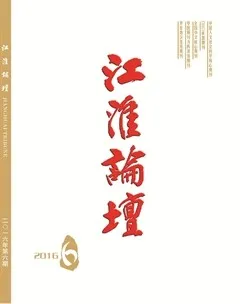知識分子對時代的批判與反思
楊武能+湯習敏
摘要:在代表作《論浪漫派》中,海涅不遺余力地“討伐”德國浪漫派。然而,作為一位與時代的各個思潮密切關聯的作家,海涅在《論浪漫派》中亮出種種看似“偏激”的觀點,實則是他身處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社會變革時期,在這部時代著作中履行知識分子反思、批判傳統與社會的職責;作為文化傳播的代表,海涅用他的文字干涉公共事務,力圖使文學藝術介入當代社會中。盡管《論浪漫派》中的一些觀點已隨時代的發展而過時,但它作為知識分子對時代的反思與批判,仍對現代社會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海涅;《論浪漫派》;知識分子;批判;反思
中圖分類號:I516.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1-862X(2016)06-0166-006
作為歌德之后享有世界聲譽的德國詩人,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在中國讀者中知名度極高,可惜卻還未受到國內學術界足夠的重視(1),學界甚至仍存有海涅曾一度追隨革命導師馬克思的結論。(2)而在國際日耳曼學界,對海涅及其作品的研究呈多元化趨勢,海涅的現代性成為現代海涅研究的一大重點。本文擬從現代性的角度,以散文名篇《論浪漫派》的創作為例,探究海涅作為知識分子對社會、對傳統的反思與批判。
一、海涅: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intellectual)在近現代西方語境中,主要指的是掌握一定知識基礎上,深切地關懷公眾社會,保持獨立批判性的群體。也就是說,知識分子在擁有知識(“知識性”或稱“專業性”)的同時,還應具備高度的社會責任感與使命感,持批判意識與懷疑精神積極介入當下公共事件(“公共性”)。“捍衛真理和堅守正義應該是公共知識分子的職業道德。”[1]從這種角度看,知識分子可謂一個社會的公共良知。
當代德國哲學家、社會學家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曾撰文《精神與權力——一個德國話題。海因里希·海涅和知識分子在德國的角色》,文中認為,海涅作為德國知識分子的一個剪影[2],他是作家充當有責任感的公共角色的例子,而這種角色在現代德國文化中發展滯后。在哈貝馬斯看來,海涅深切地明了知識分子的使命,他清楚知識分子肩負參與并引導公眾討論的義務,同時又不以某黨派的名義或充當某個社會群體的代言人;憑借這一點,海涅不同于他那個時代以及后世的其他作家。[3]
哈氏對海涅作為知識分子的大力肯定,無疑展示出解讀海涅另一種身份的可能。但是,作為德國第二大詩人的海涅,往往給人過于感性的形象,其作品的語言太形象化了,以致于語言背后的思想性容易遭到忽視;而且,海涅在不同時期表達出不同(甚至矛盾)的觀點,給人造成缺乏堅定立場甚至投機的印象。實際則完全不是這么一回事。身處19世紀上半葉風云際會的歐洲,時代的不安定給與時代緊密聯系的海涅造成不穩定的影響,面對現代社會的種種矛盾,海涅沒有像同期的浪漫派作家那樣退縮于內向性,而是以論戰之筆(從而樹敵無數)投身時代的發展,試圖重新找回藝術和現實的聯系,用以展示人生的廣度、深度以及社會的現實生活。這一點,可以說是貫穿海涅不同時期作品的一大主線。
青年時期,海涅與浪漫派一樣,在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體驗中感受到一種痛苦的分裂。抒情詩《短歌集》(1817—1827)成就海涅詩人之名后,海涅越來越感覺到時代狀況難以用詩歌的形式表達,他在1837年回顧道:“我早就看到了,我已不再能駕馭詩句前進,故而我把自己轉到寫作好的散文方面。因為在散文里光有美好的天氣、春天的太陽、美妙的五月、桂竹香和綠樹是不夠的……于是我沉思默想地去考慮各種現象的內在意義、考慮諸事物的最終原因,考慮人類的使命和使人變得美好和幸福的手段等問題。”[4]于是,海涅將散文創作比重逐漸加大,在不斷增強對時代、對社會的批判中尋找一種更符合表達時代精神的方式。在七月革命感召之下,海涅自愿流亡到巴黎。此后,散文成為他這一階段理解時代的主要表達方式,隨后更近一步地發展為通訊報道以及新聞短評(Essays),大大拉近他的創作與讀者的距離。“現在是思想斗爭的時代,期刊是我們的要塞。”[5]在海涅一生中最斗志昂揚的30年代,詩人看到:在封建落后的德國,公共領域的政治生活被壓抑,藝術無法反映現實世界,而只能淪為用以麻痹生活的戲劇等替代品。面對德國落后的政治狀況、文學淪為政治不自由的畸形表現,海涅進而強調藝術的社會效果,疾呼需要一種參與社會生活的新文藝,一種反映時代精神、注重藝術實踐效果的文藝。他主張作家以藝術家為內核,從民眾的利益出發,通過藝術(海涅這里即為文學創作)為民眾剖析歷史與時事(尤其是政治事件)諸現象背后的因果關聯,對其起一種教化作用。“我不想從黨派的工場里借用他們陳舊的尺子來衡量人和事,更不想按照夢幻的個人感情確定其價值和重要性,我要盡可能客觀公正地促進人們對當代的理解,我首先要到往昔中找尋解開喧囂的現實之謎的鑰匙。”[6]海涅欲凸顯的,乃作家所應擔當的社會責任:民眾的教育者、社會的批判者與反思者。可以看到,海涅作品中時代的印記表現得尤為鮮明,其間跳躍著的,正是海涅的那顆赤子之心,是流亡他鄉、遙望祖國而夜不能寐的痛楚,是知識分子應有的擔當——對社會、對民眾的公共關懷。
值得特別強調的是,在詩人海涅睿智、恣意的諷刺背后蘊含著他對時代、對社會作出的深刻的理性思考,而這并非憤世嫉俗,更非玩世不恭。在1848年以后,海涅由于健康的原因,遠離現實的社會生活,但他以另外一種方式作出自己對歷史的反思;晚年海涅作品中主觀性因素的更加,并不意味著海涅對社會的責任心降低[3]181,在他晚年的神話題材的抒情詩中仍不乏公平、正義等主題,激發讀者反思。
因此,從知識分子反思、批判時代的視角解讀海涅,挖掘海涅的現代性,對現代海涅研究必當有所增益。而《論浪漫派》的創作,正是體現海涅具備知識分子批判與反思精神的范例。
二、知識分子海涅創作《論浪漫派》
說起《論浪漫派》,不少讀者很容易產生一個疑問:為何寫出動人詩篇、辛辣散文的海涅,卻創作出這樣一篇“欠考慮”的作品?多少年塵埃落定后,晚年海涅在回憶錄中承認曾將恩師痛毆一頓,承認自己現在需要一個上帝,卻未見他對《論浪漫派》中的觀點有任何悔過的表示,而他在《論德國宗教和哲學的歷史》的1852年前言中卻是那么懇切地坦言要收回自己在該作品中的觀點!殊不知,海涅與時代的各個思潮密切關聯,創作《論浪漫派》,正是作為知識分子的海涅對傳統文化的反思,對自我的反省,更是對現實的批判。《論浪漫派》創作于19世紀30年代初,在此之前海涅逐步經歷歷史與個人的重要轉變,如浪漫主義和黑格爾哲學早年對海涅的深刻影響,以及移居巴黎的生活給海涅的視角所帶來的巨大變化等;借助于這些轉變,海涅的創作獲得更廣闊的社會維度,在加深對時代的反思中,海涅完成了向知識分子的蛻變。
(一)反思浪漫主義文學傳統
19世紀初,德國浪漫派處于鼎盛期。青年時代的海涅,在家鄉杜塞爾多夫所接受的教育(1807—1815)基本為晚期啟蒙主義性質,但由于他對民間文學傾向的浪漫主義比較偏愛,喜歡閱讀當時流行的以霍夫曼(E.T.A.Hoffmann)為代表的鬼怪文學、富凱(de la Motte Fouqué)的騎士小說《魔術指環》、烏蘭德(L.Uhland)的詩歌等。上大學后,海涅對浪漫主義的認識進一步深入。在波恩學習期間(1819—1820),海涅不但加入由大學生組成的晚期浪漫主義圈子,還遇見了對自己的文學發展起到至關重要作用的老師奧·威·施萊格爾(A.W.Schlegel)。通過閱讀施萊格爾的著作,聆聽其文學講座課,甚至是與之親密的私人關系(海涅寫的詩曾受其逐行修改、批注),海涅接受到正規的文學教育,在抒情詩、格律學以及詩藝學等方面受到專業的指點,并對德國文學(尤其是古代文學)和外國文學(如莎士比亞以及印度文學)的認識有較大的提高。當時海涅對施萊格爾懷著一種學生式的崇拜,在信中他寫到:“關于我和施萊格爾的關系我可以給你寫很多令人高興的事。他對我的詩很滿意,對詩中的獨創性感到既高興又驚奇……我越是常去他那兒,越發覺得他是個了不起的人物……”[5]25
不過,海涅并非單方面地全盤接受這位浪漫派代表的觀點。在波恩學習時,史學家許爾曼(K.D.Hüllmann)教授的啟蒙主義思想一定程度地促進了海涅逐漸對浪漫派神秘主義和脫離現實的傾向進行反思;后兩度在哥廷根求學,海涅還深受啟蒙主義傾向的史學家薩托里烏斯(G.Sartorius)教授的影響。在1820年,海涅還曾撰寫一篇名為《浪漫主義》的短小文章,對浪漫主義提出一些與浪漫派觀點不一致的構想,其中海涅認為,“基督教和騎士制度只是進入浪漫主義的手段”;真正的浪漫主義,不是“西班牙的柔光、蘇格蘭的朦朧與意大利叮當鈴音的大雜燴,不是含混模糊的圖像”[7],浪漫的詩應該也是形象化的詩(3)等等。可以說,盡管海涅的總體觀點仍處在浪漫派的理論框架內,但他在接受浪漫主義的同時,已有意無意地覺察到浪漫派在對中世紀的模仿中某些需要糾正的東西,開始有了自己的獨立思考。
總的說來,海涅在整個20年代對浪漫主義有較為全面的接受,他的早期創作也不乏受浪漫主義影響的明確例證(如成名作《短歌集》),浪漫主義的“乳汁”將海涅孕育長大,他深諳浪漫主義之精髓。但接受中伴隨著反思,尤其是20年代中期起,海涅開始對浪漫派有了疏遠,浪漫主義的主題、母題以及藝術手法等雖然仍是他創作的重要源泉,卻往往被諷刺地揚棄,或是被有意與異質于浪漫主義的不和諧音符相混雜。
(二)接受黑格爾哲學
進一步加深海涅反思文學傳統、批判現實社會的,是在海涅的精神發展中打上重重印記的黑格爾哲學。
于柏林求學時,海涅學習黑格爾的“世界史哲學”課程,并通過凡爾哈根(K.A.Varnhagen)夫婦開闊了個人交往的圈子。在凡爾哈根的沙龍,他不僅與黑格爾本人接觸,甚而經常討論,還認識了對黑格爾法哲學原理加以運用的青年法學家甘斯(E.Gans)。1822年8月,海涅加入由甘斯等成立的“猶太人文化與科學協會”(其成員多屬黑格爾學派),積極參與協會組織的講座。與眾多黑格爾學派人物的交往,一定程度地加強了海涅對黑格爾哲學的理解。一位該協會成員這樣描述海涅:“黑格爾這位偉大的思想英雄的那些概念,盡管無法將這位詩人直接拉進星云圈以及深不可測的秘奧,但是通過他那兩位將黑格爾的抽象觀念與實際生活聯系起來的朋友甘斯和摩澤爾,他的精神間接地從黑格爾哲學中獲得一種活力與廣度。”[8] 在《思想·勒格朗篇》(1826)中,海涅將黑格爾與法國大革命、汽船一同列為“出自天神創造之夢的個別出色的念頭”[9],而整部作品的核心思想之一則是以拿破侖作為新的時代精神的代表,勒格朗為其革命思想的鼓手,借此向封建落后的德意志挑釁。
丹麥批評家勃蘭兌斯說:“把那些才子們逼到動蕩的歷史政治生活中去的,是黑格爾的哲學和七月革命。”[10]的確,對于海涅所處的那個時代而言,黑格爾哲學(尤其是黑格爾對歷史的理解)起到了一種解放精神與批判時代的作用。加上1830年的七月革命,海涅進而轉向對社會政治現實的批判,而這一轉變反過來也加深了他對黑格爾哲學的接受甚至發展。海涅從20年代關注世界歷史中個人的命運(如《思想·勒格朗篇》中世界歷史主題下的拿破侖),轉而強調文學與藝術、宗教與哲學的現實性影響,有了把革命的理論導向實踐的要求,由此產生了《論浪漫派》以及《論德國宗教和哲學的歷史》(1834)中對這些問題的探討。在《論德國宗教和哲學的歷史》中,海涅甚至得出結論,德國的哲學革命已經結束,“黑格爾完成了它的巨大的圓運動”[11],并預言繼宗教的、哲學的革命之后第三階段的政治革命即將到來。海涅之所以能如恩格斯所稱贊的那樣,最早預見到德國古典哲學充當政治變革的前導,無疑是深刻領會到黑格爾哲學的劃時代意義。不僅如此,海涅還將黑格爾哲學往社會實踐方向大大推進,這一點在他移居巴黎之后切實地體現出來。
(三)隔岸反思德國社會
1830年七月革命之后,波旁王朝的復辟統治被推翻,天主教會與貴族階級也隨著封建王朝的倒臺而式微。與法國風起云涌的政治運動截然不同的是,位于萊茵河彼岸的德意志仍舊邦國林立,政治、社會生活處于停滯狀態,貴族與教會勾結而成的封建復辟牢籠嚴重阻礙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因此,七月革命的爆發,也在德國喚起了人們對自由的渴望;繼法國大革命之后,巴黎被視為“革命的燈塔”[12],不少德國知識分子紛紛流亡至此。大學時代便出版詩作的海涅,在1825年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受洗加入新教后的輾轉幾年間卻謀生無望,直到七月革命重燃起消沉低落的詩人心頭的戰斗火焰。由于在拿破侖曾統治過的萊茵河畔長大,海涅深受法國大革命的自由思想浸潤,七月革命更是印證了他對歷史發展的構想,被其視為法國大革命的延續:“高盧的雄雞已啼叫兩遍,德意志也行將破曉。”[13]
1831年5月,海涅移居巴黎。作為歐洲當時的政治、文化中心,巴黎開闊了他的視野,使他的生活與創作開始了新的階段。通過切身體會法國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文化生活,海涅對革命理想和現實的認識得到深入,因而能更清醒、更透徹地觀察發生在德國的一切。此時的海涅,已然不再是《短歌集》中詠嘆不得意愛情的抒情詩人。在身處巴黎的海涅看來,德意志各個邦國的政治與社會結構都顯得過時;淪為一種時代錯誤而茍且存活的封建德意志,其土地上繁盛著的德國浪漫主義,勢必無法滿足時代發展的需要。因此,七月革命以及移居巴黎后的生活,促使海涅對德國政治經濟落后的根源進一步反思,并使他開始真正有意識地審視德國精神生活中(尤其是浪漫主義文學)所欠缺的內容。
在抵達巴黎后,海涅與云集于此的各界名流如大仲馬、巴爾扎克、戈蒂耶(T.Cautier)與喬治·桑等密切交往,其中即有他此前較為關注的圣西門主義者。海涅在此不僅結識圣西門弟子安凡丹(P.Enfantin)等領導人物,還定期閱讀圣西門主義的刊物,多次參加圣西門主義者的集會。圣西門主義之所以受到海涅的關注,一方面由于海涅此前在波蘭之行中接觸到農民、猶太人等被壓迫階層的悲慘生活,在英國之行體驗到資本主義社會貧富差距、人剝削人以及國家教會等;在巴黎期間,身為新聞報道記者與法學博士的海涅,深入到時代的發展中,對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運作進行剖析考察的同時,對資本主義社會階級結構、對七月革命僅滿足了資產階級的利益等都有了切身感受,凡此種種促使海涅更加冷靜地關注社會問題(尤其是日益嚴重的階級分化)。另一方面,圣西門主義的不少觀點使海涅感興趣,尤其是根據個人才能劃分社會等級(天才、藝術家受到尊敬)的社會學說——既不陷入平均主義,又體現精英階層價值,以及肯定感官性、強調精神與肉體和諧的宗教觀,對海涅具有不小的吸引力。
(四)反駁斯太爾夫人的《德意志論》
眾所周知,浪漫主義是一個遍及歐洲的文學運動。德國作為浪漫主義的發源地之一,在時間上要比法國浪漫主義稍早。1800年前后,德國浪漫主義運動達到鼎盛,1830年時已趨于尾聲。浪漫派的一些重要代表人物,在20年代都已相繼去世(4),在世的不少代表如布倫塔諾(C.Brentano)、阿尼姆等也都退出人們的視線。而在法國,19世紀初主要還是根深蒂固的新古典主義占據正統,斯太爾夫人1810年的《德意志論》掀起了法國反古典主義的討論,法國浪漫主義才正式發展起來。而且與歐洲其他國家不同的是,法國的浪漫主義盡管最初以夏多布里昂為代表贊美中世紀、宣揚基督教的面目出現,但是由于受法國大革命的影響,法國的浪漫主義與政治聯系相對要緊密得多。在海涅移居巴黎時,斯太爾夫人的《德意志論》在法國被視為經典,法國浪漫主義正處于鼎盛期,奧·威·施萊格爾等被法國浪漫主義者們奉為權威。[14]
移居巴黎后,作為流亡者的海涅致力于德法兩個民族的相互了解。20年代的抒情詩人(成名作《短歌集》)和游記作家(《游記》系列)開始有意識地轉變自己的角色,他開始在詼諧批判的散文中對照德國落后的現實和法國先進的政治與文化思想。他先是撰寫了一系列文章(如《法蘭西現狀》)觀察并批評法國的公共生活,使德國讀者了解法國;獲得成功后,一些重要的期刊遂向海涅約稿,要求介紹一些關于德國的內容。海涅于是致力于將18世紀末19世紀初德國所完成的文學和哲學革命介紹給法國公眾。《文學歐羅巴》雜志的發行人博海恩(Victor Bohain)委托海涅以斯太爾夫人《德意志論》的樣式來寫有關德國的情況,海涅卻要求以與之相反的方式來寫。他認為,作為“目前法國讀者手頭唯一的一本全面介紹德國精神生活的書籍”[9]9,斯太爾夫人的《德意志論》“贊揚德國的精神生活、唯心主義”[11]10,卻忽略了德國浪漫主義運動所產生的具體政治背景,因而對浪漫派的一些本質的特征產生了誤解,有美化封建落后的德國之嫌;而且在《德意志論》出版20年后,早已喪失活力的德國浪漫派已經過時,不宜對蓬勃發展中的法國浪漫主義產生負面的影響,使其步入自己的后塵,淪為守舊的反動勢力。他認為,“在那些描述德意志天主教浪漫主義文學階段的文章中(5),我本想部分地給法國人一個告誡性的形象,并與對法國人產生危險影響的、我們的教皇極權主義派別相抗衡。”[4]249 因此,《論浪漫派》也是對斯太爾夫人筆下的德國印象一種撥正。
19世紀上半葉,社會的變革伴隨著文學市場的不斷整合。近代報刊業的繁榮,使海涅作為自由作家得以主要依靠稿酬生活,通過獨立的文化創造活動實現自身獨立的社會存在。作為文化的承載者與傳播者[15]的代表,海涅用他的文字干涉公共事務,力圖使文學藝術介入當代社會中。因此,從知識分子海涅的身份去考量《論浪漫派》的創作,不難發現,《論浪漫派》這部時代著作正是身處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社會變革時期的海涅,在履行知識分子反思、批判傳統與社會的職責。從這一角度解讀《論浪漫派》中海涅的“偏激觀點”,頓時讓人豁然開朗;而《論浪漫派》之所以在德國文學史上產生深遠的影響,很大程度也在于它深深根植于反思時代的土壤。盡管《論浪漫派》中的一些觀點已隨時代的發展而過時,但它作為知識分子對時代的反思與批判,仍對我們現代社會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注釋:
(1)國內學界對海涅的研究主要為:1987、1997年海涅誕辰190、200周年之際,在北京大學舉辦的兩次國際海涅學術討論會,以及由此集結出版的會議論文集。由于受意識形態、研究條件所限,1987年研討會的論文可以說社會意義大于學術意義。據本人統計,1956年至今國內對海涅及其作品介紹或評述的期刊論文不到100篇,具備一定學術價值的不到一半,如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談論海涅與馬克思關系話題的論文就有10篇之多。國內權威的、系統研究海涅的學者,主要以張玉書為代表(如其選編的《海涅選集》的分卷序言《詩人海涅》與《思想家海涅》、《戰士海涅》與《政論家海涅》等影響較大)。總的來說,國內海涅研究的縱深度還遠遠不夠。
(2)參見1983年有關馬克思與海涅的多篇論文,如:馬征《馬克思與海涅交往述評》,載《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3年第一期;農方團《導師、詩人——馬克思與海涅》,載《廣西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3年第一期等。
(3)施萊格爾的觀點是,浪漫的與古典-形象化的(plastisch)是對立的。海涅在《浪漫主義》中將歌德與奧·威·施萊格爾視為最偉大的浪漫主義者與最偉大的雕塑家(Plastiker),意在消除浪漫的詩與形象化的詩之間的對立。
(4)霍夫曼(1776—1822)、魏爾納(Z.Werner,1768—1823)、讓·保爾(Jean Paul,1763—1825)、弗·施萊格爾(F.Schlegel,1772—1829)均去世較早。奧·威·施萊格爾后期也有較大轉變。
(5)指《論浪漫派》。
參考文獻:
[1]白夏.公共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法國的歷史與現實[C]//許紀霖,劉擎,主編.麗娃河畔論思想:華東師范大學思與文講座演講錄.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261.
[2]Jürgen Habermas.Geist und Macht-ein deutsches Thema.Heinrich Heine und die Rolle des Intellektuellen in Deutschland.[C]//In Kruse,Joseph & B.Kortl nder(Hg.).Das Junge Deutschland.Kolloquium zum 150.Jahrestag des Verbots vom 10.Dezember 1835.Hamburg:Hoffmann und Camqpe,1987:36.
[3]Hohendahl,Peter Uwe.”Kritische Eingriffe:Der Intellektuelle als Dichter.[C]//In ders.Heinrich Heine Europ?ische Schriftsteller und Intellektueller.Berlin:Erich Schmidt Verlag,2008:158.
[4][德]海涅.海涅全集(第12卷)[M].章國鋒,胡其鼎,主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253.
[5]Heine,Heinrich.S?kularausgabe.Werke,Briefwechsel,Lebenszeugnisse(Bd.20)[M].Berlin:Akademie,Paris:Editions du CNRS,1970-1986:350.
[6][德]海涅.海涅全集(第9卷)[M].章國鋒,胡其鼎,主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146.
[7]Heine,Heinrich.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Bd.10)[M].Windfuhr,Manfred(Hg.).Hamburg:Hoffmann und Campe,1973-1997:195.
[8]Kanowsky,Walter.Vernunft und Geschichte:Heinrich Heines Studium als Grundlegung seiner Welt-und Kunstanschauung[M].Bonn:Bouvier Verlag,1975:187-188.
[9][德]海涅.海涅文集.游記卷[M].張玉書,選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123.
[10][丹麥]勃蘭兌斯.十九世紀文學主流(第六分冊)[M],高中甫,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241.
[11][德]海涅.海涅文集.批評卷[M].張玉書,選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335.
[12]張芝聯.法國通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273.
[13][德]海涅.海涅全集(第11卷)[M].章國鋒,胡其鼎,主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95.
[14]Heine,Heinrich.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Bd.8/2)[M].Windfuhr,Manfred(Hg.).Hamburg:Hoffmann und Campe,1973-1997:1054.
[15]李漢秋.《儒林外史》可作認知中華傳統文化的形象教材[J].江淮論壇,2015,(1).
(責任編輯 黃勝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