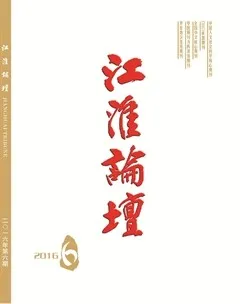民初皖籍知識分子與文化公共領域的建構
朱妍
摘要:民初皖籍知識分子因同質性文化身份聚合為《新青年》知識群體,他們以學校、社團和報刊為平臺,在文化場域中建構了主體間平等交往對話的公共文化空間。在合群意識的心理訴求下,他們拓展了文化空間,書寫了公共輿論,彰顯出鮮明的民族意識,為公眾自我身份的認同提供了價值依托。皖籍知識分子在公共領域所構筑的民主機制昭示了自由社會的運作模式,為國家的現代化建設樹立了精神風標。
關鍵詞:皖籍知識分子;同質身份;文化空間;民主機制;現代化指向
中圖分類號:I206.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1-862X(2016)06-0183-005
民國初年,政權的頻繁更迭斷送了國民的共和夢想,政局的混亂衍生出政治權威的真空和價值信仰的缺席,國勢衰微,民心萎靡,文學精英企圖力挽狂瀾,以文學寓言譜寫民族國家想象,皖籍知識分子以社團、報刊和學校為平臺,在民初的文化場域中建構了主體間平等交往對話的公共領域。
一、聚合歸因:同質性的文化身份
20世紀初,中華民族遭遇內憂外患之困,皖籍知識分子在共同的文化價值觀念和思想話語體系的鏈接下,聚合為《新青年》知識群體,他們擺脫了私人領域的統攝,積極參與社會公共事務,展開了公共性的社會交往。“公共性本身表現為一個獨立的領域,即公共領域,它和私人領域是相對立的。”[1]2
陳獨秀是民初皖籍文人聚合為《新青年》知識群體的凝聚點。在清末民初的革命風潮中,他從事反清倒袁的政治活動,組織革命團體以廣結同志,編輯文化報刊做萬戶鼓吹,聯絡了眾多皖籍志士。1903年,汪孟鄒在蕪湖長街徽州會館創立了科學圖書社,科學圖書社是皖籍志士重要的交往場所,陳獨秀將《安徽俗話報》的編輯部設立在科學圖書社的樓上,且岳王會的創立也正是在這座小樓上策劃的。[2]1905年,陳獨秀在蕪湖安徽公學創立了岳王會,高語罕、李辛白、光升是岳王會的重要成員,協助陳獨秀聯絡革命志士,而劉文典此時就讀于安徽公學,深受岳王會革命激情的感染,立志與陳獨秀同仇敵愾、同氣相求。岳王會成立后,其組織骨干陳獨秀、高語罕、李辛白、光升、劉文典等常在科學圖書社聚議,交流思想,討論時局,聯絡感情,構建了公共空間的關系網絡。
胡適與陳獨秀的相識歸因于汪孟鄒的引薦,汪孟鄒與胡適同為績溪人,二人素有來往,交情匪淺,胡適在陳獨秀的邀請下,加入了《新青年》文化陣營,陳獨秀與胡適的聯手,更多的是基于“文化啟蒙立場上對傳統的反叛與現實的改造” [3]。高一涵與陳獨秀有師生之誼,高一涵在安徽高等學堂讀書時,陳獨秀為其授業恩師。1912年,高一涵赴日本留學,留日期間,他在章士釗主編的《甲寅》雜志中擔任英文編譯。1914年,陳獨秀在二次革命失敗后,應章士釗之邀東渡日本,協助章士釗編輯《甲寅》雜志,與高一涵再次聚首。陳獨秀創辦《青年雜志》時,高一涵加入了《青年雜志》的編撰隊伍。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創辦《青年雜志》)(后改名《新青年》),《新青年》最初兩卷的作者群以皖籍知識分子為主,這些撰稿人多是陳獨秀在革命生涯中結交的同鄉。《新青年》首卷的撰稿人有高一涵、劉文典、潘贊化、李辛白、高語罕,第二卷增加了胡適、光升、程演生、王星拱、蔡曉舟,王星拱和蔡曉舟在《新青年》遷至北大后加入撰稿者隊伍。同鄉情誼、革命背景是皖籍知識分子聚合的本質性文化歸因,他們廣泛聯絡了社會成員,在自由民主的維度中構筑了溢出官方政治權力控馭的公共文化空間。
二、外在方式:開放型的文化空間
在西方學者查爾斯·泰勒的研究視域中,公共領域呈現為兩種形態,分別是主題性的公共空間和跨區域的公共空間。在主題性的公共空間中,公眾因共同主題而聚集在一個有形的空間,如沙龍、廣場、學校、社團等;而跨區域的公共空間則囊括了報紙、雜志等文化傳媒,呈現為無形的、想象性的共同體。民初文化公共領域的建構與學校、社團和報刊緊密相連,“從功能的意義上說,學校、報紙和結社,既是現代中國的公共網絡,也是中國特殊的公共領域。”[4]
(一)北大校園:師生聚合的公共場所
民初皖籍知識精英匯集于北京大學,追溯于陳獨秀在1917年1月13日被蔡元培聘任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當月,陳獨秀將《新青年》從上海遷往北大,《新青年》的編輯多被延聘為北大教員,他們將嶄新范式的教學理念傳播于課堂之上,沖擊了北大原有的教學體制,洗刷了學生的文化構想和學術心態。皖籍知識分子趨新化的思想潮流引起守舊文人的攻訐,如章門弟子黃季剛公然丑詆胡適,教授英國文學的辜鴻銘公開擁護帝制,但北大文化兼容的指導策略制衡了校園內的差異性信仰格局,北大的教學氛圍中既彌漫著科學民主的學風,又充斥著復古主義的道統,同時兼雜著無政府主義和文化調和論的思想,呈現出眾聲喧嘩、多元鼎立的文化態勢。在多元話語的裹挾下,北大師生自由言說,公開論辯,在紅樓形成了兩個師生互動和研討的公共空間,一是文科教員休息室,二是圖書館主任室。[5]文科教員中皖籍知識分子占有相當大的比重,蔡曉舟此時在圖書館任職,他利用職務的便利為北大師生的互動提供了公共的交往空間。皖籍知識分子積極參與公共空間中的自由辯駁,利用課余閑暇與學生相互探討,彼此激勵,建構了自治化的公眾聚合場所,營造了以對話為載體的公共性交往網絡。
(二)文化社團:協同創建的公共組織
民初皖籍知識分子以《新青年》雜志為聯結紐帶,聚合為《新青年》社團,《新青年》社團對北大學生的結社起到了引領示范的功效,學生社團活動在校園內蓬勃開展。北大學生傅斯年、羅家倫和徐彥之以《新潮》雜志為言論陣地,發起成立了新潮社。《新潮》雜志的成功發行與皖籍文人的協助密不可分。陳獨秀從經濟上支持《新潮》雜志的創辦,允諾由學校承擔雜志的辦刊經費,推薦由汪孟鄒創辦的亞東圖書館代理《新潮》雜志在上海的經銷;李辛白作為庶務主任,協助《新潮》雜志落實印刷、發行等事宜,最終確定由北大出版社負責雜志的印刷發行;在傅斯年和羅家倫的邀請下,胡適擔任《新潮》雜志的顧問,引導學生傳承《新青年》科學民主的文化精髓,創造出契合現代文體的“國語的文學”。
在皖籍教員的感召動員下,北大校園內組建了多樣化的文化社團,如進德會、新聞研究會、學術演講會、哲學研究會、成美學會、北京工讀互助團等,社團的成員不僅有各院系的青年學子,還有引領北大學風的皖籍教師。[6]1919年3月,北大學生發起組織了平民講演團,李辛白、陳獨秀、高一涵加入了社團,并親自赴往長辛店等地的工人夜校進行思想動員,宣傳反封建和自由民主的理念。民初皖籍知識分子以在場者的身份竭力支援并積極參與了社團的公共性文化活動,他們依憑學校中的文化資源和交流網絡實踐了公共領域的組織化,建構了公共領域的有形空間。
(三)《新青年》雜志:報刊傳播的公共網絡
公共領域無形的想象文化空間附載于報紙雜志的傳播策略中,皖籍知識分子編撰的《新青年》開拓了公共領域的傳播空間。《新青年》在傳播模式上,建立了有效的民間網絡發行機制。《新青年》雜志的報刊實體位于北京,發行總部定于上海的群益書社和亞東圖書館,以北京和上海為中心,陳獨秀在全國范圍內招募代派處、發行所,截至第7卷1號,《新青年》雜志在全國各埠的發行所有76個,幾乎覆蓋了全國的大中城市,不僅在文化底蘊深厚的浙江、湖北、湖南、山東、安徽等地廣泛傳播,在相對閉塞的四川、山西、甘肅等區域也獲得良好的傳播態勢。《新青年》的發行機制體現了獨特的市場營銷策略,依托代理商和經銷商建立了廣泛的銷售網絡,促進了資源的整合和信息的傳播。
在傳播語言的抉擇中,《新青年》廢棄了貴族化的文言書寫范式,運用了平民化的白話語言文體,白話文體契合了民眾的審美文化水平,使文學建構主體和審美接受主體在同頻共振中完成了文化的對接,將文學從閉塞的式樣引向開放的狀態,“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成敗始終離不開普遍開放的原則。”[1]94皖籍知識分子開辟了白話文學啟蒙的路徑,用通俗化大眾化的語言報道社會議題,在工具論視域中推動了文化公共領域的延展。
三、內在機制:民主式的倫理秩序
在公共領域中,公眾自發聚集,公開討論,自由辯駁,在對話語境中建構了開放型的交往網絡。公共領域在內部的運行機制上需遵循群體空間的倫理秩序,“合群”心理是公共領域建構的合法性基礎,公眾在共同體內部的溝通中預設了人格的平等與組織的民主。
(一)文化組織建構:合群的心理訴求
“公共領域可以理解為一個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眾的領域”[1]32,群體內部的整合團結、相互扶助是公共領域建構的本源性基礎,合群思想是公共性組織的價值源泉,提供了公共性交往的心理紐帶。民初皖籍知識分子在公共領域的組織建構上預設了“合群”的文化理念,言說出“合群”的心理期待。針對一戰期間關涉到國家存亡的對德外交問題,陳獨秀倡導“國人應群起從事于利害是非之討論”[7]11,他希冀中國加入協約國,期望借助國家的聯盟更新民族的凝滯狀態,并展望了國人相互提攜、摒棄私憤的協作場景,“南北軍人將以患難相倚,泯其畛域”[7]12。高一涵借鑒了克魯泡特金的思想,將互助視為社會進化的根源,“社會是由人類協進的本能造成的,是群眾意志合力造成的,因此,互助是社會成立的重大要素。”[8]光升褒揚了民族融合過程中“獨維系團結而不散”的優質精神資源,將“協和萬邦”奉為引以為豪的民族資本。在皖籍知識分子的視域中,人類應創建互助的組織,發揚互助的理念,聯絡文化同盟,推進民族的現代化轉型。
皖籍知識分子參與組建的社團及報刊正是在“合群互助”意識的驅動下,將分散的個體聚合為具有凝聚力的社會團體,《新青年》群體是在地緣學緣的趨同背景下得以組織創建,安徽籍和革命性成為《新青年》團體整合的身份歸因。《新青年》雜志預設了與青年共同商榷探討治國之道的文化理想,言語中滲透了“合群”觀念,體現出對群體力量的重視。新潮社以相互激勵相互支持的精神呼應了皖籍文人對文學革命的倡導,憑借著“共同前進”的意志發揮了社團的群力效應。[9]胡適與鄭陽和等人發起成美學會,號召教職員工募集資金,從經濟上資助貧困學子,劉文典、王星拱積極參與,師生共同體的意識得以強化。陳獨秀、高一涵、李辛白、王星拱參與的平民教育講演團積極開展城鄉演說,側重于聯絡底層民眾,集合勞工力量扭轉民族的頹敗之氣。民初公共領域的組織建構彰顯出皖籍知識分子“合群”的心理訴求,“合群”思想促進了文化共同體內部穩定有效的溝通,確保了成員身份的平等性和組織體制的民主性。
(二)文化空間拓展:自由的交往場域
公共領域的建構依托于開放型文化空間的拓展,在皖籍知識分子的聚合中,傳統的地緣意識、同鄉觀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隨著一校一刊的結合,初期依憑鄉誼建構的文化空間得以迅速拓展,北大校園、《新青年》雜志及胡適的私人寓所反映出公共領域在空間維度上的拓展和生活領域中的滲透。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他廣泛延攬名彥碩儒,聘請陳獨秀擔任文科學長。在陳獨秀的引介下,胡適、高一涵、劉叔雅、光升等皖籍學者被聘為北大教師,他們在校園中積極傳播自由民主的精神理念。陳獨秀大刀闊斧地整頓文科,擯棄灌輸式的教育理念。啟發學生的研究意識,增設自由選課制度,鼓勵學術團體的創立和文化刊物的出版,營造了開放活潑的校園氛圍。胡適開設《中國古代哲學史》課程,擺脫了傳統經典注疏的理路,借助考證的治學路徑系統梳理了古代哲學流派的演變,開創了嶄新的學術研究范式,震撼了北大學生的思維慣習。劉文典翻譯了赫胥黎的《近世思想中之科學精神》、《美國人之自由精神》,提倡用進化的眼光看待宇宙萬物,推崇科學的態度和自由的精神。學生深受科學民主理念的影響,積極宣揚文學革命精神,師生在校園空間中相互砥礪,彼此啟發,建立了依自由民主邏輯而運轉的文化體系。北京大學以“兼容并包”的開放氣度支持了陳獨秀與胡適發起的文學革命,維護了主體間的自由對話,捍衛了文化的自治權,排斥了外部力量特別是政治權威的干涉,在民初強權林立的語境中構建了相對自主的公共文化空間。
皖籍知識分子在革新北大陳腐風氣的同時,以《新青年》雜志為平臺,為公共討論確定題域,規約話語形態,在傳媒范疇內形塑了自由的言論空間。公共領域的生成需要具備兩個必不可少的條件,“一是公共議題,二是公共媒介。”[10]《新青年》雜志作為公共媒介,設置了眾多的公共性議題,如孔教、家族制度、青年問題、婦女解放等,鼓勵民眾對公共性文化議題進行探析研討,號召公眾自主闡述,公開刊登讀者意見,報導民眾輿論訴求,依憑自由穩定的意見表達平臺強化了議題的公共性。“文學公共領域必須有公眾的廣泛參與并就重大的社會文化議題進行公開和理性的討論。”[11]《新青年》在欄目設置上,策劃了互動式欄目,開設了“通信欄”、“讀者論壇”等交流園地,刊載讀者信件,解析公眾疑難,溝通聯絡了社會的有識階層。《新青年》的互動欄目架起讀者與編輯聯絡的橋梁,加強了閱讀公眾與報刊編輯的互動,為讀者提供了自由言談的公共空間。
隨著皖籍文人在北大學術界地位的鞏固,他們參與創建的公共空間不是局限于校園、社團、報刊,甚至擴展到私人寓所。在皖籍文人中,胡適性格溫文儒雅,平易可親,待人真摯誠懇,以非凡的人格魅力贏得時人的高度認可。在北平,胡適的住宅是知識分子重要的公共文化空間,從胡適的書信可管窺一斑。胡適在一封《致母親》的信中,提到“陳獨秀先生可于一二日內到,且俟他來一談再定何時歸里”[12]97。在《致高一涵、張慰慈、章洛聲》的信中,開頭寫道:“別后我們就睡覺了。”[12]212說明三人昨晚聚集在胡適家,高一涵與胡適曾于1918年同住北京南池子緞庫胡同,皖籍同鄉汪原放、陶行知到北京后基本居住在胡適家中,胡適的私寓成為民初皖籍知識分子的公共交往場所。每到周六,胡適家中高朋滿座,各派思想文人紛至沓來,匯聚于此,彼此交流,以對話討論的形式譏議時政,臧否人物,積聚共識,構筑了具有廣泛參與性的公共活動空間。
(三)公共輿論書寫:普泛的民眾意志
輿論是社會集合意識的外化,是公眾交融凝聚的民意,公共輿論則是群體中主導型的自發社會意見。哈貝馬斯指出“說到底公共領域是公眾輿論領域,它和公共權力機關直接相抗衡。”[1]2民初變幻的國情亂局激發了民眾對傳統政治倫理的反思和現代性價值信仰的期待,皖籍知識分子抨擊封建倫理道德,鞭撻專制思想意識,在顛覆舊秩序的同時重塑了文化體系,他們普及了現代性的價值觀念和思維取向,在文化啟蒙的視閾中闡發了公眾的輿論訴求。
針對甚囂塵上的尊孔復古逆流,陳獨秀以文學革命為民族進化的利刃,以自由平等的質素為思維驅動,將科學民主作為建構價值體系和生存秩序的有效武器,置換墮落退化的民族奴性,救贖衰頹委頓的國民精神,彰顯出與儒家傳統倫理徹底決裂的革命態勢。胡適以智性思維反對儒家的精神霸權,他將白話作為宣揚文學理念的適宜媒介和傳播渠道,希冀通過語言的變革剝奪傳統士大夫的話語霸權,拆掉民眾與文學的藩籬,實現語言表達上的民主自由,話語建構中蘊含著對傳統文學秩序的顛覆和等級意識的摒棄。基于盧梭的“天賦人權”和“主權在民”的理論,高一涵抨擊了儒家思想中的國家至上言論,要求限制國家權力的行使范圍,他在民族共同體場域中言說了國家施政的準則,強調國家存在的合法性依據在于保障國民的權利和謀求人民的幸福。民初皖籍知識分子對儒家思想、科學民主、國家體制的言說涵蓋了道德、語言、政治等諸多文化領域,涉及了民眾廣泛關注的公共性話題,碰觸了公眾亟待解決的社會癥結,以文化言說的形式在公共輿論領域訴說了公眾的欲求。
四、歷史影響:現代化的精神風標
民初皖籍知識分子在公共空間中廣泛聯絡了社會各階層,積極履行著知識分子的社會職責,堅守著民族救亡的時代精神,以公共關懷意識參與共和體制的建構。民初公共空間中的主題建構、話語形態和活動表征彰顯出皖籍知識分子民族振興的宏圖遠志。《新青年》雜志在輿論空間倡導愛國主義,號召國民凝聚力量,輯內御外;北大學生在《新青年》同人的教導下,關心時政,自覺地投入到民族建設偉業;平民講演團成員定期在鄉村、工場進行演說,啟迪了民眾的愛國意識;工讀互助團秉持互助的宗旨,以改造社會為旨趣。民初公共領域的組織建構貫穿著民族主義的主線,涵蓋了民族重塑的價值共識,契合了公共領域的文化內涵。“公共領域,關鍵要看,討論中的私人是否就其主體性的經驗達成共識。”[1]59民族救亡和國家強盛是皖籍知識分子參與創建公共領域的原動力,也是公共空間中的群體性意識。“一個人身份在某種程度上是由社會群體或是一個人歸屬或希望歸屬的那個群體的陳規所構成的。”[13]公共領域中的民族意識為空間成員的自我身份認同提供了價值依托和文化歸屬,有助于成員明確自我的歷史使命與文化責任。
民初皖籍知識分子以社會先鋒的角色參與建構了文化公共領域,他們利用公共領域合群互助、平等交流、輿論傳達的功能,積極介入社會公共事務,自覺參與國家體制建設,有效制衡了國家權力的運作,推動了自由社會的建構。民初,袁世凱和張勛妄圖復辟帝制,康有為倡導將孔教列為國教,社會彌漫著尊孔讀經的復古心態,皖籍知識分子在《新青年》雜志中抨擊孔教,從學術自由的角度顛覆孔子的意識形態權威,在進化論視域中否定孔子之道,駁斥了儒家的尊卑觀念和禮教制度,消解了儒家的正統地位,摧毀了袁氏的復辟陰謀。《新青年》雜志遷入北大后,北大學生爭相閱覽,熱烈討論,深受啟發;《新潮》社成員批判北洋軍閥的統治和紊亂的社會秩序,關注俄國、朝鮮的社會運動,當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傳入國內后,《新潮社》的核心成員發起了五四運動,引發了全國的抗議行為,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中國代表拒絕在合約上簽字,五四運動以勝利告終。民初文化青年以公共空間為載體干預現實,參與社會活動,最終影響了政府機構的決策。皖籍知識分子參與創建的公共領域有效制約了政府權力的泛濫,弱化了國家機關的強制約束力,構成了自由社會建構的體制保障和文化導向。
皖籍知識分子參與創建的公共領域呈現出自由、開放、民主的精神表征,《新青年》雜志標榜出“與青年共同商榷”的平等態度,北大青年在公共空間中自由辯論、彼此切磋,文化精英在胡適性格魅力的感召下,聚集于其住所,交流感悟,暢談理想,建構了開放型的對話空間。皖籍知識分子在公共領域建立了象征化的現代世界,寓言式地書寫了文明體制所依傍的人文理念。民主、自由、和諧是現代化國家的精神標識,民初皖籍知識分子參與創建的公共領域蘊涵著現代文明的核心質素,契合了現代化國家的價值維度,為現代化體制建設提供了精神指引。
民初,皖籍知識分子在地緣、學緣、革命意氣的牽引下聚合為自律性的文化團體,他們依托于公共性的交往媒介,建構公共領域的文化空間,在校園中組建了互動的文化社區,協助學生創建社團,參與社團的文化活動,利用大眾媒介闡發公共輿論,為公共領域的體制建構提供組織保障。他們書寫了普泛化的民族情懷,促進了國民自我身份的認同與覺醒,其在公共領域所構筑的合群互助、開放民主的價值取向昭示了自由社會的運作模式,為國家的現代化建設樹立了精神風標。
參考文獻:
[1]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M].曹衛東,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
[2]郝先中.五四時期皖籍先進知識分子群體的產生及其典型特征[J].民國檔案,2003,(3):63-65.
[3]方習文.五四前后皖籍文人的聚結與分化[J].阜陽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4):52.
[4]許紀霖.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9.
[5]楊早.清末民初北京輿論環境與新文化的登場[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169.
[6]汪楊.新文化運動與安徽[M].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4:119.
[7]陳獨秀.對德外交[J].新青年,1917,3(1).
[8]高一涵.“互助論”的大意[J].新中國,1919,1(5):22.
[9]朱壽桐.中國現代社團文學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68.
[10]方平.晚清上海的公共領域1895—1911[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60.
[11]陶東風.論文學公共領域與文學的公共性[J].文藝爭鳴,2009,(5):29.
[12]耿云志,歐陽哲生.胡適書信集(上)[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13][荷蘭]D·佛克馬,E·蟻布思.文學研究與文化參與[M].俞國強,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120.
(責任編輯 黃勝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