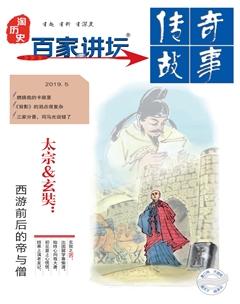燃燒我的卡路里
史小姐1O號
肥胖實在算不上什么新鮮事,因為最先提出“節食”觀念的是那群古老而飽含智慧的古希臘人。希臘哲學家和醫師希波克拉底是第一位撰寫如何攻略肥胖的人,他堅信健康的根本在于少食與多動。行走是他最為推崇的運動,他鼓勵肥胖者早餐后光著身子來回行走,走越久越好,也可從事摔跤等運動。
不過由于知識水平的限制,他的攻略我們也不可全然盡取。在當今看來極度病態的“催吐法”可是他極力倡導的,在當時甚至算是一種藝術形式。“減肥者必須一連六天逐日增加步行時間和運動量,到了第七天吃過全餐后再施以催吐。體重過重者應在中午時分催吐,催吐劑應用咸味清湯或醋,催吐前需進行奔跑或從軍等運動。”
盡管如此,以希波克拉底為代表的古希臘人的飲食法大前提是正確的——他們很清楚,不會有適用于全體人類的完美節食配方,每個人的體質不盡相同,他們所倡導的是一種清淡自律的個人生活方式和社會氛圍。
除去個人健康,古希臘人還將節食的必要性上升至哲學領域。“均衡節制是一切的根本,飲食也不例外”的觀念剛好與當時早期斯多葛學派堅韌自制的理念不謀而合。
后來的畢達哥拉斯學派則認為人體必須隨時處于掌控之中才能保持均衡,這個任務困難又漫長,最好的方式便是通過飲食來實踐。
然而,古希臘人以個人健康和社會節制為根本的節食卻在歷史行進中逐漸變了味道。到了基督教早期,節食已成為禁欲里不可或缺的一環,“貪食不像私通這種邪念,無法一勞永逸地擺脫”。
貪食作為不可饒恕的七宗罪之一,束縛著人們與生俱來的欲望。如果你以為簡單控制食量就算逃脫了貪食的罪孽,那在看過中世紀教皇之父圣額我略一世對于貪食的定義后可能會瑟瑟發抖——“吃太多,吃相不得體,飲食毫無節制,未到用餐時間便吃了起來,對飲食過度挑剔……”
這般嚴苛的罪行定義,中槍之人數不勝數,天主教神父暨哲學家托馬斯阿奎那便是其中的大拿——他因過度肥胖,去世后差點讓扶柩的人無法將他安葬。回首一生時,他字字珠璣——“享受人間的后果是穢物與肥胖,來生則是烈火與蠕蟲。”
就這樣,最初古希臘人富有真知灼見的生活及飲食計劃“diatetica”在時代中被賦予各種道德、哲學、宗教乃至人性的枷鎖。時至今日,我們依然對其理念一知半解。而現代人也因追求更快捷、流行的節食方式,逐漸忘記最初古希臘人的智慧。
古往今來,人們在與卡路里奮戰的路上前赴后繼,一個人倒下了,千千萬萬個人站起來。
19世紀英國最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萬千少女的夢中情人——拜倫,便是其中赫赫有名的節食狂魔。為了維持膚白貌美的修長身形,他幾乎天天要與叫囂的食欲抗爭。他的食量少得可憐,蘇打水配餅干是他的最愛。他甚至推掉了一頓大餐,只為嘗試將馬鈴薯在醋中浸泡的創意減肥餐。1822年,病態的過度節食已讓他染上心理和生理上的怪病,嚴重的胃病與情緒失控讓他不得不靠吸食鴉片和藥酒入睡。
時人指控拜倫和他引領的節食浪潮助長了厭食癥和抑郁癥,浪漫時期的青年們都“恐懼肥胖如夢魘”,他們不僅效仿喝醋減肥,還吃米飯以讓皮膚看起來更加蒼白。
當然,女性在這條路上狠起來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茜茜公主也是不可不提的重度節食患者。
身高172厘米的她體重只有47公斤,再穿上用鯨骨縫制的堅硬束身衣,那僅僅四十多厘米的驚人小蠻腰讓人不得不擔心她下一秒就會如火柴桿一般斷折。造型師每天都會替她測量腰圍,只要大于50厘米她就拒絕進食。因不肯進食,她不久便患上了貧血和萎黃病。然而為了調節身體,她吃得更加粗淡——兩塊餅干,一杯牛奶,晚餐只喝一碗清淡的湯。
她還越發沉迷于各種運動,暴走、騎馬、吊環、單杠……她甚至在旅途中設立隨行移動的健身房。54歲時,她的希臘文教師克里斯托馬羅在日記中寫道:“今早皇后召我至交誼廳,寢室與交誼廳間的大門敞開著,韻律繩、單杠、體操環都已就位。我看到她時,她正在拉著吊環起身……”
過量的運動和嚴苛的節食讓事情更糟了,她被診斷出厭食癥,此時的她已經“對任何食物皆深惡痛絕,什么都不愿吃了”。這個為了身材付出一切的全歐洲最美麗的女子,61歲被刺殺時還保有不足50厘米的纖腰。
這條路上從不缺用生命譜寫攻略的以身試毒者,他們大多將自己作為小白鼠的個人經驗無限推廣——所謂“王婆賣瓜,自賣自夸”。
15世紀,柯爾納羅出版了紅遍大江南北的減肥圣經《長壽的藝術》。限制卡路里攝入量的節食法本質上繼承了他的飲食原則,然而他的本意只是為了挽救自己因前40年放蕩不羈而行將就木的身體。
18世紀,法國人布里亞·薩瓦蘭是最早期低碳水化合物節食法的支持者,其著作被巴爾扎克、大仲馬奉為飲食圣經。一個大腹便便的美食家豪言提出,挨餓、低碳水、多運動是減肥的三大絕對法則。
19世紀,威廉·班廷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明確提出依靠節食減肥的書-《一封寫給公眾的關于肥胖的信》,主人公班廷通過反淀粉飲食法在一年內瘦了21公斤。一時間“我正在班廷”的熱潮席卷全球,這一熱詞不僅被新聞記者寫進《美國語言》,甚至如今瑞典語中的“jag bantar”還代表著“我正在減肥”。
19世紀后期的霍勒斯·弗萊徹是一位腦洞清奇的男子,嘗試各種減肥法都以失敗告終后,他突發奇想,將口中的食物咀嚼上百遍直到滋味全失,如此一來,或許就能避免食物在腸胃中分解的過程。
這種聽來有些荒誕的減肥法,在當時可是風靡英美上層階級,卡夫卡、愛迪生等都將其奉為“偉大的弗萊徹”。英國的上流貴族甚至舉辦咀嚼派對,并以碼表計時確保每口食物都要足足咀嚼五分鐘以上。
然而,除去這些立足于自身經驗或科學的先鋒,這條路上也從不乏一些掛羊頭賣狗肉的謀利者。
20世紀早期,一些女性靠吞食一種罐裝的易吞咽的蟲子來減肥。現在聽來簡直喪心病狂,然而沒人能抵得住減肥的誘惑,更遑論“輕松減肥”了——因為廣告上說:隨便怎么吃都不會胖,根本不用節食。
直至今天,以減肥為噱頭的各種節食方法和精心策劃的騙局更是層出不窮。無疑,持續了兩千多年的人與卡路里的斗爭還在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