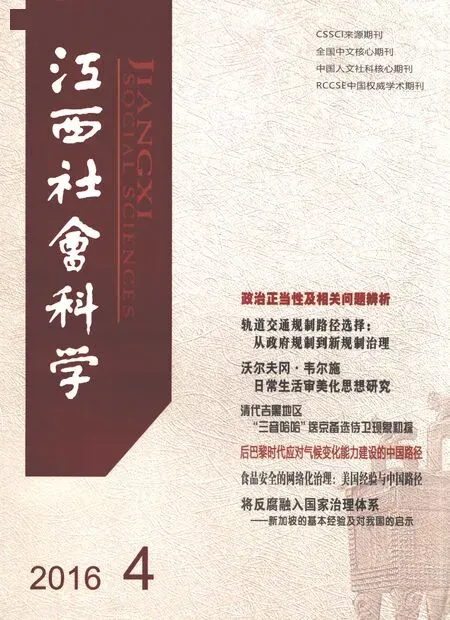認知視角下福克納與莫言作品篇名隱喻研究
■朱鳳梅
認知視角下福克納與莫言作品篇名隱喻研究
■朱鳳梅
認知視角下的隱喻觀認為隱喻不僅是一種修辭手法,更是人類認知和改造世界的方式。在認知視角下,文學作品中隱喻意象的運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家的生活背景、文化認知和精神訴求。福克納和莫言是中美文學界的重要代表人物,福克納對莫言的寫作手法尤其是隱喻手法有著深刻的影響。比較兩位作家代表作品篇名中的隱喻,可以發現,福克納與莫言在運用作品篇名隱喻抨擊社會現實、寄托鄉戀鄉愁方面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兩位作家以隱喻為紐帶,穿越時空,跨越國界,向世人揭示“面具”背后的深意,令世人領略文學意境的震撼。
福克納;莫言;隱喻;作品篇名
朱鳳梅,寧波大紅鷹學院人文學院講師。(浙江寧波 315175)
一、引言
認知語言學認為隱喻是一種思維方式,也是人類認知和改造世界的方式。語言文字是人類的一種思維創造,文學中的隱喻運用不能脫離人對世界的認知而產生。因此,文學作品中的隱喻反映著作家的認知心理,與作家生活背景、成長環境和精神訴求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莫言是一位善于運用隱喻手法的鄉土文學作家。2012年,他以《蛙》為代表作,憑借“將魔幻現實主義與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社會融合在一起”的寫作造詣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的作品主要是以故鄉農村為敘事背景,反映當地風土人情的鄉土小說。在充滿鄉土氣息的背景之下,莫言用其獨特的寫作風格達到反映風土民情,表達鄉戀鄉愁,批判老舊制度,懲惡揚善等創作訴求。莫言在 《兩座灼熱的高爐》中曾表示他1985年撰寫的作品在思想上和寫作的藝術手法上都受到了外國文學的極大影響。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是對他寫作產生影響的一部重要作品。[1](P298)莫言曾撰寫《說說福克納老頭》一文紀念福克納先生誕辰一百周年,文中提到他在沒有接觸福克納之前對作品《透明的紅蘿卜》中打破常規的描寫忐忑不安,但在閱讀福克納作品的時候他變得無比堅定,他仿佛聽到福克納鼓勵他:“小伙子,就這樣干。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讓鮮紅的太陽照遍全球!”[2](P289)莫言在自己書的序言中也以福克納的學生自稱,他還提到福克納小說對他的震撼和沖擊以及對他文學創作的深刻啟發。
縱觀福克納和莫言的代表作品,行文筆墨中高頻使用隱喻手法,達到潤色文字、提高表達效果、渲染小說主題等多重作用,也有學者將福克納作品中的隱喻比喻為“面具”[3](P5)。隱喻在他們作品篇名中的運用更是比比皆是。無論是用中文或是英語創作,隱喻手法的深入運用為文學作品蒙上了神秘的面紗,等待世人揭示。與此同時,隨著認知語言學的不斷發展,認知視角下透視文學作品中的隱喻有助于更好的揭示作品主旨,剖析作家的創作風格。
二、認知視角下隱喻在文學作品中的運用
“將魔幻現實主義與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社會融合在一起”是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詞,這一評價表現出莫言傳奇魔幻式的語言有較高的文學價值,而無處不在的隱喻正是這一特色語言的重要組成元素。沒有隱喻的運用,莫言的作品主題和風格就不能得以淋漓盡致地展現。
兩千多年前隱喻理論中的亞里士多德學派觀僅將隱喻視作一種修辭手法,是文字的一種修飾,其作用是生動貼切地展現事物的特點,提升文字的表現力。19世紀英國浪漫主義詩人們所提出的柏拉圖學派觀則認為隱喻是一種語言內部的機制,既反應了語言的本質,又反映了人的本質。20世紀的學者們繼承和發展了上述兩大學派的觀點。20世紀80年代,在萊考夫和瓊斯的著作《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出版之后,人們意識到隱喻的本質是 “通過一事物來理解和體驗另一事物”。[4](P8)隱喻的機制是從源域通過映射到達目標域,從而完成從已知到未知的過程。
隨著認知語言學的不斷發展,隱喻的普遍存在性不斷為人們所意識。隱喻思維能力是認知能力的產物,前者受后者發展的制約。文學語言中的隱喻基于作者認知世界的能力,作者對隱喻意象的駕馭能力受自身生活環境、人生閱歷及其對世界認知程度的影響。文學隱喻能幫助作者通過隱喻機制呈現意象,烘托主題,形成寫作風格。文學隱喻雖然與普通隱喻基于同樣的機制和圖式,但文學語言能更多地表現語言的形象性與文藝性。故而,認知視角下文學隱喻的機制簡單圖示如圖1:

圖1 文學隱喻機制圖
文學隱喻通過普通隱喻發展成為更富深刻含義的表達,創作者需要具備獨特的對事物的洞察力和較高的表達技能,讀者也要有較深的感知能力。一個個隱喻就是一張張神秘莫測的面具,被文學創作者們通過巧妙的運用為文學語言提供超出其本身含義的思想感情,從而揭示出文學藝術的內在意味和深層意蘊。
三、福克納與莫言作品篇名隱喻的功能分析
福克納和莫言作品篇名中為烘托主題而采用隱喻意象的運用有較大的相似性,他們在篇名中運用隱喻抨擊社會現實,寄托戀鄉情結,表達人生感悟。
(一)以隱喻抨擊社會現實
福克納和莫言都善于運用動物意象服務主題烘托,賦予所選取的動物意象以深刻的隱喻含義,從而映射社會現實。兩位作者都直接采用動物意象作為小說篇名,在全文中深入骨髓的剖析其隱喻含義,達成自己的寫作目的。
福克納的《熊》是一個描寫人類狩獵的生動故事。文中有一只大熊名叫“老班”,它體形碩大,力大無窮,但最終被槍法拙劣、只能捕松鼠的布恩所殺。布恩殺熊是對人類的無聲控訴,隱喻了人類盲目、魯莽行為對自然造成的摧毀和破壞,表達了福克納對人、自然和社會的思考。而老熊的隱喻含義還遠不止如此,它是大自然的象征,是自然法則的遵循者,它沒死在技藝超群的艾克手中,反而倒在了布恩的面前,隱喻著自然界物競天擇的不變法則。福克納將熊的形象在整部小說中創作成一個凝聚的靈魂,將對人類的控訴無聲地傳遞,也將自然的法則通過布恩屠熊悄然卻又擲地有聲地展現。讀過福克納的人會發現小說《熊》是他對人類焦慮的一種表現,是他創作訴求的一個轉折。從原先執著地在現實中做痛苦掙扎轉而進入一個新的創作時代,他思考人性、道德與自然。文中主人公艾薩克·麥卡斯林的成長和思考也正是福克納對現實的思考,對世界的認知和對自己精神訴求尋找的一種映射。
莫言也不乏以動物意象為源域映射社會現實的作品,《蛙》便是其巔峰之作。故事講述計劃生育工作者“姑姑”早期作為迎接無數生命的醫務工作者和后期成為扼殺無辜生命“劊子手”的經歷。小說蘊含大量的隱喻,巧妙地表達作者對人性、人權和社會制度的態度。全文最大的隱喻就是“蛙”:蛙生命力旺盛,隱喻早年實行計劃生育之前,農村子嗣繁衍生生不息的景象,映射蛙無限的生命力;而蛙與女媧的 “媧”和娃娃的“娃”諧音,隱喻“姑姑”扼殺無辜生命的愚昧和殘忍,同時也通過“姑姑”這一角色表達作者對中國計劃生育的斥責及無奈。晚年的姑姑走過一片稻田,聽聞蛙聲一片,隱喻被“姑姑”扼殺的娃娃們對其的控訴,而“姑姑”為自己一生的行為無聲地后悔自責。貫穿全書的隱喻讓人在閱讀小說的過程中唏噓不已,覺得既玄幻又真實,是“蛙”隱喻讓這部作品得以成形,也是“蛙”隱喻及其他的隱喻(如書中人物姓名的隱喻)成就了作品的藝術價值。
兩位作家雖然身處不同的時代,但受到文化環境和社會現實的觸動,卻同樣是從篇名到故事主線都采用了動物意象隱喻折射自己的思考和認知。熊和蛙穿越時空共同控訴著人類破壞生態自然的愚昧無知。除了動物意象,福克納和莫言也擅長采用時間或者事物作為作品篇名,用其隱喻含義折射作品主旨。此時的時間或者事物不再單純,它們成為有精神、有靈魂的隱喻,映射向作者希望讀者所感知的世界。
《干旱的九月》是福克納1931年的作品,故事圍繞發生在杰弗遜小鎮上的一起謀殺案展開。傳言小鎮上的黑人威爾·梅也斯強奸了白人老處女明妮·庫柏。因此,黑人威爾在九月的一個黑夜被麥可蘭登為首的暴徒殺害。但是,威爾是無辜的,所謂的強奸是明妮的一種臆想。這個故事蘊含多種隱喻意象,如流言、塵土等。秉承一貫風格,小說題目“干旱的九月”也有其深刻的隱喻含義,映射著主旨。九月的源域是一年中的第九個月,根據人們的認知,九月的秋季蕭瑟、悲寂、衰敗,“干旱”的九月是生命枯竭的悲劇意象。就在這個九月的夜晚,黑人威爾被冷血無情地殺害。福克納以《干旱的九月》為題,為全篇籠罩一層悲劇的面紗,單看題目,便讓人對全文的悲劇基調有所預測。
莫言善于運用事物為隱喻的本體,如 《枯河》、《紅樹林》、《白棉花》。1988年,基于真實故事,他以“天堂蒜薹之歌”為篇名,為大家呈現了一部反映社會底層弱勢民眾生活疾苦的優秀作品。故事中的天堂縣村民受到政府鼓勵大規模種植蒜薹,結果大量蒜薹滯銷,民眾被激怒,圍攻鄉政府,最終引出了一連串的如“方四叔車輪下慘死”和“金菊上吊自殺”的悲劇。蒜薹是一種十分常見的作物,正如小說中的小金菊、方四叔、方四嬸這些社會底層農民一樣普通。圍繞蒜薹展開的事件及最終導致的悲劇讓人感嘆底層農民文化水平低,思想落后的無奈生活狀態。而莫言采用的天堂蒜薹之歌隱喻預示著人們的悲慘結局,讓人似乎聽到了平常百姓被命運主宰,被文化水平所限,悲傷且無奈的哀號。
無論是通過福克納的“熊”、“九月”,還是莫言的“蛙”、“蒜薹”,人們看到的絕不是純粹的一個個實體,其淺顯的外表下隱藏著作者對社會現實、民眾惡習的一種抨擊和鞭撻,表達著作者通過文學作品傳遞的訴求,彰顯著他們作為作家的正義和良心。
(二)以隱喻寄托鄉戀鄉愁
老作家伍德·安德森曾啟發福克納:一個作家必須要有一個地方作為起點。因此,福克納虛構的“約克納帕塔法縣”成了他故事的源泉,他以隱喻的手法創造出在這片土地上發生著的一個又一個生動而又離奇的故事。莫言在讀了福克納作品后意識到他應該高舉起“高密東北鄉”這面大旗,把那里的一切寫進他的小說,創建一個屬于他的文學共和國。[2](P289)于是,“高密東北鄉”成了莫言的文學創作根據地,它不再局限于一個地理概念,其外延擴展為一個文學空間。莫言和福克納作品都以特定的時空為起點,借由隱喻的篇名寄托他們對自己故鄉的依戀或對過去時代的紀念。
福克納1930年的作品 《獻給艾米莉的一朵玫瑰》講述的是守舊、傲慢的美國南方沒落貴族艾米莉在父親死后殺害自己的情人,與尸體為伴終其一生的悲劇故事。通常在文學作品中,玫瑰是愛情的象征,美好而又令人向往。但是,福克納筆下獻給艾米莉的玫瑰卻被渲染上了沉重的民族和時代特色,產生一種讓人揪心的震撼。美國南北戰爭之后,奴隸制被廢止,美國南方權貴的生活日趨沒落。在父親死后,艾米莉的生活每況愈下。她渴望愛情,卻不能品嘗愛情的甜蜜,最后毒害自己的情人,以將其常留身邊。她是人們眼中舊南方的一個豐碑,她在經歷病態的愛情和生活后倒下了。在她死后,每個人向她敬獻一朵玫瑰花。此時的玫瑰花隱喻了太多的情感,有艾米莉對愛情的執著追求,有南方沒落貴族對舊制的緬懷和追思,也有男人們對艾米莉這一舊南方淑女的扼腕紀念。這朵玫瑰花意味深長,仔細品讀,由于作者賦予它的特殊隱喻含義,它是黯淡的。它緬懷南方舊制時是灰色凋零的,它在艾米莉死后被人發現毒殺情人時甚至是黑色死寂的。福克納的玫瑰隱喻讓人刻骨銘心,無法忘懷。
幾十年后,莫言賦予了黃土地人民賴以生存的食糧“紅高粱”以深刻的隱喻含義。《紅高粱》以抗日戰爭為背景,講述了奶奶九兒的一生。那一片紅燦燦的高粱地是奶奶和爺爺余占鰲的定情之地,紅高粱被爺爺做成天然的婚床。日本侵略者征地修路時期,踐踏了整片的高粱地,奶奶九兒設計復仇,最后中彈犧牲。此時的高粱地雖然被毀滅了,但它們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抗日激情。最終,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后的“和平”時期高粱地的廢墟上種起了雜種高粱。可惜,“我反復謳歌贊美的、紅得像血海一樣的紅高粱已被革命的洪水沖擊得蕩然無存。”[5](P304)這一片紅高粱有著深刻的隱喻含義:高粱倒了隱喻著封建舊習的破壞,代表著性和自由的解放;那不朽的紅色謳歌了九兒與命運和日本侵略的抗爭精神;它的衰敗則隱喻了那一去不復返的過往——封建的舊制和抗日戰爭。
《紅高粱》的創作似乎讓人們看到了美國南方文學的影子。美國學者謝柏認為《紅高粱》讓人們聯想起一種美國南方文學類型,因為兩者都能產生道德廢墟與舊日美德的反差,“只有在作者被迫回望無法尋回的過去,預想似乎無法忍受的未來時,南方文學才會呈現出一種肅穆與壯麗。”[6](P26)同樣是用最具鄉土人情的事物映射社會的現實,玫瑰花和紅高粱隱喻了人們對過去一個時代的追思,也暗示著人們對過往一去不復返的無奈。
此外,福克納和莫言也都致力于運用童年對故鄉人和事的記憶創作文學作品,作品的篇名蘊含深刻的隱喻含義,表達他們的鄉戀與鄉愁。
福克納的故鄉情結不僅寄托他對美國舊南方時代的哀思,更多的是表達他對故鄉美好過往和昔日輝煌和榮耀的追憶。小說《八月之光》正是隱喻其念念不忘的每年八月故鄉讓他感受到的神秘感覺。1957年,福克納在弗吉尼亞大學演講時對《八月之光》的涵義做了陳述,他提到在密西西比州的八月中旬會有幾天突然出現秋天即至的跡象:“天氣涼爽,天空里彌漫著柔和透明的光線,仿佛它不是來自當天,而是從古老的往昔降至,甚至可能有從希臘、從奧林匹克山某處來的農牧神、森林神和其他神祗。”[7](P199)這種天氣雖然短暫,但是每年的八月必然如約而至。對福克納而言,《八月之光》能喚起他久逝的兒時記憶,引起他無限遐想,并能讓他領略那比基督教文明更古老的透明光澤。小說最主要的線索是莉娜懷著身孕尋夫的歷程,隱喻 “大地母親”的形象。這個引人遐想的篇名融入了其對故鄉的記憶,故事主線雖然有悲劇色彩,但表達的確是作者認為“人生中總有曾經榮耀的時刻”的樂觀信念。
反映莫言故鄉情結的作品也不勝枚舉,在那《紅高粱》和《白棉花》蓬勃生長的“高密東北鄉”,有著《豐乳肥臀》的母親和“貓腔”演繹出的《檀香刑》,有時也會“爆炸”《球狀閃電》和《四十一炮》。[8](P3)其中最具爭議的一部就是1995年出版的《豐乳肥臀》。作品篇名給人粗俗的印象,但這本書并不是想象中描寫性愛的小說。莫言說:“《豐乳肥臀》里邊有比較多的我的人生體驗和故鄉、家族等原始素材,是對自己進行清算的一種寫作方式。”[9](P432)篇名“豐乳肥臀”隱喻的是母親的形象,而全文的情節更多的是讓人對母親這一形象產生敬仰,甚至是對其代表的孕育人,乃至整個民族的崇高價值膜拜。
福克納和莫言的鄉戀情結從他們各自創設的“約克納帕塔法縣”和“山東省高密縣東北鄉”這兩個文學地標中可見一斑。在那片土地上,有著福克納對美國南方貴族沒落的追思,對童年記憶中那模糊而又清晰的八月之光的追憶;也有著莫言對那一片紅高粱地的泣血謳歌和對偉大母親的深深依戀。莫言表示在福克納的鼓勵和引領下,他建立的這片精神家園讓他有了表達鄉愁的無盡源泉。認知視角下的文學隱喻有著神奇的魔力,讓福克納的作品看似怪誕,卻寓意深長,讓莫言的作品以魔幻的方式折射最真的現實。
四、結語
隱喻是作家語言創造、思想表達的重要手法。認知視角下的隱喻觀能較好地闡釋作家認知和思維影響下的源域向目標域映射的機制,換言之,它能幫助讀者較好地理解文學作品中隱喻的運用背景和使用目的。福克納作為美國文學的代表之一,鍛造豐富的隱喻意象,使其與作品的主題完美契合,成功創造了諸多佳作。莫言也是一位獨特的作家,他總能出其不意,作品的隱喻意象鬼斧神工。兩位作家將對各自生活時代的認知,對社會現實的思考幻化為層出不窮的文學隱喻,寓意深遠,且他們在運用篇名隱喻烘托小說主題,抨擊社會現實和表達鄉戀鄉愁的方式上極其相似。這種相似是文學世界中的一種無聲的影響和傳承。莫言看到福克納畫像時曾說:“我多次注視著這幅照片,感到自己與福克納息息相通。”[2](P290)而兩位文豪在不同歷史時代的一個重要維系就是隱喻手法,它像一張“面具”,對作品意象的凸顯,主題的烘托和作家精神訴求的表達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大大提升了文學作品的內涵和藝術價值。
[1]莫言.兩座灼熱的高爐[J].世界文學,1986,(1).
[2]莫言.莫言作品精選[M].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 2013.
[3]Lothar Honnighausen.Faulkner:Masks and Metaphors. Mississippi: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7.
[4]Lakoff,G&Johnson,M.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5]莫言.莫言文集·紅高粱家族[M].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3.
[6](美)謝柏柯.高粱地廢墟與民族式微:文學與電影中的《紅高粱》[J].盧文婷,譯.張箭飛,審譯.長江學術, 2014,(3).
[7](美)F·格溫,J·布洛頓.福克納在弗吉尼亞大學演講錄 (1957—1958)[M].里士滿:弗吉尼亞大學出版社, 1959.
[8]朱賓忠.跨越時空的對話——福克納與莫言比較研究[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
[9]莫言.莫言對話錄[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2010.
【責任編輯:張 麗】
I1
A
1004-518X(2016)04-0081-05
浙江省教育廳科研項目“認知視角下福克納與莫言作品中隱喻的對比研究”(Y201329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