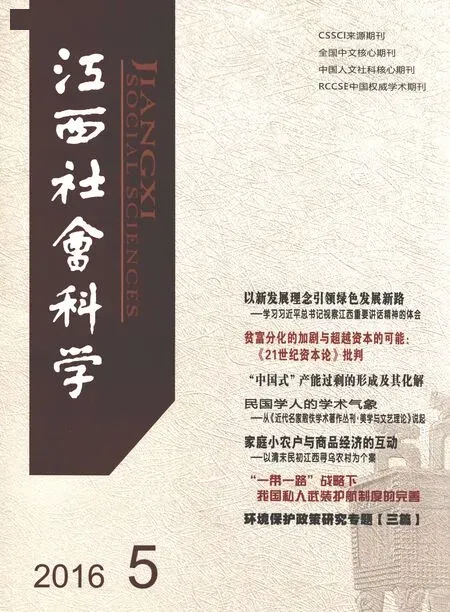“中國式”產能過剩的形成及其化解
■王秋石 萬遠鵬
“中國式”產能過剩的形成及其化解
■王秋石 萬遠鵬
在國內外文獻中關于產能過剩概念的區別與聯系的基礎上,本文厘清了“中國式”產能過剩的內涵,認為其與國外所述的產能過剩現象存在巨大差別,是中國特有的經濟現象。它的形成、惡化與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中央與地方政府經濟行為的利益博弈、地方政府與當地企業的利益博弈關系相互關聯,因而化解它需要從重建政府與市場及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兩方面關系入手,要點是不斷推進市場化改革和政府轉型。
“中國式”產能過剩;政府行為;市場與政府關系
王秋石,江西財經大學副校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萬遠鵬,江西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生。(江西南昌 330013)
“產能過剩”可以說是國內研究的焦點與熱點,一直備受各方高度關注。大部分學者認為當前中國存在著“產能過剩的頑疾”,但我們發現在國外的主流經濟學文獻論述中,對產能過剩這一現象本身并沒有太多的關注,甚至并沒有把它看作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因而國外文獻中并沒有具體的針對治理產能過剩的對策與建議。國內外文獻對待產能過剩這一問題的巨大反差,不禁使我們反思與懷疑,國外文獻中所論述的產能過剩問題與中國當前面臨的產能過剩問題是否是同一概念。因而,本文試圖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形成“中國式”產能過剩的理論內涵,并深究其特殊的形成機制,進而提出化解“中國式”產能過剩的建議。
一、“中國式”產能過剩的內涵
一般認為,國外最早論及產能過剩的經濟學家是E.Chamberlin[1],他將產能過剩描述為“過剩的生產能力”,并把它看作是壟斷競爭市場的主要特征,他認為產能過剩是“競爭的浪費”,也是市場產品多樣性所必須付出的代價,籠統地說,產能過剩反映的是某一種產品在一定時期內的最大產量(產能)與實際產量之間的差距。從這個角度上看,國內外產能過剩的概念有一定的相似性,其描述的都是產能與實際產量或需求量之間的差距,只不過國內學者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按照產能超過實際產量的程度,將產能過剩細分為適度的產能過剩與嚴重的產能過剩。嚴重的產能過剩指的是一定時期內,某行業的實際產出數量在一定程度上低于該行業的生產能力的狀態,并且這種程度超過了行業的正常水平范圍,而未達到這一程度的實際產量與最佳生產能力之間的差異定義為適度的產能過剩或產能閑置。適度的產能過剩是推進企業競爭力和產業結構升級的最為重要的推動力,它的存在不可避免,我們應允許它的存在,需要予以化解的是形成實際產品積壓的嚴重的產能過剩。
(一)國內外產能過剩概念的區別
1.產能過剩的界定標準不同。由于國外文獻主要集中于對產能和產能利用率的測算,很少有直接論述產能過剩概念的文獻,因而國外文獻中對產能過剩的界定大部分是從產能或產能利用率的概念界定中延伸的,如Kirkley,Paul, Squires[2]把產能利用率(CU)定義為通常觀察到的實際產出y與產能(產出)Y之比,所以CU=y/ Y;如果產能利用率小于1,就說明存在產能過剩。從產能的角度上看,國外學者們主要將產能分為工程產能、經濟產能[3]和技術產能[4],若從工程產能概念出發,產能過剩即為某一生產廠商生產設備的設計生產能力與其實際產量之間的差異;若從經濟產能概念出發,產能過剩即為某一生產廠商成本最小化或利潤最大化時的產量與實際產量之間的差異;若從技術產能概念出發,產能過剩即為某一廠商運用可用的投入要素所能達到的最大、最優或潛在產出與實際產量之間的差異。
反觀國內文獻,主要是從產能過剩的成因及其造成的不良影響方面對其進行界定,從產能過剩的成因上看,如王立國[5]認為,重復建設是導致中國產能過剩最直接的原因。周勁、付保宗[6]認為產能過剩的形成與經濟周期相關,將產能過剩分為“周期性產能過剩”和“非周期性產能過剩”兩類。前者是指由經濟周期波動所形成的,后者是指在非經濟周期波動形成的產能過剩,從產能過剩造成的不良影響上看,學者們一致認為當產能超過生產量或消費量達到一定程度,且對經濟運行產生的負面效應超過了正面效應即出現了產能過剩現象。
2.產能的界定標準不同。國外研究通常將產能分為工程產能、經濟產能、技術產能與經驗產能,并假定企業會選擇生產能力最大的設備,因而所得到的產能利用率都較高。與發達經濟體不同,在中國由于存在多種非市場因素的影響,落后產能普遍存在。因此,工程產能的技術有效性假以及經濟產能的企業生產成本最小化或者利潤最大化假設可能并不適用于分析中國的產能過剩問題。同時,經驗產能因缺乏廣泛而規范的企業調查也不適用。因而,技術產能可能更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從定義上看,它指的是企業擁有的固定資本存量被用來購置生產能力最大的設備并且這些設備達到充分利用時的生產能力,這里把當前中國存在的大量落后產能對生產資源造成的浪費也放在考慮中。
3.產能過剩的成因不同。大部分國外學者易把產能過剩的形成與市場因素聯系在一起,主要可以歸結為市場競爭、市場不確定性以及市場結構的影響,總的來說,他們認為過剩的生產能力是壟斷競爭市場上各廠商共同競爭的結果,它可以在長期內得到發展卻免于懲罰,價格總能包含成本,造成產能和產量之間差距的最重要的原因是由這些行業自身的特點決定的,他們的產品供給彈性很低,產量的大幅度上升不僅需要增加人工、原料等可變成本,而且需要大量的資本投入,包括增加設備、生產技術改造等,因而這類企業在發展過程中普遍存在著相對充足的產能[7],或者說是“產能過剩”,以應對需求的突然增長,且低集中度[8]的市場結構中這種現象最為明顯。
然而,國內產能過剩卻主要源于非市場因素,如國內經濟增長方式、體制機制改革的滯后等。同時,這些非市場因素的存在又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市場的供給與需求狀況,使得行業產能利用率指標并沒有呈現出與經濟周期的波動相關的變化,進而形成“結構性產能過剩”與“體制性產能過剩”[9]。
4.產能過剩造成的后果不同。由于政策部門關注產能過剩對整個經濟市場造成的影響,因而大部分國內學者立足中國實際,緊扣產能過剩對宏觀經濟運行的不利影響來對產能過剩進行分析與研究,這些負面影響可以概括為企業經營狀況的惡化,具體表現為設備利用率低、產品庫存增加、企業利潤減少甚至虧損等,并進而對整體經濟產生危害。相反,國外文獻對產能過剩的后果卻論之甚少,大部分國外學者們都將產能過剩的形成看作是為產品多樣性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因為它的產生一定伴隨著商品的多樣性,因而它的出現不言而喻地證明著,社會公眾從某種程度上來講,相對于低廉的產品,更偏好于產品的多樣性。
(二)“中國式”產能過剩的界定
瞿東升[10]曾指出,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目前在鋼鐵、建材、造船等傳統行業以及光伏、風電設備制造業等新興產業出現的嚴重產能過剩可謂“中國式”產能過剩。這種產能過剩具有以下幾種特征:一是“一哄而上”,目前的過剩產能都是最近幾年所在行業井噴式增長形成的,這種產能過剩因其來勢迅猛、產能適度期短,給社會和企業造成的危害相比國外發達市場經濟國家更大;二是“火上澆油”,我國一些企業在產品市場需求疲軟和價格下跌情況下,仍然貿然擴能、進入;三是“垂而不死”,主要表現在我國一些企業技術水平低下,在市場競爭中已處于被淘汰的境地,但由于地方政府或母公司的市場保護、補貼等因素,總能強撐著生存;四是“過剩與不足”共存,過剩的都是中低端產品的產能,高技術、高性能、高附加值產品不但不能滿足國內市場需要,反而還要依靠進口。陳剩勇、孫仕祺[11]認為政府權力獨大、一把手擁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機制,以GDP為主要指標的政績考核與官員升遷機制,以及由此種激勵機制激發的地方政府之間的政績“錦標賽”,直接造成了中國式的產能過剩以及中央政府宏觀調控的失效。
綜上所述,國內文獻與國外文獻對于產能過剩這一概念的界定存在著巨大的差別,中國的產能過剩有著與國外的產能過剩不同的特征與本質。因而,本文將“中國式”產能過剩界定為:在中國特有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由于政府直接或間接地干預經濟而造成產能超過需求量達到一定程度,且對經濟運行產生嚴重的、難以化解的不良結果的經濟現象。“中國式”產能過剩是大量落后產能的產能過剩,是中國特有的經濟現象,主要表現為結構性產能過剩與體制性產能過剩,前者是由于長期技術創新乏力、經濟增長不足,而造成的低端產品供給嚴重過剩而高端產品供不應求的產能過剩現象;后者是由于政府過多介入和干預企業投資決策所導致的企業過度投資的產能過剩現象。
二、政府經濟行為與“中國式”產能過剩的關聯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決定了“中國式”產能過剩的主要特征
在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國家,市場發揮著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且有著相對完善的價格信號及價格形成機制,企業面臨著真實成本以及市場優勝劣汰的競爭壓力,在這種成熟的市場環境下,很少存在過剩產能與落后產能。而中國目前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夠成熟,且存在許多計劃經濟時代所遺留的體制弊端與思維定式,因而存在著大量的結構性產能過剩與體制性產能過剩。
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當前中國政府尚未建立行業產能利用率的監測預警機制,使得企業沒有辦法完全掌握市場信息。再加上,“中國式”企業的不成熟,對市場的殘酷性認識不足、盲目樂觀,從而導致市場中產能過剩愈演愈烈;其次,在中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過程中,體制改革不夠徹底,使得中國計劃經濟時代所遺留的體制弊端與思維定式仍存在于經濟運行中,地方政府與企業“重速度與數量,輕質量”的傳統計劃經濟思維根深蒂固,因而使得“一擁而上”式的投資擴張行為大量存在;再次,中國政府為實現特定的政策目標,通過其所掌握的各項要素的定價權或定價影響能力,扭曲市場生產要素價格,從而影響企業的投資方向,進而造成大量的體制性產能過剩。
(二)“中國式”產業政策是“中國式”產能過剩的導火索
1.“中國式”產業政策。產業政策通常指的是一國政府為了取得在全球的競爭能力,在其國內推行的發展或限制某類特定產業的政策總稱。一國設計和實施產業政策的初衷,都是為了提升經濟發展質量。但中國由于分權治理模式的存在,使得中國的產業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延續了計劃經濟時代的色彩,是典型的“中國式”產業政策。“中國式”產業政策最為明顯的特征即是政府在產業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以政府自身的判斷和預測來替代市場機制,進而直接或間接地干預市場經濟主體的投資決策。
具體可從中央政府經濟行為和地方政府經濟行為兩個角度進行分析:從中央政府經濟行為角度來看,主要表現在中央政府在制定產業發展戰略、產業政策及相關的化解“中國式”產能過剩的建議時用大量行政手段替代市場機制發揮作用。從地方政府經濟行為角度來看,由于地方政府同時面臨著政治晉升的激勵和市場發展水平的約束,從而使得地方政府在落實產業政策時行為易受扭曲,這不僅會使得其與政策預期目標相去甚遠,更會造成大量的企業過度投資,從而加重“中國式”產能過剩。
除此之外,“中國式”產業政策還具有很強的限制競爭的特征。最具代表性的“中國式”產業政策是2009年初制定的十大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雖然該項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使得我國在國際金融危機的背景下仍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但不可否認的是,它也是我國目前國內大量的產能過剩,尤其是鋼鐵等重化工業行業的產能過剩的導火索。
“中國式”產業政策的行政干預性特征主要表現為部分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中明確規定不再核準新建或擴建項目,且規定所有項目都必須以淘汰落后產能為前提,而且淘汰落后產能必須依靠行政手段進行。如《船舶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有色金屬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鋼鐵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等。“中國式”產業政策的限制競爭特征突出表現在《鋼鐵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中,規劃中明確指出:“力爭到2011年,全國要形成寶鋼集團、鞍本集團、武鋼集團等幾個產能在5000萬噸以上、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特大型鋼鐵企業;形成若干個產能在1000萬~3000萬噸級的大型鋼鐵企業。”
2.中央政府化解產能過剩的宏觀調控措施。近幾年,面對產能過剩,中央和相關部門都非常重視,提出了許多指導意見。國務院2006—2013年公開發布了4個關于化解產能過剩、淘汰落后產能的通知意見(表1)。

細究2006—2013年中央關于化解產能過剩的指導措施,可以發現措施逐漸變得嚴格,不管是從嚴格的市場準入到更為嚴格的核準審批制度,還是從嚴控新項目到嚴禁建設新增產能。這不僅可以看到產能過剩現象愈演愈烈,同時也反映出政策效果并不顯著。2015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更是把“去產能”作為五大結構性改革任務的重中之重。
因此,有必要反思一下相關指導思想與做法。首先,政府仍然以自身對市場供需的判斷以及未來供需形勢變化的預測為依據來制定相應的產能投資控制措施,核準審批的管法是否能管得住企業擴張?從結果來看,管住了膽小的,管不住膽大的。同時,核準審批易形成“圍城效應”,即圍城抵擋城外者的同時,保護了城里的。因此,城外者極力沖破城門,進來后積極擁護把城門關嚴實,防止城外者進來分享待遇。反過來想,若沒有這個圍城,一部分城外者并不一定會進入城內區域。目前一些競爭力強、市場占有率高、產能適度的產業并沒有嚴格的準入限制,反而是存在核準審批制度的產能過剩行業產能過剩較為嚴重;其次,一些調控措施助長了產能過剩,如為了推進企業兼并重組,一些地方和部門推行的“大魚吃小魚”做法,使得企業爭相擴張產能。
(三)地方政府經濟行為是“中國式”產能過剩的催化劑
改革開放后,黨和政府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建立了以考核GDP增長為主要指標的政績考核體系,以及基于政績的官員晉升機制。這種激勵機制使得地方政府(官員)在任期的限制下,更傾向于追求短期經濟增長,并引導或縱容企業選擇促進規模擴張的發展戰略。具體來講,地方政府有干預企業生產的動機、能力和手段。地方政府干預企業生產的動機可以分為經濟動機和政治動機,經濟動機就是希望轄區內經濟總量、稅收水平、就業率越高越好,政治動機就是希望在地方政府間的橫向競爭中,比其他地方政府獲得相對靠前的位次,而獲得政治晉升的機會和空間[12]。
實際上,在中央GDP考核指標刺激下,地方政府的經濟動機也是為其政治動機服務的。地方政府之所以具有能夠干預企業生產的能力,主要源于我國土地產權模糊、環保產權模糊、財政預算軟約束等,使得地方政府可以利用手中所掌握的行政資源和生產要素資源引導企業投資,從行政資源上看,一是政府擁有對企業生產經營活動廣泛的審批和檢查權,企業能否設立、設立以后能否開業、開業以后能否正常經營、經營能否獲利都與政府活動相關聯。如著名的江蘇常州“鐵本事件”,即是地方政府及官員為了地區財政收入和政治升遷,不惜與企業共謀,規避國家的法律、法規和相關的產業政策的典型案例;二是地方政府會以多種形式對企業予以財政補貼,如設立“產業發展基金”“技術改造資金”“銀行貸款貼息”等;三是在稅收方面提供優惠。
從生產要素資源上看,為了鼓勵地方企業投資,政府會以低價或優惠政策為企業提供生產經營活動所需要的生產要素,極大地降低企業生產成本和自有資金投入比例,利誘企業進行遠超過自身的投資能力和經營管理能力的過度產能投資,進而造成大量的“中國式”產能過剩,主要概括如下:
一是土地資源。土地是企業生產所必需的基礎性生產要素,也是地方政府手握的一張王牌。因而各地政府常以遠低于實際土地價值的價格或零地價向企業供地,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陳錫文在2012年的一次講話中指出:“當年公布的土地價格,每一平方米的商業和服務業用地價格為5700元,每平方米的住宅用地為4500元,而每平方米的工業用地的價格僅為659元。每平方米工業用地價格只相當于商業和服務業用地價格的11%,相當于房地產用地價格的14%。”
二是能源資源。在鋼鐵、電解鋁等制造業的生產過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的水電,地方政府為了鼓勵該類企業投資生產,通常會出臺電價、水價的補貼政策,如貴州省某市出臺的《2013年工業企業虧損補貼和用電補助方法》中,提出對全市規模以上的電解鋁、工業硅、電解錳、鐵合金、高碳鉻鐵、中低碳錳鐵、電解二氧化錳等行業,企業按0.03元/千瓦時實施補貼,企業用電枯水期按0.02元/千瓦時給予補助,平水期按0.04元/千瓦時給予補助。在一些具有資源相對優勢的省份,地方政府會通過降低資源使用價格或特有的資源開發權來吸收投資。如內蒙古自治區曾出臺規定,凡在當地投資超過40億元的企業,每投資20億元,政府就可以為企業配備1億噸煤炭儲備開采權。
三是銀行信貸資源。伴隨著中央政府逐步下放金融資源的控制權,使得地方政府擁有了干預當地金融活動的權力,一方面,國有商業銀行分支機構的存在使得地方政府通常會默認甚至助長企業通過展期、拖欠甚至逃廢債的方式來攫取地方金融資源,以擴大企業投資規模;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會以優厚的“配套”條件或其他因素來吸引服務于地方的金融機構的建立。
(四)地方政府與當地企業兩組利益博弈關系的存在使得“中國式”產能過剩惡性循環
綜上所述,本文將政府經濟行為分為中央政府經濟行為和地方政府經濟行為,首先,從“中國式”產業政策以及中央宏觀調控政策出發,研究中央政府經濟行為在“中國式”產能過剩的形成過程中所做出的鋪墊作用;其次,從以GDP為核心的政績考核體系出發,分類介紹地方政府經濟行為為“中國式”產能過剩的形成所提供的體制土壤及資源優勢。
總的來講,兩組利益博弈關系的存在及動態變化導致了“中國式”產能過剩的惡性循環。這兩組利益博弈關系分別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利益博弈、地方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利益博弈。從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動態博弈上看,當“中國式”的產能過剩大量存在并嚴重危害中國宏觀經濟的相對平穩運行時,中央政府為了實現經濟的軟著陸,一般會先采取相對溫和的“微調”措施,以警示地方政府應放緩經濟增長的勢頭,但由于地方政府逆向心理的作祟,會使得地方政府不按中央政府所期望的那樣行動,反而反其道而行之,在經濟進入緊縮前把握住最后的沖刺,因此,中央政府的“微調”措施一般都會以失敗告終。這就迫使中央政府采取更加嚴厲的、極具行政色彩的調控手段來遏制“中國式”產能過剩。以行政手段為主的調控方式確實能及時見效,能夠暫時緩解非常嚴峻的“中國式”產能過剩,但這種調控方式并不是長久之計。因為這種方式也有副作用,隨著調控手段的執行,很容易造成經濟的迅速下滑,更重要的是,也并不能從根源上解決“中國式”產能過剩問題。一旦中央政府的調控政策因經濟下滑而有所松動時,地方政府又會伺機而動,與此同時,中央政府也缺乏對地方政府監管的強烈意愿,上級政府的弱監管又會使得各地的產能擴張行為死灰復燃,并引發新一輪的“中國式”產能過剩,進而造成“中國式”產能過剩的惡性循環。
從地方政府和企業的動態博弈上看,企業不僅是實行“中國式”產業政策的執行主體,還是地方的納稅主體。因此,為了推動當地經濟的發展,各地方政府都傾向于通過各種手段來干預企業投資及企業行為,這種互利互助的政企關系是中國經濟得以實現高速增長的微觀基礎,但這種關系也為“中國式”產能過剩的形成與惡化埋下了隱患。當中央政府將GDP增長作為政績考核的主要指標時,地方政府官員出于經濟動機和政治動機的雙重考慮,可能會幫助企業隱瞞其通過不當的生產方式所進行的經營活動,從而導致“政企合謀”的產生,進而演化成各地愈演愈烈的“中國式”產能過剩。
基于中央與地方政府經濟行為的利益博弈、地方政府與企業行為的利益博弈這兩組博弈關系下“中國式”產能過剩形成機制圖,如圖1所示。
三、化解“中國式”產能過剩的建議
(一)重構政府與市場關系,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
在各國經濟舞臺上,政府和市場不斷變化著角色,展示著自己的作用,為實現效率而發揮不同的職能。雖然政府在矯正市場失靈時確實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政府本身也存在著更加難以忽視的失靈問題。政府失靈使各國政府面臨兩難局面:市場失靈必須訴諸政府權力,而政府手段的局限又使其在克服市場失靈時出現了新的缺陷。因而,如何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如何實現兩者的均衡是各國面臨的重要問題。

圖1 中央與地方政府經濟行為與“中國式”產能過剩的形成機制
“中國式”產能過剩的產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國市場化改革的滯后,使得市場不能完全發揮其優勝劣汰和配置資源的積極作用。因而,要從根本上化解“中國式”產能過剩的困局,要大力推進市場化改革[13]:首先,必須促進市場法律機制的完善,通過打造良好的法治環境和社會生態環境,讓市場主體平等競爭,使得國企和民企享受相同的市場待遇;其次,建立和完善公平競爭的市場機制,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優勝劣汰作用;再次,必須加快推進資源要素配置的市場化改革,減少或約束各級政府的資源配置權,還要完善資源要素價格,尤其是生產性資源要素價格的市場化形成機制,使市場真正成為資源配置的主體。
(二)重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關系,清楚劃定各級政府職能
“中國式”產能過剩的惡性循環是中央與地方利益反復博弈的結果,而中央與地方利益博弈的癥結在于財稅體制的改革的滯后。自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來,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都取得了飛速發展。但經過十余年的發展,中央政府不斷將地方政府財權上收,將事權和責任下放,導致地方財政財權與事權不匹配的矛盾日益突出。在此情形下,地方政府只能更多寄希望于土地財政及招商引資來增加財政收入,并由此產生了大量的“中國式”產能過剩現象。
因而,要化解“中國式”產能過剩,必須從調整當下的財稅體制入手,主要是從憲法層面明確各級政府的職能、權限和責任:一是以事權定財權,明確界定中央政府及各級地方政府的事權,然后依據事權大小來劃定相應的財權;二是適當賦稅于地方,對于一般地方稅稅種,在中央統一立法的基礎上,賦予省級人民政府稅目稅率調整權、減免稅權,并允許省級人民政府制定實施細則或具體實施辦法。
(三)推動政府轉型,重構政績考核體制
“中國式”產能過剩的形成,離不開以GDP為主要考核指標的政績考核體系與根深蒂固的地方保護主義的相結合。因而,要化解“中國式”產能過剩就必須重建地方政府行為的激勵約束機制,即在政績考核指標的選取上,要降低長期以來與粗放型增長方式相關的產值指標,提高就業、社會穩定和民生改善等其他指標的考核,如“綠色GDP”、“消除落后產能”等。因此,各級地方政府應痛下決心,勇于拋棄此前的GDP崇拜及各級政府間的“政績錦標賽”,回歸經濟發展的本真,還利于民,藏富于民,造福社會。
(四)轉變政府調控理念,打造法治政府
從中央政府對產能過剩的調控中,我們發現中央政府常常以自身對市場供需的判斷以及對市場的預測為依據來制定調控措施,并且在具體的調控措施中,簡單化的行政管控也屢見不鮮,這無異于對法治的漠視。沒有對法律的嚴格尊崇,中央政府就會習慣于主觀性地調控,地方政府也會習慣于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因此,若要化解“中國式”產能過剩,亟須推進法治建設,以法治政府限制公權力的肆意擴張,將權力關進憲法和制度的籠子里[14]。只有在法治的框架下,中央政府才會逐步擯棄主觀化、簡單化的行政管控,轉向法治化、市場化的宏觀調控。
[1]Chamberlin,Edward.H.The theory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I st edition,Cambridge1933;6th edition,1948.
[2]Kirkley,J.J.Catherine.P.Morrison and S.Dale.Capacity and Capacity utilization in common-pool resource industries:definition,measurement,and a comparison of approaches,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2002,(22).
[3]Cassels,J.M.Excess Capacity and Monpolistic Competition.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37,(51).
[4]Fare,Rolf,Shawna Grosskopf,and Edward C.Kokkelenberg.Measuring plant capacity,utilization and technical change:A nonpara metric approach.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1989,(30).
[5]王立國.重復建設與產能過剩的雙向交互機制研究[J].企業經濟,2010,(6).
[6]周勁,付保宗.工業領域產能過剩形成機制及對策建議[J].宏觀經濟管理,2011,(10).
[7]Fair,R.C.The short-run demand for workers and hours,North-Holland,1969.
[8]Bain.Industrial Organization.New York:John Wiley, 1959.
[9]江飛濤,耿強,呂大國,李曉萍.地區競爭、體制扭曲與產能過剩的形成機理[J].中國工業經濟,2012,(6).
[10]瞿東升.解析“中國式”產能過剩[J].宏觀經濟管理,2013,(7).
[11]陳剩勇,孫仕祺.產能過剩的中國特色、形成機制與治理對策——以1996年以來的鋼鐵業為例[J].南京社會科學,2013,(5).
[12]周黎安.晉升博弈中政府官員的激勵與合作——兼論地方保護主義和重復建設問題長期存在原因[J].經濟研究,2004,(6).
[13]王秋石,萬遠鵬.政府應從化解產能過剩中逐步淡出[J].福建論壇,2015,(6).
[14]周枝田,夏洪勝.長期性產能過剩問題研究探究[J].商業時代,2006,(10).
【責任編輯:薛 華】
F269.24
A
1004-518X(2016)05-0044-08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發達國家去工業化與中國產業發展路徑研究”(10BJL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