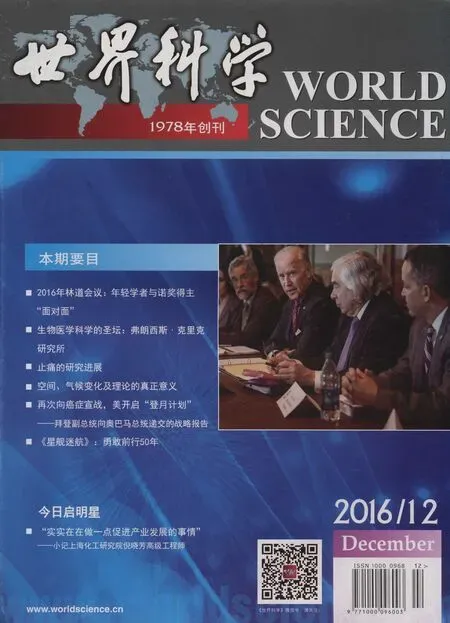生物醫(yī)學(xué)科學(xué)的圣壇: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
胡德良/編譯
生物醫(yī)學(xué)科學(xué)的圣壇: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
胡德良/編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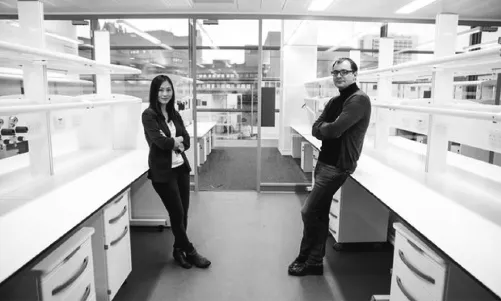
維維安·李(Vivian Li)博士和安德烈亞斯·舍費(fèi)爾(Andreas Schaefer)教授在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的新實(shí)驗(yàn)室中
●倫敦一家新成立的研究所將成為最大、最先進(jìn)的生物醫(yī)學(xué)類研究機(jī)構(gòu)之一。有關(guān)該研究所未來(lái)的愿景,所長(zhǎng)保羅·納斯爵士分享了他的看法。
人們稱之為保羅爵士大教堂——在陽(yáng)光燦爛的冬日,走過(guò)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你就很容易明白他們?yōu)槭裁催@么稱呼了。大面積的窗格玻璃在圣潘克拉斯周?chē)慕值郎细吒哓Q起,反射出來(lái)的陽(yáng)光照亮了這家生物醫(yī)學(xué)研究機(jī)構(gòu),而該機(jī)構(gòu)很快就會(huì)成為歐洲最大的生物醫(yī)學(xué)研究機(jī)構(gòu)……而那堅(jiān)固的赭石外立面跟許多古老建筑不變的外觀相呼應(yīng)。
我穿過(guò)施工現(xiàn)場(chǎng),戴著安全帽,進(jìn)入到內(nèi)部。這座建筑的風(fēng)格跟教堂不無(wú)關(guān)系——酷似教堂大型正廳的部分處于中庭的中心,看起來(lái)很像袖廊的通道橫穿中庭,腳下是地下結(jié)構(gòu),多達(dá)四層,按規(guī)定要放置許多敏感的科學(xué)儀器,這里很像一個(gè)由拱頂室構(gòu)成的巨型網(wǎng)絡(luò)。
保羅·納斯(Paul Nurse)爵士是諾貝爾獎(jiǎng)得主,前英國(guó)皇家學(xué)會(huì)主席,現(xiàn)任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研究所所長(zhǎng),因此他的名字就自然地跟該研究所聯(lián)系起來(lái)。納斯的臨時(shí)辦公室設(shè)在維康信托基金會(huì),他說(shuō):“我們確實(shí)考慮到建筑問(wèn)題,可以到樓里面去找一下靈感。這就是中世紀(jì)大教堂的美妙之處——不論你的信仰是什么,都可以激發(fā)你的靈感。”
然而,這座建筑花費(fèi)了7億英鎊,因此納斯希望這棟樓的功能不僅僅是激發(fā)靈感,這是不足為奇的。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擁有最先進(jìn)的設(shè)備,高度封閉的能容納嚙齒動(dòng)物、斑馬魚(yú)的場(chǎng)所,甚至擁有專門(mén)容納負(fù)鼠的場(chǎng)所,因而該研究所的志向之高,就像其樓頂上的椽子。約1 500名科學(xué)家和工作人員將在這里對(duì)生物醫(yī)學(xué)各領(lǐng)域進(jìn)行探索,包括從癌癥研究到神經(jīng)科學(xué)、流行病,甚至再到對(duì)人類胚胎實(shí)施基因編輯技術(shù)等大膽的新項(xiàng)目,生命本身將置于顯微鏡之下。
當(dāng)然,這是一次團(tuán)隊(duì)合作的壯舉,是六個(gè)創(chuàng)建機(jī)構(gòu)共同努力的結(jié)果。這六個(gè)機(jī)構(gòu)是:醫(yī)學(xué)研究理事會(huì)、英國(guó)癌癥研究中心、維康信托基金會(huì)、倫敦大學(xué)學(xué)院、倫敦帝國(guó)學(xué)院和倫敦國(guó)王學(xué)院。醫(yī)學(xué)研究理事會(huì)的設(shè)施位于倫敦北部的磨坊山,該理事會(huì)曾經(jīng)受人尊重,但其設(shè)施正在趨于老化。這家新的研究所將會(huì)取代醫(yī)學(xué)研究理事會(huì)和倫敦癌癥研究所的兩個(gè)辦事處,將其現(xiàn)有的人員集中起來(lái),跟新招募的研究人員和臨時(shí)調(diào)派的大學(xué)學(xué)者一起工作。納斯說(shuō):“對(duì)于研究工作來(lái)講,人們忘記了資金已經(jīng)到位;這些新資金是為建筑而籌集的,并且新資金在不斷地籌集到位。”
然而,或許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擔(dān)憂。約克大學(xué)杰克·伯奇分子致癌研究所所長(zhǎng)珍妮·索斯蓋特(Jenny Southgate)教授說(shuō):“我認(rèn)為,最大的風(fēng)險(xiǎn)之一是,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得到了一些最大資助機(jī)構(gòu)的支持,這些資助機(jī)構(gòu)希望對(duì)研究所里的研究成果予以支持,而在很大程度上我們或許正在創(chuàng)建一個(gè)可有可無(wú)的科學(xué)團(tuán)體。”
巴斯大學(xué)干細(xì)胞與發(fā)育遺傳學(xué)教授羅伯特·凱爾什(Robert Kelsh)也懷有一種復(fù)雜的感受。他說(shuō):“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是很棒的,它會(huì)運(yùn)行得極其順利。但是我認(rèn)為,人們(尤其是倫敦之外的人們)對(duì)此會(huì)有些擔(dān)憂,該研究所不可避免地會(huì)吸引到各方資助,且資助總額之大,可以想象。”凱爾什將該研究所的資源跟大學(xué)的資源進(jìn)行對(duì)比,他認(rèn)為,涉及獲得資助的問(wèn)題,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具有絕對(duì)優(yōu)勢(shì)。

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所長(zhǎng)保羅·納斯爵士

竣工之后,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將延伸至12層,8層位于地面以上,4層位于地面之下
做好管理
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的中心任務(wù)是實(shí)驗(yàn),而納斯也正在著手進(jìn)行自己的一項(xiàng)大型實(shí)驗(yàn)。納斯掃除了學(xué)術(shù)環(huán)境中普遍存在的部門(mén)之分,他希望將財(cái)務(wù)控制權(quán)下放到研究所120個(gè)實(shí)驗(yàn)小組組長(zhǎng)的手中,而不是讓少數(shù)部門(mén)主管來(lái)控制財(cái)權(quán)。科學(xué)家們需要一筆接一筆地爭(zhēng)取資助,為自己的研究籌集資金,這對(duì)于他們來(lái)說(shuō)是司空見(jiàn)慣的煩心事。研究所里每個(gè)實(shí)驗(yàn)室都有一筆核心資助,因此爭(zhēng)取資助的問(wèn)題將會(huì)得到緩解。成果發(fā)表的壓力也會(huì)減輕,因?yàn)檠芯咳藛T不必反復(fù)通過(guò)同行審核的障礙,就可以獲得資助,允許他們專注于需要冒險(xiǎn)的長(zhǎng)期研究。納斯說(shuō):“我們當(dāng)然也會(huì)注重高質(zhì)量的論文,但是重點(diǎn)在于我們不利用評(píng)估單位,不利用《自然》雜志的審核程序來(lái)判斷你的研究工作做得如何。我們擁有一支資深的管理團(tuán)隊(duì),包括享有聲望的路易斯-讓泰醫(yī)學(xué)獎(jiǎng)獲得者和一組名副其實(shí)的皇家學(xué)會(huì)會(huì)員,由他們來(lái)鑒定高質(zhì)量的研究。我們的鑒定水平相當(dāng)高!”
此外,研究所認(rèn)真地為不同領(lǐng)域的研究人員分配了辦公室和實(shí)驗(yàn)室,但分配起來(lái)相當(dāng)艱難,不亞于最為艱難的座次安排任務(wù)。盡管如此,不同于部門(mén)與部門(mén)之間的情況,隨著研究工作的展開(kāi),科學(xué)家們將穿梭于所謂的“興趣小組”之間。納斯希望,最終會(huì)產(chǎn)生一種“輕度無(wú)政府”的狀態(tài)。這可能也是對(duì)納斯本人的描述——他在解釋時(shí),看看周?chē)髨D尋找一種方式來(lái)描述自己的計(jì)劃,想讓我明白如何加快把有前途的研究轉(zhuǎn)化為創(chuàng)新成果和具體療法。我為他提供我自己的鋼筆,可是他卻有選擇地拿起幾只茶杯,相繼地散擺在桌子上。他開(kāi)始解釋,比如說(shuō)這張桌子代表知識(shí),接著他快速地到處移動(dòng)他的“道具”,就像魔術(shù)師正在進(jìn)行三只茶杯的雜耍。
其實(shí),納斯的想法遠(yuǎn)遠(yuǎn)不像他所解釋的那樣復(fù)雜。納斯稱: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將會(huì)采取不同的合作方式,不會(huì)接受完全不切實(shí)際的研究,也不會(huì)側(cè)重于追求遙遠(yuǎn)的目標(biāo)。在這里,科學(xué)家一邊展開(kāi)自己的研究,一邊跟一個(gè)專家小組進(jìn)行密切合作,這樣有助于做出發(fā)現(xiàn),做出具有潛在臨床意義的發(fā)現(xiàn)或者經(jīng)證明可用于其他領(lǐng)域的發(fā)現(xiàn)。納斯說(shuō):“事實(shí)上,我們會(huì)對(duì)那些做出發(fā)現(xiàn)的人予以獎(jiǎng)勵(lì),但是我們總是還要著眼于這些發(fā)現(xiàn)能否實(shí)現(xiàn)轉(zhuǎn)化。更重要的是,跟制藥公司進(jìn)行合作會(huì)為研究所的科學(xué)家提供機(jī)會(huì),他們會(huì)受益于制藥行業(yè)的專業(yè)知識(shí)。”我提出,并不是每個(gè)人都對(duì)接近企業(yè)的想法感興趣。但是不出所料,納斯不以為然。他說(shuō):“我們這樣做的意思是,大型制藥公司擁有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人物,正在進(jìn)行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研究;我們也都是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人,但在某種程度上我們的研究有著不同的目標(biāo)——我們雙方合作起來(lái)沒(méi)有害處,我們?nèi)匀豢刂浦覀兊闹R(shí)產(chǎn)權(quán)。”
這是一個(gè)大膽的設(shè)想,但并非完全史無(wú)前例。凱爾什在其他實(shí)驗(yàn)室曾經(jīng)采用過(guò)類似的跨學(xué)科方法,他根據(jù)自己的經(jīng)歷說(shuō)道:“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的想法并不是全新的,但是我認(rèn)為這是經(jīng)過(guò)證實(shí)的想法。”納斯也這么認(rèn)為,研究所是建立在堅(jiān)實(shí)基礎(chǔ)之上的。在曾經(jīng)給予納斯靈感的單位中,他提到紐約洛克菲勒大學(xué)(他曾經(jīng)在該校任8年校長(zhǎng))和歐洲分子生物學(xué)實(shí)驗(yàn)室,他說(shuō):“我所做的一切,不過(guò)就是在全世界看到了最佳操作方式,并將其‘偷’了過(guò)來(lái)。”然而,他的計(jì)劃不僅僅體現(xiàn)在研究所的團(tuán)體精神上,而且也體現(xiàn)在這座建筑本身中。閃光的樓梯蜿蜒上升至頂層,希望能夠?yàn)榭茖W(xué)家之間增加偶遇的機(jī)會(huì)和新的合作機(jī)會(huì)。光潔的白色長(zhǎng)凳等待著許多不同領(lǐng)域的工作人員到來(lái),墻壁好像地下酒吧的秘密櫥柜那樣伸展出去,以將白色書(shū)寫(xiě)板凸顯出來(lái),供研究人員寫(xiě)寫(xiě)畫(huà)畫(huà),所記下的內(nèi)容有可能是天才研究人員在無(wú)意識(shí)的情況下獲得的靈感,這無(wú)疑也是書(shū)寫(xiě)板創(chuàng)設(shè)者的熱切希望。
然而,你只能把一匹馬帶到水邊,卻不能強(qiáng)迫它喝水。“在一定程度上,我認(rèn)為把大家集中到一起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身懷不同技能的人們有著不同的思維方式和不同的背景,他們擁有許多不同的專業(yè)知識(shí),應(yīng)該能夠發(fā)揮巨大的協(xié)同作用,這應(yīng)該是一件非同尋常的事情。”索斯蓋特說(shuō),“但是,你無(wú)法強(qiáng)迫人們?nèi)ズ献鳎瑑H僅將他們置于同一個(gè)房間,并不意味著會(huì)產(chǎn)生合作。”
又有一家配置完備的研究所歸于倫敦的地盤(pán)上,那么,英國(guó)其他地方的科學(xué)家會(huì)不會(huì)有點(diǎn)惱火呢?“哪些人是搞研究的中堅(jiān)力量呢?是20歲至35歲的科學(xué)家,他們喜歡倫敦。”納斯說(shuō)道,“對(duì)此,我們就直言不諱了:目前我正在努力從紐約、東京或柏林吸引人才,但是如果我們研究所處于偏僻地區(qū),我就不會(huì)這么做了。”納斯堅(jiān)持認(rèn)為:這個(gè)位置不僅容易使科學(xué)家們前來(lái)訪問(wèn)、容易接待全國(guó)其他研究所的客人,而且該研究所將會(huì)促進(jìn)研究在全國(guó)范圍內(nèi)展開(kāi),請(qǐng)到富有想象力、具有冒險(xiǎn)精神的研究人員,例如,我們將要招聘許多新的研究領(lǐng)導(dǎo)人,固定聘期為12年。納斯說(shuō):“我們的研究所是一個(gè)培訓(xùn)機(jī)構(gòu),收納處于事業(yè)早期的科學(xué)家,在這個(gè)階段,他們通常具有創(chuàng)造性,但可能還會(huì)有些脆弱,有點(diǎn)經(jīng)驗(yàn)不足,研究所會(huì)為他們提供真正的高質(zhì)量培訓(xùn)和指導(dǎo)。然后,我們?cè)俦M量將他們輸送到英國(guó)其他地方的大學(xué)中。”

倫敦圣潘克拉斯附近新落成的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

詹姆斯·布里斯科(James Briscoe)博士(左)、卡羅琳·希爾(Caroline Hill)博士(中)和尼克·勒斯科姆(Nick Luscombe)教授(右),均為新落成的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研究人員
做好宣傳
然而,正如索斯蓋特指出的那樣:“這個(gè)方式本身可能會(huì)給研究人員帶來(lái)壓力。他們將不得不在倫敦生活六年,而且之后還有可能再生活六年,沒(méi)有長(zhǎng)期聘用的保障,他們知道有朝一日不得不搬走,去找別的工作。我認(rèn)為這會(huì)為他們?cè)斐蓧毫Γ@對(duì)家庭是不太有利的。”
吸引聰明年輕的研究人員到倫敦是一回事,在住房費(fèi)用飆升的城市里能否使他們擔(dān)負(fù)得起是另外一回事。納斯說(shuō),他的夢(mèng)想就是搞到一棟公寓,在新來(lái)的研究人員適應(yīng)新環(huán)境期間,為他們提供住所。“我曾努力想從資助單位搞到那筆錢(qián),但是那些單位都不愿意出資。”他看起來(lái)面帶一些失望的樣子,但他也沒(méi)有完全放棄自己的計(jì)劃,“這事一直浮現(xiàn)于我的腦海中。”他一邊說(shuō),一邊用手指戳著他那有些蓬亂的白發(fā)。對(duì)于其他的障礙,在應(yīng)對(duì)能力上他是比較有信心的。
橫貫鐵路2號(hào)線未來(lái)將會(huì)橫穿倫敦市。一提到這條鐵路線,納斯就怒不可遏。“當(dāng)我們建設(shè)這幢樓房的時(shí)候,橫貫鐵路2號(hào)線本來(lái)是在尤斯頓路之南穿過(guò)的,可是后來(lái)所發(fā)生的情況是:橫貫鐵路2號(hào)線的承建公司改變了主意,要在我們大樓最敏感的區(qū)域下面挖一條隧道,這將會(huì)造成災(zāi)難性的破壞。在搞建設(shè)期間,我們很可能會(huì)無(wú)法正常施工,或許一耽擱就是幾年。”納斯堅(jiān)持認(rèn)為,這條鐵路應(yīng)該再尋找另外一條路線。他說(shuō):“他們真的對(duì)我們很生氣,因?yàn)樗麄儾坏貌豢紤]變換路線了。然而,不僅僅是鐵路公司企圖暗中破壞研究所,有些人擔(dān)心該研究所將會(huì)變得規(guī)模太大而不會(huì)倒閉。其實(shí),這個(gè)說(shuō)法是我編造的。”納斯用開(kāi)玩笑的語(yǔ)氣說(shuō),“我說(shuō)過(guò)研究所會(huì)變得規(guī)模太大而不會(huì)倒閉,是因?yàn)槲覀儾坏貌皇蛊浒l(fā)揮作用。”
要是不能發(fā)揮作用怎么辦?納斯說(shuō):“如果一所大學(xué)不能正常發(fā)揮作用,我們就會(huì)把它踢出去;如果一家醫(yī)院不能正常發(fā)揮作用,我們會(huì)把它踢出去;如果這個(gè)方式不能正常發(fā)揮作用,我們同樣也會(huì)把它踢出去!”如果不務(wù)實(shí)的話,納斯就是一個(gè)不值得一提的人了。“如果理念錯(cuò)了,我們會(huì)從中吸取教訓(xùn),做出改革,但我不會(huì)把這一點(diǎn)刻進(jìn)墓碑。我想我們可以對(duì)此進(jìn)行嘗試,如果能夠行得通,那么我認(rèn)為這就是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如果有某些方面無(wú)法發(fā)揮作用,那么我們可以對(duì)其進(jìn)行修改。如果這一切都無(wú)法發(fā)揮作用,我也會(huì)被踢出去!”
的確,到底怎樣才算成功是另外一回事,尤其是在利用傳統(tǒng)的指標(biāo)(如發(fā)表的論文)進(jìn)行衡量、在互相之間信任不足的情況下,更是如此。然而,納斯卻很坦率:“每隔五年,都會(huì)由我們的資助單位進(jìn)行審核,因此如果我們沒(méi)有順利地拿出高質(zhì)量的研究成果,我們就算失敗了——當(dāng)然,其中某些成果還要發(fā)表在高知名度的期刊上。我們不得不通過(guò)審核,而且在我看來(lái)我們不得不高標(biāo)準(zhǔn)地通過(guò)審核,要比全國(guó)任何大學(xué)的標(biāo)準(zhǔn)都要高,不然的話,成立我們的研究所就沒(méi)有任何意義了。”
在許多方面,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是大思想家們實(shí)實(shí)在在的家園,用一位諾貝爾獎(jiǎng)得主的名字命名,由另一位諾貝爾獎(jiǎng)得主來(lái)管理,得到了一些科學(xué)界最享有盛名的人物給予的支持。事實(shí)上,捐贈(zèng)者之一就是跟克里克一起搞DNA研究的先驅(qū)——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他的贈(zèng)品是出資購(gòu)買(mǎi)的克里克的一幅畫(huà)像,即將掛在研究所。納斯說(shuō):“通常情況下,吉姆(Jim,詹姆斯的昵稱)會(huì)開(kāi)玩笑說(shuō)‘弄一張克里克洗澡時(shí)的畫(huà)像,豈不是很有趣嗎?’”然而,最終的畫(huà)像遠(yuǎn)沒(méi)有那么異乎尋常。克里克站在一塊黑板前面,雙手放在他那具有重大影響的論文上,眼睛注視著前方,套在脖子上的領(lǐng)帶帶有雙螺旋圖案,他的臉上好像帶有一種靜靜期待的表情。
[資料來(lái)源:The Guardian][責(zé)任編輯:絲絲]
本文作者尼古拉·戴維斯(Nicola Davis)為《衛(wèi)報(bào)》和《觀察家報(bào)》科技專欄撰稿,她也是《觀察家報(bào)》科技月刊的責(zé)任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