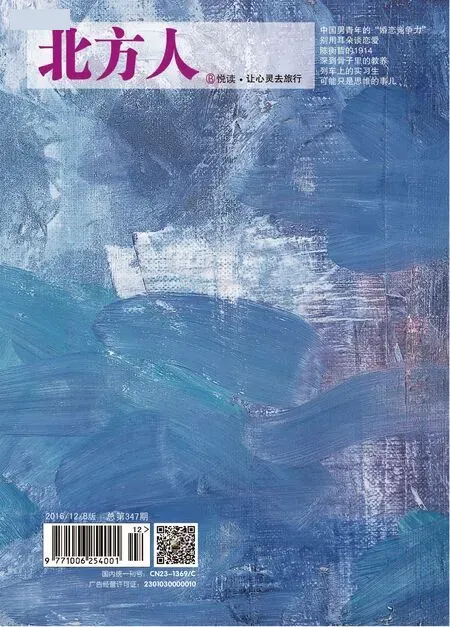明朝的詩人圈
文/黃亞明
明朝的詩人圈
文/黃亞明

明詩透露的明代經濟
明初的高啟老頭纂修過《元史》,是大學問家,他寫過《采茶詞》:“歸來清香猶在手,高品先將呈太守。竹爐新焙未得嘗,籠盛販與湖南商。山家不解種禾黍,衣食年年在春雨。”意思是采茶的美眉邊采茶邊對歌,愛心萌動。但采茶人難飲好茶,高檔茶得先獻給高官品嘗,剩下的由湖南商人異地收購。
且慢,湖南客販茶,沒那么容易,要有政府的茶引許可。古代鹽、茶、鐵、酒之類重要物資,一直由政府壟斷專賣,嚴禁私下流通。比如商家要做茶葉貿易,由中央政府給產地府州縣一定數額指標,商家找關系,交錢購買,待指標憑證(茶引)到手,才準許出境買賣。在政府的嚴密控制下,工商業(yè)自然只能戴著鐐銬跳舞,“安守其業(yè)”,緩慢發(fā)展了。
盡管發(fā)展緩慢,但還是發(fā)展了。詩人貝瓊、張羽、徐賁,均曾代言當時的商業(yè)復興情景,貝瓊說“賈客晨沖霧”,張羽說“商船無數青山繞”,徐賁《賈客行》更稱:“賈客船中貨如積,朝在江南暮江北。”顯然,洪武末期和永樂時期休養(yǎng)生息的重農政策像一帖靈藥,醫(yī)治了明初的坐骨神經痛,老百姓坐擁余錢余糧,購買能力和欲望大增。舉國上下,商貨紛呈,逐利的商賈朝暮轉徙,工商業(yè)的繁榮咫尺可待。
歲月翻轉到明代中后期,農耕技術提高,大興水利,農業(yè)經濟持續(xù)發(fā)展。利潤驅動下,商品交換日益頻繁,常熟的布匹,一半以上賣給齊魯大地;嘉定的棉布,遠販于河北、遼寧、山西、陜西。陸深在《江南行》中炫耀,“江南佳且麗,沃野多良田……東通滄海波,西接闔城煙。既饒魚稻利,復當大有年。登眺何郁郁,井市互糾纏。商賈競啟關,逋流愿受廛。”薛瑄、李東陽、唐文鳳忍不住驚嘆:“臨清人家枕閘河,臨清賈客何其多”;“官船賈舶紛紛過,擊皷鳴鑼處處聞”。其繁華盛況,幾令人眼花繚亂了。
明代手工業(yè)也沒閑著,礦冶、紡織、陶瓷、印刷業(yè)等均頗具規(guī)模。盛澤等鎮(zhèn)因絲織業(yè)而發(fā)展,景德鎮(zhèn)以陶瓷著稱,佛山則以鐵器聞名。趙慎徽對朱涇棉布業(yè)有詩贊曰:“萬家煙火似都城,元室曾經置大盈。估客往來多滿載,至今人號小臨清。”
明詩里的商販地位
晚明香艷小說《金瓶梅》里的妓女李桂姐,一身好妖嬈,穿著湘裙、白綾對襟襖、紅羅裙、油鵝黃銀條紗裙。在明代,這都是“僭越”服裝,違規(guī),不守本分。
李桂姐是妓女,妓女在皇帝面前沒面子,是賤民,和商販、仆役、奴婢、表演工作者一類。按照朱皇帝的規(guī)定,妓女和表演工作者被編入樂戶,世代相傳,不得更改,不得與官員、平民通婚(除非交付贖身錢并取得從良文書),其后代不準參加國考。商販也如此,正德元年規(guī)定商販、吏典、仆役、娼優(yōu)、下賤皆不許服用貂裘。有劉基寫于元末明初的詩句“家家種田恥商販”為證。
但農民靠耕田,日子漸漸難過,“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自四五十年來,賦稅日增,繇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遷業(yè)……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農而改業(yè)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巨大的賦役壓力下,守著半畝三分地,蠢!于是趕緊經商,緩解謀生壓力,提升生活質量,于是商賈的地位漸漸咸魚翻身。
王燧《商賈行》云:“揚州橋南有賈客,船中居處無家宅。生涯常在風波間,名姓不登鄉(xiāng)吏籍。前年射利向蠻方,往來行販越海洋。歸來載貨不知數,黃金繞身帛滿箱。小婦長干市中女,能舞柘枝謌白苧。生男學語未成音,已教數錢還弄楮。陌頭車輪聲格格,畊夫賣牛買商舶。”為商多低賤,漂泊有風險,但架不住錢多,“黃金繞身帛滿箱”,引得那些農民羨慕嫉妒恨,“畊夫賣牛買商舶”,賣掉耕牛,聚資購買商船,灑家也搞海洋貿易去也。
普通種田人一樣耐不住貧困,萬歷《上海縣志》里有一首《竹枝詞》,“平川多種木棉花,織布人家罷緝麻,昨日官租科正急,街頭多賣木棉紗”。老婆婆、小媳婦加入小攤販的行列,清早就在街頭叫賣棉紗,弄點兒小錢改善生活。
讀書人也追求市場利益
《金瓶梅》里的讀書人,混得好的,有蔡狀元、安進士,還沒授官,西門慶就屁顛屁顛兒送禮。混得差的,是溫秀才、水秀才。溫秀才專愛小白臉,給西門慶干秘書。至于水秀才,承蒙幫閑應伯爵推薦,也不過是寫寫書信打打雜。
溫秀才、水秀才們,沒邁過國考那道坎,仕進無門,經濟窘況,巨大的差距瓦解了士農工商的等級界限,讀書人只好當師爺、做幕僚、干秘書、教私塾、開診所、做商販了。這就是古人所言的“治生”。
這里單來說說讀書人棄儒就商。明辨義利歷來是儒家重要的道德尺繩,放下架子經商,雖是無奈選擇,但進入商場,卻需遵循商家職業(yè)原則:喻于利。“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賈而成功也十之九”,因科舉不第而棄儒就商,在明代社會中比較普遍。袁宏道詩曰“海陽多賈人,纖嗇饒積聚。握算不十年,豐于大盈庫。富也而可求,執(zhí)鞭所忻慕。金口親傳宣,語在《述而》處。師與商孰賢,賜與回孰富?多少窮烏紗,皆被子曰誤”。老袁所蘊牢騷不平,自不必言,卻真是活畫了士人“治生”的眾生相。
窮書生最大的賣點,其實還是筆底詩文。于是作文鬻利,收取潤筆,成為“治生”大法。話說唐伯虎因科場案受挫,曾作《貧士吟》,“十朝風雨若昏迷,八口妻孥并告饑。信是老天真戲我,無人來買扇頭詩。青山白發(fā)老癡頑,筆硯生涯苦食艱。湖上水田人不要,誰來買我畫中山。荒村風雨雜雞鳴,轑釜朝廚愧老妻”。
常熟有個知識分子桑思玄,遇到某人求文,馬屁拍得好,就是不掏錢。老桑對某人說,哎呀,兄弟,咱一生從沒給人白作文,不給稿費咱筆底枯澀,不如你暫時在咱面前放一錠四五兩的銀子,等咱興沖沖靈感來襲,一揮而就之后,再把銀子還你?此事雖為笑談,仍折射出收取潤筆已為明代士人通習。
要吟詩,要雅集,要喝酒賞舞,要混個紅塵逍遙,自是無可厚非。但面對“告饑”的妻兒,先得解決生計大事。這是一個男人、丈夫、父親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