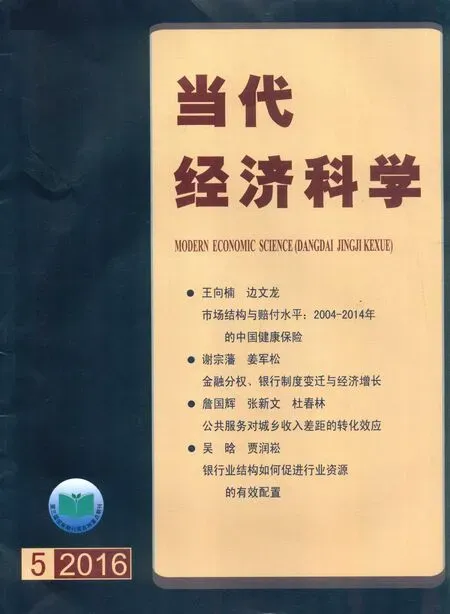民營企業經營者的股東權力關聯及其績效影響研究
王新霞,柳 春
(1. 西安外國語大學 經濟金融學院,陜西 西安 710128;2. 西安交通大學 金禾經濟研究中心,陜西 西安 710049)
?
民營企業經營者的股東權力關聯及其績效影響研究
王新霞1,柳 春2
(1. 西安外國語大學 經濟金融學院,陜西 西安 710128;2. 西安交通大學 金禾經濟研究中心,陜西 西安 710049)
以實際控制人為邏輯起點,本文理論剖析了民營企業經營者的股東權力關聯及其績效影響,并探討了薪酬激勵對其績效影響的調節作用。實證檢驗發現:①在兩職合一民營企業中,經營者的股東權力關聯對企業績效不存在顯著影響;②在兩職分設民營企業中,董事長的股東權力關聯有利于改善企業績效,而總經理的股東權力關聯對企業績效不存在顯著影響或產生不利影響;③薪酬激勵有助于強化經營者股東權力關聯的積極影響,抑制其消極影響。
經營者;股東權力關聯;薪酬激勵;績效影響
一、引 言
改革開放30余年,我國民營經濟的成功奇跡挑戰了傳統智慧,為主流經濟學發展做出了新的貢獻。1992年“深華源A”(現名“沙河股份”)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揭開了我國民營企業上市的序幕;截止今日,民營上市公司在我國滬深兩市占比超過50%。統計發現,絕大多數的民營上市公司存在家族控股現象。家族大股東控股不僅體現在占有控制性股權比例,更重要的是體現在對經營者聘任和職務的掌控上;換言之,圍繞民營上市公司經營者的權力配置受到大股東意志的影響。
國內外學者針對現代企業經營者權力問題的相關研究取得了豐富且頗有價值的成果[1-2]。然而,鮮有文獻從控股股東角度研究民營企業經營者的權力。在我國民營企業中,經營者的出身背景往往比較復雜,要么本身就是企業實際控制人或控股家族成員,要么由控股股東任命/推薦而來,要么曾在控股股東單位任職,甚至現在仍在控股股東單位擔任一定的高管職務①畢艷杰(2006)以2004年324家家族控股公司為樣本,發現約54%的公司中董事長或總經理由控股家族成員擔任;鄧德強(2007)發現2003年230家民營上市公司中,53.9%的董事長在大股東單位任職,且絕大多數是大股東單位的董事長。。與控股股東的種種關聯都有可能是經營者權力的形成渠道,衍生出關系型權力。借鑒政治關聯這一概念,本文將經營者與控股股東的上述關聯定義為股東權力關聯。以實際控制人為邏輯起點,本文將從企業績效的角度解讀民營企業經營者的股東權力關聯,并探討薪酬激勵對其績效影響的調節作用,以期為我國民營企業如何配置經營者權力提供借鑒和參考。
二、理論分析
(一)股東權力關聯的內涵
民營企業經營者的股東權力關聯需要從兩個層面來解讀——聘任層面與職務層面。
受傳統文化及制度環境的影響,民營企業的實際控制人試圖利用血親(或姻親)關系建立信任聯盟,家族治理色彩濃厚[3]。通常而言,民營企業的實際控制人或其代表直接擔任董事長和總經理。若經營者由實際控制人或家族成員擔任,或者由控股股東任命/推薦產生,或者從控股股東單位選派而來,本文將此類股東權力關聯稱之為任命權力關聯,即因為任命關系所衍生出來的權力關聯。在民營企業中,任命權力關聯既具有明顯優勢又存在潛在弊端。一方面,擁有任命權力關聯的經營者多是家族或類家族成員,與實際控制人或控股股東之間的特殊關系促使其有動力最大化企業價值[4]。此外,家族或類家族成員擔任經營者,有助于塑造與保持企業內部權威,形成穩定的領導權結構①現實中,某些民營上市公司一旦公布董事長或總經理的人事變更消息,股價就會出現劇烈波動,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投資者擔心企業即將喪失權威治理。。另一方面,盡管實際控制人(或控股股東)傾向于遵循能力取向原則,指定更有能力的人擔任公司經營者[5],但較之職業經理人,家族或類家族成員的經營才能尚有不足,將更具天賦及才能的職業經理人排斥在外。換言之,任命權力關聯的裙帶關系限制了經營者人力資源的市場競爭范圍,可能損害企業績效[6]。此外,若經營者同實際控制人存在血親(或姻親)關系,其有可能為了實際控制人利益最大化而做出有損企業利益的行為。
大股東除了控制經營者的人選外,往往還掌控著經營者在控股股東單位的兼職情況。若經營者在控股股東單位擔任一定的高管職務,其可借職務之便與控股股東發生關聯,本文將之稱為任職權力關聯。對于民營企業而言,經營者的任職權力關聯具有關系網絡資源效應。在經濟轉軌過程中,民營企業面臨所有制歧視導致的政策壁壘以及資金、技術等要素限制。假如在控股單位擔任高管職務,經營者可以憑借其與大股東之間的密切聯系、頻繁接觸和多重社會關系,為企業爭取信息、技術、資金等資源。簡言之,任職權力關聯可以提升經營者的資源獲取與協調能力。需要注意的是,經營者的任職權力關聯源于其既在民營企業擔任高管職務又在控股股東單位擔任高管職務。身兼數職的經營者很可能受時間和精力有限的制約,分身乏術,力不從心,不能很好地勝任自己的工作。更有甚者,任職權力關聯“綁架”經營者的選擇,以實際控制人或控股股東利益為重,甚至為后者侵蝕企業利益提供便利。
(二)經營者任命權力關聯的績效影響分析
在兩職合一企業中,實際控制人(多是企業創始人)親自擔任經營者。如此,任命權力關聯能夠產生強烈的控制權激勵和權威治理效應,形成穩定的領導權結構,保證企業決策機制順暢;然而,囿于職業生涯能力曲線變化,經營者的能力水平可能無法滿足企業長遠發展的需要甚至成為企業發展的羈絆[7]。因此,在正反兩種效應的綜合作用下,我們就無法簡單判斷經營者任命權力關聯對企業績效的影響。
在兩職分設企業中,對于不同的經營者(董事長和總經理),其任命權力關聯要區別對待。具體而言,董事長的任命權力關聯往往意味著實際控制人擔任董事長,這與兩職合一企業中的情形既有相同之處,又有不同之處。相同之處在于實際控制人身份及權威治理激勵其追求企業價值最大化,此處不再贅述;不同之處在于兩職分設企業中董事長的能力制約問題得到緩解,因為即使經營決策取決于董事長的意志和偏好,總經理的存在可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信息溝通和智慧共享,避免董事長的片面認知和武斷決策。所以,董事長任命權力關聯的控制權激勵和權威治理效應將超過能力制約效應,有助于改善企業績效。然而,總經理的任命權力關聯多意味著家族或類家族成員擔任總經理,可能對企業績效產生負面影響。首先,在董事長絕對權威的情況下,總經理的任命權力關聯并不會帶來明顯的控制權激勵和權威治理效應;其次,家族或類家族成員的經營才能可能存在不足,沒有能力為董事長決策提供有效信息及智慧共享,易引發決策低效率[8]。再者,大股東任命產生的總經理對董事長(特別是創始人)有很強的情感依賴,難免滋生松散態度和懶惰行為。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說H1和H2:
假說H1:在兩職合一情況下,經營者的任命權力關聯對企業績效不存在顯著影響。
假說H2:在兩職分設情況下,董事長的任命權力關聯有利于改善企業績效,而總經理的任命權力關聯與之相反。
(三)經營者任職權力關聯的績效影響分析
在兩職合一民營企業中,經營者多是企業創始人親自擔任,創始人身份激勵其為企業動員一切資源,能夠充分發揮任職權力關聯的關系網絡資源效應。但前文述及職業生涯能力曲線變化導致經營者能力成為企業發展的羈絆,而經營者同時在控股股東單位和民營企業擔任關鍵領導人職務,精力分散會進一步放大能力不足的制約效應。因此,在兩職合一民營企業中經營者任職權力關聯對企業績效的影響是不明確的。
兩職分設民營企業的董事長脫離日常經營管理瑣事的困擾而著眼于企業長遠發展,任職權力關聯帶來的精力分散效應并不嚴重。同時,董事長在控股股東單位任職多不是虛職,而是懂管理、懂業務、有實權的職位,不難推斷董事長任職權力關聯的關系網絡資源效應是非常顯著的。任職權力關聯的精力分散影響完全可以被關系網絡資源效應彌補,并進一步優化企業的資源配置。然而,總經理任職權力關聯的績效含義略有不同。根據相關政策,若總經理在控股股東單位擔任一定的高管職務,其往往是擔任董事。囿于董事在企業高管層中的權力有限,其所能夠獲取或協調的資源有限,民營企業總經理任職權力關聯的關系網絡資源效應是非常有限的;另外,在集權文化和權威治理約束下,絕大多數總經理往往變成董事長的助理,主要扮演董事長指令執行人的角色,所以任職權力關聯的精力分散效應并不嚴重。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說H3和H4:
假說H3:在兩職合一情況下,經營者的任職權力關聯對企業績效不存在顯著影響。
假說H4:在兩職分設情況下,董事長的任職權力關聯有利于改善企業績效,而總經理的任職權力關聯不產生顯著影響。
(四)薪酬激勵對經營者股東權力關聯績效影響的調節作用
民營企業經營者除了本身存在傳統代理問題外,還可能因其特殊身份(主要是指其與實際控制人或控股股東存在血親或姻親關系)而加劇大股東與中小股東之間的代理問題。作為理性經濟人的民營大股東有能力和動力設計薪酬契約來激勵約束經營者[9]。
在兩職合一民營企業中,若經營者在企業領薪或持股,受經濟因素激勵,其將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關注企業利潤創造,強化任命權力關聯的控制權激勵和權威治理效應。在穩定的領導權結構下,經營者有更高的積極性搜集、篩選與甄別信息,提高企業決策效率;另一方面,面對前文提及的經營能力制約問題,經濟利益刺激經營者積極主動提升自身的經營才能,比如“干中學”、進修深造等。在兩職分設民營企業中,無論是董事長還是總經理,在企業獲取薪酬都能夠與任命權力關聯產生正向的交叉績效影響。就董事長而言,與兩職合一企業中的情形相類似,薪酬契約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董事長個人利益與企業利益的相關聯,能夠強化任命權力關聯的控制權激勵和權威治理效應,同時提高穩定領導權結構的決策效率。對于總經理來說,雖然任命權力關聯的控制權激勵和權威治理效應有限,但受薪酬激勵,總經理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有動力積極提升自身的經營才能,努力為董事長決策提供有效信息及智慧共享;與此同時,總經理積極發揮主觀能動性,嘗試轉變思維方式,而不是一味地支持或依賴董事長。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說H5:
假說H5:經營者的任命權力關聯和領薪(持股)對改善民營企業績效產生協同促進作用。
在兩職合一民營企業中,經營者的任職權力關聯既具有正面的關系網絡資源效應,又產生負面的精力分散制約效應。受利益趨同效應以及身份激勵效應的驅使,在企業領薪或持股的經營者有積極性利用一切手段為企業尋求所需的各種資源,最大限度地發揮任職權力關聯的關系網絡資源效應。另一方面,經營者將花費更多的時間、精力關注企業經營管理活動,努力勤勉盡責地完成其所任職位的任務,緩解精力分散的負面影響。在兩職分設民營企業中,董事長任職權力關聯帶來的精力分散等負面影響并不嚴重,而關系網絡資源效應能夠提升其資源獲取與協調能力。薪酬獲取有助于強化董事長任職權力關聯的關系網絡資源效應,而總經理的情形稍有不同。民營企業總經理任職權力關聯的關系網絡資源效應有限,即使受薪酬激勵驅動,其有動力為企業謀求資源支持,但其獲取或協調資源的能力亦是有限的。需要說明的一點是,領薪或持股通過人力資本定價、身份激勵和利益趨同可以促使總經理花費更多的時間、精力用于優化企業生產經營管理。在經營權與控制權掌握在董事長手中的情況下,總經理更加積極地為董事長決策提供有效信息及智慧共享,盡可能地避免決策失誤,同樣有助于優化企業的資源配置并實現良好的經營效益。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說H6:
假說H6:經營者的任職權力關聯和領薪(持股)對改善民營企業績效產生協同促進作用。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取及數據來源
鑒于2011年以后我國資本市場的政策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本文以2005-2011年為研究窗口,對滬深兩市A股主板民營上市公司進行篩選,最終確定包含2080個樣本點的有效樣本。具體篩選步驟如下:①考慮到PT類和ST類公司的財務報表存在失真的可能性,予以剔除;②由于金融類公司財務指標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剔除保險、證券、銀行等金融類公司;③經營者變更屬于重大事項,會影響研究結果的穩定性,剔除董事長或總經理連續兩年或兩年以上發生變更的公司;④為消除極端值的影響,采用縮尾方法處理了高于95%分位數和低于5%分位數的樣本點。
手工整理獲取經營者股東權力關聯的相關數據。檢索公司高管人事信息以及查閱公司財務報表,判斷經營者是否擁有股東權力關聯。若經營者由實際控制人或家族成員親自擔任,或者由控股股東任命/推薦而來,或者曾在控股股東單位擔任中高層職務,則認定其擁有任命權力關聯;若經營者同時在控股股東單位擔任一定的高管職務,則認定其擁有任職權力關聯。其它數據主要來源于色諾芬(CCER)數據庫以及國泰安(CSMAR)數據庫。
(二)指標設置
1. 被解釋變量
在這里,本文實證研究了以企業績效為被解釋變量,并且參考Koka and Prescott[10]以及李新春等[3]的做法,企業績效采用ROE和托賓Q兩個指標來度量。
2. 解釋變量
鑒于經營者的股東權力關聯帶有明顯的0-1屬性,本文設置若干虛擬變量。①App:若經營者擁有任命權力關聯,App取值為1,否則為0;考慮到兩職分設公司存在董事長和總經理兩位經營者,分別設置App_BC、App_CEO來度量二人的任命權力關聯。②Off:若經營者擁有任職權力關聯,Off取值為1,否則為0;類似任命權力關聯,針對兩職分設公司的董事長和總經理,分別以Off_BC、Off_CEO來度量其任職權力關聯。
為檢驗薪酬激勵對股東權力關聯績效影響的調節作用,設置薪酬變量Sal和Sha。①Sal:若經營者在上市公司領薪,Sal取值為1,否則為0;以Sal_BC度量兩職分設公司中董事長的領薪情況,以Sal_CEO度量兩職分設公司中總經理的領薪情況。②Sha:若經營者在上市公司持股,Sha取值為1,否則為0;以Sha_BC度量兩職分設公司中董事長的持股情況,以Sha_CEO度量兩職分設公司中總經理的持股情況。
3. 控制變量
借鑒既有研究文獻[11-12]的做法,設置可能影響企業績效的多個控制變量,具體見表1。

表1 本文設置的控制變量
(三)模型設定
(1)
(2)
上述模型中,i表示公司,t表示年度;εit為隨機擾動項,ai表示不隨時間改變的影響因素;Performance表示ROE或托賓Q;模型1主要用于檢驗經營者股東權力關聯的績效影響,解釋變量是App和Off;模型2旨在檢驗薪酬激勵對股東權力關聯績效影響的調節作用,除App和Off外,解釋變量增加了App×Sal、App×Sha、Off×Sal、Off×Sha等四個交叉項。對于兩職分設公司而言,App、Off、Sal和Sha采用App_BC、Off_BC、Sal_BC和Sha_BC,或App_CEO、Off_CEO、Sal_CEO和Sha_CEO。
四、實證檢驗結果
(一)主要變量的描述性分析
由表2可知,2080家民營控股公司的ROE均值為0.0802,托賓Q均值為1.8887,二者標準差分別為0.0976和0.9324;在377家兩職合一公司中,App均值為0.7348,Off均值為0.4297,說明平均73.48%的經營者擁有任命權力關聯,42.97%的經營者擁有任職權力關聯;在1703家兩職分設公司中,App_BC均值為0.8097,App_CEO均值為0.3570,說明平均80.97%的董事長和35.70%的總經理擁有任命權力關聯。初步推斷實際控制人或控股股東更傾向于任命民營企業的董事長。Off_BC均值為0.6653,Off_CEO均值為0.2184,表明平均66.53%的董事長和21.84%的總經理擁有任職權力關聯,更多的董事長在控股股東單位任職。分組均值差異檢驗結果顯示:在兩職合一公司中,基于App或Off的分組ROE和托賓Q均值與參照組不存在顯著性差異,粗略推斷經營者的股東權力關聯對企業績效不存在重要影響;在兩職分設公司中,基于App_BC或Off_BC的分組ROE均值顯著大于參照組,而托賓Q均值并未發生顯著變化;基于App_CEO或Off_CEO的分組ROE和托賓Q均值與參照組不存在顯著性差異,初步表明董事長的股東權力關聯對兩職分設民營企業的經營效益影響顯著,而總經理的股東權力關聯則不然。

表2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分析
(二)基于兩職合一公司樣本的回歸結果
表3給出了基于兩職合一公司樣本的回歸結果。整體來看,App和Off的系數均為負,但無法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在兩職合一民營企業中,無論是任命權力關聯還是任職權力關聯都不會對企業績效產生顯著影響。假說H1和H3得到經驗數據的支持。Model 2-4中,App×Sal和Off×Sal的系數均為正,且基本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說明在兩職合一公司中經營者領薪能夠影響股東權力關聯的績效影響,股東權力關聯和領薪對企業盈利存在協同促進作用;與之類似,App×Sha和Off×Sha的系數同樣為正,且具有統計意義上的顯著性,表明在兩職合一公司中經營者的股東權力關聯和持股對企業盈利存在正向交叉作用。這些結果有力地支持了假說H5和H6。Model 6-8中,App×Sal和Off×Sal的系數為正,盡管未能通過顯著性檢驗,仍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經營者的股東權力關聯和領薪對企業市場價值存在協同促進作用;App×Sha和Off×Sha的系數為正,在10%水平下顯著,說明經營者的股東權力關聯和持股對企業市場價值存在協同促進作用,再次支持了假說H5和H6。

表3 基于兩職合一公司樣本的回歸結果
(三)基于兩職分設公司樣本的回歸結果
對于兩職分設公司樣本,首先檢驗董事長的相關數據,見表4。在Model 1-4中,App_BC和Off_BC的系數顯著為正,在很大程度上表明董事長的股東權力關聯對于改善企業盈利有積極作用;App_BC×Sal_BC和Off_BC×Sal_BC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董事長領薪有助于強化股東權力關聯對企業盈利的促進作用;然而,App_BC×Sha_BC和Off_BC×Sha_BC的系數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在Model 5-8中,App_BC和Off_BC的回歸系數都不具備統計意義上的顯著性,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董事長的股東權力關聯并不會對企業市場價值產生重要影響。App_BC×Sal_BC和Off_BC×Sal_BC的系數不具有顯著性,而App_BC×Sha_BC和Off_BC×Sha_BC的系數顯著為正,意味著董事長持股有助于實現股東權力關聯對企業市場價值的積極作用,而領薪并不具備這種調節作用。總體來看,在兩職分設民營企業中,董事長的股東權力關聯有助于改善企業盈利,但無助于提升企業市場價值,部分支持了假說H2和H4。托賓Q是公司市場價值與資產重置價值的比值,在很大程度上是全體投資者智慧以及情緒的結果,董事長股東權力關聯這一變量的影響尚不足以體現出來。董事長的股東權力關聯和領薪對企業盈利存在顯著的協同促進作用,董事長的股東權力關聯和持股對企業市場價值存在顯著的協同促進作用,假說H5和H6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支持,也恰好印證了年薪和持股分別是從短期和長期兩個角度設計薪酬制度的結果。
下面分析兩職分設公司樣本中總經理的相關數據,見表5。在Model 1-4中,App_CEO和Off_CEO的系數為負,基本通過了顯著性檢驗,意味著總經理的股東權力關聯對于企業盈利存在消極影響;App_CEO×Sal_CEO和Off_CEO×Sal_CEO的系數在1%水平下顯著為正,而App_CEO×Sha_CEO和Off_CEO×Sha_CEO的系數不顯著,表明領薪有助于抑制總經理股東權力關聯對企業盈利能力的消極影響,而持股并不具備這種調節作用。在Model 5-8中,App_CEO和Off_CEO的系數為負,且分別在10%和5%水平下顯著,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兩職分設民營企業中總經理的股東權力關聯可能導致企業市場價值顯著降低;App_CEO×Sal_CEO和Off_CEO×Sal_CEO的系數均為正,且具有統計意義上的顯著性,而App_CEO×Sha_CEO和Off_CEO×Sha_CEO的系數不顯著,又一次表明領薪有助于抑制總經理股東權力關聯對企業績效的消極影響,而持股并不具備這種調節作用。概括來講,兩職分設民營企業中總經理的股東權力關聯對企業績效存在顯著的消極影響,支持了假說H2,但與假說H4不符。后者可能是因為擁有任職權力關聯的總經理往往與實際控制人存在血親(或姻親)關系,導致總經理在情感上過度依賴實際控制人(或董事長)并一味支持后者的決策。總經理的股東權力關聯和領薪對企業績效存在協同促進作用,而股東權力關聯和持股對企業績效不會產生顯著的交叉作用,部分支持了假說H5和H6。究其原因,可能是總經理持股強度偏低。李斌和孫月靜[13]研究發現民營上市企業中總經理的持股強度遠小于董事長,前者的激勵效果也要遜于后者。

表4 基于兩職分設公司樣本董事長相關數據的回歸結果

表5 基于兩職分設公司樣本總經理相關數據的回歸結果
五、結 論
受傳統文化及制度環境的影響,我國民營企業存在明顯的實際控制人主導的家族控制特征。即使上市之初民營企業按照證監會相關要求,建立了股東會、董事會和監事會等組織機構,形式上具備了現代公司治理結構,但并未真正做到遵循現代企業制度進行管理。隨著接班大潮的來臨,“子承父業”或“女承父業”現象凸顯,加重了民營企業的家族控制色彩。
鑒于民營企業經營者的任命和職務受到大股東意志的影響,本文以實際控制人為邏輯起點,理論剖析了民營企業經營者的股東權力關聯及其績效影響,并探討了薪酬激勵對其績效影響的調節作用。實證檢驗發現:①在兩職合一民營企業中,經營者的股東權力關聯對企業績效不存在顯著影響;②在兩職分設民營企業中,董事長的股東權力關聯有利于改善企業績效,而總經理的股東權力關聯對企業績效不存在顯著影響或產生不利影響;③薪酬激勵有助于強化經營者股東權力關聯的積極影響,抑制其消極影響。
根據研究結論,本文就民營企業中經營者權力配置提出四點建議:第一,考慮到兩職合一情況下,經營者能力有限和精力分散抑制了股東權力關聯的積極效應,再加上民營企業的集權文化和權威治理會伴隨接班大潮逐漸消逝,建立民營企業的經營者由董事長和總經理二人共同擔任,即兩職分設。第二,董事長可由實際控制人或家族成員親自擔任,或由控股股東任命/推薦產生,或從控股股東單位選派,并且可繼續在控股股東單位擔任核心高管職務(如董事長或總經理)。如此,有利于充分發揮董事長股東權力關聯的控制權激勵、權威治理以及關系網絡資源效應。第三,總經理應由內部競選或市場選聘產生,且不得在控股股東單位任職。即使民營企業中存在董事長絕對權威的現象,具備經營才能和獨立判斷力的總經理通過信息溝通和智慧共享能夠弱化董事長股東權力關聯的不利影響。第四,借鑒國外家族企業高管薪酬激勵的經驗教訓,完善經營者年薪和股權激勵制度,特別是增強總經理的持股激勵強度,挖掘薪酬激勵對經營者股東權力關聯績效影響的調節作用。
[1] Sesil J C, Lin Y P. The impact of employee stock option adoption and incidence on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US panel data[J]. Industrial Relations: a Journal of Economy and Society, 2011, 50(3): 514-534.
[2] 周仁俊, 楊戰兵, 李勇. 管理層薪酬結構的激勵效果研究[J]. 中國管理科學, 2011, 19(1): 185-192.
[3] 李新春, 楊學儒, 姜岳新, 胡曉紅. 內部人所有權與企業價值——對中國民營上市公司的研究[J]. 經濟研究, 2008(11): 27-39.
[4] 柯大鋼, 畢艷杰. 董事會家族特征與公司績效研究[J]. 經濟管理, 2006(14): 34-38.
[5] 王河森, 陳凌, 王明琳. 親情原則還是能力取向?——家族上市公司權力配置機制的實證研究[J]. 財經論叢, 2012(2): 104-110.
[6] Pérez-González F. Inherited control and firm performance[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6, 96(5): 1559-1588.
[7] 秦麗娜. 自然人控股公司的治理與績效[M]. 北京: 經濟管理出版社, 2009.
[8] Burkart M, Panunzi F, Shleifer A. Family firms[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03, 58(5): 2167-2202.
[9] 張敏, 姜付秀. 機構投資者、企業產權與薪酬契約[J]. 世界經濟, 2010(8): 43-56.
[10] Koka B, Prescott J. Designing alliance networks: the influence of network position,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strategy on firm performance[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8, 29(6): 639-661.
[11] Gottesman A A, Morey M R. Manager education and mutual fund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Empirical Finance, 2006, 13(2): 145-182.
[12] David P, O’Brien J P, Yoskikawa T. The implication of debt heterogeneity for R&D investment and firm performanc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8, 51(1): 165-181.
[13] 李斌, 孫月靜. 經營者股權激勵、約束水平與公司業績——基于民營上市公司的實證分析[J]. 中國軟科學, 2009(8): 119-131.
責任編輯、校對:李斌泉
2016-07-17
王新霞(1985- ),女,山東省聊城市人,西安外國語大學經濟金融學院講師,經濟學博士,研究方向:公司治理;柳 春(1987- ),陜西省榆林市人,西安交通大學金禾經濟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營企業與經濟轉型。
A
1002-2848-2016(05)-010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