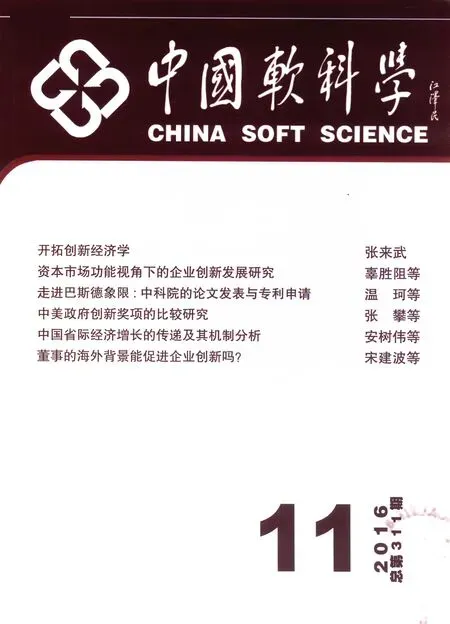長江中游城市群可持續發展對策研究
周正祥,張楨禛
(長沙理工大學 交通經濟研究所,湖南 長沙 410015)
?
長江中游城市群可持續發展對策研究
周正祥,張楨禛
(長沙理工大學 交通經濟研究所,湖南 長沙 410015)
依托長江黃金水道優勢,主動承接“一帶一路”區域經濟發展,打造經濟增長級,推進產業集群發展,鞏固城市群核心競爭力,是實現長江中游城市群可持續發展的關鍵。為研究長江中游城市群可持續發展,文章通過分析長江中游城市群可持續發展支撐條件,采用面板數據從長江中游城市群經濟聯系強度、產業集群輻射作用、需求結構、交通設施改善等角度出發,研究了現階段長江中游城市群可持續發展面臨的問題,提出了資源因地制宜利用、產業轉移發展等對策建議,對長江中游城市群可持續發展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長江中游城市群;可持續發展;長江黃金水道
一、問題的提出
1987年,以挪威前首相布倫特蘭夫人為首的WECD成員們向聯合國大會提交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首次正式提出了“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和模式。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是一種注重長遠發展的經濟增長模式,反映了“動力、質量、公平”的有機統一。2015年4月5日,李克強簽批《長江中游城市群發展規劃》,這是貫徹落實長江經濟帶國家戰略的重大舉措,是《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出臺后批復的第一個跨區域城市群規劃,對于加快中部地區全面崛起、探索新型城鎮化道路、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加速發展、我國發展進入新常態的大背景下,長江中游城市群已成功走過了一段非均衡發展之路,城市化速度不斷加快。但城市化水平依然很低,呈現“虛高”和“冒進”態勢,發展中的各種矛盾急劇增加,城市群內核心城市輻射帶動作用不強,需求結構不穩定,交通網絡系統層次低等問題依然存在。因此如何對長江中游城市群未來發展提供建設性政策,將長江中游城市群建設成為長江經濟帶重要支撐、全國經濟新增長極、推進城市群可持續發展,是政府百姓普遍關注的問題。因此,就長江中游城市群可持續發展建設問題進行專題研究,有利于跨區域整合優化資源要素,探索城市群合作發展的新路徑和新模式,引領全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
二、國內外研究現狀述評
(一)國外研究現狀
1.城市群發展
早在20世紀初,國外學者對城市的規模、特點進行了深入研究。戈特曼(1957)提出大都市帶特點:由多個發育成熟、各具特色的都市區鑲嵌形成自然、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多方面有機聯系、分工合作的組合體[1]。其他學者則根據不同方法對城市群進行劃分,Harris C D(1954)根據銷售額指標對城市規模進行設定[2],Brü lhart M(2006)則根據地區生產總值GDP來度量城市規模[3],Ottaviano G I P(2006)和Mu L, Wang X(2006)直接通過Voronoi圖對城市空間進行空間分割[4]。此外,Holden(2004)提出了城市發展的四種模式:城市蔓延、綠色城市、緊湊型城市、分散集中型,并認為分散集中型更有利于城市的可持續發展[5]。
2.城市群可持續發展
1987年可持續發展作為一種環境管理思想被提出,此后可持續發展逐漸成為一種價值觀。世界衛生組織(WHO)提出,城市可持續發展應在資源最小利用的前提下,使城市經濟朝更富效率、穩定和創新方向演進。因此學者們建立了各項評價指標評價城市群可持續發展水平。環境問題科學委員會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2008)根據人類活動和環境相互作用的概念模型,提出了一套高度合并的可持續發展評價指標體系——SCOPE指標體系[6]。Frank Nevens(2013)在研究中提出政府沒有從長遠角度衡量消費與生產的經濟總值,因此通過模擬“城市轉型實驗室”,提出創新有利于城市群可持續發展[7]。N. Gaitani(2014)從環境與能源的消耗角度,研究雅典中型城市,提出了可持續性城市化與資源可用性、環境惡化和能源消耗等有著密切關系[8]。Patrick T.I. Lam(2015)認為生態承載能力失衡是城市群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指標[9]。國外學者從指標分析與選取的不同角度構建模型對城市群可持續發展進行了驗證分析。
(二) 國內研究現狀
1.城市群可持續發展
20 世紀80年代,周一星首次提出了“都市連綿區”的概念。姚士謀(2006)同樣在《中國城市群》一書中對城市群的概念進行定義[10]。國內學者對城市群發展的研究首先重點在于城市群發展的模式研究。如周永章(2002)對珠三角城市群可持續發展總體格局分析提出 “內外圈層分工”、“點軸集聚發展”、“三大都市區協調建設”和“四種用地模式分類管制”模式[11]。宋建波、武春友(2010)根據協調發展度模型也將城市群劃分4種發展類型[12]。在模型研究方面,刁琳琳(2007)運用層次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構建可持續發展綜合測度體系。張協奎、林劍(2009)使用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并提出消除各城市間的貿易保護主義,減少貿易壁壘,保證要素的自由流通的建議[13]。張遼、楊成林(2014)基于灰色關聯分析方法與變異系數法進行結合,歸納了四個影響中國城市群可持續發展水平的因素:經濟發展水平(EDL),社會進步程度(SPD),生態環境因素(EEF),資源供給能力(RSC)[14]。王麗(2013)則從核心指標人口與企業和輔助性指標工資、產品、投資、公共服務兩方面利用潛力模型度量城市規模[15]。
2.長江中游城市群可持續發展
早在 1995 年,國內就有學者提出依托湘鄂贛“加速建設長江中游城市群區”的建議。肖金成(2008)提出長江中游城市群具有兩頭強中間弱的格局,沒有形成合理的分工模式[16]。魏后凱(2012)提出了長江中游城市群的建設有利于擴大內需和中西部市場的重要意義。吳道子(2015)則從交通運輸方面指出以長江“黃金水道”為突破口,構建互聯互通的區域交通運輸網絡可以推進區域一體化的進程[17]。
(三)國內外研究述評
國內外學者對城市群可持續發展研究較早,形成了比較完善的體系模型,研究成果的應用效果明顯。國內外學者主要是從城市群規模的劃分、以及城市群可持續發展的指標選取進行不同方向的研究。研究結論歸結于城市群的不同發展模式與運行機制以及影響城市群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因素。對單個城市群有較為豐富的研究成果,但對長江中游城市群整體的可持續發展、運行動力機制以及存在問題的研究文獻資料不全面,因此在對現有的研究基礎上,結合在長江黃金水道的背景下,對長江中游城市群可持續發展的現狀、制約因素、發展模式進行深入探討,大力促進產業結構優化發展,提升經濟、生態、資源的可持續發展潛能。
三、相關概念
(一)相關概念
1.城市群
城市群是在特定的區域范圍內聚集相當數量的不同性質、類型和等級規模的城市,以一個或兩個(有少數的城市群是多核心的例外)特大城市(小型的城市群為大城市)為中心,依托一定的自然環境和交通條件,城市之間的內在聯系不斷加強,共同構成一個相對完整的城市“集合體”。
根據國內外學者的研究,總結得出城市群的演進方式與基本特征(表1)。

表1 城市群的演進方式與基本特征
2.長江中游城市群
長江中游城市群是以武漢城市圈、環長株潭城市群、環鄱陽湖城市群為主體形成的特大型城市群,涉及湖南、湖北、江西三省份,國土面積約31.7萬平方公里,承東啟西、連南接北,是長江經濟帶三大跨區域城市群支撐之一,也是實施促進中部地區崛起戰略、全方位深化改革開放和推進新型城鎮化的重點區域,在我國區域發展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
2012年2月,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在武漢簽署了《加快構建長江中游城市集群合作框架協議》。“中三角”的概念正式提出,名稱呼應“長三角”和“珠三角”。2012年12月28日,在江西九江召開的區域發展與改革座談會上,有關方面建議,把安徽也納入長江中游城市群。2013年,由于安徽省會合肥的加入,武漢、長沙、南昌由“中三角”變為“中四角”。但2014年9月,國務院出臺關于長江經濟帶發展的指導意見,其中明確把合肥都市區劃入長三角,長江中游城市群由武漢、長沙、南昌三大城市組團。2015年國務院批復的《長江中游城市群發展規劃》,再次明確了界限,因此長江中游城市群將與“一帶一路”相關地區形成上下覆蓋關系,彼此支撐、交相輝映。從2013年的《武漢共識》到2014年的《長沙宣言》,再到如今的《規劃》,一個繼“珠三角”、“長三角”、“環渤海”之后的新增長極正在崛起。
四、長江中游城市群可持續發展的支撐條件
(一)長江中游城市群空間布局
長江中游城市群(圖1)是由武漢城市圈、環長株潭城市群、環鄱陽湖城市群為主體構成的多中心城市群,是我國具有優越的區位條件、交通發達、產業具有相當基礎、科技教育資源豐富的城市群之一,具有多中心結構、一體化網絡的結構模式。
長江中游城市群 2014 年實現地區生產總值達 6 萬億元,占全國約 9.4%,總人口約2.22億人,占據全國的16.2%,總面積約為31.7萬平方公里。具有繼長三角、珠三角與環渤海地區之后,成長為全國第四經濟增長極的巨大潛力,在我國未來空間開發格局中,具有舉足輕重的戰略地位和意義。
三大城市群構成長江中游城市群的主體,對我國中部地區的經濟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構成湖北的武漢都市圈(1+8)“極核網絡”模式、湖南的環長株潭城市群(3+5)“成長三角”模式和江西的環鄱陽湖經濟圈(3+6)“雙核驅動”模式(表2)。

圖1 長江中游城市群空間布局

表2 三大城市群的主要覆蓋城市
(二)豐富的資源為可持續發展提供充足的資源支撐
長江中游城市群擁有著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優勢,江河縱橫,河港溝渠交織,湖泊庫塘星布,幅員遼闊的鄱陽湖是中國第一大淡水湖,洞庭湖為全國第二大淡水湖,洪湖、東湖等水湖形成以長江為干流的龐大水網,水流、水庫占比較高。背倚長江經濟帶,擁有豐富的地下水資源,可作為醫療水源、礦產養殖。城市群內擁有豐富的礦產資源,鐵礦石探明儲膨潤土、珍珠巖等31種非金屬礦探明儲量,被譽為鄂東“聚寶盆”。 擁有全國最大的熔劑石灰石、白云巖、石英砂巖基地。形成鐵礦開采到鋼鐵冶煉的冶金產業集群。物產富饒,分布著物種獨特稀有的動植物、古老植物、“活化石”銀杏等。俗有“湖廣熟,天下足”之謂,是著名的“漁米之鄉”。礦產豐富,礦種齊全,是馳名中外的“有色金屬之鄉”和“非金屬礦之鄉”。
(三)經濟實力為可持續發展提供強大的經濟保障
長江中游城市群是中國發展較早、基礎較強的老牌工業重地之一。隨著長江經濟帶沿線城市的發展,該地區工業發展迅猛,工業產值屢創新高。2014年長江中游城市群GDP總值為73524.33億元。占全國總值的11.6%。長株潭城市群形成了 “5+5+X”的產業布局即新材料、高端裝備等5個主導產業;移動互聯網、綠色建筑、高技術服務業等5個先導產業;以及3D打印、工業機器人、可穿戴設備等一批產業呈現齊頭并進的態勢,統籌產業集群發展。2015年武漢城市圈中建三局綠色建筑產業園、機器人產業、天馬第6代低溫多晶硅(LTPS)生產線建成投產,引導圈內大中型企業建設技術研發中心,進入全國智能裝備產業示范基地名錄。提出“互聯網+產業”發展的五大目標、六大任務,利用“互聯網+”創新產業發展新模式,提升傳統產業。江西省有色金屬行業制造行業、鋼鐵行業、鋰電產業引領新興產業經濟,2015年綠色食品制造業完成增加值461.8億,占江西省十大戰略性新興產業的22.2%。形成以軌道交通、智能裝備制造、新型材料、有色金屬為主導產業,集工程機械、農業機械、環境產業和金融服務等多板塊為一體的高端裝備產業經濟帶(圖2)。
以上數據統計分析反映了三大城市群主要城市中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呈逐年遞增的趨勢,武漢城市圈則遙居榜首,經濟發展潛力巨大。為企業經濟可持續發展夯實了堅固的基礎。2014年武漢、長沙、南昌三次產業比分別為:3.5:47.5:49.0,4.0:54.3:41.7,4.5:55.0:40.5,工業、服務業占比均衡,提供較為雄厚的產業體系基礎。
(四)潛力巨大的科技教育實力為可持續發展提供人力基礎
長江中游城市群擁有濃厚的文化底蘊,經過長期的文化積累,具有較為健全的教育體系與優勢。2014年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擁有普通高校329所、重點高校12所,三省普通高校與重點高校分別占全國高校數量的12.9%、9.1%,擁有國家級重點實驗室154所,國家級工程技術研究中心132所,在校研究生21.07萬人,在校大學生347.17萬人,優秀的精英和先進的技術為城市群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物力資源。龐大的規模和高素質人才充分的顯示了城市群的科技實力和潛力優勢。

圖2 2009-2014年三大城市群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數據來源: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統計年鑒2009-2014年)
(五)區位交通優勢為其可持續發展提供便捷的區位條件
長江中游城市群具有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獨特的地理位置占據著國家的中心,以平原為主的地形為交通運輸提供了便利。在公路上,環長株潭城市群構建“一核、主軸線、半圓、支線”的交通網絡(圖3),武漢城市圈“一體化”的綜合交通運輸體(圖4)與環鄱陽湖城市群“三縱四橫”高速公路主骨架(圖5)基本建成。城市群交通運輸系統正朝著信息化、現代化的方向發展:大陸運輸安全衛星定位導航監控系統、道路運政管理系統、稽查征費業務管理系統、高速公路聯網收費ETC系統的逐步建成與完善,使得交通運輸網絡深度與廣度初步實現。公路建設已進入以高速公路和特大型橋梁為代表的現代化交通新紀元。在水路上,三省積極融入國家“一帶一路”戰略、加快推進長江經濟帶建設,相繼開通了中國遠洋岳陽—澳大利亞接力航線開通,岳陽—東盟接力航線,承接了絲綢之路的航線發展。2015年長江干線貨物通過量達到21.8億噸,與2010年的15.02億噸相比,5年增長超過45%。航道通暢,葛洲壩船閘及三峽船閘年貨物通過量相繼創歷史新高,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江海聯運”。“十二五”以來,水運行業以轉方式調結構為主線,做好“加”“減”法,加大“調”的力度,加快“轉”的步伐,激發市場活力與發展動力。在鐵路上, 2016年長株潭城際鐵路建成后 “半小時通勤圈”為交通出行提供了便捷。長沙將精心規劃湘江兩岸城市建設與空間形態,加快“公交都市”建設,啟動城市慢行系統和“海綿城市”建設。在航空發展上,武漢城市圈的天河機場,環鄱陽湖城市群的南昌昌北國際機場、景德鎮機場和環長株潭城市群長沙的黃花機場為空運提供了有力的基礎設施。

圖3 環長株潭城市群交通布局圖

圖4 武漢城市圈交通布局圖

圖5 環鄱陽湖城市群公路網絡布局圖
五、長江中游城市群可持續發展面臨的問題及原因
(一)經濟聯系強度不足
在研究測算城市間經濟聯系強度的過程中,地理學家塔費根據引力模型得出經濟聯系強度的測算公式:
(1)
其中R為經濟聯系強度;Vi、Vj為兩城市的工業生產總產值;Pi、Pj分別為i、j兩城市的總人口數;Dij為i、j兩個城市之間的最短交通距離。
根據數據統計計算出三大中心城市武漢、長沙、南昌三市的經濟聯系強度,如下表(表3,表4)。

表3 武漢、長沙、南昌統計值

表4 三大中心城市經濟聯系強度隸屬度分析
(數據來源: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統計年鑒2015年)
從區域經濟聯系層面分析,三省會中心城市呈現出不強的經濟聯系態勢,但武漢與長沙的經濟聯系強度指數57.32高于武漢、長沙兩市與南昌的經濟聯系強度指數31.81與20.21,南昌作為長江中游城市群的三大中心城市之一,發展明顯落后與武漢長沙,動力不足,沒有形成具有核心競爭力的城市產業基礎和特色,地區生產總值3667.96億元明顯低于武漢10069.48億元。
武漢、長沙、南昌雖然是交通要道,運輸便捷,但由于公路規劃不完善,存在許多斷頭路的現象,造成彼此之間的聯系不暢。各獨立的中心城市之間沒有建立完善的運輸體系和貿易制度,導致經濟要素往來分布不均。城市集群的形成需要周邊小城市的相互依存關系形成強大的依托支撐力量,促進區域內各種要素的自由流動。城市群內核心城市與大中小城市尚未形成良好的分工、協作、互補關系,城鎮梯度建設結構不緊密,聯系密度不緊切,城市功能定位不清晰,低水平重復建設仍較普遍,使得城市體系呈兩頭強中間弱的格局。
(二)核心城市對城市群的輻射帶動作用不強
統計武漢、長沙、南昌核心地區經濟產業,占全省經濟的百分比,對全省經濟貢獻率(表5,圖6)。
統計分析,武漢、長沙、南昌的地區總值占區域內經濟總值的比例分別為26.79%、28.90%、23.34%,略高于廣州和深圳,成為三省內部經濟的主要支撐。武漢、長沙、南昌三座省會城市產業發展能力充足,單個城市的有支撐經濟能力,但是總體上而言城市群的經濟密度不強。和珠三角城市群深圳、廣州相比,雖然第一產業農業發展潛力大,但是二、三產業工業、服務業發展不足,尤其是服務業發展嚴重落后,南昌城市工業服務業發展則明顯落后于武漢、長沙地區。工業發展是一個地區的經濟支柱,而服務業的發展帶動了地區消費結構的變化,促進就業率的提升,從而帶動地區生產總值的大幅度提高。縱向觀測表格數據,長江中游城市群中心城市經濟發展潛力大,卻不能帶動周邊城市發展,金融、貿易中心實力不足,經濟發展很不均衡。而和較為發達的珠三角城市群相比,深圳、廣州發展則較為均衡。

表5 中心城市三次產業經濟值表

圖6 中心城市三次產業經濟值圖(數據來源: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廣東省統計年鑒2014年)
由于群內城市有效基礎設施的不足,聯通性較差; 產業結構趨同,產業競爭過度,管理制度的不完善,跨行政區域的產業轉移無法實現,不僅阻礙了當地進行產業結構的高度化轉型,也阻礙了地區差距的縮小。對于內部產業集群,未充分發揮市場與政府調節作用并存,沒有明確好二級城市群產業分工,導致多處地方呈現產業趨同現象,使得集群優勢不明顯,劣勢產業未能快速提高發展水平。在城市體系上,發展成熟的城市群都具備比較完善的城市等級結構,而對于長江中游城市群,三中心城市在經濟總量與城市功能上存在較為明顯的距離,三省城市群內部其他城市與中心城市的差距也過大。
(三)教育資源分布不均
根據數據繪制重點城市(武漢、長沙、南昌)教育結構圖表(圖7)。
三大城市群核心城市武漢、長沙、南昌三座城市的在校大學生、在校研究生、重點高校、普通高校占湖北、湖南、江西三省的百分比分別為64%、86%、100%、58%。優秀的人力教育資源密集地匯聚在省會城市,省會城市中心能力比較強。
教育科研發展過于集中在中心城市,對周邊城市沒有有很好的輻射作用。資源分布的不合理性使得中心城市知識密集型產業越來越多,吸引了外部投資和勞動要素的不斷流入,使得周邊城市人才的流失,不能充足地積累人力資源和科研資源,城鎮化率指數不高,資源密集集中在省會城市。呈現中心城市越來越強、附屬城市越來越弱的趨勢,形成周邊城市發展滯后中心城市5-10年之久的局面。

圖7 2015年三大中心城市教育資源分別占三省百分比(數據來源: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統計年鑒2015年)
(四)社會層面負擔過重
城市政府和企業負擔過重、社會保障工作滯后、就業壓力較大,地區財政收入經濟值對承擔人民保障生活負擔過重。由2010-2014年五年的數據可以看出,湖北、湖南、江西三省離退休養老保險參與者與在職養老保險參與者相比比重較大,政府要負擔沉重的保險繳納費,加重了社會的負擔(表6)。

表6 三省社會保障參與人 (單位:萬人)
(數據來源: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統計年鑒2010-2014年)
我國的經濟處于一個大轉軌時期,市場、企業、政府都由二元結構向一元結構轉型,國家需要新鮮的血液注入。而我國提前進入老年化城市,退休人員勞動能力下降,市場勞動力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養老保險中的經濟補償是作為老年退休人員收入保障的來源。由政府、企業負擔的過重的養老負擔使得經營效率降低,同時存在一定的運營風險,對投資效應、收入再分配效應、儲蓄效應都有深重的影響。因此十三五規劃中也明確提出實現職工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建立基本養老金合理調整機制。
(五)需求結構不穩定
需求結構決定著相應的產業結構,需求結構合理性與產業結構合理性呈正向變動關系。需求結構合理性能夠反映經濟結構的合理性。從對外貿易依存度、投資率和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增長率三個方面對武漢、長沙、南昌三個城市需求結構進行評價(圖8,圖9,圖10)。
對外貿易依存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一地區對外貿易在其區域經濟中的重要性。對外貿易依存度越高,表明該地區經濟發展對外貿的依賴程度越大,同時也表明對外貿易在該區域經濟中的地位越重要。武漢、南昌的對外貿易依存度明顯高于長沙,說明長沙的對外貿易發展優勢不足,能力不夠。同時也體現了長沙的外商投資流入較少,積極性不高,跨國企業數量明顯趨勢不足。長沙與武漢的投資率較相近,南昌的當地投資呈逐年上漲趨勢。南昌、長沙的社會消費率基本呈逐年增長趨勢,但武漢的社會消費率明顯偏高于其他兩市,合理的投資率要與消費率相適應,武漢城市的投資率與消費率偏差不大。武漢經濟發展較為突出,動力十足,社會消費總值高,從需求方面推動了企業經濟的發展。

圖8 2014年武漢、長沙、南昌三市對外貿易依存度

圖9 2014年武漢、長沙、南昌三市投資率

圖10 2014年武漢、長沙、南昌三市社會消費率(數據來源: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統計年鑒2014年)
需求結構不足存在的原因有幾點:第一,由于武漢、長沙、南昌地處中部城市,缺乏有力的對外貿易的地理優勢,航海運輸與沿海發達城市相比劣勢明顯。第二,國營企業占比較大,民間私企發展不足,外商投資企業存在空隙,商業模式單一,經濟缺乏活力。第三,對于進出口貿易,由于地方政府保護主義的存在,各地區設置了較高的市場準入標準,導致進出口額呈現下滑趨勢,阻礙了對外貿易之間正常的商品流。第四,國民需求持續低迷,消費指數不高,無法帶動生產力的發展和企業的生產,進一步導致失業率的增加。
(六)資源過度開發,能源利用效率不高
能源消費彈性系數的發展變化與國民經濟結構、技術裝備、生產工藝、能源利用效率、管理水平乃至人民生活等因素密切相關。在國民經濟中耗能高的部門(如重工業)比重大,科學技術水平還很低的情況下,能源消費增長速度總是比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快,即能源消費彈性系數>1。
選取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以及珠三角地區的能源消費彈性指數繪制成圖11。
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國民經濟結構的變化和耗能工業的迅速發展,能源消費彈性系數會普遍下降。在經濟和科技發展水平都相當高時,能源消費彈性系數可降至0.2 左右,甚至能以能源消費的負增長實現經濟的低速發展,這時能源消費彈性系數亦可出現負值[18]。從湖北、湖南、江西、廣東四省2009-2014年的能源消費彈性系數統計分析得出,珠三角城市群以廣東省為分析,能源彈性系數比較穩定,數值較其他三省相比較為穩定,而珠三角城市群經濟發展較為迅猛,輕工業服務業發展態勢良好,能源消耗低。湖南、江西、湖北三省經濟發展較依賴于能源利用。2013年湖北能源消耗系數甚至達到0.9之高。

圖11 2009-2014省市能源消費彈性系數(數據來源: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廣東省統計年鑒2009-2014年)
中部地區的石油資源不足,主要依賴于礦產、煤炭。部分地區依賴于水能、風能發電。節能資源基礎設施不盡完善,過多地依賴于外部貿易帶來的資源促進企業生產反而限制了企業發展空間。由于自然資源開發市場秩序混亂,資源開發利用效率較低,無法形成區域資源開發利用的綜合優勢;產業結構布局不合理,企業未形成一定的規模效應降低成本,說明了城市群內城市在資源利用、提高效率這一部分有待提升。
(七)交通結構完善度低
城市的空間結構制約著交通運輸系統的發展,而同時交通網絡的層次性同樣影響著城市空間的發展。湘鄂贛三省的交通運輸網絡雖然已經在逐步建設中,但是運輸系統的結構性矛盾、規模不足引致了各種經濟社會問題的矛盾突起。因此選取了湖北、湖南、江西三省的交通運輸量指標繪制成圖(圖12)。
由圖表分析得出,湘鄂贛三省的交通運輸體系較為發達,水陸空發展全方位覆蓋。但是數據顯示公路占值比重大,占所有交通指標的81%。而鐵路和水路分別占值3%、16%,比重明顯低于鐵路貨運量。綜合交通網缺乏統一規劃,鐵路、水路運輸方式不齊全,設施建設重復落后。高速公路能力已經飽和,省內省外都市圈快速通道尚未形成,交通一體化、城市便捷化體系有待改善。

圖12 2014年長江中游城市群湘鄂贛 三省交通運輸貨運量占比 (數據來源: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統計年鑒2014年)
由于交通運輸發展對經濟的推進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作用。經濟的發展有待于便捷的運輸體系的形成,促進運輸成本最小化、效率最大化。公路的運輸對短途運輸快捷便利時間短的效果明顯,但由于公路交通運輸對能源利用消耗品中單一,對石油產品依賴性較高,存在著資源利用程度不高的劣勢。公路耕地占用率比重增大,對用地的不合理性導致土地資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長江中游城市群有著先天的水運優勢,倚靠長江黃金水道,長江航運是貫穿東西的運輸大動脈,是沿江運輸的骨架支撐力量。湖南、江西航運市場不景氣,運價持續走低,企業邊際報酬遞減更加阻礙了航運市場的發展,未能充分發揮航運優勢。交通運輸的建設是一項規模龐大的工程,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資本等其他物質資源。各種運輸系統的建成有著其前評價的時限性與項目建成后的深遠意義需要納入考慮。而由于三省投資比例不足,人力成本逐漸增高,項目可行性研究使得交通運輸建設需要耗費幾年甚至數十年的規劃和動工,因此阻礙了運輸系統格局的發展。城市群需要注入創新的動力,將交通數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深入到交通規劃、建設、運營和管理的各個方面。
六、 促進長江中游城市群可持續發展的對策建議
(一)長江中游城市群的功能定位
打造長江中游城市群建設成為經濟增長極,對城市群的發展應有合理性的布局結構。對城市群設置明確的功能定位,重點發展特色產業與中心城市,推動“極核模式”布局建設,以點帶面協調發展(表7)。

表7 長江中游地區三大城市群功能定位表
(二)強化金三角中心,增強經濟輻射效應
要以武漢為主中心、長沙和南昌為副中心,共同打造漢長昌復合型極核,把武漢城市圈建設成為全國重要的綜合交通運輸樞紐、先進制造業和高技術產業基地、中部地區現代服務業中心。強化“金三角”中心的穩固性,構建布局緊密的運輸網絡,通過城際快速交通體系將各中心城市有機連接起來。全面增強中心城市的綜合實力,提高城市的輻射力度與范圍,著力推進附屬外圍層城市的競爭力,資源整合和產業鏈重組,積極推進武漢城市圈、環長株潭城市群和環鄱陽湖城市群三圈融合,構建一體化的特大型長江中游城市群,將充分發揮“1+1+1>3”的系統集成效應。促進“綠心”漢長昌,兩個城市群的“綠肺”洞庭湖和鄱陽湖生態文明化建設。依托現有國家級開發區和產業基地,提升長江中游城市群開放型經濟走廊發展水平,支持長株潭圍繞“兩型”社會建設,促進武漢城市圈產業高端化發展,增強產業集聚能力,推動環鄱陽湖城市群的生態人居環境建設示范區和低碳經濟創新發展示范區,發展生態經濟、循環經濟。
(三)完善教育基礎網絡建設
武漢、長沙、南昌作為科教資源比較密集的城市,可以共同建立一批協同創新平臺,推動創新驅動轉型升級,建設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推進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充分發揮政府投入引導作用,推進城區縣教育改革,開發人才資源。保障教育科研合理均衡的分布。優化學科專業布局和人才培養機制,鼓勵具備條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應用型轉變。因此三省應加大力度促進教育機構的完善,使得科研機構與教育設施全面地覆蓋周邊下線城市。科技是改革第一動力,科學技術推進了國家經濟的發展。湖南、湖北、江西三省的教育資源過于集中于省會城市,優秀的畢業生資源密集地聚集在發達城市,導致發達城市更發達、落后城市更落后的局面。政府應該整合資源,鼓勵人才向中小地區城市發展,為地級城市創業人才提供優越的貸款資金條件。
(四)基礎設施互聯互通
完善公路網、水運網、航空港、鐵路網,加快信息網建設,打造交通樞紐,構建一體化交通網絡,實現公路網絡化、客運便捷化、物流智能化、服務最優化的公路運輸體系。提高科研創新能力,集成應用ETC、AIS、CCTV等科技廣泛應用于運輸系統。促進新能源的開發,提高運輸工具對能源的利用率。要充分憑借長江航運優勢,把全流域打造成黃金水道。借助產業集聚的輻射效應擴大航運市場的要素集中與資源發展,充分發揮橫貫東西、聯接南北、江海聯動的優勢,將航運系統的“節點”效應和“輻射”效應全方位覆蓋。推進湘江、漢江、洞庭湖等流域航道整治,打造緊密協作的水運網絡:形成以長江航道為主軸,漢江、洞庭湖水系、鄱陽湖水系為補充,干線暢通、干支銜接的長江中游內河航道體系。加強與武漢城市圈、環長株潭城市群之間的經濟聯系,形成以點帶軸、以軸促面的城鎮集群發展模式。完善互聯互通的陸運網絡:建設以武漢、長沙、南昌為中心的“三角形、放射狀”城際交通網絡,實現省會城市之間2小時通達,省會城市與周邊城市之間1-2小時通達。建設高效便捷的空運網絡:強化武漢天河國際機場、長沙黃花國際機場的區域樞紐功能,發揮南昌昌北機場等干線機場作用,增加國際國內運輸航線。
(五)資源發展因地制宜
對城市群的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進行統籌規劃,保證城市群的可持續發展。要建立城市群統一的開發利用和保護措施,調整電源的結構,加大關停小火電力度,確保“上大壓小”任務的完成,提高資源開發利用效率。交通運輸行業和建筑行業一直是高能耗產業。充分發揮“十三五”規劃會議精神,推進交通運輸低碳發展,實行公共交通優先,實施新能源替代、節水資源計劃,以水定產、以水定城,建設節水型社會。城市群內部在西電東送、西氣東輸的同時可以形成水電-天然氣互補的能源格局,減少原油、油品長途運輸的巨大壓力和高成本,以允許天然氣化工發展來帶動經濟結構的調整,促進東西部能源與經濟協調發展。調整能源消費地區格局,強調能源的就近利用和分布式能源消費,調整電源的結構,提高二次能源利用率,減輕運輸上的巨大壓力。建造綠色經濟、低碳經濟的環保社會,構建沿江沿湖的綠色網絡化廊道。
(六)聯手打造優勢產業集群
發揮產業優勢,擴展延伸產業鏈,依托沿江、滬昆和京廣、京九、二廣“兩橫三縱”重點發展軸線,形成沿線大中城市和小城鎮合理分工、聯動發展的格局,建成特色鮮明、布局合理、生態良好的現代產業密集帶,以武漢、長沙、南昌、株洲、襄陽、景德鎮等為重點,提高勞動密集型產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圍繞裝備制造業技術自主化、制造柔性化、設備成套化、服務網絡化開展合作,著力提高裝備設計、制造和集成能力,支持有自主品牌的龍頭企業繼續做大做強,更廣泛地開辟國內外市場。充分利用產業組織調整結構,建立系統營運中心,由營運中心總部統一指揮協調,諸如引導武漢、長沙、南昌、九江、株洲、湘潭、等地開展汽車產業合作與企業重組,建立汽車產業聯盟,構建配套協作、體系完整的汽車及零部件產業鏈。加快推進武漢城市圈、環長株潭城市群、環鄱陽湖城市群金融協同發展。
(七)促進需求結構轉變
在進出口貿易環節,增強對外投資和擴大出口結合度,提高進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有利地位。培育以技術、標準、品牌、質量、服務為核心的對外經濟新優勢。依托湘江保稅區、臨港產業新區、東湖綜合保稅區建設,規劃自由貿易實驗區。促進“漢-長-南”貿易便利化,打造經濟走廊。推進貿易便利化,全面推廣國際貿易“單一窗口”,實施優進優出戰略,推進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營造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新優勢,提高我國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在居民消費環節,發揮消費對增長的基礎作用,由出口拉動的經濟增長變為依靠消費拉動的經濟增長,擴大內需著力點,轉移發展重心方向。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中堅力量,做好加減法,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使供給和需求協同促進經濟發展,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引導消費朝著智能、綠色、健康、安全方向轉變,以擴大服務消費為重點帶動消費結構升級。在投資環節,發揮投資對增長的關鍵作用,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優化投資結構創新投資方式,增加有效投資,為區域經濟要素自由流通提供便利。帶動社會資本PPP模式的廣泛應用,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
七、研究結論與展望
本文參考了國內外學者對城市群以及可持續發展理論的研究,在此基礎上,對我長江中游城市群部分經濟指標進行面板數據分析,并對城市群可持續發展建設提出了相關政策建議。國家省政府應該加大力度對城市群結構布局進行合理規劃,從需求結構、產業布局、能源利用等角度發展綠色循環經濟。但由于數據的有限性,資料的局限性,限制了研究深入性,并未建立合適的定量分析模型,在今后的研究上需要不斷積累改進經驗,深入探討可持續發展面臨的問題以及原因,不斷完善對策的研究。
[1]Gottmann J. Megalopolis or the urbanization of the northeastern seaboard[J]. Economic Geography,1957, 33(3): 189-220.
[2]Harris C D. The market as a factor in the localization of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54, 44(4): 315-348.
[3]Brülhart M. The Fading attraction of central regions: An empirical note on core periphery gradients in Western Europe[J]. Spatial Economic Analysis, 2006, 1(2): 227-235.
[4]Ottaviano G I P, Pinelli D. Market potential and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finnish regions[J].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006,36(5): 636-657.
[5]Holden E.Ecological footprints and sustainable form[J].Journal of Housing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19(1):91-209.
[6]聯合國人居署.和諧城市——世界城市狀況報告[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8.
[7]Frank Nevens.Urban Transition Labs: co-creating transformative action for sustainable cities[J].Jouru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3,(50):111-122.
[8] Gaitani N, Gaitani N.Microclimatic analysis as a prerequisite for sustainable urbanisation: Application for an urban regeneration project for a medium size city in the greater urban agglomeration of Athens, Greece[J]. 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 2014(13):230-236.
[9] Patrick T.I. Lam.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A review on urban carrying capacity assessment[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5,(46):64-71.
[10]姚士謀.中國城市群[M].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2006:16-37.
[11]王樹功,周永章. 大城市群(圈)資源環境一體化與區域可持續發展研究——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為例[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2,12(3):52-57.
[12]宋建波,武春友 .城市化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評價研究——以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為例[J].中國軟科學,2010(2):78-81.
[13]張協奎,林劍. 廣西北部灣經濟區城市群可持續發展對策研究[J].中國軟科學,2009(5):184-192.
[14]張 遼,楊成林. 城市群可持續發展水平演化及其影響因素研究——來自中國十大城市群的證據[J].統計應用研究,2014,29(1):87-93.
[15]王麗.城市群的界定與識別研究[J].地理學報,2013,68(8):1059-1070.
[16]肖金成.論長江中游城市群的構造和發展[J].湖北社會科學,2008(6):55-59.
[17]吳道子,長江中游城市群構建背景及發展對策[J].區域經濟,2015,6(26),55-59.
[18]張 抗,梅新. 我國能源及油氣彈性系數分析[J]. 中國能源,1992(11):25-29.
(本文責編:王延芳)
Study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ity Group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
ZHOU Zheng-xiang,ZHANG Zhen-zhen
(InstituteofTransportationEconomics,Changsha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Changsha410015,China)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It is essential to build the economic growth level,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consolidate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In order to study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upport condition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using the panel dat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nsity of economic ties, industrial clusters radiation, demand structure and traffic facilit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Middle Agglomeration, and makes suggestions on the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transfer. It is of guiding significanc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golden waterway of the Yangtze River
國家社科基金年度項目(13BJY122);湖南省2015年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15ZDA01);湖南省交通運輸廳科技進步與創新項目(201549);湖南省現代服務業發展與湖南新型城鎮化協同創新中心資助項目;湖南省國際經濟與國際工程管理研究中心資助項目的階段性成果。
周正祥(1965-),男,湖南長沙人,長沙理工大學交通經濟研究所所長、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交通運輸經濟學與高速公路管理。
F061.5
A
1002-9753(2016)11-008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