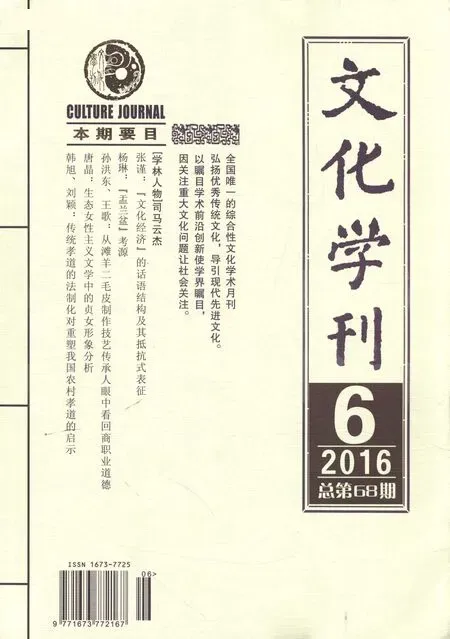淺析佛教發展成為吐蕃社會主流文化的原因
李 艷
(陜西師范大學宗教研究中心,陜西 西安 710000)
?
【傳統文化】
淺析佛教發展成為吐蕃社會主流文化的原因
李 艷
(陜西師范大學宗教研究中心,陜西 西安 710000)
通過對吐蕃社會象雄文明時期的原生性宗教苯教與佛教的傳入背景,佛教與苯教之間的斗爭與融合以及文化間的交流的論述,來研究佛教在西藏文明中成為主流文化的原因。現分別從政治經濟的發展、威權選擇和歷史機遇、佛苯之間內容形式的差異和文化借鑒融合的幾個角度對這個問題進行研究。
苯教;佛教;主流文化;文化借鑒和融合
根據根敦群培的《自史》,苯教來源于吐蕃。苯教,創始人辛饒米沃,藏語為“bon”,又寫作“本教”。現在大部分學者認為苯教起源于約一萬八千年前的象雄王國;也有另一個說法,認為苯教來源于嘉絨地區。苯教現在在四川、青海、甘南均有寺院,全國共有218座苯教寺院。苯教一出現便被置于極高的地位,成為象雄王國的國教。它作為西藏原生性的宗教,具有很強的地域性,并且在地域上影響了東亞文明。在被稱作世界屋脊的廣闊高原和人煙稀少的地方,自然環境十分惡劣,但也造就了苯教信仰者信奉的神山圣湖,苯教認為周圍的動植物都有靈魂。之后苯教改良成為較原始苯教更為完善的雍仲苯教。松贊干布入藏后,建立吐蕃王國,并改象雄文為藏文。與此同時,在統治者權力低于苯教國師權力、封建統治者迫切尋求一種新的宗教代替苯教時,恰好佛教隨著兩位公主,帶著釋迦摩尼八歲和十二歲等身像一同入藏。這時松贊干布順勢引入印度佛教,從此開始了印度佛教和西藏本土宗教苯教的斗爭與融合。當時佛教是一種外來宗教,而吐蕃的本土性信仰以及傳統的苯教信眾遭遇了佛教的入侵,但松贊干布弘揚佛教,抑止苯教發展,苯教信眾自然會抵制佛教。可以這樣認為:從松贊干布建立了統一的奴隸制王朝,到吐蕃社會滅亡這一歷史時期,西藏文化的發展是以佛教文化和苯教文化的不斷沖突、反復較量和最后融合為主線的。苯教作為一種原生性宗教,其信仰神祗并有獨特的儀軌,帶著原始的萬物有靈觀存在于吐蕃社會。佛教作為一種創生性宗教,有較為完整的經典理論體系,但佛教是如何可以在苯教信仰者數千年來根深蒂固的苯教信仰中取得一席之地,并發展成為現在西藏地區的主流宗教文化是非常值得探討的一個問題。
一、政治經濟的發展決定了吐蕃王朝的選擇
在公元7世紀,西藏地區的政治經濟得到極大發展,農業手工業發展迅速,在這種舊的政治經濟發展已不適應新的發展態勢的情況下,西藏客觀上需要打破之前的政治經濟關系,并建立發展適應新的統一的社會政權;加之自古以來西藏天際遼闊人煙稀少的自然條件,使得藏民族生來便具備親近宗教的特征,因此,在古老的苯教已無法適應新的生產力時,客觀上迫切需要一種新的宗教信仰。在松贊干布從雅魯藏布江入藏后,他作為一個強有力的統治者,內外結合,征服了大小羊同、蘇吡等地區,統一了西藏,并使西藏的社會經濟得到了極大發展。他創立了西藏文字,統一度量衡,制定藏法,升級了西藏的經濟治理體系。由于侵犯了苯教舊的貴族勢力,苯教舊的部落貴族與新興的吐蕃王室進行殊死斗爭。在苯教文化中,種族都是平等的,因此其無法承受一個超越于各個部族平等權利之上的政權存在,但因為苯教對西藏的影響已根深蒂固,宗教意識深深滲透到了人們的生活中,所以吐蕃王朝只能求助于當時外來的有更完善教義教理,即佛教,來促進西藏的進一步發展,并鞏固其政治統治。
二、選擇佛教文化是吐蕃社會的威權選擇和歷史機遇所決定的
“一種新的宗教思想信仰,傳到一個陌生的民族中間,并要求取得當地群眾的信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傳教者要善于迎合當地群眾的思想和要求,并且采取一些辦法以滿足他們的要求。理論在一個民族中實現的程度,決定于理論滿足于這個民族需要的程度。”[1]佛教在初入吐蕃及之后的發展成長過程中恰恰符合當時吐蕃時期社會進步的需求。王室是支持佛教發展的首要力量。苯教的僧侶階層在吐蕃社會之前的處于一種教權高于皇權的地位。在見到國師時,信眾會紛紛頂禮膜拜并愿意出資供養苯教高僧。在這個幾乎人人信教的社會中,信眾對苯教的國師的尊崇甚至超過了當時的藏王贊普。在這種情況下,新上任的松贊干布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必須要求消滅舊的苯教王權貴族勢力,建立統一的政教合一的國家。因此,他迫切需要一個新的宗教來替代原有的苯教。但事實上,信奉佛教的主要是吐蕃王室和為謀取利益的大臣。佛教變成了贊普王室和苯教進行權利爭奪的武器,苯教依然在西藏擁有廣泛的民眾基礎。而這時,松贊干布和文成公主、尼婆羅的赤尊公主的通婚無疑給急于尋找一個代替苯教文化的新鮮文化的松贊干布帶來了契機。文成公主同赤尊公主紛紛帶來了釋迦摩尼等身像,許多佛教典籍,佛教僧侶和精美佛像。在兩位公主的共同推動下,松贊干布修建了大小昭寺,創立文字,翻譯佛教經典。為保障佛教在吐蕃地區的長期發展,松贊干布在拉薩乃烏塘親自為王孫芒松芒贊摩頂祝福,并為其講解佛教經典,引導幼小的芒松芒贊學習和了解佛法。又如在唐貞觀十七年(643),吐蕃派貴族子弟到唐都長安的太學學習文字、詩書和佛經,將大量中原佛經帶回。[2]為了吐蕃社會的長治久安,松贊干布積極尋求更能帶領西藏人民走向新生活的宗教文化。松贊干布去世后,由于對外擴張的需要,之后的兩代贊普并未積極發展佛教。到了第四代贊普赤德祖贊登基后,即便殘留許多苯教的勢力,但佛教仍然得到了極大發展,并且在他的統治下,苯教再無力與佛教抗衡。赤德祖贊時期,吐蕃國力大為增強,對佛教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文化基礎;加之赤祖德贊本人十分崇敬佛祖,大力倡導興佛。赤德祖贊從印度和大唐請來高僧為信眾講經說法,出資修建桑耶寺,組織佛苯之辯,由于佛教的勝出而禁止苯教發展,因此使得佛教勢力愈來愈大,苯教勢力式微。正在這時,佛教密宗的發展正如火如荼地在唐朝迅速發展。當時唐朝的政策是三教并存,鼓勵佛教繁榮,佛教在普通民眾之中的隱性地位甚至超越了儒道兩家。而吐蕃地處佛國印度和密宗繁榮發展的唐朝之間,這種歷史地理條件再加上有理論化的教義教理,自然成為了松贊干布以及赤德祖贊威權需求的不二之選。
三、苯教和佛教各自的內容和形式決定了各自的發展
佛教和苯教共同擁有對“神”的崇拜和信仰,但他們的形式和內容卻大不相同。苯教沒有經典,理論也只有簡單的《九乘經論》,還有一些極其簡單的宗教觀念和原始宗教儀軌。在苯教看來儀式非常重要,它可以催化情感,是行為的再一次規定,是聯系宗教行為和宗教情感不可或缺的紐帶,然而,佛教具有較為系統化的理論和大量的佛教經典,印度的佛教不講儀軌,傳入中國后也有一套宗教儀式。苯教視祭祀為其最重要的儀軌:設祭壇,獻牲口,誦祝詞,拜神靈,卜卦象,問吉兇等。按照苯教的觀念,苯教所信仰的是“天神萬能論”,神可以庇佑人,而鬼會給人帶來厄運,人的吉兇禍福依賴天神的意愿,所以苯教有一系列求神鎮鬼占卜祭祀的儀軌。而苯教儀軌中的祭祀活動需要進行大規模的殺生。苯教講究定期性祭祀和特殊事情祭祀。通常而言,一年被稱為小祭,兩年為中祭,三年為大祭。在特殊事情如出兵打仗、求雨、贊普登基這些大事時,會殺掉牲口來進行祭祀儀式;若是遇到了十分重大的事情,甚至會宰殺上千頭牲畜,然而,佛教講究一切皆空,一切所相,皆為虛妄。對于桑耶寺的佛教徒來說,苯教的理論及教義對社會生產力是一種極大的破壞,不利于經濟發展。佛苯的根本不同體現在思想、文化上,于是兩者產生沖突。佛教內容要求解救蕓蕓眾生,不分種族、膚色、國度,加上佛教提倡慈悲、友善、和平,這一義理在戰亂頻繁、民不聊生的社會中,對安撫人心促進發展有很大的價值和意義。其次,佛教的因果說、輪回說可以讓民眾減少抗爭,更加相信一切都是由因緣和合而成。今生的貧富貴賤都是前世因緣的結果,貧民不應該覬覦他人的財富、權勢和地位;相反,應當與世無爭,安居樂業。這種思想對統治者安撫那些想要挑起戰爭不滿現狀的人有很大的意義。此外,佛教教育民眾要遠離紅塵,脫離苦海,追求超凡脫俗的出世境界。希望民眾可以努力做善事,升入極樂世界。統治階級最希望看到的就是民眾與世無爭,佛教的這種教理對統治階級的統治意義重大。
“總之,無論從社會發展還是文化發展的角度來考慮,與佛教相比,苯教都是社會結構和人類思維的低級階段產物。顯然在吐蕃強盛時期,以它繼續作為統治意識,會給社會帶來許多難以克服的矛盾,故選擇佛教文化自當成為西藏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3]筆者并不認同“苯教是社會結構和人類思維的低級階段產物”這一說法。不論佛教還是苯教,它們都是一定歷史經濟條件下必然存在的產物。苯教和佛教是一種政治和宗教發展的不同階段,從社會功能上來看,很難比較其高下。就宗教觀念而言,只有簡單和復雜、不成熟和成熟之分,同樣不存在高級或低級之分。所以,苯教即便是在佛教外來文化的沖擊下,卻依然在吐蕃社會中占有一定的社會地位,依然有眾多堅定虔誠的信眾,這從后期的朗達瑪滅佛也可以看出。
四、佛教對本土苯教的主動適應
佛教可以成功傳入的原因就在于能適應苯教文化中直觀的思維方式和宗教儀軌。佛教傳入過程中吸收了苯教的神秘主義,宗教儀軌和多神崇拜的思維方式滿足了人們的心理需求。同時,佛教較為理論化、系統化的教理體系更加適應吐蕃社會的生產力發展,這也是佛教能進入吐蕃社會并作為主流文化存活下來的一個重要原因。每種文化在取代的過程中不僅會此消彼長,也會共生。佛教在最初傳入吐蕃社會時,與原生性宗教接觸后主動包容并適應其文化。佛苯之爭的實質也是佛教和苯教相互接近、借鑒、比爭和融合的結果。苯教產生于世界屋脊,在人和高原惡劣的自然斗爭的歷史中,它被視為可以對抗天災人禍的有力武器,苯教的儀軌與當地人的生活習俗息息相關,一代代像基因一樣流傳并記載下來。佛教如果想要進入這種文化,必須要學習苯教中的精華,必不可少需要尊重苯教的宗教心理和生活方式。
五、結語
本研究說明佛教在西藏之所以能發展到今天的地位,與政治經濟的發展、王權與歷史機遇、自身教義教理、宗教儀軌及文化的主動適應是密不可分的。佛教發展成為吐蕃社會主流文化的原因多種多樣,是多種條件共同作用的結果。同時,佛教自身的包容性使得其愿意接受和吸納苯教的儀軌,使得苯教信眾心理得到滿足。現如今,藏傳佛教已成為西藏人民主要的宗教信仰,它對西藏的發展功不可沒,藏戲、藏藥和佛教寺廟的發展使得西藏擁有了一個更加絢麗多彩的文明。
[1]任繼俞.中國佛教史[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73.
[2]王道品,劉峰.淺談佛教在吐蕃社會早期歷史中的發展[J].牡丹江大學學報,2012,(8):100.
[3]喬根鎖.西藏的文化與宗教哲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57.
【責任編輯:王 崇】

漢 衛
B949
A
1673-7725(2016)06-0085-04
2016-03-05
李艷(1990-),女,山西太原人,主要從事宗教學理論、宗教心理學、佛教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