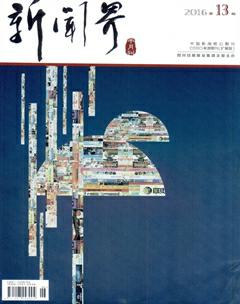抗戰時期貴州的出版業探究
沈磊 劉坤厚
摘要 在近代西學東漸之際,貴州華氏三代人在依靠經營鹽業和酒業發家致富之后,以敢為天下的精神,涉足新聞出版業。先后斥巨資創建貴陽文通書局、貴陽永豐抄紙廠,并在抗戰時期不畏艱難成立編輯所,聘請全國知名學者擔任書局的編委,從而使文通書局成為與商務、開明等并立的七大書局之一。文通書局為貴州及西南一地的近代化乃至中國的出版事業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關鍵詞 抗戰時期;貴州;出版業;文通書局
中圖分類號G210.9 文獻標識碼A
作者簡介 沈磊,貴州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劉坤厚,貴州師范大學宣傳部,貴州貴陽550001
1840年以后,隨著帝國主義國家的入侵以及西方文化的不斷東進,以商務印書局為代表的一大批具有私人資本背景的現代私營性出版機構慢慢發展起來。以此為契機,我國具有現代意義的新聞出版業開始出現并逐步發展起來。各種書局在中國大地上如雨后春筍般層出不窮,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的新聞出版業的發展,尤其是在交通便利且經濟發達的沿海城市,特別是上海更是相繼成立了商務、中華、大東、世界、開明等實力雄厚、貢獻突出的出版機構。與此同時,在中國文化比較落后、交通及其不便的貴陽卻創辦了在中國近代史創造了多個第一的貴陽文通書局(1908)。文通書局是由華之鴻出資創辦的貴州歷史上第一個具有現代意義的新聞出版機構。為了提高出版質量和技術,文通書局不惜余力,是第一個出國購買先進的出版儀器設備的貴州企業,第一個專門派人出國學習當時最先進的技術。文通書局不僅積極地“走出去”,同時還創造性的“引進來”,聘用國外專業的技術人才來做技術顧問。不僅如此,文通書局還依托企業優勢創辦學校來專門培養人才。從貴州近代工業發展的角度來看,文通書局還是當時第一個在工業生產中使用蒸汽機作動力的近代企業。文通書局的這些先進的理念、創造性的行為,尤其是對西南地區乃至全國近代工業、近代出版業的積極效應,應當引起專家學者的高度重視。
一、文通書局的生存環境概述
華氏家族世代行醫,在康熙末年由江西臨川遷至貴州遵義,以鹽業起家致富。在民族危機時刻,在維新變革的思潮中、西學東漸的影響下,華氏家族意識到教育在民族振興、家族發展中的重要性。華之鴻在中國近代大教育家嚴修等人的影響下,出任仁懷廳的儒學訓導,開始涉足教育,隨著參與的深入開始捐資推動貴州省教育的發展。在“端賴書籍”之余,華之鴻開始“思貴州地處邊陲,交通阻塞,新興知識傳播至黔,每每曠日持久,長此以往,則貴州文化,將永遠落于全國各省之后。而欲傳播知識,唯賴書籍。不如利用鹽業所積資金,創辦一所規模較大之書局,既可繼承先祖未盡之遺志,又可發展貴州之工業與文化”。正是基于這樣的思考,他逐漸萌發了創辦本地書局的念想。
文通書局成立于20世紀初期,發展于20世紀中期,這一時期被稱為民國經濟的黃金十年時期。因此,文通書局得以慢慢發展,但是過了這黃金十年,民族工業又被外國資本控制壓榨,漸漸難以為繼。東部沿海城市都不能幸免,更何況西部地區,尤其是抵抗外侮的八年抗戰影響更是如此。文通書局處在這樣一個時代大背景之下,可以說是步履維艱。一是設備運輸十分困難,成本難以控制。貴州山高林密,交通極其不便,基本的交通工具就是肩挑人扛,尤其是大型工業機器更是難以運輸到貴陽。從海外購買的設備順長江一路向西到重慶,或者通過洞庭湖到湖南,然后剩下的就是原始交通工具的使用。當時貴州幾乎沒有像樣的道路,山溝縱橫,山路蜿蜒狹窄,樹高林密,只能依靠人抬、馬馱,且路途遙遠,大宗貨物運輸有時要耗時一年乃至數年方能運送到,運費極為高昂,有時甚至超過貨物本身的經濟價值;二是在民國初期,封建軍閥混戰,橫征暴斂,企業生存環境惡劣,企業疲于應付政府的壓榨。文通書局從成立開始處在壓榨、壓迫之中,在夾縫之中艱難生存。各路軍閥混戰不斷、輪流上臺,政策飄忽不定,苛捐雜稅橫行,私人企業成為官僚資本的眼中釘肉中刺。軍閥和國民黨政府多次企圖強行吞并文通書局,未達到目的便無所不用其極,要么征收各種奇怪的稅費,要么直接搶奪企業的物質,要么直接強行扣押作為軍產,不斷壓榨盤剝,造成企業經營難以為繼,最終不得交給官僚資本,比如永豐抄紙廠被霸占;三是抗戰后期,國民政府經濟政策失效,通貨膨脹,物價飛漲,貨幣貶值,企業經營困難,同時政府拖欠各種費用,就不結賬甚至不認賬,使文通書局年年虧損,甚至工人的工資都無力承擔。
1931年,華氏家族新一代掌門人華問渠接過文通書局的“爛攤子”。華問渠一方面采取動用“成義酒坊”賺取的利潤竭力維持文通書局的正常運轉;另一方面采取加強內部管理,擴大經營業務范圍,更重要的是加緊引進各方人才。這一系列強有力的措施終于使曾經資不抵債、近乎破產的文通書局扭虧為盈,并逐步在出版業站穩腳跟,成為當時中國出版業的“七雄”之一。
二、文通書局在抗戰時期的發展及成就
“七七事變”之后,“抗戰不到半年,華北危急,平津早已淪陷,滬戰不利,上海、南京相繼失守。在這種大動蕩的情況下,以上海為中心,以北平、南京、天津為次中心的我國現代出版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擊”。中國著名的出版機構絕大多數都在東部沿海,只能紛紛遷往西南地區。貴陽——一個西南地區不起眼的小城鎮一躍成為陪都重慶的南大門、西南地區乃至全國抗戰的交通樞紐,也成為吸引東部地區撤退人口的集聚地。貴陽文通書局面臨著巨大的機遇,也承擔著巨大的風險,大量人口內遷,機關、學校的到來極大地擴大了貴陽的消費市場;另一方面其他出版企業的到來形成了激烈競爭。華問渠認真分析了文通書局面臨的形勢,他決定充分利用抗戰所帶來的全國性出版市場洗牌的機會,積極進行改革以求適應市場。他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完善內部組織架構,成立編輯所;重組書局,整合書局各類資源經營模式和業務范圍,等等。經過積極改革和努力.并借助發行全國大中小學課本的機會,文通書局從一個掙扎在死亡線上的地方小企業一躍成為在全國具有影響力的大企業,銷售市場由地方擴大到面向全國。
華問渠抓住戰火原因造成印刷的間歇性停頓、配送不準時等商機,在書局經營困難、資金短缺、瀕臨倒閉的情況下,毅然從家族其他產業之中抽調人力、資金、資源苦苦維持文通書局的運行和發展。通過自己的關系,在馬宗榮教授的幫助下,開始經營課本業務,完全按照民國設置的課程標準出版中小學教材,統一及時有效地供應全國各地中心小學和國民小學。后又創造性地出版了與之相對應的教輔材料和初高中課本。經過不懈努力,文通書局成為教育部成立的“國定本中、小學教科書七家聯合供應處”(簡稱“七聯處”)成員之一。文通書局僅占3%的供應份額,卻意義重大,因為這意味著在一定程度上文通書局得到了官方認可,并因此迅速成為全國七大書局之一。
文通書局借中國出版機構及大批知識分子遷移西南的機會浴火重生。為了吸引更多的人才,華問渠于1941年成立了編輯所和編審委員會,并通過各種關系聘請當時的文人名士到編輯所和編審委員任職。如聘請馬宗榮教授、謝六逸教授分別擔任文通書局編輯所的正、副所長,全權負責編輯所工作。馬宗榮、謝六逸兩位教授不僅學識淵博而且是當時的名士,在社會上具有很大影響力和廣泛人脈。馬、謝兩位就任文通書局編輯所正副所長,在短時間內就極大地擴大了文通書局的影響力,提高了編輯所的稿源量和質量水平。而且,華問渠在他們的建議之下,聘請了全國各領域的112名知名專家學者擔任編審委員,如張奚若、馮友蘭、歐元、姚薇元、竺可楨、陳建功、茅以升等專家、教授、詩人、文學家、學者、著作家和政界名流。可以說,文通書局編輯所的審定、編輯、撰稿等工作都是由這些知名專家學者來負責的。如此,不僅能保證高質量稿源的穩定,也確保了編審嚴格、規范。而且,文通書局建立十分科學而嚴格的審稿、編輯、定稿等出版流程,在這一流程中充分尊重編審委員的專業意見和建議。這樣,文通書局出版的產品無論是品味、質量還是影響都越來越好,無可爭議地成為當時中國出版業的“七雄”之一。
1941年,華問渠委托謝六逸創辦《文訊》月刊(文通書局通訊的簡稱),同時確定《文訊》的宗旨在于“刊載學術論著,文藝作品,名著提要,文化動態,以及其他與出版事業有關的文字”。《文訊》一直秉承著這樣的理念堅守文化陣地,即使是在《文訊》的首任主編謝六逸病逝后,主編一職幾易其主,但依然堅守“團結抗戰,繁榮學術、文藝”的指導思想,刊登的文稿質量也一直未曾改變。《文訊》因其稿件高質量、編審嚴要求,而獲得了廣泛認可和好評,取得了經濟和社會效益的雙豐收。
經過華問渠、馬宗榮、謝六逸等不懈努力,文通書局在抗戰期間成績斐然。1941年到1945年短短的四年時間,據不完全統計,文通書局共編輯出版188種、約10萬余冊各種圖書,內容涵蓋十分廣泛。文通書局始終不忘初衷,在國難當頭,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堅守“團結抗戰,繁榮學術、文藝”的指導思想,啟迪了民智、鼓舞了信心,在中華民族的抗戰勝利的進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文訊》月刊在這一時期成為當時國內很有影響力的刊物之一,也使得文通書局成為中國近代尤其是抗戰時期最重要的出版社之一。
三、貴陽文通書局對現代出版業發展的意義
文通書局是黔地本土近現代史上“有現代方法經營印刷所之嚆矢”的具有現代化萌芽的家族企業。華氏家族投入了大約相當于同一時期貴州省全年財政收入的25%資金到現代造紙業與出版業。從華之鴻出資創辦文通書局到華聯輝派遣人出國學習國外先進的印刷技術再到抗日戰爭時期華問渠變賣祖產家業,擴大文通書局的業務范圍,文通書局在百年前文化落后、交通不便、政治混亂的貴州生根發芽,并最終成長為七大書局之一的參天大樹,其發展對當下現代出版業依然有著很多的借鑒意義。
(三)堅守傳播文化、啟迪民智的傳媒初衷
華氏家族三代人,艱苦奮斗、無私奉獻在交通不便、文化落后的貴州,創辦并且發展壯大了文通書局,在貴州的教育及文化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為貴州教育、文化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華氏家族苦心經營文通書局,并不是僅僅為了經濟利益。華之鴻經常告誡子孫:“須知銀錢,本天地間公物,特假手于人使用之耳。用得其當則福,不當則為禍。爾等宜望我積德,不應望我積財也。”由此可以看出華家三代人無謂艱難困苦,投入巨大人力、財力創辦文通書局,不是為了出名,更不是為了謀利,而是為了“矯正時弊”,“解除民困”,“提倡文明”,“轉移風化”,培養“推動貴州富強的先行者”。當代出版人應該學習華氏堅守創辦出版機構是為了傳播文化、啟迪民智的傳媒初衷,為我國的文化建設和人民的精神發展負責。
(二)重視人才對新聞出版的重要作用
文通書局從建立到退出歷史舞臺的四十余年間,遇到了難以想象的困難,但最終都堅持了下來,并在抗戰時期迎來了它的春天。這與華氏祖孫三代善于發現和重用人才是分不開的。他們聘請了大批具有專業知識、思想開放、堅持學術、認真負責的知識分子,也正是在這些知識分子的不懈努力之下,文通書局才能迅速發展、不斷壯大。尤其是在抗戰時期,國家重心向西南遷移,大批的科研院校、大批的學者專家相繼來到貴州,這為文通書局的大發展提供了大量的人才。華問渠深知人才的重要性,積極通過各種渠道聘請各方面的專業人才,特別是聘請了一百余位知名學者擔任文通書局編審委員,并極大的提升了文通書局的編委會的地位。大批新的專業型的人才為書局注入了新理念、新知識、新技術,新思維和新方法,促進了書局的發展,提升了書局的專業性、科學性和權威性,這些都極大地拓展了文通書局業務。正是有了人才的持續支撐才有文通書局的持續性發展。正是這些優秀人才的努力,文通書局才有在內憂外患的時期可以絕地反擊,起死回生。在當下競爭更為激烈的時期,優秀人才對于出版業的發展顯得尤為重要。
(三)注重品質和品牌
文通書局非常重視企業的品質和品牌,尤其是注重與民族國家相結合的情懷。創辦《文訊》月刊(文通書局通訊的簡稱),以此來樹立形象,打造品牌。《文訊》非常重視刊物的質量,聘請謝六逸等專業人士負責審稿核稿,保證審稿嚴格、規范;邀請知名學者、文化名人為撰稿,保證文稿質量。《文訊》不僅關注當時學術前沿,刊登最新的學術研究成果,也刊登反映國內外反法西斯戰爭等情況的讀物,鼓舞國民抗戰的決心和信心,并緊跟時代步伐,為人民發聲。因此,《文訊》極端困難的時期,短時間就贏得了廣大讀者的認可,產生了極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在各種刊物滿天飛的當下,我們更應當學習文通書局。更多刊物創辦和發展在某種意義上是代表了我國文化的繁榮,但是我們更應該注重質量。單方面的數量不能說明什么問題,大量的垃圾產品也難以抵得上一件精品。因此,當代出版人面對浮躁的學術界更需要注重質量,樹立品牌,出精品。
“百年前封閉落后之貴州能夠出現文通這樣的與全國最大書局比肩的現代出版業與現代工業,不能不說是近現代中國出版史與工商業史上的一大奇跡。”尤其是抗戰時期,文通書局的積極發展不僅大大改善了經營狀況,更為重要的是在國人中樹立了貴州人的形象。當下出版業應當以文通書局為榜樣,承擔傳播文化、啟迪民智的責任,為人民和社會負責,重質量,出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