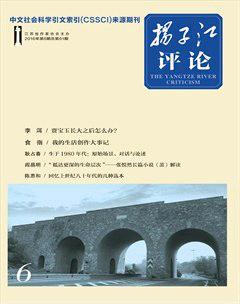交通意象轉型與臺北文化風格的變遷
林強
近二三十年來,乘坐地鐵已漸成為中國一二線城市市民常態化出行方式。隨著都市化步伐的快速推進,更多二三線城市也將進入擁有地鐵的城市名單中。都市交通系統的快速更替升級,似乎是解決大中型城市交通瓶頸的大趨勢。然而,日夜穿梭在地鐵中,市民們感知城市景觀、體驗城市的方式與內容已悄然發生變化。都市新人類無法想象工業城市時期城市內部鐵道旅行將是何種景象。唯有中老年人還能依稀辨識昔日的城市鐵軌遺跡、沿途的城市意象以及彼時的諸種體驗。在個人的懷想和文學的書寫中,工業城市的鄉愁氤氳生成。因此,我們有理由從紀實性的散文文本中梳理出從工業城市的鐵路到后工業城市的地鐵這一城市交通空間意象的變遷,提煉出世代居民感知體驗的結構性變化,建構一種屬于鐵道與地鐵的城市空間詩學。臺北,作為東亞華文城市的先進者,城市交通系統的更替略早于北京、上海,其作為國際性大都市的現代—后現代都市景觀也頗具典型性。本文即以臺北的鐵道—捷運空間轉型為考察對象,意在勾勒臺北居民城市體驗與臺北城市文化風格的轉型,也想以此與東亞幾大華文城市空間詩學研究展開對話。
一、中華路鐵路:邊界及其空間縫合
1949年年中,大陸來臺民眾漸增,街上攤販明顯增多,臺北市政府為減少路上攤販,委托臺北市警民協會在中華路鐵路東側興建兩列用竹篾搭建每個約四公尺見方、沒有墻壁的攤棚,全長約六百五十公尺,收容攤販并由警民協會管理。1949年底,國民黨撤退去臺,大陸赴臺民眾激增,造成嚴重的居住問題,原來攤棚遂被加筑墻壁并向前后擴大作為居所。同時又在中華路鐵路西側增建第三列臨時建筑,各列又向南延展,總長度達一千兩百公尺。這些臨時建筑都是不規則的、臨時以木板和竹料陸續添搭的,區域內橫巷交錯,呈現十分強烈的暫時蝸居性質,它們圍著鐵道興建,為50年代搭火車進城的旅客建構了獨特意象。在短時間內繁衍起來的中華路棚屋成為臺北都市中以貨物低廉著稱的地方,各類日用品至古董書畫都有,而最著名的則是它的各省飯館。中華路的吃食、逛店購物和西門町看電影,成了當時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消遣a。
以上文字雖呈現出50年代臺北的都市狀況,但作家的書寫更能表達私人的記憶和體驗;只有二者的參證,方能更立體而生動地還原特定時代中華路鐵路的空間形態和感覺結構b。丘秀芷在《三線路》一文中就詳細還原了中華路鐵路及兩旁攤棚的空間演變和個體體驗。在她的童年記憶中,光復時期西門町沒有中華路,也沒有中華商場,只有三線路。起初,由于日本人大多被遣返,城中區空房子到處都是,誰先住進去,誰就有居住權。慢慢地,空房子沒了,“三線路上鐵道旁開始有人搭棚子住。竹子架子,上頭搭些木板、鐵皮、油紙、水泥紙,像辦家家酒,十分‘有趣似的”;繼而,鐵道旁的竹棚屋愈來愈往小南門延伸,丘秀芷看到棚屋中“很多人家燒煤球、焦炭、生火很難,就把爐子端出屋外生。但下雨天又不能在屋外,只好又放在屋門口。我上學上得早,正好看他們家家戶戶在生火做飯,這些人好像沒我媽媽那么會生火,常熏得一臉烏七抹黑的”c。由于時局不穩,絕望情緒彌漫,中華路鐵道上慘劇不斷:“日子不好過,有人熬不下去,干脆臥軌自殺,自殺有傳染性,民國四十年前后,中華路鐵道上常有這種事。夜里有班車,都在半夜自殺。……一兩次,碰到那東一條腿,西一個頭支離破碎的尸體之后,嚇死了!”d丘秀芷以孩童的眼光來看光復初年中華路鐵道的眾生相,其中既有童趣的細致觀察,也有突然直面死亡的恐怖。這些都展現了動蕩時局中顛沛流離的底層民眾與臺北空間的內在關聯。臺灣光復至50年代,中華路兩旁的錯雜棚戶既是當局的權宜之計,也是底層百姓暫時居所和謀生之地。這種臨時性、錯雜混亂的空間特征表征出底層民眾的茍且偷安、焦慮乃至絕望情緒。
除了臨時性的空間特征外,中華路鐵道在當時具有很強的通道與邊界功能。它是連接臺北與中南部市鎮的主要通道。中華路沿途的棚屋成為人們搭火車進臺北城見到的主要城市意象。對于初次抵達臺北的乘客而言,這種視覺景觀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過了淡水河,再看大到一片違章建筑,夾著西門町的鐵路拖曳而來,臺北就到了!那時還沒建起商場,一片雜亂,一排排竹籬笆貼著鐵道,家家燒著煤球,熟悉的煤煙味,混著蒸汽火車的煤煙味飄進窗來,后院曬得衣服似伸手都夠得著,火車簡直就是擦身而過。”e中華路上的鐵軌連接著城里與城外,溝通著鄉土與城市。這既是城鄉之間通路的連接,也意味著空間的區隔。盡管中華路沿線的攤棚顯得錯亂逼仄,但這也呈現出城市所特有的繁忙雜亂景象。
城市空間的邊界也意味著空間上的某種連接。“1950年代崛起的中華路攤棚以一種臨時建筑的空間形式收納了大量的外省政治移民,并發展成為都市中新興的帶狀商業區,在空間區位上,它以一帶狀空間如拉鏈般將西門町與城中區接合起來,形成更具中心性的商業街區。”f在此后的發展過程中,中華路的這種縫合作用更加明顯。
由于中華路兩旁的違建越建越長,為了整頓市容,臺北市政府擬定中華商場整建計劃,于1960年春,將鐵路兩側的棚屋全部拆除,在東側建造全長1171公尺的鋼筋水泥三層店鋪八棟,自北向南以八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命名,計有1644個鋪面,中華商場成為臺灣最大的百貨總匯商場。1969年,中華商場各棟二樓以陸橋相連,1971年更與武昌、漢口和開封等街道的陸橋相連。從衡陽路至漢口街三棟的商場二樓已成為西門町游客必經之道,由是,西門町與城內中央行政區緊密連結在一起。“中華商場具體地連接城中與西門町而成為中心。”g可以說,中華商場的運營,也開啟了西門町黃金時代。逯耀東便記錄下中華商場興的繁華景象:“中山堂后向中華路,中華路自中華商場建妥以后,八幢大樓一字排開,從北門到小南門,臺北市又出現了一道發光的城墻,各種不同的小百貨商店向這里輻輳,各種不同地方風味的餐廳向這里集中,尤其在新生大樓擴建后,樓下的新生大戲院開幕,入夜之后,這一帶地方燈火輝煌,人聲與過往火車聲交織在一起,成為當時臺北市最嘈雜也是最有活力的地方,逛罷衡陽街到中華路吃飯,成了臺北或外地人到臺北休閑的例牌。”h原本雜亂無章的攤棚變成頗具現代商業形態的百貨商場,這無疑是臺灣當局立足臺灣發展經濟的一部分計劃,同時也表明相對穩定的兩岸時局讓一度處于不安、焦慮乃至絕望的底層民眾重建起穩定的庶民日常生活世界。當時的中華商場甚至成為流行文化的集散地,“喇叭褲、AB褲、迷你裙、雞窩頭,都在這條走廊流動著,美國的嬉皮文化也隨著唱片海報與電影流行過來”;新生戲院外的巨幅電影廣告看板,就是繪畫藝術,“從中華商場這邊看過去,那個戲院就是現代文明的最高殿堂,那時的戲院好大,看電影是種文化儀式”i。來自美國的流行文化隨著資本流動滲透進中華路的商業形態,無形中塑造了年輕世代追求時尚同時反抗國民黨威權統治的感覺結構。
中華商場的繁華并沒維持多久。1972年,當丘秀芷再到臺北時,中華商場又與1951時違建棚屋極為相似。王盛弘初抵臺北時,看到的已是“幾棟爛房子”的中華商場。中華商場最后的四年時光竟是如此景象:“一棟連著一棟踏著低低高高的階梯逛去,集郵社、古玩社,公廁終年彌漫尿騷腥臭、地板永遠泛潮,舊衣店、成衣店,點心世界舊桌椅上陽光斜斜射來,把鍋貼、酸辣湯剛送上桌那一霎映顯得云蒸霞蔚,唱片行、電器行,商場后方當當當鐵路道口柵欄放下,火車硿嚨硿嚨駛過,建筑物好似也有了一陣輕顫。”j垂死之際的中華商場,一樓的生意竟然比以前還好,“尤其在它將要拆遷的前夕,擠滿了搶著做最后拍賣的攤位,主要仍是衣服、皮鞋、皮包,又是人潮洶涌,好一幅回光返照的景象”k。殘破、凋敝以及被拆除前最后的畸形繁華,在在宣告中華商場死亡的命運。出人意料的是,似乎只有當中華商場被徹底拆毀,人們才會重新記起它,甚至才會重新認識它的前世今生:“我才知道它原來是清代的臺北城墻,日本人敲去建了鐵路,所以兩邊才那么寬。”l邱秀芷、郭冠英等人的記述生動還原出中華商場的生與死,王盛弘也抓住了中華商場死亡前氤氳而出的懷舊氛圍。這種文獻式記錄必將比建筑物更具生命力,也更能召喚出20世紀50-70年代臺北市民隱微而繁復的感覺結構。甚至于,隨著建筑物的死亡,早已堙沒不聞的歷史文獻也會隨著建筑物倒塌的聲音浮出水面,隱隱約約回響著空間、權力和意識形態綰結、更迭的身世。
中華商場興衰演變史,在見證者的記述中,既是空間的公共歷史,也是個人的私密史。從三線道到中華路鐵路沿線的攤棚,再到中華商場直至被拆除,個人的感知體驗在空間中被塑造,也參與進空間歷史演變進程中。世代的感知體驗匯聚成特定時空中的感覺結構,表征著那個時代的精神結構和空間結構。在時間長河中,在城與人的磨合建構中,城與人最終涵容成空間—生命共同體。正如雷驤在回首過往時所意識到的:“我成了臺北的一部分——而臺北卻是我生命的全部。”m
如果說,中華路鐵軌、中華商場曾經作為城鄉的通路、邊界和地標,曾經起到區隔和縫合的作用,那么當縱貫線鐵道地下化后,作為邊界的城市意象已經不存在了。隨著城市空間結構的變化,中華路不再是城市地標,它成了城市空間的文化象征。
二、北淡線:夢想通道及失落的鄉土世界
日據第二十年,年方十歲的郭雪湖跟隨母親,開始首次的滬尾(即淡水)旅行。他們從雙連驛上車,搭乘筑好不久的北淡線鐵道。在列車上,母親提及淡水河口的小鎮,特別會說到“大船”及“蛤蜊”。前者包括日本統治者的鐵殼右炮艇以及來自“唐山”廈門、福州的大帆船,后者則是全島知名的滬尾海產。如果說,在郭雪湖的童年世界中,北淡線還充滿了國族迷思和鄉土眷念;那么,時移世易之后,戰后新生代對北淡線和淡水的感知包含更多的童年夢想、異國情調和未來的詩意想象。
一直居住在北淡線鐵道旁,北淡線幾乎成為林文義生命中不可磨滅的牢固記憶。曾經的北淡線,藍色的車廂,綠色膠皮的坐椅,稀疏的乘客以及列車長質樸的聲音,都在童年記憶中散發出鄉愁般的溫暖。對于林文義而言,淡水曾經是一個遙不可及的陌生名詞,幾乎是另一個遙遠的世界。十五歲時,他用零用錢買了去淡水的火車票,想象著一場夢幻般的、屬于少年的初旅。“淡水很美,去的時候適逢向晚,淡水河口潮漲,許多魚狀的舢板在漫漫的潮水間奮力搖擺,晚霞在逐漸幽暗下來的遠天,許多人等著渡輪過河,他們要回到對岸顯得荒瘠的八里鄉。……十五歲,開始擁有一個永遠不渝的戀人,美麗而充滿異國之美的淡水鎮。一直到現在,這個年過卅的男子依然沒有變節。”n到遠方的鐵路與青少年的夢想相連,淡水鎮的異國情調恰恰具備夢幻的顏色。這讓林文義產生近乎偏執的眷念和溫暖的慰藉。由北淡線勾連起的現實和夢幻空間,竟包含林文義的兩種生存姿態:一種是對冷酷現實的抗爭與逃離,另一種則是對理想與溫情的向往和堅守。因此,雖經過重重的世事變遷,林文義仍時時省思和追溯:“從十五歲到三十歲,荒謬、純情、痛楚、傷感都已不再有任何的意義;至少,北淡線永遠伴隨著我期待黎明,黎明里有一個濱海的小鎮,是我不渝的眷愛。”o其實,不止是北淡線,伸向遠方的鐵道永遠給人無限的遐思,那是邁向夢想的通道,理想的未來將在鐵道的遠方展開。作為夢想的大都市臺北,同樣在鐵道的終點處讓少年雷驤產生無限遐想p,而彼時火車的緩慢和鐵道的漫長均構成對夢想的考驗。
然而,在工業化城市的日常生活中,北淡線的功能意象更為鮮明。作為交通運輸線路,北淡線及其各站剝離了夢幻的色彩,大多數時候呈現為百無聊賴的都市交通節點和人群集散地。“北淡線一串六節的火車廂,在過平交道的轉彎處緩慢下來,車列向離心的外角傾斜,然后煞停。人群從車門如傾倒出來一般,紛紛落在鐵軌和碴石上。這是數十年來北投小站王家廟(現在捷運稱‘唭哩岸站)的固定風景,把每日沿中央南路兩側廠家的職工們,運送到此。”q顯然,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北淡線缺乏詩意和夢想。被都市生產束縛的人們在日復一日的往返中早已失去了夢想的能力。唯有游離在都市生產節奏之外的人才會對日常生活中的鐵道寄予奇幻感。或者說,在工業化生產之中,鐵道已被簡化為單一的交通意象。而唯有鐵道被淘汰時,它們才會憑借文字回光返照。雷驤對藏青色的柴油車廂、擺著空魚簍打盹的小販等舊景物的描寫與其說是對工業時代柴油火車的懷舊,毋寧說是對鄉土文明的寧靜、和諧、溫情以及諸氛圍的傷悼和召喚。不僅如此,曾經因為火車行駛的緩慢而殘存于鐵道旁的鄉野景致,也會勾起人們對鄉土社會的無限留戀。在雷驤的觀測中,北淡線的鐵軌旁,在一塊不及五碼的礫石土地上,曾有一位從澎湖來的老人開墾種植天人菊。因為對泥土的不舍和對鄉野生活的眷念,不為生計所困的老人固執地置身在想象的都市田野中。這位老人頗可作為城市中最后一名農夫的縮影。
毫無懸念,當1999年淡水線被廢弛,那殘存的花圃和老人也必然消失在高速運轉、毫無人格特征的捷運系統中。“那套新的網路系統,正是要重疊在原來鐵道線上的,那種植在窄窄的鐵道腹地的天人菊消失了,整個被捷運工程局的鋼片圍籬包裹起來。照拂它們的那個老人,此刻也許就在對街某一幢公寓的窗口,遙望這些藍色鋼皮。為此,他失去了勞動的愉悅而怔忡罷。”r早在1990年代初,北淡線老站一律要被拆除時,雷驤就一回又一回地守在那兒,試著描繪老站里的空氣和氣氛。他無奈地看到:“在都會捷運系統的計劃里,支線鐵道成了重復和多余。事實上,除開列車到站的前后幾分鐘之外, 北投站早就想撤離廢置也似,空寂已成為正常情狀。”s鄉土世界的氣息已經遠去,失去功能的北淡線以及舊站最終變成荒蕪之地,有待被捷運系統改造。更令人不堪的是,那些失去土地的農民有的竟然變成城市的流浪漢和拾荒者,他們流連于即將被拆除的舊車站里,絲絲縷縷地賡續著只有鄉土社會中才會自然流露的溫情。雷驤曾在空蕩蕩的候車室里觀察到:“一個頭戴斗笠的赤腳大漢,濃黑的眉目,四肢粗長。那樣貌,理應在田間忙于農事,但他的襤褸說明了異地的流落,神色也顯示與體貌不配稱的失緒——正躬身揀拾剛剛離站而去的人拋落在地的煙頭兒”t;此時,另外一名拾荒老人竟然慷慨贈煙,這讓雷驤莫名感動。拾荒者和流浪漢之間惺惺相惜,正如涸轍之鮒,這是一個世代凋零的悲情。這也恰恰意味著,捷運系統的空間變革,必將催生新的世代及其感覺結構。
三、 捷運系統:后工業社會的都市奇觀和心理時空
臺北快速都市化,必然促使城市交通更加便捷化和網絡化。捷運系統的出現呼應了臺北城市國際化的節奏。臺北人不得不經歷捷運興建過程中城市交通的堵塞,也受惠于捷運系統完善后生活的便利。而對于作家而言,日常交通的便利化、立體化、高速化,并不僅僅停留在實用層面,他們更在意捷運系統所引發的一系列生活變遷,比如由捷運線串聯起來的商圈經濟、輻輳的人流、多元文化群落及其內在的關系。他們更在意書寫捷運車廂內外、商圈場所中人的感覺方式、行為方式乃至文化模式的嬗變。于是乎,敏銳如雷驤、張維中等便開始對捷運系統及其沿線的社會觀察。他們穿梭于臺北城的地下和地上,用文字和圖畫勾勒一個世代的社會風景和時代精神,或者更深入到書寫者——旅者的心靈境地。
記錄一座城市有多種方法,雷驤的捷運觀測及其書寫行為卻有較清醒的自覺意識。他曾看過一部西方的圖繪本,“畫家用了社會學和歷史學的方法,把一座德國城市,從二百年前一個人口稀疏的農業村聚,一步步形成都市的流變過程,寫實的呈現出來——以固定的一個角度,同一個空間視野,描畫它在不同時代下的樣貌。讀者從村集形式到目前的都市商業街之間,比較出時代演替的意義”u。也許是受此影響,雷驤“仿佛肩負這一類市街演化論的圖鑒使命,我踟躕游走,以一己的圖錄方法描記它們。”
(一)自動化、非人格化與新技術奇觀:捷運系統景觀特質
捷運成為臺北市內交通的主要工具,這不僅意味著臺北市內交通系統和交通景觀體系的更新換代,也意味著市民在行走過程中感知內容和感知方式發生巨大變化。此前的鐵路,雖然是工業時代的產物,但它畢竟還具備鮮明的人的特質——諸如開火車的人、列車乘務員以及較慢的行駛速度;而到了捷運系統,除了將此前的鐵軌拆除另建高架鐵軌、開掘地下軌道之外,也將人的因素消除于無形。鐵軌設備的更替必然引發都市人新的鄉愁,即對工業時代遺跡的懷想;而電氣化時代高科技的全面盤踞、人的因素被抹除無痕,也將產生新的疏離感和荒原感。此二者均在雷驤的觀測中被精準捕捉。“我猶記支線廢駛之后尚未拆除時,鋼軌紅銹厚結,灰綠色的勁草瞬間即從碴石縫中攀上鋼軌,或有力的伸向四方,這一種停駛即變成廢跡的景象,予人強烈毀杇的印象。”v工業時代的鐵軌一遭荒棄便如遺跡。北淡線曾經是林文義通向未來、異域的夢想之旅,如今難覓蹤影,這也意味著對工業時代的鄉愁只有在物象和感知的雙重消亡之時才會被召喚出來。而后工業社會的感覺結構也隨之呼之欲出。可見,感知形式、感知內容的內在更迭,恰如生命形態的此起彼伏,代代相傳以及變異,在不斷懷想、遺忘乃至排除中生成、演繹出新的感覺結構。
捷運木柵線是臺北市最早通車的一條線。這條線勢必給剛開始體驗捷運線的乘客帶來新鮮感和刺激感。捷運木柵線的轉彎設計便十分離奇,“自‘科技大樓站往前,幾乎是一個九十度的大轉彎,(車速此時‘自動降到5k/h),接著在‘六張犁停靠,起步后又是一個相反四十五度大轉彎,然后等到直道時,又幾近‘飛馳的速度轟然鉆進往‘辛亥站的長長隧道里”w。速度的驟然變化、路線的大幅度轉折以及高度的巨大落差,給初乘者的視覺和身心構成極大挑戰。在自動化的技術控制之下,捷運木柵線展現出新時代的交通奇觀。此外,捷運系統高度統一的空間美學設計,又構成新的交通景觀體系,這最終會內化進市民新的審美評價標準和身體—空間感知模式中。而捷運站上,“不過三、五分鐘,嘩啦,嘩啦的,長條銀梭般的列車駛來煞停,旋即駛離,像似什么獸類,快速的舔吸一過,月臺便空無人跡”x,這倏忽即來倏忽即去的捷運以及空蕩蕩的月臺,又會產生新的陌生化、荒原化體驗。這與林文義筆下充滿溫馨的童年記憶、充滿理想化幻夢感的鐵道旅行體驗,有著明顯差異。信息化時代高科技的物質文明已然實質性楔入世代居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并孕育著新型感覺結構。歷史經驗表明,新形態物質文明的出現在引起陌生感乃至恐懼感之時也將帶來新鮮感和奇幻感;而當它變得司空見慣時,新技術文明又會制造出新的奇觀。特別是進入現代—后現代文明之后,這種視覺—心理上的奇幻感更替得尤為快速。
通過文字與繪畫,雷驤成為捷運系統這一景觀美學的闡釋者。可見,文學藝術乃至商業文化(如廣告、影視等)、通俗文化共同塑造了新的美學原則和感覺結構。或者說,捷運系統只是后工業社會的通道形式,其他如消費空間(大型商場百貨、酒店、展覽會等)、網絡空間等早已讓消費社會的感覺結構粉墨登場。就捷運系統而言,非人格化的美學特質表現得尤為明顯。這已充分展示在雷驤描繪捷運月臺的畫作中。諸如人的消失或渺小化、星空和天際線的凸顯以及高架鐵軌流暢的線條,均緣于捷運月臺被高大水泥柱高高擎起。這也意味著從高處觀看到的世界,少了些人情味,多了些冷漠。“遠遠近近十分美麗”的捷運月臺夜景最顯著的特質就是無人化和非人化。
另外,捷運以及高度發達的都市工程也徹底改變了地方的景觀與風格。比如,士林一帶曾是雷驤年輕時熟悉的地方。那時的士林仍是“獨立鎮街性格”,閩式二樓連排的鋪面和民居組成類似大陸閩南內地的村鎮;而在都市規劃、資本運作等諸種機制的合謀中,如今聞名遐邇的士林夜市,已然成一消費奇觀,人潮摩肩接踵。可以說,捷運系統的開通與連接,在人潮、物資的輸送和消費時尚信息交流方面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而在快速流動中,都市人更易產生不確定性和疏離感。
(二)流動性、拼貼與分裂:捷運系統的心理時空
高速化的捷運系統將臺北各商圈以及中途各站網絡化,人們只要用比以往坐公交車甚至小車更短的時間就能到達城市各個角落。便捷化、高速化的捷運系統一方面固然拉近了市民之間的空間距離;但另一方面,空間障礙被消除之后,城市景觀變成片段化或者點狀化,捷運線路沿途的景觀印象日益模糊不清或者支離破碎;更具意味的是,人潮加速流動后,人與人的關系愈加流動不居,人人變成孤島,人群變成非人格化和類型化,個體心理深度逐漸消失或者愈加碎片化在快速運轉的捷運線路和無數個相同形制的車廂分身中。以此來看雷驤的《捷運觀測》,我們不無驚訝地發現,由捷運帶出來的城市景觀和人物,多呈現出印象式的浮世繪,不僅人物個體心理深度消失或者碎片化,城市空間統一性的景深也消失了;流動性、臨時性、碎片化、平面化乃至假象化變成雷驤筆下意象(人物、空間、景觀)的主要特征;雷驤書寫和摹畫的策略也有意無意地表現為拼貼和蒙太奇。這不能不說是后現代都市風格審美特質的具體展現。
在《捷運觀測》中,舉凡盛極而衰的面線攤、帶著重度灼傷面具假借“愛心藝人”名義的乞討者、剪藝者、販售泡泡槍的少年攤販……都在雷驤的行旅書寫和摹畫中被快速勾勒。他們沒有前世今生,有的只是暫時性地輻輳與展示。捷運車站里,人潮短暫的匯聚與流散,說明了都市中人與人關系的流動性、不穩定性和陌生化,而這種都市關系和情感狀況無疑是建立在諸如捷運系統之類的都市基礎設施之上。追求更快速、更高效的都市工程必然改變都市人的生活方式和感覺結構。另一方面,流動著的都市人潮和在車廂中暫時定格的人群,面目也變得類型化而非人格化。當雷驤在捷運車站觀察候車的人群時,他不是近距離地讀出候車人的臉部表情,而是從整體上描摹候車人大體相同的肢體動作,并把他們詮釋為“候車人們”或“群體的孤獨”,這種整體觀察的眼光正如“我們從不分辨此一批蟻,與若干年所見的另一批蟻有何不同;這一群雀,與別一群雀有何不同,總以等一距離觀看而無從感觸‘身受的體察”y。冷漠化或神性的觀察視角恰恰說明偶然聚集的人群類型化和非人格化特征。
在現代—后現代都市中,人已成為一座座漂浮的孤島,他們彼此之間似無連接,心理深度或者分裂狀態似乎也消失在人潮洶涌的現實水平面之下。因此,雷驤用浮世繪的方法成功地捕捉到了臺北人的精神—心理肖像。在諸如《穿越時空》 《足印》 《浮世》等篇中,雷驤勾繪出了捷運車廂內外并置而不無矛盾分歧的時空、荒誕的都市情境和分裂的心理時空與顛倒的精神世界……凡此種種,與林文義、雷驤筆下那曾經溫情脈脈的北淡線人情世界相比,都表明了后現代都市感覺結構的典型特征。顯然,后者以一種逆向的單線時間統一了北淡線的鄉土特性和情感空間,而前者則采取多元并置、共時、分裂、顛倒的方式呈現出后現代都市精神狀況。
在《穿越時空》一文中,雷驤觀察并臨摹了一張海報:“畫面看到兩巨列公眾交通工具:蒸汽火車在左、捷運電聯車在右,同時從背景的古城門洞穿前而來。”因要凸顯的主題是“穿越時間100年”,故而海報將“百年前劉銘傳時代購入的蒸汽火車,與前幾年購入的捷運電車行駛,同一時從更古老的公共建物前貫穿”。雷驤意識到這張海報是由三張來源不一的圖片——北門城、老火車、捷運列車——經由電腦繪圖合而為一。由此,我們不難發現,時間的穿越、空間的并置、電腦科技的拼貼諸種元素被整合進一張海報中,整張海報以不無違悖社會現實(蒸汽火車早已淘汰)和空間規制(北門城無法容納捷運電車更遑論同時容納電車和蒸汽機車)的奇幻方式被呈現出來。僅僅就這張普通的海報(甚至無需考慮它的經典性意義),我們就已把握住后現代狀況下已然無處不在的都市拼貼審美特質。
正如捷運系統已經將臺北城網絡化一樣,后現代狀況已經悄然改變每一個都市人的心靈世界。在《足印》中,雷驤以近乎小說虛構的筆法描繪了這般場景:一位女子深夜在空蕩蕩的地下捷運月臺候車,月臺上的黃色警戒線以及警戒線內那一對用油漆涂畫出來的小小足印子引起她的聯想,她“總覺得那雙小足印像某些兇案留下的血跡——尤其與那隔離效果的黃色帶狀在一起的時候,仿佛尸體傾間才被移去……”z由此,女子想起若干年前自己寫給某男子的信:“我現在最想做的事是殺死你!然后再殺死我自己。”這是出于彼時為戀情所苦無法自拔的絕望手筆。然而,時過境遷之后,那酷烈的心態竟有些荒謬。此時,“從遙遠的黑洞里射出列車頭的強烈光柱兩條,接著轟隆的聲音將她略有不悅的聯想,徹底的掩蓋過去”,門啟處,正對著那雙小小的血足印。雷驤對女子內心世界的想象一反此前浮世繪的無心理深度的肖像描摹與勾畫。他通過深度的內心展示,勾連出女子內心深處存在過的殺人念頭。殺人念頭,只不過是一種象征化的表達,它代表深藏在每個人內心深處最瘋狂的想法和心理狀態。在日常生活世界中,諸種瘋狂念頭雖然不斷生成,但總會在倏忽之間被壓抑到無意識深處直至被永久禁錮。因此,當捷運列車從黑暗中射出光柱奔騰而至且門啟處正是那雙血足印時,這就意味著那是一輛開往無意識深處內心罪證的列車,每個人皆可以對號入座。捷運月臺上女子的浮想聯翩,實際上是其內心世界分裂狀態的展示,這種分裂普遍存在于都市中每一位乘客的心靈中。只不過,隨著呼嘯來去的捷運列車,這種不斷被勾連起來、又不斷被驅散或壓抑下去的想法正是每個人日常生活中的常態。
在《浮世》中,雷驤更是在捷運月臺中揭示出頗具象征性的感覺結構類型。當雷驤站在電扶梯頂端勾頭下望,他看見“逐級靜立的男女老少的頭頂,在畫面的遠近法中上升、變大”;由此,雷驤想象天堂司閽者與之近似的日常所見:“純凈質輕而羽化的形體,在人間獲得歇息之后,靈魂浮升上來,它,正接待著哩。”@7死亡之后,靈魂脫離形體飛升到天堂,竟然與電扶梯不斷向上輸送人體的過程有些相似,這不能不讓我們感嘆雷驤不無奇詭的想象力。而更令人震驚的是,雷驤由此想起自己曾從相反的角度描摹過醫院電扶梯的場景:“一所巨型醫院的門廳,寬闊的電扶梯分作并行的兩行,把前來就診的歪倒人形,緩緩提升到極高的頂端;而另外一列,則是毫無希望的、沉重的人們,又慢慢滑墜下來。這些抱病者的身形是欲望累積的罪軀,在死亡之門前,在浩大的醫院門廳,構畫出人間的‘地獄變圖。”@8對醫院電扶梯自下而上的觀望與想象,勾畫出的是欲望累積的病罪之軀墜落地獄的圖景,這無疑是對捷運月臺電扶梯天堂想象的顛覆;但這兩種圖景確然構成對電扶梯想象的兩極。或者說,日常生活中,我們時刻都在兩極的路途中上升或者墜落,只不過無法如雷驤般警覺而已。電扶梯隱藏著天堂—人世—地獄的兩極世界,這是人類生活狀態—精神狀態的結構性描畫。可以說,憑借著捷運月臺上自動化的電扶梯這一物質構件,雷驤成功揭示了人類感覺結構的兩極及其過程,即下墜與超升以及循環往復。
四、結語
從中華路鐵路、北淡線再到捷運,我們見證了臺北交通干線空間意象及其功能的結構性轉換,那就是從工業城市交通動脈的通道、邊界意象與空間縫合的功能到后工業城市網絡化、自動化、非人格化空間奇觀的呈現。隨著城市交通空間的結構性轉型,世代居民的感覺結構也由動蕩時期的絕望、偏安一隅時的世俗化追求和以流行時尚的追逐反抗威權社會,一變為對日漸遠去的工業時代鐵道及其鄉土溫情的追懷,再變為碎片化、拼貼的、分裂的后現代心理時空。換句話說,每一個時代的城市空間結構與意識形態彼此涵容,它們共同孕育出類型清晰又彼此承續的感覺結構類型與城市文化風格。
【注釋】
afg曾旭正:《戰后臺北的都市過程與都市意識形構之研究》,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1994年博士學位論文,第141-143、141-143、152頁。
b本文借用英國文化理論家雷蒙德·威廉斯的“感覺結構”概念。所謂“感覺結構”即指“一個時期的文化”,“整個生活方式”,一種生活的特殊感覺。它“不是與思想相對立的感覺,而是感覺過的思想和思想過的感覺,是一種當下的實際意識,處在鮮活的相互關聯的連續體之中”。也就是說,感覺結構可以用來描述特定時期人們對生活的普遍感受,它包含時人共有的價值觀和社會心理;它還具有突出的潛意識特征,即人們認知世界常常是通過經驗世界而不僅僅是理性意識,這些都鮮明地表現在文學作品之中。可見,感覺結構能夠較有效地分析長時段中社會群體的感覺、心理、價值觀和審美經驗,也有利于分析人們從鄉土到都市社會轉型過程中獲得的社會體驗。參見Williams, Raymond, The Long Revolution, Greenwood Press, 1975, p.48.以及Williams, Raymond,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p.132.
cdehijl 人間副刊策劃主編:《回到中山堂——延平南路98號和周遭生活圈的故事》,臺北:臺北市文化局2002年版,第128-130、131、122、64、124、124-126、123頁。
mpqrstuvwxyz@7@8雷驤:《捷運觀測》,二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82、180-181、51、53、56、57、48、4-5、16、4-5、104、98、100、100頁。
k王盛弘:《十三座城市》,龍門書局2011年版,第113頁。
no林文義:《北淡線鐵道》(原載《聯副》1984年3月23日),《寂靜的航道》,九歌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6-2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