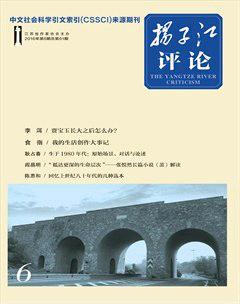“抵達更深的生命層次”
閻晶明
張悅然名下有一個很重的標簽:“80后”。無論是從年齡、出道時間還是創作成績上,她都是這個概念里打頭陣的一位。我一向對十年為一代際的寫作劃分保持警惕,因為它非常短視且并不能說明多少文學問題,說到底是一種話題、姿態的說法而非美學意義上的標識。可是面對張悅然,這個概念好像揮之不去。2016年,張悅然以她的一部新出版的長篇小說《繭》又一次刮起一股旋風,這一方面印證了她在小說創作上的實績,另一方面更加加重了她作為一個年齡層次的代表性。“繭”不但是一個忽然跳到眼前的單字,而且沒有任何依靠小說名字抓住讀者眼球的刺激性。這也從另一方面證明,張悅然是自信有力量挑動一個簡單字詞深邃含義的小說家,也是一位自信可以讓小說人物故事證明一切的寫作者。
《繭》究竟是一部怎樣的小說,它在當下小說界有著怎樣的暗示和意味?“繭,1.完全變態昆蟲的囊形保護物。2.手腳掌因摩擦而生的硬皮。”(見《辭海》)作者或許借用了這樣的比喻:“繭”是成長的代價,同時也是成長的呵護者。它制約著生命的自由生長,卻也保證了其成長性。“繭”并沒有在小說中成為直接隱喻,甚至沒有對這個字詞刻意引用,但“繭”的意味卻成為籠罩整部小說的象征,沒有完整讀過小說,是無法體會到“繭”的外殼作用及其堅硬度的。
沒有“繭”的《繭》卻有一個更加堅硬的意象:一枚砸入人腦中的鐵釘。這枚鐵釘牢牢地、殘忍地釘入到故事的核心,所有的人物躁動、掙脫、游走,都以這枚鐵釘為圓心,在很小的半徑范圍內撕扯、掙扎。從故事層面上看,這枚鐵釘是砸入一個人腦袋里、造成其終生植物人狀態的刑事案件和殘酷悲劇。在文革的混亂中,醫科大學教授程守義遭批斗后,繼而被人將一枚鐵釘砸入腦袋,從此成為植物人。同一所大學的教授李冀生,隱約成為這一事件的“當事人”,雖然另一個叫汪良成的人自殺身亡而被“確定”為行兇者,李冀生卻是逐漸浮出水面、不被懲處的“兇手”。
戲劇性在于,同在一所大學工作生活的程李兩家,他們家人的生活、后代的成長都勾連在一起。植物人程守義,是橫陳在所有人物和事件當中的一道沉重、深厚的壁障,令人窒息,令人厭惡,卻又不可逃離,這個植物人打斷了所有人通往未來的道路,同時又讓歷史在這種打斷、阻隔中被奇異地貫通、串接、延續。
我們不妨先放下小說想要表達的主題,先來看看小說透過這枚“鐵釘”,營造出的小說性、小說意味以及小說的現代性質感。
一是讓“現在”與“歷史”產生變異性、扭曲性的沖撞和勾連。程恭、李佳棲兩個人的成長、情感,無不烙上自己未曾經歷的祖輩、父輩歷史,這種歷史以強大的陰影投射在他們的人生道路上,他們的關系一刻都不能脫離,又因此不可能產生相交。橫陳在醫院“317”病房的植物人程守義,既打斷、阻隔他們的交往,又牢牢控制著他們不可剝離的“一體化”關系。他們未曾經歷文革,依靠什么去寫自己未曾經歷的歷史?歷史如果完全遠隔現實,作者當然可以寫一部“歷史小說”,而呈現在《繭》里的歷史,恰恰是李佳棲、程恭剛好錯過的昨天,是祖輩和父輩們人生中的一部分。于是,小說中的歷史就是現實的組成部分而非獨立于現實之外。在這個意義上講,“80后”這個概念對認識張悅然的小說寫作還是有價值的,因為這一代作家熱衷于寫“今天”,歷史的沉重可以在自己的筆下不出現,因為他們未曾在其中生活過。但張悅然選擇了面對一個同齡作家極少去面對的過往,回應了今天的現實與昨天的生活密不可分的聯系。從小說敘述上,可以說作者找到了打通今天與昨天、當下與歷史的通道,盡管這個通道是借助于一枚鐵釘完成的。現代小說或藝術表現“現代”歷史,總會找到某種契合點,使其成為“當代史”中的一部分,讓人感受到歷史的巨大存在,這樣,作家藝術家就有了足夠的“資格”去書寫和表現自己未曾經歷過的歷史,就使得這種書寫和表現不能簡單地被劃分到某種“歷史題材”中去,而使其成為表達現實感受的必要組成部分。
二是因為一個特殊情節的刺目般楔入,使得嚴肅小說的主題隱喻與流行小說的傳奇故事之間實現了有效拼接。這是當代西方嚴肅小說在美學上漸成趨勢的新敘述策略。奧汗·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紅》,羅貝托·波拉尼奧的《2666》,都是化流行故事之腐朽為嚴肅小說之神奇的例證。那些小說里有深遠的歷史,精致的文化,有高深的專業和藝術,但也有謀殺、偵探,有世俗的愛情和緊張的情節。小說的美學抱負和可讀性同時呈現,結出現代小說的“惡之花”。《繭》在這一點上有同構色彩,過去的歷史以一枚鐵釘為意象注入今天,今天的現實逃不脫與昨天的聯系,不可能不受其沉重影響。
三是小說營造的情境、氛圍,敘述方式的獨特選擇,體現了作者創作前的準備可謂深思熟慮。小說采取了李佳棲、程恭兩個人交叉敘述、平行推進故事的敘述方法。但這種敘述卻又不是當代小說流行一時的拆解補充法,即同一個故事由兩個或以上(通常是兩個以上)人物來敘述,他們是故事的不同程度的參與者或見證者,他們對同一故事的敘述,在使故事不斷奔向完整的過程中又互相拆解,使故事本身產生分裂,含義發生分歧,題旨變得復雜曖昧。張悅然在《繭》里讓李程二人交叉講述,但并不對故事本身進行拆解,不發生理解上的直接“糾紛”。他們講述的是各自看到的世界,實現的是共同向著一個沉重主題靠攏,表達的是同一代人面臨的現實問題和精神危機。從語氣上,他們二人仿佛進行的是一場對話,雖然不是面對面,但都把對方想象成惟一的傾聽者,第二人稱“你”在小說里頻繁出現,雖然不能說這是一部第二人稱小說,卻強化了敘述中的對話色彩。可以說,李佳棲、程恭是互為傾訴者和傾聽者的關系,漫長的傾訴和耐心的傾聽構成了小說的敘述格調。小說的第一章具有更強烈的對話色彩,這應該是小說從一開始立下的敘述基調,李佳棲、程恭共同講述著見面時的故事,但兩個人的敘述在情節上是“分工”進行的,并不對同一情節進行“各自”表述。當李佳棲講述自己的堂姐李沛萱與之交往的故事時,與程恭的對話味道開始減弱,這也預示著,單純的對話不可完成對復雜故事的敘述,盡管姐妹倆的故事并不需要全部細節化地讓程恭傾聽,但敘述必須按這樣的方式進行。其后的大部分敘述在對話性上時強時弱,但通篇所制造的這種對話與傾聽關系一直維系著。張悅然為自己的寫作挑選了最具難度的方法,當然也獨具效果。
戲劇性在于,所有人的活動都與植物人相關,難點在于,為他們的關聯性尋找故事的粘合度,邏輯的必然性需要花更多心力。在小說里,所有人物間的關聯呈扇面展開或合閉,而造成植物人的鐵釘,正如扇子尾部的扇釘,起著控制、收攏的作用。在《繭》里,每個人物的命運、性格都與“鐵釘+植物人”有關。程守義妻子性格的乖張是因丈夫成植物人引發的,在挽救無望后,她和一個普通工人有了往來并熱切希望能夠在一起生活,卻被對方離棄,她在絕望中有過干脆將植物人丈夫置于死地的沖動,最終卻不得不認命,過上了最不愿意又只能如此的不幸生活。程恭的父親成為施虐式人物,性格的由來自然離不開程守義的遭遇。在李家,李冀生和程守義的命運正好相反,他成了“仁心仁術”的院士,成了新聞人物,成了學習典范。在程守義的植物人狀態對比下,他的輝煌被添加了諷刺意味,更加上他實為“兇手”的身份,這一輝煌更具道德上的陰暗色彩。輝煌后面的黑幕才是故事的核心,盡管小說并沒有深挖這一黑幕,因為小說要表達的是他們對后輩命運的影響。李佳棲的父親李牧原,大學中文系的高材生,卻同時是一個父親形象的背叛者和父命的反抗者。他以自己的婚姻為殺手锏,一次次打擊這個在外面風光無限的父親。他娶農村妻子,離婚后又與汪良成的女兒汪露寒共同生活,都是徹底反叛的舉動。汪露寒作為汪良成的女兒,自幼背負著罪犯女兒的陰影,長期的壓抑讓她不得不逃離,她曾想過用呵護程守義來贖罪,卻遭拒絕。和李佳棲的父親李牧原共同生活也注定得不到應有的幸福,最終一無所得。
李佳棲和程恭,是所有人物中打開幅度最大的扇面。李佳棲的戀父而不得其愛,程恭性格中的復仇底色,這一切都為小說涂抹上了不可揮去的沉重陰霾。他們本來都有很好的家族背景、家庭教養,但他們的成長卻不可抑止地被加上沉重的心理負擔。小說故事的戲劇性、夸張度,全部因這段過往的歷史造成。如此網織故事,愛與恨交織推進中,復仇、曖昧、隱秘、失控,歡樂與痛苦,出身驕傲與現實不堪相混合,營造出強烈的、混雜的、神秘的、詭異的小說氛圍。故事足夠復雜多變,情境足夠陰晴不定,必然的命運結局與偶然的情節因素共存其中,將所有的人生推向不可預知的境地。
小說故事都由李佳棲和程恭的自述來完成,他們的“口述實錄”,讓故事在“局限”中散點式與漸進式地展開,而這種“局限”,是作者選擇的結果,也產生了比全知視角更有魅惑性的效果。“傾訴”與“對話”的對位行進,讓所有的故事先在地經過了情感過濾,色彩、色調也變幻不定。李佳棲與程恭,比之同在一個屋檐下的祖輩和父輩,經歷的歷史時間是最短的,小說卻恰恰讓他們來承擔起敘述的職責。這是一種敘述策略,它使現實和歷史之間,凡俗現實的比例遠遠大于“重大歷史”,讓歷史成為影響和制約“成長”的巨大投影而非線性歷史的一部分。“植物人”的沉重肉身,有氣息但不發言的狀態,殘酷地干擾著現實。這就意味著,這是一部表現當下現實的小說,為了探究現實所從何來,緊挨著的過往必然成為不可繞開的一部分,歷史既非現實也非背景,它是現實的閘門、包袱和刺目的聚光燈,也是現實的一面或平面或凸凹的鏡子。作為新時期出生的作家,在小說里寫祖父輩的昨天,這是一種有勇氣的選擇和探索,藝術上需要有獨特的切入角度。《繭》里邊的祖父輩們的恩怨情仇,有限地、謹慎地進入到今天的生活中。張悅然小心翼翼地處理了這個難題,確保其出現的藝術合理性及情節可信度。同時,小說也傳遞出這樣的信息:歷史只有同當下發生關聯時,或直接影響,或間接啟示,才具有追問、深究的必要。
當然,這畢竟是一個難題,探索還需要走很長的路。對張悅然以及她的同代作家而言,讓小說記述更長的時代和生活,必須有此道義擔當和美學抱負,同時還要在保證其創作的藝術品質的前提下進行。《繭》所呈現的歷史場面相對有限,比例上顯然明顯少于“當下”,小說里提到的一些歷史場景,也并無還原的要求,仿佛是過渡式交代。這似乎是作者防止情節失真的謹慎,生怕損傷小說品質的嚴謹所致。在我看來,或許還可以再大膽一些,更進一步,讓歷史本身有“說話”的機會而非主要靠“影響力”。這當然只是一種猜測,卻也是閱讀過程中積累而成的一點認識。作為一部細節綿密的小說,作者體現出對故事線索的清晰把握,對戲劇性的有效控制。不過,有的情節設制也或可以討論。作為一部正劇色彩深厚的小說,人物的命運結局應更多體現在必然性上,有的情節表現如李牧原死于車禍,畢竟屬于偶然性結局。與李牧原的命運相比,或可找到更具說服力、更能證明其悲劇結局必然性的情節。我的意思是說,對一部正劇來說,偶然性與小說故事之間,還是有重要程度區別的。李牧原是這部小說里除了兩個敘述人之外被描寫筆墨最多、最具故事性且影響了所有與之相關人物命運的角色,他的命運結局極具打擊力度。“有人在死,有人在生,我們在生死的隔壁玩耍。床上躺著的那個人,不在生里,不在死里,他在生死之外望著我們。他的充滿孩子氣的目光猶如某種永恒之物,穿過生死無常照射過來。我們被他籠罩著,與人世隔絕起來,連最細小的時間也進不來。”小說如此透徹地描寫了程守義與“我們”之間的關系,我同樣愿意看到其他人物具有相同的不可脫離性。
一個小說家,特別是年輕的小說家,一旦獲得相應的名聲后,往往會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豐富多彩而創作著漸趨簡單化的小說。不要說懷著強烈的美學抱負去努力寫出進入小說史的小說了,連稍微復雜一點的故事也疏于編織。張悅然的《繭》是一部認真之書,是一個不厭其煩做抽絲剝繭之繁復工作的漫長過程,是對歷史、現實,成長、人生,親情、愛情,道德、倫理的一次深刻探究之旅,是在藝術表達上力求尋找新意和獨特性,為了“抵達更深的生命層次”(作者《后記》言)的一次全力沖擊。去創造只有小說才能表現的世界,執著于只有文學才可以挖掘到的人生意義,這正是當代小說家特別需要表現出來的創作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