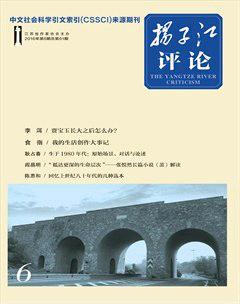新舊道德的糾葛
艾翔
閻連科的爭議性是廣泛的,作家本人曾說:“在我的寫作中,《日光流年》是爭議最小的一部書,是好言偏多的一曲長調。”a此時包括《風雅頌》在內的幾乎全部長篇代表作均已問世,各種批評和辯駁的聲浪自然也席卷了《堅硬如水》,研究關注點往往集中于“革命的狂歡與性的狂歡在形態上的極為有趣的對稱”b,但這部小說應該還有除此以外的深意。
一
閱讀《堅硬如水》,“革命”當然是一個關鍵詞,但與之對應的似乎并不是“性”。如評者言“革命”和“性”呈現出一種可置換性的關系,那么二者就是本質相同的不同表現了。如果按照人們的共識,“革命”乃是一出發生在特定時代的戲劇;那么,此劇的演出舞臺則是耙耬山脈中的“程崗鎮”,是否注意到這一點對閱讀并非無關緊要。小說在第二章起首便介紹了這個看似偏僻實則重要的村落:“程崗鎮原來叫程村,然而可不是隨隨便便的一個村;現在叫了程崗鎮,也不是耙耬山脈間雞零狗碎的小集鎮。它是宋朝‘程二夫子程顥、程頤哥倆的故居。元朝仁宗那會兒,為了紀念先祖圣人,在程村曾修下一座廟,過了明景泰六年,這廟你修我補,誰都為封建階級添磚加瓦,那廟就成了三節大院:前節有欞星門、承敬門、春風亭、立雪閣;中節有道學堂大殿和‘和風甘雨、‘烈日秋霜二廂房;后節呢,有啟賢堂大殿,兩側對立著講堂四座。這三節大院,占地數十畝,雕梁畫棟,龍飛鳳舞,石碑如林,松柏參天,是封建主義的活教材。”c二程一向被尊為理學大師,是上承周敦頤、張載下啟朱熹的關鍵性人物,以其冠名的“程朱理學”成為元明正統意識形態,其巨大影響足以代表中國的理學思想甚至中國傳統思想體系。小說敘述中不時顯露的嘲弄語氣或許表明了作者的某種態度立場。
由于作者采取的是(高愛軍)第一人稱敘事,程崗鎮被推向了“革命”的對立面:“死氣沉沉山區天,沉沉死氣鄉村地。……看見那程家大廟時,我心里緩緩下沉,決計有一天我不僅要砸掉‘兩程故里的石牌坊,還要一把火燒了這寺廟,我從程家崗搬下來就想燒想砸這寺廟,沒有緣由我就想燒砸這寺廟和那石牌坊。當兵思念回來我越發想燒了砸了這寺廟。”d高愛軍對傳統文化的敵意并不是來自文件綱領的機械執行或盲目的破壞原欲,而是由其“革命”的身份所決定的。他越是義無反顧地投身革命,就越是會激烈地向傳統文化發起挑戰:“我們是一對偉大的革命者,又是一對卑瑣的偷情者。既是一對覺悟者,又是一對執迷不悟的沉淪者。……在程崗附近的河灘、林地、田頭、開會的路上,檢查生產的溝里,哪兒都有我們的歡愉和悲哀,都有我們的高尚和卑劣,都有我們的興奮和羞恥。”e表述的矛盾不表示邏輯的矛盾,在“現代”話語模式下的“革命者”“覺悟者”的“歡愉”、“高尚”和“興奮”自然就是“傳統”語境中的“偷情者”、“沉淪者”的“悲哀”、“卑劣”和“羞恥”。或者說,在傳統視角中越是偷情、沉淪、卑劣,作為一個革命者就越是高尚和成功。
革命推進的快感充沛了性欲的快感,表現為高愛軍聽著革命歌曲、向舊勢力發動進攻的時候尤其能引發蓬勃愛欲。同時,高愛軍和夏紅梅的通奸尤其在墓穴中的激情,更具有突破傳統倫理、自主支配身體的象征意味,與“革命”一樣是對傳統道德的激烈對抗。后來高夏二人隱藏身份進入王家峪大隊無意中發現私自分田的行為而展開調查取證并揭發,同樣是以革命的集體主義挑戰傳統的小農意識。可以說,小說中出現的眾多細節其實都在圍繞著一個中心,即“革命”的“現代”與“理學”的“傳統”的紛爭。“革命”要建立自己的烏托邦,“傳統”也要維持自己的烏托邦,二者之間的劍拔弩張正是小說發展的巨大內在張力。
這種紛爭不但體現在觀念的對立上,更呈現出現實的搏殺狀態。在高愛軍尚未開展“革命”斗爭之前,夏紅梅作為一個“革命先覺者”因宣稱在北京握了毛主席的手而被村人認定得了魔癥f,但小說后文寫到“革命”即將進入高潮時夏紅梅對這段經歷一清二楚,不希望再被扎針,表明這種“瘋魔”只是一種“被敘述”,并非真正的癲狂,僅僅因為夏紅梅“革命”的思維邏輯在程崗村中顯得另類、顯示出對傳統道德秩序的潛在顛覆性便被視為“非正常”狀態,背后體現出的不是病理學而是一種社會權力分配的關系。
值得注意的是對夏紅梅進行“治療”的是鎮長(程天民-幕后操控者)、村支書(程天青-實際下令者)與“老中醫”(具體實施者),權力的天平分明傾向了傳統文化勢力及其支持者傳統政治勢力。可以說,在最初的交鋒中“革命”并不能構成與“傳統”旗鼓相當的對手,結果只能是以“治愈”為假象的屈服。直至當高愛軍加入“革命”后,事情才逐漸發生了重大逆轉。
二
兩個烏托邦的第二次正面交鋒發生在高愛軍、夏紅梅率領“革命青年”砸毀程寺牌坊的途中,遭遇了保護牌坊的村民:“更為重要的是,那上百的人群里,沒有年輕人,大多都是村里的成年壯勞力和上歲的老人們。他們發白的胡子在日光里像是一團團的火,他們都是我們隊伍中每個人的父親或爺爺,偶爾的幾個婦女,卻是我們隊伍中幾個沒有父親的母親們。”g毛澤東比墨子“兼愛”更進一步要求愛別人的父母勝過自己的父母,革命倡導的是較為激進的道德倫理,應該擺脫傳統親情的羈絆,倡導一種更廣泛的階級感情。雖然馬克思強調的世界范圍內才有效的無產階級概念在列寧處被改寫,但世界范圍內的階級感情并未受到動搖。在這種更為現代的情感倫理語境下,理學為代表的傳統文化提倡的“忠孝節義”不可避免成了革命的對象。
此后的“革命”的方向被明確,即混合了奪取政權和奪取話語權的雙重目標。先用水泥和紅漆重新涂抹“兩程故里”牌坊,刷上宣傳毛澤東、共產黨的標語,之后寫出經驗材料《關于程寺究竟是封建余毒還是文化遺產的思考》,列舉二程故里建筑群“九大罪狀”并上報縣委、地區日報和省報。在此期間代表傳統的一方一直謹言慎行,直至二程之父生日來了外鄉程家后人燒紙燒香拜祭,被高、夏二人視為是“典型的一起有預謀、有計劃、有后臺的反黨、反革命、反社會主義、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最最典型、又最最反動的一起反革命事件”h,遂發起“程寺之戰”,釀成正面沖突。最終雖然一批御匾御碑石獅被毀而被高愛軍宣布勝利,但可以很清晰地看到,這種“勝利”是以相當的妥協為代價的:首先是釋放被拘留的外鄉祭祖者以獲得沖入程寺的民眾支持;其次“燒書”的首要目的并未達到,二程著作被程天民事先藏起替換成了馬列著作。因此這次正面沖突并不是一次徹底的征服,反而造成二者間的內在矛盾。
后來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帶入拘留室,高愛軍反復默念的也是反抗理學的宏愿而非越獄:“這會兒我突然極想抱著炸藥包像董存瑞那樣把程寺給炸掉;……我自小看見成家人在那集合拜祖時,就想著有一天要扒了那程寺和牌坊,炸了那程寺和牌坊。”i最后報復性地在程天民面前的激情表演再次說明,“革命”和“性”實在是二而一的,在這樣的嚴肅文學中不會有沉溺式、目的性的性描寫,而是為了強化對傳統倫理的沖擊力度,根本上還是以描述“革命”為中心。
雖然一直保護程寺的鎮長王振海被稱為“走資派”,但是閻連科讓我們看到歷史的真相,即無論怎樣界定,基層確實是不存在名副其實的“走資派”的,被稱作“走資派”之人不過是受到較深的傳統倫理影響。作家敏銳地發現了這一點,并在小說中明確指出“革命”的真正對象是“割封建主義尾巴”:“那倉庫里有二百公斤縣里為興修水利、開渠挖洞下發的炸藥和雷管。我從倉庫里拿出三十卷油紙包好的半斤裝炸藥,拿了三把雷管,兩盤導火索和一把新剪子,又安上倉庫門,安上大隊部的榆木大門,便大步流星地往程寺走去了。”此后很快再次通過象征筆法暗示了這一點:“我沒想到他原來那么輕,就如一捆干枯的柴火樣。沒想到我在部隊為防帝反修學到的擒拿術這當兒一股腦兒都又復蘇在了我的手上、腿上和腳上。”j防帝反修的革命招式最終被用在了對抗物化和人格化的程朱理學上,而且引文出現于借用“炮打司令部”這一毛澤東揭批黨內高層“走資派”的歷史文獻的節題之下,更表明“反帝反封建”在共和國階段一定程度上是脫節的,即高層的“反帝”和民間的“反封建”。
由于強大的意識形態機制的規約,國家內部出現了統一的話語方式,事實上造成了概念使用的模糊,難免導致上下步調不能一致,有效的管理和引導便難以真正展開。這種脫節不僅表現于此,另一個當時更廣泛使用的概念“階級斗爭”也存在這一問題,“在階級和階級斗爭問題上的理論混亂,對文化大革命很快成為一場動亂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人們根據不同的理論和政治立場,輕易地給組織或個人戴上‘階級敵人的帽子并進行迫害”k。這在1970年代小說中都有較清晰的反映。可以說《堅硬如水》真正值得受到關注的是對時代話語裂隙的洞察,根本不是時下被津津樂道的性描寫,許多熱評實際將小說精神內涵庸俗化和淺薄化了。
因為傳統意識在民眾思維中居統治地位,現代革命在用自己的一套倫理和邏輯沖擊前者小農意識的同時,還另開第二戰場以更為現代化的性觀念沖擊傳統倫理道德的建構。今日談論“革命”,是站在“革命”勝利的結果之上在談論,當年“革命”所要革除的“傳統”弊病的危害早已大幅減小,因此會造成一種“傳統”缺失亟待召回的錯覺,并以此抨擊現代革命的破壞性,其實這是不公允的。也許“革命”作為歷史途徑的惟一性會受到一些人的質疑,然而可以統一意見的是傳統社會及其思維模式必須要轉化到現代階段。小說中王家峪大隊私自分田被上級追究責任后,“王家峪的人認為,如果不是這個李林隊長,我和紅梅便不會發現土地下放的事,王振海就不會被政府抓起來,趙秀云就不會自殺在監獄里,他們的土地,當然也就不會重新被收回到集體的籃子里。如此,她就自殺了,他被打死了。悲劇、令人痛心的悲劇!這簡直就是農民的狹隘思維和短視,是一種被封閉的愚昧和無知共同創作的一出大悲劇”l。這里體現出革命倫理與傳統倫理的尖銳矛盾,以及受傳統思維束縛的基層干部對革命倫理/國家意志的不理解。底層民眾或許因為所處位置不能看到整個國家的宏觀規劃,這正是基層干部應該進行雙向解釋與說明的地方。當然并不是說民眾就應該為國家付出一切代價,但也不能無視雙方之間需要相互妥協的事實,畢竟國家進行集體化是為了快速發展工業增強國力以抵御外部世界的侵擾,這是內部包括每個個體發展的根本保障。此外村民還是以陳舊的善惡觀來進行事實判斷,并且多少帶有類似“子為父隱”的傳統倫理思維方式,這些都是現代革命推動的現代意識明確摒棄的概念。
三
摒棄傳統的行為并不僅僅是觀念上的不一致,不然尚不會水火難容,事實是傳統道德對“革命”產生了現實的阻礙,表現在小說中是前者并非始終被動。程天青無意中撞見了麥秸垛中偷情的高愛軍、夏紅梅,程天民則有可能發現了夏紅梅衣柜中供高夏幽會的地道入口,兩人都對高、夏二人的“革命”構成了潛在威脅。需要注意的是,同程顥、程頤的兄弟關系一樣,從名字可知程天民、程天青至少是同一輩的叔伯兄弟,更關鍵的是后二者不但繼承了前二者傳統道統捍衛者和人格化象征的地位,更因其擔任的鎮長、村支書而具有現時態政統維持者身份,如此“革命”的任務便如前所言就是文化和政治雙權力的爭奪了。
二程認為,“人該在喜怒哀樂上求其不失和之理與和之氣,便該求喜怒哀樂之發而皆中節。但喜怒哀樂一發,便早見是和或不和了,在這上無從下功夫。若僅從失和了要它和,總不如在其未發時下功夫,使之發而皆中節,發而無不和”m。看似是意圖對農民進行知識分子化的“改造”,同時令知識分子攜帶上平和的中立態度,實現其與農民的分離,成為頗受統治階級歡迎的意識形態工具。兼具烏托邦生產機器的軍隊在建國后不但涌現了邱少云、黃繼光等戰斗英雄,還塑造了雷鋒這樣的道德楷模,周恩來對所謂“雷鋒精神”的一個重要詮釋就是“愛憎分明的階級立場”,這與程朱理學顯得格格不入。另外二程“人欲肆而天理滅”的思想傳到朱熹處,“把天理看成是永恒不變的教條,視天理至為神圣,不允許人們有絲毫的違反和輕視。他事先懸掛一個不變的至上的標準,再來套古今人們的行為,認為凡違此標準的即是不義的、不道德的行為。他讓歷史符合道德的教條,而不是使教條去適應并指導現實。他把道德的教條看成是僵死的、一成不變的和至為神圣的,所以認為歷史是漆黑一團”n。正因如此,“以朱熹為代表的程朱理學完全服務于封建等級秩序要求得到的目的與宗旨,顯然不能適應社會進一步發展的需要”o。如此便能理解高愛軍在程寺怒斥程天民誓死效忠理學行為這一細節:“程顥、程頤的得意弟子朱熹這個宋朝的反動哲學家,販賣和發展了程顥、程頤的臭學問,寫了那么多的書,說了許多話,如今大家都忘了,都不記得了,但有一句我們還沒忘,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p
最終的結局是耐人尋味的,傳統道德的代言人程天青發瘋,程天民迅速衰老,最終在高、夏二人的性表演時被氣得雙眼流血,又被埋在了程寺被炸后的瓦礫廢墟中。二人或瘋或衰的直接誘因分別是前者其女程桂枝破壞“革命物品”后上吊自殺(被判反革命罪)、后者其子程慶東因發現高夏通奸而被殺于地道。不但“新一代”的“二程”神滅身死,而且其家庭絕后象征著傳統道德的后繼無人,足見現代革命反傳統的激烈程度。因為上一代人力量的被毀滅和高妻程桂枝、夏夫程慶東的死,高愛軍和夏紅梅感情之路的障礙終于被徹底清除,兩人才能更加大膽地攜手實踐革命與性事,可以說這正是五四文學破除包辦婚姻、逃離舊式家庭的新革命時代升級版,如同文革面對傳統(“四舊”)的激進主義正是五四運動的歷史回響與深化一樣。
還需要說明的是,《堅硬如水》人物關系表中有一個意味深長的現象,即程崗鎮的“革命積極分子”甚至可以說“激進革命派”高愛軍和夏紅梅還有另一層身份,“舊道德”形象化身程天青的女婿和程天民的兒媳,也就是說二人與他們反抗的對象有著緊密的聯系。“在西方大多數學者看來,中國傳統文化對毛澤東的影響是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毛澤東與中國傳統文化有著千絲萬縷、難舍難分的聯系。英國的格雷在《中國:共產主義和孔夫子主義》一文中指出,毛澤東在中國傳統中吸取了大量思想材料,毛澤東的思想與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聯系非常緊密,幾乎是中國傳統政治的主要思想特征的相應對偶。美國的費正清則認為,毛澤東思想與儒家思想差別很大,但類似之處也多,不懂得儒學,就無法理解毛澤東。”q閻連科對中國社會的深刻認識正反映在文本肌理的象征層面。
《堅硬如水》的關鍵并非形式層面的文革語言和內容層面的性愛敘事,作家真正想要呈現的是對社會主義中國的“革命”和“傳統”兩個道德烏托邦關系的細致探討,相比之下語言和性愛其實都是載體和表象。小說開頭沉浸在革命歌曲中的高愛軍面對夏紅梅產生了豐富的性幻想,然而一旦廣播終止,交流再未能如期發生。革命作為一種烏托邦,自然包含一種幻想的成分,但這種幻想是一種推理結果,并不能簡單表述為“癲狂”與“非理性”。通過高愛軍的性幻想,道出革命的這一內涵,從這個意義上說起首長篇大論的虛擬性愛描寫就并非奪人眼球之舉。“后來,我聽說就是我在撫摸她的紅腳趾甲那一刻,先廣播站被人搶占了,輿論工具又回到了革命者的手里邊。”r敘述上的并列再明顯不過地透露出了作者的構思,暗示“性”和“革命”只是統一概念的不同表達或同一目的的不同路徑。閻連科小說正是這樣,無論采取什么形式講述故事,根本旨意大抵都是探尋社會主義邏輯的內部脈絡,而并非僅僅提供作為視覺沖擊的語言戲擬或性活動描摹。
【注釋】
a閻連科:《敬畏呼吸(再版后記)》,《日光流年》,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頁。
b汪政、曉華:《論〈堅硬如水〉》,《南方文壇》2001年第5期。
c閻連科:《閻連科文集(堅硬如水)》,人民日報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頁。
d閻連科:《閻連科文集(堅硬如水)》,人民日報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頁。
e閻連科:《閻連科文集(堅硬如水)》,人民日報出版社2007年版,第103頁。
f閻連科:《閻連科文集(堅硬如水)》,人民日報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頁。
g閻連科:《閻連科文集(堅硬如水)》,人民日報出版社2007年版,第49頁。
h閻連科:《閻連科文集(堅硬如水)》,人民日報出版社2007年版,第119頁。
i閻連科:《閻連科文集(堅硬如水)》,人民日報出版社2007年版,第215頁。
j閻連科:《閻連科文集(堅硬如水)》,人民日報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240頁。
k[美]莫里斯·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后——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杜蒲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86頁。據其分析,文革前夕中共意識形態包含三種不同的階級理論,有“保守”、“革命”和“改良”之別。
l閻連科:《閻連科文集(堅硬如水)》,人民日報出版社2007年版,第191頁。
m錢穆:《宋明理學概述》,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77~78頁。
n羅國杰主編:《中國倫理思想史(上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526~527頁。
o沈慧芳:《道德烏托邦的歷史嬗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30頁。
p閻連科:《閻連科文集(堅硬如水)》,人民日報出版社2007年版,第241頁。
q尚慶飛:《國外毛澤東學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11頁。
r閻連科:《閻連科文集(堅硬如水)》,人民日報出版社2007年版,第14、1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