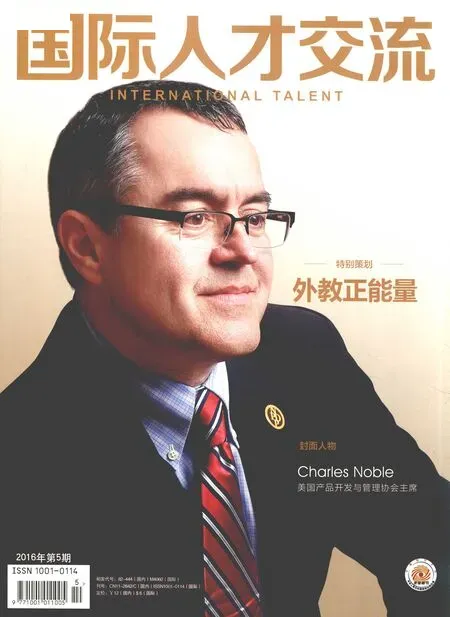老朋友的故事
文/吳星鐸
老朋友的故事
文/吳星鐸

陳美銀(中)給孩子們講故事
年年歲歲“情”相似,歲歲年年“文”不同。
每一年,“我與外教”全國征文大賽都會出現風格各異的文章,新鮮有趣的故事,給我們帶來相似的感動,熟悉的溫暖。而在這些感動與溫暖中,我們發現,有這么一些優秀的外教,他們的身影,他們的笑容,他們的奉獻,他們的故事,多次出現在不同學生的作品中。這些外教,是我們的“老朋友”。
打開一篇篇作品,聆聽老朋友的故事。
馬珍妮:傳播大愛的“馬奶奶”
馬珍妮是我們的老朋友。她來自美國,從1996年開始創辦孤兒之家,專為農村貧困家庭提供服務。如今年逾古稀,含辛茹苦地撫養了近百名孤兒。
“她喜歡穿寬松衣服和一雙白色的運動鞋,她有藍色的大眼睛,像是會說話,她每次來后,都要與大家一一擁抱,并問:‘過得好嗎?’這似乎已成了習慣……”谷思源在《有一種愛可以橫跨地球兩端》一文中,這樣描寫他們的“馬奶奶”:“我與她并沒有血緣關系,可是,我們之間卻有一種說不出的情,是親情?我相信我們的感情超越了國界、血緣,凝聚成這世間最偉大的愛。”
另一位小作者李柯,在2006年的某一天,收到了神秘的禮物:芭比娃娃、毛絨小熊、小天使,還有幾件漂亮的碎花裙、公主衫。這些禮物嚇壞了她,在她看來,這些是“只有公主才可以擁有的,也只有在夢中才可以擁有的。”這些禮物,來自馬珍妮。“馬奶奶”給了她一個用愛編造的英文名字:Kaite。Kaite寫道:“從1996年建院至今,我不知道她為我們操了多少心,我不曾數過她為我們白了幾縷頭發,我也不曾猜到她在半夜為我們流下了多少眼淚。但我知道,她從東半球到西半球,再從西半球到東半球來回坐了89次24小時的國際飛機。在我們面前,她不曾有過任何怨言,她給我們的永遠是她的笑容,她為了我們總是付出、付出、再付出。”
朱浩然在他的文章里提到他第一次看到“馬奶奶”落淚,因為他們幾個男生調皮犯錯,他知道,“馬奶奶”的傷心是因為愛他們,關心他們。讓朱浩然印象深刻的還有“馬奶奶”帶來的美國的風俗,其中他最喜歡最期待的活動是染彩蛋,就是把雞蛋殼染上各種顏色,有能力的話還可以畫上圖案,最后還要評比誰的彩蛋最漂亮、最有創意,獲勝者還會得到“馬奶奶”精心準備的小禮物。
《我和馬奶奶的情緣》的作者呂聰慧在文中介紹說,“馬奶奶”每年會往返中美兩次,為孩子們的生活經費奔波,每次都會推著兩大包捐贈品和自己的行李,路線從來沒有一次是直來直往的,總是會轉來轉去,她還得頂著暈車、船的困擾,一次次地告訴自己堅持下去。這位小作者的語言如詩一般:“年輪,從明凈平滑的額頭上走過,從依舊鮮活的心坎上走過,銘刻下十幾道彎彎曲曲的執著,每一個執著里都播種著大愛的希望,每一個執著里又回蕩著無悔的長歌。”

獲獎“功勛外教”合影,自左至右依次為佩德羅·雷諾、杰弗里·雷蒙、伊莎白·柯魯克、潘威廉、戴偉 (王泱攝影)
葛潘:鶴發銀絲映日月,丹心熱血沃新花
北京外國語大學亞非學院泰語系,也有我們的一位老朋友,早已滿頭銀發,卻仍孜孜不倦地為中國培養泰語人才的教師——葛潘。從1992年起,她先后多次來到中國執教,她的學生遍布中泰兩國的外交、外貿、教育、傳媒等行業,于2005年榮獲中國政府“友誼獎”,2014年獲得我刊評出的“我最喜愛的外教”榮譽稱號。
“一頭短發被匆匆流過的時光染成了銀白色,鶴發童顏的葛潘笑起來時,小小的眼睛瞇成一條線,整個人散發著親切和藹的氣息。”馬婉欣在《老了也可以是天使》中這樣描寫葛潘,“盡管歲月已然在她的面龐上留下了痕跡,但我們相信,她的內心一定和我們一樣年輕”。葛潘在上課時,表情和肢體動作總是很豐富。當她向學生們解釋在泰國伸出大拇指是表示生氣時,她側著身子,噘著嘴巴,伸出大拇指,撇過頭,用蹩腳的中文一字一頓地說:“我、生、氣、了!”當時學生們哄堂大笑,直說葛潘老師好可愛。當葛潘老師調侃某位同學時,她總會在話說完后把頭別到一邊,半仰著頭,微閉著眼,嘴角偷偷上揚,等著大家做出反應。這時的她就如同一個惡作劇得逞的孩子,讓人忍俊不禁。
有一次談到水燈節的活動,可愛的葛潘神采奕奕地蹺起蘭花指,哼著小曲兒,有板有眼地踩著舞步,還不忘糾正學生們滑稽的動作。曹旭輝的《滿懷赤子之心》文中寫道,“我們夸贊您美極了,您羞澀地笑了,像個忸怩的小女孩,惹人喜愛。”每個星期,大家總會期待去葛潘老師家學習,說不定還能吃到老師親手做的泰國炒飯或者喝到老師親手泡的泰國果汁。
《我們的“老頑童”》一文中,作者盧曉東回顧道,第一次去葛潘家的時候,正準備脫鞋,葛潘擺了擺手,搖了搖頭,笑著說,現在是冬天,天氣冷,地板也冷,怕冷到大家的腳。又有一次,當葛潘看到有的學生洗完頭跑著過來上課的時候,著急地說:“下次遇到這樣的情況就直接來我家洗頭吧,洗澡也可以啊,我這里有吹風機,外面天氣冷,這樣很容易感冒的!”這就是葛潘老師,在細言微行中言傳身教,讓學生感受到她的關心與愛護。
戴小蜜在《老師,一首無言的歌》中說,葛潘除了教學生們泰語,也會告訴大家一些泰國的歷史文化以及中泰之間的關系發展。冬天,學生們去她家練習,一進門,葛潘開口第一句話總是問大家冷不冷啊,然后遞給大家一杯滾燙的熱水。一顆寒冷的心也瞬間溫暖起來。當學生們離開時,她也不忘叮囑大家要穿上衣服,看看每個人的圍巾手套是不是都武裝起來對付凜冽的寒風。
有兩句詩,形容葛潘最合適不過:“鶴發銀絲映日月,丹心熱血沃新花。”
陳美銀:中國面孔,火熱心腸
“她有一張中國人的面孔,一口地道的普通話;她有一副火熱的心腸,她心直口快,講標準的美式英語。她工作起來風風火火、雷厲風行、不講休息、不計報酬。”這是洪弘筆下的陳美銀,2011年江蘇“友誼獎”獲得者,2012年中國政府“友誼獎”獲得者,徐州市彭城培智學校名譽校長兼外語教師。
陳美銀是美籍華人,出生于美國舊金山。2009年退休前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駐北京辦事處行政官,曾獲教科文組織頒發的“和平獎”。陳美銀對中國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在聯合國任職期間就特別關心中國的基礎教育和特殊教育事業。她曾經先后幫助創建和資助了我國貧困地區十幾所希望小學。在教科文組織的協助下,陳美銀為徐州市彭城培智學校募集資金,創建嶄新的校舍。洪弘寫道:“陳美銀女士幫助我們學校并不是一時一事,而是不斷的、持久的,往往是在學校最需要的時候伸出援手。她關心每一位老師,關愛每一個兒童。”
洪弘介紹說,連續多年的時間每個學期都有20余名家境困難的學生得到她和教科文組織減免學費的幫助。學生倪朋,天生有苯丙酮尿癥,需要長期不間斷地服用藥物維持生命,每箱藥2600元,僅夠服用三個月。倪朋家長愁腸百結,痛哭流涕。當得知這一消息后,陳女士毫不猶豫地從工資里拿出錢來幫倪朋買藥,從2004年至今一買就是12年從未間斷過。她說,只要我還有這個能力,我還會持續地幫助下去。倪朋同學在她的資助下,個子長高了,臉色紅潤了,也更懂事了,至今仍快樂地生活著,學習著。倪朋一家人更是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倪朋父親說:“這樣一位和我們并不十分熟悉的外國人能這樣毫無私心地、持久地幫助我們,真是太難得了。我們衷心地感謝她,我們永久地感激她!”
李琳在《我和外教老師》中這樣描寫自己的老師陳美銀,“聽見她說話就會心安、放松,能夠放心地把所有的都給她。她喜歡這群孩子。”
同事李影在《跨越國界的愛心》中回顧了第一次見陳美銀的情景。她的第一印象中,陳美銀是一位大約五六十歲,個子不高,穿著樸素,笑容和藹,身材微胖的中年婦女。當時韓汝芬校長說:“15年前,我們的學校設在一個即將拆遷的危樓里,學生全是智障兒童,家庭生活非常困難,學生即將面臨失學的困境,是陳美銀奔走呼吁,四處募集資金為我們建校舍,才有了我們現在漂亮的校園,孩子們才有了可以上學的地方,陳校長幫助我們的還有很多很多……”說著說著韓校長哽咽了,淚水在眼眶里打轉,只見陳美銀女士掏出手帕拭去老人眼角的淚水,大家被這場面深深感動,孩子們親切地叫著:“陳老師好!”
陳美銀的課堂總是充滿著歡笑,整個課堂很活躍,孩子很放松,有些孩子甚至跑到前面拉著陳校長的手,陳校長說:“hand in hand,手拉手,好朋友”,說著又在孩子的額頭上親了親,孩子們甚是喜歡這位外籍教師,總是親切地叫著“陳老師、陳阿姨、陳奶奶。”
2015年12月,陳美銀獲得“2015年情動江蘇·杰出國際友人”稱號,李影帶領學校5名智障學生去參加頒獎典禮,與陳美銀同吃同住,“陳校長帶孩子去吃肯德基,吃了薯條、漢堡包,孩子們可興奮了,因為有些孩子都沒有吃過這些東西,陳校長很幽默,和孩子們聊著天,一起做游戲。”第二天的頒獎典禮上,5名學生走到臺前和陳美銀一起合唱《澎湖灣》,并給臺下的觀眾送了學生們親手制作的衍紙賀卡,場下傳來了經久不息的掌聲。
有一種愛可以橫跨地球兩端,有一種關心可以永久滋潤心田。像馬珍妮、葛潘、陳美銀這樣的老朋友還有很多,比如學生征文中的“洋”教授奶奶吳雪莉;比如北外最年長的教授、新中國第一代外語教師、我國當代德高望重的外籍專家伊莎白,更是很多次出現在征文當中,是我們的老朋友;比如“十大功勛外教”獲得者,以及那些獲得“我最喜愛的外教”稱號的諸多外教老師,都是我們的老朋友。
老朋友的故事,老朋友對教育的奉獻,老朋友與學生的情誼,老朋友跟中國的緣分,永遠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