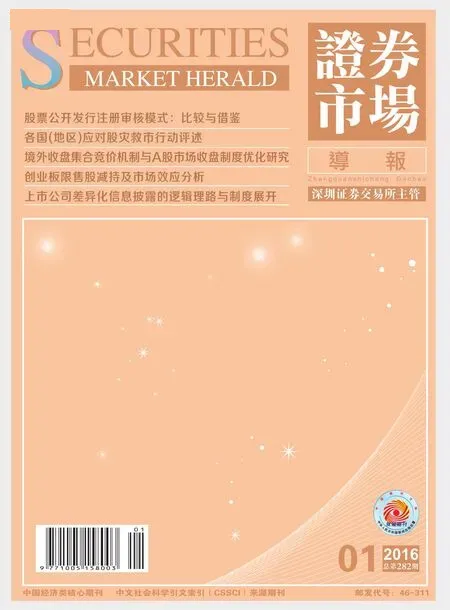上市公司差異化信息披露的邏輯理路與制度展開
(西南政法大學民商法學院,重慶 401120)
引言
我國證券市場正在經歷著以注冊制改革為起點的整體性變革,從“核準制”向“注冊制”的順利轉型需要一系列配套制度的跟進配合。而核心始終是證券市場之靈魂——“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誠然,近三十年以來我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與證券市場一同經歷了從無到有、逐步完善的發展過程,有效緩解了市場建立初期信息供給不足、內幕交易遍布的歷史困局。但時至今日,證券產品復雜化、投資者構成多元化、上市公司分級化、市場功能層次化已成必然趨勢。作為博弈雙方的投資者與上市公司,其利益訴求也存在顯著變化:投資者對信息內容的現實需求從“形式規范性”邁向“實質有效性”,甚至不同類型的投資者對于信息需求的多與少、詳與簡、以及所關注的重點都在發生變化分離;與此同時,不同行業、不同經營水平的上市公司,其信息披露動機和質量也出現分化差異。因此,如何滿足投資者多元化的信息需求?如何鼓勵上市公司從源頭上提高信息披露質量?如何以有限的監管資源來應對數量眾多的上市公司?這些都是亟需解決的現實困境。本文著眼于我國目前信息披露實踐中存在的供需沖突,并在透析理論和關注改革動向的基礎上,試圖通過下文論述來探究“差異化信息披露”,并依次回應三個問題:(1)差異化信息披露的法理依據?(2)何謂差異化信息披露?(3)如何實現差異化信息披露?
供需沖突: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價值解構
公平與效率是任何經濟倫理的價值尺度或標準,也是包括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在內的所有商事法律規范的基本價值。按照從“結果公平”到“機會公平”再到“制度公平”的深化趨勢1,“公平”價值在信息披露制度中具有四層逐步遞進的含義:一、信息在供給者和需求者之間分布均衡;二、信息需求者之間具有公平獲取信息的機會;三、信息的使用價值在需求者之間公平實現;四、披露信息所產生的效益在供給者之間公平分配。同理,“效率”價值在信息披露制度中也體現為三個方面:一、融資者能以較低的成本付出遵守法定規范并贏得投資者的信任與信心;二、投資者能以較低的成本處理信息并將其反應于證券價格之上;三、監管者通過對信息披露實施監管來創造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環境,使證券價格隨信息的公開披露而充分變動。2
從實踐來看,在日益充盈的信息披露法律規范體系下,上市公司向投資者提供的信息總量不斷增加,緩解了信息分布不均的原始困局。但與此同時,信息披露內容同質化、模版化和擴大化的問題也逐漸凸顯。根據深交所發起的問卷調查結果來看,目前,我國上市公司對信息披露有效性的平均認可程度達到七成,但僅有不足五成的投資者認同這一觀點。3信息供求雙方對于披露文本中有效信息含量的迥異判斷折射出信息披露存在供求沖突的客觀事實,而其根源則在于供需主體之間存在多樣化的利益訴求。
一、上市公司與投資者之間的供需沖突
信息供需矛盾又表現在披露數量和質量兩個方面:在披露數量上,上市公司希望提供較少信息而贏得投資者的更多信任4,但投資者希望對方提供更多信息以節約自身的搜集成本;在披露質量上,出于保護商業秘密、維護競爭能力或避免引發訴訟等動機,上市公司傾向于提供歷史信息或進行選擇性、含糊性的披露,亦或利用“信息平衡術”披露大量通用信息以替代一些重要的個性化信息,這反而誤導投資者陷于大量冗余信息之中不知所措,幾乎成為“睜著眼睛的瞎子”。
二、監管者與投資者之間的需求沖突
市場監管者的監管方式與監管力度對信息供需也會產生諸多影響。一般而言,在以行政監管為主導的實質審核方式下5,上市公司會傾向于披露更多“合規”、“規范”類信息,而那些能夠反映其發展價值和風險的非監管類信息可能披露不足。雖然監管信息與非監管信息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矛盾,但如果在篇幅有限的招披露文本中同時出現,必然存在數量上此消彼長的關系。
三、公眾投資者與機構投資者之間的需求沖突
上市公司按照統一規范披露信息,而不同類型投資者因為其信息加工意愿和加工能力的差異而對信息需求的多與少、詳與簡,以及所關注的重點都有所不同。例如機構投資者善于對信息進行二次加工、分析,因此他們對信息的深度、廣度和及時性要求很高,更需要獲取大量以真實數據為主要內容的原始型信息,以便得出不同的定量和定性結論。6從信息獲取方式上看,機構投資者也更注重在公開披露的信息以外與發行人或上市公司的高管、同行或特定研究人員進行溝通獲取其余信息。
相較而言,公眾投資者在信息挖掘、分析、理解等方面的能力顯弱。同時,其投資期限短、換手率高、熱衷于進行短線投資。因此,他們更青睞于由原始信息加工而成的事實性信息和結論性信息。從信息使用方式看,公眾投資者多以閱讀理解為主,較少使用輔助工具進行統計分析,因此他們希望信息供給者以通俗易懂、圖文結合或索引的方式提供真實信息。
綜上可見,信息供需沖突不僅存在于上市公司與投資者之間,甚至不同主體的需求也并非完全一致。這種沖突的實質是一種“期望差距”,供求雙方無法通過自己的成本付出給對方帶來相應效益,但公平與效率兩種法律價值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中的真正實現恰恰需以消解這種沖突為前提,并且這也是整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不斷發展演進的動因。誠如有學者指出,證券信息披露制度的演變過程,就是一個在鋼絲上行走并尋求平衡的過程,鋼絲的一邊是投資者保護和信息需求,另一邊則是公司發展和經濟增長[1]。因此,我們需要在尋找誘因的基礎上搭建一種解決路徑。
調和方向:差異化信息披露的界定及其法理依據
導致這種供需沖突或“期望差距”的原因可能有兩個方面:其一,供求雙方的立場不同,信息使用者游離于公司之外,在信息不對稱的客觀前提下與上市公司存在溝通隔閡。但應當承認,這是市場博弈的必然風險也是盈利機會。其二,現行立法理念和監管思路可能會增加信息供給負擔,同時也存在偏離投資者決策需要的引導傾向。在整齊劃一和“一刀切”式的信息披露規范下,細分的市場功能、多樣的投資者需求和公司樣態等差異事實未被充分關注。披露文本體現的是對法定規范的“遵守”,而非與投資者之間的“互動溝通”。其結果是:上市公司耗費成本重復披露許多冗余的通用信息,而與公司實際經營情況、未來發展趨勢密切相關的個性化信息往往被一筆帶過。投資者付出時間、精力、物力但卻無力在這些爆炸式的信息中衡量公司的優劣與價值。那些真正具有發展潛力的公司未能脫穎而出,它們可能會因為沒有從其高質量的信息披露中獲取市場溢價而喪失持續合規的利益動機。上升到法律價值的高度來看,這種信息披露制度可能沒有為證券信息的生產、傳輸創造一種公平并高效運作的市場環境。
據此,破解這種困境的基本思路是:以信息供求雙方的多樣性區分和信息傳遞空間的層次化區分為視角,嘗試安排一種不同一、不統一,區別于一體強制披露的體系。我們將此稱為“差異化信息披露”。需要強調的是,差異化信息披露并非是要返回到早期完全自愿披露的歷史時期以“新瓶裝舊酒”。而是在現有框架下兼顧不同信息供給者、使用者以及信息使用環境的差異屬性,打破引發信息披露制度中不公平或不效率的“同一性”因素,將原本屬于“差異”的一切還給差異。
其法理依據至少在于以下三個方面:
1.滿足投資者多樣化的信息需求
其中,“投資者”和“多樣化”這兩個關鍵詞意味著這種信息披露既有別于以往那種面向監管者的供給傾向,也要對不同投資者的信息需求予以回應。原因在于,在證券發行注冊制的改革征途上,監管者意在逐步退出市場博弈,省去以往在發行入口處代替投資者來對上市公司進行“優劣淘汰”前置環節,實現由“參賽者”向“裁判者”的角色轉化,進行“補正式監管”。其職責限于:完善并執行披露規范以維護信息傳輸機制的暢通,加強對違法行為的事中和事后監管,防范和糾正信息傳播中的誤導和失真。據此,應當調整過去以“監管需求為導向”規范取向,將要求上市公司“披露什么”以及“如何披露”的話語權交還給投資者,使信息披露成為投資者和上市公司之間進行博弈的有力工具。此外,還應兼顧不同投資者對有效信息認知的深度和廣度存在差異的客觀事實,適時提供兩種深度有別但主旨相同的披露文本,對此將在后文述及。
2.降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成本
前文提到,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中所付出的成本不僅包括那些可以計量的顯性成本,還包括難以預估的隱性成本。作為逐利的市場經濟人,降低成本是其行動的最好激勵。由此,信息披露的制度設計應當盡量契合上市公司的利益旨趣,避免出現“法律更多但秩序更少”的尷尬處境[2]。而差異化信息披露正是將不同上市公司的不同信息以不同方式予以披露。這樣,既可以使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內容“少而精”,也可以自由選擇披露渠道。對投資者而言,能夠便捷獲取可讀性更強的信息內容以提高決策準確性。
3.突出信息披露的監管重點
在即將到來的證券發行注冊制時代,我國上市公司數量可能會在較短時間內迅速增加,市場監管的難度和復雜程度也會進一步加深,這無疑給極其有限的監管資源帶來新的挑戰。差異化信息披露的推進雖然可能增加立法成本,但卻有助于突出信息披露監管的針對性,監管機構可以集中精力識別并監督那些風險更高或行業特色顯著的上市公司及時披露重要信息,從不同行業和不同公司入手逐步提高市場中信息披露的整體質量。
行業細分與風險評級:差異化信息披露的展開維度
通過上文闡釋可以看到,差異化信息披露并非苛求每個公司都呈現完全“差異化”的樣態。更理性的安排是確定上市公司“同質性”和“異質性”的區分維度,對不同類型或同一類型不同情況的上市公司適用不同的規范內容,以形成層次有序的差異化體系。這種區分可將公司所在行業以及風險水平的差異作為基礎。
一、行業細分下差異化信息披露的展開維度
同一行業內的組織單位具有相同的生命周期、產品結構和競爭態勢,企業的興衰總是和其所處的行業周期息息相關,所以行業類比是判斷企業是否具有同質性的一個重要標準。信息披露外部性(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Externality)理論研究發現,一家上市公司所披露的信息會對其他主體產生直接或間接影響[3],而這種影響在同行業中的表現最為明顯。7事實上,這種制度實踐在許多國家資本市場中早已存在:
比如,美國納斯達克市場與香港聯合交易所分別針對石油與天然氣、銀行、房地產、保險、礦業等行業的發行披露與持續性披露進行了特殊規范,并制定格式指引。8澳大利亞資本市場中約有一半上市公司的主營業務均與礦產有關,因此,其交易所的上市規則要求在季報中披露有關礦產資源開采、勘探、生產成本費用,并在年報中披露資源儲量。另外,上市規則附錄中還規定了對勘探結果、礦產資源和礦石儲量的最低公開披露標準和要求,并制定了礦業、石油和天然氣開采行業的季度報告披露格式指引。9
我國自2000年起也開始關于一些特定行業的信息披露并制定相應規范。這些規范包括部門規章(證監會發布)和自律規則(滬深兩大交易所)兩個層次,涉及銀行、房地產、保險公司、石油天然氣、煤礦、廣播電視、藥品和生物制品共七大行業。同時,證監會于2012年對《上市公司行業分類指引》(2001年發布)進行了修訂,包括將行業分類目錄與國民經濟行業分類目錄調整至基本一致;成立上市公司行業分類專家委員會,專門負責行業分類咨詢與判斷;建立了行業分類的動態維護機制,以提高行業分類的時效性和生命力。10依此,滬深交易所分別于2013年針對前述行業發布了信息披露指引,深交所更是在今年7月和9月分別推出了針對創業板上節能環保服務行業和互聯網行業的信息披露指引。這些指引使我國分行業差異化信息披露的實踐邁出了實質性的步伐,起到了很好的試點作用。但在此基礎上仍有待改進的空間:
1.《指引》中反映公司風險因素的信息居多、與投資價值有關的信息較少。翻閱目前已經制定行業《指引》的上市公司年報可以看到,多數公司僅套用指引中有關行業風險的一些原則性描述,大幅羅列公司財務數據、風險因素,但以行業整體發展情況為背景結合上市公司之個體的深入分析并不多見,也沒有關于公司投資價值的定量或定性分析。
2.《指引》中結合行業經營特點的法定披露內容居多,留給公司自愿披露的內容較少。但事實上,即便針對某一行業制定相應的信息披露《指引》,也難以在其中完全揭示某一行業內特定上市公司的投資價值。因此,在制定《指引》類的法定規范外,還需尋找其它的跟蹤監管措施。
3.同一行業內上市公司的差異化披露體現不足。雖然以行業區分為基礎進行信息披露已經是一大進步,但同一行業的上市公司會依照相同的標準和格式,披露幾乎同樣的內容,從而同一行業內依然實行強制一體的信息披露方式。因此,建議未來制定的行業信息披露指引中應當注意適用差異化信息披露的工具性方法,以使同一行業內不同上市公司之間的信息披露也有特殊體現。
2015年1月5日,上海證券交易所正式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監管模式由轄區監管調整為行業監管。11這一監管方式的轉型有利于投資者更為準確的了解上市公司的投資價值,同時,也將繼續加快推進我國差異化信息披露的立法與實踐。
二、風險評級下差異化信息披露的展開維度
同一層次市場或同一行業內的不同上市公司,他們可能因公司治理結構、風險管理能力、規范運作程度的不同而存在不同的風險水平,對于不同公司信息披露的監管難度也各不相同。事實上,對金融類公司的監管實踐中早已按不同風險水平實施分類監管,并取得了較好的實踐效果。因此,為了緩解不斷擴大的市場容量和相對有限地監管資源二者之間的現實矛盾,并引導上市公司將外部監管壓力轉化為內部規范動力,形成良性循環的激勵機制,也可考慮對所有上市公司進行風險識別,并確定風險水平,以此為基礎,在不同公司之間實施差異化的信息披露。
要保證風險識別的客觀性和科學性,需要確定統一的評價指標,常見的基礎性指標包括:公司治理水平、財務水平、風險指標、信息披露質量等。當然,在每個基礎指標之下還可以設計更具體的二級、三級指標,根據每項指標所揭示的風險重要性的不同,對其配以不同權重。指標設計越精細,評價結果越接近客觀事實。在確定評價指標之外,還需確定風險等級。等級劃分太少,則會顯得粗略草率,不能突出眾多上市公司之間的實質差別,但等級種類太多也會造成投資者的識別困難,增加監管負擔,因此如何確定恰當的等級劃分還值得仔細衡量。
實現路徑:差異化信息披露的內容與形式
探索了差異化信息披露的展開維度以后,接下來從內容與形式兩個方面來探討其實現路徑。
一、披露內容的差異化安排
1.強制性披露的邊界及自愿性披露的補充
強制性信息披露的確立有助于緩解證券信息這種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的困境,但其迅速擴張也可能成為一種危險趨勢。一方面,從規則供給角度講,“規范供給者”(立法者和監管者)與投資者一樣置于公司之外,在事前未必能掌握比投資者更多的證券信息,即對于被約束者擁有或掌握哪些信息并不清楚。另一方面,從規則執行角度講,對那些從外部不可觀測或不可核實的公司信息12,強制性披露制度無法規制。因此,強制性信息披露的規范供給應當被控制在一個“合理范圍”之內,余下的空間則需要采用靈活的軟性規制路徑及自愿性信息披露來填充。
部分國家和地區通過在上市規則中嵌入“不披露即解釋”(Explanatory Disclosures)規則來對此進行軟化。13即允許本國或本地區境內的上市公司對《上市公司治理準則》進行選擇性適用,既可以選擇完全遵守這些規則,也可以排除適用部分條款,但必須在公開披露的文件中對其排除適用的原因進行解釋,并說明所采取的替代性做法。“解釋性披露”是該模式的核心要素,因為市場機制的運行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公司就治理問題進行了怎樣的披露。14一般而言,上市公司需要解釋披露的內容包括:(1)聲明公司各項運作安排是否遵守《準則》建議;(2)如果沒有遵守的,需要特別指出,并作出相應的解釋和說明;(3)對此采取了哪些替代性措施。15
“不披露即解釋”以公司的契約屬性為基礎,在承認公司之間存在差異化的前提下賦予其更大自由并提供了一種分散性的試錯機會。同時,如果公司進行“選擇性”偏離,也會引起投資者乃至整個市場的高度關注。
于我國而言,建議在我國《上市公司治理準則》中納入“遵守或解釋披露”的規則。具體可以將《準則》規范分為效力不同的三個部分:現有法律闡述、約束性規范和建議性內容。第一層的法律闡述是對現有法律精神及要點的提煉,幫助上市公司更好的理解遵守;第二層的約束性建議中引入“不披露即解釋”的規則,要求公司在每年的定期披露報告中對本報告期間內公司遵守《準則》的情況進行披露,指出沒有遵守的內容,并對其采取的替代性做法進行詳細說明。第三層的建議性內容可以不遵守并且無需解釋。
同時,由于自愿性信息披露本質上是披露義務人對成本收益進行權衡以后自愿從嚴遵循或補充披露的行為結果,其內容和質量更多依賴于公司自身的利益驅動。如果這種披露不受任何約束而放任自流,則無法保證質量的信息可能成為一種市場噪音。因此,通過法律對自愿性信息披露的質量進行引導、規范是保持其生命力的必要途徑,只是在管制力度和管制方式上與強制性披露有所區別,即有所為和有所不為。立法應采取因勢利導的方式為信息供給者提供降低成本或提高收益的可能渠道,積極引導上市公司自身改進。從各國已有的實踐來看,降低成本主要是減輕因自愿性披露而引致的訴訟風險16,而提高收益則體現為縮小發行人與投資者之間在自愿性信息披露的供給與需求上的鴻溝。17此外,還可以通過建立經理人聲譽機制、建立有效的內部控制體系、建立公司信息評級體系、完善公司治理結構來間接提高自愿性披露的正向效應。
2.全面披露與簡化披露
如前所述,機構投資者與公眾投資者之間的信息需求在某種程度上存在差異。而提高信息披露文件的可讀性,并非從“專業化”、“全面化”的極端走向“通俗化”、“縮減化”的極端,而應針對不同投資者的需要和不同上市公司的日常表現對披露文本進行重新設計和調整,以達到簡化披露之目的,結合已有的實踐經驗,本文總結了以下三種簡化方法:
(1)濃縮報告摘要。建議未來在披露摘要中進一步簡化會計報表及其附注,因為這部分內容對公眾投資者來說理解難度較大;其次是一些在短期內沒有發生重大變化,且重要性略低的內容可以刪減或做總結性陳述。另外,對于評級較高的公司可以考慮允許其只披露年報摘要。
(2)簡化報告文本。在不減少有用信息含量的基礎上,縮減披露文本中細枝末節的信息記載或簡化各項指標。具體可通過建立索引、附注;簡化財務指標、財務述評;采取相互引證;刪減重復的介紹性信息等方式進行。但對于公司業績影響較大的指標或市場普遍關注的行業動態以及公司重大事項等,均應當詳細披露,并在報告摘要和正文中分別進行提示和詳細性闡述,以引起投資者注意。
(3)調整披露時間。未來實踐中,可以探索根據上市公司日常表現進行評級的基礎上,對于評價較高的公司,其運作風險較小,因此定期報告的披露時間可以延長;而評級較低的公司,其運作風險較大,需要密切關注,因此定期報告的披露時間可以縮短。
二、披露形式的差異化安排
網絡媒介作為信息披露的新型載體不僅改變了傳統的信息傳輸方式,甚至正在改變著整個市場結構。但就現狀來看,紙媒披露的方式也沒有被完全取代,因此,如何利用這兩種披露方式共存的事實來進行差異化安排也值得探究。
“七報一刊”是目前法定的紙質媒體。18法定的網絡披露方式主要包括在特定網站、電子布告欄、文件傳輸協議、用戶新聞組中進行的信息披露。19其中我國滬深兩市交易所推出的“直通車”和“互動易”兩種電子信息披露系統最為常用。“直通車”是指上市公司將擬對外披露的信息公告直接交給指定披露媒體進行對外披露的便捷方式,證券交易所僅對已披露的信息進行事后審核。20它實現了信息報告從提交到發布的全程電子化,也顛覆了信息披露事前審核的傳統,增強上市公司自律規范的意識,是監管理念轉型在信息披露載體中的直接體現。目前,兩大交易所均已開通該項系統。但為了便于信息供需雙方更加直接、便捷地互動溝通,深交所于2011年11月推出了“互動易”,其優化功能體現于投資者提問、投訴與回復功能以及定制化的信息服務等方面。21
結合我國現有的信息披露形式,本文選取幾種方式舉例說明,以期為信息披露形式的差異化提供一些探索思路。
1.不同風險水平公司披露形式的差異化安排
如前文所述,根據若干指標來衡量上市公司的風險水平并進行風險評級是差異化信息披露的展開維度。在此基礎上,應當嚴格監管那些風險較高的上市公司同時對風險較低的公司適當放松,賦予其更大自由。具體建議:(1)針對風險較低的上市公司,取消通過紙媒方式披露的強制性規定,讓其自由選擇以網絡形式進行單一披露,或運用兩種方式雙重披露。(2)允許風險較低的上市公司將公司網站作為法定的信息披露形式。既可以在不增加風險的前提下豐富信息披露的法定形式,也可以滿足投資多元化的信息獲取習慣。(3)針對風險較高的上市公司,繼續強制進行紙媒披露。目的在于使其付出較高的披露成本,以主動改進治理,規范信息披露行為,積極降低風險水平。(4)嚴格禁止高風險級別的上市公司在目前法定的信息披露方式之外進行其他形式的披露,以防止出現泄漏內幕信息而難以監控的情況。
2.鼓勵風險較低的公司進行自愿性披露
根據我國信息披露的現有規定和實踐來看,“互動易”這類公益性信息披露平臺還局限于為法定強制性信息披露提供創新渠道。上市公司與投資者的交流溝通僅限于已經披露的法定范圍,不能涉及未披露的信息或法定范圍以外的信息。因此本文建議,未來可以借助這種交互式的披露方式來鼓勵上市公司提供更多的自愿披露內容,比如根據自愿,將接待機構投資者來訪的資料、宣傳推介資料、各類重大新聞等內容通過“互動易”向全體投資者發布說明,當然,通過這種載體進行自愿披露也必帶來更多的監管難題,這也是未來繼續探討的方向。
注釋
1.有學者指出,從公平訴求的表現形式來講,人類對公平價值的追求基本經歷了結果公平、機會公平和制度公平三個階段。參見楊清望.和諧:法律公平價值的時代內涵[J].法學論壇, 2006, (06).
2.See Zohar Goshen and Gideon Parchomovsky, The essential role of securities regulation, Duke Law Journal, vol55(2,2006) ;See Jeffrey N.Gordon and Lewis A.Kornhauser, Efficient Markets, Costly Information,and Securities Research, 60 N.Y.U.L.REV.761, 802(1985).
3.2013年, 深交所就我國目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有效性的問題
展開問卷調查,調查結果顯示:約有71.31%和69.98%的上市公司認為信息披露的有效信息含量大于70%,但僅有8.16%的個人投資者和36.26%的機構投資者對此表示認同。參見趙立新.構建投資者需求導向的信息披露體系[J].中國金融, 2013, (6): 78.此外,也有學者調研發現,僅有32%的調查對象認為我國上市公司的年報、半年報中有效信息含量超過70%,但近九成的調查對象都認為信息披露存在明顯的重復披露問題。參見陳華敏.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有效性[J].資本市場, 2012, (08): 99.
4.信息披露成本是指信息供給者進行信息披露時可能發生的一切支出,包括可以用貨幣計量的顯性成本(信息編制成本、傳播成本、訴訟成本)和不能用貨幣計量的隱性成本(因信息披露所引起的訴訟成本、競爭劣勢成本和經營行為的約束成本)等。
5.信息披露的實質審核是在對整個證券市場實行實質監管的前提下,以監管者對信息披露的“事前集中判斷”來代替零散的市場選擇。在此過程中,信息披露法律規范以及監管實踐都傾向于要求發行人及上市公司披露與其營業性質、財務杠桿率、組織結構、發行數量和價格相關的大量信息,以此衡量和判明擬發行證券品質“優良”與否。
6.一般而言,證券分析師的解讀對于機構投資者作出一項投資決策發揮著重要作用。這種解讀是根據歷史數據來把握推動公司成長的業績驅動要素和價值驅動要素,分析驅動要素在未來的發展方向,據此對公司未來業務進行預測并提供證券投資評級。Hope, O.,”Disclosure Practices, Enforcement of Accounting Standards,and Analysts’ Forecast Accuracy: An International Study”,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03, 41(2): pp.235-272.
7.Foster教授最早曾以上市公司財務信息披露中的盈余公告為研究對象,指出公司披露的信息不但影響投資者對本公司的市場預期,而且還會影響投資者對同行其他公司的市場預期,從而產生同行信息傳遞效應。See George Foster, “Intra-industry information transfers associated with earnings releases, ”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vol.3, no.3, December 1981, pp.201-232.
8.美國早在1933年《證券法》和1934年《證券交易法》出臺之際就頒布兩則產業指導條例:《證券行業指南801條例》(Securities Act Industry Guides Item801)和《證券行業指南802條例》(Securities Act Industry Guides Item802)。兩份指南對石油與天然氣、銀行、房地產、保險、礦產經營行業內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提出了特別要求。See SEC Standard Industry Code, 數據來源:http://www.nasdaq.com/screening/ 2015年7月2日訪問。香港聯合交易所曾于1999年發布了一份名為《年度披露報告的參考資料》,該資料總結了特定行業內具有代表性的上市公司一些常用的信息披露做法,并參考世界其他主要證券交易所對上市公司年度報告的披露規則,以此作為上市公司從行業角度披露年報信息的參考資料。其中包括不同行業的經營特點、統計數據、監管標準、行業專用名詞解釋等,涉及包括航空、制藥、石油化工等所15個行業。這份資料發布以后,在港上市的許多公司都據此形成了固定的信息披露自我約束要求,時至今日,該資料雖已被作為歷史檔案封存,但其對于推動在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質量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
9.See http://www.asx.com.au/listings/listing-IPO-on-ASX.htm 2015年7月2日訪問。
10.舊《指引》規定未經證券交易所批準,上市公司不得擅自改變公司類屬,對自己所被劃歸的行業存在疑義,或因兼并、重整等原因而至主營業務發生重大變動的,可以向證券交易所提出書面申請并提交相關的財務資料,由證券交易所對上市公司所提申請進行審查和批準。但新《指引》第6.2條規定上市公司行業分類在進行初次分類的基礎上還要按季度進行定期調整。對于那些不能依據統一指標進行分類的上市公司,則交由專家委員會進一步幫助審定。這種做法不但增強了行業分類的時效性,也提高了《指引》(2012)的實用性。
11.在本次信息披露監管模式調整以前,上海交易所公司監管部門采用的是按轄區監管模式,即按照上市公司所在的不同區域,對應安排監管人員,履行相應的監管職責。參見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http://www.sse.com.cn/ 2015年7月3日訪問。
12.通常是指能夠反映公司未來發展空間和競爭實力的各種“軟信息”(Soft Information)。
13.根據OECD在2003年發布的《OECD成員國公司治理發展報告》的統計顯示,英國、德國、比利時、意大利、荷蘭、波蘭、葡萄牙、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等國的《公司治理準則》的實施已經采取此種模式。See Org.Econ.Cooperation and Dev., Surve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Developments in OECD Countries 27, (2003),pp.26-31, http://www.oecd.org/dataoecd/58/27/21755678, 2015年7月3日訪問。
14.See Annaleen Steeno, “Corporate Governance: Economic Analysis of a Comply or Explain Approach, ” Stanford Journal of Law,Business & Finance, vol.11, no.2, Spring 2006, pp.387-408.Also see Oliver Krackhardt, “New Rules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A Model for New Zealand, ”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Law Review, vol.36, no.2, August 2005,pp.319-358.
15.Corporate Governance Committee ,The Belgian Code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p.10,
http://www.corporategovernancecommittee.be/library/documents/final%20code/CorpoGov_UK.pdf 2015年7月3日訪問。
16.如美國在1979年制定了“安全港規則”,并在1995年頒布了《私人訴訟改革法》(Private Securities Litigation Reform Act)予以修正,同時輔以“預先警示理論”和“心理確知要件”,三者共同形成一個健全的法律保護機制。只要不是出于惡意、人為的虛假披露來誤導投資者,就應當免除公司的責任,這樣既能保護投資者的合法利益,又不會打擊公司自愿披露信息的積極性。
17.美國證券市場中這方面的規范內容相對完善。比如,美國注冊會計師協會(AICPA)、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和SEC三大監管部門就投資者對自愿性信息披露的需求做了許多數據調查,并發布報告供上市公司參考。如1994年AICPA發布《改進公司報告:面向用戶》的報告;2001年FASB發布《改進財務報告:提高自愿性信息披露》;此后美國SEC為了強化公司治理與社會責任,列出了證券發行人需要自愿披露的20個方面的信息;更為細致的是,FASB還總結了一套上市公司可以用于確認哪些信息有助于投資者的決策,以及決定是否披露以及如何披露這些信息的框架。這些報告雖沒有強制實施力,但能夠對發行人起到良好的指引作用。參見FASB.Improving Reporting: Insights into Enhancing Voluntary Disclosure, http://www.fasb.org/brrp/brrp2.shtml 2015年7月4日訪問。
18.業內俗稱的“七報一刊”是指:《中國證券報》、《上海證券報》、《證券時報》、《金融時報》、《證券日報》、《中國改革報》、《中國日報》和《證券市場周刊》。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第70條、《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辦法》第6條。
19.參見武俊橋.證券信息網絡披露監管法律制度研究[D].武漢大學, 2010: 13.
20.參見《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直通車業務指引》(2014年修訂)第3條。
21.在“互動易”系統中,每位投資者可以通過注冊會員的身份享有自己的服務專區,包括添加、關注自己感興趣的上市公司,系統也會將其關注的上市公司有關最新消息推送給投資者,以方便閱讀,獲取最新消息。參見《深圳交易所互動易業務操作指南》,http://irm.cninfo.com.cn/szse/, 2015年7月4日訪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