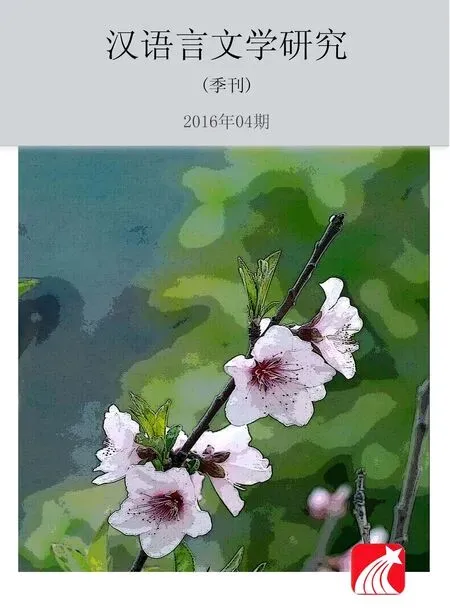從教為文三十年
《王向遠教授學術論文選集》編委會
從教為文三十年
《王向遠教授學術論文選集》編委會
編者按:在王向遠教授①王向遠,1962年生于山東,文學博士,著作家、翻譯家。1987年北京師范大學畢業后留校任教,1996年破格晉升教授,2000年起擔任博士生導師。獲“北京師范大學教學名師”稱號。現任北京師范大學東方學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東方文學研究會會長、中國比較文學教學研究會會長,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1項,獨立承擔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2項,重大項目子課題1項,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1項。兩部著作入選“國家社科基金中華學術外譯”項目。在《中國社會科學》《文學評論》《外國文學評論》《外國文學研究》《中國比較文學》《北京師范大學學報》《人民日報》等刊物發表論文200余篇。著有《王向遠著作集》(全十卷)及各種單行本著作20多種、合著4種,譯作有《日本古典文論選譯》(兩卷四冊)等日本名家名著10余種,共約300余萬字。曾獲首屆“高校青年教師教學基本功比賽”一等獎、第四屆“寶鋼教育獎”全國高校優秀教師獎、第六屆“霍英東教育獎”高校青年教師獎、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獎。有關論著曾獲第六屆“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第六屆“中國人民解放軍優秀圖書獎”、首屆“‘三個一百’原創出版工程”獎等多種獎項。從教滿30周年(1987-2016)之際,臺灣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王向遠教授學術論文選集》全十卷,選收1991-2016年間作者在各學術刊物上公開發表的220余篇學術論文、50余篇學術序跋等,共計200余萬字,與十年前出版的十卷本《王向遠著作集》互為姊妹篇。十位編委會成員分別撰寫的《編校后記》,圍繞《王向遠教授學術論文選集》各卷的編校,從不同角度談了讀書教書、求學治學以及學術史、學科理論等一系列普遍性問題,有一定參考價值,特加以整理刪節,刊發于后。
中國東方學的開拓
李群(湖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博士)
我編輯的《國學、東方學及東西方文學研究》是《王向遠教授學術論文選集》的第一卷,所收二十多篇文章都是2008年后,也就是最近八年間陸續發表的,反映了王老師近年來關于學科建設的理論思考與實踐的一個側面。本卷書名中的三個關鍵詞“國學”“東方學”“東西方文學”是相互連帶的概念,最關鍵的是“東方學”。實際上,老師最近幾年的主要精力也是在做“東方學”研究,特別是在2014年開始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東方學”體系建構與中國的東方學研究》以后。但是在此之前,他關于“東方學”的理論思考和建構早就開始了,最顯著的是在《宏觀比較文學講演錄》(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8)一書及相關文章中提出的“宏觀比較文學”這一范疇,以及與此相關的“民族文學”“國民文學”“區域文學”“東西方文學”等一系列概念。本卷所收錄的若干文章,如《論阿拉伯文學的民族特性》《論猶太-希伯來文學的特性》《試論波斯文學的民族特性》《論歐洲文學的區域性構造》《論俄羅斯文學的宏觀特性》《從宏觀比較文學看法國文學的特性》《論德國文學的民族特性》《拉丁美洲文學區域特性論》《黑非洲區域文學特征簡論》等,都體現了老師在這些方面的思考。然后,由文學研究出發,老師的研究進一步超越了文學而進入跨學科研究,于是順乎其然地跨入了“東方學”。
正如王老師所說,中國的“東方學”研究有豐厚的歷史積淀,但是關于“東方學”學科原理意義上的學科理論卻一直處在空白狀態。王老師的“東方學”研究首先聚焦于“東方學”學科理論的建構,要說明“東方學”是什么,就要清理“國學”與“東方學”、“國學”與“涉外研究”、“西方學”與“東方學”的關系,由此,他提出了“國人之學即是國學”“涉外研究是外傳中國文化的有效途徑”“中國的東方學是‘國學’的自然延伸”等一系列重要論斷。不僅如此,他還把東方學的學理與現實關懷聯系在一起,寫了《“一帶一路”與東方學》等文章,強化了東方學的應用性。這一切都令人耳目一新,體現了可貴的理論創新與學術勇氣。
“東方學”的理論建構及中國的東方學學術史研究,是王老師眼下正在進行的課題,也是未來若干年老師的工作重點。他所努力提倡的“東方學”學科,目前在我國學科體制下從事的人很少,但卻有重大的學術價值與現實意義。我輩愿追隨王老師,為中國的東方學貢獻自己的微薄之力。
比較文學的改革與我的親歷親證
周冰心(中央財經大學文化與傳媒學院教師、博士)
2016年8月,我一邊為即將開設的“比較文學概論”課程備課,一邊為《王向遠教授學術論文選集》第二卷《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研究》做最后的統稿工作。按理說編輯校對工作稍顯枯燥,不想當我面對一篇篇文章,同時準備一節節課程的時候,屏幕上的語字卻分明變得生動起來,每一篇文章的誕生、發表、回響乃至爭議,都恰似在眼前一般,而距離我第一次聆聽先生關于比較文學理論的見解,已經過去了整整15年。
2001年夏天的夜晚,我選修了文學院開設的“學術研究導引”課,值得慶幸至今的是,我曾一動不動地聽了三個小時王老師關于比較文學學科前景與發展的講座。現在想來,這個講座應該是本卷論文集的首篇 《21世紀的比較文學研究:回顧與展望》的擴展版。也因為此次講座,促使我今天成為了比較文學研究者中的一員。
2002年春季學期,北師大當年破舊的“新一”教室里,200名左右的本科生齊聚 “比較文學概論”課堂,我們一邊用著陳惇等教授的《比較文學概論》教材,一邊頗有些困惑地聽著講臺上王老師對這本經典教材的一些建議與評述。平心而論,厚厚的《比較文學概論》我們看起來有些吃力,而王老師相應的講解,我們聽起來也并不那么容易。到底影響研究與傳播研究是怎么回事?平行比較為什么容易做不好?所謂的“可比性”是什么意思?比較詩學和比較文論的不同究竟在哪里?甚至什么叫“詩學”……諸如此類的疑問,困擾著大二的我們。當然,我們并不知道的是,正是在課堂上侃侃而談的同時,王老師的這些關于比較文學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的新見解也迅速在各大核心期刊公開發表,并引起了熱烈反響,而懵懵懂懂的我們成了比較文學學科發展史的親歷者,只是不自知而已。十幾年過去了,當我再看到這些論文的時候(如論文集中的《論比較文學的傳播研究》《大膽假設,細致分析——比較文學“影響研究”新解》《比較文學平行研究功能模式新論》《比較詩學:局限性與可能性》《論比較文學的超文學研究》等),不禁有些悔意,悔的是面對這些充滿睿智與銳氣的文章,我們似乎沒有格外“珍惜”當年的時光。當然,這種悔意姑且也算作是一種學術上的成長吧。尤為重要的是,十幾年后,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學者意識到:比較文學中很多關鍵的理論與概念在引進的原初階段并沒有得到很好的界定、厘清,乃至造成了混淆。這些現象,先生早在上述論文中一一進行了指明、解析與論證。
更難能可貴的是,在中國比較文學的發展歷程中,老師一直站在中立客觀的角度,耐心地等待著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的成長。上世紀90年代,當比較文學學科發展表面看來欣欣向榮之際,大量“時髦”的文章充斥在“時髦”的雜志期刊上,甚至發出了建立“中國學派”的呼聲,而王老師在已經建構了一系列學科新論的同時,卻又清醒地意識到,需要給中國比較文學的勢頭稍微降降溫。于是,就有了《“闡發研究”及“中國學派”——文字虛構與理論泡沫》這篇文章的誕生。這篇論文言辭犀利、有理有據卻又苦口婆心,直擊當時中國比較文學發展的要害,引發了諸多學人連鎖性的思考。
而若干年之后,當有西方學者不看好比較文學的發展,甚至提出了“比較文學危機論”的時候,王老師又及時寫出了文章回應(見論文集中的《世界比較文學的重點已經移到中國》)。他在列舉了中國比較文學近年來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國比較文學學者所付出的大量艱辛勞作之后,鮮明地指出:中國比較文學超越了法國學派與美國學派的“學派”局限,將東方與西方文化相融合、文化視閾與文本詩學相整合,從而形成了“跨文化詩學”這一新的學術形態與新的學術時代。這看似簡單的寥寥數語,背后卻是中國比較文學同仁們走過的百余年的歷程,也是王老師審慎看待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發展史之后的冷靜思索。而我們,當時忝列于王老師筆下的“青年學子”之列,幸運地成為了這一歷史發展的親歷者。
2006年9月開始,作為研究生助教的我,全程跟聽了王老師的本科新課程“宏觀比較文學”。先生曾提起,這是他從教近30年來講課最累的一學期,因為所謂每周“備”的課,是每一周都要真正完成一篇高質量的學術論文,然后直接在課堂上宣讀講解,同時也囑咐我觀察學生的接受情況。不得不說,這似乎也是我做學生以來聽得最累的一學期,這種“累”不再是一知半解的懵懵懂懂,而是源于巨大的信息接受量,以及課下需拼命補充相關知識才能跟上老師思路的“累”,當然這種“累”,更意味著巨大的收獲和無比的滿足。我相信當年聽課的學生和我的感覺是一致的,因為在學期末的時候,學生對這門新課程的評價創下了歷史新高,或許,這是對本卷論文集中關于比較文學教學改革方面的文章(如《“宏觀比較文學”與本科生比較文學基礎教學內容的更新》《比較文學學術史上的宏觀比較及其方法論》《打通與封頂:比較文學課程的獨特性質與功能》等)最好的回報吧。
與此同時,老師在研究生課堂上的教學改革也在如火如荼地進行,這一思想主要體現在本卷《從“外國文學史”到“中國翻譯文學史”:一門課程面臨的挑戰及其出路》等論文中。雖然這篇論文主要是針對中文系本科生的基礎課程,但是王老師也在研究生的小范圍課堂 “翻譯文學導論”上試了一下水,正如他在論文中所提到的,這門課程“除了縱向的加強中外文學關系史的線索的梳理和描述外,在橫向上,還要進行對名家名作的賞析與批評。特別是注意對翻譯文學文本自身的鑒賞與批評。理想的狀態就是在必要的時候對重要的譯文與原文進行比較分析,看看翻譯家如何創造性地將原文譯成中文”。本次“試水”借由王老師的點撥,當時我身邊的很多同學選擇了不少頗具創新性的翻譯文學的題目,繼而寫出了優秀的翻譯文學的論文并公開發表,我想,這無疑是對王老師以上文章最有力的“證明”。
時至今日,作為書稿編校者,作為一名教師,再重新感受先生當年課程改革的系列觀點時,我似乎更加理解身為一個拓荒者,先生推進改革的不易。有創見、有勇氣、有膽識,也有未知,但這種“未知”,經由課程改革真刀實槍的實踐之后,在眾多學人的見證之下,變成了“真知”與“灼知”。
2015年9月,我進入中央財經大學文化與傳媒學院工作,第一次為學院的本科生開設“比較文學概論”課程。這一學期,我選用了王老師的專著《比較文學學科新論》作為上課教材。
這本書的誕生,如上文“親歷”部分所述,曾引起了巨大的反響,也“打”了幾場筆戰(如論文集中的《拾西人之唾余、唱“哲學”之高調談何創新——駁〈也談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創新問題〉》),從另一側面也凸顯了當時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爭鳴的繁榮。但是在我看來,這本書所引起的“教材”爭論卻更為重要,由教材的選擇、使用情況等所激發的反省與思索,對后來中國比較文學教學發展的影響甚為深遠。
在與夏景先生的論戰文章《邏輯·史實·理念——答夏景先生對〈比較文學學科新論〉的商榷》中,王老師系統闡述了學術專著與教材的關系,他指出:只有好的學術著作才配用作教材,凡有資格作教材的都必須具有“學術著作”的品格,而且是“好的學術著作”的品格,那種拼拼湊湊、“只編不著”的東西絕不能算是“好的教材”。
這場爭論十年后,我學識素養尚淺,還未達到先生所要求的用自己的書講自己的課的程度,但是我對先生的“教材”觀卻深以為然。此時,我并不是作為先生的門下學生選擇了這本書,而是作為一名比較文學的青年教師,在經過認真的比對與考慮之后,出于對學生學習的需要,慎重地選用了這部書作為教材。
在恩師30年的教學生涯面前,由僅僅教授一學期課程的我來談論使用教材的情況,未免顯得渺小而狂妄。但我想,經歷了15年之后,一直得益于先生比較文學學術思想滋養的我,以另一種角色、另一種立場,開啟后來的年輕學子們對比較文學的興趣和選擇,是一種責任,更是一種歷史的傳承。我也很欣喜地看到,在這一學期的講授中,學生們喜愛這本教材,甚至根據教材后面例舉的論文也嘗試著寫出了自己人生中第一篇學術論文。這種結果,我想,無論對于哪一位老師來說,都是莫大的鼓勵與安慰。
所以,一篇論文的選擇與收錄或許很快就能決定,一場筆戰爭論的硝煙或許很快也會退散,但是從論文與筆戰中所誕生的思想與創見,在很多年之后卻依舊在無聲而有力地發揮著它的影響。
學在現場,憶在當下,樂在其中,僅以此篇小文總結我對本卷論文集的些許感想。我期待下一個“現場”,依然能夠追隨著先生。
厚重精深的學問來自學術史的研究
盧茂君(中央財經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副院長)
承蒙王老師信任,這些年來不斷地校閱他的著譯文稿,在這個過程中我也受益多多。記得我第一次幫老師校對的是《日本物哀》那本書。當時,一想到自己手中的打印稿將來要成書出版,像自己以前在書店看到的老師其他著作一樣陳列在店頭,就深感責任重大。一個半月時間,我反復校對書稿三遍。最近一年幫老師校對的書稿是《日本文學研究的學術歷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新中國外國文學研究60年”的結項成果之一),我反復看了七遍,并寫了長達萬字的書評。
校閱書稿之外,就是聽王老師的課。王老師的課既有學術史的深邃與厚重,又有學術前沿的活躍與開闊。我在工作之余,只要能抽出空來,就跑到北師大蹭王老師的課。盡管每學期的課程類型一樣,但是王老師每次的講授都有不同。他把新思考、新思路不斷加進去,還有更多的即興發揮,因而我每次聽講都會有不同的啟發與收獲。聽完他的課,許多疑惑都沒了,甚至連參加學術會議的愿望也大減了。
我負責編輯的 《王向遠教授學術論文選集》第三卷是比較文學學術史研究的論文集,除最后一篇《“百年國難”與“百年國難文學史”》外,都屬于中國比較文學學術史方面的文章。但即便是對中國百年國難文學史的研究,也是運用比較文學的觀念與方法。收錄的20篇論文大多是王老師在寫作《中國比較文學20年》一書時邊寫作邊發表出來的,這也是王老師從博士論文《中日現代文學比較論》開始就形成的一貫做法,也是他著述的一個特點。王老師曾反復說,學術刊物可以起到一個檢驗過濾的作用,著作的重要章節經學術期刊的過濾檢驗,就能保證成書時的質量。這確實應該是著述上的一個不二法門。
我常想,王老師學問厚重精深,大概與他常年注重學術史、學科史的研究密切相關。寫學術史,就要多讀書,也要研讀歷史上各家的學術成果,一個學者也就有了底氣和底蘊,也就能夠從歷史走出來而站在最前沿。這些年,王老師為東方文學、日本文學、比較文學、翻譯文學等學科領域寫出了五六種學術史,可以說他是學術圈中為數很少的寫學術史寫得最多的人之一。
“譯文學”與獨辟蹊徑的“少數派”
尹玥(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碩士生)
投入王老師門下學習和研究東方文學,是一件很巧合的事情,但這個巧合卻成了我最大的幸運。王老師喜歡和學生聊天,將自己的想法娓娓道來,潤物有聲。不過,按老師自己的話說,無論是課上還是課下,說得再多也都是有限,主要還是希望能夠啟發學生,讓思想活躍起來,不被現有的觀念禁錮。如果能對思維有一定程度的“撼動”,那就達到了目的。
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們剛入校,與王老師交流今后的研究課題時,老師說:“年輕人做選題,不能僅僅出于現有的興趣,不能只因為自己現在喜歡什么就去研究什么,‘喜歡’是因為你熟悉;不熟悉甚至不知道的,你不可能‘喜歡’,但是那里卻有很多有價值的課題。越是以前沒有人或很少人觸及的領域,就越是有研究的價值,所以要了解既往的學術史,要了解學術研究的現狀,然后找出問題,定下路子。”換句話說,研究不是個人愛好,不是趕時髦湊熱鬧,而應該甘受寂寞,獨辟蹊徑,有意識地努力做開路者。
這不僅僅是對我們莘莘學子的告誡和教誨,也是老師一直以來貫徹和堅持的做法。他常講,他在學術上屬于 “純粹的少數派”。這個 “少數派”,在我鄙陋地揣測看來,就是他現在所做的事情都是獨辟蹊徑,很少有人做的,因而呼應者寡。例如,十多年前他做的日本侵華文學、日本對中國的文化侵略的研究,便是篳路藍縷之舉;近些年做的對日本古典文論與美學原典的系統的翻譯與研究,在中國似乎也沒有幾個人做;現在正在做的“東方學”,在偌大的中國恐怕沒有多少人做。而“譯文學”這個學科范疇,恐怕即便是翻譯研究界的人,乍聽上去都不一定耳熟。試想,作為“少數派”寫出來的文章,哪能有那么多“引用率”“關注度”呢?哪能以此“出名”呢?但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老師的態度似乎就是如此。
翻譯研究與翻譯理論研究,是王老師近年來投入精力較多的一個領域,并且做了深入的開掘。他最重要的建樹,是將長期被忽略的“譯文”作為研究的重心和主體,從而提出了“譯文學”這一概念并與“譯介學”相對。老師首先從中國傳統譯論文獻中,首次發現了“譯”與“翻”這兩個基礎概念作為“譯文學”體系建構的基礎與出發點。然后,提出了“迻譯/釋譯/創譯”“正譯/誤譯/缺陷翻譯”“異化/歸化/融化”“創造性叛逆/破壞性叛逆”等一系列概念,論述了這些概念之間的關系,建起了不同于以往的“翻譯學”即“譯介學”獨特的框架體系,為翻譯學以及比較文學研究輸送了新的觀念與方法,拓展了研究領域,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研究前景。
我負責編輯的第四卷 《翻譯與翻譯文學研究》,共收錄了21篇相關論文,前半部分是關于翻譯文學宏觀理論體系的構建和一些個案研究,從《“翻”、“譯”的思想——中國古代“翻譯”概念的建構》一文之后,都屬于“譯文學”的內容。老師的“譯文學”體系建構邏輯嚴密,論述精深。我在編輯校讀的過程中收獲很多,感觸也很多。其中,對老師論證的“翻譯度”這一概念感觸尤深。在翻譯實踐與翻譯評論中,都會接觸到關于譯文的“還原度”與“翻譯度”的問題。翻譯家楊絳先生曾用 “翻譯度”來表達譯文對原文的還原程度,從“經驗談”的感性角度較早使用“翻譯度”這個概念。王老師則將“翻譯度”作為譯文生成與評價的延伸概念,無論是 “迻譯/釋譯/創譯”“正譯/誤譯/缺陷翻譯”“創造性叛逆/破壞性叛逆”,還是作為譯文風格判斷的“融化”,都可以用“翻譯度”來進行統籌和評價。翻譯行為原本就是較為主觀的,除了譯詞、譯意的準確性之外無法進行精確判斷,老師用這一系列概念來規制“翻譯度”,將原本虛無縹緲、不易衡量的“感受”評價,變成了一個具有“模糊的精確度”的學科概念,認為無論是譯文生成還是譯文評價,都可以歸結到一個“翻譯度”問題。這是很有理論價值和啟發性的。
“譯文學”以及相關翻譯理論的構建,只是王老師豐碩學術成果的一個方面。但從這一個方面,我們不僅能清楚地看到老師的治學態度和學術方法,也能看出他的學術價值觀。那就是不為成見所囿,不為時潮所湮,不為名利所牽,用他的話說,“做學問就是不能走群眾路線”,要把學術成果“留給后代”,做真正有價值的、不會被時間湮沒的學問。與此同時,幾十年如一日的筆耕不輟,沒有周末、沒有節假日的工作模式,將讀書思考變成一種習慣,將研究寫作視作一種生活方式,也讓我們學子從心底里深深地敬佩。
翻譯家與研究家
姜毅然(北京工業大學外語學院教師,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生)
十年前,王向遠先生《源頭活水》一書的《后記》一開頭就寫了這樣幾句話:“我寫了七八十篇與日本有關的文章,也寫了多部與日本有關的著作。但迄今為止,除少量論文外,我并沒有寫過單純研究日本或日本文學的書。換言之,我所研究的實際上大多是中日文學與文化關系。”王先生強調自己的研究是屬于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或中日文學與文化之關系,而不是“單純的”日本文學研究。我覺得,這一表白對于我們理解其日本文學研究很有參考價值。王先生歷來主張中國人研究日本一定要有自己的立場、視角與方法,而不能一味地模仿、轉述、祖述日本人,特別強調對于日本學者所普遍使用的“作家作品論”的模式,不能再無條件地茍同了。現在十年過去了,王先生較為“單純”地研究日本文學的論文,也已經有20多篇了,本卷從中選取了19篇,獨立編為《王向遠教授學術論文選集》第五卷 《日本文學研究》。
在編輯校對第五卷的過程中,我深深感到,即便是這些“單純”研究和評論日本文學的文章,也反映出了王先生作為中國學者的獨特角度與鮮明立場,在選題范圍與論題上的拓展,以及學術研究方法上的更新與探索,而且篇篇有新意。例如,對日本文學的特征加以概括的文章,無論在中國還是日本,都有人寫過,日本學者吉田精一的相關文章早就有人翻譯成中文了,但是有誰能夠像《日本文學民族特性論》這篇論文一樣,從文學史的實證研究與文藝理論的邏輯思辨的結合中得出如此扎實而新穎的結論呢?關于日本古代文論,日本人固然寫出了一些大作(如久松潛一的《日本文學批評史》),但是有誰能用一萬來字的洗練篇幅,把日本文論千年流變的規律與五大論題清楚地揭示出來呢?對于日本近代文論亦復如此,王先生的《日本近代文論的系譜、構造與特色》一文,理論概括依然是如此的強有力。能夠做到這一點,是因為這些高度概括性的文字是建立在對日本古典文論原典文獻的翻譯基礎之上的。王先生在此前翻譯出版了《日本古代文論選譯》(兩卷四冊)、《日本古代詩學匯譯》(兩卷)等二百多萬字的相關譯文。在翻譯基礎上的研究,保證了研究的扎實可靠。
同樣,王先生對日本作家作品的研究,也建立在對原作翻譯的基礎之上。例如,對于井原西鶴,王先生翻譯出版了該作家的五部代表作,包括《好色一代男》《好色二代男》《好色五人女》《好色一代女》《日本永代藏》《世間胸算用》。只有對西鶴的小說藝術有了切實的體驗,才能寫出像《浮世之草,好色有道——井原西鶴“好色物”的審美構造》那樣的文章,得出“物紛”方法、“饒舌體”、“偽淺化”等新穎的結論。將翻譯與研究結合起來,同樣也表現在王先生對日本現代作家的研究中。1990年代初,王先生翻譯出版了三島由紀夫的長篇小說《假面的告白》,正是因為有此翻譯在先,王先生在《三島由紀夫小說中的變態心理及其根源》一文中表現出了對三島創作心理的精到體察。至于村上春樹,據王先生在《二十世紀中國的日本翻譯文學史》的《后記》中說,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他曾翻譯了村上春樹的中篇小說《1973年的彈球游戲機》和長篇小說《尋羊冒險記》,雖然最終因版權問題未能出版,但也正是因為有了這個基礎,才有了《日本后現代主義文學與村上春樹》這篇文章。1994年發表的這篇文章,被后來的村上研究者公認為是中國大陸最早的兩篇相關論文之一,最早將村上春樹定性為“后現代主義”并概括其創作特色,此后也被廣泛征引。
王先生關于日本文學研究另一方面的文章,是中國題材的日本文學。在這方面,其《中國題材日本文學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一書是學界公認的一部開拓性著作,而現在收錄在《王向遠教授學術論文選集》第五卷中的有關論文,就是作為該書的階段性成果發表的。相關的作家作品大多是王先生在“中國題材的日本文學”這一視域中最早加以觀照并做出系統、透徹的分析和論述的。王先生這些文章中所論及的作家作品,不僅具有文學史上的價值,而且在中日關系史上也具有重要意義。
作為一個外國文學研究者,像王先生這樣,把翻譯作為文本細讀的方式與途徑,將翻譯與研究結合起來,我覺得是很值得效法的。
學者之道與學問之美
寇淑婷(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生,日本菲利斯女學院大學客員研究員)
我所編校的第六卷 《中日現代文學關系研究》(上)中收錄的22篇文章,是王向遠師早期的作品,是1995年至1998年間作為博士學位論文《中日現代文學比較論》的階段性成果陸續發表的。那幾年老師幾乎每年都要發表10多篇論文,所載刊物又都是重要期刊,到最終成書之前,博士論文的全部章節內容都作為單篇論文發表出來了。這要在今天,又有多少人能夠做到呢?而且據《中日現代文學比較論》《后記》記述,那幾年他還兼做中文系副主任。教學、研究與行政管理三管齊下,還有這么大的發表量,足見當時向遠師的勤奮與創造力。現在二十年過去了,這種勤奮與創造力一直保持,甚至“變本加厲”了。我們做學生的隨著對老師的了解逐漸增多,知道老師的幾乎所有時間都在讀書寫作。二十多年前行政工作兼做了一屆,之后再也不干了,只管教書、寫書,這是他至樂所在。在今天這樣追名逐利的浮躁社會,有多少人能夠甘心坐冷板凳,淡泊名利,只為學術而學術,一坐就是三十年呢?而且還會繼續坐下去。他所安坐之處,是他的書齋,這是老師所擁有的自己的天地與宇宙。
編校過程中,我對這些文章反復細讀,不斷感受其中的風格魅力。我一直在琢磨:為什么本來枯燥的學術論文,讀起來非但不枯燥,而且反復品味,每次都有不同的感受呢?我在心里自問,也試圖從中尋求學術創作的底奧。感到老師文章最大的特點,就是能夠深入淺出而又邏輯嚴謹地將深奧的道理講得明白,從不裝腔作勢、強詞奪理,從不故作高深、無病呻吟。他善于發現問題,并以問題的新穎性而使人耳目一新,以問題提出的方式而給人啟發,以解決問題的步驟與方法而使人入彀,以水到渠成的結論而令人信服。用字用詞十分精準,許多地方讓人覺得無可代替,而且不同文章的風格又搖曳多姿,如《從“余裕”論看魯迅與夏目漱石的文藝觀》輕快舒暢,《新感覺派文學及其在中國的變異》雄辯滔滔,《日本的侵華文學與中國的抗日文學》冷峻凝重,《“戰國策派”和“日本浪漫派”》慷慨激昂。無論哪種風格,都以豐富的資料實證、細致的文本分析、科學的比較研究而運思行文。
向遠師也常跟我們說:不僅文學作品應該有審美價值,好的學術論文也應該具有審美的價值,學術文章也可以當美文來寫、當美文來讀。記得有一次我在本科生課堂上旁聽,他說自己在學術著作閱讀中所得到的快感,往往比在虛構性的小說中所得到的快感更多;又說,假如是出于休息消遣,身邊放著兩本書,一本是虛構性作品如小說之類,一本是非虛構的學術著作,兩者選其一,那么自己很可能會不由自主地把學術書拿過來。這話,大多數年輕學生恐怕都難以理解和共鳴。對知識與思想的接受消化,本身就是艱苦的勞作,因而讀學術書會覺得很累,這應該是不少年輕人的感受吧。但是,像我這樣已經做過幾年大學教師的人,現在是能夠充分理解向遠師的話了。的確,讀學術書、讀論文原來是很有快感的。這種快感來自于多方面。滿足了求知欲,覺得滿足;發現了新材料,覺得欣喜;有了新的發現,覺得振奮;獲得了新的思維方法,覺得茅塞頓開;搞懂了邏輯與論法,覺得酣暢淋漓。而且那些準確、洗練、嚴謹而又文氣沛然的語言,也有相當的美感。
或許正是因為這些原因,向遠師的文章特別耐讀。常見許多論文,時過境遷變作故紙,內容上淺陋,基本上用眼睛掃描一下就夠了,因為其選題、材料、觀點都是舊的。而向遠師的這些文章,需要一字一句地讀。讀的過程卻一點也不艱澀枯燥,常常會充滿發現的喜悅與頓悟的豁朗。但即便如此,讀完之后,仍覺得難以完整復述,因為這些文章從選題、材料到觀點與論證都太新穎了。我們以前的知識儲備太少,往往一時難以全部消化,也難以全面理解掌握,于是就需要再讀、三讀。人都說藝術欣賞是有重復性的,例如一首音樂作品需要聆聽多次,體味與理解才能逐漸加深。其實,好的學術論文的閱讀何嘗不是如此。它也需要反復閱讀,每讀一遍都會有新鮮的獲得。也正因為這樣的緣故,老師的這些關于中日現代文學比較研究的文章,雖然問世已二十多年,讀起來卻舊文如新,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與讀者的檢驗。在相關論題上,這些文章是很難被覆蓋掉的,已經成為學術史上堅實的存在。
俳人、寂心與學問
龍鈺涵(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碩士生)
其實王老師是個不折不扣的“俳人”。作為學者,老師對俳句的創作歷史進程與美學理論構造有深入的探討。而閑暇之時,老師亦喜歡創作漢俳,并喜歡與他人交流切磋。猶記得本科時上“東方文學史”課程,講到松尾芭蕉與“寂”之美學時,老師便鼓勵大家嘗試創作漢俳,并發送與他加以“品鑒”。一天早晨,我照例早早地去中學實習,匆忙出門后才發覺忘了戴近視眼鏡,于是拿出手機,寫了一首自嘲的漢俳——“眼鏡忘了戴/眼前一片印象派/五顏又六彩”,然后順手發給了王老師。不久收到王老師的回復——“眼鏡忘了戴/眼前一片印象派/無霾也有霾。”那年北京的霧霾確實很嚴重,老師給我改了最后一句,至今難忘。
而這次,作為“王門”剛“入門”的學生,我有幸負責編輯校對第七卷,即《中日現代文學關系研究》(下),當校到《“漢俳”三十年的成敗與今后的革新——以自作漢俳百首為例》這一篇時,不由得在心底一笑,同時也感慨不已。王老師的這篇文章,首要主旨當然是以自作漢俳為例為漢俳的創作與理論提供參考,而我從中讀出的是老師日常生活中的諧趣與童心,不禁感嘆:三十年來老師筆耕不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學術成果,而在如此繁忙的學術研究之余,還保持著漢俳創作這般閑情逸致。不過,轉念一想,這不就是一種“俳心”或“寂心”么?
我們從老師的論述中知道,“寂”是俳諧美學的核心概念。創作與鑒賞俳句,就要去聽“寂之聲”、觀“寂之色”、品“寂之心”、作“寂之姿”。其中,“寂心”是“寂”之美學構造中最核心、最內在、最深層的內容與范疇,是充分體悟“寂”之美感的審美狀態與精神品位。同時,亦可看作是在寂寞平淡乃至寂寥清貧之中保持獨立、淡泊、自由、灑脫的人生境界,是對某一客體不過分偏執、膠著乃至沉迷的游刃有余的主體狀態。老師多年來從事教學與研究的狀態,相當接近于這種“寂心”的境界。
老師在《論“寂”之美》一文中,對日本俳論關于“寂心”的四組范疇——虛/實、雅/俗、老/少、不易/流行——做了深入闡發,指出其中“不易”與“流行”也就是永恒與變化的矛盾統一、“動”與“靜”的矛盾統一。記得在與老師的閑談中,他也曾提到,做人做事也要講究“不易”與“流行”。從這一點上看,王老師的“不易”首先表現在,三十多年如一日,把學術以外的活動減少到最低限度,不出風頭,不摻和校園政治,不追名逐利,集中精力,堅持按照計劃有板有眼地做學術、寫文章。王老師曾在一篇訪談文章中自述:“學術研究本身就是一種修行,需要培養長年累月甘坐冷板凳的耐力。”(《社會科學家》2007年第6期)正是靠著這種“苦中作樂”的堅持與耐力,老師才有了今日這樣的學術成就。另一方面,老師的“流行”表現在,對某一領域有了足夠、充分的研究之后,或者說有足夠啟發他人進行進一步探討的成果之后,就去挖掘新的問題、探索新的領域,不吃老本,不走輕車熟路。三十年來,老師的研究課題與方向已經從最初、最基礎的東方文學史、日本文學研究、中日比較文學研究,擴展到比較文學、翻譯文學學科理論、翻譯學、美學、東方學等眾多領域,在各個領域都有自己的創新。老師學術生涯中的“不易/流行”,是值得好好玩味的。
勇于揭開日本文學與文化的陰暗面
祝然(大連外國語大學《東北亞外語研究》編輯部,博士、副教授)
2001年,當第一次在大連外國語大學圖書館讀到王向遠先生的《“筆部隊”和侵華戰爭》一書時,我心底掀起的波瀾是前所未有的。這本書使讀者看到了日本文學的另一面,也是黑暗的一面。繼此之后,王先生又陸續發表日本對華文化侵略以及日本右翼歷史觀的研究文章,到2005年,《日本對中國的文化侵略》《日本右翼言論批判》兩部著作同時推出,與之前的《“筆部隊”和侵華戰爭》一并構成對日本侵華史研究的 “三部曲”,被列入國家新聞出版署重點出版項目、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全國百種重點圖書”以及解放軍總政治部全軍讀書書目,堪稱學界獻給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的一份大禮。
閱讀《“筆部隊”和侵華戰爭》時,我還只是一名普通的學生讀者,手捧《日本對中國的文化侵略》與《日本右翼言論批判》時,我已經是一名初涉研究領域的研究生了。在這些著作中,先生不但為我展開了全新的學術視野,他的學術品格與學術精神同樣對我產生了極大影響。日本右翼勢力的囂張氣焰眾所周知,很多學者對其都抱有避之唯恐不及的態度,不愿對其進行研究,更遑論對其進行揭露與批判。然而先生卻反其道而行之,右翼勢力越是囂張,先生越是認為自己有責任對于這種文化挑釁做出反應,即便存在危險,同樣在所不辭。這是一種強烈的責任感,更是一種難能可貴的學者良知。由于先生的這部分論著大都寫于他在日任教期間,《中國青年》的記者亓昕曾打趣說這是“跑到日本右翼的身邊去反右”。對此,先生笑而答曰:“對。感覺身臨其境,也很痛快。”這句簡單的回答,透出些許俠義,更有滿滿的大家器量。同時,由于國內針對“文化侵略”的研究少之又少,先生需要在國內外大量搜集、整理各類資料,這個過程不但耗時、耗力,想必也很孤獨寂寞,然而先生卻憑借自己對于研究的執著追求堅持了下來。這種鐵肩擔道義的學者良知、執著研究的學者態度教會了我如何在研究領域做人,如何樹立起自己的學術品格,使我受益終生。
而今,我借著編輯《王向遠教授學術論文選集》第八卷《日本侵華史與侵華文學研究》的機會,將先生的有關單篇論文收編為一卷,同時完成了對于先生的相關研究成果的再次閱讀。面對案頭這摞厚厚的文稿,感慨良多。
最為感慨的一點,是先生勇于解開日本文學、文化的陰暗面,在這個領域中敢為人先。在十多年前乃至二十年前,當“中日友好”曾是那個時代的一個主旋律的時候,先生卻敢于呈現“非友好”的一面,研究日本的侵華文學和文化侵略,研究和批判日本右翼的歷史觀。最近這些年當中日關系翻轉變冷的時候,先生卻改變了方向,去研究日本的審美文化、美學與古代文論了,這是從歷史文化研究向審美文化研究的轉向,先生自嘲是“逆潮流而動”,但這樣可以更多地擺脫時局的制約而更為超越。據我所知,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時,許多媒體、雜志社、出版社跟先生約這方面的稿子,先生卻告訴他們:那都是十多年的研究了,現在不再寫這些了。他只是應雜志要求把早先的書稿發給他們使用,于是至少有《作家通訊》《海內與海外》等三家雜志在2015年中連載了他的舊文。與此同時,他的侵華史研究三部曲也在2015年出版了精裝第三版。我覺得這一切至少表明了兩點:第一,先生確實喜歡做學術上的“少數派”,而不愿隨大流、走輕車熟路,喜歡不斷開辟新的研究領域;第二,先生十幾年前的研究到今天仍沒有過時,仍在持續地發生著影響。若翻一翻現在已通過答辯的各校相關選題的博士、碩士論文,在綜述先行研究成果的時候,都不能不提到先生的開拓性的貢獻。如今我再讀先生的這些文章,看不出時光流逝對這些文章有什么影響,而只有一種痛快淋漓的新鮮感。
日本審美文化的發現
(郭雪妮 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師、博士,日本創價大學訪問學者)
六月初,忽受恩師王向遠先生吩囑,說臺灣萬卷樓圖書公司要出版《王向遠教授學術論文選集》十卷,問我能否負責編校其中的第九卷。老師已發表的論文數量已經蔚為大觀,能系統編纂出版,是一件大好事。特別是在恩師從教滿三十周年之際,這當然是一個很好的紀念。特別是先生讓我負責第九卷《日本古典美學與文論研究》,我很感念他的良苦用心。先生定是知我近幾年一直在藤原定家及其周邊歌論上艱苦用力卻收獲不多,故特別囑我分校這一卷吧。遺憾的是,我學術根基尚淺,這次所謂的編校,其實只是逐字拜讀學習領悟的過程,這里的編后記,至多是一篇讀后感而已。
《王向遠教授學術論文選集》第九卷《日本古典美學與文論研究》所收17篇文章,絕大多數是先生于2010年至今陸續發表的新作,是以其對多部日本古代經典文論的翻譯為堅實基礎,圍繞日本古代文論的諸多核心概念生發出來的一系列重要研究,實踐他提出的“比較語義學”的構想,將“考”與“論”結合起來,篇篇有新意。這些文章中有一部分是我在北師大讀書期間曾在先生課堂上聽過的,如《日本的“哀·物哀·知物哀”》《入“幽玄”之境》等,又有一些篇目是先生在門里聚會時講過,如《日本身體美學范疇“意氣”語義考論》中涉及的“意氣”概念。大約在2012年9月,先生門下的新老碩博士生齊聚一堂,席間無酒,先生侃侃而談九鬼周造的《“意氣”的構造》,從九鬼周造的身世說到岡倉天心,繼而暢談九鬼“意氣”所指的媚態、意氣地、諦觀三個層面,最后又自然引申到現實中如何處理戀人關系的問題,并諄諄教誨在座的女生們如何談一場高品質的戀愛。我覺得大家當時都有些醉。
關于《論“寂”之美》所涉“寂”之問題,我最深刻的感受莫過于2011年5月底在華山之巔聽先生論“寂”了。恰逢機緣巧合,我和幾位師兄師姐陪同先生登華山南峰。盡管乘了一段索道,但至中途眾人還是被眼前綿延無盡的蒼莽奇峰給震懾了,于是索性坐在絕壁邊一顆老松下,俯眺如帛鋪展的漠漠平原。這時,一枝干枯的松椏掉落在石桌上,驚嚇了一只小松鼠慌忙逃竄。那枝干松彎曲在石桌上,背后是近在咫尺的天與纏綿繚繞的云,那場景真是美極!先生看著這一幕,忽然說,你們看,這就是“寂”啊!接著順口吟詠了一首“五七五”格律的漢俳(可惜當時沒有記下來)。這是先生如詩人的這一面。
當然,《王向遠教授學術論文選集》第九卷中更多的內容是我所未讀過的,如 《日本 “物紛”論》,現在這篇文章和本居宣長的《物哀論》,已經成為我和學生解讀《源氏物語》時的座右之書。另有《日本的“侘”、“侘茶”與“侘寂”的美學》是剛剛發表的新作,深度闡釋了“侘”字所蘊含的“人在宅中”之美學,提出在離群索居中體味和享受自由孤寂的美感,是與茶道之美密切結合的。校對此篇文字時,我已暫時移居至東京近郊的武藏野,獨自就著山中寓所之四壁。怕是此情此景之故,讀這篇論文時毫無澀滯之感,甚至多處讓人生感動虔敬之心,這也是我此番校對的最深刻感受吧。是為后記。
三十年的翻譯與研究——從文學史研究到理論建構,再到超學科的“東方學”
王升遠(復旦大學外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我記得老師是1987年開始在北師大執教的,到今年正好是三十周年。前些日子與老師通電話時,我說:“老師執教滿三十周年了,當教授也都二十年了,該舉辦個活動紀念一下吧?我可以來張羅。”老師說:不用做什么活動,但是李鋒建議出一套書作個紀念。于是我們分工合作,在王老師的指導下,將這套書編了起來。
我負責編輯的《序跋與雜論》是《王向遠教授學術論文選集》最后一卷,內容也較為特殊。所選的是三十幾部著作、譯作的序跋,而且大部分是跋文(后記)。因為老師的序文大部分是作為正規的學術論文來寫的,分別編在了頭九卷,而老師寫“后記”仿佛是干完活兒之后的小憩與閑聊,是隨筆散文的筆法,雖然聊的仍然是干的活兒,但畢竟都如大汗淋漓或長途跋涉之后的歇腳,透露出一種輕松愜意,這類文章都編在了第十卷。
這些序跋雜論文章,是老師三十年的學術歷程的印記,顯示了老師在研究領域上的選擇、開拓與轉換,從中可以看出一個基本軌跡,那就是:從早期的文學史研究到中期的學術史研究,再發展到理論研究與理論建構,再到眼下正在做的跨學科的“東方學”研究。
老師的早期研究是先從文學史入手的。其中,1994年初版的《東方文學史通論》是我國第一部個人撰寫的、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體系的東方文學史著作(這一評價參見陶德臻先生為初版本寫的序言)。第二部《中日現代文學比較論》則進入了中日比較文學領域,而所依托的仍然是中日近現代文學史。第三部《“筆部隊”和侵華戰爭》可以看作特定側面的日本文學史研究。而《二十世紀中國的日本翻譯文學史》(再版改題《日本文學漢譯史》)則是第一部日本文學漢譯史著作,也屬于文學研究的一種門類,但此書是這一門類文學史的開創者,也就是說,它是我國第一部國別的翻譯文學史。接下來的《東方各國文學在中國——譯介與研究史述論》則是把翻譯史的研究由日本擴展到整個東方。最后是王老師率領幾屆研究生用十幾年時間寫成的《中國百年國難文學史》。這些都屬于文學史研究,但不是一般的文學史研究,而是一方面運用了傳統文學史研究的嚴格的資料實證、文本分析的方法,另一方面也有著比較文學、翻譯文學、戰爭文學、國難文學等特定的新穎角度,從而成為填補文學史空白的文學史研究。我認為,這是王老師對文學史研究的一個貢獻。
進入21世紀后,老師的研究重心由 “文學史”研究進入了“學術史”研究。前者是對作家作品的研究,后者是學者的學術著作的研究。很顯然,對學術史的研究與王老師的學科建設的構想密切相關,其目的是為了在學術史的研究中總結汲取學科建構的歷史經驗,為此,他主編了《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建設叢書》《中國比較文學論文索引(1980~2000)》和《中國比較文學年鑒》(合作)等書,在這些文獻學資料學工作的基礎上寫成了《中國比較文學研究二十年》,這是第一本1980至2000年中國比較文學的斷代史。接著,王先生又與樂黛云先生合作寫出《20世紀中國人文學科學術研究史叢書·比較文學研究》,進而最終以一人之力寫出了《中國比較文學百年史》。從文學史到學術史,研究領域有所變換,但不變的是選題上填補空白的學術價值。
在學術史研究的堅實基礎上,王老師的研究順乎其然地進入了文學理論的研究,特別是比較文學、翻譯文學學科理論的研究,寫出《比較文學學科新論》《中國文學翻譯九大論爭》(合著)《翻譯文學導論》《宏觀比較文學講演錄》等著作。這些著作在比較文學、翻譯文學、宏觀比較文學三個方面都提出了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形成了獨特的理論體系。而近幾年連續發表的關于“譯文學”以及比較語義學(特別是中日文論范疇關聯考論)的系列文章,雖然還沒有來得及結集成書,但已經清楚顯示了老師的理論研究與學術思想上的進一步拓展和深化。目前老師正在做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東方學”的研究,則在“東方學”的學科平臺上跨越了學科,將文學與其它學科相貫通,又將學術史研究與學科理論建構相結合。
除了上述學術研究之外,王老師的另一項重要工作是翻譯。既有學術理論著作的翻譯,也有文學作品的翻譯。收入本書的有老師為他的十幾部譯作所寫的《譯者后記》。可以看出,翻譯與研究,這兩個方面在王老師那里是相輔相成的。他常說翻譯是一種“調節”,可以換換工作方式,減輕單純的學術寫作的單調感,但翻譯對王老師而言絕不是純粹的消遣,因為他翻譯的那些文獻和作品大都是古典或經典,難度很大。他常年堅持不懈地翻譯這些東西,每天拿出三分之一的時間做翻譯,竟然已經譯出了三百多萬字。對翻譯的投入和執著,根本上是出于老師對“翻譯”本身的重視,而他的翻譯理論研究也需要翻譯實踐做支撐。并且,正如《翻譯的快感》一文中所言,他在“翻譯”中感受到了語言與文化轉換所具有的創造性,體會到了其中的“快感”,所以他說翻譯會“上癮”。在中國,一般搞翻譯理論研究的人往往翻譯實踐做的不多,而做翻譯實踐的人對翻譯理論則不甚措意。王老師既有翻譯理論的建構,又有大量的翻譯實踐,是很不容易的。另一方面,翻譯做得好的人不少,研究做得好的人也不少,但像王老師這樣翻譯與研究做得又多又好的,恐怕就很少了。
收入本卷的序跋與雜論都有著獨特的見地,固然可以當學術論文來讀,但比一般的學術論文含有更多的感受與體驗,又可以看作學術散文,因為讀起來很有美感。我常想,王老師實際上是很擅長寫這類隨筆散文的,甚至是很能寫詩的(他發表了不少漢俳),因為他很有詩心,很有感受力,充滿知性而又不乏情趣,文字老到而又靈動,文氣充盈而又內斂,格調灑脫而又儒雅。特別是他為前輩學者所寫的懷念文章、為后輩學者所寫的那些序言,更表明他是一個很有人情味的人。當然,作為一個研究人文學科的著作家,作為一個翻譯家,這些都是必須的,也頗值得我們晚輩效法。
2016年8月
【責任編輯 孫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