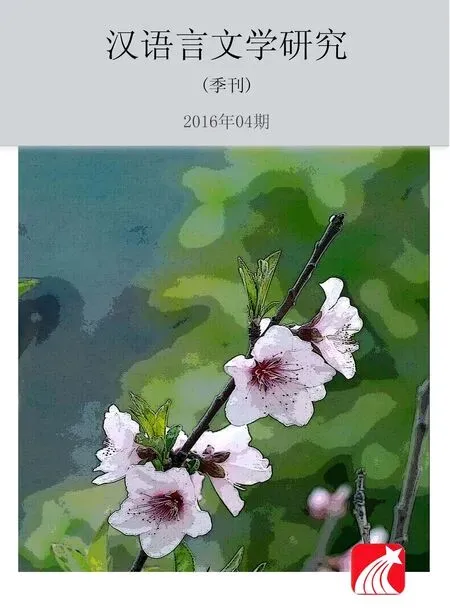現代文學家傳記雜談
吳福輝
現代文學家傳記雜談
吳福輝
談傳記,完全可以從獨立的傳記文學系統或散文寫作的立場去說,也可以從傳記與文學研究的關系上來探討。我偏向于后者。因為我是研究現代文學的,從學術的角度伸入到作家傳記的領域,正是我特別關注之處,也是我的興趣所在之處。
先說作家傳記的現狀。近30年來,大量的傳記紛紛面世,其中要數記述現代作家的為大宗,而作者的大部分便是曾經研究過這些作家的學者(其他作者如相知的文學家,如作家本人或親朋,均屬少數)。這是個頗有意味的現象,不是科學家被“立傳”的多,也不是政治家被“樹碑”的多,反倒是操筆的身影瀟灑的作家受到青睞。學者們原本在書齋(假設他們都有書齋。但是據許多人回憶,書房這種奢侈品要到本世紀初以后才普遍為文人所擁有,所以,改“書齋”為“圖書館”可能更確切些)坐得好好的,突然叫外面的世界“誘惑”了,覺得往日熟悉的作家的文學筆頭,自己不妨也來弄弄。于是給研究過的作家寫個曲折生平故事啦,讓作家的文學個性更加張揚、彰顯啦,便自然成了一種學術的延伸。我個人就是在寫出了沙汀論文后,寫了《沙汀傳》,后來還出了他的簡傳、畫傳;與錢理群合作給江蘇文藝出版社主編過一套“名人自傳叢書”,有幾十個作家入選,我具體編了胡適、梁實秋兩種;另給蘇青、葉圣陶等的傳記寫過序文、書評之類。雖然我個人的傳記工作微不足道,卻順便也能列舉出若干來,更不必說整個現代文學研究界同傳記的廣泛關聯了。這樣,從上世紀50至70年代屈指可數的幾種傳記(如我借抄過的王士菁《魯迅傳》、讀過的林辰《魯迅傳》片斷和《遼寧日報》連載的彭定安《魯迅傳記》——當年留有剪報。郭沫若則有自傳。此外就是空白,兩個巴掌絕對數得過來),到今日突然冒出千百種文學家傳記來,一時竟有眼花繚亂之感。最多的還是魯迅,可能有三十幾種,并有名品,如林志浩的《魯迅傳》、王曉明的《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林賢治的《人間魯迅》及朱正的《魯迅傳》。富有10種到20種傳記的作家是巴金、胡適、茅盾、徐志摩、林語堂、郁達夫、周作人。最熱門的女性作家張愛玲、蕭紅、林徽因、丁玲每人都坐擁多種傳記,張愛玲傳記直逼魯迅數目,蕭紅的十幾種傳記有的很有分量。過去被忽視的京派、海派、通俗作家如沈從文、廢名、汪曾祺、柯靈、戴望舒、徐訃訏、張恨水等,都有了傳,而且不止一本。有爭議的作家傳記更出版得快,像王實味、高長虹、路翎、邵洵美。文學史上歷來偏于一隅的作家,如蘇曼殊、陳衡哲、錢玄同、靳以、耿庸、陳企霞、陸晶清、石評梅,現在都傳上有名。類型也是各式各樣的,巨型大傳如四卷本超百萬字的《葉圣陶全傳》,小型十萬字左右的有簡傳、別傳、外傳、畫傳。夫妻檔的合傳格外受歡迎,偏偏我們的作家夫妻店和才子佳人店開得還真不少,比如,《魯迅與許廣平》《巴金與蕭珊》《蕭紅與蕭軍》《徐志摩與陸小曼》《郁達夫與王映霞》《梁思成與林徽因》《陸侃如和馮沅君》,等等。總之,幾乎重要一點的現代作家都有了傳記,幾乎重要一點的現代文學研究者都卷入了作家傳記大潮。研究帶動了傳記寫作,傳記標志著研究的深入,我們迎來了文學家傳記寫作的繁盛年代。
次問繁盛的原因何在?過去的讀書市場本來就重視傳記,著名的翻譯家傅雷就專譯了五種外國傳記,僅羅曼·羅蘭寫的就有三種:《貝多芬傳》《彌蓋朗琪羅傳》和《托爾斯泰傳》。文學對鉆研“人”之不懈的努力,就貫穿在這對傳記的重視中。不同年齡和不同職業的讀者大都喜歡讀傳記,也是顯然的。進入1950年代以后,政治、文化環境大變,變得對傳記不利了。本來,如郁達夫所說,中國只有“諛墓文”(見《傳記文學》,《郁達夫文集》第6卷),傳統上就少自由臧否人物的環境。政治成了人物評價的主要的或者說是唯一的標準,政治起伏不定,評價也一日多變。以某個人物為原型的文學作品都有了“影射”“反黨”之嫌,何論專寫人物歷史的傳記呢?于是人人自危,不敢寫別人,也不敢叫別人寫自己。左翼的標桿郭沫若、茅盾都無傳,遑論他人!新時期開始的寬松的政治文化環境,給傳記寫作注入了新的生命。而學術上,新時期發軔的文學史重寫思潮,必然帶來重新評價左翼作家、民主作家、市民作家的重大契機。學術新勢頭成了傳記寫作的新推力。研究突入了傳記,傳記帶動了研究。主流文化帶來對左翼文學的反思,便有了《周揚傳》。流行文化可以帶動海派作家傳記的出版,施蟄存的生平就會重起爐灶,有人來敘述。地方文化也有一定的帶動性,它尊鄉賢而發揚光大之,山西收集高長虹的資料聚成他的傳記,哈爾濱一再出版蕭紅的畫傳,山西會把對趙樹理的懷念置入多種《趙樹理傳》當中。很顯然,如果讀書市場正常運行,社會的政治清明,思想束縛得到解禁,文化的環境自由、松動、繁榮,那么,人物傳記的寫作就絕不會寥落寂寞。在某種意義上,作家傳記寫作的風氣是作家研究的試金石,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繁盛里面沒有點問題嗎?有。傳記理論薄弱是顯然的一條。這個文學和學術交叉的寫作文體,在中國還是個新事物。如果“散文加評論”是傳記文體的基本模式,我們雖然有“起承轉合”文章作法的強大傳統,無奈現代散文的理論輸入和學理探討從來就不夠,記敘性和評論性兼有的傳記寫作理論就強不到哪里去。有人稱,傳記文體存在不確定性,為我們的寫作和研究帶來了不確定性,這也有道理。還有一條是傳記的讀書市場的不可測。最明顯的是這幾十年其作品被市場絕對看好,即經典化過程之中文學史地位節節升高的作家如老舍,他的傳記卻出人意外的少。是老舍的評價難以把握,還是老舍的生平資料收集不易,甚至是老舍的傳記需要更有實力的寫家而這個寫家還未產生嗎?這是個謎。市場選擇傳記的傳主,必然有它合理的一面,也有媚俗的一面,需要學術界的參與。假如專家和媒體及早來研究有水平的老舍傳記為何不能如魯迅、胡適、蕭紅、張愛玲那么多地涌現,對市場給出補充性的建議,或許遲早會改變這種不合理的情況。
至于說到寫作傳記的要素,我認為第一是材料。材料是傳記的“實體”。一本傳記主要看它有沒有人物的材料,即人物以往的歷史行跡。材料精彩,傳記就精彩,材料稀松,傳記就稀松。司馬遷《史記》所記歷史人物經久而熠熠發光,因太史公精于調查、搜集、選擇材料,他是中國撰寫人物傳記的不朽祖師。我寫傳記的時候,最早進入“情況”的也是材料。開辟“材料”的來源要從多方面入手。閱讀作家傳主的全部作品,是不可逾越的第一步。一直到第N步,到傳記的文字都寫出來了,有一天你還會感覺對某部作品的形成沒有從傳主的生命旅程里找到根據,作品還沒有讀透。要讀“全部”作品,最好比作家全集的編輯者還要讀得全、讀得用心才好,包括軼文、非主流作品、未刊稿等等。因為這些作品很可能泄露出傳主特別的心思及心理過程。理解郭小川主要不看他到東北鋼都、煤都寫的《兩都賦》,而要讀他如何寫“團泊洼”,如何“望星空”。傳主的全部作品,最是“信史”。不要將花哨的材料讀了一大堆,反而漠視作為“信史”的最能傳達出作家真實信息的作品。此外,還要讀與傳主有關的“回憶錄”,歷史回憶和人物回憶,傳主自己的和別人的回憶,帶細節帶感情的回憶,以幫助你進入或接近進入歷史現場。檔案里,公家的材料和私人的材料都不能輕視,鑒定、表格、書信、日記、筆記、交待揭發類手稿都十分重要。口述材料不可忽視。本人口述、親歷者口述、親密者口述都可能帶有個人偏見,但經過辨析就是最真實的帶著體溫的記憶。“口述自傳”自有特殊價值,不然就不會有研究者專門給胡適、張學良錄音了。人物對立面的材料,反面的材料,是尤其可貴的,如果你到開始動筆的時候竟然發現所有的材料都是“一邊倒”的,不妨專門下功夫去聽點不同的聲音,讓你不至于被材料傾向所淹沒,而“驀然回首”,你或許會找到那個俯視材料的制高點。
當“材料”進入傳記,對它的處置方式不外兩種:客觀地如實寫下,是謂“紀實”;主觀地加以文學化,則是“虛構”。紀實與虛構,關系到傳記的根本。或許你認為紀實用的是材料,虛構靠的是想象,那是個誤解,因為傳記的想象是在材料基礎上生發的,無從憑空產生。白薇這個女作家和楊騷的同居及其分分合合的一波三折,是《白薇傳》的基本材料違背不得,你只能在紀實的基礎上才能想象他們是如何相處的。在傳記里,人物生平的大關節、時代命運的主要走向、主人公的基本性格,都是不能虛構的;能虛構的只是次要情節、場面,個別的對話和內心活動。便是這些具體的虛構也要以紀實為依據,并不能隨意向壁而造。這就是說“想象力”在傳記寫作中應受到限制,只能適當使用。“紀實”和“虛構”似乎使用了兩種材料,但都歸向材料的真實性。紀實并非一定真實,虛構絕非虛假。凡歷史記述性的作品,虛構、紀實都會發生嚴重的復雜糾葛:以影射為主要目的的歷史小說和歷史劇,往往做出拋棄“紀實”的姿態;報告文學,或與新聞結合的各類歷史作品,甚至概括大歷史的史詩,就要牢牢守住“紀實”這個基業。而傳記無論有多少虛構,“紀實為主”是不能丟的。有一種考證型的傳記,全書處在駁難的過程中,言必有據,言必不己出,并著力研究人物、故事的原型,即便是“評傳體”,仍然是以紀實為主的。只是這種傳記把學術性和文學性高度結合了,比如高長虹的傳記,考證高氏與魯迅的關系,重述狂飆社的文學歷程,足以沖擊已成的文學史,補正了文學史,但它還是立足于基本的人物史實,以“紀實”為主的。有的傳記材料多,有的少,材料多的傳記要注重選擇,材料少的傳記就容易鋪張。但鋪張不能過度,比如坊間流行的張愛玲和林徽因的傳,因生平材料太少而竭力鋪張作品的故事與加入許多作品分析段落,顯得“虛胖”“浮腫”。還是要從深處挖掘兩位女性作家的材料出發,來寫好她們的文學活動史和生命史。
傳記的另一個要素,據我的體會是對話。正是作者和傳主的對話關系,決定了某一種傳記的記述個性。因為傳主已經被歷史定格,作者卻是站在當代立場上來記述他的,作者當下的主體性和傳主歷史客觀品格之間的張力,會影響到傳記整體和各個局部。傳記的歷史價值有沒有被歪曲,傳主的思想行動有沒有被作者給予同情的理解并恰當地傳述,文字風格有沒有融化了過往與今昔,傳記結構是不是一種特別的“對談”,它們最終影響到一本傳記的成敗優劣。而作者的關鍵,是有沒有在傳記中創造性地闡釋作家。看作者能否重新解讀作家作品,揭示其遭受歷史或以往評價的重重遮蔽。傳主的地位還可能過度地影響作者的傳記。大作家的傳記價值,一部分被他的社會地位所制約,以至于平庸的傳記也能得到膨脹。這是社會價值對傳記的投影。另一種情況是作者在寫作傳記過程中始終不能與傳主同步同調。給魯迅寫傳你達不到傳主思想的高度。給錢鍾書寫傳你覺得在他的博聞強記的知識系統中你很迷惘。你已經盡量在走傳主走過的“路”,在一個虛擬的世界里覺察到兩人已經同行過了,但中間還是有“隔”。整個寫傳的過程,你在試圖打破這個障壁,可能打破一部分,也可能一隔到底。所以寫傳的作者始終要尋找那個平等的“對話”關系。這當然不是指你在思想學問上要和傳主平起平坐,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但“平等”可以。貼近傳主、理解傳主,還要持獨立不倚的寫作立場。要少受或不受傳主及其親友的偏見的影響,找到“對話”的平等口氣和語言,而不至匍匐于傳主之下,在今日應是無須饒舌的了。
傳記的文體要素,是“敘評”二字。傳記有敘有評,要處理好敘事和評論的關系。傳記究竟是以“敘”為主的,“評”是內在,有時是含蓄隱蔽的,有時是經過特殊的設計體現的。傳記既然多半是“敘述”出面,敘事學的一套方法還是可用:敘述人的位置、角度要講究,敘述的視野,時空的插入和調動,都還可用。只是因虛構性小,要與小說做一區別罷了。要依據傳記讀者對專注點的不同和對語言風貌的要求的不同,來調整文體。有的傳記是給大眾看的,大眾性的傳記要求人物命運的悲歡離合,突出傳奇性;有的是給知識分子讀的,文字就文雅一些,書卷氣重些,要求對傳主能提出獨特的看法。文人型的傳記在對大眾傳記起一定的引領作用。大眾型的傳記有進行全社會文學教育之功。提倡文人為大眾寫傳,另有一番意義。現在還缺少一種為兒童寫作的作家傳記。家長們在選擇適宜孩子閱讀的勵志人物傳記時,經常會覺得科學家傳記過于深奧,政治家傳記用盡計謀,作家傳記充滿男女情長,都不是理想的兒童讀物。其實傳記是最適于少年的。我自己小時候最初知道的人物除了白雪公主小矮人,便是發明家愛迪生。我想只要是不板著面孔訓人,多寫些讓孩子們閱讀的作家傳記,該是個好主意。當然,對給兒童看的傳記應該如何寫,成熟的寫作經驗應如何研究,那又是學術界的事情。
了解作家的曲折生平,詮釋經典作品的產生和流傳的真意,推動作家研究的學術進程,追溯偉大作家生成的原因及生命呈現,依我看,作家傳記的文學、教育、學術等多方面潛在的功能和意義,還是可以高估一點的。
【責任編輯 鄭慧霞】
2016年10月14日避京城陰霾兩日于小石居
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主編,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現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