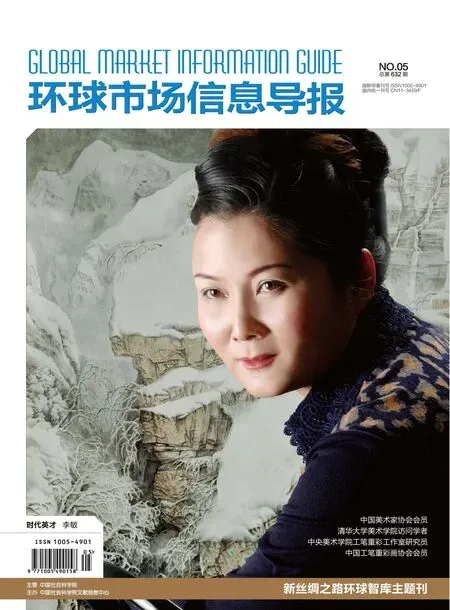中西法律、哲學思想的比較研究
——以《荷馬史詩》與《詩經》為例
◎劉倩
?
中西法律、哲學思想的比較研究
——以《荷馬史詩》與《詩經》為例
◎劉倩
《荷馬史詩》與《詩經》是東西方的兩大詩歌巨著,其內容具有重要的史實價值,反映了時代思想。通過對兩者的比較,可以較為全面地獲知東西方奴隸社會的民風、政治與道德等方面的差異與相似之處。從作品所持的價值觀念與故事描寫,亦可了解到奴隸社會時期東西方的法律、哲學思想。
作品內容與背景簡介
《詩經》分為風、雅、頌三個部分,分別為民間歌謠、宮廷正樂與宗廟祭祀舞樂,整體以抒情為主。而《荷馬史詩》以敘事為主。《伊利亞特》與《奧德賽》集中講述了兩個人神匯雜、事實與想象并存的故事,反映了彼時人們對人神關系的思考與對戰爭的謳歌,最終顯示出人的理性的萌芽。
兩部作品,或者說兩個社會的差異主要源于不同的自然與政治差異。孕育《詩經》的漢民族生活在廣闊的大河流域,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給人口的擴張與和平相處提供包容的可能,無需通過對外擴張與侵略獲取資源,也因此打下了大一統的基礎。而古希臘文明發源于海島之上,有限的生存區域使各族人民產生巨大的生存壓力,通過武力獲得資源成為最快捷有效的方式。這樣的差異反映在作品中就是對戰爭的態度截然相反。地理差異也帶來社會制度的不同,漢民族建立起統一的國家,對人民施以道德教化,重人倫與秩序。古希臘則發展出樸素的民主制度,相對寬容的思想環境激發人們的思考與人性的覺醒。故兩個社會對人神關系與道德法律的取向也有所差異。
相同點比較
雖然《荷馬史詩》與《詩經》在很多方面存在不同,但都作為奴隸社會的作品,制度構建與人的發展的相似性依然帶來一些共通之處。
人在社會中的地位的思考。《荷馬史詩》中,人與神呈現出一種混雜的局面。神并不是智慧的象征,而與人一樣有七情六欲,有憤怒與嫉妒,也會犯錯。而人在某種程度上又被賦予了神性,擁有人性的關懷,也有神的力量與刀槍不入的能力(除腳后跟外)。最終,依然是人更具有理性,這是人的覺醒,也是理性的萌芽。人與神的關系和地位逐漸發生轉變,回歸本位。《詩經》之中的表現雖有不同,但也可窺見一二。其收錄國風的詩篇最多,共160篇,大量描寫勞動人民的生活與愛情,自由地表達情感。“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經典之作《關雎》即直白表達男女之間的愛慕之情。《詩經》之中的人勇敢追求自己的幸福,表達自我喜惡,是人文精神自我覺醒的表現之一。
等級森嚴的社會。這是奴隸社會不可避免的特征之一。《詩經》中有表達自由情感的普通人、欺壓勞動人民的剝削者、感謝祖輩恩德的統治者,社會的固有秩序一覽無余。《荷馬史詩》也是如此,人類社會其實是神界社會秩序的映射。人類生來就具有屬于自己的社會地位,神的領域中,也存在宙斯這樣一個最高的神。略有不同的是,《荷馬史詩》中的社會結構更為清晰,可以看出人民大會等基本機構,而《詩經》中的描述更為籠統。
不同點比較
人神關系不同。在《荷馬史詩》中,理性的覺醒正是通過人神關系的發展變化體現出來的。人與神有服從、互愛、反抗等關系,在《伊利亞特》中,狄俄墨得斯在混戰中先后刺傷愛神阿芙洛狄忒和戰神阿瑞斯,人與神的能力呈現出一定的平等,并存在矛盾。而在《奧德賽》中,俄底修斯最終能夠回家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眾神的憐憫。《荷馬史詩》中的神就像是更高層次的人,參與到人世生活中,但情感和欲望卻沒有被摒除。人與神的生活相互混雜,共同構成《荷馬史詩》的世界。
《詩經》之中體現的則是傳統的臣服于神的思想。《詩經》中《周頌》的全部和《大雅》的一部分都是祭祀詩,其對象包括神靈與先祖。可見周人對于神靈的崇敬之情,將山川、社稷、大地之神奉為高高在上之人。統治者權力的獲得也籠上一層神意的面紗,體現了濃厚的神權法思想。敬神的特征也使《詩經》中的人文意識的覺醒在于與統治者的矛盾中,而非《荷馬史詩》中通過人神關系體現。
表達的現實思想不同。《詩經》的重要價值之一就在于如實反映人民的思想感情,包括對上層的腐朽與壓迫的譴責。“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狟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這是伐木者諷刺剝削者不勞而獲。“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統治者享受他們的勞動成果,享受優裕的生活,而勞動人民卻缺衣少食,形成鮮明的對比。《詩經》雖以抒情著稱,卻是基于現實的無力發出的最原始的反抗的聲音。
《荷馬史詩》則側重于對戰爭場景的描寫呈現出貴族性,多是稱頌其中的英雄。《荷馬史詩》歌頌勇敢,歌煩英雄,歌頌攻城奪壘,歌煩海上冒險;并且有明顯的貴族傾向,《伊里亞特》著力歌頌的四十多個人物,全為氏族貴族,而對平民士兵,全書僅提到一個忒耳西忒斯,還賦予他饒舌、兇狠、丑陋卑劣的性格;《奧德賽》中,奴隸形同牲口,可以肆意占有、處死。《荷馬史詩》對英雄主義的贊揚與《詩經》反映的底層人民的思想感情差異巨大。
對戰爭的態度不同。《詩經》中反對戰爭,倡導百姓相安和諧。在諷刺詩中,百姓雖有不滿,卻也只是表達自己的情感而無反抗起義之感。在集權制度下,人們習慣于接受與忍耐,如“悠悠蒼天,曷其有極?”即使存在大量的反戰爭詩,也多表達歸鄉心切,厭惡戰爭曠日持久及同伴之情。“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正是戍卒思歸不得的哀嘆。人與物、人與人之間,總是尋求一種協調交融、相安和諧。即使是怨詩哀歌,也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目的仍然是追求一種天人相安、人際和睦的境界。這實際上是重德重禮教的結果,《鴇羽》表達的最終還是不能贍養父母的憂傷。《荷馬史詩》則不然。《奧德賽》中,俄底修斯漂流十年,始終與大海對立,與風暴、雷霆、巨浪博斗,不是你毀滅我,就是我戰勝你;《伊里亞特》更是歌煩戰爭掠奪,崇尚武力亞服,以殘酷廝殺為榮,以擴張占領為上。《荷馬史詩》正是通過人與自然之間的對立與搏斗,以顯示人在自然面前的不屈與堅強,從而歌頌英雄的頑強意志。
(作者單位:華中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