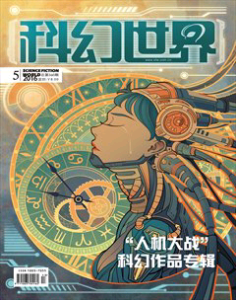答案
鈴聲響起。
該去上課了,我慢悠悠地站起來,從辦公桌上拿起課本、講義和塑料大三角尺。下意識地,我把手伸向桌角的幾何計算器。
什么時候我也開始依賴這東西了?我的心里咯噔一下。
幾何計算器本質上是一臺小型量子計算機。由于它極高的運算速度,只要正確地將圖形的各項數據輸入,它就可以繪制出一幅完整精準的圖形,從而直接得出各種結論,比如說角的相等,或者線的垂直。
大概五年前,幾何計算器普及了,于是我的任務就從教學生證明角相等,變成了教他們在幾何計算器中精準地繪制出這個角,其余都是計算器的工作。
我最終沒有拿上那只計算器。我匆忙地走進教室,“不好意思,我來晚了一點兒。今天的內容是——中位線定理……”學生們紛紛拿起了幾何計算器。
“同其他證明一樣,應用中位線定理的題目在考試中可以采取兩種證明方式:一種是寫出錄入幾何計算器的步驟;另一種就是常規證明……”我很討厭這句話,但是我不得不說。這句話我說過無數次,學生們也懶得聽了——沒有人會用常規證明。這里的每個學生都買得起幾何計算器。
但是我不希望他們用。我也不知道為什么。
我很快結束了講解,“現在請大家做課本第二十五頁的第三題,注意要寫出完整的證明過程。”我踱下講臺,開始四處巡視。
不出所料,每個人都選擇用幾何計算器。我順著一列課桌走下去,每一個閃著熒光的屏幕上都整整齊齊地寫著:判斷結果:垂直。我的心中隱隱有些失落。數學課堂對我展現出的魅力正在慢慢消減。
教室里靜默無聲。我忽然看到一張寫滿常規證明的練習本,本子的主人是個女生,叫曉蘭,她正低著頭奮筆疾書,以完成證明的最后幾行。
我極快地掃視了一眼她的證明過程,立刻發現了三處嚴重的錯誤。我用手指著練習本,說:“曉蘭,這里,為什么由三角形中位線可以得到垂直的結論?”我用溫和的語氣問她。
曉蘭抬起頭疑惑地看著我,“難道不是嗎?三線合一……”
我有點生氣,這張冠李戴得有些離譜。“三線合一是指等腰三角形的底邊中線、底邊高和頂角平分線在同一直線上,這與中位線無關……”
她竟不耐煩地打斷了我:“老師,不好意思,要是用幾何計算器就不會出現這個問題了。”
我更加生氣,但我努力使自己的語氣保持平和,“你根本沒有理解中位線定理,以及它是怎么推導出來的。”
曉蘭顯然沒有明白我的意思,她繼續說:“我今天只是忘記帶幾何計算器罷了,所以我才用常規證明。老師,我下次一定記得帶……老師?”
我徑直走回講臺,不知道該說什么。
“大家看一下,如果用常規證明法,中位線定理有這幾個規則,首先……”
有些學生已經拿出了作業。
我松弛地坐在辦公室舒適的轉椅上,一動不動。
辦公室里只有寥寥幾位老師,墻上的時鐘滴滴答答地走著。下一節我沒有課。
我仍不住地回想這節糟糕的數學課。幾何計算器讓學生對邏輯推導過程一無所知。但是幾何計算器逐步替代常規證明,這是中學數學教學大綱的要求,我又能怎么樣呢?
我悶悶不樂地發著呆。
辦公桌旁邊的柜子上擺滿了獎杯,都是我的。獎杯旁邊還有一個精美的盒子,里面裝著一只嶄新的幾何計算器,是我畢業那年參加全國數學競賽的獎品。
頒獎現場熱鬧非凡,我焦急地等待著主持人宣讀獲獎名單。終于,當廣播里傳出我的名字時,我迫不及待地沖上領獎臺。國家數學院的院長——一位臉白須的老人——接過獎牌掛在我的脖子上,然后遞給我一個精美的盒子。
他隨后發表了一段頒獎詞:“今年競賽冠軍的獎品是一只量子幾何計算器。眾所周知,量子計算機技術已經成為現實,并逐漸轉入應用領域……下個月國家數學院即將落成的新大樓的三維模型,就是由量子計算機精確繪制的……我希望你們這些明天的數學家,能夠在量子計算方面取得更高的成就,為國家的建設貢獻力量!”
如潮的掌聲中,我在臺下已經迫不及待地拆開了包裝。彼時,量子計算機還未普及,這樣一只最新款的量子幾何計算器價格不菲,也很難買到。
距離頒獎現場不遠處的國家數學院新址上,一派熱火朝天……
這只量子幾何計算器現在已經十分落后了。事實上,除了頒獎那天試用過一次之后,我就再也沒有打開過那個盒子。從我第一次按下上面的ENTER鍵,得到一個“判斷結果”之后,我的心中就升起了一種莫名的失落感。
國家數學院的大樓早已建好,通過我辦公室的落地窗就可以看到。我曾無數次凝望那座大樓——全國第一座用量子計算機設計的大樓。那里的每一個圓形都完美無缺,每一個矩形都棱角分明。
雖然大樓的設計中還保留了許多具有建筑藝術感的流線、不規則圖形,但是那都掩蓋不住它骨子里的方正規則。我這雙對幾何圖形無比敏銳的眼睛,毫不費力就可以看出那些圓、矩形、等腰梯形,盡管它們在表面上被扭曲了。
我經常想象著一個畫面:我雙臂張開,身體緊貼著那標準圓柱體的主樓,徒勞地摸索著,想找到一點點的缺陷。它那么圓,即使在放大鏡下也完美無缺。
在國家數學院大樓的周圍,乃至整座城市,越來越多的新樓以這種方式建了起來。它們越來越規則。那層藝術設計的紗布越來越薄,里面幾何圖形的骨架越來越明顯。
如建筑院和數學院的發言人所說,新的城市規劃以節省空間為主旨,呈規則幾何形狀的建筑比以前節省了超過百分之五十的空間。
在沒有課的時候,我習慣捧一杯滾燙的咖啡,站在落地窗前,凝望著那頭水泥怪獸。
國家數學院新大樓落成的那天,在嶄新的樓頂上舉行了一場小型的慶祝儀式。我和小劉作為數學工作者代表一起去了。小劉是我大學數學系的同學,后來和我一起做了教師,現在是我們學校教務處的劉主任了。
夜色下,城市華燈璀璨,新大樓在燈火的簇擁之中矗立。樓頂臨時搭起的場地被四周的強光籠罩,各行各業的代表在演講臺周圍推杯換盞。我和小劉手中各拿著一杯香檳,靠在欄桿邊。深秋的晚風夾著涼意輕拂著我的臉。
我們無可避免地談到了量子計算器。
“你知道學生們給你取的外號是什么嗎?”小劉忽然問我。
我當然知道,他們叫我“計算器殺手”。
在幾何計算器進入教學大綱之前,我的課堂上從不允許出現幾何計算器,見一個收一個。后來允許學生用了,我還是極少用,無論是課堂上還是私底下。學生們總能在我的桌面上看到一疊寫滿推導過程的草稿紙,于是這個外號一直被沿用至今。
事實上我很難說自己反感它。
小劉繼續說:“或許事情真的不像你想得那么壞。為什么那么抵觸它?你看,量子計算用于建筑,這不是挺好嗎?”
我無法反駁。
“數學要發展,某些基礎的東西就要交給計算機去做。人的精力有限,必須用在刀刃上。”
“劉哥,你還記不記得我們在數學系的日子?每天在路上、在食堂里爭論數學問題;把寫滿演算的草稿紙摞成一疊;晚上在被窩里談論哥德巴赫猜想……我喜歡那種生活。”
小劉沉默了一會兒,說:“可是我們依然沒有在數學上取得什么突破,哥德巴赫猜想依然無法被證明。而現在,量子計算機卻很有可能完成這一切!”
我不再作聲。杯子里的香檳緩緩晃動著,晶瑩剔透,其中似乎還有幾個氣泡。香檳中的氣體在壓力和張力的作用下呈現出一個個完美的球體,它們生來就那么精確、那么標準,無須計算。
我推開教務處的門。
劉主任看到我,立刻招手讓我過去。他把厚厚的一疊紙放在桌上。我掃了一眼,看出是我上個星期提交的課題研究材料。
劉主任直截了當地說:“我建議你換一個題目。”
最上面的那張紙寫著:
常規推導證明過程的優化和完善
底下那些印滿字的紙是我一個月來的心血。
“這個題目多半拿不到資金。你很清楚,現在教學的中心由常規證明漸漸轉變為幾何計算器的使用。你現在提交這個課題,說得不好聽,真是沒有什么意義。”
稍頓,他又用老朋友的口吻說:“不要死撐了,你不能改變什么。”
我不置可否。
劉主任拿出一張紙,遞給我,“我想了一下,你不如寫這個:幾何計算器的創新教學……”他小心翼翼地看了我一眼。
“我會……再想一想。”我知道他肯定為此花了不少時間。
走出教務處,三三兩兩的學生從身邊經過。
我慢慢地走在走廊上,一邊把手里的紙揉成一團。經過樓梯間的垃圾桶時,紙團劃出一條標準的二次函數曲線,掉進桶里。我篤定地想,那條曲線一定比幾何計算器畫出來的更完美。
我決定回一趟我的大學,到數學系聽一聽后輩們爭論數學問題。或許我能找到答案之外的什么東西。
【責任編輯:王維劍】
小雪說文
這是一篇……關于數學的科幻,嗯。
印象比較深的寫數學的科幻是何夕的《傷心者》(收入小說集《人生不相見》,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2011),還有特德·姜的《除以零》(收入小說集《你一生的故事》,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
《傷心者》并沒有描寫數學的具體內容,但強調了數學在其他學科中的應用。故事的結尾提到,歷史上有很多數學家的研究在當時不受重視,但后來都成了自然科學探索的重要工具。那些在自己的時代受到嘲笑與質疑、甚至因為研究而生活困苦的數學家,都是“傷心者”。這就把數學與人的自我實現、社會分工與社會公平等問題聯系了起來。可以說,這篇小說偏重數學的社會作用。
《除以零》則以特殊的三線結構,將數學知識同數學家的研究內容、數學家的情感關系等編織在了一起。它對數學體系的合理性進行了思辨,也強調了數學研究成果對數學家本人的直接影響。能看出在研究過程中,數學家的思維、情感等都會發生相應的變化。可以說,這篇小說更偏重數學家的內心體驗。要是“何夕”曾經讀過這篇小說,可能就會避免沉默二十年的悲劇了。
而蔡旭恒同學的《答案》,則把技術進步同人在研究和學習中的獨特體驗對立了起來,隱隱透出人類活動被技術成果取代后的恐懼。這種恐懼可能存在于自動化機械取代工人、計算器取代草紙、機器人取代醫生做手術、自動駕駛程序取代司機……的過程中。當具有學習能力的阿爾法狗贏了四盤圍棋之后,我們也開始質疑人類本身是否會被取代了。所以大家還等什么呢,快站起來像“我”一樣用自己的方式尋找答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