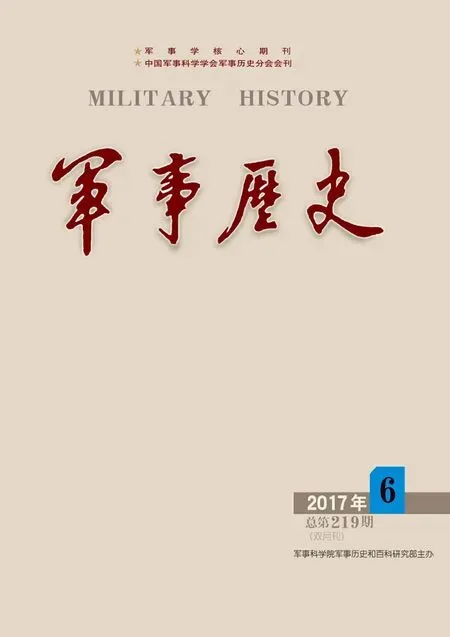明清易代之際的張應種及其家族
★
一、東征游擊張應種的兩種形象
張應種,字崇元,號肖泉,占籍廣寧,與父張九思在承襲軍職前,均先習儒業,為衛學諸生,襲職后改軍職。朝鮮申欽記載張應種“以欽差統領南北調兵涿州參將,領馬兵一千五百出來”。其他包括柳成龍、李德馨在內的朝鮮人文集中提到張應種的材料均記載他為參將。但對照東征經略宋應昌萬歷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奏疏所載入朝明軍序列,“原任副總兵李寧、游擊張應種領遼東正兵親兵”*宋應昌:《經略復國要編》,卷四,《報進兵日期疏》,臺灣華文書局1990年據萬歷刊本影印本,308頁。共1189名入朝,隸屬李如柏統率的左軍,張應種的職銜卻為游擊。這種差異是如何產生的?
東征之前張應種實為參將,駐扎薊鎮與蒙古各部作戰。萬歷十五年(1587)九月,張應種為“山海管參將事游擊”*顧養謙:《沖庵顧先生撫遼奏議》,卷十三,明萬歷刻本。,報告蒙古來犯消息,涉及“東虜”“西虜”“土蠻”等部落將要搶掠廣寧東西、錦州、義州等地。他的同事如薊鎮臺頭、喜峰、馬蘭等路總副參游張臣、解一清等與永平兵備道稟報相同。查《明實錄》記萬歷十六年(1588)六月癸亥條:“薊鎮督撫張國彥等奏:屬夷干多羅忽令部夷扯落等沖放筏板,潛入潘家口,殺死運軍二人,奪去馱磚馬三匹,隨被官兵擒獲賊夷卜兒大等五人,失事官熊世錦等分別罰治。上依擬。”*《明神宗實錄》,卷一九九,萬歷十六年六月癸亥,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7年校勘本,3738頁。張應種此時職為山海關參將,當在“分別罰治”之列。至次年三月初五,事情有所轉圜,薊鎮夷酋小阿卜戶、猛可真等將部落毛什哈所擄明戍卒送還,叩關服罪,以求額賞。督撫張國彥等請釋放古北口留質諸夷,“而誅其就縛者,予賞如故,從之”*《明神宗實錄》,卷二○九,萬歷十七年三月壬子,3909~3910頁。。這是壬辰戰爭前薊鎮發生的與蒙古部落沖突事件,張應種既為參將,亦當被“罰治”,故其入朝后,朝鮮人稱之參將而非游擊,蓋為尊之。
東征第一階段入朝明軍的兵源主要來自薊鎮、保定、宣府、大同等衛所鎮兵,萬歷二十一年(1593)十二月初中旬陸續至遼陽。先鋒則是初三日出發的南兵將吳惟忠所領的5000步兵,任務是大張聲勢、安慰國王、護衛糧草。初八日,提督李如松到后,才會同遼東撫臣趙耀、按臣李時孳及提督李如松、贊畫員外劉黃裳、主事袁黃、管糧主事艾維新、遼東總兵官楊紹勛,分守遼海道參議荊州俊并標下中軍以及各偏禆將領等官,彼此咨詢籌劃后合議,將明兵分為三部分:中陣、左、右二翼各萬余人。*宋應昌:《經略復國要編》,卷四,《報進兵日期疏》,306~309頁。
平壤戰役是明軍入朝后的首個大勝仗。經略宋應昌事后匯報:陣斬獲倭級1285顆,獲馬2985匹,倭器452件,取得重大勝利。張應種在左軍,當隨李如柏從大西門攻進平壤,并伏擊了從平壤城撤出的日軍:“李提督復料賊計已窮,夜必逃遁,遵照經略密諭設伏江東之計,陰遣副參等官李寧、張應種、查大受、祖承訓、孫守廉、葛逢夏等領精兵三千,趨江東小路埋伏,倭果扶傷從小路宵遁。”*宋應昌:《經略復國要編》,卷七,《敘恢復平壤開城戰功疏》,562頁。故宋應昌在敘功疏中,將排在第二的張應種與其他分統將領等官王有翼等28人共列,評語是:“諸將共懷報國,克破堅城,率死士而爭先用命,奉將令而陷陣摧鋒,均應并敘。在見任者相應升級,原任者相應復職。”*宋應昌:《經略復國要編》,卷七,《敘恢復平壤開城戰功疏》,575頁。受表彰的將領有南有北,如孫守廉、祖承訓、查大受、佟養中等與張應種均為北將,葉邦榮、胡鸞、王必迪、周易、李都、婁大有等為南將,克破堅城與陷陣摧鋒相提并論,大致可看出宋應昌平衡南北將領的企圖。至于各將領在戰役中所擔任的具體角色并不易分辨。但“設伏江東”的張應種與破城克堅卻得不到首功而忿忿不平的南兵將的區別還是清楚的。張應種后來屢被朝鮮人稱為參將,或許也得益于宋應昌“復職”的建議。
萬歷二十二年(1594)正月二十一日,朝鮮漢城府判尹李德馨到達開城府,看到日軍撤退后一片殘破景象:喬木盡伐,公廨燒毀, 閭家余存者十之八九。他急忙“督造浮橋,初昏馳到東坡”, 見到“李寧、張應種等領精騎六七千, 由淺灘過涉, 結陣坡州, 將薄京城。”*《宣祖實錄》,卷三十四,宣祖二十六年正月癸未條,二十八日。平壤戰役后,張應種所領的六七千遼東精兵到達坡州,作為東征大軍南下前鋒,等待浮橋造畢前進,為提督李如松、經略宋應昌開路。但在二十七日,遭遇碧蹄館敗績時,張應種既沒有象楊元那樣殺入重圍救護李如松、李如梅兄弟,也沒有象李氏家丁李有升那樣舍命救主而被表彰,當如望風先逃而被點名批評的祖承訓一樣,屬于“各軍退走以致僨事”*宋應昌:《經略復國要編》,卷六,《檄李提督》,486頁。之一員,故平安無事。而他所領兵員從1500人減少至1100人,蓋為碧蹄館之役所損傷。八月,宋應昌上《議朝鮮防守要害并善后事宜疏》,酌議“應留官兵一萬六千名”*宋應昌:《經略復國要編》,卷十,《議朝鮮防守要害并善后事宜疏》,837頁。,張應種部1100人亦在其中。但到十二月初八日,已改為“除劉綎一枝暫留外”,“其宋應昌、李如松俟有倭歸確報,著便回朝。”朝廷批準兵部咨文,東征議貢議封均屬失策,議將吳惟忠、駱尚志、谷燧、宋大斌、張應種等留守南北官兵盡數撤回。*《經略復國要編》,卷十三,《慎留撤酌經權疏》,1025頁。明朝將東征軍全軍撤回的主要原因是糧餉不繼,影響到軍事計劃的落實和執行,連一度議留的劉綎部5000人駐守朝鮮計劃也被取消。在東征中,張應種無突出表現,惟率遼東步兵隨大軍執行任務,雖歷經激戰危險,但應屬表現不佳的“各軍”之一。
張應種部在部分明軍入漢城之前撤回。《再造藩邦志》記載:“副總兵王有翼、參將張應種、趙之牧、張奇功,依經略檄文回去。朝廷乃遣漢城判尹柳根馳入京城,慰撫遺民。”張應種回國的時間是萬歷二十一年在部分明軍進入漢城之前的四月,這點中朝史料并無歧義,朝鮮史料認為明軍是受制于“和事”而放棄追擊日軍。
張應種從萬歷二十年(1592)十二月進入朝鮮,次年四月撤回,總共駐守朝鮮5個月*申欽:《象村稿》,卷三十九,《志·天朝詔使將臣先后去來姓名》(記自壬辰至庚子),見《韓國文集叢刊》,第72冊,269頁,首爾,景仁文化社,1990;另《朝鮮宣祖實錄》,卷三十四,宣祖二十六年正月丙寅十一日條載“統領南北調兵涿州參將張應種, 領馬兵一千五百名”同。。時雖不長卻有代表性。他既沒有參與東征第一階段最艱苦的萬歷二十一年冬季駐守朝鮮南部之役,更與第二階段的血腥戰事無緣,如稷山之戰、南原之戰、蔚山攻堅戰、泗川戰役及最后海上收官之戰等,明軍都有不少損失。而張應種所在的遼軍,卻因早撤保存了實力。
東征回國后,張應種復職寧遠參將,很快又以作戰不力被撤職。據萬歷二十二年十月丙寅條記:“先是,長昂以七千騎犯中后所。趙夢麟悉斂人畜,遣家丁趙子明等保小屯臺,斬虜哨三級,又射斃一酋,虜怒攻臺破,子明等力戰死之。當小屯告急時,副總兵秦得倚、趙夢麟各遣兵挑戰,虜始斂眾北歸。副總兵李平胡、游擊崔吉、參將張應種列陣大戰,追至半邊山,虜復并力來攻,我兵遂卻,各阻險自守,獨得倚、夢麟兩軍在陣鏖戰良久,多所殺傷。備御高清領兵百余自東來,徘徊不進。虜見塵起,疑有伏,遁去。兵部上功罪,秦得倚、趙夢麟各賞銀十五兩,夢麟以功準罪,張應種、崔吉等禠職提問有差。”*《明神宗實錄》,卷二七八,萬歷二十二年十月丙寅,5144~5145頁。中后所屬寧遠,張應種時為寧遠參將,與能戰敢戰的同僚相比技遜一儔,被禠職提問。這也印證了他在朝鮮戰場表現不佳的猜測。
當壬辰戰爭進入第二階段時,張應種未入朝參戰。萬歷二十五年(1597)十月,朝鮮使臣黃汝一出使明朝,次年正月到錦州,得知駐守“錦州西北又有義州參將張應種”*黃汝一:《海月先生文集》,卷十,《銀槎日錄》上(己亥正月),見《韓國文集叢刊續編》,第10冊,152頁。,主要任務是防守蒙古出掠。而《明實錄》則載,萬歷二十六年八月升“分守永寧地方都司僉書張應種為遼東右參將,分守義州地方”*《明神宗實錄》,卷三二五,萬歷二十六年八月甲戌,6035頁。。
接下來,張應種何時何事從參將再次降革不清楚。唯七年后,他第三次從都司添補為游擊。萬歷三十三年(1605)冬十月,“添設遼東戚家堡游擊一員,以都司張應種升補,仍將選鋒見在官軍移駐填實,其義州各城堡逃故軍士二千三百有奇,令該路將官開造姓名、衛所貫址呈送分巡道,遴委中軍等官徑赴各原籍,該道勒限嚴拏僉補。”*《明神宗實錄》,卷四一四,萬歷三十三年冬十月癸丑,7759頁。揆諸詞義,或許是他在義州參將任上,因逃故軍士過多而遭的處分。
張應種任戚家堡游擊4年后升任開原參將,這是他三落三起后的第四次任參將。萬歷三十七年(1609)二月,遼東巡按熊廷弼考察將領,認為開原參將張應種“精詳老練,久歷行間,其才獨優于整飭戎伍”,并不擅沖鋒陷陣,故建議將其調任寧遠右屯游擊,取代李繼武:“若以張應種居此,必能起廢修墜,有壁壘一新之效。”*熊廷弼:《按遼疏稿》,卷一,《糾劾將領疏》,見《熊廷弼集》,35頁,北京,學苑出版社,2011。四月,開原參將張應種就任寧遠右屯游擊*《明神宗實錄》,卷四五七,萬歷三十七年四月庚辰:“調劉世杰等寧遠各參將、張應種等右屯各游擊、祖天壽等懿路各備御”,8632頁。。張應種既然打仗不行,修城干活又怎樣呢?
很快,熊廷弼承認自己看錯了人。他在遼東跑了一圈,考察自萬歷三十四年正月起三十六年十二月止,三年錢糧、險隘、兵馬、器械、屯田、鹽法以至胡馬、逆黨等各項事務,得出結論:“見任右屯營游擊張應種”為應撤職的二位“道將”之一,“其為人也,口多游詞,外虛恢而中實貪婪,無所顧忌。一在戚家堡,為部軍所告,賄佒郝廵道而調寧遠矣;一在寧遠,為軍民所訐,行求舊撫鎮而調開原矣;一索取常例,月扣軍餉四、五十兩,而李必茂等扣送矣;一更換旗牌,每名得銀五兩免換,而劉世亨等過付矣;一領闔營軍,陸續采打柴木,賣銀千余兩,而修城為騙局矣;一占使騾四十頭,曰每輪載所造各色器物運赴廣寧私家,而馱砲為名色矣;一生辰諷各軍孝順,馬步每隊各攢銀五兩,約四百金上壽矣;一伊男張士彥赴京襲職,駕言缺費,科門下殷實員役數百金,充行槖矣;一占軍匠織網、結席、造器、駕鷹、打魚等項,而取盡錙銖矣。此一臣者,桑榆已逼,溪壑難填,所當革任回衛,以恤軍困者也。”*熊廷弼:《按遼疏稿》,卷四,《閱視疏》,見《熊廷弼集》,168~169頁。在九項罪名中,靠收受賄賂為升職調任開路,貪扣官兵軍餉中飽私囊,道德人品都有問題。萬歷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奉旨革職回衛。易代后,張應種之孫張朝麟曾言及“祖應種,官都指揮同知而歷任開原左參將升副將,誥封定國將軍,凡十二任。”*《(遼寧北鎮)張氏族譜》,第1冊,15頁,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兩相參照可知張應種四任參將,分別為山海、義州、寧遠、開原,副將任在開原;其余七任即遼東游擊及參將降職所任游擊、都司等更低的軍職。張應種由此成為晚明著名“廢將”。湖北巡撫梅國禎等雖曾建議“求舊易于得人,使功不如使過”*陳子龍等:《明經世文編》,卷四百五十二,梅國禎:《為叛丁悖亂異常時事萬分可慮疏》,中華書局,1962;參見張自烈:《芑山詩文集》,卷十七,《傳》二,《明少司馬衡湘梅公傳》,清初刻本。,啟用退閑遼東李家將李成梁父子及以戴罪閑住的史宸、張應種、麻貴等廢將卻未果。這即歷史上真實的張應種。
而吳正治替張應種所作的《神道碑》卻顯示出另一種模范將領的形象:
弱冠補博士弟子員,試輒高等。后襲祖職為指揮同知,遂投筆輟業,慨然有班定遠之嘆,以功遷游擊將軍,鎮守遼海……屹然長城,三韓倚重焉。山海關為畿輔咽喉,往時守者多不慎,烽煙一傳,震驚三輔……公甫抵關,即講求方略,諸凡汰冗弱、補卒伍、增樓堞、繕城堡,旬日之間,厘然具舉,壁壘為之一新。旋調寧遠、開原,所在著有成績。遷副總兵,卒于任。*《張氏族譜》,第1冊,吳正治:《皇清誥封光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二級肖泉張公神道碑》,52~53頁。
對照其確切履歷,可知歌功頌德的神道碑,在真實性上要大打折扣。
二、廣寧張氏家族的前世后生
張應種所來自的廣寧張氏家族,發源于河南。洪武三年(1370),張留注以指揮同知由上蔡移居廣寧,是為張氏始祖。“先世自青陽肇基,歷千余載。迄漢、唐諸族,散處吳、豫間。君游公以漁陽太守家南陽,至留注公以指揮使由上蔡移廣寧,是為公之始祖,六傳俱蔭顯秩。及鳳儀公官參戎,是為公之曾祖,生九思,官參戎,是為公祖;生應種,則公父也。官副將,封定國將軍,生東越公。”*《張氏族譜》,第1冊,《張士彥傳》(原無題,筆者自擬)。始祖張留注,自河南上蔡移居廣寧,遂占籍遼東。中經六傳,第七代張鳳儀、第八代張九思均為參將,第九代張應種為副將,延至第十代東越公張士彥,在廣寧居住已逾兩百年,成為一個遼東土著軍事家族。
參將張鳳儀事跡無考。
參將張九思,嘉靖三十四年(1555)時任游擊。兵部尚書楊博匯報九邊秋防功過,提到過薊州游擊張九思:“薊州兵備副使趙忻,副總兵吳珮、羅文豸,參將楊照、蔣承勛,武勛線世祿、劉淮,游擊尹秉衡、許棠、王允中、張璣、張九思……分守信地,竟保無虞。”*楊博:《楊襄毅公本兵疏議》,卷三,《覆宣大薊遼等處總督尚書許論等獻捷升賞疏》,明萬歷十四年刻本。薊州游擊張九思因“分守信地,竟保無虞”名列“量升職級”的37人名單中。
五年后,張九思已任開原參將。嘉靖三十九年(1560),因開原馬市遭受朵顏三衛人襲擊,參將張九思被罰俸一月:“福余衛夷人長孛羅等入開原馬市,索賞不遂,夜襲殺哨軍,遁出關。巡撫侯汝諒以聞,因請治失事諸將罪……奪參將張九思、備御姚鉞俸各一月。”*《明世宗實錄》,卷四八○,嘉靖三十九年正月丙戌(二十日),8021頁。
隆慶三年(1569)三月,張九思為廣寧參將:“錄修浚遼東三岔河廣寧鋪路河工,賜巡撫都御史魏學曾、鎮守總兵王治道、副總兵王重祿、參將張九思、游擊畢朝銀有差。”*《明穆宗實錄》,卷三十,隆慶三年三月己酉(初五日),787頁。這兩任參將都是張應種之父無疑。而萬歷二十一年,為救護慶云堡官王鳳翔戰死的“軍丁張九思”*按:萬歷二十一(1593)年夏,有慶云堡“軍丁”張九思因救護被三衛蒙古伯言兒誘執的慶云堡官王鳳翔戰死,從身份及事跡看,都不會是原任遼東參將張九思,否則替張應種作《神道碑》的吳正治或張氏子孫《自敘》恐難放過如此英勇事跡。具體參見《明神宗實錄》,卷二八五,萬歷二十三年五月辛巳(初九日),5279頁;瞿九思:《萬歷武功錄》,卷十三,《東三邊·煖兔拱兔列傳》,明萬歷刻本;《明史》,卷二三九,《列傳》一二七,《董一元》,6213頁,中華書局,1974。以及可能來自錦州軍營的“張九思”*熊廷弼:《按遼疏稿》,卷六,《覆哈流兔捷功疏》載,萬歷三十六(1608)年十二月,錦州營軍丁張九思,執行遼東總兵杜松之令,在大福堡門首砍下了駐邊熟夷陶太的頭顱,“張九思為首,謝告為從,斬熟夷陶太”。(見《熊廷弼集》,295頁)。,均為同名者。
張九思之子張應種生有四子:長士彥,次士奇、三士英、四士杰,以士彥最為著名。
萬歷三十九年(1611)六月,熊廷弼再次奉命巡閱遼東,薦舉了兩批人才。第一批是副總參游檔次的官員;第二批薦舉的是操司衛所官員。在第二批人才中,張應種長子張士彥赫然排在第一名:“訪得巡撫標下旗鼓、廣寧衛指揮僉事張士彥逸度飄然,霞舉雋才,颯爾風生,警敏多能,緩急可用。”建議“將張士彥等及時擢用”*熊廷弼:《按遼疏稿》,卷六,《舉將材疏》,見《熊廷弼集》,308頁。守備、備御,使邊疆不致有乏人之嘆。從結果看推薦落實了。只是10年后,“逸度飄然”“警敏多能”的守備張士彥,在天啟二年(1622)廣寧城失陷時,擔任的角色卻是迎降者。
但《清史稿》提到張士彥時,兩個關鍵點都很“模糊”。一是他以守備身份降于廣寧:“太祖……下廣寧,游擊孫得功、守備張士彥……皆以有功授世職。”僅記載張士彥等以降得授世職,具體細節不詳。張氏子孫載:“先大人東越公……因遼陽失守,太祖武皇帝豁達神智,延攬英雄,先大人識時歸順,首建大功……及守牛莊,為濱海重地,島寇聞風匿影。而大凌河之役,設法堵御,決策運籌咸中機宜,戰守之功尤著。”*張士甄:《張氏族譜序》,見《張氏族譜》,第1冊,7~8頁。提及張士彥“識時歸順首建大功”的地點在遼陽而非廣寧。
明遼東廣寧巡撫王化貞揭報,談到了張士彥等人在廣寧城陷中的作用。當時廣寧城內,尚有守兵1.6萬余人,但人無固志,且流行謠言“奴恨廣寧人甚,城陷必屠之”。故從十九日開始,城內人聽聞敵軍過河,即多奔避山中,喧填街市,共謀斬關,“關一啟不可復止”,守兵隨出且多有自城縋下者,城空煙起,“張士彥、孔從周等公然為迎降之事矣”*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卷七,王化貞揭,明崇禎刻本。。可見,廣寧城陷是張士彥等主動迎降拱手送出,時間就在天啟二年正月十九日。但清朝史料幾乎都抹去了張士彥主動迎降這個重要細節*按:《清史稿》只說張士彥以降有功得授世職,《八旗通志》也對“廣寧投誠游擊張士彥”一筆帶過(鄂爾泰等修:《八旗通志》,卷十六,《旗分志》十六,《八旗佐領》,第1冊,285頁,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85),《滿文老檔》更沒有提到,只在二十日載“廣寧出迎之官皆升授官職”(《滿文老檔》,上冊,305頁,北京,中華書局,1990)。,所謂“早識天命”“首建大功”被虛化。至其“仗劍以從”跟隨清太祖廓清四海,“屹然有萬里長城之望”*康熙十八年北海后學法若真所作的張士彥傳,見《張氏族譜》,第1冊,5~6頁。之評,若被熊廷弼得知,不知又會有何反應?從事后看,熊廷弼對張應種、張士彥父子的評語都錯得離譜,只是對于前者,他有糾正機會,而對后者,則無能置喙了。
二是《清史稿》說張士彥為“(王)化貞中軍守備。太祖兵至,化貞走入關,士彥降。漢軍旗制定,隸正藍旗。天聰八年,與一屏同授三等甲喇章京。旋乞休。子朝璘,襲職。”*《清史稿》,卷二三一,列傳一八,《張士彥子朝璘》,9343頁,北京,中華書局,1986。《清太宗實錄》也記載:“三等甲喇章京張士彥年老,以其子朝璘襲替,仍準襲三次。”*《清太宗實錄》,卷二十一,天聰八年十一月乙丑(十三日),278頁,北京,中華書局,1985。官書所載張士彥年老將世職讓于長子朝璘繼承,但事實卻頗有曲折。
法若真作張朝璘傳:“惟豫閩督公年十四,即遭先公變,賴繼母太夫人王氏鞠育有成,襲先職。”*《張氏族譜》,第1冊,6~8頁。張朝璘《自敘》也說:“予年甫十四,即遭先大人見背……幸邀父蔭襲三等阿達哈哈番職。”*《張氏族譜》,第1冊,16頁。則張士彥在天聰八年(1635)十一月十三日張朝璘襲職前已去世*《張氏族譜》,第5冊,2頁。張朝璘天命七年(1622)三月二十九日生,康熙三十四年(1695)八月十九日卒,享年73歲。天聰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年十四歲襲職三等輕車都尉。,官書所謂“年老”“乞休”與私記“見背”襲職間,相差的不僅是先后次序,還有一個重要史實。
天聰九年七月,已死半年余的張士彥仍名列“罰銀百兩”的名單中。《清太宗實錄》及《八旗通志》均載當年七月“分別管理漢人官員,以各堡生聚多寡黜陟之”:李成梁之孫李思忠升為三等梅勒章京。張士彥因“原管壯丁”450名,“今減”128名與高鴻中、金玉和等“各罰銀百兩”;高拱極等被“革職為民”;而金海塞接管壯丁減287名,除罰銀百兩、革旗鼓職外,還“永與本貝勒為奴”*參見《清太宗實錄》,卷二十四,天聰九年七月癸酉,315頁;《八旗通志》,卷十七,《旗分志》十七,《八旗編審》,第1冊,296頁。《通志》注明材料來源于《太宗實錄》。。這才是張士彥降清后所面臨的真實歷史。在法若真所作的傳里,勞頓不堪的實相完全被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光輝所淹沒。而對一個失去家長、諸子皆幼的家庭來說,罰銀百兩的重擔落在年僅14歲的少年肩膀,張朝璘學得的人生第一課就是襲職權伴隨著義務債。
官書不諱之事在家譜里卻不相宜。張朝璘的自述提到歷經各大戰役,幾乎沒有錯過一場與明清鼎革相關的重大戰事:如松錦大戰、山東膠州和登州之戰;克中后所、前屯衛,潼關戰役、平定江南屠江陰、克揚州及蘇松江浙等地;隨漢三王平定湖廣,與洪承疇犄角相支數年,經歷寶慶、武岡、沅州、黔陽之戰;克衡、永諸郡及廣西、貴州;平定山西姜瓖等戰。所謂“屈指二十余載,身經數百余戰”*《張氏族譜》,第1冊,15~24頁。,哪一次不是死里逃生的賭博?這些降將為清軍開辟了一條入關之路,作為開路先鋒,這也是明末清初絕大多數遼將(也稱漢軍旗人)的普遍經歷。張朝璘仕至江西、福建總督*按《清史稿》,卷二三一,《列傳》十八,《張士彥子朝璘》,9343頁。,享年73歲。在他出生之前的兩個月,其父張士彥降清:或許即將出生的長子,正是他降清的私心之一?為現實便利,主動迎降爭取較好待遇的想法壓倒了軍人的使命。故張士彥死后,年僅14歲的張朝璘得以承襲三等輕車都尉世職,這和明朝首位降清大員薊遼總督、兵部尚書洪承疇死后酬勞相等,但后者替清朝平定江南、西南,獨力支撐南中國數年之久。由此可見,降清越晚、職位越高的明廷大臣,在清朝的地位或越不堪。
在《八旗通志》里,正藍旗漢軍第四參領第二佐領即張氏世管佐領:“系崇徳七年(1642)編設,初以廣寧投誠游擊張士彥之子、三等阿達哈哈番張朝璘管理。”*《八旗通志》,卷十六,《旗分志》十六,《八旗佐領》,第1冊,285頁。在承襲父職十年后,因升任江西巡撫,由弟張朝政*珍管理,張朝珍升任湖廣巡撫,以其子御史張圣碩管理。這個佐領一直由張氏家族承管。
仕至湖廣巡撫的張朝珍行五,最著名的功績是平定三藩:“調集兵將,極力捍御,幸保無虞……此實撫軍弟之功,于斯而益見矣。”*《張氏族譜》,第1冊,29~30頁。
登封知縣張朝瑞行四,最著名的功績是“擒獲偽總督李企晟,搜有偽印偽札數十,將赴楚豫各處誘惑布散,倘漏網貽害,可勝言哉!”*《張氏族譜》,第1冊,26頁。
廣寧張氏成員主要就是由這三支子孫構成。從張九思到張應種,三代墳墓俱在“廣寧北風水關外五里許”。至“始祖以下諸墓,傳在四里屯樂鹿堡者,五十年來兵革之余,荊榛滿野,碑碣無存,皆遠不可識。”四里屯樂鹿堡當在廣寧衛轄境。自康熙十七年(1678)前推五十多年,正是晚明天啟、崇禎間,樂鹿堡因兵革頹廢無聞也是自然。張應種死于明亡前,未曾見到明清鼎革。張士彥的墓地在“盛京北二十里大凹”*《張氏族譜》,第1冊,33頁。,則親歷見證了故國家園淪陷。
三、總結和啟示
廣寧張氏這個在遼東繁衍200余年的家族,雖有數代軍功,但最高職銜僅為副將,與李成梁這種著名家族相比,只能算作三流軍事家族。在明代一些重要的軍事行動中,如萬歷壬辰戰爭及之后,張家三代參將都沒有突出表現,反倒是通過明清鼎革,實現了家族快速崛起。與之相反,明代一流的李氏家族,卻在易代過程中被徹底瓦解、衰落*參見葉高樹:《明清之際遼東的軍事家族——李毛祖三家的比較》,載《臺灣師大歷史學報》,2009(42)。。由此可見,易代這樣的政治性事件,對張氏家族的影響是決定性的。而清朝著重利用的就是原屬明朝二、三流的軍事家族,打造為新政權的中流砥柱:張朝璘順治年間為江西督撫,康熙初年任福建總督,張朝珍三藩叛亂期間任湖廣巡撫,都屬不易。可以說,張家子弟可為清朝擔任馬前卒的遼將代表。
在思想意識方面,以張朝璘為代表的新遼人,已與明朝脫離關系。“因憶先大人即世以來,余兄弟自幼賴先慈諭之以大義,長復詔之以服官,余兄弟亦惇遵惟謹,以至今日,俱仰承休命,累秩重封,撫躬自省,固不能報答皇恩于萬一,庶幾無愧于祖宗世澤,而次亦不負先慈家訓也。”*《張氏族譜》,第1冊,30頁。明朝的“祖宗世澤”與“先慈家訓”,在清朝“累秩重封”面前得以無縫彌合。明清兩個政權的爭斗、滿漢民族的隔閡,在東征游擊張應種之孫朝璘、朝珍、朝瑞三兄弟為代表的土著遼人間,并無選擇困難。張士彥背叛明朝,主動迎降,但他入關前即已去世,朝璘兄弟自幼由繼母養育,長于清治,以身經百戰換得仕途攀升,既無思明基礎,也無父親污點影響。他們融入清朝的過程,也正是后金擴張凱歌行進的過程。作為原明衛所中下級職官,從駐地失陷入清開始,歷史已重新書寫:朝璘三兄弟均為清朝封疆大吏,為逐鹿中原立下汗馬功勞,所得比失去多,這當是多數原明中下層衛所官兵融入清朝的現實邏輯。
從制度史角度看,明代衛所制下的累世參將張氏家族,被改造成清代八旗制下的佐領,遂徹底掩沒了明代衛所制與清代八旗制間的聯系。清朝的具體做法是改造人員,將所繼承的衛所成員分散、打亂,重新攪拌、灌裝到八旗制度內,從而成功抹去明朝的痕跡,從形式到內容徹底地取代了明代衛所制。清代內務府中的旗鼓佐領、內佐領及外八旗中的漢軍旗人,都是明代衛所制被成功改造的成果,新瓶混裝舊酒,身份改變伴隨著制度的脫胎換骨。
由此可見,得遼人者得天下的說法是有一定道理的,遼人確實是由明入清的關鍵。從萬歷壬辰戰爭的普通北將到明清易代后的清朝新貴,張氏家族是在被消滅、俘掠之外主動投靠后金—清政權的明朝將家,增加了“遼人”研究類型的豐富性。不僅具有學術意義,也有現實意義:展示了一批生活在天高皇帝遠的多民族交叉地帶的漢將,在歷史轉折關頭,對生存環境擁有一定的選擇權。從政治史的角度說,他們站在哪一邊,哪一邊就擁有更多奪取政權的勝算,明清鼎革的歷史就是通過這樣不同類型的軍事家族,展示出不斷增加的豐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