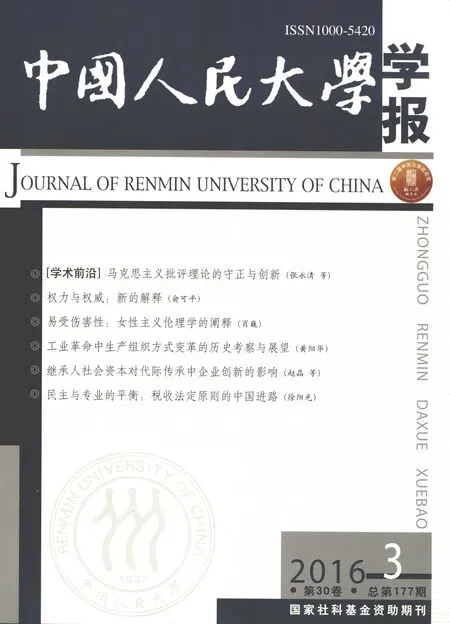工業革命中生產組織方式變革的歷史考察與展望
——基于康德拉季耶夫長波的分析
黃陽華
?
工業革命中生產組織方式變革的歷史考察與展望
——基于康德拉季耶夫長波的分析
黃陽華
對當前新一輪產業變革可以按照技術經濟范式核心組件協同演化的框架加以剖析。新一輪產業變革可能是第六次技術經濟范式(也即第六次康德拉季耶夫長波)的導入期,將在如下方面發生“革命”:數據要素將成為新型核心投入,以新一代互聯網技術為支撐的通信基礎設施的重要性超過交通基礎設施,以數據和新一代互聯網技術驅動的制造業智能化將引領國民體系的智能化;最終,大規模生產也將受到嚴峻挑戰,大規模定制化和社會化制造等新的生產組織方式將興起。為此,我們必須從技術經濟范式的視角認識新一輪產業變革的進程。在此背景下,我國深入推進工業化不僅要如《中國制造2025》那樣重視裝備工業的高端化,更需要重視制造業各環節數據要素的利用和新一代互聯網基礎設施的配套升級,增強各類政策之間的協調聯動。
工業革命;技術經濟范式;長波;生產組織方式
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爆發出的巨大能量使得經濟首次實現了持續增長,人類社會發展軌跡也得以改弦易轍。機器、能源和材料的推陳出新及廣泛應用使勞動生產率得到史無前例的增長,與人均收入、人口總量、知識、投資及技術創新形成了正反饋機制,助力人類跳出了“馬爾薩斯陷阱”[1](P259-260)。誠然,一系列重大發明的產業化是促成這一切的必要條件,但是如果沒有與之相適應的生產組織方式變革,技術進步就只能是一種“潛力”,伴隨技術創新擴散過程而漸次出現的經濟社會巨變也僅是一種可能性。本文試圖在微觀層面上從工業發展史中歸納出歷次重大技術變革中生產組織方式的變革規律,并以這種“理性化的歷史”為啟發式,展望新一輪產業變革中生產組織方式的演變特點與趨勢。
本文將在演化經濟學經典的技術經濟范式分析框架下,剖析新一輪產業變革中初現端倪的新的技術經濟范式的核心構件的演進,力圖在如下三個方面拓展既有研究:一是在演化經濟學家已有工業革命史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補充當代現實變化,并根據新一輪產業變革的最新進展對他們過去做出的預測加以必要的校正。二是推動現有關于新一輪產業變革的研究從現象描述向結構化、系統化和理論化研究轉變,以更好地把握這場變革的核心節點,為制定和優化產業政策提供扎實的理論指導。三是重視微觀層面生產組織方式的變革,推動當前以宏觀戰略和產業分析為主的新工業革命研究深入至微觀層面,為更好地認識和推動新一輪產業變革奠定堅實的微觀基礎。
本文的分析結構如下:第一節對生產組織方式與技術浪潮進行歷史考察,重申演化經濟學家對“工業革命”、“技術浪潮”、“康德拉季耶夫長波”和“技術經濟范式”等概念的界定,并主張以創新及其擴散作為工業革命分析框架的核心,指導后文對技術經濟范式演進的研究。第二節對歷次康德拉季耶夫長波中的生產組織方式變革進行細致梳理,說明歷史上典型生產組織方式的演進并不是自發的,而是與要素結構、產業結構和基礎設施形態所構成的特定情境相匹配,其基本功能是有效提升生產管理效率,降低企業組織的制度成本。基于上述理論與歷史的研究,第三節展望新一輪工業革命中技術經濟范式各核心構件的演進,特別關注演進過程更漫長、更復雜的生產組織方式的變革,以增進我們對新一輪產業變革的理解。第四部分以一些政策性評論對全文進行總結。
一、生產組織方式與技術浪潮的歷史考察
相比于歷史學家常用“工業革命”概念,深受熊彼特創新理論影響的演化經濟學家更青睞“技術浪潮”這一概念。在傳統工業革命史研究中,技術雖然居于重要地位,但是技術在工業革命中的作用卻常被視為是外生的和線性的。在演化經濟學家看來,工業革命史更為復雜。
第一,重大技術演進本身就是一項重要的研究課題。如果僅僅將技術作為外生沖擊,那么對工業革命的解釋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這也是以新政治經濟學家為代表的制度主義在解釋工業革命時面對的主要批評。例如,圖洛克(G. Tullock)認為,英國大刀闊斧地削減特許專營數量、廢除限制性制度,從而提高了尋租成本,引導人們從尋租活動轉向生產活動,這是工業革命發生在英國的主要原因。[2]阿西莫格魯(D. Acem ̄oglu)等指出,1500—1850年大西洋貿易孕育了對私有產權保護懷有強烈訴求的新興商業階層,它們以多種方式限制了王室權力侵犯私有財產,為工業革命的爆發奠定了制度基礎。[3]我們認為,這些研究過于強調制度是英國工業革命的充分條件,以至于忽視了技術創新是工業革命的必要條件,故不能充分解釋為什么其他私有產權得到有效保護的時代(或國家)沒有發生工業革命。
第二,技術創新對產業的影響不是簡單的“沖擊—反應”模式。如果機械地認為技術突破將自發地導致工業革命,那就容易陷入技術決定論。演化經濟學家堅持認為,發明必須經成功的商業化才能成為創新,才能引發產業、經濟和社會系統的變化。這個過程極為漫長、復雜且不確定,應成為工業革命史研究的重點。創新可分為非連續的激進創新和既定技術路線上的漸進創新,對產業結構的影響也存在明顯差異,那么,引爆“工業革命”的是激進創新還是漸進式改進呢?對此,弗里曼(C.Freeman)和盧桑(S.Lou??)認為,激進創新帶來了通用技術的更替,導致全要素生產率出現跨越式增長。[4](P140)因此,在工業化歷史長河中發現里程碑式的激進創新,成為研究工業革命的切入點。
第三,研究創新及其擴散的歷史甚至比技術史更為重要。激進創新通常是在某些先導產業率先出現后向其他產業擴散,對其他產業的帶動效應是多種形式的,如提供關鍵原材料和通用裝備,或者改善交通和通信基礎設施。因此,聚焦先導產業的成長有助于深入揭示工業革命的發展過程。在給定技術機會的前提下,先導產業的發展受制于三個因素,即核心要素的可得、基礎設施的支撐和經濟組織的支撐。先導產業與這三個因素共同構成了技術經濟范式的核心構件。可見,管理與組織變革貫穿于歷次長波當中[5],以至于錢德勒(A. Chandler)以“組織能力”所處的制度環境、組織能力的構建和擴散分析歷次工業革命中典型國家產業競爭力的形成,提出“組織能力即為核心能力”這一著名命題[6](P594)。
綜上,在注重過程分析的演化經濟學家看來,工業革命的發展過程可用圖1表示。首先,從技術突破到非均衡產業結構變化是一個漫長、復雜但層次清晰的歷史過程。在此過程中,創新的發生及其擴散居于核心地位,先導產業是激進創新的載體。其次,激進創新的擴散需要與核心投入、基礎設施和生產組織協同演化,促進先導產業部門的成長。再次,先導產業通過直接或間接的產業關聯和示范效應,帶動產業體系發生顯著變化。整個過程也被稱為技術經濟范式的轉變。

圖1 以創新為核心的工業革命分析框架
演化經濟學家借助該分析框架,運用翔實的史料,不僅全景式地分析了18世紀工業革命以來的產業演化史,而且還精巧地將歷次激進創新浪潮與康德拉季耶夫長波相匹配(見表1),賦予創新浪潮更豐富的經濟學意義。[7]在技術層面看似跳躍的工業革命在經濟層面卻是連續展開的,“革命”一詞雖然突顯了工業革命對經濟社會的巨大影響,但模糊了技術創新及其擴散過程的連續性。因此,弗里曼和盧桑主張使用“連續發生的工業革命”來反映波瀾壯闊的產業演進過程。相應地,他們提出18世紀中期英國第一次工業革命實現的工業機械化,實質是第一、第二次創新浪潮的演進過程,19世紀第三、第四次創新浪潮則實現了以工業自動化為特征的第二次工業革命。依照上述理論分析框架和歷史過程研究,有學者推斷,20世紀下半葉以來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很可能是第五、第六次創新浪潮的涌現與拓展過程。[8]當前被熱切關注的新一輪產業變革極可能是第六次創新浪潮,應該按照成熟的技術經濟范式加以系統化的深入研究。

表1 技術創新浪潮與康德拉季耶夫長波
二、前五次長波中的生產組織方式變革
(一)第一次工業革命中的生產組織變革
第一次工業革命也被稱為“制造業的機械化革命”,由第一次和第二次康德拉季耶夫長波組成。在這兩次長波中形成的典型生產組織方式是工廠制和技工承包制。
1.第一次長波與工廠制度的形成
棉紡織業是第一次工業革命重要的經濟增長點,在工業革命史研究中占據了重要地位。紡織機械的技術進步極大地提升了生產效率,棉花加工效率從1780年的1磅/小時提高至1830年的14.3磅/小時,單個工人在一個童工的配合下可同時操作4臺動力織布機,生產效率相當于20名手織工。[9]鐵是軋棉機的主要原料,鐵的成本在相當大程度上決定了軋棉機的成本。所以,在演化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下,鐵成為制約先進生產工藝大規模推廣的瓶頸。18世紀焦炭煉鐵法和科特攪煉法兩項關鍵煉鐵技術的突破,使得鐵能夠廉價供給,促進了以蒸汽機和軋棉機為代表的機械裝備的廣泛采用,工業革命步入快車道。蒸汽機的廣泛應用引致了煤炭需求,采煤業引入蒸汽機后生產效率得以提升,煤炭價格下降又降低了蒸汽機的使用成本。因此,受棉紡織業刺激而發展起來的鐵和煤成為工業革命的核心投入要素,不僅極大地帶動了其他產業的機械化,而且還推動運輸力從水力轉變為蒸汽動力。
1890年前后,紡紗業經歷了從分包制到工廠制的轉變。一方面,傳統生產工藝下紡紗業勞動密集程度高,早期企業不具備雇傭、培訓和監督工人的管理能力。另一方面,以農民為主的勞動者不適應工廠的工作制度,不愿意進入工廠工作。按照經典的企業理論[10],企業主傾向于采用市場交易的方式,將紡紗外包給紡紗工(即“外包制”),降低企業招聘、培訓和監督工人的成本。隨著企業增加專用性固定資產投資,外包會導致高昂的交易成本,不利于發展規模經濟。18世紀90年代,工廠制憑借資本集中、企業內部分工、再生產和分銷網絡的優勢及嚴格的勞動紀律,成為紡紗業的主流生產組織方式。諸多行業紛紛效仿。蒸汽動力代替水力、風力等自然力,為工廠的選址帶來更大的自由度,也促進了工廠制的流行。早期工廠內部管理分工尚不發達,限制了工廠規模的擴張,隨后出現的合伙制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這一限制。
2.第二次長波與技工承包制
瓦特改良的雙動式蒸汽機雖然大幅度提升了功率,但由于成本高昂,在相當長時間內并未取得商業成功。直到以下兩個條件具備后,瓦特蒸汽機才被廣泛采用:一是機器、鐵、煤被廣泛應用,特別是機床的出現降低了蒸汽機的成本;二是鐵路網的擴張拉動了蒸汽機車制造、鐵路車輛和鐵路裝備產業的成長。機床作為通用裝備可被廣泛應用至其他產業,形成了“鐵—煤—蒸汽機—鐵路裝備—精密機床”之間的協同效應,既提高了工業生產率,也促進了工業革命向更廣闊地區(特別是歐洲大陸)傳播。首先,工廠增加機器和專用設備種類后,專用性投資隨之提高,企業規模不斷擴大,工廠組織的制度成本也不斷上漲。為此,工廠內部興起了技術工人承包制(即“內包制”),即將生產責任發包下放至技術工人或領班,由他們組織工人生產和管理機器。[11]這一時期的分包制是在工廠內部分包(“內包制”),而18世紀90年代以前則是“外包制”,在一定程度上是外包制與工廠制的結合。相比于工廠制,技術工人承包制增加了生產的科層,形成了多層委托代理關系,降低了監管成本。相比于外包制,工廠可以實行指令管理,節約了交易成本。技術工人承包制持續了約1個世紀,促進了英國產業工人積累專業技能,提升了行業合作精神和技術工人的責任感,塑造了精益求精的工匠文化。其次,鐵路對現代企業制度的形成產生了示范效應。[12](P79)今天高效企業所具備的屬性很多源于鐵路運營和擴張(特別是長距離運輸)的實踐,例如守時、前向服務規劃、慣例化檢修、控制關鍵供應商、及時配送、總部管控、分段運營形成的科層制、層次分明的職責體系,乃至圍繞鐵路建設運行創新投融資體系(如股份制)等。
(二)第二次工業革命中的生產組織變革
第二次工業革命被稱之為“制造業的電氣化革命”,由第三次和第四次長波組成,依次形成了泰勒制和福特制兩種典型的生產組織方式。
1.第三次長波與泰勒制的誕生
電力對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意義堪比鐵和煤之于第一次工業革命。19世紀中期電樞、交流發電機、轉子等發電設備的核心部件得以突破后,一些國家率先實現了大規模發電和輸變電。電力作為一種新興工業品,初始市場是有軌電車和城市電氣軌道交通,在推廣過程中涉及昂貴的設備、先進的技術、復雜的保養、繁瑣的會計核算及各類協調工作。過去所有者和經營者不分的馬車市政管理機構難以勝任電氣化交通的管理任務,受薪職業經理人階層應運而生[13](P226),對工廠制形成了較大沖擊。電力通過改善工作環境和優化工業流程重塑了工業生產組織方式。[14](P187)在使用電力之前,生產線依靠多臺蒸汽機協作提供動力,任一蒸汽機故障都會影響整條生產線的運轉。經電氣化改造后,生產流程變得簡潔、穩定、靈活,電網擴張也提高了工廠選址的靈活度。電力還改變了機械裝備的設計、制造和操作,優化了生產流程。在這些創新的驅動下,不僅工業生產效率快速增長,而且工業生產組織方式也發生了重要變化。[15](P185)
在制造業電氣化浪潮的推動下,一批新興產業特別是原材料工業快速發展,并且產生了極強的溢出效應。鋼材具有良好的延展性且可被有效壓縮,價格下降空間大,以鋼為原材料的中間產品創新提升了下游產業的效率,形成中間產品和終端產品相互促進的“內生增長模式”。[16]在交通運輸方面,工程性能更優的鋼軌替代了鐵軌。銅是理想的導電材料,電解銅技術降低了銅價,廉價銅線壓低了輸電成本和電價,又反過來降低了銅的成本,形成“銅材—輸變電—電價”的正反饋效應。這個時期,蒸汽船、鐵路得到長足發展,電話電報和打字機促進了生產和分銷的快速擴張,全球市場一體化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形成了早期的國際產業分工網絡,工業領域內出現了最早的跨國公司,工業生產組織方式出現了新的形式。一是小工廠演變成對產業和國家具有重要影響的大企業[17],對傳統的企業治理結構提出新挑戰。二是產品復雜度不斷提高,生產流程的持續延長和技術知識的快速增長提高了管理的專業化水平,企業內部的協調成本急劇上升。三是技術工人難以掌握全部生產知識,職業經理人管控模式逐漸形成。四是企業主和管理者不分的私人企業演變為所有權和管理權分離的公司治理結構,被后世稱為“管理革命”。[18]企業管理的職業化、專業化促進了成本會計、生產流程控制、營銷等發展成為專業技能,企業內部的研發設計、人力資源、公共關系、信息、市場研究等管理活動也逐漸專業化。以專業管理團隊為基礎的“泰勒制”發展起來,企業管理逐漸從車間上移至管理團隊。[19]專業管理團隊的分工協作也增強了企業的動態能力,多元化戰略逐漸流行。
2.第四次長波與福特制的形成
福特制的建立標志著制造業進入了自動化階段,被視為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標志。制造業自動化可上溯至19世紀末的“美國制造體系”。[20]“美國制造體系”脫胎于美國軍工產業,基本特征是產品(武器)標準化,可互換零部件和采用大功率生產設備。這種基于標準化制造的理念不僅提高了軍工產業的生產效率,而且衍生了龐大的制造體系,成為美國工業化重要的推進器。這一時期,以新型機床為代表的裝備工業大發展強化了以高效率、標準化、可互換性為特征的“美國制造體系”,為推廣流水線奠定了產業基礎,并最終使其成為第四次長波的典型組織方式,推動了國民經濟從電氣化向自動化躍升。在本次長波中,產業結構的突出特征是耐用消費品制造業成為先導部門,需求因素超過供給因素成為拉動產業成長的首要驅動力。首先,1929年“大蕭條”抑制了第一次全球化進程,國家之間的利益沖突激化,全球籠罩著戰爭陰霾。鐵路投送軍隊不再適應機動化作戰的需要,軍事列強紛紛加快了摩托化和機械化的進程。巨大的軍事需求刺激了汽車、卡車、坦克和航空器的增長。其次,汽車、卡車和拖拉機等耐用消費品雖頗受民用市場青睞,但居高不下的生產和使用成本抑制了需求。在福特“T型車”之前,主流的生產方式是用戶直接向汽車制造商“定制”汽車,雖滿足了用戶的個性化需求,但缺乏規模經濟,汽車價格昂貴,交付周期較長,汽車是富人標榜社會地位的炫耀性商品。福特“T型車”實現了從定制生產到標準化生產的轉變,極大地降低了汽車生產成本。以伯頓裂化煉油工藝和胡德利催化裂化工藝為代表的煉化技術進步降低了汽油的價格,加油站和公路網的拓展降低了汽車使用成本。
福特制利用標準化生產打破了工人技能對產量的限制,上下游工序流程再造形成了流水線,專業化分工提高了各工序的生產效率,標準化零部件生產形成了規模經濟效應,從而降低了生產成本。勞動生產率的大幅提升提高了工資水平與消費能力,金錢外部性又刺激了對其他產品的市場需求。產品標準化程度提高后,企業的主要競爭策略有二:一是產品多樣化策略。設立不同的產品線,開拓細分市場并差異化定價。采取這種策略的企業規模也會隨之擴大,如美國通用汽車公司。二是成本控制策略。實施福特制的必要條件是零部件的標準化和及時供應,供應鏈和車間管理效率對福特制的成敗具有決定性意義。該策略的成功案例是日本豐田汽車公司采取的精益生產方式(即“豐田制”)。[21]
總之,在第三次和第四次長波構成的第二次工業革命中,不僅涌現了資本和技術更為密集的新興產業,產生了復雜耐用消費品和高效率的長流程生產工藝,新材料、新能源被廣泛應用,交通和通信基礎設施具有更強的網絡效應,而且為了提高對復雜度日益增加的生產的管理效率,企業管理現代化也快速推進,泰勒制、福特制(和豐田制)等代表性生產組織方式相繼建立起來,主宰工業生產組織方式長達一個世紀之久。
(三)第五次長波與生產組織變革
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工業信息化時代可以被視作第五次長波。在這次長波中,電子芯片扮演了核心投入的角色。自20世紀50年代末第一塊集成電路板誕生后,電子產品日趨小型化、高精度、高穩定、高能效和智能化。與前四次長波類似,核心投入產品的供給速度決定了先導產業和基礎設施發展的水平。“摩爾定律”很好地歸納了電子芯片技術的演變特征,即每隔1~2年芯片容量就會翻倍,電子芯片的性價比不斷提高,加快了電子計算機的普及和應用速度。
計算機的出現對工業的影響極為深刻。20世紀中期,機床植入了計算機系統后形成了數控機床的雛形,逐漸發展出工業控制系統,促進了工業設計、控制和編程的持續改進。1972年英特爾處理器大幅降低了計算機的成本,計算機同時在消費品市場和資本品市場得到快速發展。制造業信息化促進了自動化水平的顯著提升,出現了至今仍具有廣泛影響的“柔性制造系統”(FMS)。建立在標準化之上的大規模生產減少了產品種類以追求規模經濟,但是數控機床出現后,廠商可將消費者的個性化需求分門別類,減少生產設備的調整,縮短生產延時,生產出不同批次的差異化產品。柔性生產方式對企業競爭策略具有顯著的意義,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美國、歐洲、日本和韓國等紛紛著手構建FMS。得益于計算機芯片、傳感數控機床、軟件工程、目標導向數據庫、可視化工具和數控檢測設備的改進,FMS不斷更新換代,到了20世紀80~90年代,“靈活制造”(agile manufacturing)風行一時,不僅實現了更高水平的自動化,而且制造柔性更高,適應小批量生產之需。
生產工藝的巨變使生產組織方式發生如下變化:一是企業組織結構扁平化。在大規模生產方式下,企業為了實現產品差異化,通常會在內部設立不同事業部負責不同的生產線,科層組織可以更有效地協調部門之間的信息傳遞,降低企業內部的交易成本。但是隨著企業規模的不斷擴大,特別是一些企業橫向一體化發展速度加快后,部門間信息傳遞效率低下的“大企業病”日益嚴重。但是到了信息化時代,信息的收集、傳遞和分析的成本明顯降低,企業管理對科層結構的依賴程度也相應下降,企業結構呈現出扁平化的趨勢。二是企業網絡這一新型產業組織興起。在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生產高度一體化要求企業具有較強的資源動員能力,要求企業掌握技術、職能和管理三類知識。[22]通常而言,一體化大企業能夠利用相對穩定的盈利支撐這三類知識的獲取,因而更具優勢。但是到了信息化時代,生產一體化轉向碎片化,原先在企業內部完成的業務流程越來越多地由企業間協作完成。更為重要的是,信息大爆炸一方面降低了企業的知識學習成本,另一方面,企業間信息傳遞效率的提高也更方便利用知識的互補性。因此,企業網絡這種新型產業組織方式的重要性不斷提升。
三、第六次長波與技術經濟范式轉變
目前關于新一輪工業革命最常見的表述有:一是第三次工業革命,二是工業化的第四個階段(又稱“工業4.0”)。[23]無論采用哪種表述方法,均認為呼之欲出的“工業革命”將助推工業從信息化向智能化躍升。按照技術經濟范式理論,新一輪工業革命并非孤立事件,而是200多年“連續發生的工業革命”的拓展與升華。因此,筆者吸納賈根良的觀點[24],將新一輪工業革命稱之為第六次技術浪潮。我們將嚴格按照技術經濟范式的分析框架,結合當前主要工業化國家及我國應對新一輪工業革命的探索實踐和政策調整,研判第六次長波發生與拓展過程,展望生產組織方式可能的變革及相應的理論含義。*根據前五次康德拉季耶夫長波的周期(特別是第五次長波拓展期)可以判斷,第六次長波的導入期可能發生在2020年前后,到本世紀30年代中期都將是長周期的上升期,之后進入拓展期,延續到本世紀中期結束。這與德國“工業4.0”計劃規劃的愿景將于本世紀30年代實現相吻合。受傳統工業革命史研究思路的影響,人們關心的首要問題是新工業革命的“標志性”技術是什么,是3D打印、工業機器人,抑或是人工智能?按照演化經濟學家的觀點,這些新型制造技術更準確的表述是先導產業,它們雖然對產業和經濟社會的轉型升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其發展并不是自我實現的,而是依賴于兩個前提條件:一是核心要素變得物美價廉,二是基礎設施及時升級以滿足先導產業發展所需。因此,雖然各界普遍關注新一輪工業革命中的標志性技術或者先導產業,但是忽略了兩個本質性問題:一是什么要素是這些先導產業部門擴張所必需的核心投入?二是這些先導產業擴張需要什么新型基礎設施的支撐?
(一)數據將成為新一輪工業革命的核心投入
種種跡象表明,不同于以往技術經濟范式的轉換高度依賴于物理裝備的升級,驅動第六次長波的核心要素將是數據。換言之,數據要素將成為決定未來工業化水平的最稀缺的要素。[25]因此,相比于先導產業的更替,核心要素的更替更具革命性意義。雖然工業機器人、3D打印、人工智能等新型制造裝備提升了生產的自動化和柔性水平,但僅是生產效率的提升還不足以引發“革命性”的變化。按照美國“工業互聯網”、德國“工業4.0”計劃和我國“互聯網+”戰略的設計和部署,新一代互聯網技術將加速向制造業領域滲透,與新型制造技術深度融合后推動既有制造系統發生重大轉變[26],這就促使數據成為驅動生產組織方式變革的關鍵要素。
雖然20世紀70年代工廠引入“可編程控制器”(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PLC)*可編程控制器即工業控制計算機,其基本架構與個人計算機類似,即通過可編程存儲器執行順序控制、定時和計算等操作指令,通過輸入和輸出接口控制各類制造設備,達到干預生產過程的目的。后逐漸完成了初等信息化,但是與智能制造仍然有顯著區別。PLC僅實現虛擬信息世界向現實物理世界的單向輸出,物理世界并不能向信息世界作出反饋,數據的產生、采集、分析和利用也都是單向的,數據要素對企業邊際利潤的貢獻附著于物質資本之上,缺乏顯著性和獨立性。新一代互聯網技術向生產的全面滲透將徹底改變這種局面,大幅提升數據對企業邊際利潤的貢獻。當前,代表全球制造業最高水平的國際知名企業的探索實踐征兆著數據的獲取和配置不僅進一步提高了生產效率,而且正在挑戰流水線生產方式。博世集團和西門子集團等德國工業巨頭是德國“工業4.0”計劃的主要倡導者和實踐者,它們圍繞數據構建智能環境,并以此為基礎建立“智能工廠”,即在制造裝備、原材料、零部件、生產設施及產品上廣泛植入智能傳感器,借助物聯網和服務網實現終端之間的實時數據交換,達到實時行動觸發和智能控制,對生產進行全生命周期的個性化管理。智能工廠為智能產品的生產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智能產品記錄了消費者的需求特征以及從生產、配送到使用的全過程數據,在生產過程中可根據消費者的個性化需求,以數據交換的形式與生產設備“對話”,選擇最優的配料和生產方案,極大地提高了制造系統的柔性。曾被福特制替代的“大規模定制”生產組織方式重新具有了技術和經濟可行性。
數據要素對于生產系統重構的意義還在于形成智能工廠和智能產品的閉環。依托物理—信息系統,生產數據和消費數據形成大數據系統,經實時分析和數據歸并后形成“智能數據”,再經可視化和交互式處理后,實時向智能工廠反饋產品和工藝的優化方案,從而形成“智能工廠—智能產品—智能數據”的閉環,驅動生產系統智能化。這一切的實現既依賴于數據這一新型生產要素的生成和利用,也依賴于“云設施”的升級與完善。如同資本要素的供給來自于資本積累,勞動要素的供給來自于人口增長和教育,數據要素的供給則依賴于傳感器和高速通訊設施的廣泛應用。因此,在數據要素成為核心投入的過程中,可以廉價獲得的傳感器便是新一輪長波中派生出的核心要素。按照德國“工業4.0”計劃的部署,新型傳感器單價將降至1歐元以下,即便廣泛植入也不會造成使用成本的顯著增加,這可以有效提高數據要素的積累效率。
(二)通信基礎設施的重要性將超過交通基礎設施
核心投入與基礎設施的動態匹配是促進先導產業快速發展的必要條件。歷史經驗表明,核心投入可以廉價獲得是基礎設施快速完善的產業基礎,基礎設施建設的巨大需求為核心投入產業的發展提供初始市場,從而形成正反饋效應。例如,與鐵、煤相匹配的基礎設施是運河和鐵路,與鋼相匹配的基礎設施是鋼軌和鋼船,與石油、天然氣相匹配的基礎設施是高速公路、機場等,與集成電路相匹配的是互聯網。隨著數據要素(及其相派生的傳感器)成為新一輪長波的核心投入,會產生一個新的問題,即第五次長波中形成的基礎設施——互聯網——是否與新興的數據要素相適應?
互聯網發展至今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代互聯網(1969—1989),即軍事和科研阿帕網,主要用于公共部門的內網使用。第二代互聯網(1990—2005),即基于個人計算機的萬維網,刺激了電子商務爆炸式增長。互聯網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時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一是架構靈活性不高,難以適應不斷涌現的新業態的需求;二是難以滿足未來海量數據增長的需求;三是實時性、安全性和靈活性尚不能滿足產業融合發展所需,工業互聯網、能源互聯網、互聯網金融、車聯網等對互聯網的升級提出了強烈且迫切的需求。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互聯網技術正在通過多條技術路線向第三個階段演進。其中,傳統IP網絡向軟件定義網絡(SDN)轉變便是一大趨勢。SDN可實現數據層和控制層的分離,定義和編程網絡設備資源,實時反饋網絡及網絡設施的運行狀態,提高網絡部署的靈活性和穩定性。
當前,新一代互聯網基礎設施對核心要素和先導產業的支撐還遠遠不夠,但已經在加速集聚爆炸式發展所需的資源。首先,在政府層面,美國、歐盟和日本等的公共研究機構立項研究新一代互聯網技術路線,討論和制定新一代互聯網的協議。例如,2011年美國通過了《聯邦政府云戰略》,將聯邦政府1/4(約200億美元)IT支出轉為采購第三方公共云服務;2012年歐盟發布“發揮歐洲云計算潛力”戰略,在各領域推廣云計算的應用。其次,在產業層面,2012年,13家全球主要電信運營商共同發起了網絡功能虛擬化組織,截至2014年10月,已有250家網絡運營商、電信設備供應商、IT設備供應商以及技術供應商參與。另外,2013年全球主要電信設備和軟件公司聯合開發SDN控制器和操作系統。再次,在技術層面,新一代光網絡、新一代無線網絡(5G、Wi-Fi)、物聯網、云計算(云網絡)等網絡基礎設施在硬件設備開發、網絡協議和標準制定、網絡傳輸速度和頻譜利用率提升、功耗和延時降低,以及兼容性、靈活性和安全性提升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進展。最后,新一代互聯網基礎設施在應用層面的潛力逐步顯現。在產業應用層面,2012年全球物聯網市場規模約為1 700億美元,預計2015年將接近3 500億美元,年增長率約25%。2012年全球云計算市場規模達到1 072億美元,預計2017年將達到2 442億美元。在企業應用層面,除了德國企業正在利用物聯網和服務網構建智能工廠之外,谷歌公司數據中心也通過SDN將鏈路平均使用率從30%提升至95%,并于2014年第1季度投入23億美元,采用最新網絡技術構建骨干網,以滿足公司快速增長的需要。在政府應用層面,2014年6月,新加坡推出建設世界首個“智慧國家2025計劃”,為大多數家庭提供超快的1Gbps網速,在線提供98%的政府公共服務。我國政府也提出“互聯網+”,促進互聯網技術更廣泛、更深入地融入到各行各業。[27]
新一代互聯網基礎設施的逐步完善將為數據要素的積累和配置提供有力支撐,同時數據的利用能夠提升新一代互聯網基礎設施的投資收益率,從而形成第六次長波的兩大核心構件。
(三)制造業智能化將發揮先導產業的作用
新一代互聯網技術與制造業融合后,將為制造業的效率提升和價值創造帶來新的機遇。第一,引領產品的智能化和網絡化。“硬件+軟件+網絡互聯”正逐漸成為產品的基本構成,并呈現出個性化和差異化趨勢。智能產品可通過網絡,實時和廠商、第三方服務提供商或上層智能控制平臺通信,拓展產品功能和延伸服務需求。第二,推動生產和管理流程智能化。企業內部制造流程將整合至一個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平臺,各種機器設備和數據信息互聯互通,為優化決策提供支持。制造業的柔性進一步提高,消費者的個性化需求能得到充分滿足。第三,推動研發設計的網絡化協同發展。研發設計部門和生產制造部門的界面信息進一步整合,“虛擬制造”提高研發效率,客戶可通過網絡參與在線設計,融入個性化需求,縮短研發設計周期。第四,推動企業組織變革。不同層面的數據和信息可通過高速網絡便捷傳遞,企業組織進一步扁平化。企業間組織趨于模塊化,最大限度地降低信息成本,重塑產業價值鏈。第五,推動制造業企業服務化轉型。制造過程高度數字化,產品數據全生命周期集成,企業通過互聯網及時獲取消費者需求,從而實現服務型制造,“私人定制”、“按需定制”和“網絡定制”等服務模式將更加普遍。
制造業智能化將為其他領域提供通用技術。第一,在生產端,智能工廠生產的智能化裝備和中間產品是其他產業的投入物。無論是新一代互聯網設施的建設,傳感器價廉量大的供給,還是智能交通、智能電網、智能物流、智能家居等智能系統的建設,都依賴于智能中間品的供給。第二,在消費端,滿足消費者對智能化、個性化產品需求的前提是生產系統的智能化,沒有制造業智能化的商業模式的創新將是空中樓閣。第三,智能制造將對其他產業產生較好的示范效應。以美國通用電氣公司的工業互聯網為例,該公司的新一代GEnx飛機發動機上裝有26個傳感器,以16次/秒的頻率監測300個參數,僅一次長途飛行就可以存儲1.5億份數據,翔實地記錄航班的運行狀態、發動機性能與效率。這些數據被傳送至駕駛室和地面數據中心,經分析后用于監測、預測和改進發動機性能,有效緩解飛機的維修壓力,從而降低航班延誤的損失。僅此一項,每年就可以節約20億美元的成本。
(四)新型生產組織方式的興起
雖然企業內部治理結構的扁平化和企業間網絡不斷增強,但并不表示生產組織方式不會出現“革命性變化”。以數據為核心投入、智能制造為先導部門、新一代互聯網基礎設施為主要內容的新一輪技術經濟范式正在蠶食福特制(及其改進版)的經濟合理性。
零部件的標準化是流水線生產的前提,這就限制了產品的多樣化,導致產品多樣化大幅度減少。之所以出現產品多樣化(個性化)和產量(規模經濟)之間的權衡,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制造業的生產流程投資具有專用性,調整產品種類需要轉換生產線;二是產品零部件標準化程度高,零部件的調整成本高。過高的生產線和零部件轉換成本使得產品調整不經濟。因此,以標準化為核心的福特制雖然提高了生產效率,但是必須支付制造系統柔性低下的機會成本。
以數據為核心投入的新型制造系統具有更高的柔性。
第一,剛性生產系統轉向可重構生產系統,客戶需求管理能力的重要性不斷提升。可重構生產系統以重排、重復利用和更新系統組態或子系統的方式,根據市場需求變化實現快速調試及制造,具有很強的兼容性、靈活性及出色的生產能力,實現生產制造與市場需求之間的動態匹配。例如,德國大眾汽車開發的“模塊化橫向矩陣”實現了在同一生產線上生產所有車型的底盤,可及時根據市場需求的變化靈活調整車型和產能。這一過程表明制造業從產品模塊化演化為生產線模塊化。
第二,大規模生產轉向大規模定制,范圍經濟可能超過規模經濟成為企業的優先競爭策略。[28](P14)可重構生產系統使得大規模定制具備經濟可行性,企業依靠規模經濟降低成本的競爭策略的重要性也將有所下降。未來,滿足消費者個性化需求將取代規模經濟成為企業的主流競爭策略。為此,未來的企業組織將開放更多的接口直接面對消費者。例如,海爾集團進行企業組織的“倒三角”變革和組建以訂單為中心的“自主經營體”就是為了應對這種變化。企業組織正演變為連接用戶和員工的平臺型企業。
第三,企業內部組織結構需要調整,以提高數據要素的附加值。制造業智能化顯著增加了生產的復雜度,對企業管理復雜度的能力也提出了更高要求。為此,企業內部的組織結構,從產品設計、原型開發、企業資源、訂單、生產計劃獲取和執行、物流、能源到營銷、售后服務,都需要按照新的產品價值鏈加以整合。包括:順應制造業服務化的趨勢,提升企業內部支撐制造的服務部門的重要性;順應從提供單一產品到提供一體化的解決方案的趨勢,增強與消費者的互動能力;利用新型基礎設施進行投融資方式和商業模式創新;加大對員工(特別是技術工人)終身學習計劃的投入。
第四,工廠制造轉向社會化制造,產能呈現出分散化的趨勢。企業組織的主要功能是降低生產的信息成本,隨著大量物質流被數字化為信息流,生產組織中的各環節可被無限細分,從而使生產方式碎片化,企業的信息成本大幅度增加,生產出現了“去企業化”,從而呈現出社會化制造的勢頭。目前一些地區出現了專門為網絡設計者、用戶提供制造和產銷服務的在線社區工廠,有效地降低了產業的進入門檻;社交網絡上出現了由個體組成的“虛擬工廠”,個人能夠通過在線交流進行產品的研發、設計、篩選和完善,社會制造這一新型產業組織逐漸形成。[29]這將有利于向全社會疏散產能,有效防范產能的集中和過剩風險,這對深受產能過剩問題困擾的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有重要的意義。
四、結論
本文運用正統的技術經濟范式分析框架梳理了自英國工業革命以來核心投入、先導產業、基礎設施和工業生產組織方式的演進規律,對新一輪產業變革中技術經濟范式可能的演進形態與特征做出展望。新一輪產業變革中涌現出的技術經濟范式的核心構件具有如下特征:數據要素將成為新一輪產業變革的核心投入,數據的分析與利用能力將成為國家之間競爭力的重要決定因素;新型通信基礎設施的重要性或將超過交通基礎設施,信息標準的競爭與合作將成為國際產業分工體系調整的基礎;智能制造仍然是國民經濟體系進步的先導部門,范圍經濟的重要性可與規模經濟比肩,智能制造的發展還將影響服務業的發展層次,重塑產業價值鏈;大規模定制將與當前主流的大規模生產方式分庭抗禮,企業內部結構也必須按照新的價值鏈加以重新整合,企業組織的變革將使生產呈現出平臺化和社會化的趨勢。
我國已經制定頒布了以智能制造為方向、以建設制造強國為戰略目標的《中國制造2025》,這是我國制造業中長期發展的綱領性文件,將對我國制造業的提質升級產生深遠影響。今后我國的產業政策和創新政策宜按照技術經濟范式核心組件的變化規律進行系統性調整,增強各類政策之間的協調性。按照本文的分析框架,要增強我國把握新一輪工業革命的機會窗口的能力,《中國制造2025》仍然有進一步拓展的空間。
首先,要從重視“硬”裝備轉向重視“軟”系統。《中國制造2025》提出國家將引導社會各類資源集聚,推動新一代信息技術、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航天航空裝備、海航工程裝備及高技術船舶、先進軌道交通裝備等十大重點領域突破發展。雖然這些復雜裝備是我國制造業高端化的重點,也是推動我國制造業發展水平整體升級的重要支撐,但相對而言,低估了數據要素在制造業智能化中的核心地位。實際上,長期對數據要素的重視不夠,不僅是我國高端裝備產業發展相對滯后的原因之一,也是影響我國高端裝備產品品質(如產品穩定性)提升的制約因素。更重要的是,對數據要素的輕視不符合制造業智能化的發展趨勢。相比于美國工業互聯網、德國“工業4.0”計劃以數據要素重新定義制造業,發展以“智能裝備+智能軟件+網絡互聯”三位一體的智能制造架構,我國“重裝備、輕軟件”的局限性必將顯現出來,可能在未來的全球價值鏈中處于不利地位。因此,我國需要培育出能提供全流程數字化解決方案的集成企業,加強數據要素的積累和開發利用,促進制造裝備、工藝、產品和服務的智能化。
其次,信息通信基礎設施需要加速升級。我國雖然已經在寬帶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取得了長足發展,社會信息化水平和信息化滲透率等指標都上升較快,但是距離滿足“互聯網+”向各領域融合的需求仍有較大差距,要在網絡傳輸速度、降低網絡能耗和降低數據服務資費方面繼續加強。目前,我國通信基礎設施的發展局限于信息通信技術本身,發展重點著眼于消費領域,對制造業智能化的支撐作用直到最近才開始被關注。通信基礎設施升級是數據要素能廉價且大量供給的必要條件,是制造業智能化的基礎。今后在通信基礎設施升級中應加強信息通信服務商與工業企業的對接,使信息通信服務與企業智能化改造的需求相匹配。同時,在信息通信技術的標準制定方面加強國際合作,以信息通信技術標準的國際合作推動智能制造的國際化發展。
再次,數據要素和新一代互聯網技術向制造業領域的滲透亟須加速。制造業智能化是驅動國民經濟體系智能化的主要驅動力,脫離制造業升級的商業模式創新難以為繼。我國互聯網服務最廣、數據要素積累最多、利用水平較高的是商業服務領域,如百度積累的用戶需求數據、阿里巴巴積累的消費數據和騰訊積累的社交數據。但是,這些在我國互聯網高速發展中涌現出的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互聯網企業尚未將資本、數據、品牌、人才和技術優勢導入制造業領域。應鼓勵這些企業集合各方面的資源,積極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制造業智能化發展之路。
最后,以開放、包容的態度對待生產組織方式的變革。相比于核心要素、基礎設施、主導產業的演變,生產組織方式變革過程中新舊利益集團的斗爭更為激烈。生產組織方式變革過程順利與否,直接影響到技術經濟范式轉變的效率。目前的產業規制和政策形成于上一輪技術經濟范式,過去行之有效的公共政策可能會成為新型產業組織成長的障礙,如產業邊界劃定、行業準入標準、知識產權保護和產業政策等都可能難以與新型生產組織方式相匹配。在這種情況下,應該給予新型生產組織試錯機會,及時調整不合時宜的管制和政策。
[1] 哈巴庫克、波斯坦:《劍橋歐洲經濟史》,第六卷,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
[2] G. Tullock. “Why di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ccur in England”. In Charles K. Rowley, Robert D. Tollison,and Gordon Tullock(eds.).ThePoliticalEconomyofRentSeeking. Boston / Dordrecht / Lancaster: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8.
[3] Acemoglu, D., Johnson, S.,and J. Robinson. “The Rise of Europe: Atlantic Trade,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 2005, 95(3).
[4][13] Freeman, C., and F.Lou??.AsTimeGoesby:TheInformationRevolutionandtheIndustrialRevolutionsinHistoricalPerspectiv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5] Freeman, C., and F.Lou??.AsTimeGoesby:TheInformationRevolutionandtheIndustrialRevolutionsinHistoricalPerspectiv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W. Lazonick.CompetitiveAdvantageontheShopFloo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A. Chander.TheVisibleHand:TheManagerialRevolutioninAmericanBusine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6][18] A. Chander.TheVisibleHand:TheManagerialRevolutioninAmericanBusine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7] Freeman, C., and F.Lou??.AsTimeGoesby:TheInformationRevolutionandtheIndustrialRevolutionsinHistoricalPerspectiv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C. Perez.TechnologicalRevolutionsandFinancialCapital:TheDynamicsofBubblesandGoldenAge.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2002.
[8][24] 賈根良:《第三次工業革命與新型工業化道路的新思維:來自演化經濟學和經濟史的視角》,載《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3(2)。
[9] 蘭德斯:《1750—1914年間西歐的技術變遷與工業發展》,載哈巴庫克、波斯坦:《劍橋歐洲經濟史》,第六卷,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
[10] R. Coase. “The Nature of Firms”.Economica, 1937,4 (16).
[11] Freeman, C., and F.Lou??.AsTimeGoesby:TheInformationRevolutionandtheIndustrialRevolutionsinHistoricalPerspectiv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W. Lazonick.CompetitiveAdvantageontheShopFloo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12] Chandler,A.,and T. Hikino.BigBusinessandtheWealthofNations.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14][15] D. Nye.ElectrifyingAmerica:SocialMeaningsofaNewTechnology. Cambridge: MIT Press,1992.
[16][25][29] Agion, P.,and P. Howitt.EndogenousGrowthTheory. Cambridge: MIT Press, 1998.
[17] A. Chandler.TheVisibleHand:TheManagerialRevolutioninAmericanBusine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Chandler, A., and T. Hikino.BigBusinessandtheWealthofN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9] W. Lazonick.CompetitiveAdvantageontheShopFloo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20] Pisano, G., and W. Shih.ProducingProsperity:WhyAmericaNeedsaManufacturingRenaissance.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 2012; 羅森伯格:《探索黑箱:技術、經濟學和歷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21] T. Ohno.ToyotaProductionSystem:BeyondLarge-ScaleProduction. New York: CRC Press, 1988; T. Fujimoto.TheEvolutionofaManufacturingSystematToyot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22] A. Chandler.ShapingtheIndustrialCentury:TheRemarkableStoryoftheEvolutionoftheModernChemicalandPharmaceuticalIndustri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23] 黃陽華:《德國“工業4.0”計劃及其對我國產業創新的啟示》,載《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5(2)。
[26] 黃陽華、呂鐵:《市場需求與新興產業演進——用戶創新的微觀經濟分析與展望》,載《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3(3)。
[27] 黃陽華、林智、李萌:《“互聯網+”對我國制造業轉型升級的影響》,載《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15(7)。
[28] A. Chandler.ScaleandScope:theDynamicsofIndustrialCapital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責任編輯 武京閩)
A Retrospect of the Evolution of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in Industrial Revolutions and Beyond——An Analysis Based on Kondratiev Long Wave
HUANG Yang-hua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836)
This paper employs the orthodoxy Techno-economic paradigm theory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and brings the currently emerging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back into a two centuries’ glob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proposes that 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would be grounded on established theory by analyzing the co-evolution of core components of in the shift of techno-economic paradigms.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is likely to be an extension period of the 6thtechno-economic paradigm(or the 6thKondratiev long wave)and introduces revolutional changes as follows:data would be a new core input;the significance of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based on new internet technology would exceed traffic infrastructure,and the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based on data and new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is going to build a smart national system.As a consequence,the dominating mass production model is challenged by emerging mass customization and social production.China should move its policy from emphasizing the high-end equipment industries to the utilization of data and upgrading new supportive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and improving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different policies.
industrial revolution;Techno-economic paradigm;long wage;production organization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應急管理項目“技術創新發展對通貨緊縮預期的影響研究”(7154100026);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制造2025’的技術路徑、產業選擇與戰略規劃研究”(15ZDB149)
黃陽華:經濟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北京1008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