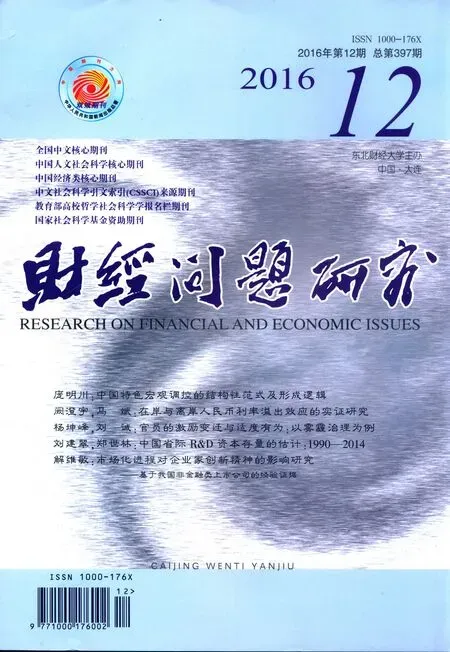中國省際R&D資本存量的估計:1990—2014
劉建翠,鄭世林
(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北京 100732)
·區域經濟·
中國省際R&D資本存量的估計:1990—2014
劉建翠,鄭世林
(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北京 100732)
本文采用永續盤存法,系統地估計了中國31個省級行政單位1990—2014年各年末的R&D資本存量。在估計過程中,對部分R&D內部支出和科技人員勞務費部分缺失數據進行了處理,并對基期R&D資本存量、折舊率和R&D投入價格指數的選擇進行了研究。本文與現有文獻估計的R&D資本存量增長趨勢基本一致,但略微低于現有文獻的估計結果。筆者發現,中國R&D資本存量在1990—2014年間經歷了快速增長,年均增長率為13.66%。但R&D資本存量的省際差異較大,東部地區的R&D資本存量占GDP比重顯著高于中西部地區,而且還有進一步拉大的趨勢。因此,中西部地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路徑之一在于加大R&D投入力度。
R&D資本存量;永續盤存法;經濟增長
一、引 言
近年來,中國提出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奮斗目標,尤其是“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提出之后,研發(R&D)投入呈現迅猛增長趨勢,已從1990年的125.43億元增長到2014年的13 015.63億元,提高了一百多倍;R&D人員數量從1990年的61.71萬人增長到2014年的371.06萬人;R&D支出占GDP的比重由1990年的0.67%提高到2014年的2.05%,超過歐盟28國2014年1.94%的總體占比,但與美國、日本、韓國和瑞典等發達國家相比還有較大差距。R&D積累是生產率增長和財富創造的一個重要因素。R&D活動創造和積累知識,促進產品創新和工藝創新,最終會推動經濟的可持續增長[1],因而R&D資本存量是估計國家和地區經濟增長的重要依據,是研究創新問題的基礎數據,那么,1990年以來中國各地區R&D資本存量積累程度究竟如何?地區之間是否存在R&D資本積累的巨大差距?
國外學者對R&D資本存量的研究始于20世紀60年代,大多數學者對行業R&D資本存量,尤其是制造業的R&D資本存量進行了估算。例如,Griliches[2]測算了美國制造業對生產率增長的作用;Goto和Suzuki[3]估計了日本50個行業的R&D資本存量;Kim和Park[4]估算了韓國制造業28個行業的R&D資本存量;Kwon和Inui[5]利用日本企業的R&D數據,發現高技術企業的R&D資本存量遠遠高于非高技術企業;Hu等[6]采用中國大中型制造業企業的面板數據,研究了中國R&D產出彈性;Bernstein和Manuneas[7]研究了美國和加拿大制造業的R&D資本存量增長情況及其對TFP增長的貢獻,發現隨著R&D投入的增長,R&D資本存量對TFP增長的貢獻也在提高。2009年,聯合國統計委員會公布的國民經濟核算標準(SNA2008)規定,R&D支出作為固定資產放在固定資本形成下,這為估算R&D資本存量提供了依據。
相比之下,中國學者對R&D資本存量的研究只有近十年的歷史,分為:全國層面上,對不同時段R&D資本存量的估計[8-9];行業層面上,對行業R&D資本存量的估計[10-11];區域層面上,對不同時段內各省級行政單位(以下簡稱“各省份”)R&D資本存量的估計[12-13]。這些估計結果得到的相同結論是區域之間差異較大,東部區域具有明顯的優勢;不同之處是計算結果差異較大。主要是因為參數選擇有差異,基礎數據和采用的基期不一致,計算的R&D資本存量差異較大。
在借鑒和參照現有文獻的基礎上,本文估算了中國各省份1990—2014年的R&D資本存量。與現有研究相比,本文的主要貢獻如下:鑒于R&D投入中的勞務費也是增加值的一部分,為了避免重復計算,將扣除勞務費后的R&D投入作為計算R&D資本存量的當期R&D投入;對折舊率的處理不僅考慮了資產性支出和日常支出的區別,還考慮了資產性支出中設備和儀器及其他資產性支出的差異;現有文獻都對折舊率統一取值,但本文根據各省份R&D投入的發展程度進行分時段取值,這種做法使得估計結果更可靠;將中國省際R&D資本存量延長到1990—2014年,相對余泳澤等[13]一文,筆者補充估算了1990—1997年的缺失數據,并匹配了R&D投入的估算范圍,使得本文的估算結果具有較強的連續性,為后續估計R&D資本存量、經濟增長來源分解和科技進步貢獻率等相關研究提供準確和客觀的基礎數據。
二、R&D資本存量的估算方法、變量估計和數據處理
(一)R&D資本存量的估算方法
關于如何估算R&D資本存量,學界并沒有明確的統一方法,鑒于估算物質資本存量的一般方法是永續盤存法,本文也沿用永續盤存法進行估算,其基本公式為:
(1)
其中,Ct和Ct-1分別表示第t年和第t-1年的R&D資本存量,Rt-i表示t-i期的R&D投入(不變價),i表示滯后期,βi表示Rt-i支出的滯后貼現系數,δt表示資本存量第t年的折舊率。對于R&D投入的滯后期,多數學者采取Griliches[14]的建議,即滯后1年,R&D資本存量估算公式為:
Ct=Rt-1+(1-δ)Ct-1
(2)
從式(2)可以看出,估算R&D資本存量需要對當期R&D投入、基期R&D資本存量、R&D投入價格指數和折舊率進行確定。
(二)變量估計和數據處理
1.當期R&D投入
本文數據來源于《中國科技統計年鑒》和各省份的統計年鑒,由于浙江和上海公布了1990—1997年的R&D投入數據,還有部分省份公布了某一年度的R&D投入數據,因而不需要估算。為了詳細反映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各省份創新能力的增長,本文使用不同企事業單位的R&D投入數據來估計1990—1997年各省份的R&D投入數據。在1990—1997年《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中僅給出了各省份大中型工業企業、研究與開發機構和高等學校的R&D經費內部支出額,這三者的合計明顯小于全部R&D投入。根據中國R&D經費的統計范圍和包含的內容發現,1990—1997年缺失的數據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企業的R&D支出扣除大中型工業企業支出后的數據,另一個是R&D支出中的其他部分。本文根據1990—1997年缺失的兩部分合計數占全國R&D支出的比重,估算各省份的R&D投入數據。R&D支出的估算公式為:
RDit=(IRDit+RRDit+CRDit)/(1-πt)
(3)
式(3)中,RD表示1990—1997年包括勞務費的R&D投入,IRD表示大中型工業企業的R&D投入,RRD表示研究與開發機構的R&D投入,CRD表示高等學校的R&D投入,π表示企業的R&D支出扣除大中型工業企業支出的數值與R&D支出中其他部分的合計數占全部R&D經費的比重。
1998—2014年各省份R&D投入來自1999—2015年的《中國科技統計年鑒》。鑒于R&D投入中的勞務費也是增加值的一部分,為避免重復計算,本文將扣除勞務費后的R&D投入作為計算R&D資本存量的當期R&D投入。此外,由于《中國科技統計年鑒》只公布了2009年以來各省份R&D投入中的人員勞務費,因而1990—2008年各省份人員勞務費占R&D投入比重采取2009—2014年各省份的平均數,以此估算應該扣除人員勞務費的數據。各省份扣除勞務費的R&D投入計算公式為:
Rit=RDit×(1-μi)
(4)
式(4)中,R表示扣除勞務費后的R&D投入,RD表示沒有扣除勞務費的R&D投入,μ表示勞務費占R&D投入的比重。
余永澤[13]用的是1990年全國R&D投入和1998—2000年各省份R&D投入平均占比來估計1990年各省份R&D投入,依據是這3年各省份R&D投入增長較為均勻。但現實情況是這3年R&D投入增長并不均勻,R&D投入的穩定增長出現在2005年以后。1990年各省份大中型工業企業、研究與開發機構和高等學校的R&D經費內部支出額的合計數大于1990年全國的R&D投入數值;2004年以前,各省份R&D投入的合計數大于全國R&D投入的數值。用全國的R&D投入數據計算各省份的數據并不恰當,且各地的發展速度不同,用1998—2000年的平均比重代替1990年的比重并不合適。使用余永澤[13]的方法計算的數據與筆者計算的數據相比有較大差異。如浙江、上海和安徽,用余永澤[13]的方法計算的結果高于實際投入的數據,原因在于經過近十年的發展,R&D投入有了較大提高,用1998—2000年的平均比重計算1990年的數值將會偏高。如青海,用余永澤[13]的方法計算的結果低于實際投入的數據,原因在于青海的R&D投入增長速度低于全國平均水平,造成這些地區根據余永澤[13]的方法計算結果偏低。
2.基期R&D資本存量
對于基期的確定,由于中國各省份的R&D投入數據公布年份始于1998年,部分學者確定基期為1997年、1998年或2000年,為了擴大后續問題的研究樣本,本文將基期定為1990年,并將不變價格設定為1990年不變價。
目前有兩種常見的使用永續盤存法來估計基期R&D資本存量的做法:一種方法是假定基期R&D資本存量的平均增長率等于R&D投入的平均增長率,是由Griliches[14]提出、多數學者采取的方法。另一種方法是假定在穩定增長的狀態下,R&D資本存量與經濟總量存在正向相關關系,基于此求出基期的R&D資本存量。鑒于20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處于轉軌時期,R&D投入并沒有穩定增長,顯然采取第二種方法不合適,故本文采取第一種方法,基期R&D資本存量的計算方法如下:
(5)
式(5)的θ表示R&D投入R的增長率。當t=1時,C1=(1+θ)C0。根據式(2),當t=1時,C1=R1+(1-δ)C0。根據上式,可以得到計算基期R&D資本存量的公式為:
C0=R1/(δ+θ)
(6)
3.R&D投入價格指數
R&D投入價格指數的構造對估算R&D資本存量影響巨大。鑒于目前沒有統一的標準,不同文獻構造的R&D價格指數不同,從而造成R&D資本存量存在很大差異。關于R&D投入價格指數的設定,大部分學者選取不同名目的價格指數和權重進行加權平均,如工資價格指數[15]、GNP價格指數[16]、消費物價指數[17]、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11]、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18]、原材料價格指數[13]等。大部分學者采用主觀設定的方法確定權重,而李向東等[11]與朱有為和徐康寧[18]根據對應名目占R&D投入的比重作為權重,比較客觀。本文R&D投入已不包括勞動力成本,故采用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和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來構造R&D投入的價格指數,對于部分省份某一年度缺失的數據用全國平均數代替,2009年以前的數據使用2009—2014年的平均數代替,以各省份R&D投入中資產性支出占比為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的權重,其他支出占R&D投入的比重是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的權重。各省份價格指數的計算公式為:
RDPIit=INVPIit×(INVit/RDit)+CMPIit×(CMit/RDit)
(7)
式(7)中,RDPI表示R&D綜合指數,INVPI表示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CMPI表示居民消費價格指數,INV表示R&D投入中資產性投入,CM表示其他日常費用。鑒于2009年以前沒有詳細的分類數據,余永澤[13]用科技活動經費的內部比重代替,但筆者認為科技活動經費的內部比重與R&D投入的內部比重是有區別的,尤其是涉及到各省份時。因此,本文使用2009—2014年R&D投入的平均內部支出代替2009年以前的內部支出更為合理。
4.折舊率
與物質資本不同的是,知識的擴散和傳播使得知識專用性不斷下降[19],尤其是在知識經濟下,知識的傳播和擴散速度遠遠大于信息不發達的年代,因而普遍認為R&D資本的折舊率一般應高于物質資本的折舊率。但對于折舊率的取值幾何,目前學者們沒有一致的意見,例如Griliches[14]采用的固定折舊率是15%,Bosworth[20]通過計算專利凈收益,估計的折舊率是9.91%—15.31%。Goto和Suzuki[3]使用專利產生收益時間長度的反函數來確定各個行業的折舊率在7.5%—24.6%之間。國內學者采用的折舊率也不盡相同,吳延兵[10]、謝蘭云[12]用的是15%,劉建翠等[9]用的是10%和15%。
考慮到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和經濟發展程度不同的地區,資本的更新速度不同,即折舊率不同,本文根據31個省份R&D投入的快慢程度采用了不同的折舊率。在20世紀90年代,各地區的R&D投入較低,屬于知識積累階段,折舊率一般來說會比較低;進入到21世紀,信息化和知識經濟不僅提高了知識的傳播和更新速度,也同時促進了技術的更新換代,折舊率提高是必然的。為此需要估算兩個階段的折舊率。葉宗裕[21]估計1993年建筑安裝類和機器設備類的折舊率分別為7.86%和19.7%,1994—2008年建筑安裝類和機器設備類折舊率,每年分別遞增0.04%和0.02%,則2005年建筑安裝類和機器設備類的折舊率分別為8.32%和19.94%。本文采取葉宗裕[21]1993年和2005年的建筑安裝類和機器設備類的折舊率估算兩個階段的資產性支出的折舊率,各省份資產性支出的折舊率計算公式為:
INVDPit=D1t×(FAit/INVit)+D2t×(EQit/INVit)
(8)
式(8)中,INVDP表示資產性支出的折舊率,D1表示資產性支出中非儀器和設備的折舊率,兩個階段的取值分別是7.86%和8.32%,D2表示儀器和設備的折舊率,兩個階段的取值分別是19.7%和19.94%,FA表示資產性支出中非儀器和設備的支出,EQ表示儀器和設備的支出。
計算R&D投入的折舊率,資產性支出部分的折舊率采用式(10)計算的數值,其他非資產性日常支出采用通用20%的折舊率[13]。各省份R&D投入的折舊率計算公式為:
RDDPit=INVDPit×(INVit/RDit)+20%×(CMit/RDit)
(9)
式(9)中,RDDP表示R&D投入的折舊率。用式(8)和式(9)計算的折舊率與謝蘭云[12]的最大不同在于沒有采取固定折舊率,考慮了時間的異質性。2009年以前缺少的R&D投入內部支出比重采用2009—2014年R&D投入的平均內部支出代替。
本文計算的折舊率與余永澤[13]的區別在于,一是本文根據R&D投入的增長情況劃分了兩個階段,二是關于資產性支出,本文區分了儀器和設備與非儀器和設備,余永澤[13]認為資產性投入80%以上為儀器和設備投入,采取黃勇峰等[22]估算出的設備經濟折舊率17%,事實上,2009—2014年資產性投入中儀器和設備所占的比重區間是52.42%—98.82%,與余永澤[13]的說法出入較大,而黃勇峰等[22]估算出的設備經濟折舊率是中國制造業的設備折舊率,與全社會的設備折舊率是有差別的,且計算區間是1985—1995年,與余永澤[13]的計算周期有時間差。基于以上原因,本文所計算的折舊率與余永澤[13]計算的折舊率有所不同。
三、計算結果和分析
本文計算了中國各省份1990—2014年的R&D資本存量,表1是部分典型年份各省份及三大地區的R&D資本存量和年均增長率。

表1 典型年份各省份及三大地區R&D資本存量和年均增長率(1990=1) 單位:億元,%
注:東部地區有11個省份,分別是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和海南;中部地區有8個省份,分別是山西、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區有12個省份,分別是四川、重慶、貴州、云南、西藏、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廣西和內蒙古。
從全國來看,1990—2014年中國R&D資本存量經歷了跨越式發展,1990年R&D資本存量僅為452.17億元,2014年就達到了9 883.01億元,年均增長率高達13.66%,遠遠高于GDP不到10%的增長率。中國R&D資本存量高速增長,不僅與市場中企業注重通過R&D投入取得競爭優勢有關,也與中央乃至地方政府通過項目體制方式,資助高校、科研機構、企業和學者的R&D活動相關[23]。
(一)各省份之間的比較分析
各省份的R&D資本存量絕對數和增長率差異較大,分布很不均衡,區域差異非常明顯,基本呈現從東向西逐步遞減的趨勢,與中國的經濟發展特征基本吻合。2014年,北京、江蘇、山東、廣東和上海等5個省份的R&D資本存量占全國的48.92%,接近R&D資本存量的“半壁江山”;廣西、內蒙古、云南、甘肅、貴州、寧夏、新疆、青海、海南和西藏等10個省份R&D資本存量占全國的比重只有4.60%。經濟發展快速的地區,R&D資本存量增長較快,例如,浙江的年均增長率是23.22%,而全國年均增長率只有13.66%。
東部地區的優勢更加明顯,且不斷擴大;中部地區的湖北和西部地區的四川、陜西是區域的R&D活動中心。這與王孟欣[24]的計算結果相似。除了北京和上海,其余省份在20世紀90年代R&D資本存量增長較慢,1990年和2000年的R&D資本存量分布更為接近。各地區R&D資本存量的迅速增長發生在21世紀,尤其是2005年以來,國家先后提出增強創新能力及建設創新型國家,把自主創新納入到“十一五”規劃和《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以后,各地區的R&D投入迅速增長,R&D資本存量也就迅速增加。
本文對各省份R&D資本存量進行聚類分析,將31個省份分為4類。第一類是北京、江蘇和山東,2014年R&D資本存量分別達到1 152.63、1 127.98和1 011.66億元,占全國總量的比重分別是11.66%、11.41%和10.24%。北京作為中國的首都,不僅聚集了中國最多的具有頂尖科研水平的高校和科研機構,還有大量的高科技企業,是創新能力與R&D投入較高的地區。江蘇和山東在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始終位于全國前3名,強大的經濟實力成為R&D投入的堅強后盾。第二類包括廣東、上海和浙江等3個省份。2014年,這些地區的R&D資本存量均超過600億元,占全國比重均超過6.51%。3個省份都處于東部沿海地區,是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創新能力和競爭力較強,屬于中國創新活動的重點地區,是建設國家創新體系不可或缺的部分。第三類包括遼寧、湖北、四川、陜西、天津和河南等6個省份,2014年R&D資本存量均超過300億元,占全國比重均大于3.03%。在這些省份中,遼寧是東北部區域R&D的活動中心,是東北老工業基地的中心;湖北是中部區域R&D的活動中心,也是全國理工科院校的聚集地之一;四川集中了西南區域的主要高校;陜西集中了西北區域的主要高校。建國初期的三線建設也把主要的科技資本投入到湖北、四川和陜西,因而這些省份均成為各自區域的R&D活動中心。天津作為直轄市之一,隨著《京津冀都市圈區域規劃》和《京津冀協同發展綱要》的實施,天津經濟快速發展,R&D投入也有較大的提高。第四類包括其余19個省份,大多數處于中西部區域,經濟基礎弱,發展相對落后,R&D經費投入較少,R&D資本存量也較低。因此,這些地區的R&D活動相對較弱,需要R&D活動強的地區帶動。
(二)三大地區之間的分析
三大地區R&D資本存量占GDP比例的總趨勢是先下降后上升。在不同的年份,各地區的比重變化較大,尤其是中西部地區。中部地區R&D資本存量占GDP的比重在1990—2011年期間一直是最低的,2012年開始高于西部地區;1993—2003年期間,西部地區的R&D資本存量占GDP的比重一度是最高的,此后處于波動狀態,2010年才開始上升。一定程度上,各個地區R&D資本存量的巨大差距是不同區域之間創新能力懸殊的關鍵。實施創新驅動戰略,倡導“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有助于推動中國經濟結構調整、打造發展新引擎、增強發展新動力、走創新驅動發展道路。但“雙創”不僅需要創新精神也需要充足的R&D投入。
通過比較從業人員人均萬元R&D資本存量的均值來看,東部地區R&D資本存量的均值在1990—2014年整個區間內均高于其他地區R&D資本存量的均值,1990—2007年間,西部地區人均萬元R&D資本存量高于中部地區數值。在20世紀90年代,東部地區R&D資本存量的均值高于其他地區和全國的均值;全國平均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區;中西部地區非常接近。進入21世紀后,東部地區R&D資本存量的均值迅速增長,遠遠高于其他地區的均值,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差距拉大始于2007年,建設創新型國家戰略提出后,全國的均值位于東部和中部地區的均值之間,與東部地區的均值差距也越來越大。從業人員人均R&D資本存量的差異在一定程度上再次說明了R&D投入的高低與創新的密切關系,也說明了三大區域之間創新程度產生差距的根源。
四、與現有結果比較分析及其拓展
為了驗證本文計算結果的合理性,本文將計算結果與現有研究結果進行了比較分析。從計算結果看,唯一相同的一點是,各省份間資本存量的差距較大,增長速度亦有差距。
根據肖敏和謝富紀[25]、謝蘭云[12]、王孟欣[24]和本文計算的數據,本文選取2006年的數據,從絕對數、相對數進行分析,*因為肖敏、謝蘭云和王孟欣的計算周期分別是2000—2006年、2000—2006年和1998—2007年,本文計算周期是1990—2014年,便于比較選取2006年的數據。并分析增長趨勢。第一,肖敏和謝富紀[25]、謝蘭云[12]計算的基期相同,可以對絕對數進行分析。因為,科技經費籌集額是R&D投入的2—2.3倍,計算的R&D資本存量顯然大于用R&D支出數計算的R&D資本存量,謝蘭云[12]的計算結果是肖敏和謝富紀[25]計算結果的1.7—3.9倍,顯然是因為謝蘭云[12]使用科技經費籌集額計算R&D資本存量,過高地估計了各省份的R&D資本存量,影響進一步利用R&D資本存量對創新的研究結果。第二,從各省份R&D資本存量占總量的比重看,雖然有差別但不是很大,尤其是西部地區。第三,用31個省份的平均值比較增長趨勢。謝蘭云[12]的計算結果增長迅速,肖敏和謝富紀[25]、王孟欣[24]的計算結果趨勢基本一致,在計算周期中,先期是緩慢增長,后期是較快增長,本文的計算結果是在20世紀90年代緩慢增長,2005年后迅速增長,這是因為2005年國家頒布了多項科技創新政策,地區的R&D投入開始穩步快速增長。
造成以上差異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五點:一是本文計算的基期是1990年(價格基準為1990年),王孟欣[24]的計算基期是1998年(價格基準為1995年),肖敏和謝富紀[25]、謝蘭云[12]計算的基期是2000年(價格基準為2000年),這導致相同年份的R&D資本存量存在較大差異。二是包含的內容有差別。本文的R&D資本存量不包括人力資本,其余三者的R&D資本存量包括人力資本,謝蘭云[12]以科技經費籌集額作為R&D支出,遠遠大于現有統計體系下的R&D支出數。三是折舊率存在差異,肖敏和謝富紀[25]、謝蘭云[12]的折舊率是15%,王孟欣[24]在東、中、西三大地區采取了不同的折舊率,分別是18%、15%和12%,本文按照R&D投入的內部比重計算了兩個時間段的折舊率,不僅具有時間上的異質性,還具有區域上的異質性,其依據是在長時期、不穩定的經濟發展中,資本的折舊率不是一成不變的。四是價格指數的構造不同。肖敏和謝富紀[25]、王孟欣[24]使用各省份GDP平減指數作為R&D投入的價格指數,謝蘭云[12]使用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固定資產價格指數和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構造價格指數,三者的權重是勞務費、原材料費和固定資產購建費在科技經費籌集額中的比重。本文使用固定資產價格指數和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構造價格指數,二者的權重是資產性支出和日常性支出在R&D投入中的比重。五是本文計算了1990—2014年各省份的R&D資本存量,時間序列更長,并匹配了R&D投入的估算范圍,使得本文的估算結果具有較強的連續性。這為研究各省份經濟增長與R&D投入的關系、技術創新的源泉和經濟增長質量等提供了更為科學可靠的基礎數據。
肖敏和謝富紀[25]是最早計算各省份R&D資本存量的學者,此后有學者開始估算區域R&D資本存量,肖敏和謝富紀[25]在理論和應用兩方面推動了區域R&D資本存量的估算;謝蘭云[12]的價格權重處理方法考慮了時間和區域的異質性,為R&D投入價格指數的構造提供了新思路,區別于以前學者采取固定的參數;本文對折舊率的處理不僅考慮了資產性支出和日常支出的區別,還考慮了資產性支出中設備和儀器及其他資產性支出的差異,這種處理方法比余永澤[13]的處理方法更為細致合理。謝蘭云[12]以科技經費籌集額作為R&D支出計算R&D資本存量,計算結果偏大不可避免。
五、結 論
本文通過拓展各省份R&D投入數據序列,使用永續盤存法估算了中國31個省份R&D資本存量,估計結果顯示:中國仍有較大R&D投入空間,持續R&D投入對實現創新驅動戰略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長期以來,固定資本投入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并表現出粗放經濟增長模式的特征。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科技創新是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必須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雖然中國R&D資本存量在1990—2014年經歷了快速提升,但與發達國家R&D投入相比仍存在較大差距。OECD數據顯示,2013年美國的R&D投入強度為2.74%,2014年德國、日本和韓國的R&D投入強度分別為2.84%、3.58%和4.29%,不僅遠遠高于中國的R&D投入強度,甚至高于《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設定的到2020年達到2.5%的目標。因此,中國仍有較大的R&D投入空間。通過各地區持續增加R&D投入,對于提高中國自主創新能力,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突破資源、能源和環境的制約具有重要作用。
[1] 吳延兵.中國工業R&D產出彈性測算(1993-2002)[J].經濟學(季刊),2008,(3):869-890.
[2] Griliches,Z. R&D and Productivity: Measurement Issues and Econometric Results[J].Science, New Series, 1987,237(4810): 31-35.
[3] Goto,A.,Suzuki,K. R&D Capital, Rate of Return on R&D Investment and Spillover of R&D in Japa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89, 71(4):555-564.
[4] Kim,T., Park,C. R&D, Trade,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Korean Manufacturing[J].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2003,139(3):460-483.
[5] Kwon, H., Inui,T. R&D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Japanese Manufacturing Firms[R].ESRI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NO.44, 2003.
[6] Hu, A. G.Z., Jefferson, G.H. ,Qian, J.C.R&D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Firm-Level Evidence From Chinese Industry [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05, 87(4): 780-786.
[7] Bernstein,J.,Mamuneas,T.P.Depreciation Estimation, R&D Capital Stock, and North American Manufacturing Productivity Growth[J]. Annales Déconomie Et De Statistique,2005,(79-80):383-404.
[8] 嚴成樑,龔六堂.R&D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測度[J].投資研究,2014,(1):13-23.
[9] 劉建翠,鄭世林,汪亞楠.中國研發(R&D)資本存量估計:1978-2013[J].經濟與管理研究,2015(2):18-25.
[10] 吳延兵.R&D存量、知識函數與生產效率[J].經濟學(季刊),2006,(7):1129-1156.
[11] 李向東,李南,白俊紅,等.高技術產業研發創新效率分析[J].中國軟科學,2011,(2):52-61.
[12] 謝蘭云.中國省份研究與開發( R&D)指數及其存量的計算[J].西安財經學院學報,2010,(4):65-71.
[13] 余泳澤.中國區域創新活動的“協同效應”與“擠占效應”[J].中國工業經濟,2015,(10):37-52.
[14] Griliches, Z.R&D and the Productivity Slowdown[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0,70 (1):343-348.
[15] Jaffe,S.A. A Price Index for Deflation of Academic R&D Expenditure[R].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 72-310 , 1972.
[16] Loeb, P.D., Lin, V.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Specification Error Approach [J].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1977, 26(1):45-51.
[17] 朱平芳,徐偉民.政府的科技激勵政策對大中型工業企業、R&D投入及其專利產出的影響[J].經濟研究,2003,(6):45-53.
[18] 朱有為,徐康寧.中國高技術產業研發效率的實證研究[J].中國工業經濟,2006,(11):38-45.
[19] Pakes, A.,Schankerman, M. The Rate of Obsolescence of Knowledge , Research Gestation Lags and the Private Rate of Return to Research Resources[R]. NBER Working Paper,1979.
[20] Bosworth,D.The Rate of Obsolescence of Technical Knowledge——A Note[J].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1978, 26(3):273-279.
[21] 葉宗裕.中國資本存量再估算:1952-2008[J].統計信息論壇,2010,(7):36-41.
[22] 黃勇峰,任若恩,劉曉生.中國制造業資本存量永續盤存法估計[J].經濟學(季刊),2002,(2):376-396.
[23] 鄭世林,周黎安.政府專項項目體制與中國企業自主創新[J]. 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5,(12):73-89.
[24] 王孟欣.我國區域R&D資本存量的測算[J].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1):84-88.
[25] 肖敏,謝富紀.我國R&D資本存量的空間分布特征[J].科技管理研究,2009,(8):435-436,439.
(責任編輯:鄧 菁)
2016-10-02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工程項目“科技戰略與科技政策研究和評價”;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互聯網基礎設施對中國經濟發展及公民政治參與的影響”(71573272);中宣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重大項目“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與‘雙創’研究”(2015YZD03)
劉建翠(1971-),女,山東萊蕪人,副研究員,博士,主要從事技術經濟分析、投入產出和生產率等方面的研究。E-mail:liujc@cass.org.cn鄭世林(1975-),男,山東日照人,副研究員,博士,主要從事技術經濟分析與政策等方面的研究。E-mail:zhengsl@cass.org.cn
F224
A
1000-176X(2016)12-010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