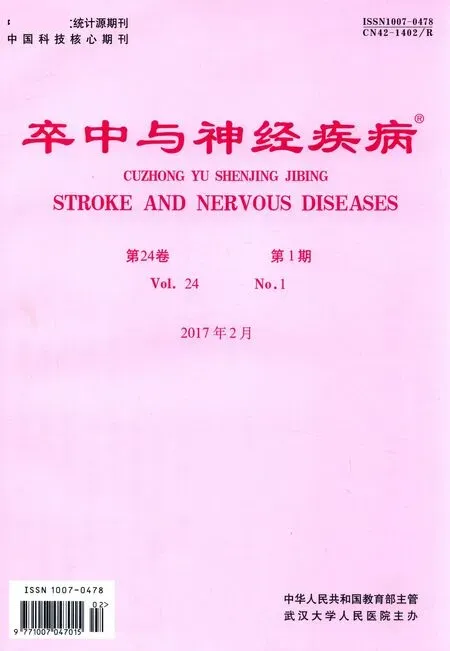帕金森病診療策略-從循證醫學到精準醫學
孟憲月 李雪莉
?
帕金森病診療策略-從循證醫學到精準醫學
孟憲月 李雪莉
帕金森病作為僅次于阿爾茨海默病之后的第二大神經退行性疾病,近年來的流行病學調查顯示其發病率及致死率不斷升高,由于其早期臨床表現不易察覺,確診該病時已到達疾病的晚期階段,因此該病對家庭及社會均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1]。病理學研究證實,由a-突觸核蛋白及泛素等構成的路易小體(Lewy-bodies)異常積聚于黑質多巴胺能神經元的胞質內,通過誘導神經元的凋亡,最終產生靜止性震顫、肌強直、運動遲緩、步態異常等相應的臨床表現[2]。清除胞內異常積聚的異常蛋白,終止多巴胺神經元的凋亡成為帕金森病治療的關鍵。
1 帕金森病治療的現狀
目前臨床用于帕金森病治療措施主要包括(1)藥物治療包括多巴胺替代療法、多巴胺受體激動劑、抗膽堿能制劑、單胺氧化酶抑制劑等在內的神經保護治療依然是所有治療方式中的首選;(2)外科手術治療包括神經核團毀損術、DBS(腦深部電刺激術);(3)干細胞移植。人臍血間充質干細胞、誘導多能干細胞、脂肪細胞、人視網膜色素上皮細胞等;(4)神經營養因子、神經免疫調節因子的移植治療[3-4]。目前針對帕金森病的病因研究仍處于探索階段,以上各種治療方式雖可緩解患者的臨床癥狀,但不能阻止帕金森病的進展。如何在臨床診療過程中對帕金森病患者做到精準化、個體化,在病理水平上終止甚至逆轉該病的進程成為今后研究的熱點。
2 帕金森病與精準化診療
現階段,廣大的神經內科醫生對帕金森病的診療依舊停留于循證醫學的階段,基于患者的臨床表現,結合醫生的診療經驗,輔以相應的實驗室檢測指標,對患者進行相應的治療。帕金森病早期非運動癥狀的出現極易導致對該病產生模糊的診斷、分期及治療,延誤患者最佳的治療時機。近年來,隨著基因組學、蛋白組學、海量數據處理的計算機技術等學科的發展,對大樣本人群和特定疾病的生物標記物進行分析與鑒定,精確尋找產生疾病的病因與治療靶點,最終實現對患者的精準化治療[5]。2015年美國總統奧巴馬總統”精準醫學計劃”的提出,掀開了新醫學時代的序幕。隨著精準醫學在癌癥及基因突變等疾病領域內的發展,廣大的神經內科醫生也終將促使帕金森病的診療、預防邁入精準醫學的時代,為帕金森患者帶去福音。
2.1 綜合風險評估-帕金森病的預防
風險評估的實施主要為根據現階段已闡明的機制,針對高危人群進行篩查并早期給予有效的干預措施。現階段已有部分帕金森病的致病因素得到證實,致病基因與環境因素(工業或農業毒素,如殺蟲劑、異喹啉等化合物)的長期作用或許可導致帕金森病的發生。早期對高危人群(有家族史、長期暴露于工農業毒素環境中等)進行選擇性的篩查[6],同時對其罹患帕金森病的概率進行預測,加強對該類帕金森病高危人群的監管與隨訪,消除潛在的致病風險,在降低帕金森發病率的同時減輕該病對家庭及社會帶來的負擔[7]。
2.2 通過合適的方式尋找潛在的致病因素-帕金森病的診斷
基因突變常被人們認為是帕金森病發病的重要因素,然而研究發現某些突變基因(LRRK2、SNCA、PARK、HTRA2、PINK1等)攜帶者終生也未出現帕金森病的臨床表現[8]。因此,我們在疾病診斷過程中不僅要關注突變的基因,同時可利用功能基因組學、蛋白組學等學科對引起基因突變的潛在病理生理的改變進行更深層次的探討。分子病理學的快速發展為帕金森病的分期奠定堅實基礎,與以往神經內科醫師憑借臨床經驗判定分期不同,其利用流式細胞術、熒光原位雜交、免疫組化等多種方法對帕金森病進行精確分期。精準醫學要求我們今后對帕金森病的診斷需在循證醫學的基礎之上聯合基因組學、蛋白組學、分子病理學、功能神經影像學等[9],對帕金森病做到精確診斷,精確臨床分期,從而指導日后進行相應的臨床治療。
2.3 針對不同個體的病理改變進行干預-帕金森病的治療
帕金森病目前的治療措施依舊停留在外源性補充左旋多巴、拮抗膽堿能神經元活性等方面的緩解治療,干細胞移植及外科手術治療雖彌補了藥物治療的不足,但均不能阻止疾病的最終結局,成為目前帕金森病治療的瓶頸[10]。在腫瘤患者治療過程中對于同一TNM分期的同一腫瘤選用相同的治療方法獲得的臨床收益不盡相同。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帕金森病的治療過程中,處于同一時期的不同患者對美多巴的作用療效千差萬別,這說明神經內科醫師借助眾多的量表與自身的臨床經驗所確定的臨床分期并不能滿足臨床治療。
基于對帕金森病分子水平的研究發現,不同的帕金森病患者在分子水平上的表現截然不同,現階段我們的治療主要建立于循證醫學基礎上,緩解帕金森病患者的運動癥狀。精準醫學在腫瘤治療方面取得的成功引導對帕金森病的治療也步入“靶向治療”的時代,其中靶向作用于a-突觸核蛋白的單克隆抗體成為目前研究的熱點,通過內吞機制進入血腦屏障后誘導異常聚集的蛋白遷徙至自噬小體。 隨著我們對帕金森病在分子水平上探討的逐漸深入,我們堅信針對不同帕金森病患者精準化醫療的臨床時代終將到來。
3 精準化醫療在我國帕金森病臨床應用中面臨的問題
3.1 大數據處理VS小樣本難題
隨著二代基因測序的飛速發展,目前人們僅需花費幾千元就可獲知自己的遺傳密碼,該技術的發展為現代精準醫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然而,人類整個基因組是復雜的,現階段針對基因組中非編碼基因的探索仍處于起步階段,非編碼基因之間的相互作用及其對蛋白表達的調控異常復雜,或許只有獲取整個基因組內所有密碼子的功能才會使人們對精準醫學有更加深刻、更加準確的認識。發展精準醫學離不開對大數據的整合與處理,但或許同是帕金森病患者,但其基因突變發生在不同的位點上(如引發a-突觸蛋白產生的點突變基因包括A30P、E46K、A53T、H50Q、G51D等)[11-12],因此對于這樣一個樣本來講,雖然我們可以獲得該組帕金森病患者的大數據,然而真正相同的樣本量少之又少。這樣就導致在疾病的治療方面產生了矛盾,我們寄希望于同種藥物或治療手段可以治愈盡可能多的患者,但同時又要兼顧到個體化差異,這要求我們要加強在大數據處理過程中對該事件的平衡能力, 盡可能使數據的代表性達到最高。
3.2 精準醫療在帕金森病診治過程中的建立、整合、運行、監督
(1)以基因檢測為例,帕金森病患者需不需要進行基因檢測?這需要臨床醫師與專業的基因檢測人員溝通協商后確定,避免冗長多余的檢查給患者帶來不必要的經濟負擔;(2)精準醫學需要處理大量的臨床數據。目前大多數的神經內科醫師對分子生物學的檢測結果與帕金森病之間的相互關系無法給患者做出詳盡的解答,對帕金森病高危人群不能準確預測疾病發生的概率,這也就最終導致無法針對患者的檢測信息,對其“量身定做”制定相應的治療方案;(3)精準醫學的目標在于對疾病進行精確診斷。在恰當的時機對疾病進行精確干預,改變當前神經內科醫師根據自身經驗選取藥物的治療模式,對帕金森病患者無疑帶來顯著的社會效益。但目前的制藥企業依舊是傾向于受眾范圍較廣的新藥,對于受眾范圍較窄、回報程度不高且風險性較大的靶向藥物何時能夠上市依舊是個未知數[13];(4)精準醫學所帶來的倫理問題同樣不容忽視。如何確保自身遺傳信息的安全性?遺傳信息數據庫如何監管?或許只有國家通過完善的立法及監管措施才能確保遺傳信息數據的保密性、安全性與共享性,才能調動眾多的帕金森病患者積極主動地提供自身遺傳信息,參與到精準醫學的研究中來[14]。
精準醫學的發展必將對未來帕金森病的治療帶來深刻的變革,伴隨著精準醫學理念的不斷深入、基因組學及蛋白組學技術的發展,對帕金森病患者及其高危人群的診斷、治療、預防、隨訪等方面終將做到人性化,精準化!
[1] Murray CJ,Atkinson K,Bhalla G,et al.The state of US health,1999~2010:burden of diseases,injuries,and risk factors[J].JAMA,2013,310(6):591-608.
[2] Lees AJ,Hardy J,Revesz T.Parkinson's disease[J].Lancet,2009,373(9680):2055-2066.
[3] Faberqvist T,Bergstrom J,Lannfelt L,et al.Immunotherapy targeting a-synuclein,with relevance for future treatment of Parkinson's disease and other Lewy body diso-rders[J].Immunotherapy,2014,6(2):141-153.
[4] Rascol O,Lozano A,Stern M,et al.Milestones in parkinson's disease therapeutics[J].Movement Disorders,2011,26(6):1072-1082.
[5] 焦怡琳,王吉春,何廣學.中國在精準醫學領域面臨的機遇與挑戰[J].中國公共衛生管理,2015,31(5):601-603.
[6] Goldman SM.Environmental toxins and Parkinson's disease[J].Annu.Rev.Phannacol.Toxicol,2014,54(3):141-164.
[7] Montine TJ,Montine KS.Precision medicine:Clarity for the clinical and biological c-omplexity of Alzheimer's and Parkinson[J].s diseases.J.Exp.Med,2015,212(5):601-605.
[8] Verstraeten A,Theuns J,Broeckhoven CV.Progress in unraveling the genetic etiol-ogy of Parkinson disease in a genomic era[J].Trends Genet,2015,31(3):140-149.
[9] Roe CM,Fagan E,Grant J,et al.Amyloid imaging and CSF biomarkers in predicti-ng cognitive impairment up 2 to 7.5 years later[J].Neurology,2013,80(19):1784-1791.
[10]Strauss I,Kalia SK,Lozano AM.Where are we with surgical therapies for Parkinso-n's disease? [J].Parkinsonism Relat Disord,2014,20(1):187-191.
[11]Kiely AP,Asi YT,Kara E,et al.Alpha-synucleinopathy associated with G51D SNCA mutation:a Link between Parkinson's disease and multiple system atrophy? [J].Acta Neur-oPatbol,2013,125(5):753-769.
[12]Appel-Cresswell S,Vilarino-Guell C,Encarnacion M,et al.Alpha-synuclein p[J].H50Q,a novel pathogenic mutation for Parkinson's disease.Mov.Disord,2013,28(6):811-813.
[13]趙曉宇,刁天喜,高云華,等.標題為空[J].“精準醫學計劃”解讀與思考.軍事醫學,2015,39(4):241-244.
[14]楊煥明.對奧巴馬版“精準醫學”的“精準”解讀[J].西安交通大學學報,2015,36(6):721-723.
(2016-05-20收稿)
252000 山東聊城市,泰山醫學院聊城臨床學院/聊城市人民醫院神經內科[孟憲月 李雪莉(通信作者)]
R742.5
A
1007-0478(2017)01-0078-02
10.3969/j.issn.1007-0478.2017.01.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