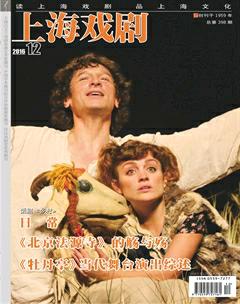湯顯祖的兩種“自在”之間
黃銳爍

在戲初和終場時,湯顯祖外在呈現出了相似的狀態——半臥在低案上、賞著放置在臺前的金魚缸——十分自在的模樣。但在這兩種看似相像的狀態之間,是長達九十分鐘的進退兩難和長吁短嘆,因此,內里的兩種“自在”被區分:前者是強作歡顏,后者是此生無夢。主創對湯顯祖辭官歸鄉后人生狀態的一次觀察與演繹,有了切題的落點。
得益于湯顯祖逝世四百周年的契機,各式有關湯顯祖的紀念活動、展覽、演出層出不窮。萬歷年間湯顯祖寫成“四夢”“幾令《西廂》減價”,常演不衰,但以湯顯祖作為主角的戲劇,至今仍然罕見。我們知道清人蔣士銓曾作《臨川夢》,敷演湯顯祖“一生大節,不邇權貴”,其間穿插因讀《牡丹亭》抑郁西去的俞二娘與“四夢”中人的故事。但自《臨川夢》后,這種表達幾乎絕跡。今年借著紀念湯顯祖的東風,就筆者目之所及,出現了兩部類似的作品,一部是上海音樂學院主創的音樂劇《湯顯祖》,另一部則是本文要論及的《枕上無夢》。
看得出來,《枕上無夢》的主創為創作這部作品做了大量的功課,其探究邊緣甚至觸碰到了學術的領域。就編劇而言,其對“臨川四夢”有著屬于自己的明確認知,編劇將“四夢”視為湯翁一生的精神寫照:第一階段充滿希望(《紫釵記》)、第二階段不甘失望(《牡丹亭》)、第三階段痛苦絕望(《南柯記》)、第四階段超脫出原來的范疇,去往了另一個方向(《邯鄲記》)。且不論這種總結是否片面,編劇都尋得了“四夢”中的四個引路人——黃衫客、胡判官、契玄禪師、呂洞賓——暫且忽略了前兩夢的言情本質,找到了理解湯顯祖的另一個入口——在入世與出世之間徘徊的精神困境。
循著這種思路,《枕上無夢》的故事發生在湯顯祖辭官歸鄉期間,彼時湯先生百無聊賴,寫戲抒情,樂得一份真假難辨的“自在”。全戲基本演繹了三件事:一是知己好友吳序勸其出仕;二是湯先生萌發出家之念為夫人所斷;三是湯先生長子湯士蘧之死。與《臨川夢》和音樂劇《湯顯祖》類似,“四夢”中人在慣常思維的引導下被充分穿插在主要情節之中。相對而言,《枕上無夢》對戲中人闖入現實的處理較為有創意:除湯先生外,此戲寫了四個真實人物——湯友吳序、湯妻傅氏、湯翁三子湯開遠與長子湯士蘧,這四個真實人物還同時在戲中扮演“四夢”中人——湯開遠為黃衫客、湯士蘧為胡判官、傅氏為契玄禪師、吳序為呂洞賓。四人分著梔黃、赤紅、素白、青綠四色衣服,有戲上臺,無戲則靜坐舞臺兩側。
就這樣,現實與虛境構建起全戲的基本結構,工整且清晰。吳序以棋道勸湯先生出仕,引出黃衫客;湯先生出家之念被夫人所斷,引出契玄禪師;湯士蘧猝死南京,引出胡判官;湯先生萬念俱灰,引出呂洞賓。全戲三個基本事件,俱是湯先生入世與出世之困境思索。與吳序下棋,一番唇槍舌劍,辯明了湯先生的堅持與對世道的失望;起出家之念,為夫人所斷,了然俗世也是一種道場,夫人也可以是他的菩薩;長子猝死南京,連寄望也徹底了斷,終于遁入精神自由之境,獲得了真正的自在,此生再無夢。
《枕上無夢》在現實中的三個基本事件,各有亮點,也各有瑕疵。與吳序以棋論道,寫出了難分對錯的兩種價值觀的碰撞。吳序認為湯先生既然歸鄉之后仍協助地方官員修建文昌橋,有志于造福百姓,何不成就更大的功德,前往安徽拜會許國,以求重回政壇,成大事者不拘小節。但湯先生一生不事權貴,當年五次科舉因不事張居正而不得都不曾低頭,此刻更是難以從命。一番爭論如同棋盤上的黑白棋子,看似水火不容,但二人畢竟是知己,告別之際,仍存惺惺相惜之心,君子和而不同。黑白二色看似涇渭分明,終究也融于同一棋盤之上。起出家之念被夫人所斷,寫出了湯妻傅氏的大智慧與豁達。受達觀和尚的度化,湯先生萌生了出家之念,這一段直指湯先生的逃避心理——他竟欲拋家棄子避世而去。傅氏一番言語,令其了然俗世也可修行,心之所靜,處處都是道場,夫人傅氏也可成為他的菩薩。這一段落寫出了一種言不由衷,夫妻二人臥于梅樹之下,談的是陳年情事,心里想的卻是別離,戲劇張力全在言辭與舉手投足之間,及至夫人一番澄澈的言語,方將湯先生度化至一個直面的境界。湯士蘧猝死南京一段,以夢的方式呈現,見了匠心,也呼應了湯先生的一生多“夢”。湯先生在書房中做了一夢,夢見湯士蘧從南京歸來找父親解惑,他不明白為何父親不愿出仕卻對其寄予厚望。湯先生答以父子二人性格畢竟不像,自己人情世故一竅不通,但兒子人情練達、處世通透。夢醒,南京傳信,湯士蘧猝死了。此一節矮案搭建的書案成了奈何橋,湯先生送了兒子一程又一程,叫人幾分感慨、幾分心酸。
我們對戲的不滿足之處,也確實是頗令主創為難之處。三個基本事件,其一僅憑了大量的臺詞進行辯論,將劇場變成了一個辯論場,失了戲的張力。其實只要辯論內容足夠精彩曲折,互占上風,甚至以戲謔方式互擊對方痛處,原本也是無妨,但觀此段,仍因不夠吸引人而覺得冗長;其二同樣憑借大量的臺詞推進,可因有內外兩層情緒的交互,令人感覺曲折有趣,耐人尋味。如果說有什么瑕疵,那就是夫妻二人的情感狀態,稍嫌過于“偶像劇”而失卻生活質感了。這是一對中年夫妻,且多次經歷喪子喪女之痛,桃樹雖佳,但秋之蕭條二人絕非可以忘卻;其三則是情感節制的問題了,湯先生奈何橋上送子,確實是可以大加渲染的段落,但如若沒有足夠的情感能量支撐,原本令人心酸落淚的段落,也因無法點到為止容易覺得冗長。
主創塑造了一個什么樣的湯先生呢?從文獻資料中,我們得知,湯先生清瘦。此一說有湯先生友人虞淳熙的《徐文長集序》為證,虞在此書中以湯先生的“小銳”同徐渭的“頎偉”相對照。湯先生也在其詩文《三十七》中自述道“清羸故多疾”。但我們在舞臺上看到的,是一個中等身材略胖的湯先生,像是我們可以想象的一個常年久坐的編劇會有的樣子。他著灰黑二色衣服,舉手投足之間帶著濃重的文人氣。作為父親,他十分慈愛,作為丈夫,也算得上體貼。這樣的湯先生,是讓人信服的。但問題恰恰出在這里,如若將湯先生與“響當當一粒銅豌豆”的關漢卿作比較,前者令我們敬而難親,后者卻讓我們恨不能與其把酒言歡、逍遙度日。這或許正是前人罕將湯先生入戲的原因之一。因此,我們可以講,寫湯顯祖太難了,從文獻中,我們太難讀出他身上的“煙火氣”,他的形象也不知道在何時變得符號化而失卻了可以入戲的鮮活,正如清傳奇《臨川夢》就直接將其塑造成了一個“忠孝兩全”之人。面對這樣的湯先生,入了戲,骨氣可有,哲思可有,詩意可有,但戲劇的行動和作為人本身的缺點,卻寥寥難尋。《枕上無夢》的主創似乎也沒有勇氣或者說沒有意圖去構建一個讓人可以親近的可愛的湯先生,這也就造成了前文我們對這個戲的不滿足之處——人設。
在三個現實的基本事件之外,穿插“四夢”中人,作為書中人物,這必然令此戲來到一個有別于現實空間的虛境。在這個空間里,主創的選擇仍然不是行動,而是湯先生與自我內心的對話。這本無可厚非,但在現實事件已然像極了外化的自我問答之后,再重疊以相似的段落,這讓全戲波瀾不大,吸引力有所減弱。“四夢”中人,令我們較有記憶點的是黃衫客和胡判官。前者在湯先生的自我拷問下成為一個“廢人”:一個管得了戲中事但解不了現實難的“廢人”;后者借著湯士蘧之死,生發出了連胡判官都無法逆轉生死的徹底悲涼與戲劇高潮。相對而言,契玄禪師與呂洞賓的塑造就弱了一些。
《枕上無夢》充滿了中國元素,鋪滿舞臺的草席延伸至布景成幾扇錯落有致的屏風,屏風后橫亙一簡練的樹枝,上掛戲中道具若干。臺邊除了四個金魚缸之外,還有十分古典的方紙燈。全戲主要道具為八方矮案,靈活變換拼用,時而是書案,時而構建出庭院空間,時而成為奈何橋。由此可見,導演也有著十分明確的追求——古典的簡約寫意。但不得不提及的是,有三處元素的運用,對這種寫意是破壞了的。第一是金魚缸,方形透明玻璃固然可以讓觀眾看清金魚,但終覺格格不入,且前面的地燈直接投在玻璃上,反光嚴重;第二是庭院一段,桃花飄落,本是美境,但舞臺上空制造花瓣飄落的鼓風機并不爭氣,風吹數秒,停,再吹數秒,花瓣飄落一陣一陣,節奏感讓人感覺過于人工,失卻自然;第三是煙霧機的聲音過大,在聽覺上,較為嚴重地破壞了觀眾對戲的關注。
從導演到演員,我們可以見到對于所謂“中國學派”的追求。但何謂“中國學派”?戲曲化的身段?古典的布景?時空虛實的靈動變幻?從外入內是路徑之一,這點我們不可否認,主創的嘗試也不應被否定。但“中國學派”是一個太大的命題,焦菊隱先生在數十年前做出了自己的嘗試,繼承者寥寥,難見有效持續的嘗試。筆者拙見,“中國學派”首先應當是一種精神,一種足以構建起中國舞臺意象及美學的獨特的戲劇精神。在近幾年西方戲劇強勢涌入中國,我們對于“中國學派”的思考與持續嘗試,應當被鼓勵,但同時也應當被質疑,如若“中國學派”僅能表達古典題材,那它于今何益?“中國學派”所倡導的寫意舞臺與美學,如何實現與現代性的對接?在精神上,注重“時間性”與“天人感應”的“中國學派”,可以像《茶館》那樣橫跨數個時代,可以像《竇娥冤》那樣借了天地的力量去表達個體生命的情感,但在現當代它的土壤有多深厚?我們仍然相信嗎?有趣的是,在今年烏鎮戲劇節上,我在日本戲劇《櫻之園》的內內外外看到了這種精神的流淌,此戲也成為戲劇人所追捧的對象。那么我們中國戲劇中的這種精神,可見的有多少呢?言之難盡,但總而言之,我們正處于湯先生兩種“自在”之間的階段,雖難免迷茫、進退兩難,但吾輩之探索,不可荒廢。《枕上無夢》的主創借此戲為我們探索了“中國學派”的一種可能性,但更多的可能性,需要更多有志于此的戲劇人去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