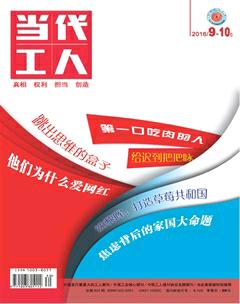外交憤青,毀了宋朝毀明朝
袁南生
“憤青”雖是現代詞匯,但“憤青”現象卻古已有之,不絕于史。自宋以來,產生了一種新的國民心態——清流心態,深刻影響了中國外交的走向。千年外交史上的“憤青”現象,無論是古是今,一味主戰,誰主張和,誰就是賣國。也一味主張強硬,遇有談判,不顧自身實力和對方訴求,漫天要價,獅子大開口,視任何妥協為軟弱。
憤青提案 大軍覆沒
蒙古崛起之后,雖然多次戰勝金國,但終究無法消滅金國,只得尋求與南宋合作。如果當時南宋對蒙古的滅金戰爭選擇不作為,至少可以贏得30年的準備時間。然而,靖康之恥激起的全國性的仇金情緒,造成南宋外交戰略失誤。雖然當時有清醒之人反對,但很快被彌漫全國的仇恨所淹沒。
目光短淺的宋朝君臣把宋朝與蒙古聯合滅金看作是報靖康之恥、建立不朽功業的天賜良機。為誘使宋朝聯合蒙古滅金,蒙古答應滅金后將河南歸還宋朝。于是,宋朝軍隊兩萬人在大將孟珙率領下,攜帶盟約規定饋贈給蒙古軍隊的糧秣30萬石相助。金國滅亡后,南宋如愿分得了一部分領土。
事情本可到此為止,遺憾的是,南宋并不滿足于分得的土地。一個“憤青”提出了著名的“據關阻河,光復三京”北伐蒙古議案。意思是趁蒙古在中原立足未穩,把蒙古人趕到黃河以北,再以重兵防御潼關—黃河一線,與蒙古隔河而治。南宋朝野被這封不切實際的奏折深深打動,不懂軍事的文人們紛紛主戰,不顧滅金戰爭中同蒙古并肩作戰的將領們的反對,終于走出了錯誤的一步,南宋大軍北伐蒙古。結果北伐大軍全軍覆沒,蒙古三路大軍南下,南宋滅亡。
在南宋滅亡前的德佑元年正月,文武百官只有6位大臣出現在朝堂上。當初那些主戰的“憤青”們,全部逃亡,只丟下小皇帝和謝太后孤兒寡母加上6個大臣一共8個人。《二十四史》中如是曰:“南宋啟釁,自招入侵。”可見“憤青”之誤國。
錯失4次機會 煤山上吊尋死
崇禎帝勤政廉政,怎么會落得個亡國上吊的下場呢?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被“憤青”現象所綁架。老天爺曾給崇禎4次機會,哪怕抓住一次,他就可能不必上吊。
第一次機會是封后金(清)首領為王。努爾哈赤一直希望明廷封其為王,以號令東北各少數民族。其實,封王的做法在明朝并非無先例,但這樣做明朝需要付出代價,即承認后金(清)實體的存在,劃出地區供其統治。這雖然損害了明統治者的威望,卻可以平息戰火,安定遼東,國家減輕困擾,而保持明朝“天朝大國”的地位不變。無奈滿朝文武之中,持這種見解的人少之又少,而且不敢公開說出來。
第二次機會是與清軍議和,分界而治。松錦失守之后,崇禎便想和清軍議和,以便專心對付李自成起義軍。兵部尚書陳新甲暗中與皇帝籌劃講和,但他因為著急上朝議事,就將信件隨手放在幾案之上,他的書童誤以為是“塘報”,未請示陳新甲就拿出去交給各部門傳抄。這一下可惹了大禍,很多大臣紛紛上書彈劾陳新甲貪生怕死、妥協求全、私定議和條款。崇禎皇帝迫于壓力,下令將陳新甲處死。崇禎帝這樣做雖然保全了面子,卻又一次關上了本是由他授意打開的議和大門。一次本來很有成效的議和,一次可以改寫歷史的救國良機,表面上是因為崇禎皇帝死要帝王的面子和陳新甲的不謹慎導致最終草草收場,實質上是朝廷內外為“憤青”的思維定式和輿論所綁架。
第三次機會是遷都。李自成大軍挺進山西,兩個月就可攻進北京,形勢瞬息萬變。大臣李明睿建議南遷,他認為,只要向南進行戰略轉移,就能緩過氣來。咱們大明的條件比那時強多了,地方比它大,物產比它豐富,關鍵是祖宗當年遷都北京時,設南京為陪都,有一套完整的行政體系在。
誰知,宰相陳演反對南遷,故意把消息捅出去,弄得沸沸揚揚,謠言四起,人心大亂。絕大多數官員和“憤青”們站在一起堅決反對南遷,為什么呢?因為士大夫階層長期被正統教育洗腦,堅信撤退可恥,在政治上是錯誤的;加上如果南遷,官員們的美宅良田不可能帶走,丟了北京還不知便宜誰。
官員們唱高調唱了一個多月,李自成大軍此時已攻下了居庸關和昌平,北京危殆。
第四次機會是與李自成議和。李自成本對迅速的勝利毫無思想準備,也不太清楚進了北京意味著什么。當年3月17日都打到今北京城的復興門一帶了,他居然在次日上午給崇禎寫信,要求割讓西北一帶給他,西北實行高度自治,不向朝廷報告工作;朝廷撥付100萬銀兩慰問金給他,他替朝廷打擊敵對勢力,包括虎視眈眈的東北清軍。
然而大臣們個個慷慨陳詞,調子一個比一個高,要與北京共存亡。李自成送的大禮,根本不在明朝最后一次御前會議的議題之內。
崇禎本想趁著夜色混出城去逃命,但是從安定門、朝陽門到前門,沒有一個門為他打開。眼看天要亮了,只好孤獨地走向了煤山……他死后僅3個小時,李自成拍馬直搗金鑾殿。那些政治堅定、慷慨激昂的部長們血戰到底了嗎?第二天他們就去李自成辦公室外,排隊請求安排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