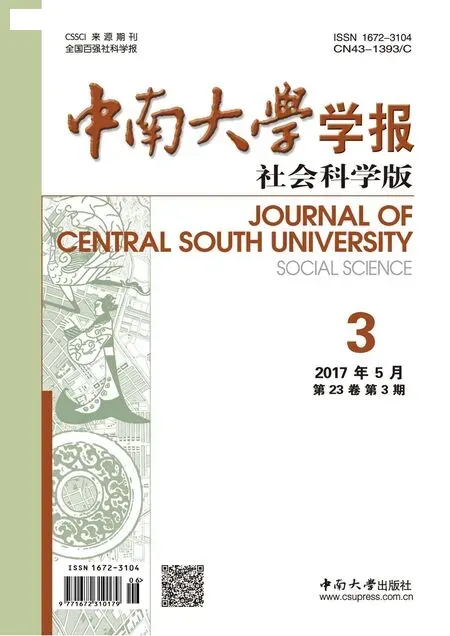TPP環境條款創新對我國締約工作的啟示
馮光
?
TPP環境條款創新對我國締約工作的啟示
馮光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北京,100872)
由環境問題引發投資仲裁的核心是對東道國行使“政府管理權”合法性的判斷。文章闡述了《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在環保制度上的創新:明確了“環境法”的定義、東道國調整環境法規的主權權利,規定了公眾參與、締約國磋商和爭端解決制度,重新平衡了東道國政府管理權和投資者利益的關系。針對我國在環境條款的使用上缺少標準和實踐的現狀,從環境保護制度設計的角度,建議在締約工作中明確多邊環境公約的效力、環境法的定義、公眾參與制度和爭端的東道國司法解決優先效力。
《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環境條款;國際投資協定;政府管理權
自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環境保護成為國際社會的熱點問題,迄今這一熱點沒有任何降溫的趨勢。《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以下稱TPP)總結了國際社會涉及環境方面的締約實踐,將環境保護的標準進一步提高。聯合國大會于2015年9月通過了《改變我們的世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以下稱2030議程),推動在全球范圍內進一步促進可持續發展的全面落實,其中很多內容都與環境保護有關。我國“十三五”規劃的很多內容與2030議程不謀而合,因此國務院統一組織了2030議程在中國的全面落實工作,這表明環境問題已經成為推動我國發展、幫助我國謀求國際規則制定話語權的重要問題。此外,近年來與環境問題有關的爭端有增無減,這方面的國際司法實踐因此不斷發展,與此有關的國際法規則也開始有了新的發展。正如Merrill案裁決中所說,“習慣國際法并沒有凍結,它一直伴隨國際社會的現實情況在發展”①。事實上,不斷發展的并不僅僅是習慣國際法,《國際法院規約》第38條規定的整個國際法淵源所涵蓋的領域都在伴隨著國際社會的現實情況不斷發展。
《國際投資協定》(,以下稱IIA)在誕生之初的核心目的并不包含環境保護等與可持續發展有關的問題,其目的僅僅是為了保護投資的安全與收益[1]。IIAs中環境保護義務是伴隨著全球生態危機和環境保護意識的增強而逐漸出現的[1],尤其是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以下稱NAFTA)簽訂之后。但當時的環境保護在締約目的中也屬于從屬性的,缺乏與投資保護之間關系的明確定位,缺乏有效的涉及環境問題的爭端解決機制。隨著環保問題的日益嚴重,與環境相關聯的各類投資仲裁案件日漸增多,仲裁庭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對東道國新制定的環境法規是否違反IIAs中的投資保護義務進行裁定,其核心是:在條約規定不明確的情況下通過法律的適用過程劃定東道國為保護公共利益而正當行使政府管理權(police power)的界限。這種現狀促使主要投資輸出國開始考慮對IIAs中的環境保護條款進行系統性的升級調整。這也是TPP的環境制度設計希望解決的主要問題。
長期以來,由于法律制度的不完善、締約權的分散和條約審核工作的力量有限,我國的對外締約一直處于一種各自為政的分散狀態。條約締結工作缺乏有力的統一管理,對于國際法發展的規律、相關領域核心法律原則的發展規律缺少統一的研究和認知,導致條約締結缺少應有的延續性和制度創新。本文擬從TPP的環境制度設計出發,分析其環境制度及誕生的背景,并在總結多年來我國條約締結實踐的基礎上兩相比較,對我國下一步的締約工作提出適當的建議。
一、TPP的環境保護制度
從本質上講,環境保護與投資保護的沖突是人類經濟發展對于自然資源的無節制索取與生態環境供給能力有限的矛盾所引發的必然。其沖突核心是環境保護重要性的日漸凸顯,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過程中逐漸超越了“經濟發展”和“投資自由化”的重要性,使得之前并未出現交集的兩個因素在實踐中產生了碰撞。其涉及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東道國基于公共利益的政府管理權行使與國際法中原有投資保護義務之間的關系平衡。TPP的環境保護制度設計是美國反思NAFTA生效后一系列投資仲裁案件暴露出的問題后采取的應對措施[2]。
(一)TPP環境保護制度設計的背景——政府管理權的合法性之爭
國際法確認了國家對于國內資源開采、利用和保護的主權權利,但這一權利的行使必然會影響到已經存在的投資,這種影響在何種范圍內是合理的、必需的、可以免責的,則是國際法領域尚未完全厘清的一個問題。這也是環境保護與投資保護沖突的利益焦點。
由于早期的IIAs在簽訂時并沒有考慮環境保護的問題,而國際環境法的發展又給主權國家施加了保護環境的義務,因此,當國家行使政府管理權對國內環境法律、法規、政策進行調整時不可避免地與原有保護投資的義務產生沖突。在解決這一沖突的過程中,最為核心的一個問題就是政府管理權行使的合法性判斷標準。究其原因是,如果政府管理權的行使是為公共目的、合理的、非歧視的、公平的[3],那么其行為構成違反公平公正待遇、征收的可能性就幾乎沒有,因而也就不需要承擔國家責任。NAFTA之后一系列投資仲裁不但將這一沖突推至公眾視野,同時也為標準的設定提供了可供參考的寶貴實踐。
1. 問題的緣起——Metalclad案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有關政府管理權邊界問題的探討并非是從Metalclad案開始的。1922年美國最高法院判決的Pennsylvania Coal Co. v. Mahon案對管理性措施是否能夠構成征收已經有了探討②,但Metalclad案對政府管理權邊界的探討是與環境保護有關的投資仲裁中比較典型的。
Metalclad Corp是一家美國的垃圾處理企業,該公司在墨西哥設立了一家有害廢棄物處理工廠。Metalclad公司聲稱,其設立該工廠的原因是墨西哥官員承諾除地方政府的一份特別授權外,該工廠的設立和運轉無需政府的特別許可。但墨西哥地方政府拒絕了許可的頒發,Metalclad公司以此為由啟動了根據NAFTA第11章的仲裁程序。在仲裁程序啟動后,當地政府頒布了一項環境法令,將工廠所在區域列為了環境保護區③。
該案仲裁庭認為墨西哥地方政府拒絕頒發許可的行為構成了對公平公正待遇(NAFTA第1105條)的違反,進而構成了征收(NAFTA第1110條),而政府頒布的環境法令也違反了NAFTA第1110條,構成征收。仲裁庭認為,征收不僅包括財產所有權的轉移,還包含“對財產權的干預導致事實上剝奪了財產所有人合理的經濟利益預期的全部或大部分”③。雖然后來法院駁回了仲裁庭關于墨西哥地方政府拒絕頒發許可的行為違反NAFTA義務的裁定,但仲裁庭有關地方政府環境法令性質的認定得到了保留。
該案仲裁庭的裁決受到了多方的批評,特別是有關政府管理權行使的方面。批評意見尖銳地指出Metalclad案的裁決嚴重限制了NAFTA成員國保護其環境、勞工標準和公共健康的能力,甚至有學者認為該案將NAFTA變成了三個成員國之上的“超憲法”機構[3]。從仲裁庭的裁決可以看出,仲裁庭完全沒有考慮政府管理權問題,沒有考慮為保護公共目的和非歧視的法律、法規、政策的制定可以不構成對公平公正待遇的違反和征收。
2. 新的平衡點——Methanex案
Metalclad案裁決留下的質疑在5年后迎來了答復。Methanex案是加拿大Methanex公司與美國政府之間的糾紛。該公司是全球最大的methanol(甲醇)的生產商,該產品是汽油添加劑MTBE的主要生產原料。由于MTBE被測出滲入了加利福尼亞州的地下水源,并對當地居民的身體健康造成威脅,加州政府頒布法令禁止了MTBE在加州的生產和銷售。這一禁令導致Methanex幾乎被完全擠出加州市場,該公司以此為由申請仲裁庭認定加州政府的該項禁令構成征收。
Methanex案的仲裁庭在裁決中完全棄用了Metalclad案仲裁庭使用的推理方法。仲裁庭認為,在國際法上基于公共目的、經由正當程序制定的、非歧視的法律法規不能被認為是征收并對其導致的損失進行賠償,除非政府之前作出過相反的特別承諾。④從該案仲裁庭的推論內容可以看出,仲裁庭將公共目的、正當程序和非歧視作為判定政府管理權行使是否構成對NAFTA條約義務違反的因素。雖然在考量因素的設定上并不完善,但該案的裁決體現出一種新的趨勢,即在政府管理權的行使與投資保護之間達成一種新的平衡,以兼顧雙方的利益需求。
遺憾的是,該案的判決完全沒有考慮NAFTA第1110條有關征收問題四個要素之間的互相連接。由于該條規定的最后一個要素是提供賠償,因此有觀點認為只有在四個要素全部滿足的情況下,一項政府管理性措施才不構成征收。仲裁庭在裁決中并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僅通過論證管理性措施的合法性就排除了構成征收的可能性,從而割裂了第1110條的整體邏輯性,因此該案裁決除了結論正確之外一無是處[4]。
盡管批評意見尖銳而強烈,但出于對東道國管理權的尊重以及環境問題的突出重要性,后來的很多案件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Methanex案對于環境保護與投資保護之間重新平衡的態度。
3. 爭論的繼續
無論如何Methanex案的裁決為仲裁庭平衡環境保護與投資保護的關系做了一次好的嘗試,同時也提供了新的思考方法。S.D.Myers案在其裁決中就認為,對于政府管理權的行使(是否構成征收)就應當在“將國家實踐、條約以及國際法案例對其進行的司法解釋視作整體”⑤的情況下進行思考。在另外一個案件Fireman’s Fund vs.Mexico的裁決中,仲裁庭列舉出了15個在作出政府管理權行使是否構成征收的決定時應當考慮的因素[3],包括了Methanex案和S.D.Myers案提出的各種考量因素,也包括善意等一系列新的 因素。
關于政府管理權邊界的討論在國際法上的實質是探討其行使的結果,即頒布的管理性措施是否違反國際法。從目前的實踐看,主要涉及是否違反公平公正待遇和征收的有關國際法。在具體的判斷上,每個案件的仲裁庭都有自己的標準。雖然后續案件在裁決的大方向上大同小異,但在細節上卻千差萬別。出于統一判斷標準,限制仲裁庭對有關國際法原則進行隨意解釋的情況,NAFTA項下北美自由貿易委員會(Free Trade Commission,以下稱FTC)曾經在2001年7月31日發布了有關第1105條具有約束力的解釋的通知,明確了第1105條規定的公平公正待遇等同于習慣國際法中的最低標準待遇,并要求仲裁庭放棄使用擴展的解釋適用方法。但是,該解釋并沒有起到真正的效果。原因一是該解釋僅對涉及NAFTA第1105條的問題進行了限定,并明確與“政府管理權”行使有關的內容;二是在該解釋頒布不久,就有仲裁庭明確拒絕了它的適用。
正如前文所述,環境保護與投資保護之間的沖突實際上是政府管理權與投資者利益之間的沖突,在國際法原則層面上則表現為對違反公平公正待遇和征收的構成要素的探討與變革。雖然政府管理權這一概念在法律領域由來已久,但其在國際投資仲裁領域的探討卻依然在進行,而且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可能都不會形成共識。不久前的Glaims Gold⑥案就拋棄了Methanex案以后有關這一理論的所有發展,回歸到最早的Neer案的標準來判斷國家責任的構成。雖然該案廣受詬病,但其體現出的不同法律觀點的交鋒的確值得重視和深思。正是因為仲裁庭在標準適用上的不統一,TPP的有關條款才嘗試對政府管理權的行使進行了規定,并設立了相應的判斷標準,比如“善意”,同時對“環境法”的范圍進行了定義。
(二)TPP環境條款的創新
TPP中有關環境保護的內容主要體現在:序言部分、第1章、第9章和第20章“環境”。其中,序言、第1章和第9章闡述了TPP環境保護的目標、環境與投資的關系以及多邊環境公約與TPP的效力關系,這三點內容自NAFTA以來已經成為IIAs締結過程中反復出現的常規內容,在許多此類條約中均可以看到實例,TPP在此的進步僅僅是將有關內容變得更為細致,創新之處并不多。TPP真正獨樹一幟的是第20章“環境”,其整個環境保護法律制度圍繞對政府管理權合法性的規范而進行的改進集中體現在這里。
1. 明確了定義、目標和締約方調整環境法律和政策的“主權權利”
NAFTA生效后,根據其相關條款提起的涉及環境問題的投資仲裁案件有很多,包括但不限于Ethyl案、S.D. Myers案、Metalclad案、Methanex案、MTBE案、Tecmed案、Glaims Gold案、Waste Management案等。前文論述過幾個典型案例關注的政府管理權行使的合法性問題,而討論這一問題的前提是締約方制定、采取或修改其環境法律、法規和政策的主權權利并沒有在條約中得到明確的確認,也沒有明確“環境法”在條約里的概念和覆蓋的國內立法范圍。
為了盡可能地避免上述情況的重演,在第20章前三條中,TPP明確了“環境法”的定義,確立了“高水平的環境保護和環境法律的有效實施”的目標,并對締約方“制定、采取或修改其環境法律和政策的主權權利”進行了確認。雖然此次環境法的定義排除了“勞工安全和健康直接相關的或首要目的為管理自然資源的生存或土著居民收獲的”法律、法規或其中的條款,但終究還是為明確“環境法”的概念作出了條約實踐中的有益嘗試。而明確了締約方“制定、采取或修改其環境法律和政策的主權權利”,意味著為締約方制定和調整有關環境保護的管理性措施提供了清晰的條約法依據。上述兩條內容為解決此類國際糾紛鋪平了道路。第2條確立的“高水平的環境保護和環境法律的有效實施”的目標則會為TPP約文的解釋提供更有利于環境保護的依據。因此,上述三條內容結合起來相當于明確了締約方調整有關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和政策空間,最大可能地消除了管理性措施制定和實施過程中的模糊地帶。
結合附件9B第3款b項規定的不構成間接征收的管理性行為,包括“旨在并用于保護公共健康、安全和環境等合法公共福利目標的非歧視性管理行為”,意味著在“環境法”定義下包含的法律法規的調整和適用基本上被排除了構成國家責任的可能。
2. 設立公眾參與制度,規定了程序事項
TPP第20章第7—11條規定了公眾參與的制度和有關程序事項,為個人和其他締約方就環境保護問題提出申訴設計了渠道。該部分內容要求締約方應保證相關信息向“公眾公開”,并要求締約方為利益相關人設置申訴渠道。同時,TPP要求締約方對“實施本章信息的請求予以考慮”。這條規定本身并未對主體資格進行限制,因此可以理解為“個人”有權利依據TPP申請締約方公開履行環境章節的相關履約信息。從同類條約的執行情況看,有能力啟動申請程序的“個人”實際上就是非政府組織、各類投資和投資人。第20章第9條規定了締約方應將“答復向公眾公開”,這就意味著締約方應當就與環境有關問題的咨詢進行答復并將答復內容公開。為了確保有關環境規則的落實和締約方之間的溝通,TPP進一步規定各締約方應當將有關“未能有效實施其環境法律”的意見通知其他締約方,這就將一個國內的法律實施問題推進到國際層面進行探討。雖然這一規定的效果有可能涉及干涉內政,但同時也給環保水平較低的國家在國內政策制定方面帶來相當大的壓力。
整體上看,TPP的這套制度強化了國內個人申請的實際效果,通過其他締約國介入的方式提升了個人申請的影響力。這種制度設計應該是TPP在環保問題上的一個創新。而從制度設計本身很容易看出《北美環境合作協定》(,以下稱NAAEC)的個人申請程序的影子。雖然對NAAEC個人申請程序依舊存在比較大的爭議[5],但從目前的階段性效果看,NAAEC的委員會公布了22份事實記錄,的確有效地督促和推動了美、加、墨三國有關環境保護國內規則的演進和提高。
這里最大的不同是NAAEC的個人申請是NAFTA的一個附件程序,而TPP的個人申請則是擁有強制力的條約程序。如有意見(包括個人申請)認為某一締約方未能有效實施環境法律,其他締約方可要求環境委員會對該書面意見和答復進行討論,并要求使用專家和現存制度性機構向環境委員會提交報告,報告由“基于該問題的相關事實的信息組成”。從約文規定的程序和目的看,向環境委員會提交的報告和NAAEC要求的“事實記錄”也十分類似。
3. 設立了環境委員會和磋商制度
第20章第19—22條要求設立一個環境委員會并制定了磋商制度。磋商制度共分三個級別,包括環境磋商、高級代表磋商(專門委員會代表)和部長磋商。環境委員會和磋商制度相互銜接,在非特殊情況下磋商內容均要求信息公開,勢必能夠在環境保護問題上給締約方政府形成較大的國際壓力。
4. 規定了爭端解決制度
如果環境委員會和磋商制度未能解決締約方之間有關環境問題的糾紛,則有關締約方可以將糾紛提交依據TPP爭端解決條款設立的專家組,這是一個類似于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構的糾紛解決機制。如果說之前國際仲裁庭對于有關涉及環境問題的案件作出的裁決在法理解釋、法律原則適用等方面存在諸多不一致,造成了國際投資法領域的碎片化,導致各國在調整國內環境政策時極難預知產生的后果,那么統一的環境糾紛解決機構則可以避免這一問題。TPP爭端解決機構專家組作出的報告是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件。
因此,從TPP有關環境保護法律制度的設計可以明顯看出,它深入總結了國際司法實踐和締約實踐的雙重經驗,體現了國際法內在的延續性,為涉及環境問題的糾紛開創了一條國際司法的通道。此前,國際法院曾有設立環境問題特別分庭的實踐,但由于種種原因未能成功。目前尚無法推測TPP爭端解決機制的實際效果,如果能夠成功,它將成為解決環境保護問題的開創性國際司法實踐。
二、我國IIAs環境條款的現狀與問題
多年來,我國締結的IIAs都有納入環境條款的具體實踐。有不少學術著作都認為我國簽訂的雙邊投資協定超過130個[6, 7],筆者以商務部官方網站公布的生效雙邊投資協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以下稱BIT)和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以下稱FTA)為研究對象 (截至2015年12月31日),統計出我國對外締結且已生效的BIT為104個,FTA(含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不含港澳臺)11個。
由于我國長期奉行“先污染、后治理”的理念,也因為我國對外締結IIAs缺少統一的戰略規劃和部門協調,在締約過程中缺少對環境問題的關注,因此我國締結的BITs和FTAs長期缺少與環境保護有關的內容。在所有104個生效的BITs中,僅有8個含有環境保護的有關內容,占7.6%。這8個BITs是我國分別與新加坡(1985年)、毛里求斯(1996年)、圭亞那(2003年)、馬達加斯加(2005年)、烏茲別克斯坦(2011年)、日本和韓國(2012年)、加拿大(2012年)、坦桑尼亞(2013年)簽訂的。從BITs分布的年份可以看出,環境保護內容穩定地出現在我國相互鼓勵和保護投資協定的內容中是從2011年與烏茲別克斯坦簽約開始的,此后所有的BITs都或多或少地含有環境保護內容。這充分體現了環境保護進入有關條約主管部門的視野最早也是在2011年以后。
環境保護在FTAs中的體現要比在BITs中的情況好很多。在所有11個FTAs中有7個包含有環境保護的內容,占64%,分別是與新西蘭(2008年)、秘魯(2009年)、哥斯達黎加(2010年)、瑞士(2013年)、冰島(2013年)、韓國(2015年)和澳大利亞(2015年)簽訂的。
隨著環保意識的加強和全球環境問題的不斷惡化,環境保護已經成為國際政治對話中無法回避的話題,也越來越多地進入包括IIAs在內的各種雙邊、多邊條約中。與此同時,伴隨近年來多邊國際司法機構的發展,與環境有關的爭端越來越多地被訴諸國際司法解決,在條約規定不嚴謹的情況下導致在適用過程中難以合理預計案件的發展走向,同時也難以規范國內管理性措施的制定和實施。綜合分析各種環境有關的法律風險后,筆者認為制定前瞻性的締約談判戰略迫在眉睫。然而,就目前我國在締約方面的實踐來觀察,很難發現這種前瞻性和整體規劃。
(一)環保條款缺少統一標準
從我國簽訂的包含環境條款的BITs的年份可以看出,環境保護內容較多的出現是從2011年與烏茲別克斯坦簽約開始的,而之前與新加坡、毛里求斯、圭亞那、馬達加斯加的BITs中出現環境保護內容僅能理解為一種偶然事件。即使在2011年以后,環境問題依然不是主管部門關注的重點,因此缺少合理的事前規劃和統一的表述。
縱觀我國BITs中的環境保護條款,主要有如下幾種表現形式:首先是序言部分。如我國與圭亞那簽訂的BIT以及同日本、韓國簽訂的三方投資保護協定,其序言部分以倡導和鼓勵性語言為主,如中、日、韓協定序言中的“各締約方均承認,通過放松環境措施來鼓勵締約另一方投資者進行投資是不適當的。為此,各締約方均不得放棄或以其他方式減損此類環境措施去鼓勵在其領土內設立、收購、擴展投資”。其次是“禁止和限制”條款。通常采用“本協定的規定不應以任何方式約束締約任何一方為保護其根本的安全利益,或為保障公共健康,或為預防動、植物的病蟲害,而使用任何種類的禁止或限制的權利或采取其他任何行動的權利”這種表述方式,如我國與新加坡、毛里求斯的BITs。第三是“公平公正待遇”條款。如我國與馬達加斯加簽訂的BIT,其第3條第2款規定:“公正和公平待遇在法律或事實上的障礙主要系指,但不限于:各種對生產和經營手段進行限制的不平等待遇,各種對產品在國內外銷售進行限制的不平等待遇,以及其他具有類似效果的措施。而出于安全、公共秩序、衛生、道德和環境保護等原因采取的措施不應被視作障礙。”這種規定的方式在我國BIT實踐中如曇花一現,就此消失。第四是“征收”條款。這是在實踐中使用頻率最高的,在我國與烏茲別克斯坦、加拿大和坦桑尼亞的BITs中都曾出現過。征收條款中包含環境保護內容的目的一般是用來排除政府調整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時構成間接征收的風險。如我國與烏茲別克斯坦的BIT第6條第3款就明確規定:“除非在例外情形下,例如所采取的措施嚴重超過維護相應正當公共福利的必要時,締約一方采取的旨在保護公共健康、安全及環境等在內的正當公共福利的非歧視的管制措施,不構成間接征收。”
總結我國BITs在環境保護條款方面的實踐可以發現,其內容多出現在“禁止與限制”和“征收”條款中,主要目的是為制定環境立法預留空間,排除因國內環境保護法律法規的調整而導致承擔國家責任的風險。但從環保條款的使用頻率和形式選擇上完全無法看出是否使用和如何使用的前后連貫和內在邏輯,有關環境保護的內容是否應當寫入IIAs也無法從締約實踐的變遷中看出官方政策選擇的演變。因此,只能說我國在環境保護的條款使用方面暫時沒有相關標準,對其必要性也沒有過理論論證。
(二)環保條款使用存在偶然性
我國的FTAs有關環境保護內容多出現在序言、一般例外、投資、環境等章節里。值得指出的是,從序言、一般例外、投資等章節涉及環境問題的內容上能直觀地看出,我國在締約過程中對于與環境問題有關的內容如何在條約約文中體現缺乏統一的規劃和考慮,甚至沒有考慮眾多FTAs文本之間的相互一致。而在所有7個包含有環境保護內容的FTAs中,僅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瑞士聯邦自由貿易協定》就環境保護問題設立了專門章節。雖然這種做法有效地解決了IIAs與國際環境條約之間的潛在沖突,在我國FTA締約實踐中也是一種創新,但在實踐中依然是曇花一現。
縱觀我國FTAs締約實踐可以發現,有關環境保護問題最常使用的兩類條款是序言條款和一般例外條款。其中“一般例外”條款自中國與新西蘭的FTA首次使用后便逐漸固定下來成為我國FTAs的標配,行文以轉引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以下稱WTO)有關協定內容為唯一方式。這種方式雖然文字明確且方便締約部門實際操作,但客觀上增加了條約適用過程中的不穩定性,尤其是WTO有關條款的解釋性注釋內容,很難確定其在我國締結的FTAs中的法律效力。對此連締約部門本身也沒有答案。序言條款在中國與冰島的FTA中形成之后,后續FTAs基本上沿用了它的文字內容,申明了環境保護問題的重要性。可惜的是,在最新的中國與澳大利亞的FTA中這種序言條款又消失了。由于我國目前尚未解決條約的國內法效力層級問題,如果能在FTAs和BITs里規定其與多邊環境條約的效力關系,將可以從條約的角度部分解決上述條約的潛在沖突。至于像前文所述的某些BITs條款中規定的不得降低環保標準吸引外資的內容以及為環境立法預留空間以降低國家責任風險等內容,也曾在我國FTAs締約實踐中出現過,但未能成為條約內容的穩定組成部分,其出現存在較大的偶然性。在目前全球都在關注環境保護的大背景下,我國IIAs締結工作中對環保條款的使用缺少必要的研究和系統的實踐,不能不說是工作中的一項失誤。
(三)缺乏對國際實踐的系統總結
對比我國的締約實踐和TPP有關環境保護的內容后可以發現,TPP有關環境保護的條款在內容設計上是相對完善的,覆蓋了投資與環境的關系(序言、第9.15條“投資與環境、衛生和其他管理目標”)、多邊環境公約與TPP的關系(第1章)、企業責任(第9.16條“企業的社會責任”)、環境保護與征收(附件9B第3款b項)、環境保護與政府管理權行使(主要在第9、20章)。這一系列規定幾乎解決了目前在國際仲裁過程中暴露出來的環境保護與投資保護之間需要解決的所有問題。
此外,TPP的文本還對IIAs中的環境保護制度進行了更為細致的設計,從核心法律概念的定義、公眾參與程序、爭端解決、非政府當事方的參與途徑等方面作了詳細的規定。此舉不但完善了環境保護的制度設計,更認真參考了以往涉及環境問題的糾紛中國際司法機構關心的具體問題,從實踐的角度對其進行規范,增強了相關條文的可操作性,大大提高了條約規范的實際法律效果。
對比我國眾多IIAs中零散的環境保護條文的規定,能夠清晰地看出我國在對外締結IIAs時缺少統一的戰略規劃和部門協調,在締約過程中長期缺少對環境問題的關注和系統研究。因此,我國締結的BITs和FTAs長期缺少與環境保護有關的內容,近年來即使在條約約文中出現了有關內容,但具體行文缺少前后呼應,多是以對方提供的談判方案為準,難以體現我國在經濟發展和改革進程中的實際需要。
三、TPP環境規則對完善我國IIAs環境條款的啟示
(一)將環境保護寫入IIAs的必要性
對于環境保護納入IIAs的必要性,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闡述。
首先,是環境問題與環保意識的全球化[8?11]。環保問題早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就已經出現了,但真正的環保概念和環保意識卻是隨著后來的污染加劇而逐漸形成的。隨著環保問題逐漸進入國際視野,人類意識到這不是一個局部問題,而是全球性問題。環保主義者認為國際投資與貿易的增長以犧牲環境和子孫后代的生存權為代價,是導致全球環境惡化的罪魁禍首[12]。某些投資主體,尤其是跨國公司通過國際投資把高污染企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以求節約成本,最大限度地獲取利潤。為了規范跨國投資行為,解決環境問題,實現可持續發展和綠色經濟,對國際投資行為和投資政策進行反思成為必然的趨勢。
其次,是跨國投資的影響。國際投資自由化對于東道國生態環境的影響是一分為二的[11]。發展中國家引進投資,有利于加快其經濟發展,解決資金不足的問題。但由于缺乏相應的環境立法,使高污染、高能耗企業接踵而至,在某些地區造成生態災難,20世紀后期出現的八大公害充分證明了缺少必要的監管所帶來的后果。
針對跨國公司污染轉移的特征,有學者歸納為三個特點:隱蔽性、長期性、歧視性[13]。關于跨國公司污染轉移的動機,目前有三種假說:污染避難所說、環境成本轉移說、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說。“污染避難所”理論對國際貿易的環境效應進行了深入分析,認為發達國家的環境法規一般比較嚴格,因此將企業轉移至環境法規相對寬松的發展中國家將獲得明顯的競爭優勢,所以貿易自由化一方面減輕了發達國家 的環境污染,另一方面加劇了發展中國家的環境污 染[13]。“環境成本轉移說”認為資源密集型產品的生產會對當地生態環境造成破壞,因而這類產品進行國際貿易時會產生環境成本轉移[14]。該假說將資源密集型產品的國際間流動視為生態流動,因此資源密集型產品的“生態流動”造成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環境成本轉移”,從而使發達國家改善了本國的環境質量,同時惡化了發展中國家的環境質量[13]。“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說”是指,因市場機制本身所固有的缺陷,不能正確地估價和分配資源,不能將環境成本內部化于產品和勞務價格之中,使得環境污染或環境成本外部化[13]。雖然學界對三種假說的定義還存在分歧,但其核心是指投資者選擇環境管理要求低而廉價且有效率的區域投資,通過比較優勢獲得最大化的利潤[10]。更有甚者,為了保護對外投資,某些國家甚至要求投資東道國在一定期限內凍結環保法規,也有東道國為了吸引外資而主動降低環保標準。
關于國際投資與環境保護兩者的關系,通常認為二者既可以相互促進,也可能相互產生不利影響。從國際投資對于環境保護的影響角度看,如果通過恰當的資金和技術轉移,國際投資的確可以提高發展中國家的污染治理能力和資源利用效率,但并非所有的跨國公司都會使用較高的環保標準,比如世界各地出現的許多污染災害和跨國公司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因此,必須通過IIAs有關條款內容的調整對污染轉移進行必要的限制。
第三,是國際法發展的必然。正如Merrill案指出的,國際法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領域,它會伴隨社會的發展變化而作出相應的調整。
對如何平衡投資保護和環境保護沖突的問題,不少研究在總結現有問題的基礎上提出了建議。有觀點認為,我國目前由外資造成環境污染的原因[15?17]主要有:國內立法環境標準較低,地方政府為單純追求經濟增長、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對外許諾優惠條件,跨國公司將高污染企業建設在我國境內,治理跨國公司污染的法律依據不足,外資審批不嚴,環境信息公開制度不完善等。從國內層面[9, 15]來說,一是應考慮完善國內立法。修改環保法、貿易法和投資法,做好各部門法之間的協調和銜接;嘗試統一外資立法,變三資企業法為外資法,條件成熟時可出臺控制跨國企業污染轉移的專門立法。二是加強相關執法,強化環境領域的法律監督。①要嚴格外資審批制度,堅持環保審批嚴格把關。②要建立環境信息公開制度,將外國投資環境評估與影響放置于公眾監督之下,便于監督管理。三是要加快完善環境標準體系,制定國家環境政策和執行環保法規的相關評估依據和法律標準,確保內資、外資一體化,避免實踐中的雙重標準,徹底改變我國環保立法水平低、缺乏制裁手段和執法不嚴的現狀。上述三個方面已經成為目前國內環境保護工作的重點。而在國際法層面,重視環境保護,將環境保護的內容寫入IIAs也就顯得十分重要。
(二)完善我國IIAs環境條款的建議
綜合全文對于IIAs國際締約實踐的分析和環境有關爭端的案例分析,可以發現一個現實,即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環境與投資的關系變得越來越錯綜復雜。由環境問題引發的國際爭端在各個仲裁庭的不斷實踐中引發了對投資待遇具體標準的適用和重新界定,這種實踐也導致了新一輪對于管理性措施邊界的探討,也就是對東道國政府管理權具體邊界的探討。眾所周知,可持續發展是聯合國倡導的新一代投資政策的核心原則,在新的IIAs中體現為環境保護、勞工保護、反腐等理念。為東道國環境政策的調整留下合理的空間將是未來多年IIAs條約中一個重要的主題,我國的締約實踐也不例外。
作為最新一代多議題綜合性FTA,TPP繼承了傳統FTA保護并促進“投資與貿易自由化”的目標,同時通過將可持續發展目標融入FTA文本,實現了在保護和促進的基礎上進一步推動投資自由化、平衡可持續發展等目標。
正如本文指出的,環境保護與投資保護在國際司法實踐中沖突的核心是政府管理權行使的邊界。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十分重要的一點便是在IIAs中對相關核心概念、公眾參與制度、爭端解決等作出清晰的規定,最大程度地提升二者關系的穩定性。TPP的環境條款從結構設計到規則設計體現了對現有自由貿易協定的繼承,同時也包含了對現有自由貿易協定的發展。對比我國締約實踐中前后不統一、缺少明確戰略規劃等問題,我們需要借鑒的正是這種清晰的規則設計方式。從這一點出發,筆者結合前文分析,對我國IIAs的環境條款設計提出如下建議。
第一,明確IIAs與多邊環境公約的關系。有關這一點,《歐洲能源憲章》(,以下稱ECT)曾經有過不成功的實踐。其第16條規定了有關ECT與多邊環境公約之間的關系,但由于規定不清晰、不明確導致了德國在Vattenfall案中敗訴。在Vattenfall案中,Vattenfall公司認為德國漢堡市政府依據《歐盟水框架指令》要求其電廠必須保證不能對易北河水量、水溫和含氧量等產生影響的做法是不切實際的、非經濟的。仲裁庭認同了這一看法,進而判定漢堡市政府的做法構成征收。對這一點NAFTA有比較成功的嘗試,其第104條規定了NAFTA與國際環境公約的關系,明確了國際環境公約的優先效力。但遺憾的是,該條規定并沒有徹底解決問題。在S.D. Myers案中,針對加拿大政府采取禁止PCB跨境運輸的禁令,仲裁庭認為《巴塞爾公約》沒有允許加拿大禁止PCB跨境運送[18]。而且NAFTA第104條規定的多邊環境公約有明確的清單限定其范圍,這就為新的多邊環境公約與NAFTA之間的效力沖突問題埋下了伏筆。TPP在其“環境法”的定義中規定,應當包括雙方共同參與的多邊環境條約,同時確定了在出現糾紛的情況下協商解決的原則做法。這種規定方式雖然不能完全解決環境保護與投資保護的沖突問題,但至少從制度設計上肯定了雙方的效力并為沖突的解決提供了可行的方案。
第二,明確規定東道國政府管理權行使的合法性并設定具體標準。在現有的國際投資仲裁案例中,涉及環境保護的案件的沖突多數都是東道國法律法規的調整造成的。在這些案件中,仲裁庭關注的焦點也是東道國政府管理權行使的合法性。在IIAs文本沒有明確規定的前提下,仲裁庭會根據自己的理解去確定國內法律法規的合法性,導致了多數東道國因政策調整而構成對公平公正待遇或征收條款的違反,從而承擔國家責任。為了避免或降低這一風險,TPP明確了基于環境保護而進行的法律法規的調整不構成間接征收。這一調整在美國2012雙邊投資保護條約范本中也被明確過。
無論是投資者還是政府部門,如果對政府管理權的行使后果缺乏預期,會使雙方的判斷都處于一種不穩定的狀態,這種不穩定對投資者來說蘊含著極大的經濟風險,對東道國來說則蘊含著極大的國家責任風險。結合判例和締約實踐,政府管理權行使過程中的“善意”和“正當程序”是判斷其合法性的重要因素,TPP和美國2012雙邊投資保護條約范本都明確規定了這兩點內容,我國的IIAs文本中也可以接受上述兩點,以降低承擔國家責任的風險。
第三,在條約中明確“環境法”的定義。環境法的定義對東道國政府管理權的行使非常重要,因為確認了“環境法”的定義就幾乎等于劃定了政府在環境保護方面的管理性措施的邊界,從源頭上對管轄權、準據法選擇、征收的確定等法律問題作出了立法上的回答,并將可持續發展和環境保護與貫穿全球化過程的“投資自由化”放在了同等重要甚至更高的位置,為更好地實施環境保護法律法規、平衡環境保護和投資利益帶來了更大的可能。因此,即使不對其他有關環境保護的內容進行規定,單單是定義的明確就足以為有關環境保護法律法規的實施創造了更好的外部環境,并為政府調整環境政策明確了空間,使環境保護和投資保護之間的界限更為清晰。
第四,明確公眾參與制度。與投資保護不同,IIAs中的環境保護除了涉及締約國和投資人外還會影響到其他機構和個人。NAFTA談判過程中就已經有了明顯的體現。如果沒有眾多非政府組織的參與和壓力,NAAEC幾乎沒有出現的可能,個人申訴制度也不會出現[19?21]。在經歷了多年的磨合之后,非政府組織和個人直接參與到環境保護相關的各類案件中已經有了一套相對成熟的做法,并最終被TPP采納,通過條約義務進行了強化。環境保護對于投資保護的制約已經不僅僅是一種趨勢,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已經成為一種現實。為了應對這種變化,需要我們對IIAs的內容和案例實踐進行系統的研究和提煉,并結合我國的實際需要形成自己的方案。
第五,明確環境問題糾紛的國家間磋商制度和東道國司法解決優先。由于目前環境問題糾紛多與東道國政府的國內管理權行使有關,因此國家間的磋商機制更有可能從宏觀的角度解決糾紛,同時兼顧環境保護和投資保護兩方面的利益。
近年來,國際投資仲裁案件數量急劇增加,被訴方大多是發展中國家。以阿根廷為例,其在經濟危機后因國內貨幣政策調整而引發的仲裁案件超過20起,索賠總額超過800億美元[22]。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和外國投資的增多,糾紛勢必越來越多。雖然目前針對我國的仲裁案件不多,但這種現狀并非糾紛數量少,而是我們并不信任國際仲裁,因此將絕大多數糾紛解決在了協商階段。不過,這并不妨礙我們下一步將糾紛真正提交仲裁。我國在加入《1965年華盛頓公約》時曾對公約做了保留,僅有關征收補償數額的糾紛可以直接訴諸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以下稱ICSID),其他爭端均“逐案審批”。然而從我國1998年與巴巴多斯締結的雙邊投資條約全盤接受ICSID的管轄權開始,后續條約在爭端解決方面一直采用這種模式。由于環境條款缺乏實際可操作性,將爭端大量訴諸國際仲裁有可能會使本已被弱化的環保規定在強勢投資條款的沖擊下變得更為弱勢,不但起不到保護環境的作用,反而被仲裁實踐確定其低于投資條款的效力。因此,在涉及此類的糾紛中,應當明確國內糾紛解決機制的優先效力能夠更好地保護東道國的環境利益。
最后,任何一件事業的完成最終依賴的都是人的因素。國際法領域除了條約締結工作,司法實踐也是推動國際法發展十分重要的一環。我國國際法的研究和起步比之發達國家相對較晚,人才的培養和積累嚴重不足,政府機構的國際法人才匱乏,難以形成高水平的應對方案,加之“文革”的破壞,使我國國際法人才出現了較為嚴重的斷層。正因如此,近年來不少可以親身感受和參與國際司法實踐的機會都被迫放棄。所以,加大人才培養的力度和耐心對于未來我國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至關重要。
注釋:
① Merrill & Ring Forestry L.P. v.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No. ICSID Administered Case (ILM March 31, 2010), para193.
② Pennsylvania Coal Co. v. Mahon, No. 260 U.S. 393, 43 S. Ct. 158, 67 L. Ed. 322 (1922).
③ Metalclad Corporation v. United Mexican States, No. ICSID Case No. ARB(AF)/97/1 (ICSID August 30, 2000),paras 33-59, 103.
④ Methanex Corporation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inal Award of The Tribunal on Jurisdiction and Merits (UNCITRAL 2005) para 7,9 (Part IV, Chapter D).
⑤ S.D. Myers Inc. v. Canada, Partial Award NAFTA (UNCITRAL) (I.L.M. 2000), para 280.
⑥ Glamis Gold. Ltd.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NCITRAL Arbitration (NAFTA) June 8, 2009).
[1] Kenneth J. Vandevelde. A brief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symposium: Romancing the foreign investor: BIT by BIT[J]. U.C. Davi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Policy, 2005?2006, (12): 157?194.
[2] The Subcommittee on Investment of the Advisory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Report of the Subcommittee on Investment of the Advisory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Regarding the Model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September 30, 2009[EB/OL]. https://www.state.gov/e/ eb/rls/othr/2009/131098.htm, 2016?12?28.
[3] Joshua Elcombe. Regulatory powers vs. investment protection under NAFTA’s Chapter 1110: Metaclad, Methanex, and Glamis Gold Senior Board Notes, comments and reviews[J]. University of Toronto Faculty of Law Review, 2010(68): 71?98.
[4] Alan C. Swan. NAFTA Chapter 11-direct effect and interpretive method: Lessons from Methanex v. United States[J]. University of Miami Law Review, 2009?2010, (64): 21?88.
[5] CEC. “2011 Annual Report.” Accessed november 25, 2015 [EB/OL]. http://www.cec.org/Storage/159/18840_CEC_ 2011_ AR_V1-e2-rev.20Oct2014.pdf, 2015?11?25.
[6] 張蹇. 美國BIT的最新發展及對我國完善雙邊投資協定的啟示[J]. 武大國際法評論, 2013, 1(16): 241?255.
[7] 羅平. 美國BIT范本(2012)“環境規則”及中國對策[D]. 上海: 華東政法大學, 2014.
[8] 劉筍. 國際投資與環境保護的法律沖突與協調——以晚近區域性投資條約及相關案例為研究對象[J]. 現代法學, 2006, (28): 34?44.
[9] 張淑蘋, 李俊然. 淺談國際投資與環境保護——兼論中國之法律對策[J]. 廣西金融研究, 2008, (7): 50?52.
[10] 王艷冰. 將環境保護納入國際投資協定的必要性[J]. 法治論壇, 2009, 24(5): 61?68.
[11] 蔣紅蓮. 國際投資與環境保護法律機制[J]. 學術界, 2008, (4): 170?176.
[12] 鐘立國. 中國: WTO法律制度的適用[M]. 長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 329.
[13] 葉萍, 張志勛. 論跨國公司污染轉移的法律治理[J]. 湖南科技大學學報, 2013, (16): 54?57.
[14] 吳蕾, 吳國蔚. 我國國際貿易中環境成本轉移的實證分析[J]. 國際貿易問題, 2007, (2): 72?77.
[15] 張虹雨. 國際投資協定與國內環境措施的法律沖突與協調[D].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 2011.
[16] 梁丹妮. 投資保護與環境保護利益平衡機制初探——以《中國-新西蘭自由貿易協定》為起點[J]. 求索, 2009, (10): 152?154.
[17] 王晶. 國際投資法中的環境利益平衡規制研究[D]. 杭州: 浙江大學, 2011.
[18] 胡曉紅. 國際投資協定環保條款: 發展、實踐與我國選擇[J]. 武大國際法評論, 2014, 1(17): 277?296.
[19] John H. Knox.Neglected lessons of the NAFTA environmental regime[J]. Wake Forest Law Review, 2010,(45): 391?424.
[20] John H. Knox. New approach to compliance with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The submissions procedure of the NAFTA environmental commission[J]. Ecology Law Quarterly, 2001?2002, (28): 1?122.
[21] Gustavo Vega-Canovas.NAFTA and the environment[J]. Denv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cy, 2001?2002, (30): 55?62.
[22] Alvarez, José E. The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regime governi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M]. Maubeuge France: Triangle Bleu, 2011: 248.
Creativity of environment clause in TPP and its inspiration for Chinese IIAs’ design
FENG Guang
(School of Law, Renm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2, China)
The key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caused by environment issues is validity of exercise of police power in order to protect environment. Base on years of practices, TPP redesigns environment-related articles. It defines environment law, stipulates the right of host country to adjust environmental legislations, sets up system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consultation and dispute settlement and rebalances the relationship of police power and interests of investors. In view that China is in lack of practices and standards of environment clauses, the present essay, from the angle of designing the system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uggests that China should clarify the definition of environment law and the binding force of multi-lateral environment treaties in IIAs. Further, China should also stipulate public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and assure the priority of domestic judicial system in disputes settlement.
TPP; environment claus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 police power
[編輯: 蘇慧]
D996
A
1672-3104(2017)03?0079?10
2016?12?20;
2017?03?20
中南大學第三批創新驅動項目“‘一帶一路’戰略下中國對外投資促進和保護的國家法律問題研究”(2016XC042)
馮光(1978?),男,江蘇徐州人,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國際司職員,主要研究方向:條約法,國際投 資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