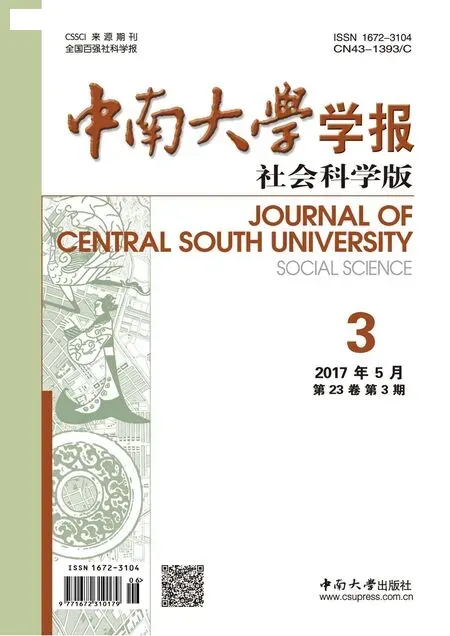政策轉移與情境嵌入:一個政策轉移有效性的分析框架
熊燁,周建國
?
政策轉移與情境嵌入:一個政策轉移有效性的分析框架
熊燁,周建國
(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江蘇南京,210023)
當前的政策轉移研究大多將政策轉移作為因變量進行研究,而把政策轉移視為影響政策結果的自變量的研究十分缺乏。政策轉移是一個轉移政策嵌入移入地情境的過程,其效果受到移入地情境特質的影響。作為嵌入客體的情境存在微觀、中觀、宏觀三個層次上的區別。基于嵌入效應受到嵌入主體、嵌入主客體關系影響的邏輯,構建出“政策再生產程度—情境適配度”的政策轉移有效性分析框架,把政策轉移劃分為象征型政策轉移、啟發型政策轉移、沖突型政策轉移、融合型政策轉移四種類型。通過對不同類型政策轉移效果的理論闡釋和案例分析,形成政策轉移與政策結果之間的因果邏輯解釋,為前瞻性的開展政策轉移奠定基礎。
政策轉移;情境嵌入;移入地情境特質;政策再生產;情境適配度
一、文獻回顧與問題提出
政策轉移的觀念與實踐古往有之,早在公元前315年,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就呼吁同胞們理性地學習偉大城邦發展中的經驗[1]。然而政策轉移的學術研究卻是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而開始興起的。20世紀90年代,有關政策趨同[2]、政策擴 散[3]、政策效仿[4]、政策學習[5]、教訓吸取[6]的研究開始出現在跨學科的文獻中,這些研究都關注到了“某個時間或某個地區有關政策、行政安排、制度等的知識被用于另一個時間或地點來發展有關的政策、行政安排和機構的過程”[7]。在層出不窮的相關概念中,道洛維茨(Dolowitz)和馬什(Marsh)于1996年創立的“政策轉移”這個學術概念,逐漸被學術界接受,成為一個涵蓋諸多相關概念的一般性框架。
政策轉移的研究大體上可以劃分為三類:政策轉移的分析框架;作為因變量的政策轉移研究;作為自變量的政策轉移研究。早期的政策轉移研究主要致力于認識、解釋政策轉移現象,而分析框架的建構無疑成為研究的重點。道洛維茨和馬什構建了一個涵蓋轉移原因、轉移主體、轉移內容、轉移來源、轉移程度、轉移約束因素、轉移失敗原因的政策轉移分析框架,為政策轉移研究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分析工具[8]。沃爾曼(Wolman)與佩吉(Page)建立了一個政策轉移的信息溝通模型,他們認為政策轉移發生在一個信息交流框架下,處于一個信息生產者、發送者、促進者、接受者的信息傳播網絡中,政策轉移就是一個信息的溝通、處理、應用、評估與應用的過程。[9]埃文斯(Evans)和戴維斯(Davies)則把政策轉移劃分為三個層面:一是全球的、國際的和跨國的層面;二是宏觀的層面;三是跨組織的層面。[10]此外,埃文斯和戴維斯分別描述了強制性政策轉移和自愿性政策轉移的過程。作為因變量的政策轉移研究的焦點則在于政策轉移的影響變量的考察。斯通(Stone)認為時間、制度框架、政治文化和國家結構力量都影響著政策轉移。[11]羅斯(Rose)則探討了項目本身的特征對政策轉移的影響。[12]作為自變量的政策轉移研究則探討政策轉移對其他政策變量的影響。阿薩雷(Asare)、唐利(Donley)在多層級治理的背景下探討了經驗吸取(lesson-drawing)在促進政策變遷中的作用。[13]帕特爾(Patel)則融合了政策轉移、漸進主義和政策溪流理論形成對英國的貨幣政策變遷的多層次解釋。[14]整體而言,當前的政策轉移研究多將政策轉移視為因變量,而將其視為自變量的研究則較為缺乏,這也成為未來政策轉移研究的發展方 向。[15]
全球化時代,政策轉移存在“失敗”和“成功”兩種可能,一項失敗的政策轉移無益于政策移入地區政策問題的解決甚至可能帶來巨大的風險和災難。將政策轉移作為影響政策結果的自變量進行研究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而當前這類研究十分缺乏。道洛維茨和馬什只是探討了導致政策轉移失敗的三種情形:不完全政策轉移、信息不足的轉移、不恰當的政策轉移②,并不足以說明政策轉移與政策結果的內在聯系。福西特(Fawcett)和馬什(Marsh)分析了澳大利亞轉移英國網關項目對公共部門采購所產生的規范效應。[16]道洛維茨(Dolowitz)和馬特里斯(Maderis)研究了德國的城市洪水管理技術轉移到美國所帶來的效應。[17]但是這些案例研究只是提供了我們分析政策轉移效果的具體素材,卻沒有提供一個有效的分析框架。正如道洛維茨和馬什所言,我們需要更多的研究來分析政策轉移和政策結果之間的內在聯系。[18]
二、嵌入性理論視角下的政策轉移
“嵌入”是新經濟社會學中的核心概念,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波蘭尼(Polanyi)所著的《大變革》。波蘭尼認為“經濟作為一個制度過程,是嵌入在經濟和非經濟制度之中的”[19]。40年后,格蘭諾維特(Granovetter)在《經濟行動與社會結構:嵌入性問題》中創造性地重塑了“嵌入性”概念,“嵌入性是指這樣一個事實,即像所有的社會行動及其后果一樣,經濟行動及其后果會受到行動者雙方關系以及整個網絡關系的影響”[20]。格蘭諾維特強調社會對經濟行動的影響,他的嵌入性概念可以定義為經濟行為的持續情景化。在《經濟生活社會學》中,格蘭諾維特進一步將嵌入分為關系嵌入和結構嵌入,關系嵌入指單個行為主體的經濟行為嵌入于他人互動所形成的關系網絡中,而結構嵌入則是對行為主體嵌入關系構成的各種網絡的總體結構描述。[21]
隨著“嵌入”概念的發展,不同學科背景的學者從不同的視角對“嵌入”進行解釋,“嵌入”概念的應用呈現泛化的局面,已經超出了波蘭尼和格蘭諾維特等最初界定的“經濟行為受社會關系結構影響”的內涵。[22]但凡涉及到兩方關系的相關性,就會看到“嵌入”一詞。嵌入作為一個概念性工具,其應用范圍并不必然局限于新經濟社會學,但我們使用“嵌入”一詞時必須謹慎,必須明確嵌入的主體和客體,層次與內涵。
政策轉移作為一項政策的跨時間或空間的應用描述,無論是空間上的轉移還是時間上的轉移都意味著政策應用的情景變更。政策轉移的過程也是一個轉移政策植入新情景的過程,引入“嵌入”這個概念,我們可以把轉移政策的情景化表述為轉移政策的情景嵌入。新經濟社會學中的“嵌入”的核心思想是經濟活動不是獨立于社會,而是受到社會廣泛影響。而我們在政策轉移的語境中使用“嵌入”這個概念,所要表達的的是轉移政策不能脫離移入的情境發揮作用,而是受其影響和制約的。正如格蘭諾維特對經濟行為的“社會化不足”和“社會化過度”的批判一樣,我們在敘述政策轉移的“嵌入”時也需避免脫離情境和機械的唯情境決定論思想誤區。轉移政策受到移入情境的影響,與此同時,轉移政策也作用于移入地的情境,兩者是一種相互引導、促進、限制的復雜關系。一項轉移政策能否成功與其嵌入的轉移情境適應度密切相關,情境嵌入也就成為我們探索政策轉移效果的切入點。
三、轉移政策嵌入的三個層次
使用“嵌入”這個概念,首要必須明確“嵌入”的主體和客體。嵌入的“主體”在不同的語境中指涉不同的事物,在新經濟社會學中嵌入的主體是經濟行為,而在政策轉移的語境中則指的是轉移政策。較之于嵌入主體,嵌入客體的內容則更為復雜,嵌入的客體存在邏輯層次與類型上的區別。Hagedoorn把企業間合作嵌入分為環境嵌入、組織間嵌入和二元關系嵌入三個層次,并強調理解這些不同層次嵌入互動的重要性。[23]Zukin和Dimaggio把嵌入分為四種類型:結構嵌入性、認知嵌入性、文化嵌入性和政治嵌入性。[24]Hess提出了構成嵌入的三個主要維度:社會嵌入、網絡嵌入、空間或地理嵌入。[25]不同于新經濟社會學領域中的嵌入客體,政策轉移中的嵌入客體有其自身特點。在借鑒新經濟社會中對嵌入層次的劃分的基礎上,筆者把政策轉移語境中的嵌入客體劃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微觀層次。其主要指的是移入方的政治系統層面,如組織、制度。第二,中觀層次。指嵌入網絡,即政策過程中公共、私人行動者因資源依賴形成的穩定的關系結構。第三,宏觀層次。指嵌入環境,主要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環境層面,如表1所示。微觀層次考察以政府為核心,而中觀層次的考察隱含著主體多元的預設,把利益集團、媒體、知識群體等非政府主體納入觀察的范圍。而宏觀層次超越了主體的層面,而是將主體所存在的環境作為考察對象。微觀、中觀、宏觀層次實質上體現的是單一主體、多元主體、主體存在環境的層次邏輯。

表1 政策轉移嵌入結構層次與要素集
第一,從微觀層次來看,政策轉移并非一個簡單的傳播與接收的過程,一項政策能否進入移入方的政策過程循環,受到移入方政治系統的約束與制約。首先,轉移政策必須與移入方政策制定主體的價值理念相符合,政府購買公共服務作為一項發源于西方的政策工具近年來在我國的蓬勃發展,也正是因為它與我國的政策制定主體的執政理念轉變相契合。其次,轉移政策受到移入方的現存制度的影響。制度是各種規則和組織化慣例的一種相對持久的聚集[26],制度限定了轉移政策的存在空間,即使是一項涉及到制度調整的政策轉移,制度變遷也受到路徑依賴的影響。再次,轉移政策受到移入方政府組織狀況的影響。轉移政策的執行主要依托政府組織,在歷史、文化、經濟等因素的影響下,不同國家乃至不同地區的政府組織發展狀況不盡相同。雖然絕大多數國家的行政組織以韋伯的科層制為藍本建構,但現實實踐卻是千差萬別,尚處于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期的發展中國家的行政組織大多存在法理型權威不足的狀況,而這構成了轉移政策執行的制約性因素。最后,移入方政策執行主體掌握的資源多寡也制約著轉移政策的執行。政策執行需要物質、技術、人才、合法性等資源的支撐,在缺乏資源支撐的情況下,僅僅憑借主觀意愿開展政策轉移往往難以取得預期成效。智慧城市建設是應對“城市病”的一劑良方,近年來發達國家紛紛開展智慧城市建設,如新加坡的“智慧國計劃”、韓國的“U-City計劃”等。但智慧城市對技術、資金人才有著較高的要求,對于一些準備建設智慧城市的發展中國家應根據自身資源的狀況而有所考量。
第二,從中觀層次來看,“在由統治向治理轉變的過程中,政府與社會的許多自治組織已形成相互依賴的政策網絡”[27]。“網絡”一詞的出現基于這樣一個事實,即“政策制定包含數量眾多的公共與私人行動者,他們來自政府與社會的各個功能領域和不同層 面”[28]。學術界對于政策網絡的概念界定并不統一,存在利益調停流派和治理流派[29]的分野。筆者使用“網絡”這個概念并非指涉特定的分析模式或治理模式,而是用于描述政策過程中行政機構、利益集團、媒體、知識群體等對政策感興趣的行動者在資源交換基礎上形成的網絡結構。政策轉移并非移入方政策系統單方面的行動。在民主化進程不斷加快,公民社會發展壯大的時代,利益相關群體在政策過程中的作用不斷擴大。權威行政機構只是公共政策行動者中的一員,它存在于行動者網絡中,受到所處網絡位置以及自身資源狀況的約束。由于政策網絡形成的方式與途徑的差異,網絡連結在強度、標準化和互動頻率等方面存在差異,而轉移政策能否產生預期效應與嵌入網絡的適配程度密切相關。政策轉移網絡建立在多元主體的基礎上,主體間權力結構和主體間互動狀況是影響政策轉移的兩個核心要素。首先,治理主體多元意味著政府、智庫、媒體、利益集團都在政策轉移中發揮著作用。然而,不同治理主體在政策轉移中所占據的位置、發揮的作用卻并不相同,位置、角色根本上是主體間權力結構的外在體現。在單一權力中心的權力結構下,政府是一個高高在上的發號施令者,權力向度上表現為自上而下。而在多中心的權力結構下,政府只是一個相對的權威主體,在特定場合、領域與其他行動者是一種合作治理的伙伴關系,盡管存在自上而下的權力行使但也存在水平權力的行使。權力結構影響著知識社群的知識供給和民眾的訴求表達,構成影響轉移政策效果的變量。其次,政府與其他行動者的互動狀況也影響著政策轉移的成效。這種影響既體現在政策制定環節也體現在政策執行環節。政策轉移可以看作是一種政策制定方式,政府與利益相關群體、知識精英的互動影響著政策轉移的科學性與民主性。在轉移政策的執行階段,政府與政策目標群體之間的良性互動則有助于減少政策執行的阻力,最終提高政策轉移的成效。
第三,從宏觀層次來看,政府、媒體、智庫、知識精英等行動主體都存在于特定的環境中,而公共政策所針對的社會問題、政策目標無不處于特定環境之中,環境情境構成轉移政策嵌入的宏觀層次。影響政策轉移的環境因素包括經濟發展水平、治理危機、大眾情緒、歷史文化傳統等。首先,經濟因素。它是影響一個國家政治架構的基礎性因素,一項出于發展經濟目的的公共政策本身也受到當前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如“自貿區”政策難以在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下運行。其次,危機因素。危機包括戰爭、自然災害、革命等。如太湖藍藻危機催生了“河長制”③的誕生,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將“河長制”作為一項常規性治理制度,其能否達到“危機”情境下的成效還需要觀察。再次,大眾情緒即公眾的價值、心理、態度。如我國地方政府信息公開制度的轉移和擴散與公眾的呼吁不無關系,是大眾情緒對政策轉移影響的體現。最后,傳統價值觀、非正式規范、信念、信仰、宗教、意識形態等文化傳統與文化環境。一項政策如果與當地的文化相沖突,將會受到深層次的抵制。正如里格斯所言:“在現代的、過渡的社會里,一直有一種建立正式的政治和行政制度的趨勢,但是這些制度卻仍然只是一種形式主義的制度。這就是說,有效的行為絕大部分取決于傳統的結構和壓力,諸如家族、宗教以及一些繼續存在的社會和經濟成規。因此,只有以生態學的觀點——亦即從非行政的因素去觀察,才能了解這些國家的政治和行政。”[30]公共政策屬于一個國家政治與行政的范疇,政策轉移也必然受到整個生態環境的影響,一項與行政環境不兼容的轉移政策,如不具備一定的經濟發展水平,與大眾的文化心理相悖等,即使是政策企業家極力推崇,也很難有效實施,并達到預期的效果。
四、政策轉移有效性分析框架
一個國家或地區進行一項政策轉移的最終目的是解決本地的政策問題,增進當地人民的福祉,而這也是評估一項政策轉移是否有效的根本標準。評判一項政策轉移的成功與失敗并非依據轉移政策多大程度上在移入地實施,而應以轉移政策在移入地所產生的效應作為依據。我們以政策轉移的有效性作為描述政策轉移成功與失敗的一個概念,有效與無效作為成功與失敗的另一種表述,在移入地產生良好效應的政策轉移即為有效的政策轉移。政策轉移有效性研究的實質就是探討政策轉移影響政策結果的內在邏輯。
從嵌入性視角來看,政策轉移的有效性也就是轉移政策嵌入移入地情境的效應狀況,而影響嵌入效應的兩個核心變量就是嵌入主體與嵌入主客體關系。筆者從嵌入主體、嵌入主客體關系出發構建“政策再生產程度—情境適配度”的分析框架。政策轉移并非單純指涉一個地區采納了另一個地區的政策模板,政策在流動過程中被各種行動者解釋和再解釋[31],因此,政策可能在轉移過程中被重新塑造。政策主體在政策轉移中存在照搬模仿和學習借鑒兩種基本行為模式,不同行為模式下的政策轉移存在程度上的差別。洛維茨和馬什把政策轉移程度分為復制、模仿、混合、啟發四個類別。政策轉移程度上的差別決定了我們不能把政策原發地的政策與嵌入情境的政策等同起來,在治理環境高度復雜化和不確定的時代,政策轉移更多的表現為政策跟隨方在特定價值導向下對轉移政策進行學習、借鑒與調整的過程,最后納入移入地的政策是轉移政策變更調整后的產物。這個學習、借鑒、調整的過程也是一個重新決策的過程,筆者稱之為政策轉移中的政策“再生產”,再生產的政策依然保留了和原生政策可識別的相似性。政策轉移中的政策再生產是一個在轉移政策基礎上的更新、再造過程,作為嵌入主體的轉移政策經歷了一個再生產的過程,因此,以“政策再生產程度”作為分析政策轉移有效性的一個維度。此外,從情境嵌入視角來看,政策轉移的整個過程都受到嵌入情境的影響,轉移政策與嵌入情境的關系狀況構成影響政策轉移有效性的另一個變量,筆者用轉移政策與情境的“適配度”作為二者關系狀況的描述。從嵌入的三個層次來看,轉移政策與情境的“適配”包括政治系統適配、網絡適配、環境適配。而一個高程度的“適配”需涵蓋這三個層次,任何一個層面的“不兼容”“不適配”都影響著政策轉移的成效。因此,轉移政策和情境的適配性構成我們分析政策轉移有效性的另一個維度。
“政策再生產程度”與“情境適配度”均可以用高、低來判斷,兩個維度交叉組合,形成政策轉移有效性的分析框架,如圖1所示。

圖1 政策轉移有效性分析框架
Ⅰ象限區:政策再生產程度高與情境適配度高(象征型政策轉移)
情境適配度高說明轉移政策與移入地區的情境高度契合,轉移政策既能夠滿足移入地區的政策需求又具備移植實施的支撐條件。在這種情況下,只需要對源發地的政策予以簡單調整,即低程度的政策再生產,就能夠獲得政策轉移成效。那么現實中是否存在第一象限中所呈現的高度的情境適配性和高度的政策再生產的情況?對一項高度適配性的轉移政策進行高程度的變更,并不符合政策轉移的有效性追求。此種類型的政策轉移追求的是一種形式而非實質效應,我們稱之為象征型政策轉移。隨著民主化浪潮的推進,政策的公共性已經成為一種全球共識。然而世界各國政治發展的階段并不同步,依然存在一些國家的政府被利益集團俘獲的情況,政策企業家迫于全球化發展趨勢、國際組織影響、民主輿論等壓力開展政策轉移,但出于特定利益集團利益的考慮卻對轉移政策進行變更,或者在執行階段消極執行,造成象征型政策轉移。此類政策轉移是政策主體應對外界壓力采取的策略性手段,背離了政策公共性的實質追求,也就難以獲得政策轉移的成效。
Ⅱ象限區:政策再生產程度高與情境適配度低(啟發型政策轉移)
情境適配度低指的是轉移政策與移入地的情境并不相容,這種不相容可能是前述的政策轉移情景中的微觀、中觀、宏觀中的某個或多層面的不相容。而高程度的政策再生產則指的是政策主體在學習轉移政策的基礎上對轉移政策進行了較大程度的變更,這個變更也是一個對轉移政策進行情景化再造的過程。政策再生產的結果可能保留了政策源發地政策的某些因素,如政策目標、工具、經驗教訓等。這種類型的政策轉移具有鮮明的再造特點,我們稱之為啟發型政策轉移。對于這類政策轉移的有效性并不能一概而論,這類政策轉移的有效性既受到影響政策效益的一般性因素的影響,如資源狀況、執行效率、精英態度、大眾心理等,在政策轉移的特定語境中,還受到政策主體的政策學習能力的影響。邁克爾·霍爾特(Michael Howlett)和拉米什(Ramesh)將政策學習分為內生學習(Endogenous Learning)和外生學習(Exogenous Learning)。內生學習與經驗吸取相對應,源于正式的政策過程,影響著政策制定者對政策方法和政策工具的選擇,主要是技術層面的改進;外生學習與社會學習相對應,源于政策過程外部,體現的是政策制定者適應或改變社會的阻力或能力, 是一種最為根本性的學習。[32]在政策轉移的語境中,政策主體的學習能力也可以從內生學習和外生學習兩個方面來理解。一方面政策主體需要充分學習轉移的政策方法與政策工具,避免道洛維茨和馬什指出的“信息不足的轉移”“不完全的轉移”。另一方面,政策主體需要具備社會學習能力,表現為吸取社會公眾利益訴求的能力,智庫合作能力、環境感知能力等。政策學習能力決定了政策再生產的結果的質量,提高政策主體的政策學習能力也就成為避免“不適當的政策轉移”的基本途徑。
以勞資集體談判在中國的發展為例,20世紀初期風起云涌的工人運動推動一些國家對集體談判立法。二戰后,開展集體談判立法的國家越來越多,集體談判成為國際勞工標準中的“核心標準”之一。1978年改革開放之后,我國開始恢復集體談判和集體合同制度。進入90年代,勞資糾紛的增多促進了我國集體談判的法制化,2001年人大常委會修改后的《工會法》中對集體談判作了規定。集體談判無疑是國際規范和政策擴散的結果,從情境適配度來看,西方國家的集體談判是存在于多元工會的環境中,而我國是一個單一工會國家,如此看來,集體談判轉移的情境適配度并不高。然而,從政策再生產的來看,中國的勞工集體談判呈現出不同于西方“自由結社”“多元工會”的運行邏輯,政策再生產的程度較高,“中國政府既要推動集體談判,又要堅持單一工會制,只能走一條國家主導下的集體談判和工會組建之路”。[32]中華全國總工會及其所屬工會是中國唯一合法的工會組織,被國家權力賦予管理職能,承擔著管理勞資沖突的使命,在勞資集體談判中發揮著主導作用。盡管生成于西方多元工會環境中的勞資集體談判制度與我國單一工會的情境適配度并不高,但政策主體在考察本國國情的基礎上對其進行了再生產。勞資集體談判與我國的單一工會制度相耦合,產生了良好的政策效果,集體合同的數量和簽約率近年來顯著上升,為勞資糾紛的解決作出了重大貢獻。
Ⅲ象限區:政策再生產程度低與情境適配度低(沖突型政策轉移)
政策再生產程度低與情境適配度低往往是照搬模仿、盲目跟風的產物。在轉移政策與移入地的情境不相吻合的情況下,政策主體并不對轉移政策作出調整、變更而是直接應用于本地的政策實踐。轉移政策與嵌入情境的不相匹配使得政策轉移過程中充滿著沖突和危機,我們稱此類政策轉移為沖突型政策轉移。沖突型政策轉移可能存在兩種結果,一種是情境影響力大于政策執行力,如利益集團的抵制、執行官僚的消極執行等,導致轉移政策在執行中夭折,難以得到有力實施。另一種情況是政策執行力大于情境影響力,在強大的國家權力的推動下轉移政策得到了執行,這不僅意味著巨大的政策執行成本,而且造成社會的對抗情緒,甚至侵蝕著執政者的合法性。無論哪種情況,政策再生產低與情境適配度低的沖突型政策轉移都是無效的。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面臨政策缺失等一系列難題,由于黨和政府治國經驗的缺乏,不得不進行全方位的政策轉移,從國家體制到經濟、科技、教育等領域都存在典型的政策轉移。此階段的我國政策轉移受到國際環境、意識形態的影響,選取以蘇聯為政策轉移的唯一來源,逐漸形成了蘇聯模式。“政策轉移模式的單一化以及政策內容的全盤接受成為這一時期轉移的主要特點”。[33]此階段存在不少全盤照搬式的政策轉移,這種低度的政策再生產和低度的情境適配度的政策轉移塑造了僵化的體制,制約了人民群眾的勞動熱情,生產力的發展受到極大的阻礙。以農業政策為例,農業集體化的社會主義改造政策是借鑒蘇維埃式的集體化,通過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建立土地和主要生產資料歸集體所有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事實證明,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建立脫離了當時生產力發展的實際狀況,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因此而受到打擊。此外,以工業化的名義將一切農業剩余都集中在政府手中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也是受蘇聯犧牲農民利益、保障工業化政策的影響的又一例。長期犧牲農民利益的政策導致城市的繁榮和農村的長期滯后。從長遠看,影響了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也造成了中國社會結構固化的惡果。
Ⅳ象限區:政策再生產程度低與情境適配度高(融合型政策轉移)
在反思照搬模仿的政策轉移時,并不意味著我們需要一味地追求高程度的政策再生產。事實上,政策轉移的有效性并非取決于轉移政策與原始政策的差異程度,它還受到情境適配度的影響。即使一項轉移政策與原始政策高度相似,但如果具備高度的情境適配度,依然可以帶來積極的成效。具備政策再生產程度低與情境適配度高的政策轉移不同于照搬模仿的沖突性政策轉移,高度的情境適配度決定了異地政策無需變更就能和移入地情境高度融合,我們稱之為融合型政策轉移。政策創新除了需要一定的成本還需要諸多條件的支撐,如政策企業家的創新動力與創新能力、制度空間、創新文化、資源稟賦等。我們處于一個鼓勵創新的時代,然而事實上并非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政府都能夠進行一項原發性政策創新。在面臨一個相同的問題時,如果異地的某項政策和當地的情境高度契合,則可以直接轉移到本地的治理實踐中,其前提是對轉移政策的情境契合度有了一個充分的考察 論證。
隨著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矛盾越來越凸顯。為了控制污染物的排放,我國政府開始積極轉移污染權交易政策。 排污權交易起源于美國,從1976年開始,美國環保局(EPA)嘗試將排污權交易用于大氣污染源和水污染源管理,逐步建立起以補償、儲存和容量節余為核心內容的排污權交易政策體系。所謂的排污權交易是指在一定區域內,在污染物排放總量不超過允許排放量的前提下,內部各污染源之間,通過貨幣交換的方式相互調劑排污量,從而達到減少污染,保護環境的目的。從政策再生產的程度來看,我國排放權交易政策與西方國家污染權交易政策高度相似,其本質都是利用市場機制解決環境污染及治理中的外部問題。從情境適配度來看,隨著我國的工業飛速發展,環境狀況不斷惡化,傳統的行政管制政策工具難以完成減排的任務,而污染權交易政策同時具備控制和激勵的效應,顯現出巨大的發展前景,可以說與我國的情境高度契合。因此,我國開展的污染權交易政策轉移具備低度的政策再生產和高度的情境適配度特性,從目前的發展狀況來看,已經對我國污染排放控制產生良好的政策效果,成為我國“節能減排”目標實現的戰略選擇。
五、結論與討論
伴隨著全球化浪潮的涌動,國與國、地區與地區之間的政策學習與借鑒越來越頻繁,政策轉移現象開始在全球迅速蔓延。然而,政策轉移存在成功和失敗兩種可能,一項失敗的政策轉移不但無助于移入地政策問題的解決甚至存在帶來沖突、風險的可能。政策轉移的有效性成為政策轉移研究不可回避的主題,然而當前學術界對政策轉移有效性的研究并不充分。本文引入“嵌入”這個概念以描述轉移政策受到移入地情境特質的影響的情形。然而,單一的情境維度并不能完整的解釋政策轉移的有效性。因此,筆者基于嵌入效應受到嵌入主體、嵌入主客體關系影響的邏輯,構建出“政策再生產—情境適配度”的政策轉移有效性分析框架,把政策轉移劃分為象征型政策轉移、啟發型政策轉移、沖突型政策轉移、融合性政策轉移四個類型。通過理論闡述和案例分析,我們可以初步發現象征型政策轉移和沖突型政策轉移往往導致政策轉移無效,啟發型政策轉移的有效性與政策主體的政策學習能力密切相關,融合型政策轉移因為具備高度的情境適配度往往也能達到較好的政策效果。
本文構建的政策轉移有效性分析框架包含了情境、政策再生產、政策有效性三個核心變量,政策再生產和情境都是作為影響政策有效性的自變量而存在。政策轉移有效性分析框架即是一個評價政策轉移結果的工具,同時也是前瞻性開展政策轉移的風向標。情境結構的考察可以看做政策轉移的前瞻性(預)評估的過程,而政策再生產則關注的是政策轉移中人的能動作用,預評估和政策再生產能力構成前瞻性開展政策轉移的兩大基石。而對于如何開展預評估以及如何提高政策轉移中的政策再生產能力則是兩個需要繼續深化拓展的主題。在政策轉移現象不斷增多的時期,深入剖析政策轉移有效性的生成機理,求索前瞻性開展政策轉移之路,對于國家治理的現代化轉型意義重大。本文建構的政策轉移有效性分析框架只是一個初步的探索,而政策轉移有效性研究的推進需要更多學者的關注和努力。
注釋:
① “信息不足的轉移”,即借用國或許只擁有關于政策或制度在移出國如何運行的不充分的信息;“不完全的轉移”,即政策或制度結構在原創國家成功的關鍵因素可能沒有被轉移,導致失靈;“不適當的轉移”即沒有充分考慮社會、經濟、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等因素在轉移國和借用國間的差異從而導致政策失靈。詳見:D. P. Dolowitz & D. Marsh. Learning from abroad: The role of policy transfer in contemporary policy-making[J].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2000, 13(1): 5?23.
② 所謂的“河長制”,由當地黨政主要負責人兼任“河長”,負責轄區內河流的水污染治理和水質保護,是由水質改善領導督辦制、環保問責制衍生而來。
[1] Mark Evan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policy transfer[J]. Policy Studies, 2009, 30(3): 237?241.
[2] Bennett C. Review article: what is policy convergence and what causes it?[J].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1, 21: 215?233.
[3] Majone G. Cross-national sources of regulatory policy-making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J].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1991, 11: 79?106.
[4] Howlett M. Beyond legalism? Policy ideas, implementation styles and emulation-based convergence in Canadian and US environmental policy[J].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2000, 20(3): 305?329.
[5] May P. Policy learning and failure[J].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1992, 12: 331?354.
[6] Rose R. Learning from comparative public policy: a practical guide[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7] David Dolowitz, Marsh David. Who learns what from whom: A review of the policy transfer literature[J]. Political Studies, 1996, 44(2): 343?357.
[8] David Dolowitz, Marsh David. Learning from abroad: The role of policy transfer in contemporary policy-making[J].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2000, 13(1): 5?23.
[9] Wolman H, Page E. Policy transfer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An information-theory approach[J].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y, Administration, and Institutions, 2002, 15(4): 477?501.
[10] Evans M, Davies J. Understanding policy transfer: A multi–level,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J]. Public Administration, 1999, 77 (2): 361?385.
[11] Diane Stone. State of learning and transferring policy across time, space and disciplines[J]. Polities, 1990, 19(1): 51?59.
[12] Richard Rose. Lesson-drawing in public policy[M]. Chatham: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1993: 41?56.
[13] Bossman Asare, Donley Studlar. Lesson-drawing and public policy: secondhand smoking restrictions in Scotland and England[C]//Mark Evans ed.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policy transfer.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126?144.
[14] Sucheen Patel. Accounting for policy change through multi-level analysis: The reform of the Bank of England in the post-war era[C]//Mark Evans ed.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policy transfer.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95?109.
[15] Benson D, Jordan A. What have we learned from policy transfer research? Dolowitz and Marsh revisited[J].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2011, 9 (3): 366?78.
[16] Fawcett P, Marsh D. Policy transfer and policy success[J].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2012, 47(2): 162?85.
[17] Dolowitz D, Maderis D. Considerations of the obstacles and opportunities to formalizing cross-national policy transfer to the United States: A case study of the transfer of urban environmental and planning policies from Germany[J]. Environment and Panning, 2009, 27(4): 684?597.
[18] David P. Dolowitz, David Marsh. The future of policy transfer research[J].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2012(10): 339?345.
[19] Polanyi K.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M]. Boston, MA: Beacon Press,1944: 10.
[20] 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91(3): 481?510.
[21] Granovetter M, Swedberg R. 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M]. Boulder: Westview, 1992: 157.
[22] 黃中偉, 王宇露. 關于經濟行為的社會嵌入理論研究述評[J]. 外國經濟與管理, 2007(12): 1?8.
[23] Hagedoorn J. Understanding the cross Olevel embeddedness of interfirm partnership formation[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6, 31(3): 670?690.
[24] Zukin S, Dimaggio P. Structures of capital: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economy[M].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34.
[25] Hess M. “Spatial” 0relationships? Towards a conceptualization of embeddedness[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4, 28(2): 165?186.
[26] 詹姆斯·馬奇, 約翰·奧爾森. 新制度主義詳述[J]. 國外理論動態, 2010(7): 41?49.
[27] Kooiman J. Modern governance[M]. Thousand Oaks, California: Sage, 1993: 35?48.
[28] Hanf K. Interorganizational policy making[M]. London and Beverly Hilla: Sage, 1978: 12.
[29] Tanja A, Borael. Organizing babylon——On the different conceptions of policy networks[J]. Public Administration. Summer, 1998, 76: 253?273.
[30] 里格斯. 公共行政比較研究的趨勢[J]. 國際行政科學評論, 1962(2): 9?15.
[31] McCann, E. Urban policy mobilities and global circuits of knowledge: Toward a research agenda[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11, 101(1): 107?130.
[32] Michael Howlett, Ramesh. Studying public policy: policy cycles and policy subsystem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176?177.
[33] 田野. 國際政策擴散與國內制度轉換——勞資集體談判的中國邏輯[J]. 世界經濟與政治, 2014(7): 118?138.
[34] 馮鋒, 程溪. 全球化視域下中國政策轉移的反思與建構[J]. 公共管理學報, 2009(3): 26?31.
Policy transfer and situational embedding:An analysis framework of effectiveness of policy transfer
XIONG Ye,ZHOU Jianguo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t present, most of the researches on policy transfer are carried out as a dependent variable, but researches on policy transfer as an independent variable of policy results are in great shortage. The concept of "embedding" is introduced in order to describe transfer policies which are constrained by the situational characteristics. Policy transfer is a process of transfer policy embedded into situation. As the objects of embedding, situation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 micro, medium and macro. Based on the logic that embedding effect is affected by the embedded subj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embedded subject and object constructs an analysis framework of effectiveness of policy transfer: “degree of reproduction policy-context adaptation degree”. Policy transfer is divided into symbolic, inspiring, conflicting, and integrated. The author make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case study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se four types of policy transfer, which may lay the foundation for forward-looking policy transfer.
policy transfer; contextual embeddedness; situational trait; policy reproduction; situational adaptation
[編輯: 顏關明]
C93-05
A
1672-3104(2017)03?0135?08
2016?09?20;
2016?10?27
2011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社會管理創新與社會體制改革”(11&ZD028);2016年度江蘇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創新計劃項目“全球化時代政策轉移中的政策再生產:結構、過程、有效性”(KYZZ16_0030)
熊燁(1989?),男,江西南昌人,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公共政策;周建國(1965?),男,江蘇如皋人,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公共政策,公共部門人力資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