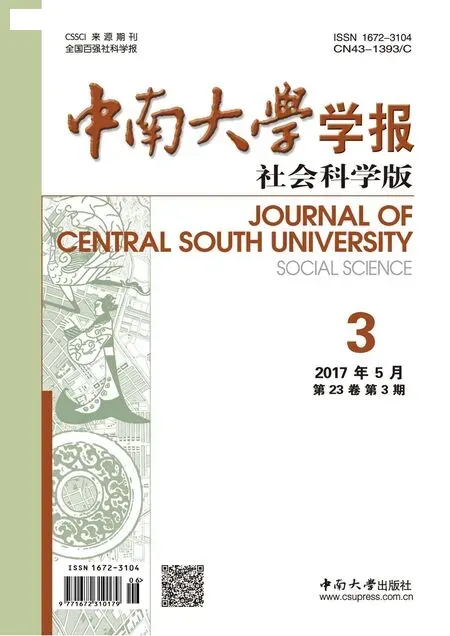論八十年代與九十年代文學的現代性關聯
盧衍鵬
?
論八十年代與九十年代文學的現代性關聯
盧衍鵬
(1. 東南大學藝術學院,江蘇南京,210063;2. 棗莊學院文學院,山東棗莊,277160)
在“年代學”或“斷代史”文學研究中,存在二元對立的思想傾向,從現代性、整體性的角度考察80年代文學與90年代文學的關系,更能發現兩者在敘事上的“歷史連續性”,其內在連續性大于表面的“斷裂”和差異性。通過“縫合”歷史的斷裂帶、對接80、90年代文學通道,梳理中國現代性歷史經驗的文學表達方式,發掘一條清晰的歷史脈絡來把握當代中國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認同,并在連續性的時空中摸索其審美邏輯和內在規律。“現代派”小說表征了80年代中國的現代化想象和社會的現代化進程,表達了“個人”對“現代”的敏感體驗,90年代關于現代性與后現代的紛爭其實在80年代就已經開始。
歷史連續性;現代性;文學現代性;年代文學;現代性敘事
進入新世紀之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走向縱深,有了新的拓展,海外學子提出了“重返八十年代”的口號,深化了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研究,學術界對90年代文學的研究也取得新的進展。但是,目前學界偏重從“年代學”或“斷代史”的角度展開當代文學研究,強調不同時間段之間的差異性、斷裂性,并且某一年代上的斷裂常常以否定以前的文學為代價來突出自身的合法性。這種以“斷裂”為特征的時間觀和歷史觀是需要反思的。具體到“80年代”和“90年代”,這種以二元對立思維來切割文學的做法就更加明顯。如:一種流行的說法是,80年代是精神高揚的年代,是“文化人時代”;90年代是物質至上的年代,是“經濟人時代”。這樣對兩個年代“斷裂性”的思維判斷自然影響了當代文學研究者對80、90年代文學之間的判斷,研究者往往強調、突出、論證二者之間的差異、斷裂的一面,如:80年代文學是理想主義、人道主義的;90年代文學是私人寫作、欲望敘事等。而對二者之間“延續”的一面卻視而不見或有意忽略。
與以上不同,我們希望以整體性的眼光重新審視80、90年代的文學,認為它們之間內在的連續性大于表面的“斷裂”和差異性,并通過重新“縫合”歷史的斷裂帶,重新對接80、90年代文學通道,在更宏觀的層面上尋找中國現代性歷史經驗的文學表達方式,從文學角度發掘一條清晰的歷史脈絡來把握當代中國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認同,尋求一種將這種自我理解和自我認同在連續性的時空中展開的自我邏輯和內在規律。
一、文學的“現代”:一個中國文學無法回避的超級詞匯
對于中國文學來說,“現代”一直以來都是一個無法回避、涵蓋性極廣的超級詞匯,這不僅由于“現代”本身的復雜性,更是源于中國社會對文學的期望和要求。“現代”的意義已經遠遠超過了其時間指向的范疇,成為承載社會轉型、文化變遷和審美轉向的指向標,每個人都有自己對于“現代”的理解,每個人都有對于“現代”文學的認識,因為每個人都有對于現在的認識和未來的想象。
“現代”的英文詞modern源自法文moderne、后期拉丁文modenus,早期意為此時此刻,文藝復興之前已經確立現代與古代的區別,19世紀之前大部分有負面的意涵,直到19世紀,尤其是20世紀趨于正面——改善的、有效率的。現代化(modernization)在18世紀最開始被用于描述建筑物和拼詞法,常與機制、工業相關,用來表示令人滿意或喜歡的事物。由現代延伸出來的詞語,比如現代主義(modernism)、現代主義者(modernist)在意義上由廣義變為狹義,專指特定的潮流、趨勢。從人類文明歷史來說,“現代”特指西方世界在近代以來形成的價值系統,這一系統包括了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多個方面。政治上,“現代”主要是民主政治體制,也就是“五四”時期就風行一時的“德先生”;經濟上,“現代”主要是指經濟上的工業化,晚清“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洋務運動就引進了西方的軍事工業,開啟了中國的現代工業歷程;社會上,“現代”主要是指城市生活方式和自由民主思想的普及;文化上,“現代”主要是指人的價值和人性的張揚。
在20世紀中國,“現代”是包括文學在內的一切學科或知識的母題,一切非現代的事物都受到質疑或否定,新文學從一開始就懷著對“現代”的憧憬和期望,“現代”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價值、理想和未來,“現代化為中國當有的出路”[1]。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為代表的知識分子群體在尋求中國未來之路的時候,很自然地將“現代”的民主與科學作為西方富強的主要原因,而將沒有“現代”特征的傳統文化視為中國落后的重要原因。作為一場全球化的社會變革,“現代化”是貫穿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的時代主題,雖然這一時代主題的外來作用力大于其內在動力,而且這種外在動力首先引起思想、文化和政治變革,然后再推動經濟、社會變革,文學在這一過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從“現代”在中國產生和使用的語境來看,讓當時的人們單從學術立場進行討論幾無可能,“復古”或“西化”的論爭已經超出了中國傳統或西方現代的范疇,“現代”對于中國文學的影響更是超出了文學的范圍。不僅如此,“現代化”在中國的演進已經超出了社會理論的范疇,以及知識分子所倡導的客觀實證原則。從西方語境來看,“現代”僅是西方現代社會理論之一,而且經過韋伯、帕森斯等思想家的反思和批判,已經認識到“現代”是西方中心主義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現代”關注點已經轉移到“什么樣”的“現代”。對于中國來說,經過保守、激進、中立等不同立場的角逐,“現代”已經演化為更為綜合的概念——“用來概括人類近期發展進程中社會急劇轉變的總的動態的新名詞”[2],而且將“現代”具體到人的現代化和社會的現代化,其中自然也包括了文學的現代化。
李澤厚以“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來概括近代以來中國社會運動的基本趨向,其核心指向是中國現代化之路——“革命”,一個在復雜性上足以與“現代化”相媲美的詞匯。在通向現代化的道路上,“革命”與“反革命”的斗爭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都是中國社會的主流,一直到1954年第一次明確提出“四個現代化”,才將社會重心轉移到“建設”。即使如此,由于國內外復雜的形勢,反特斗爭、抗美援朝等現實威脅的存在讓“革命”從未真正遠離,反而在特定時期(比如“文革”期間)被一再放大。
因此,文學的“現代”是考察中國現代變革的窗口,從中可以發現中國社會、人心的變遷,更能看出中國文學通向現代之路的艱難歷程。
二、文學的幻象:“改革”的意識形態與現代化的想象
在20世紀80年代,國家和個人有著一致的現代化追求,改革文學就是充滿現代化想象的敘事,這種敘事與20世紀90年代的現代性紛爭有著緊密的聯系,現代性紛爭圍繞“現代”展開——什么樣的“現代”?如何才是真正的“現代”?如果脫離80年代的社會實踐、文化意識和文學想象,這些問題將難以回答。
改革開放以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現代化進程得以重新啟動,而且包含了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等多個層面的現代化,文學的現代化提上日程——文學為四個現代化服務已經成為社會共識。對國家而言,盡快改變“以階級斗爭為綱”及其造成的混亂局面、快速恢復正常的國家秩序成為當務之急,掌握科學技術的知識分子成為全社會最受尊敬的人。包括作家在內的人文學科的知識分子雖然不如自然科學那樣受人矚目,但顯然也深受鼓舞,自覺地加入到為四個現代化服務的大潮中。對個人而言,融入重啟的現代化浪潮,不僅是為了現實境遇的需要,而且也是壓抑許久的精神釋放和文化理想的重新張揚。
從現代化的視角,國家和個人達成了高度的一致,在文學上表現為現代化想象,改革文學就是其中最明顯的代表。改革小說的重要作品《喬廠長上任記》發表后引發的爭論焦點是如何看待四個現代化與“揭批查”運動的關系問題[3],批判者注重以“繼續革命”的立場討伐“四人幫”、林彪等的罪行,肯定者著重以“現代化”的眼光贊揚“喬廠長”的改革,最終改革的現代化訴求獲得了勝利。“改革”的意識形態作為改革小說的內在機制,成為評價歷史、人物和文學的標準,因為“改革”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重要動力和必然要求。其中,對于“時間和數字”的推崇顯示了改革小說對現代化思維的理解,而這種理解和文學表現不久前在蔣子龍的《機電局長的一天》中還被視為“唯生產力論”而遭到批判,盡管這種表現在后者還只是處于從屬地位。這種改變其實還是文學對于政治時局的積極回應,“建設的速度問題,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一個尖銳的政治問題”[4]。當然,改革文學對于政治的回應,并非被動地、違心地跟從,而是主動地、熱情地去回應新時代的到來,因為改革不僅是政治的需要,也是包括作家內在的廣大人民的心聲。如果說蔣子龍在《機電局長的一天》中對于生產力是一種現實主義的表現,那么在《喬廠長上任記》中對生產力則更像是一種理想主義的描繪,但效果卻截然不同——“機電局長”因沖淡了革命敘事而備受責難,而“喬廠長”因擔當了改革者、推動現代化的角色而被神化。
從現代化的視角看,現代人對物質和經濟的追求是正當、合理的,改革文學試圖改變人們原來傳統落后的經濟觀念,將經濟沖動作為文學敘事的核心內容。經濟頭腦、經營管理能力、科學技術水平等成為改革人物的標簽,政治不再是衡量和評價一個人的第一標準,搞活經濟成為共同的特征。典型人物的塑造也是如此,改革中的領導者必須有經濟領導才能,他們的所作所為都是圍繞經濟行為展開的,對人的價值的重新認定也是從經濟層面來實現,個人的經濟訴求得到尊重和鼓勵。作家們在面對現代化的時候,普遍持積極和歡迎的態度,其實具有理想主義和想象的成分,“面向現代化,首先是我們的文學作品要努力反映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偉大進程”[5]。理想化、想象化的改革文學對于生活的“現實主義”反映其實仍然帶有革命浪漫主義色彩,盡管改革文學一直被視為現實主義文學。雖然有人質疑改革文學對于政治的直接響應,認為文學又一次充當了政治的工具和宣傳的渠道,但是如果政治(改革)本身就具有合法性,那么這種工具或宣傳也是極有價值的。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作家的擔當意識和參與意識在整個社會上都屬于先覺者和先行者,對于作家的創作激情和介入現實的勇氣,無論如何都要加以肯定。
改革文學對于現代化的想象來自對于“現代”的焦慮,這種文學焦慮本身就具有一種現代性特質。長期以來,文學焦慮來自因物質的匱乏而引發的身體焦慮。很難想象,在物質匱乏的世界,如何要求作家能夠超越“現實”而無視關乎生存與發展的經濟問題。赤貧不再是光榮的象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也被證明是無法實現的幻象,作家的焦慮其實代表了廣大民眾對于生活和未來的普遍擔憂。文學焦慮和現實的需要讓改革文學在細節上不那么真實,例如《新星》寫李向南在貧困縣推廣水陸養殖和生態旅游,即使放在21世紀的今天仍然不過時,顯然對改革的環境、成本等現實因素沒有細加考究,圖解政治政策的意圖大于文學審美的真實表現。
總之,中國的現代化早已開啟,重啟“現代化”也并非恢復到中斷之前的“現代化”,而是重新提出對“現代化”的理解和闡釋。從改革小說來看,現代化已經成為一個類似框架性的原則或共識,“現代化”已經由西化轉變為“中國化”——空間的轉換帶來時間的分野。就“現代化”的邏輯而言,在完成現代化之前,“改革”應該沒有休止符,而“改革文學”卻沒有因改革的繼續而繼續風行。我們不能簡單地判定“改革”對于改革文學的決定性作用,或者很難說改革文學對于現實中的“改革”具有多大的推動作用。但起碼可以推斷,“改革”或“改革文學”中的一方,出現了某種不可調和的矛盾。就如《喬廠長上任記》中對于“數字和時間”的崇拜,在某種程度上是以經濟理性和政治正確性壓倒一切,沒有更進一步深入到文化層面,這是改革小說無以為繼的深層原因。
三、現代化敘事的流變:從改革文學到“現代派”小說
如前所述,改革文學的現代化敘事充滿了理想主義色彩,對于改革的外在表現(數字和時間等)大于社會表層之下的暗流涌動,文學形象對于改革者的神化超過對于人物內心的挖掘。
其實,在改革大潮中,變動最大、影響最深的并非數字和時間等客觀的經濟指標,而是改革在人心中掀起的巨大波瀾,是深入骨髓的人性糾結和精神裂變。現代化敘事圍繞經濟層面的結果,就是改革文學在審美上仍然延續“十七年文學”甚至“文革文學”的敘事模式,在人物塑造上要么因襲傳統清官形象,要么帶有“高大全”的無產階級英雄的痕跡,造成人們對于改革文學“空心化”“刻板化”的負面印象。對此,人們希望能夠看到改革之后的人們內心深處的變動,尤其是人性和精神的深刻一面。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王蒙的一組“意識流”小說其實就是“改革文學”(現代化)的變體,王蒙等作家正是看到了改革文學的弱點,才試圖采取截然不同的敘事方式來填充和彌補這一現代化敘事的空白和缺陷。
在現代化敘事的探索上,王蒙的《春之聲》等小說對于“四個現代化”的呼應毫不遜色,同時又有意識流等西方現代文學創作手法,在文學“現代化”的形式創新上更進了一步。王蒙作為主流作家的代表,對于黨的文藝政策和時代主題的把握超出常人,他在中國作家協會第三次代表大會上指出:“要使自己的作品、自己的言行切實有利于人民、有益于安定團結、有益于四個現代化”[6]。王蒙在意識形態上向主流靠攏的同時,又大膽地實踐了西方現代派藝術手法,在某種程度上打破了改革文學的桎梏,內容的保守與形式的激進相結合,顯示出與改革文學不同的敘事策略。“意識流”是典型的西方現代派藝術手法,王蒙并不是第一個使用的中國作家,但重啟了這一現代藝術,其價值并非作品本身的藝術水準,而是“以形式解放撞開了精神解放的大門”[7]。也就是說,王蒙的意識流小說以現代派藝術的形式創新,帶來了思想解放、審美解放的效果,重新恢復了中斷已久的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現代鏈接,這才是最有價值的所在。《布禮》以碎片化的時間流來表現對人生的思考,主人公鐘亦成因詩被打成右派,時間從1957年到1966年再到1949年,再從1966年到1970年再到1949年,從被批判、毆打到參加革命活動,從被懷疑到入黨宣誓,二十多年的精神歷程被交替錯落回放,支撐主人公的信仰、愛情、親情等在磨難中書寫了知識分子的血淚史和精神史。意識流寫法的優點是直白地書寫內心和精神深處,但王蒙筆下的人物還是有明顯的理性線索(比如20多處時間明確的標題),莊嚴與荒謬的并存與對立恰恰說明了這一點。相比改革文學,我們從意識流小說中看到了更多的精神和內心,盡管這種精神是以分裂和片段的方式展開,內心的揭示也被涂抹了層層偽裝,但是畢竟能夠感受到一種舊的價值體系的坍塌,以及重建新的價值體系的努力。除了對精神世界的濃墨重彩和深入挖掘,意識流小說對于人、人性和人物的把握也與改革文學截然相反,人的渺小與卑微替代了改革文學中英雄人物的偉大與堅強,激情燃燒的歲月化為虛無縹緲的夢境。
宗璞的小說《我是誰》關注人的“異化”問題,在寫作風格上更是接近卡夫卡的《變形記》,以現代派藝術的方式重啟了文學的知識分子問題探討。宗璞在“文革”結束之后,能夠較早地認識到并創作出《我是誰》《蝸居》等小說,可見具有強烈的現代意識。《我是誰》很顯然是對自己身份的追問,主人公韋彌一直困惑并掙扎著尋找自己的身份,外界環境給的身份讓她陷入痛苦和絕望的境地。一方面,在他人看來(甚至自己也認為),自己和很多教授、講師等一樣,都是痛苦不堪、傷痕累累的蟲在地上“一本正經地爬著”[8]。這里的“蟲”是一種身份的象征,意味著階級出身不好、思想反動,甚至直接被稱為“大毒草”“大毒蟲”。另一方面,自己的內心又強烈地意識到自己并非“蟲”,而更像是回歸祖國母親懷抱、立志報效國家的“雁”——在國外學有所成而心系祖國的知識分子,放棄國外的優厚待遇,投入戰火中新生的中國。韋彌和丈夫孟文起失去了作為學者的職業、權利,以及作為人的自由和尊嚴,而被稱為“牛鬼蛇神”、作為敵人而對待。孟文起的上吊和韋彌的投湖,不僅僅是失去了教授的職業和做人的身份,而且致命的是走向了“人民”的對立面而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因為他們回國的目的就是投入祖國人民的懷抱。也就是說,知識分子追尋自我的過程,其實是身份認同的過程,韋彌們的反思并不能確認其作為“人”的主體性,因為他們已經不自覺地將自己歸入“人民”的宏大敘事,即便自殺也只是逃避身份的無奈選擇,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其身份問題。可見,宗璞對人的“異化”書寫還停留在宏大敘事層面。造成異化的原因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外在的暴力,包括語言暴力和身體暴力,語言暴力帶來的精神折磨甚至要超過身體暴力帶來的肉體傷痛。二是自身的焦慮和缺乏反思意識,既要對外界、他人(包括“人民”)進行反思,又要對自我進行反思。當然,我們這里強調的不僅是宗璞的“反思”,而且是對宗璞“反思”的反思。
相比王蒙、宗璞等對現代派寫作手法的探索,徐星、劉索拉等對現代藝術的實踐已經深入到哲學和理念的層面,他們以反叛傳統的姿態書寫城市文化,這與20世紀80年代的城市化進程之間存在著內在的、有效的歷史聯系。城市本身就是現代化發展的成果,中國的城市由“城”和“市”構成,分別具有防御功能和經濟功能[9],中國文學中的城市應該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特質,比如中國傳統的詩性文化就是底蘊深厚的文化資源。但是,徐星、劉索拉等作家對于城市文化的書寫顯然更受西方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他們以青年亞文化代言人的姿態,側重于形而上地去表現當代城市人的生存狀態,尤其是那種無以名狀的壓抑感、空虛感、孤獨感和幻滅感,以及對生存方式和個體命運的抗爭、思索、追問。徐星、劉索拉等對于現代城市的書寫是一種“想像性寫作”,“想像這一概念絕不等同于‘虛假意識’,或毫無根據的幻想,它緊緊表明了共同體的形成與人們的認同、意愿、意志和想像關系以及支撐這些認同和想像的物質條件有著密切的關系”[10]。這里的“物質條件”就是20世紀80年代之后的城市改革和迅速發展,關于城市的現代性想像并沒有完全屏蔽文學所處社會的客觀性和作家的切身體驗。正好相反,關于城市的形而上想像是作家在城市生活經驗與現代思想建構相融合的產物,因此關于城市的文本一定是關于城市的經驗(包括形象性經驗),而城市經驗轉化為文學文本其實也是現代性想像的過程。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用戲謔的敘述語言和鬧劇式的情節來非線性地展示城市生存狀態,給人以陌生化的感性認識和真實性的精神體驗。徐星的《無主題變奏》以迷茫反諷的基調來展示城市生存的玩世不恭和真實痛苦,在消解精神豐富性、復雜性的同時,實現了現代哲思的直覺化、情感化,盡管這種城市人生顯得那么厭煩、冷酷、沉悶和疏離,但是又那么真實、深刻。這些“現代派”小說從一個特殊角度表征了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現代化想象和社會的現代化進程,表達了“個人”對“現代”的敏感體驗。
因此,從80年代到90年代文學的現代敘事流變,既是中國社會現實對文學期望和要求的提高,也是文學從更高的層面反映現實的敘事策略。
四、文學現代性的紛爭:從現代到后現代
從現代到后現代的轉變來看,20世紀80年代文學到90年代文學的轉變,其連續性遠遠大于斷裂性。20世紀90年代關于現代性的紛爭其實在80年代就已經開始,或者說是繼承和延續了80年代關于現代性討論的思想成果,但在實質上已經發生了轉變。從嚴格的意義上,所謂“現代性斷裂”“重寫現代性”等紛爭,與80年代就開始的“重寫文學史”“重估現代性”等相呼應,在方法論上都是西方現代理論的又一次上演。
有人用“幽靈”比喻現代性的復雜性和神秘性,仿佛是在指稱一種熟悉而陌生的存在。如果說80年代的文學現代性存在更多的共識(共同的現代化目的),那么90年代的文學現代性趨向更多的分歧(不同的思維方式)。汪暉對現代性進行了知識考古學的分析[11],在梳理西方現代性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中國現代性的研究思路,希望通過提煉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的“關鍵詞”來探究中國現代性的形成過程。與汪暉們不同,倡導后現代的學者提出了“現代性終結”的命題,認為中國社會、中國文學要走出現代性,其依據是中國社會結構發生重要轉型——市場化、消費化,再加上西方后現代主義思想的傳播,現代性逐步將被后現代取代。我們不得不追問:“當我們在談論現代性或后現代的時候,我們究竟在談論什么?”或者說,我們的文學中有沒有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我們如何面對文學的現代性或后現代?
首先,中國文學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確實發生了重大變化,產生了新的審美因素,現實主義文學復蘇與現代主義創作實驗頻出,不斷翻新的文學潮流和新的文化立場讓文學的現代性變得復雜和多元。尤其是1987年以后很多作家開始在作品中流露出對于既有意識形態的反諷和對于傳統價值信仰的否定,以各種方式來表現躲避崇高、對抗現實、消解意義,從文字游戲到游戲人生,喧囂中彌漫著一種刻意為之的審美傾向。但是,反叛現代性不等于后現代,文學的表面新氣象不一定帶來文學內在的新質。
其次,對于文學是否現代性或后現代的判斷,出發點和觀察角度很重要,從概念出發,還是從文學出發,也許會得到不同的結論。如果從文學創作出發, 90年代的先鋒文學與西方后現代主義文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不管是形式的模仿,還是精神的因襲,都流露出或多或少的痕跡。但是我們不能因此斷定先鋒文學就是后現代文學,更不能以西方后現代主義來衡量中國先鋒文學的價值和意義。如果從概念出發,用西方后現代主義的理論體系來套中國的先鋒文學,可能會失望地發現其中摻雜了現代性的因素,或者會驚喜地發現先鋒文學豐富了后現代的視域。我們需要注意的是,中國之所以引進和吸收西方后現代文學,肯定有其內在的審美需求和文學自覺,其中既有現代性訴求,也有對于后現代主義的好奇,不能簡單而論。甚至可以說,先鋒文學在最初時可以看成是現代派,而后才被視為后現代文學,文學語境的不同可能帶來相左的文學觀念。
再次,要分清楚文學和審美層面的“現代”與“后現代”,這與中國社會現實層面的“現代”與“后現代”有所區別,兩者既存在聯系,又不能等同。根據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以及西方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的歷史經驗,中國遠沒有達到后工業社會的階段,甚至有些地區還處于前現代社會。再者,就算是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也不意味著在文學、文化和思想上就能產生與西方同步的后現代主義。同樣道理,即使中國在經濟社會層面遠未達到西方后現代主義的水平,也不等于中國不能產生后現代主義文學因素。就如魔幻現實主義產生于經濟社會相對落后的拉丁美洲,而中國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莫言也被認為在作品中體現了類似風格,但判斷文學的標準絕不僅限于某種風格。
最后,與其辨析現代性與后現代的復雜關系,不如將其看成具體文學問題的語境和方法,立足中國文學實際比跟風西方潮流更為重要。20世紀90年代晚期的“文學終結論”雖然與世紀末的悲觀情緒有關,但也在某種程度上凸顯了文學邊緣化的現實。在后現代的視域下,對于文學邊緣化的認識更為明晰——從藝術中心走向邊緣、從文化中心走向邊緣,藝術領域中影視占據了中心地位,文化領域中以科技、創意、傳媒、資金等為紐帶的文化產業成為中心。現代科技的迅猛發展改變了社會面貌和人們的生活方式,依賴技術進步的綜合媒介藝術迅速崛起,文學往昔的優勢和光環不再。人們的價值觀念和文化觀念都發生了改變,已經不再遵從審美現代性所指定的規則,尼采美學所宣示的精神虛無也影響到中國,早在“五四”時期中國現代性初建時就伴隨著尼采批判的聲音,“尼采反對的是西方的現代,魯迅懷疑的則是正在建構的中國的現代”[12]。現代性與后現代的紛爭擴展了文學研究的領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文學觀念和審美認識,其中就包括對于20世紀90年代文學的判斷。從中西比較(中國文學現代性與西方后現代主義)和內外對比(文學內外、文化內外)的多維視野,為中國文學打開了更為立體的審美空間。
總之,以“現代性”這一敘事視角,通過考察改革文學到現代派小說等轉變過程,我們有充足的理由來重新“縫合”文學歷史的斷裂帶,重新對接80、90年代文學通道。如果不再局限于時間和年代的“細節”或人為割裂,而是從更宏觀的敘事層面上尋找中國現代性歷史經驗的文學表達方式,就能夠從文學角度發掘一條清晰的歷史脈絡,這樣的歷史脈絡更容易讓我們從內在視角來把握當代中國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認同。也許,在80、90年代文學連續性研究中,更有利于實現對當代文學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認同,并在連續性的時空中找到這種自我邏輯和內在規律。
[1] 金耀基. 中國社會與文化[M]. 香港: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2: 16.
[2] 羅榮渠. 現代化新論[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3: 8.
[3] 徐勇. “改革”意識形態的起源及其困境[J].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2014(6): 123?133.
[4] 《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一九七八年元旦社論.光明的中國[N]. 人民日報, 1978?1?1(1).
[5] 王蒙. “面向現代化”與文學[C]// 王蒙文集(第6卷). 北京: 華藝出版社, 1993: 492.
[6] 王蒙. 我們的責任[J]. 文藝報, 1979(11?12): 47?50.
[7] 楊義. 王蒙小說的哲學、數學與形式[J]. 山東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3(5): 5?15.
[8] 初清華. 新時期之初小說對知識分子身份的想象[J]. 文學評論, 2005(6): 79?85.
[9] 傅崇蘭, 白晨曦, 曹文明. 中國城市發展史[M].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9: 35.
[10] 汪暉. 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上卷·第一部)[M]. 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4: 4.
[11] 汪暉. 韋伯與中國的現代性問題[C]// 汪暉自選集. 桂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1997: 1?35.
[12] 郜元寶. 編選者序[C]// 尼采在中國. 上海: 上海三聯書店, 2001: 1.
Modernity relevance of literature in the 1980s and the 1990s
LU Yanpeng
(College of Art,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63, China;Chinese Department, Zaozhuang College, Zaozhuang 277160, China)
In literature studies on chronology or dynastic history, there exist two opposing ideological trends. So if we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1980s and the 1990s, it will be easier to find out the narrative historical continuity of the two, and that their innate continuity is greater than their superficial “rupture” and otherness. By seaming historical rupture, and by abutting literature passages from the 1980s to the 1990s from modern and holistic perspective, the present essay hackles the literary expression for Chinese modern history and experience, finds a clear historical context to grasp the self understanding and self identity of contemporary China, and explores the aesthetic logic and internal rules in continuous space-time. Modernist novels represented Chinese imagination and social progress of modernization in the 1980s and expressed individual sensitive experience to the modern, from which actually started the dispute about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sm of the 1990s.
historical continuity; modernity; literary modernity; dating literature; modernity narrative
[編輯: 何彩章]
I022
A
1672-3104(2017)03?0149?06
2016?12?18;
2017?03?11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文學的‘歷史連續性’研究”(13BZW126);山東省藝術科學重點課題“文明話語中的文學觀念:從晚清到‘五四’”(1607463);山東省傳統文化與經濟社會發展專項課題(重點項目)“傳統文化視角下的女性婚姻及其文學書寫研究”(ZD20161025)
盧衍鵬(1982?),男,山東臨沂人,文學博士,棗莊學院副教授,東南大學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文藝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