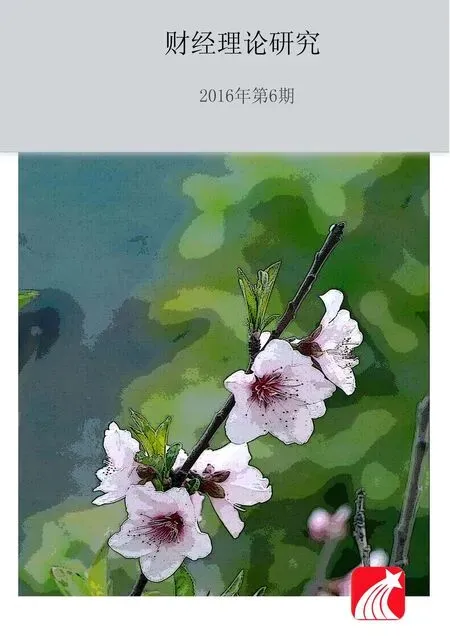糧食生產與農民收入協調性的經濟學分析
呂新業,胡向東
(中國農業科學院 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北京 100081)
糧食生產與農民收入協調性的經濟學分析
呂新業,胡向東
(中國農業科學院 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北京 100081)
糧食生產和農民收入之間的關系具有雙向性。本文通過對黑龍江、山東、吉林和河南4個糧食主產省的農戶調研數據,采用糧食生產和農民收入的協調指數,判斷糧食主產區糧食生產和農民收入的協調性。研究結果顯示,黑龍江省和吉林省糧食生產與農民收入協調性最差,這兩個省的人均糧食產量較高,農民收入主要依靠糧食生產,為糧食安全的貢獻較大,而農民的收入沒有得到相應的補償。雖然河南省也是產糧大省,但是鑒于人均耕地面積限制,其人均糧食產量較低,農民主要外出打工,投入糧食生產較少,農民收入主要依靠外出務工收入,其糧食生產與農民收入協調性較好。因此政府應該結合協調性指數,按照農民收入結構判斷其生產要素投入情況對糧食主產區分類別進行補償。
糧食主產區;糧食生產;農民收入;協調性指數
一、引言
民以食為天,食以糧為源,國家高度重視糧食生產,保障糧食安全。2004年以來,國家連續出臺涉農“一號文件”,實施相關惠農政策,歷史性的實現糧食生產“十一連增”,同時農民收入增長實現了改革開放以來的首次“十連快”。糧食生產和農民收入之間的關系具有雙向性,糧食生產規模擴大,可提升農民收入,而農民收入的提高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拉動農戶的糧食生產積極性。按收入構成,農民收入可分為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在農業生產過程中,各收入之間的比例呈現此消彼長的關系。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農業與其他行業比較效益差距不斷拉大,農民打工收入呈現快速上漲趨勢,工資性收入占農民收入的比重不斷加大,農業勞動力流出進程加快,農民土地流轉量增加,糧食生產退出現象凸顯。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政府大力支持農業,實施強農惠農政策,對糧食生產進行補貼,農民轉移性收入增多,農民生產積極性增強。究竟糧食增產對農民收入的促進作用如何,本文將從糧食生產與農民收入的協調性角度展開研究,建立相應的協調指數,運用糧食主產省份的相關調查數據進行比較,剖析糧食生產與收入協調性狀況,最終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目前關于糧食生產和農民人均純收入的關系以及兩者的協調狀況的研究較多。婁廈等(2014)利用統計數據運用因子分析方法對31個省份的糧食生產能力及農民收益進行分析,發現黑龍江的糧食生產和農民收入協調性極差,兩者的協調性要遠低于主銷區和其他主產區水平。柯炳生(1993)認為產量目標與收入目標的協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國家計委宏觀經濟研究院課題組(2002)的研究結果表示我國目前還沒有一個將糧食安全與農民收入一攬子統籌考慮的經濟政策,應該建立國家糧食安全保障體系和增加農民收入的支持體系。魏君英等(2009)和國家統計局寧夏調查總隊課題組(2015)研究發現農民收入較大幅度的增加不是由糧食增產帶來的,反而糧食增產與農民增收存在反向變動關系。糧食補貼政策提高了農民種糧積極性,但需進一步探索更為有效的補貼方式。解宗方(2012)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在于糧食價格長期偏低,糧食生產比較效益低,機會成本高;糧食生產效益不穩定,風險成本高;農資價格上漲,導致糧食生產邊際成本的增長高于邊際收入的增長,生產成本高。王娜等(2015)則認為對農民人均純收入有較大影響的是人均財政收入、家庭經營費用支出和財政支農總量;農藥施用量、第一產業從業人員數和糧食單產對主產區糧食產量有較大促進作用。
國內文獻大多采用統計數據對糧食生產和農民收入協調性進行分析,并已基本同意農民收入和糧食生產不協調。但是,關于農民收入和糧食生產協調性及農民收入結構與糧食生產之間關系的微觀研究較少。因此,本研究擬通過微觀調研數據,分析農民收入結構,并采用糧食生產和農民收入協調指數,對糧食主產省的協調性進行定量分析。
二、數據來源和糧食生產與農民收入現狀分析
(一)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來源于農業部軟科學項目“糧食生產與農民收入互動機制研究”支持下展開的實地調研。調研地區包含黑龍江省克東、山東泰安、吉林九臺、河南周口四個縣市,調查對象是當地糧食種植戶,收回有效樣本183個。樣本具體分布為黑龍江省42個,河南省38個,吉林省69個,山東省34個,其中有10個樣本量為合作社,其余均為一般農戶。本研究的糧食分類方法主要是參考《中國統計年鑒》。糧食主要是指水稻、玉米、小麥、紅薯、土豆(馬鈴薯)、大豆、綠豆等糧食作物。
(二)糧食生產與農民收入現狀分析
1.糧食主產省份的人均糧食產量分析
糧食主產省份的人均糧食產量有較大差距。根據調研數據顯示(表1),黑龍江省的人均糧食產量比其他省份的糧食產量高且糧食種類的分布較為單一。黑龍江的人均糧食產量明顯高于山東、吉林、河南等省份,且遠高于調查省份的平均水平,這得益于其耕地優勢、國家的扶持政策。黑龍江省的糧食總產量2007年為3462.94萬噸,2014年上升到6242.19萬噸,幾乎翻了一番。黑龍江省也是第一產糧大省和商品糧大省。調研數據顯示(表1),黑龍江的農戶的人均水稻和人均玉米的產量分別達到3644.0公斤和5412.0公斤,黑龍江玉米和水稻種植方面擁有比較優勢;人均小麥、人均大豆和人均綠豆的產量較小,人均產量沒有超過140公斤,而紅薯和土豆種植相對更少。對于山東的農戶來說,玉米和小麥是他們種植最多的作物,人均玉米和人均小麥的產量分別是663.8公斤和614.3公斤,其他的土豆、紅薯、大豆和綠豆的人均產量低于5公斤,說明這些糧食作物主要是農戶自食。吉林省大部分農戶都種植玉米,人均玉米產量是2444.2公斤,也有農民種植水稻、小麥和土豆,這三個糧食作物的產量在人均100公斤到160公斤之間。河南省作為傳統的農業大省,玉米和小麥是其主要的種植作物,另外作為我國的農業人口大省之一,人均耕地面積較少,導致人均糧食產量較低,人均玉米產量和小麥產量分別為519.0公斤和541.6公斤,7種糧食作物在河南都有種植,但只有玉米和小麥在人均100公斤以上,其他的農作物在100公斤以下。
4個省的總體情況,農戶水稻、玉米、小麥、紅薯、土豆、大豆和綠豆人均產量分別為563.3公斤、1910.3公斤、361.3公斤、12.1公斤、60.7公斤、34.9公斤和3.8公斤。玉米、小麥和水稻還是主要的糧食作物,尤其是玉米種植面積和產量高。這主要是畜牧業發展飼料需求量上升,玉米價格不斷上漲,農民種植玉米的經濟效益高;玉米是東北地區主要的種植品種,而調研的樣本一半來自于東北,玉米比重會高一些。

表1 調查省份的人均糧食產量 (公斤/人)
2.人均收入分析
人均收入分為人均種植業收入、人均工資收入、人均家庭自營企業收入和人均畜牧業收入,其中人均家庭自營企業收入是指自營工商業。人均種植業收入在所有的調查地區中最高的是黑龍江,達到20982.4元;其人均工資性收入在四個省中最低,僅為4186.0元;種植業方面的收入遠遠大于工資性收入、家庭自營性收入和畜牧業收入。黑龍江的農民人均土地最多(19畝/人),相對其他省份農民外出打工較少,所以農民的收入主要是種植業收入。在調查省份中,山東省的人均工資性收入最高,達到12680.1元,人均種植業收入、畜牧業收入和人均家庭自營性收入分別是8666.6元、335.3元和7755.1元。山東省第二第三產業較發達,對勞動力需求較大,農民農忙期間種植農作物,農閑期間就近打工或自己經營工商業,農民總的人均純收入較高。吉林省農民的人均收入要比黑龍江省和山東省少,和其他調查省份相比畜牧業的人均收入是最多的,吉林省畜牧業發展為農戶提供了較大比重的收入。河南省農民的人均收入僅有12725.9元,低于調查的其他地區。其中,人均工資性收入較高,主要是河南省農民外出務工的比重較高,相對來說其工資收入較多;而人均種植業收入最低,僅為2036.6元,還是地少人多,主要依靠外出打工增加家庭收入。總體而言,四省農戶人均種植業收入為7884.3元,人均工資性收入8248.8元,人均家庭自營性收入3030.3元,人均畜牧性收入是1030.3元。人均工資性收入已經成為了農戶的第一收入來源,農民外出打工已經成為了農民收入的最重要組成部分;以前的單靠種植業為生的情況已經打破,農民的收入種類多樣化(見表2)。

表2 調查省份的農戶人均收入 (元/人)
三、糧食產量和農民收入協調性指數分析
本研究引入協調性指數來對糧食生產和農民收入的協調性進行分析。此指數的原理在于利用比較優勢理論,將糧食產量和農民收入整合到一個指數當中,利用相對比較的方法,來對具體數值進行比較測度。利用數據縱向比較分析,從事物發展的角度去分析其內在規律和具體特點。其具體模型如下:
(1)
公式(1)中,k代表協調性指數,Xij代表i地區農村居民人純收入,YIJ代表i地區農民人均糧食生產量,Xj代表調研地區農村居民純收入,Yj代表調研地區農民人均糧食生產量。當該指數接近1 時,說明該地區糧食生產與農民收入處于協調狀態,該指數離1的距離越遠,該地區的協調性越差。數據主要是來自于實地調研所得,所以在本文中Xij代表i地區(黑龍江、吉林、河南、山東)的農村居民純收入;Yij代表i地區(黑龍江、吉林、河南、山東)的農民人均糧食生產量;Xj代表調研地區農村居民純收入,Yj代表調研地區農民人均糧食生產量。
從表3中的數據可以看出,調查地區的糧食生產和農民收入的協調性指數離標準值1有差距。黑龍江省的協調性指數是最小的,只有0.39,比標準值低0.61,說明黑龍江省農民的糧食生產沒有得到與之相匹配的經濟效益,農民收入和糧食生產之間極度不協調;山東省的協調性指數是3.19,遠遠大于標準值1,說明山東省農民的糧食生產得到了應有的經濟效益,且補償效益要遠遠大于總體平均水平;吉林省的糧食生產和農民收入的協調性指數是0.78,比標準值1低0.22,效益補償程度也低于總體水平。河南省糧食生產和農民收入之間的協調性指數是1.58,要高于標準值和黑龍江省、吉林省,河南省的農民種糧得到了補償主要是來源于打工收入,河南省農民外出打工較多,人均土地少,人均糧食產量低,相對來說協調性較高。

表3 調研地區的糧食生產和農民收入協調性指數
四、調查省份協調性指數差異的原因探析
通過測算協調性指數,發現調查地區糧食生產和農民收入的協調性指數差別較大,說明各調查地區的糧食生產和農民收入不協調。本文從兩個方面入手對不協調的原因進行分析,一方面是農民人均糧食產量和人均純收入之間的對應關系;另一方面是從農民的人均收入結構,分析農民的人均純收入的結構引起的協調性的變化。
(一)糧食生產和農民收入不對稱

圖1 人均純收入和人均糧食產量資料來源:調研數據.
根據調研地區的人均糧食產量和人均純收入的數據,研究中分析了人均純收入和人均糧食產量的對應關系(圖1)。黑龍江省的人均糧食產量最高,但是其收入并沒有同糧食產量一樣成為四個調研地區中最高的地區,在人均純收入中黑龍江的人均純收入只能排在第二位,和人均糧食產量沒有形成對應,黑龍江的人均糧食產量比總體人均糧食產量高2倍多,但是人均純收入比總體人均純收入高24%,協調性指數較低。山東省的農民人均收入為調查地區中最高的,達到29437元,比整個調研地區人均純收入高9000多元,但是山東省的人均糧食產量較低,只有1347.3公斤,比總體人均產量一半還低,導致了山東省的協調性要遠高于其他各省和總體平均水平。吉林省的協調性指數都在標準值以下,且人均純收入要小于總體水平,但人均產量和總體水平相差不大,所以這個調查地區的協調性是最好的;河南省的人均純收入是調查地區中最低的,只有12725.8元,比總體平均水平要低,同時河南省的人均糧食產量也是最低的,為1172.3公斤,比總體的人均糧食產量要低一半還多,但是在經過協調性的調整后,河南省的糧食生產和農民收入之間的協調性指數要好于黑龍江省和吉林省這兩個產糧大省(見圖1)。
(二)農民收入結構的變化
魏君英、何蒲明(2009)在研究中指出農民收入結構發生較大變化。本研究除了人均糧食產量和人均收入的對應關系外,協調性的極大差距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人均純收入的構成造成的。而農民人均純收入主要分為人均農業收入、人均家庭經營性收入、人均工資性收入和人均財產轉移性收入。因為人均財產轉移性收入的數據較少、不全面,因此,研究中并沒有報告其數據。在人均農業收入中,因為調查省份主要是國家糧食主產省份和地區,所以農業收入主要是種植業收入,人均家庭性收入分為人均畜牧業收入和人均家庭自營性企業收入。從表2中可以看出在人均純收入構成中,黑龍江的種植業收入是比重最大的,達83%;畜牧業收入和家庭自營性收入微乎其微;從這個比重的來看,在黑龍江省的農民主要靠種植業來增加收入,少量的農民會外出打工。在黑龍江土地資源豐富,農戶戶均耕地在40畝左右,有大約30%的農戶擁有40畝以上的耕地,較少考慮在外出打工和經營別的行業。山東省的農民人均純收入是調研地區最高的一個省份,工資性收入占農民的人均純收入接近一半(43%),另外山東省農民的種植業收入是29%,家庭自營性企業收入是26%,畜牧業2%,種植業收入占人均總收入的比重小。吉林省農民的收入來源主要是種植業收入和工資性收入,兩者比重分別是38%和40%,約占總收入的78%,吉林省農民的主要是這兩種。除此之外,吉林省的畜牧業發展較好,吉林省的畜牧業收入占人均總收入是15%,總體來看種植業收入和畜牧業收入兩者所占比例達到53%,農民的收入主要構成還是農業收入。河南省面對人多地少的情況,農民的耕地較少,人均農業收入低,很多的農民外出打工,工資性收入所占比重達到65%;人均種植業收入占16%,畜牧業收入占4%。農業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為20%,農民收入主要靠打工收入和經營性收入(見表4)。
總體來說,四個糧食主產省的農民的收入結構已經由原來的種植業收入為主轉變為以種植業收入和工資性收入為主的結構,工資性收入的比重越來越大,農民收入對種植業的依賴程度逐漸降低。

表4 調查地區農民的人均收入結構 (%)
(三)外部性補償機制不完善
婁廈等(2013)認為目前我國農民實行的種糧補貼是由國家和各個省的財政資金為主要來源,沒有一個根據市場變動和外部性大小進行調整的動態外部性補償機制。其具體表現形式為機會成本擴大,這里所提到的機會成本是由于糧農將土地、勞動力和其他生產資料都投入到了糧食生產當中,而失去了進行其他生產投入的機會;如果將這些土地、勞動力和其他生產資料投入到糧食生產以外領域糧農可能獲得更高的收益。也就是說,糧食安全的責任已經由糧食主產區的糧農承擔下來,但是應該得到的補償卻尚未兌現。把表3和表4結合來看,可以知道農民收入主要依靠種植業收入占較大比重的省份,則該省份的協調性指數低,像黑龍江和吉林;而收入中非農收入占主要地位的省份,協調性指數就高,所以說外部性補償機制的不完善使得糧食生產和農民收入協調性差。
(四)糧食增產與農民增收存在矛盾
魏君英,何蒲明(2009)通過對糧食播種面積和農民收入的相關性分析、協整檢驗、Granger 因果檢驗和離散分析,發現糧食增產與農民增收存在長期均衡的反向變化的因果關系。也就是說,糧食增產不僅不能帶來農民增收反而導致農民收入下降(包括相對額的下降),而農民要想增加收入,就應該外出打工,應該減少糧食生產。這個觀點從側面支持了調研中各省份農民投入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生產糧食不如外出務工,農民會選擇外出打工,農民工資性人均收入在人均總收入中的比重比較大,工資性收入成為農民的主要收入,投入越多生產的糧食越多,收入增長不足以彌補將投入要素放在其他地方增長得多,糧食生產和農民收入越不協調。
五、政策建議
(一)加大糧食生產補貼支持力度
農民收入結構存在著此消彼長的關系,當外出務工收入要高于糧食生產收入時,農戶也會降低糧食生產要素的投入,轉向其他領域。因此,繼續加大糧食補貼力度,對于穩定糧食生產具有意義重大。首先,應繼續推行農業直接補貼、農資綜合補貼、良種補貼和農機購置補貼,科學制定補貼發放標準,確保補貼政策落到實處。其次,糧食補貼要針對生產的規模分別實施,不同農戶要根據其生產規模分層次、分標準進行補貼,大幅提高大規模農戶的補貼力度,適度提高或維持中小規模經營組織的政策補貼力度,國家惠農政策多向大規模農戶傾斜。再者,糧食補貼向新型經營主體傾斜,重點鼓勵和扶持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依靠龍頭企業輻射帶動能力,帶動中小規模農戶進行糧食生產;同時對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及其他新型經營主體的糧食生產進行重點補貼。
(二)多層次開展財政扶持政策
針對不同地區及不同糧食生產經營主體,應推行多層次的糧食生產補貼政策。一方面,針對省級糧食生產的財政扶持政策,可以根據不同省份糧食生產對國家糧食安全的貢獻力度大小分標準進行扶持,給予糧食生產大省更多的補貼,確保主產區糧食穩定供給,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另一方面,對于省內不同地區或不同經營主體,可根據生產者糧食生產的協調性進行補貼。也即,相關部門可根據生產者的收入結構進行補貼,對于依靠農業收入的生產者給予更高的補貼,對于具有更多收入渠道且農業收入所占比重較小的農戶,可以適當縮減其糧食補貼力度。當然,該種補貼的實施可能要按照區域性整體推行,針對各個農戶分別實施其操作成本太高。
(三)多渠道提高農民收入
在進行糧食補貼的同時,要積極推進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給予勞動力轉移更多的便利,解決其轉移的后顧之憂。另外,出臺鼓勵農民進行本地務工的扶持政策,引導農民更多地向本地務工并合理分配兼業狀態,在增加收入渠道的同時確保糧食穩定生產。同時,要推進鄉鎮企業對農民工的吸收力度,給予其低息貸款、減免、稅收和法律援助等方面優惠,提高鄉鎮企業創造就業的能力。再者,積極開展糧食生產、外出務工和創業等方面的培訓,聯合政府部門、農業科研教學單位、涉農企業等力量,推行龍頭企業主導型、政府主導型、農業科研教學單位、農業合作組織主導型的技術推廣模式,為農民提供免費的技術培訓,降低個人培訓成本,提高農民增收能力。
[1] 國家統計局寧夏調查總隊課題組.寧夏糧食主產區農民收人增長問題研究[J].調研世界,2015,(5):28-31.
[2] 國家計委宏觀經濟研究院課題組.保障糧食安全與提高農民收入關系研究[J].經濟研究參考, 2002,(92):2-48.
[3] 黃利會,王雅鵬.城市化、糧食生產與農民收入增長關系研究[J].生態經濟,2009,(3):45-48.
[4] 姜天龍,郭慶海.農戶收入結構支撐下的種糧積極性及可持續性分析[J].農業經濟問題,2012,(6):14-20.
[5] 柯炳生.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業政策目標的沖突與協調——兼論糧食生產、價格和農民收入的關系[J].農業經濟問題,1993,(2):38-43.
[6] 婁廈,劉慧萍,張德華.基于因子分析的黑龍江省糧食生產與農民收入協調性分析[J].中國農學通報,2014,(14):130-135.
[7] 邱書欽.糧食生產核心區農民收入現狀與增收對策分析[J].經濟研究導刊,2013,(29):24-27.
[8] 王娜,高瑛,王詠紅.中國糧食主產區糧食生產和農民收入影響因素分析[J].青海社會科學,2015,(2):49-56.
[9] 魏君英,何蒲明.基于糧食安全的糧食生產與農民收入關系的實證研究[J].統計與決策,2009,(6):100-101.
[10] 解宗方.糧食生產過程中的不協調性分析——以河南省為例[J].農業現代化研究,2012,(5):281-285.
[責任編輯:郭秀艷]
Economic Analysis on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Grain Production and Farmers’ Income
LV Xin-ye,HU Xiang-dong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Grain production and farmers’ income are bidirectional relationship; the paper determines the coordination of grain production and farmers’ income by the coordination index of grain production and farmers’ income with household survey data of Heilongjiang, Shandong, Jilin and Henan 4 major grain producing province.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grain production and farmers’ income coordination is the worst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and Jilin province, the per capita grain yield is higher in the two provinces, the income of the farmers mainly relies on food production, food security and the larger contribution, the income of the farmers did not receive appropriate compensation. Although Henan province is the major grain producing province, but the per capita arable land area, per capita grain yield is low, mainly migrant workers, farmers, grain production investment is less, and the farmers’ income mainly depends on the income of migrant workers, the grain production and farmers’ income better coordination.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mbine the coordination index, according to the structure of farmers’ income to determine the input of production factors to compensate for the main grain producing areas.
main grain producing areas; grain production; farmers’ income; coordination index
2016-08-17
農業部軟科學項目(D201433)
呂新業(1973-),男,黑龍江克東人,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研究員,博士,博士生導師,從事糧食安全及農業政策研究.
F326.11
A
2095-5863(2016)06-00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