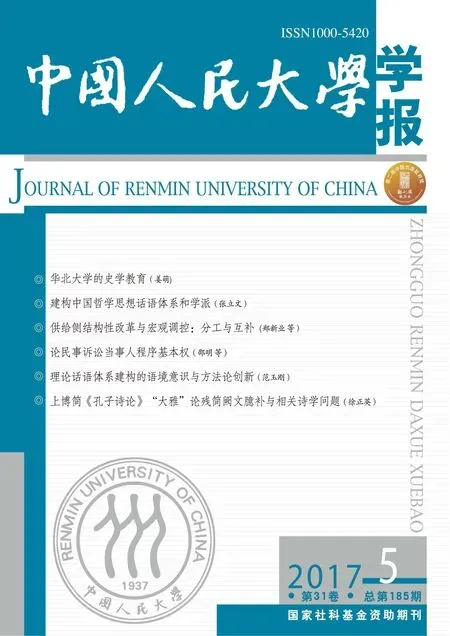理論話語體系建構的語境意識與方法論創新
——基于中國審美經驗的理論思考
范玉剛
理論話語體系建構的語境意識與方法論創新
——基于中國審美經驗的理論思考
范玉剛
任何理論都關乎現實,從理論生成性來看,每一種理論都有其生成的語境和發生作用的界域,理論建構的有效性與理論的偏頗顯現于以現實為軸心的敞開中,從而彰顯了理論話語體系建構的語境意識和反思維度。不能套用西方理論來剪裁中國人的審美體驗。要增強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自信。建構中國理論話語體系,需要立足多重視野的中國審美經驗及其方法論創新。
理論話語體系;語境意識;中國審美經驗;中國道路;方法論創新
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講話中指出:“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1](P8)伴隨中國的文明型崛起,中華民族正邁向偉大復興的征程,理論工作者應該何為?中國越來越靠近世界舞臺中心,世界也越來越重視中國,世界需要中國發聲。面對全球治理的難題和困境,需要中華民族貢獻智慧,需要中國提供解決方案。中國以什么發展理念建設一個現代化國家?任何對于中國道路的外來理論都要重新語境化,并經由本土經驗的實踐檢驗才能發揮效力。同時,文化的自信在滋長著中國話語體系建構的內在要求。伴隨文藝精品的不斷涌現和民族文藝的經典化,亟須建構基于“中國審美經驗”的理論話語體系,以中國文化的主體性來表征文論和美學的自覺。在此,本文倡導一種視界融合、多學科交叉、跨界的“中國經驗”研究范式,以建構有國際通約性和中國價值訴求的中國文藝理論,使其匹配于中國發展現實和中國道路,從而提升中國文論研究的國際話語權。
一、任何理論都是關乎現實的
從理論有效性來講,任何一種理論都有其生成的語境和發生作用的界域,都有其意識形態色彩或者價值訴求,而不能在跨文化語境中簡單隨意移植和挪用。任何外來的理論給予我們的只是啟發和參照,而不能成為本土理論建構的主宰,更不能由此成為理論霸權。某些西方理論在界域內的有效性,不能表明“理論旅行”和簡單移植后可以完全適用于中國現實,現實中往往會發生理論誤讀或扭曲“中國經驗”,導致強制闡釋中國文藝或文化現實。一些現代西方理論對中國文藝現實和審美經驗的強制闡釋,正好顯現出某些理論旅行后的無根性。近年來學界的反思愈發顯現出基于“中國經驗”建構中國理論話語體系的緊迫性和現實性,亟須中國文論和美學研究的理論自覺。
關于理論與現實的關系,文學理論家喬納森·卡勒曾指出:“文學理論并不是一套脫離現實的思想,而理論作為一種推理論證的實踐存在于讀者和作者群體之中,和教育文化機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2](P126)理論并非漂浮于空中,而是內在地嵌入現實的文化網絡,并與各種實踐、觀念發生持久性互動,由此參與文化現實的建構。理論的生命力源自對現實的回應和創新沖動,并非理論自身的單純推演,正是現實變化的壓力成為理論發展動力。有學者指出:“每一個歷史時期理論的主導因素各不相同,可以看到縱向理論譜系產生巨大作用的情況,也可以看到現實世界促使理論范式深刻變革的局面。然而,追根溯源,橫向關系的作用是決定性的。現實世界始終強有力地楔入理論。理論的真正使命是:闡釋、解讀現實世界,繼而參與現實世界的改造實踐。”[3]可以說,現實強有力的問題召喚使理論創新層出不窮,理論與現實的互動包含了多維的遞進對話,甚至是跨文化的文化間性、研究范式間的對話,從而體現基于現實經驗的理論擔當。如歐洲“現代主義”理論的建構就脫離不開資本主義發展的階段性語境。現代主義理論作為一個總括性術語主要指1890年至1930年間主導歐美知識界的理論和文化運動,其內涵從個體性的文藝實踐開始擴及廣泛性的文化運動,超越了文體學而擴大到現代主義者回應并試圖改造的社會、經濟以及政治現實。盡管其內容駁雜,但無論是前衛派或現代主義者,其理論要義都在于“回應西方文化中不斷加劇的商品化,一方通過竭力從商品化對象中清除或者抽取出他性(the otherness),借以進行藝術生產,而另一方則要徹底擺脫商品化對象,尋求作為‘純粹形式’的藝術”[4](P352)。從嚴格意義上講,“現代主義”的命名是美學意義上的,雖然表現形式多樣,甚至有不同政治立場,對其內涵的理解卻離不開如下語境:現代大都市的興起、世紀轉折時期的文化危機、“烏托邦”文化復興希望與墮落至“大眾文化”野蠻狀態的恐懼之間的危險結合,以及現代技術帶來的“時空壓縮”。洞察其美學追求可以看出,現代主義者的“審美”活動往往有著強烈的政治傾向,是一種文化視野下的政治理論;甚至可以說“他們希望更新現代生活,為了實現這一目的,他們建立了自己的組織”[5](P352)。可見,現代主義者試圖把美學造就為一種意識形態,借以抵制資本主義的商品化和物化過程,在審美基礎上重新思考政治,將文化創造的價值置于社會的中心位置。通過強調審美的優先性,追求政治審美化,現代主義者使公共領域重新恢復了活力。對此,有學者指出:本雅明和阿多諾“兩人都有一種現代主義的信念:即藝術是現代性烏托邦訴求的最后避難所,而且他們作為現代主義者,都不大愿意出于更新現代生活的目的而在理論上為其建構制度基礎。他們的烏托邦激情和實踐上的開放性所體現出的現代主義視野,再次說明現代主義作為政治理論一貫具有的巨大力量,即在思考歷史性現在時的需要方面所表現出的毫不妥協的韌性。不幸的是,他們也復制了現代主義的致命弱點,即不能形成一種足夠務實的政治視野,以引起對現實政治震蕩的嚴肅關注”[6](P368)。由此使我們認識到,理論建構的有效性與理論的偏頗往往顯現于以現實為軸心的敞開中,從而彰顯了理論背后的問題導向及其現實關懷。
從世界經驗來看,20世紀60、70年代,歐洲大陸的后結構主義(包括德里達的解構理論、福柯的話語理論、拉康的心理分析理論)、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包括法蘭克福學派、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阿爾都塞的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以及英國新左翼的文化研究,相繼經由美國各大學的比較文學研究學科,在美國的大學和社會廣泛傳播,但這些“歐洲理論”只是進入了美國的大學課堂而沒有產生很大影響。只有在80年代后與美國本土文化和社會思潮如民權運動(反種族歧視)、婦女解放運動、反越戰運動、反文化運動等相交融,有了現實問題意識后才被發揚光大。盡管學界對這場社會文化運動的性質認識不同,但正是經由美國本土文化的激蕩和理論沖擊,使這些“歐洲理論”經再語境化實現了“美國化”,生成了具有美國文化意味的“后現代主義”理論思潮,包括與之相關的性別研究、種族(族裔)研究、身份政治研究、后殖民理論等批評學派。這些理論在美國本土化后,逐漸失去原有的批判性鋒芒和政治化訴求,形成一種與美國政治、經濟相吻合的非批判的去政治化的大眾文化思潮。這種理論在凸顯“美國性”中開始關注非經典文本(如少數族裔文學、黑人文學、女性主義文學、非西方國家的文學)、非文學文本(如電影、音樂、電視劇、脫口秀等),在美國一些本土理論家如蘇珊·桑塔格等以“反對闡釋”等策略,以“為什么是莎士比亞而不是我們的《欲望號街車》?為什么不能是我們的百老匯?”等問題向大學課堂和文藝經典提出質疑和挑戰。在各種力量的合力作用下,這些變異的理論在學術競爭中成為強勢的美國理論和思潮,而開啟了美國多元文化主義思潮主導的時代,最終占據了美國大學課堂和博物館等經典闡釋的場域,并作為美國的“主流理論”,向世界推廣輸出繼而成為全球“主流理論”,有力地支撐了美國的全球“文化霸權”。
任何一種成熟的理論話語體系都是民族文化的產物,是在不斷交流互動中完善的。從理論旅行和嬗變來看,異質性理論不僅要隨時代語境的變化而變異,還要與本土文化及其社會思潮相融合,在凸顯自身理論訴求中形成不同的研究流派,才能獲得理論的有效性。這些新質的“美國理論”已失去“歐洲理論”的原初批判性、激進的政治性訴求,越來越呈現多元化、非中心和去政治化傾向,在文化多元主義的“常態化”過程中,弱化了理論批判性,為新自由主義的流行和全球傾銷掃清了障礙。理論因越來越追求“政治正確”而喪失了現實力量,使大眾文化成了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在置換和新質的理論生成中,“歐洲理論”成了“美國理論”,并融入美國的主流價值訴求。美國學界和社會對待異質性批判理論的策略,以及本土理論話語體系的建構及主流價值訴求,愈加凸顯理論生成的歷史文化語境的重要性。任何理論都不能被抽象化理解,理論旅行的再語境化不可以缺失“價值化”,這種“價值化”往往與問題導向相關聯。恰恰通過弱化原初理論的批判性和重新“價值化”,“美國理論”在本土化中流行傳播開來。由此歐洲理論經由“美國化”成為全球的,并成為世界主流理論,這背后有著強大的美國文化力量做支撐。
理論因問題意識和現實關懷成為本土的,有著本土文化的支撐,才能在競爭中被大眾接受,進而成為有本土風格和氣派的某“學派”,從而產生深刻的影響。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大量西方文論和美學理論進入中國學界,世界文化思潮的激蕩使“中國經驗”不會自閉于世界經驗,“中國理論”更不會孤立于世界理論。尤其是西方文論和西方美學已成為中國文論話語體系建構不可剔除的部分,只有在與現實問題相關聯的再語境化中增強反思意識,成為“中國理論”,才能有效闡釋“中國經驗”,而不是肢解、扭曲甚至強制闡釋“中國經驗”。有了基于“中國經驗”的成熟的“中國理論”,以厚重的中國文化為依托,同樣能成為全球性理論,其理論觀點和價值訴求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和認可,不斷增強在全球的理論競爭力和說服力,其話語體系因立足人類公共性問題,具有理論普適性和審美共通性,自然就成為國際主流話語之一。
理論的演變邏輯啟示我們,無論是西方學者對中國經驗的闡釋,還是中國學者“征用”西方理論對中國經驗的詮釋,都有一個現實的價值立場和態度問題,也就是說,必須葆有反思的維度和語境意識才能本真地切近對象。不論是中國經驗還是理論話語體系建構,其闡釋既要觀“物”也要觀“我”,這樣才能洞察理論和經驗本身的問題意識和價值訴求,從而最大限度地實現間性的溝通與平等,以自主身份參與國際學術話語生產,發出中國學者的聲音,提出中國的理論主張,從現實性來看,建構中國當代文論和美學話語體系,西方文論和美學理論不可繞過,它已然置身當下的現實文化語境。西方理論不僅是中國理論話語體系建構的“他者”,也是重要資源。但在“理論旅行”中不能簡單移植或者復制,更不能成為中國理論的主導,而是經由本土文化的洗禮或者再語境化過程,才能在一種相互沖擊甚至沖突中實現理論對話和交融。本土文化的結構、性質和開放水平決定著異質性理論對話和交融的程度,由此會出現批判性、反思性與屈從性等情形,而導致某種理論變異,進而在與本土理論激蕩中生成新質理論。這種雜糅性的新質性理論在觀照“中國經驗”時,就成為建構中國理論話語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成為“中國理論”。其背后支撐理論話語體系的是強大的文化自信及強烈的社會主流價值訴求。這個過程也許是緩慢的,但最終一定會與政治變革、經濟發展和文化建設相匹配,形成有自身文化底色和現實經驗闡釋效力的理論體系,從而擁有理論話語權,成為一種維護文化領導權的力量。
二、理論建構的語境意識及其文化自信
洞察理論發展史,任何有擔當的理論都厚植于某種民族文化自信的土壤。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曾精辟地闡釋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發展之間的關聯,在西方現代性理論背后凸顯的是基督教文明的自信。今天,基于“中國經驗”建構中國文藝理論和美學話語體系,其背后依托的是中國文化自信,是優秀中華傳統文化的自信,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自信,是能有效應對和闡釋中國問題、中國現象、中國經驗的理論自信。中國經濟經過近40年高速增長所創造的奇跡,“中國天眼”落成啟用,“悟空”號在軌運行一年多,“墨子號”飛向太空,“神舟十一號”和“天宮二號”遨游星河,等等,以及遵循新發展理念所創造的中國奇跡,積累了一系列現有理論難以有效解釋的問題,亟須“中國理論”來闡釋中國經驗和中國道路,這是當代理論工作者的責任和使命。“這種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必將給理論創造、學術繁榮提供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7](P8)正處于現代化進程中的中華民族,面對中西文化交匯、融通的未確定、未規范的雜糅狀態,如何充分表達自己的理論主張?應該以什么樣的姿態發出中國聲音?
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著重探討建構有中國特色的新理論、新范疇、新體系。“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應該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從我國改革發展的實踐中挖掘新材料、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觀點、構建新理論……提煉出有學理性的新理論,概括出有規律性的新實踐。”[8](P21-22)對中國問題的真正有效解釋,將是當代中國人對世界做出的最大貢獻,因為只有真正解釋中國,才能有效解釋世界。對于中國文論研究和文藝發展來講,就是要深入思考和探索文化自信視野中的中國當代文藝發展道路和文論與美學話語體系建構。 “中國理論”不是基于本土資源的文化部落主義式的自說自話,而是必須從人民群眾創造性的實踐活動和豐富多彩的審美活動中汲取養分,在充分開放交流的國際學術話語中張揚“中國性”。中國的也是世界的,其相互通約的底蘊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和對世界共同價值的遵循。究其根本,“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現成的教科書”[9](P21)。中國成功走出了一條不同于西方卻更加現代化之路,中國的成功必然有著價值上的感召和理論上的普適性,這種價值和理論遠未得到學術界的充分闡釋,未能建構相應的學術話語體系。“在解讀中國實踐、構建中國理論上,我們應該最有發言權,但實際上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在國際上的聲音還比較小,還處于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境地。”[10](P24)這揭示了當前理論研究的困境和局限性,亟須建構有效闡釋“中國經驗”的理論及其話語體系。
“中國理論”及其話語體系建構的邏輯起點是“中國經驗”,此中關鍵是對“中國經驗”的理解和闡釋。中國文藝理論和美學話語體系的建構同樣要以“中國經驗”為觀照對象。“中國經驗”并非自明的現成性存在,更不是固定的靜止存在,而是在流變中被不斷闡釋的概念,其內涵取決于特定的歷史文化語境。“中國經驗”雖有客觀性,是一定時空條件下和特定歷史階段的地方產物,但它并不外在于世界,而是處于與世界共在之中,有其相互交流和可通約處,故而不能過于強調“純粹中國性”。有學者指出,“中國經驗”既是客觀存在的、有待發現和闡釋的現象,也是通過理論燭照,被不斷重新發現、重新闡釋的產物。討論當代中國文論話語的“中國經驗”,應該同時在三個維度上展開:其一,從起源學和發生學的角度識別“進入中國的‘異質經驗’”,其認為“中國經驗”自身就包含了西方異質性因素的影響;其二,發掘基于人類文明共性的“共同經驗”,并非所有的外來經驗都具有異質性,文化的共同性和理論的通約性是人類文明得以交往的前提;其三,“共同而有差異的經驗”成為發掘中國經驗獨特價值的重要內容,立足于異質性差異的識別,而確立“具有中國性的‘特色經驗’”[11]。這進一步啟示我們,理解和界定“中國經驗”一定要有語境意識。當下的“中國經驗”是一種雜糅性存在,置身于當代中國現實文化語境中,現實文化是其得以可能的歷史境域。所謂“中國經驗”不能是孤懸宇宙的孤立靜止的存在,理解和建構“中國經驗”要辨析它之于“西方經驗”“世界經驗”的獨特性,在中西比較視野甚至雜糅古今的人類文明意識中,領會“中國經驗”的內涵所指,而不必計較于能指的漂浮不定。在一個全球化與本土化深度纏繞,歷史性、當下性與未來性相互交織的時代,中國發展已進入多重視界融合的“新視野”,三期疊加的現實使理論面臨的現實問題更趨復雜,人文思辨愈加激烈,促使基于“中國經驗”的理論話語體系構建必須凸顯反思維度。
現實中,盡管中國文化建設有了長足發展,國家“軟實力”不斷提升,但在文化貿易尤其是核心文化產品貿易中仍有不小逆差,更嚴重的是版權貿易中顯現的思想理論原創的落差,其差距不是在縮小而是依然在擴大,這與中國經濟的發展、國際地位的提升和世界對中國的期望極不相配,愈加凸顯了建構“中國理論”及其話語體系的緊迫性。習近平總書記一再強調,要讓世界知道“學術中的中國”“理論中的中國”,打造、建構一套有高辨識性、核心標識的為世界普遍理解和認同的學術概念及其理論話語體系。在世界文化格局重塑和理論話語權競爭的時代語境下,中國當代文藝不僅要以精品創作生成民族文藝經典,為世界貢獻特殊的聲響和色彩,還要在理論闡釋的有效性和審美經驗的傳播中做貢獻。建構中國文論和美學話語體系,必須思考理論研究的“中國問題”和“中國經驗”。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不能套用西方理論來剪裁中國人的審美,更不能用簡單的商業標準取代藝術標準,把文藝作品完全等同于普通商品。”[12](P29)中國文論話語關鍵詞的提煉和標識性符號的建構,既要看到中國文化、文藝和審美經驗的獨特性,又要關注其與西方文化(文藝和審美)的可通約性,因而厘清“中國經驗”的內涵及其復雜關聯是建構“中國理論”的邏輯起點,更是建構中國文論和美學話語體系的敘述起點。
“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3](P17)實踐表明,沒有文化自信,就不可能寫出有骨氣、有個性、有神采的作品。在理論建構上,沒有文化自信就難以實現理論擔當。中國文論和美學話語體系建構要關注“中國文藝和審美現實”“中國藝術及其審美經驗”,以文藝形式和理論思維及其審美理念來書寫現代化、城市化進程中普通中國人的心理情感變化及其價值訴求,以“作為具體的而不是抽象的人民”的情感和生活作為主要書寫和研究對象,來觀照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歷程。天是世界的天,地是中國的地,只有眼睛向著人類最先進的方面注目,同時真誠直面當下中國人的生存現實,我們才能為人類文明提供“中國經驗”,中國文藝才能為世界貢獻特殊的聲響和色彩,文藝才能說“中國話”,也才能說“世界語”,而不是依附于強勢話語充當爬蟲,以此來觀照對象的理論才能是“中國的”。所謂“世界文學”,乃是成熟的民族文學的復數形式,是各民族之間平等的互看,是揚棄“西方中心論”的多元文學話語的交流、交鋒和競爭,是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關注和文藝展望,是對“世界價值”的普遍遵循和藝術表達,而非依附于某種理論霸權的無效解讀。究其底蘊,中華文化既是歷史的也是當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是依存于中國當代現實的古今中西的匯集。只有扎根于腳下這塊我們生于斯、長于斯的土地,文藝創作和理論研究才能接地氣、增加底氣、灌注生氣,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理論建構在傳承根脈、包容發展、指向未來中,經由不斷轉化和超越,才能建構出更多體現中華文化精髓、反映中國人審美追求、傳播當代中國價值觀念、符合世界進步潮流的話語體系,在理論創新與完善中弘揚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
中國理論所依托的“中國經驗”不是作為“他者”存在,不是對西方強勢學術話語的補充,而是“世界中的共在”,是多元現實中的一元,其依托的是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這是擁有學術話語權和理論擔當的基礎;是對基于中國立場的普遍性的一種特指,是中國對全球治理的文化貢獻。它本質上體現了自覺的身份意識和文化認同,是“學術中國”自信的表征。現在有些期刊倡導講學術故事、學人故事,就體現了中國理論話語體系建構的自覺。藝術人類學強調藝術生成的社會語境,旨在對普遍理論持有一種本能的戒備和抵抗。當下,世界多元化和文化多樣性需要多聲部和包容性發展,需要中國發出聲音,需要中國貢獻方案。作為現代性訴求,審美現代性經驗并非尋求一種大一統的堅固存在,而是揭示一種多樣化、流動性狀態,展示多樣性審美體驗和藝術表達,成為“中國理論”生成和話語體系建構的機遇。作為其組成部分的中國文論話語體系建構,就要以多重視域中的“中國問題”和“中國經驗”為研究對象,在建構過程中要有明確的身份意識和價值立場,不能在熱衷于“去價值化”“去歷史化”“去中國化”“去主流化”中依附于西方理論,那種亦步亦趨、缺乏獨立性、自主性、創造性的理論遲早會被淘汰。
中國文論話語體系建構要落在“中國的”審美經驗上,體現當代中國人的藝術追求和價值訴求。審美經驗是對文藝作品和現實及其關系的藝術鑒賞與審美感知,當代文藝發展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人民是文藝的鑒賞家和評判者,理論體系建構同樣要體現人民性訴求,作為對中國人審美實踐升華的審美感知、審美意識和審美理想追求,審美經驗以其通約性和審美共通感的追求可上升為理論概念體系。“中國理論”因有效闡釋“中國問題”,在與異質性理論對話和交流中相互借鑒和參照,并訴求“和諧世界”“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而不會形成理論霸權。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新年賀詞中指出,國際社會期待聽到中國聲音、看到中國方案,中國不能缺席。在2017年新年致辭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人歷來主張“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中國人民不僅希望自己過得好,也希望各國人民過得好。這一重要宣示,深刻展現了“中國夢”的世界情懷,展現了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使命擔當。可見,中國的審美經驗不是“井底之蛙”的孤獨感,而是扎根深厚的文化傳統的傳承,有著世界情懷的大格局。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中國共產黨人不是歷史虛無主義者,不是文化虛無主義者。“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傳承者和弘揚者,又是中國先進文化的積極倡導者和發展者。”[14](P2)“當代中國是歷史中國的延續和發展,當代中國思想文化也是中華傳統思想文化的傳承和升華,要認識今天的中國、今天的中國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國的文化血脈,準確把握滋養中國人的文化土壤。”[15](P12)在“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中,文藝和審美是最好的溝通橋梁,只有把跨越時空、超越國度、富有永恒魅力、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弘揚起來,把立足本國又面向世界的當代文化創新成果傳播出去,才能建構真實的中國形象,“中國理論”才能獲得世界的認可和遵循。中國文論話語體系建構,就是基于對書寫“中國經驗”的文藝作品及其現實審美關系的觀照,其理論有效性的基礎——對文藝作品和現實的審美感知與欣賞批評,及其對系列核心概念的提煉,如人民性、崇高、形象、意象、意境、氣韻、境界等,要作為審美的“中國經驗”的標識性符號,也包括對現實世界的“審美改造”和生態環境保護與美化,并在文化傳統、現實要求和藝術追求的審美理想的平衡中訴諸世界共同價值。
“哲學社會科學的特色、風格、氣派,是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成熟的標志,是實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體現。”[16](P15)作為理論建構基礎的“中國經驗”,以中國社會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為觀照對象,以中國越來越融入世界并靠近舞臺中心、中國文化傳統與西方現代文化相互碰撞與交流的雜糅狀態為表現內容。面對如此紛繁多元共時呈現的語境,中國當代文論話語體系建構不僅受到不同文化、不同價值觀念的影響,還要面對即使同一文化、同一價值觀念也存在不同階層、不同地域、不同身份、不同趣味的思想性沖突,這決定了其必須是一種多元化的包容性對話范式。但多元中要有主導性聲音和色調,有“中國理論”的主張和價值立場,充分發揮中國美學和文藝批評介入社會現實的能力,有效辨別、辨識和闡釋復雜境遇中當代中國文藝問題、審美經驗及其情感結構的特殊復雜性和主流文化價值訴求,只有這樣,才能提高中國文論的國際話語權。
“不能套用西方理論來剪裁中國人的審美”,就要增強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自信。中國特色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有機融合,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弘揚和對社會主義文化的張揚。建構中國文論和美學話語體系,要把凸顯“面向中國的審美經驗”作為中國文藝發展的特有方式與形態。美學理論建構既要有“審美共通感”的底蘊,又要在審美經驗的藝術表達上,凸顯民族的、地方的色彩。“地方性”“民族性”越來越成為后現代文化空間中藝術表達的底色,只有文藝多樣性才能豐富人類精神家園。在全球文化思潮相互激蕩下,各民族文藝發展愈加斑駁多樣,在相互交流、交融中互鑒,在大眾文化全球互動及文化均質化的當下,凸顯審美的“中國經驗”,意味著在文藝發展多元格局中訴求一種主流文藝形態,以書寫和表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探索的“中國精神、中國力量、中國價值”,弘揚當代中國人的審美理想和藝術價值追求。這種理論著重解決和探討的是中國文藝的發展道路及其主流話語表達形態,是“中國的”審美經驗或中國文化底色,而不是什么別的國家或民族的審美經驗。不同于其他社會科學,文藝理論和美學研究關注的基本問題是人的審美經驗及其藝術表達,其獨特性是價值所在,因此其研究范式和批評話語建構要圍繞獨特性展開,卻不必執著于地方性和民族性,而是在開展文化間、范式間對話和溝通中追求一種形而上的超越。也就是說,中國特色、中國經驗要有世界意義,既要文明互鑒,又要關注文明的異質性和變異性,不能陷入西方中心主義窠臼,也不能落入文化部落主義泥潭。中國的文明型崛起是對人類美好精神家園及其意義秩序探索的貢獻,唯有自覺地、牢牢地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使命、文化權利和文化責任,以文藝或審美的方式展現中國人對美好生活的追求,才能建構基于“中國經驗”和呈現“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中國文論話語體系。
三、“中國理論”建構的方法論創新
就現實文化建構而言,中西文化相互影響。從歷史上來講,東方文化不僅幫助西方人擺脫了中世紀的蒙昧,而且西方文化率先邁上現代化之路也離不開東方文化的助力和滋養,對此一些西方啟蒙學者有著清醒認知。如伏爾泰在《風俗論》中,就把中華文明史納入世界文化史之中,打破了以歐洲史代替世界史的歐洲中心主義史學觀。不唯如此,現實文化同樣傳承和弘揚了優秀中國傳統文化,有著對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中國經驗”置身的現實語境一定有著傳統文化的底色,否則何來“中國特色”?就此而言,“中國經驗”始終浸潤在中華文化之中,它的每一個輝煌高峰都得益于傳統文化的滋養和潤澤。也就是說,“中國經驗”不僅有著現實的語境意識,還有歷史的維度和指向未來的前瞻性,從而構成一個立體的豐富的多維的現實存在,有著不同的視角和路徑的切入及其無窮的闡釋空間。因此,“中國經驗”既有西方的視域,但“不能套用西方理論來剪裁中國人的審美”;又有著歷史的維度,但不能回到歷史循環論中閹割當下的現實。
建構“中國理論”需要打破對西方文化的迷失,只有走出西方文化中心主義的陰影,才能實現理論自覺,而不會脫離文化主體性去任意表征。不僅“中國理論”是地方的,即使披著普遍性外衣的西方理論同樣是地方的,打著文化多元主義的美國理論也有其界域。這樣理解并不妨礙各種理論在全球化舞臺上同臺競技、相互交流和影響,在價值共享和理論競爭中展現超越性。“中國理論”的建構需要在平等、開放和包容中共在共處,中國理論的發展更是離不開文明的互鑒,離不開多種方法的交融使用,以普適性訴求和反思性維度而成為世界主導性理論之一。“面對一個全球化無處不在的當今世界,不同文化因素之間的滲透和影響已成為常態,我們的研究重心不是一定要去提煉一個純之又純的‘中國性’,而是真正直面這個‘混雜’‘多元’的經驗現實本身,并且在這個多元混雜的經驗之中發掘和提煉出中國的特殊性及其普遍性意義來。”[17]說到底,中國理論話語體系要扎根現實文化,而以“過去”和“他者”作為參照。
建構基于“中國經驗”的“中國理論”及其話語體系,不僅要增強反思意識,還要從大歷史觀、中國價值和中國文化主體性等視角追求方法論創新。*本文提出的建構“中國理論”的方法論創新,受惠于馮鵬志:《歷史邏輯、實踐路徑與理論自覺——論習近平總書記的文化強國思想》,載《文化視野》,2015(1),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16;溝口雄三:《中國的思想》,北京,中國財富出版社,2012。
(一)以中國崛起為歷史新紀元——重塑世界歷史邏輯
從當下既有的世界史敘述來看,中國近現代史是伴隨西方現代性擴張,中國不斷融入其中的過程,這是以西方歷史觀來剪裁中國現代史的結果。事實上,伴隨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文化自信,我們既要看到中國人對現代性的矢志追求,更要洞察復數現代性框架下中國道路的獨特性。文明型崛起的中國開啟了世界史的新紀元,世界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中國是一個積極的主導性力量。以中國為動能和發展引擎的新一輪經濟全球化,以及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具有世界性意義。“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18](P8)因此,以中國崛起為世界歷史新紀元其實是建構一種新的人類歷史觀,以此為方法重塑世界歷史邏輯,重新梳理中國史與世界史的關系,為“中國理論”的建構開啟了新的人類歷史視域。中國現代史豐富了世界歷史內涵,中國越來越現代化了,但中國不是復制西方,中國的現代性追求目標是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尤其是中國的文藝和審美經驗不是依存于西方,而是有著獨特性和世界性意義的。以中國革命實踐為觀照對象的紅色文學,作為世界無產階級文學聯合體的一部分,早已進入世界文學的多元化版圖。中國的革命、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實踐,有著“中國經驗”的世界史意義。
以中國崛起為世界歷史新紀元——世界史書寫的新視角,其前提是全面客觀地認識當代中國、看清世界、理解中國特色。闡釋中國特色,要做到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所要求的“四個講清楚”:“講清楚每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傳統、文化積淀、基本國情不同,其發展道路必然有著自己的特色;講清楚中華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講清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于中華文化沃土、反映中國人民意愿、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有著深厚歷史淵源和廣泛現實基礎。”[19]基于此,提出重新理解中國史與世界史的關系,實質上是在全球化時代如何理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如何定位中國現(當)代史、如何塑造世界歷史邏輯。就當前世界主流歷史哲學話語體系而言,中國作為東方或非西方,始終是歐洲民族國家海外擴張的對象,在其表述中始終處于邊緣性、依附者地位,“中國問題”與“中國經驗”始終是另類的“他者”存在。因此,西方歷史哲學基于對基督教文明以及現代西方文明的一種理論自覺,始終強調的是文明的沖突以及潛在的或顯在的對其他文化傳統的排斥或貶低,甚至日裔美國學者福山斷言“歷史的終結”。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新古典自由主義或新保守主義的推進,尤其是90年代蘇聯東歐劇變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低谷,西方歷史哲學呈現全面抬頭之勢。然而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道路的成功探索和文明型崛起,使得“中國經驗”對西方歷史哲學提出了尖銳質疑,特別是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是對“文明沖突論”陷阱的超越,是對人類文明發展方向的矚望。與此同時,歐盟的動蕩特別是中東難民、英國脫歐和美國特朗普上臺等表征了西方世界30多年來推行的新自由主義已陷入巨大危機,這在深層次上表征了西方歷史哲學傳統的當代危機。現實和世界發展態勢召喚“中國理論”出場,以糾偏世界發展的單向道。只有基于中華文化的特點、天下體系的而非單純民族國家的包容性的文化觀、天人合德的思想觀念,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在世界戰略格局重組中重塑一種全新的更具闡釋效力的世界歷史邏輯,發揮中國文化在全球治理中的智慧,弘揚“中國理論”的世界意義,才有可能使世界發展進入新境界。這種方法論的創新,對建構中國文論話語體系有著諸多啟示。
(二)以中國為價值參照系——重塑中國文化主體性
今日的中國是歷史的延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國獨特的優勢。基于“中國經驗”建構“中國理論”及其話語體系,就要重塑中國文化主體性。理論擔當不能缺失中國文化主體性,當代中國文藝的繁榮發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自信的表征。從世界史角度看,中華民族是一個文化內在超越意識很強的民族,一個有著天道信仰與天下情懷的文化民族,而不是一般的世俗性的民族。自堯舜以來,中華民族就有一種“克明俊德,協和萬邦”的天下關懷。獨特的天下觀意識,使中華民族不是一般單純民族主義意義上的民族,而是一個有著擔當和天下文明意識的民族,因此中國通常被某些西方學者視為一個“文明體”。在現代化道路探索中,當代中國成功推動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化,積極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正在實現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融合,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色”愈加色彩鮮明,這必然要在人類文明秩序與重建人類共同價值(人類命運共同體)上形成重要突破和建樹。雖然當前世界格局充滿不確定性,各種不穩定性因素在增多,但隨著許多國家尤其是中國堅定地走上獨立自主的現代化道路,隨著連同西方在內的區域性與民族性開始朝著全球性和人類性開放,不僅中國文化傳統的內在價值及其對于重建人類文明秩序的作用不斷凸顯,而且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中國道路自身就蘊含著一種獨立完整的有普遍意義的世界價值。
中國文化的包容性使其能有效闡釋世界的多樣性,維護世界的多元化發展,這意味著對不同文明均持有一種欣賞與學習的態度(如費孝通所說“各美其美、美美與共”),這種價值觀顯現于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愿景。說到底,“一帶一路”國家的互聯互通是文化的交流和價值共享,是民心的相通,這種價值理念是當今世界發展所需要倡導的,它體現了中華文化的智慧及普適性價值訴求。重塑中國文化主體性要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內在支撐。一方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直接推動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化;另一方面,中華文化傳統煥發的活力與生命力、它的學習性與創造性及其在現代世界歷史中的遭遇,使馬克思主義能夠在中國現實扎根,與中國傳統文化相融合,從而夯實了一個偉大民族現代復興的堅實基礎。
(三)以中國獨特道路為方法——在多重文化視閾中闡釋人類文明進程中的中國發展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曾經為人類文明做出了重要貢獻,也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堅實根基。“傳承中華文化,絕不是簡單復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為今用、洋為中用,辯證取舍、推陳出新,摒棄消極因素,繼承積極思想,‘以古人之規矩,開自己之生面’,實現中華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20](P26)中國發展道路創造的經濟奇跡,表征著中國當代文化要不負這個時代。
當代文化不單純是一個時間的概念,而是一種雜糅了中外古今的現實存在,它本身就內蘊了多重文化語境。在世界文化思潮的相互激蕩中,中國文化的主體性表征著當代中國的現代化是有主體性的現代化,是有著迥異于西方現代性的發展理念的現代化,是中華文化內生力量與包容異質文明成果在雜糅中的升華,是對中華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踐行。這一主體性不僅顯現為每一個有擔當的個體,還體現為國家、民族等多重社會實體及其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領域的發展實踐。中國的文明型崛起,其意義不唯是中國的,更是世界性的,其在當下已成為理解人類歷史發展的一種新方法。改革開放近40年來,既是中國以前所未有的氣魄和力度融入全球化進程,中國與世界同頻共振,也是近年來在中國倡導下不斷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世界歷史新時期,這一世界性意義尚未被學界充分闡釋。當年鄧小平提出的“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題”重大判斷,不僅統一了中國人的思想,也影響著西方人對于中國如何發展的判斷。顯然,這是一個由中國人帶入并深刻影響了世界新格局的重大理念。今天中國所擁有的全球化的現實成就,特別是2016年杭州G20峰會所達成的共識及其中國方案,很大程度上是這一理念的深化,這種人類文明新秩序的開啟是全世界各種機緣及其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合力所為。
中國道路的成功是一種哲學的突破,是理論自信的基石,它具有積極的方法論啟示。當下,我們既處在一個深受新自由主義主宰,而其又不斷受到挑戰和危機的全球化時代;同時,又是一個全球化非單向的西方化或美國化的時代,特別是在新一輪經濟全球化的引擎和動能轉變之際,中國在“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中的主導性作用愈益凸顯。在全球化語境下,一些非西方民族國家依據自身傳統的流變從而形成多樣化民族國家的時代,很多發展中國家現代化了,但并非西方化或者美國化。不同的民族國家既承擔著實現自身國家現代化的使命,又分擔著實現整個人類永續發展的責任。顯然,以中國道路的成功為創新方法,以中華文化智慧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在大歷史觀和方法論創新的引領下,可以洞悉中國這個古老文明及其大國的復興,不僅從客觀上不可能走依附于西方新自由主義的道路,而且中國的發展必然要形成一條有效地遏制新自由主義矛盾、有著示范效應的新型發展道路,還啟示了人類歷史將進入“和而不同”的新境界,這種方法論創新對建構中國理論話語體系有著根本性啟示意義。
[1][7][8][9][10][13][16][18] 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2] 喬納森·卡勒:《文學理論》,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
[3] 南帆:《審美的重啟》,載《中國文學批評》,2016(1)。
[4][5][6] 沃爾特·亞當森:《藝術、文學與政治理論中的現代主義》,載特倫斯·鮑爾 、理查德·貝拉米主編:《劍橋二十世紀政治思想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
[11][17] 曾軍:《西方文論對中國經驗的闡釋及其相關問題》,載《中國文學批評》,2016(3)。
[12][20] 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14] 《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 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15] 習近平:《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19] 習近平:《胸懷大局把握大勢著眼大事 努力把宣傳思想工作做得更好》,載《人民日報》,2013-08-21。
Abstract: Any theory concerns re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enerative nature of theory, each kind of theory has its boundaries generated by the context and works. The validity of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theoretical bias in reality as the axis in the open, thus revealing the context awareness and reflection dimension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We can not tailor Chinese aesthetics to Western theories, instead, we should enhance the cultural confiden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construct China’s theoretical discourse system, we need to base on the multi-perspective “Chinese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its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
Keywords: discourse system; context awareness; Chinese aesthetic experience; the China path; methodology innovation
(責任編輯林間)
ConstructtheTheoryofDiscourseContextAwarenessandInnovationofMethodology——BasedontheTheoryofChineseAestheticExperience
FAN Yu-gang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Beijing 100091)
范玉剛:文學博士,中共中央黨校文史教研部教授(北京 100091)
中共中央黨校2017年創新工程項目“文化思潮與國家文化戰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