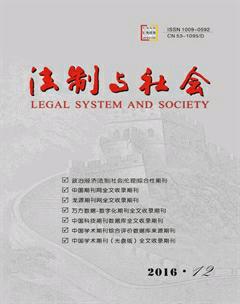抗戰時期邊區人民調解制度的評價
摘 要 本文基于歷史考察,指出人民調解制度是由于抗戰時期的政策需要以及司法調解功能的缺位而產生的,通過對抗戰時期邊區的人民調解制度的產生背景、類型、原則的梳理,從而評價抗戰時期邊區人民調解制度。
關鍵詞 抗戰時期 人民調解制度 現代啟示
作者簡介:劉芮杉,西安石油大學思政部。
中圖分類號:D929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12.011
一、抗戰時期邊區人民調解制度的產生背景
在1930年代末,由于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中國進入全面抗日的戰斗之中。正所謂矛盾無處不在無時不有,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也同樣存在矛盾,主要分為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由于人民內部矛盾具有非敵對性,不適宜通過強制性手段來解決,比較適合運用說服、教育的人民調解制度來化解,因此,各邊區政府大力提倡和積極推行人民調解制度。
西方文化的滲透,使中國的法律制度化幾乎完全所用。但是完善了中國傳統的民間調解制度的“息事寧人”、“以和為貴”的傳統糾紛解決方式,構建了人民調解制度,特別是在抗日戰爭時期,人民調解工作受到中國共產黨的廣泛推行, 并且通過人民民主政權頒布的一系列調解制度的法規、條例等都使人民調解制度得到了充實和完善,為人民調解制度在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創造了條件。1938年1月,在河北阜平成立了晉察冀邊區政府,開始的人民調解制度的發展,在邊區政府的支持下,相繼頒布了適應本地區的邊區根據地人民調解的條例、辦法,指示等。
二、抗戰時期邊區人民調解制度的基本類型
抗戰時期邊區的人民調解制度主要分為以下三種形式,即民間自行調解、群眾團體調解以及政府調解。
(一)民間自行調解
民間自行調解是指,沒有經過專門機構調解,人民群眾的直接解決爭端,是中國傳統民間調解的基本形式。也是推行新型民間調解的條件和群眾基礎。由于受我國傳統思想的影響,“告人一狀,十年不忘”的厭訟思想尤為嚴重。就如1946年馬錫五在《答考察邊區司法者問》中指出:“在社會習慣上,千百年來早己存在著張三失手打壞李四,王大出來和解的習慣,這是良好的習慣,叫做息事寧人,排難解紛。”幾乎每個村、每個鄉都有“和事佬”,民間自行調解也因此具備一定的群眾基礎。但是在抗戰時期人民民主專政的新形式下,民間調解制度的推進受到了一些阻礙:端正思想認識也是亟待解決的難題之一。也就是說,除了人民群眾,調解員、區鄉干部的思想也需要改進存在一些必須克服的思想。
(二)群眾團體調解
群眾團體調解是指,爭端各方邀請現場調解質量組織,其中,社團有自己的組織,代表和保護群眾的利益團體和爭議調解作為他們的日常業務。各種社團,是通過選舉,在群眾中有一定的威望,之間的糾紛屬于大眾,能夠得到公平合理的。如1943年6月,陜甘寧邊區人民調解在第四條規定:“由各自方邀請利林,親戚和朋友,或者人們集團審查,從田間小區問題上的重量調解建議說服雙方利益”。
(三)政府調解
政府調解是指,由基層人民政府主持的調解。政府調整在各抗日根據地的運行分為兩種,一種形式是典型的由區長、鄉長等政府負責人參加,必要時邀請勞動英雄、公正者等的形式和群眾在場協助。如1943年6月,《陜甘寧邊區民刑事件調解條例》第5條規定:“前條所列調解不成立時,得由當事人雙方或一方申請鄉(市)政府,區公署,或縣(市)政府,依法調解之。前項鄉、區縣(市)各級政府接受調解事件,必要時的邀請當地各級機關人員及民眾團體公正士紳,現場協助調解 ”。另一種方法是各邊區廣泛采用的形式,即建立各級人民政府專門機構負責調解工作——調解委員會。如陜甘寧邊區政府特在民政廳內設第三科,縣政府內設第一科,區鄉成立調解委員會,具體的負責調解工作。政府調解雖然在性質上具有行政調解的特征,但實際上與群眾團體組成的專門性的調解組織并無明顯的不同,因此仍屬于人民調解的性質 。
三、抗戰時期邊區人民調解制度的原則
(一)自愿原則
所謂自愿原則,是指在調解解紛當事人雙方的矛盾時,務必取得雙方當事人的同意,不得強迫。自愿原則包括兩方面的含義:第一,在調解矛盾糾紛時,不得有任何違反自愿意愿的情況發生,不論是調解內容、調解程序還是調解的最終執行,都必須以雙方當事人的意愿為第一要義,不得強迫或干涉;第二,在人民調解過程中,除了雙方互相尊重彼此的意見外, 達成的調解協議也應該是符合當事人的意愿,不能出現任何逼迫等行為。例如1943年6月11日頒布的《陜甘寧邊區民刑事件調解條例》第七條明確規定:調解須得雙方當事人之同意,調解人無論是政府人員、民眾團體或地鄰親友,均不得強迫壓抑 。對于調解過程中貫穿的合法原則,它既是在調解過程中最大限度地實現當事人“真實合意”的需要,也是法治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 。
(二)合法原則
所謂合法原則,指的是抗戰時期邊區的人民調解制度既要遵守政策、法令,同時還要照顧民間善良風俗習慣。邊區的人民調解絕不是簡單的“了事主義”,而是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且符合各抗日民主政權法律和政策的貫徹落實。在調解中運用政策法令,不僅能夠起到宣傳貫徹的作用,更主要的是能夠分清是非曲直,是確保協議執行的保障;而調解中運用的善良風俗習慣,一定是能夠積極向上的,且對社會起到良好推進作用的思想習慣,決不是落后的封建思想習慣。對于各邊區人民調解制度的合法原則也有明確的規定,例如1941年4月18日頒布的《山東省調解委員會暫行組織條例》第十四條規定:調查應盡量采用習慣與法理,但庸俗的道德觀念及有害抗戰與僅有利少數人之習慣,不得采用 。
(三)調解不是訴訟的必經程序原則
所謂調解不是訴訟必經程序原則有三個含義:第一,糾紛當事人可以不經任何調解,直接上訴于人民法院,任何人不得加以干涉;第二,除特定情形外,當事人在非法院調解過程中不愿接受調解,或者經調解達成協議后由于某種原因不愿執行調解協議的,不影響當事人繼續向法院提出訴訟;第三,除特殊情況外,當事人對訴至法院的糾紛,可以不經法院調解而要求法院進行判決 。
四、抗戰時期邊區人民調解制度的評價
(一)深入群眾路線,獲得群眾擁護
正如毛澤東同志在抗戰時期發表的《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和《論聯合政府》,都是對群眾路線和群眾路線方案主要內容總結,指出中國共產黨運用黨的群眾觀點之所以如此成熟,是因為中國共產黨都與人們的切身利益為基本出發點,與人民群眾的利益相聯結。再次把人民群眾聚集的想法反饋成為真正的人民的觀點,并以此作為指導實踐活動的開展,并這樣逐漸的循環往復、實踐、運動,使群眾的觀念更加明確,變得更加豐富 。抗戰時期的人民調解工作首先要做的,就是與大眾密切聯系從而開展內部調查工作。關于這一點決定性的路線,是人民調解制度的關鍵所在。“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人民調解工作亦是如此。
(二)加強人民團結,維護社會穩定
由于毛澤東同志意識到維護人民群眾的利益對穩定社會秩序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真正維護好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才能得到人民群眾對于中國共產黨的擁護,才能使人民群眾積極的投身于革命事業,從而凝聚力量、團結起來同仇敵愾。因此,抗戰時期的人民調解制度就是本著維護人民群眾的利益、增強人民群眾的團結這一特點而展開的。
在抗日戰爭這一特殊時期,人民調解制度除了維護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增強人民群眾團結的特點外,還有一個突出特點就是要服務于抗戰大局。由于日本殘暴的燒殺掠奪,中國共產黨于1935年瓦窯堡會議上便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積極尋求社會各個階層階級的合作,以穩定社會秩序。正是因為抗戰時期的人民調解制度的出現,才使得這些復雜的多元化矛盾糾紛得以妥善解決,及時避免了許多社會糾紛所導致的不良后果和影響。
(三)促進精神文明建設,普及法制觀念
首先,堅持抗日政策,號召愛國主義思想。把法律和制度相結合進行糾紛調解,通過這種調解方式的指引,能夠使人民調解員將愛國主義為主導的思想嵌入到調解中去,在調解過程中使糾紛當事人能夠馬上放下內部矛盾,積極投身于對敵抗日的外部矛盾當中去。
其次,主張善良道德觀念,抵制封建庸俗的倫理道德。抗戰時期的人民調解制度通過解決矛盾糾紛的機會,借此教育邊區人民抵制如男尊女卑、干涉子女婚姻的封建陋俗,宣傳如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善良道德觀念。
再次,提倡說服教育,拒絕徇私枉法。各抗日根據地明確規定,人民調解人員要在充分尊重當事人的民主與人權基礎之上,進行調解,以理服人,耐心細致的幫助糾紛當事人化解糾紛,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的給糾紛當事人做清思想工作;不能有任何主觀臆斷或恃勢凌人的耍“官威”,蠻橫無理的對待糾紛當事人,或是以尋求私利為目的的進行調解,甚至當事人違反人權、侮辱等各方可能的侵犯。
(四)節約訴訟成本,減輕司法壓力
由于抗日戰爭時期,所有力量都要集中起來對敵抗日,因此,解決糾紛的機制就應該具備程序快捷、成本低廉等特點,抗戰時期的人民調解制度便孕育而生。首先,抗戰時期的人民調解制度具有程序快捷的特點。人民調解制度與訴訟不同,人民調解制度沒有過多繁瑣程序的約束,一旦爭端達成協議,爭議就會解決。即使調解不成時,對當事人的損失也不大,不會像訴訟一樣出現纏訟等耗時費財的弊端;其次,抗戰時期的人民調解制度還具有成本低廉的特點。人民調解制度既不用繳納訴訟費,也不用繳納任何調解費用,即使沒有成功調解,當事人也不必產生太多費用。例如1942年4月1日《晉察冀邊區行政村調解工作條例》第十七條規定:“進行調解時,不準索取收受物品上的報酬 ”。
總而言之,抗戰時期的人民調解制度是在響應對敵抗日政策的號召下,以維護人民群眾的利益為原則;以節約司法資源,提高司法效率,從而使人民群眾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抗日戰爭為目的;以人民群眾團結一致的同仇敵愾為目標的一種糾紛解決機制。它的產生對廢除一切封建陋習,構建科學發展的道德觀念具有不可磨滅的推動作用。
注釋:
韓延龍、常兆儒.革命根據地法制文獻選編(中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1002,1003,1018,1007.
洪冬英.當代中國調解制度變遷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56.
常怡.中國調解制度.法制出版社.2013.57,59.
單靜.抗戰時期人民調解制度研究.河南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15年5月8日.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