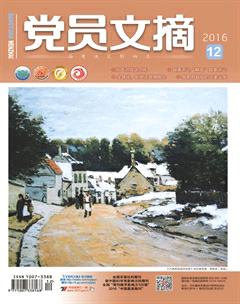閻肅受歡迎的三大原因
余秋雨
討論閻肅先生,我要提醒大家注意一個驚人的奇跡。
什么奇跡呢?那就是按照他的高邁年齡,他早已不應該是各個電視臺的邀請對象。事實上,與他年齡相仿的老人,不管是藝術家、學者,也都不會顫顫巍巍地在鏡頭中擔任評委、導師了。但是,令人驚訝的是,他卻頻頻出鏡,十分活躍。而且,據我所知,各個電視臺也總是把他列為熱門的一線邀請對象。
現在的電視臺非常重視收視率。因此,電視臺邀請的人,也可以看作是受廣大觀眾喜愛的對象。
為什么各個電視臺和廣大觀眾都會超越年齡的障礙一直喜愛閻肅先生?可能有人會誤解,以為與他的地位有關,與關系有關。其實,只要了解當代社會審美趨勢的人都知道,電視鏡頭前的緣分,與這一些都沒有關系。正因為與這一切都沒有關系,因此他確實創造了一種奇跡。
我在中央電視臺的全國青年歌手大獎賽中,曾與閻肅先生一起擔任評委很多屆,從旁觀察,反復思考,發現他被當代電視觀眾喜愛是有原因的。
第一個原因,是他身上完全沒有讓人厭煩的架子
閻肅從來不曾在公開講評和私下聊天中,夾帶一絲一毫有關自己的職位以及以前作品的信息,哪怕是暗示也沒有。于是,他在觀眾和朋友面前,不再是官員,不再是老藝術家,不再是學者,而只是一個單純、輕松的普通人。要做到這樣是不容易的。請看周圍其他年長的藝術家和學者,人也很好,但生怕被別人看輕,老是要不經意地抖摟一點“身份”出來,例如,開口閉口就是“50年前我剛剛獲得大獎的時候郭沫若先生握著我的手說”,“在那場戰爭中我率領一個采訪團到了前線”,等等。閻肅先生完全有資格說這些話,但他絕對不會說。
于是,閻肅成了一個似乎沒有顯赫履歷、官位、成就的和藹老人,這等于拆除了他與廣大觀眾之間的層層圍墻、道道阻隔。觀眾面對他,并不需要穿越什么障礙,直接碰撞他誠懇的言詞和話語,傾聽他毫無矜持的暢懷大笑。相比之下,那些喜歡抖摟“身份”的人可能一時讓觀眾敬畏,卻很難讓觀眾融入,觀眾也就很快把他們冷落了。
閻肅先生對“身份”的自我卸除,不是出于一種謀略,而是出于本心。我了解他,他在內心也對種種外在的地位毫不在乎,別人問起來,他只是輕描淡寫地匆忙繞過,絕不留連。對于那些生怕觀眾看不起而不斷暗示自己了不起的鏡頭人物而言,閻肅先生實在是為他們提供了一個相反的例證。有一次,閻肅先生聽到一位在文化領域偶得高位的官員頤指氣使地講話,悄悄捅我一下,然后輕聲在我耳邊說:“滿口假大空。”其實仔細一想,閻肅先生的資歷遠遠超過眼前這位官員,但他對這位官員的批評,好像不是出于前輩長者對于晚輩后生的不滿,而是出于平民思維對于官僚話語的抱怨。
第二個原因,是他真懂藝術
真懂藝術,首先不是指理論、概念、學說,而是指感覺。感覺,在思維過程中是起點,在藝術過程中卻是終點。閻肅先生擁有的藝術感覺,深刻而廣泛,快速而靈敏。在我看來,在文藝工作者隊伍中,他的藝術感覺能夠與之比肩的人屈指可數。他的強項,是編劇、作詞和音樂。他對劇本的要求,是干凈而有力;他對唱詞的要求,是流暢而典雅;他對音樂的要求,是濃烈而悠揚。正是出于這種感覺,他即使應邀創作一首配合“打假行動”的歌曲,也能寫成“借我一雙慧眼吧”這樣高品位的歌詞而廣泛流傳。
在我的觀察中,閻肅先生對于一段音樂的點頭、搖頭、沉默,總是基本符合普遍而公平的藝術標尺。他可能說得比較客氣、簡單,但他對藝術的取舍、揚抑一清二楚。因此,請他來評審各種作品,就會顯得很“內行”,社會各界都服氣。我有時看著剛剛發完言的閻肅先生就想:我們文化界如果多幾位他這樣的內行老人,情況就會好得多。現在,不少文化引領者有學歷、有理論,卻缺少這種藝術感覺。
藝術良知使閻肅先生堅守住了審美本位。所以,廣大觀眾都看到,不管他出現在什么電視節目中,總是溫和如春,毫無作秀嫌疑。邀請他,不會有什么讓人尷尬的風險。
第三個原因,是他天真爛漫、好學不倦
閻肅永遠處于一種李白抬頭看瀑布的驚喜狀態。他不局限于專業門戶,不擺弄專家派頭。他有很好的傳統文化根基,但他從來沒有在鏡頭前背誦名篇、甩弄典故,每次出來都是一副興致勃勃、其樂融融的學習勁頭。他像一個忘了年齡的“粉絲”,面對著各種新出現的藝術現象,天真而欣喜的表情是那么真誠。在講評時,他沒有教訓口吻,更沒有訓斥語氣,即使批評,也善良溫和,讓年輕的藝術愛好者們樂于接受。這種鏡頭態度,與他在生活中充滿好奇的學習精神有關。在中央電視臺的多次合作中,他非常注意我的講述,只要我提到一個他所不清楚的歷史細節,或者他不明白的國外文化生態,等到休息時他總會不斷詢問,認真的態度就像一個學生。但從他的問題就知道,他其實對那些課題的背景并不陌生。我們每次見面,我都叫他“老閻”,他都叫我“教授”,在整體態勢上,他似乎一直保持著一個“請教者”的謙虛地位。說實話,我從來沒有遇到過像他這樣年齡而又德高望重的“請教者”。我有時也會突然一愣,心想自己年輕時,他不曾經是我的崇拜偶像么!偶像為什么永遠高大?因為他心胸開闊。
閻肅先生的謙虛好學,使他每時每刻都對世界、對他人保持著一種新奇感。他幾乎喜歡一切給他帶來任何審美愉悅和思維愉悅的人,因此他自己也讓人喜歡了。
(劉誼人薦自《啟迪與智慧》201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