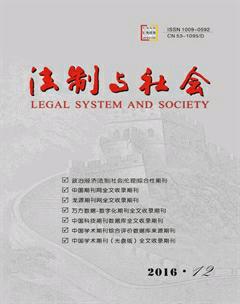網絡借貸中非法集資類犯罪的司法認定
王海雄+裘辰駒+錢雨夢
摘 要 網絡借貸是互聯網金融的典型模式之一,可以吸收民間個體閑散資金,解決中小企業資金短缺的問題,其對于傳統的銀行借貸模式具有補充作用。但現實中的網絡借貸平臺往往突破中介的性質,設立資金池,或者提供擔保業務,甚至很多觸碰到了非法集資類犯罪的紅線。由于網絡借貸形式多樣,對其非法集資類犯罪的司法認定難點較多,需要對其司法認定進行討論與分析。
關鍵詞 P2P網貸 非法集資 司法認定
作者簡介:王海雄,中國礦業大學(北京)文法學院本科生,研究方向:法學;裘辰駒、錢雨夢,中國礦業大學(北京)文法學院本科生。
中圖分類號:D924.3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12.027
一、引言
近年來,非法集資類犯罪案件在網絡借貸領域頻發。P2P網絡借貸一方面受到以e租寶為代表的線下理財和龐氏騙局的拖累,另一方面,網絡借貸的發展也的確伴隨著許許多多的問題和慘劇。截止2016年9月27日,已經有2496家平臺出事,而出事的平臺往往都涉及非法集資類犯罪。而且,史上最嚴網絡借貸監管政策在2016年8月24日到來。這將對于規范P2P網絡借貸平臺,預防非法集資類犯罪起到很大的作用。
二、網絡借貸與非法集資類犯罪
“網絡借貸是指個體和個體之間通過互聯網平臺實現的直接借貸。個體包括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組織。①”非法集資類犯罪的罪名體系包括擅自設立金融機構罪,欺詐發行股票、債券罪,擅自發行股票、公司、企業債券罪,非法經營罪,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和集資詐騙罪。其中,最基本的兩個罪名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和集資詐騙罪。
網絡借貸平臺涉嫌非法集資類犯罪的類型可以分為以下三類:自融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型,相關平臺如東方創投、財富基石,這些平臺的相同點都是自己使用資金,自己提供擔保;集資詐騙型,典型的如e租寶;涉眾傳銷型,典型的如大大寶。
三、非法集資類犯罪的四要件
(一) 非法性
非法性指網絡借貸平臺未經有關部門批準或者借用合法經營的形式吸收資金。網絡借貸是一種創新金融產品,但創新應當遵循規范,不應違反行政和刑事法律法規,網絡借貸的創新要做到規范地創新,健康地創新,達到創新與監管之間的平衡,以此實現網絡借貸乃至互聯網金融所要實現的安全性、流動性和收益性的目標。
非法性涉及到違法標準與批準標準的關系。一言以蔽之,違法性包括未經批準,但不限于未經批準。第一,從民商事活動的自由自主性而言,要求批準的活動僅指法律明文規定要求批準的活動,像日常的合法借貸并不需要批準。第二,要考慮獲得批準方式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如果以欺騙、脅迫、賄賂獲得的批準同樣是違法的。第三,如果法律直接規定為違法的行為,即可直接認定為非法性,無需再考慮批準的合法性問題。另外,行政部門對網絡借貸平臺集資性質的界定并不影響刑事性質的界定。
(二) 公開性
公開性指通過媒體、推介會、傳單、手機、短信等途徑向社會公開宣傳,其與社會性往往相關聯。 “向社會公開宣傳”,包括以各種途徑向社會公眾傳播吸收資金的信息,以及明知吸收資金的信息向社會公眾擴散而予以放任等情形。
對于公開的形式現實生活有很多,舉兩個例子。一是對于口口相傳進行宣傳的行為,二是現實生活中存在的微信朋友圈的宣傳行為,這兩者都有可能符合公開性要件的條件。實踐中可以結合集資人對此是否知情、態度如何、有無具體參與、是否設法加以阻止等主客觀因素,認定是否符合公開性的特征要件。
(三) 利誘性
利誘性是指承諾在一定期限內以貨幣、實物、股權等方式還本付息或者給付回報。利誘性主要是指有償性和承諾性,即實踐和承諾還本付息、給付回報。除給付貨幣之外,還有實物、消費、股權等形式。具體給付回報名義,除了常見的利息、分紅之外,還有所謂的工資、獎金、銷售提成等。因為非法集資行為具有利誘性,到期后重復投資常常發生。對于到期后重復投資的行為是以一次投資計算犯罪數額,還是以每次投資數額的總和加上利息計算犯罪數額,這是一個缺乏法律明確規定的問題。司法中,對于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一般以每次投資數額的總和加上利息計算犯罪數額,對于集資詐騙罪,一般以一次投資加上利息計算犯罪數額。其原因是集資詐騙罪刑罰較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重,故認定犯罪數額時需要從嚴認定,以此做到刑事政策的寬嚴有度。
(四) 社會性
社會性是指向社會公眾即社會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其集中表現為集資參與人的廣泛性和不特定性。
關于“社會公眾的”認定問題,下列情形不屬于 “針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的行為,應當認定為向社會公眾吸收資金:(1)在向親友或者單位內部人員吸收資金的過程中,明知親友或者單位內部人員向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而予以放任的;(2)以吸收資金為目的,將社會人員吸收為單位內部人員,并向其吸收資金的。
四、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
非法占有的目的是集資詐騙罪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欺詐發行股票、債券罪,擅自發行股票、公司、企業債券罪的主要區別。集資詐騙罪,由兩個條件構成,一是使用了詐騙方法,二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
具體而言,認定非法占有目的有以下兩個標準。
(一)標準一:客觀上是否返還了集資款
對于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應當堅持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不能僅以使用詐騙方法就直接推定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也不能犯客觀歸罪的錯誤,僅以造成損害結果就認定非法占有的目的。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能夠及時清退所吸收資金,可以免予刑事處罰;情節顯著輕微的,不作為犯罪處理。這符合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的情形。非法占有目的的確定并不受數額的限制。如果說集資后返還了集資款,則構成出罪條件,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這也涉及到刑事政策的問題,如果犯罪行為人已經具備了非法占有的目的,構成了集資詐騙罪后,返還了集資款,這種返還集資款的行為是不能構成出罪條件的,因為犯罪已經既遂。在計算集資款人實際詐騙的數額時,應當把案前歸還的數額扣除。這樣做可以鼓勵犯罪人犯罪既遂后積極返還集資款,減少社會公眾的損失。
(二)標準二:判定集資款的用途
對集資款用途的判定來確定非法占有的目的,司法認定中的情形如下:
1 對于現實生活中存在的“以新還舊”、“以后還前”,將后期所集資金主要用于支付前期本金和高額回報的情形,可以直接推定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這種行為屬于典型的龐氏騙局,即平常生活中所說的拆東墻補西墻,不具有可持續性。
2 現實生活中常常存在將少量資金用于生產經營活動,將投資行為作為對外宣傳的行騙手段,而大部分資金用于揮霍。對于不用于生產經營的資金認定為非法占有目的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對于用于做誘餌的少量投資資金能否認定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呢?集資詐騙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應當區分情形進行具體認定。行為人部分非法集資行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對該部分非法集資行為所涉集資款以集資詐騙罪定罪處罰。筆者認為,用于生產經營的資金雖用做誘餌,但是確實是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是可以和用于揮霍或者抽逃轉移的資金區分開來認定的。
3判定集資款用途的時候還涉及對肆意揮霍的理解。這里有一個度的把握問題,揮霍通常指的是消費性支出。對于肆意揮霍的理解是一個因人而異、主觀色彩較強的事情,需要考慮行為人的收入數額、收入來源、消費習慣等因素。
五、網絡借貸中非法集資類犯罪的司法認定的完善建議
(一)刑事政策的寬嚴有度
“刑法介入社會生活的適度性根源于法的目的,法的目的在人類的共同福利。②”面對亂象頻發的P2P 網絡借貸領域,刑法的介入具有必要性,符合法的社會福利目的。但P2P網絡借貸作為一種新出現的創新產品,應當給它一定的生存土壤。刑事政策保持寬嚴有度,使網絡借貸將其正面的融資能力發揮出來。這也符合刑法的謙抑性。
(二)刑事立法的創新與刑事解釋的合理
面對日益創新的網絡借貸形式與金融產品,刑事立法也應做到與時俱進,適應不斷發展變化的社會現實。比如,可以提高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入罪門檻。就我國現在網絡借貸平臺集資款的一般規模而言,其入罪的集資金額和集資對象門檻較低。而當前,大多數 P2P 平臺都或多或少的設立資金池,賺取利潤,一般都具有非法性。加之網貸平臺面向社會公眾,集資款數額和集資人數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超過了入罪門檻。如果提高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入罪門檻的金額或者人數,首先,給了網絡借貸平臺生存與創新的空間,可以讓網絡借貸平臺自我調整,其次,縮小了刑法的打擊范圍,把精力集中到集資數額巨大、社會影響惡劣的案件中來,解決目前司法精力有限的問題。
(三)完善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無縫銜接
根據新出臺的《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業務活動管理暫行辦法》,國務院銀監會、各省級人民政府、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以及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分工負責對網絡借貸的監管。“從行政監管的角度來看,界定非法集資活動時的核心要素只有兩個:集資性質、面向社會公眾。③”
行政監管模式具有專業化強,高效便捷的優點,與刑法規制結合起來,將共同推動網絡借貸健康、持續地發展,共同為互聯網金融創新產品保駕護航。
(四)提升公民防范互聯網金融風險的意識與知識
公民作為網絡借貸的出借方,在網絡借貸的平臺涉嫌非法集資類犯罪倒閉后,財產真正受損失的是普通公民。對于一些大型的出事平臺,受害群眾廣,損失金額巨大,即便對犯罪人處以多么嚴重的刑罰,也不會讓公眾損失的財產絲毫不差的回來。因此,要通過提升公民防范互諒網金融風險的意識與知識這一方式來避免公眾遭受財產損失。這也可以從源頭上起到預防犯罪的作用。
注釋:
①《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業務活動管理暫行辦法》第二條.2016年8月27日.
②[美]E·博登海默著.鄧正來譯.法理學 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0.324.
③彭冰.非法集資行為的界定——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非法集資的司法解釋.法學家.2011(6).38-53.
參考文獻:
[1]彭冰.P2P網貸與非法集資.金融監管研究.2014(6).
[2]鄭孟望.關于偷拍偷錄行為的法律思考.湖南社會科學.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