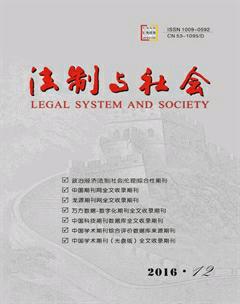關(guān)于妨害公務(wù)罪中“暴力”的幾點認識
摘 要 妨害公務(wù)罪是司法實踐中常見的犯罪類型,而且犯罪手段多樣化,嚴重影響社會管理秩序。但對于妨害公務(wù)罪的認定,理論和實踐中均存在一些爭議問題,尤其對于“暴力”的認識,存在很多種理解。為進一步加強對妨害公務(wù)罪中“暴力”的理解,準確明晰妨害公務(wù)罪的入罪標準,筆者結(jié)合自身辦案經(jīng)驗,查找相關(guān)資料,提出有關(guān)妨害公務(wù)罪“暴力”的疑難問題,并提出觀點,促進達成共識、正確適用刑法。本文分為兩個部分,從暴力的內(nèi)容、暴力的程度兩方面進行分析,結(jié)合真實案例,具體闡述妨害公務(wù)罪中的“暴力”,并總結(jié)提出筆者觀點。
關(guān)鍵詞 妨害公務(wù)罪 暴力 行為方式
作者簡介:田媛,北京市密云區(qū)人民檢察院。
中圖分類號:D924.3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12.029
我國刑法分則關(guān)于妨害公務(wù)罪的表述比較簡單,雖然司法解釋相繼出臺,但是仍不能給妨害公務(wù)罪一個具體的、明確的入罪標準,因此理論界和實務(wù)界對妨害公務(wù)罪的理解不盡相同。甚至在司法工作人員內(nèi)部,對妨害公務(wù)罪的入罪標準也會存在差異,不同司法人員對于同一案件的處理出現(xiàn)截然不同的處理結(jié)果的情況也是存在的。妨害公務(wù)罪的行為方式是該罪的一大值得探討問題,尤其對于妨害公務(wù)罪中的“暴力”的理解和認識,理論和實踐中存在很多不同的觀點,筆者結(jié)合辦案經(jīng)歷對妨害公務(wù)罪中的“暴力”進行探討,以期在司法實踐中更好地適用法律。
一、妨害公務(wù)罪“暴力”的內(nèi)容分析
什么是暴力?《辭海》中對“暴力”的解釋為“強暴并侵犯他人人身、財產(chǎn)等權(quán)利的行為是暴力”。用互聯(lián)網(wǎng)百度搜索“暴力”一詞,通過百度百科得到的結(jié)果是“暴力,暴露出來的力量”、“泛指通過武力侵害他人人身、財產(chǎn)、精神的行為”、“泛指侵害他人人身、財產(chǎn)的強暴行為”。具體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條文中的“暴力”是什么?妨害公務(wù)罪中的“暴力”又是什么?
關(guān)于妨害公務(wù)罪中的“暴力”,理論界主要存在以下幾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妨害公務(wù)罪中的暴力,應(yīng)該是僅僅針對國家機關(guān)工作人員、人大代表或者紅十字會工作人員的人身的有形、直接的強制或者打擊,并且這種強制、打擊已經(jīng)達到了足以使公務(wù)人員無法繼續(xù)履行公務(wù)行為的程度。第二種觀點認為,妨害公務(wù)罪中的暴力不僅可以是直接針對公務(wù)人員人身的強制或者打擊,也可以是針對公務(wù)人員在執(zhí)行公務(wù)過程中正在使用的諸如警用車輛之類的公務(wù)用品、辦公用品的損毀,因為這種損毀行為也將直接造成公務(wù)行為的執(zhí)行受阻。第三種觀點認為,對于妨害公務(wù)罪中的暴力應(yīng)當(dāng)作擴大的解釋,其暴力的內(nèi)涵也應(yīng)當(dāng)是所有暴力犯罪中最廣泛的一種,只要能造成對執(zhí)行公務(wù)的人員的健康權(quán)、生命權(quán)、自由權(quán)損害、侵害結(jié)果的,或者能夠造成對執(zhí)行公務(wù)所適用的物品的損害的結(jié)果的,都構(gòu)成妨害公務(wù)罪中的暴力行為,由此,無論是有形的傷害行為還是無形的行為,諸如麻醉、灌醉等都能夠構(gòu)成妨害公務(wù)罪中的暴力。
關(guān)于妨害公務(wù)罪中的“暴力”,筆者主張:
第一,以妨害公務(wù)執(zhí)行為目的,針對執(zhí)行職務(wù)人員人身而使用的有形的、直接的強制或者打擊,當(dāng)屬妨害公務(wù)罪中的“暴力”應(yīng)有之義。
第二,針對物的攻擊,是否也屬于妨害公務(wù)罪中的“暴力”,應(yīng)具體分析。具體說來存在兩種情況:一是攻擊履職必需之物;二是攻擊其他物。之所以將妨害公務(wù)罪列入刑事犯罪的范疇,主要保護對象是正常的社會管理秩序,確保公務(wù)活動的正常運轉(zhuǎn)和有效執(zhí)行,如果行為人以攻擊、毀壞警車、毀壞執(zhí)法儀器等公務(wù)用品的方式,對公務(wù)活動進行妨害,因車輛、儀器等,都是履職必需之物品,對此類物品的損毀,直接影響了正常的公務(wù)活動的進行。因此我們說,對于履職必需之物所實施的這種“間接暴力”,雖然并非針對執(zhí)法者人身實施的直接暴力,但是在客觀上也確達到了阻礙公務(wù)執(zhí)行的效果,也應(yīng)當(dāng)列入妨害公務(wù)罪中的“暴力”范疇。如果行為人所攻擊之物并非履職必需之物,如為發(fā)泄對執(zhí)法行為的不滿而故意損毀自己的物品、用拳頭擊打地面墻面以示憤怒、亦或是將執(zhí)行職務(wù)人員偶然落地的其他物品如鑰匙鏈等損毀,等等,以上行為雖然反映出行為人對公權(quán)力的挑釁和輕蔑,但客觀上并沒有起到妨害公務(wù)執(zhí)行的作用,因此不宜認定為妨害公務(wù)罪中的“暴力”。
第三,關(guān)于無形行為是否屬于妨害公務(wù)罪中的“暴力”,筆者的觀點是否定的。無形行為是相對于有形行為而言的,所謂有形行為,就是看得見、摸得著的一種直接的、公然的攻擊行為,如撞擊、毆打、撕扯、拉拽等,關(guān)于無形行為,學(xué)界還沒有確切的定義,通常會以“灌醉、麻醉”等為典型列舉。上述第三種觀點中,學(xué)者認為妨害公務(wù)罪中的“暴力”應(yīng)當(dāng)做擴大解釋,涵蓋一切有形、無形行為,但筆者不贊同這種觀點,原因在于:一是無形行為屬于暴力不符合一般人的常識判斷。筆者以“什么是暴力”為題詢問身邊非法律專業(yè)人士,給出的答案基本都是血腥的、殘忍的、強制的手段和行為,幾乎沒有人主動將暴力與灌醉、麻醉等直接聯(lián)系起來,除非是用暴力手段將人灌醉。因此,將灌醉、麻醉等無形行為歸為暴力,超出了一般人的常識判斷。二是在我國刑法條文中,除了妨害公務(wù)罪,還有其他罪名中也使用了“暴力”一詞,如搶劫罪、強奸罪的刑法規(guī)定中,關(guān)于行為人的犯罪手段,除了規(guī)定“暴力、脅迫”之外,還有“其他手段”和“其他方法”的表述,即采用暴力、脅迫之外的與暴力、脅迫效果相當(dāng)?shù)姆椒ǎ缬镁乒嘧怼⒂盟幬锫樽怼⑹褂么呙咝g(shù)等。按照刑法規(guī)定,“暴力”并不包含灌醉、麻醉等無形的手段,而應(yīng)當(dāng)歸類為“其他方法”中。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將無形行為納入到妨害公務(wù)罪的“暴力”解釋中,就會出現(xiàn)同一部法律中同一個詞語解釋不一致的情形,有違法律的整體性精神,有損法律嚴謹性。
二、妨害公務(wù)罪“暴力”的程度分析
我國刑法條文對于暴力須達到何種程度才能入罪并沒有明確的標準,理論界主要有以下四種不同觀點:一是抽象危險犯說。該觀點認為,暴力、脅迫不要求客觀上實際達到造成職務(wù)不能執(zhí)行為的結(jié)果,只要足以妨礙公務(wù)執(zhí)行即可。二是采用具體危險犯說。該觀點對妨害公務(wù)罪中暴力、脅迫的強度有具體要求,即認為該暴力必須達到使公務(wù)人員不能順利執(zhí)行職務(wù)的程度。三是采取實害犯說。該觀點認為,妨害公務(wù)罪中暴力、脅迫的程度,必須在客觀上造成公務(wù)人員被迫放棄執(zhí)行公務(wù),或者違背其職責(zé)和意愿實施依法不應(yīng)當(dāng)實施的行為的程度。
實踐中的情況相對復(fù)雜,不能一概而論的說采用了哪種學(xué)說,也很少能具體判斷行為人的暴力程度是否足以妨礙執(zhí)行職務(wù),主要還是根據(jù)案件的具體情況加以判斷,筆者以兩個案例做對比,來具體闡述實踐中對于妨害公務(wù)罪“暴力”程度的判斷標準:
案例一,甲與鄰居產(chǎn)生糾紛,警察出警進行處理,因?qū)μ幚斫Y(jié)果不滿,甲毆打民警,經(jīng)鑒定民警身體所受損傷程度不構(gòu)成輕微傷,最終甲因情節(jié)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被無罪釋放。
案例二,乙等人酒后滋事,警察出警加以勸阻,現(xiàn)場眾人圍觀,乙等人推搡、拉拽民警,經(jīng)鑒定,民警身體所受損傷程度不構(gòu)成輕微傷,判決乙等人犯妨害公務(wù)罪,分別被判處拘役、有期徒刑等不同刑罰。
傷情是判斷暴力程度的重要依據(jù),但也并非唯一標準,縱觀五年多以來密云檢察院受理的全部妨害公務(wù)案例,對于使用暴力手段妨害公務(wù)的,大致處理情況為:
首先,造成執(zhí)行職務(wù)人員輕微傷以上傷情的原則上入罪。雖然很多學(xué)者認為單純地以傷情后果來判定暴力妨害程度,容易產(chǎn)生不當(dāng)入罪和不當(dāng)出罪等諸多問題,但是在司法實踐中,暴力所造成的傷情無疑是判斷暴力程度最直觀、最簡單、最易掌握的方法,相關(guān)證據(jù)具有證明力又容易收集,符合證據(jù)確實充分的起訴標準,因此實踐中,在排除其他具體情節(jié)干擾的情況下,只要行為人的暴力程度造成了執(zhí)行職務(wù)人員輕微傷以上的傷情,均以妨害公務(wù)罪進行評價。
其次,未造成執(zhí)行職務(wù)人員輕微傷以上后果的,結(jié)合案件具體情況,由裁判者進行自由裁量。正如以上兩個案例,行為人均使用暴力阻礙執(zhí)法,暴力程度均為致執(zhí)行職務(wù)人員“不構(gòu)成輕微傷”,然而在處理上卻截然不同。顯然在案例二中,雖然行為人的暴力程度未達到致人輕微傷以上的程度,但是因案例二行為人人數(shù)多、現(xiàn)場圍觀群眾多,造成了現(xiàn)場公共秩序的混亂,因此其行為亦構(gòu)成妨害公務(wù)罪。
綜上,筆者認為,“輕微傷以上的傷情”是妨害公務(wù)罪的充分而非唯一條件,在判斷行為人的暴力程度是否構(gòu)成妨害公務(wù)罪時,除了依據(jù)執(zhí)行職務(wù)人員的傷情鑒定外,還應(yīng)綜合考慮犯罪嫌疑人的人數(shù)、是否持械、被妨害的公務(wù)的重要和緊急程度、現(xiàn)場的環(huán)境、圍觀的群眾、暴力持續(xù)的時間、造成的后果和影響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