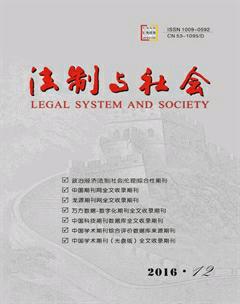入籍外國(guó)人民族成分法律確認(rèn)問(wèn)題研究
熊震+李昕陽(yáng)
摘 要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對(duì)入籍外國(guó)人的民族成分確定問(wèn)題進(jìn)行研究,既是對(duì)少數(shù)民族成分和族別問(wèn)題進(jìn)行研究的一個(gè)特殊切入點(diǎn),也是對(duì)我國(guó)移民日漸增多現(xiàn)實(shí)的回應(yīng)。本文將就我國(guó)對(duì)籍外國(guó)人的民族成分管理規(guī)定進(jìn)行梳理,分析其中的不合理因素。并在分析國(guó)際人權(quán)經(jīng)驗(yàn)對(duì)入籍外國(guó)人民族或族群進(jìn)行分類的優(yōu)點(diǎn)和限制條件的基礎(chǔ)上,對(duì)我國(guó)的現(xiàn)行管理辦法提出相應(yīng)的建議。
關(guān)鍵詞 少數(shù)民族成分 入籍外國(guó)人 法律確認(rèn)
作者簡(jiǎn)介:熊震,云南新秀律師事務(wù)所專職律師;李昕陽(yáng),云南云投股權(quán)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級(jí)項(xiàng)目主管,執(zhí)業(yè)律師。
中圖分類號(hào):D821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12.089
一、入籍外國(guó)人民族成分法律確認(rèn)問(wèn)題
由于我國(guó)到目前為止僅有3000余入籍外國(guó)人中國(guó),對(duì)移民入籍管制相對(duì)于其他國(guó)家嚴(yán)格甚多,同時(shí)加入中國(guó)籍的外國(guó)人民族成分確認(rèn)需要本人自主申請(qǐng)和經(jīng)過(guò)嚴(yán)格的程序批準(zhǔn),所以對(duì)于移民的民族成分進(jìn)行確認(rèn)多為個(gè)例,并沒(méi)有產(chǎn)生較大的影響。
但是,一方面,隨著經(jīng)濟(jì)全球化和我國(guó)經(jīng)濟(jì)的持續(xù)高速發(fā)展,人才與資本在世界范圍內(nèi)的流動(dòng)日益寬松和頻繁,外國(guó)移民的增多在未來(lái)會(huì)成為一個(gè)趨勢(shì)。另一方面。入籍外國(guó)人的民族成分確定問(wèn)題作為一個(gè)特殊的切入點(diǎn),有利于對(duì)少數(shù)民族成分和族別問(wèn)題進(jìn)行思考。
筆者綜合梳理了我國(guó)對(duì)于入籍外國(guó)人入籍后的民族成分的現(xiàn)行管理辦法(詳見本文下一章),是根據(jù)是否有相近民族成分來(lái)分別處理的:有相近的民族成分,則入籍外國(guó)人者可在入籍兩年內(nèi)申請(qǐng)?jiān)撓嘟褡宄煞郑粺o(wú)相近的民族成分,則可以采取在外國(guó)人原民族名稱上加注和申請(qǐng)加入我國(guó)某一民族成分兩個(gè)措施中的任一。
對(duì)于上述的現(xiàn)行管理辦法提供入籍外國(guó)人獲得民族成分的途徑并參照少數(shù)民族待遇對(duì)待,筆者認(rèn)為是不合適的,原因如下:
首先,對(duì)于有相近民族成分的外國(guó)入籍者可申請(qǐng)加入該民族成分的規(guī)定,筆者認(rèn)為是不符合我國(guó)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的目的的。在我國(guó)的建國(guó)初期,中央所建立的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是在結(jié)合實(shí)際國(guó)情的基礎(chǔ)上所作出的重大政治抉擇:“建立這一制度,目的是從制度上消除舊中國(guó)長(zhǎng)期存在的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保障少數(shù)民族當(dāng)家做主的權(quán)利,實(shí)現(xiàn)各民族的真正平等和真誠(chéng)團(tuán)結(jié)。” 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的建立是為了促進(jìn)中國(guó)本土民族的平等團(tuán)結(jié)和維護(hù)國(guó)家的統(tǒng)一。入籍的外國(guó)人并非我國(guó)本土的少數(shù)民族,不屬于我國(guó)民族政策所針對(duì)的適格主體,僅僅只是當(dāng)時(shí)從權(quán)的特殊規(guī)定,對(duì)其按照少數(shù)民族對(duì)待并不符合我國(guó)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的目的。
其次,入籍的外國(guó)人在性質(zhì)上并不能簡(jiǎn)單的歸類為應(yīng)受照顧的少數(shù)人群體。國(guó)際上對(duì)于少數(shù)人群體的概念是有嚴(yán)格的限制。筆者認(rèn)為我國(guó)的入籍外國(guó)人既不符合國(guó)際上的少數(shù)人標(biāo)準(zhǔn),也不符合我國(guó)對(duì)少數(shù)民族的相關(guān)標(biāo)準(zhǔn)。
二、入籍外國(guó)人民族成分法律確認(rèn)規(guī)定
在我國(guó)建立的以《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民族區(qū)域自治法》為核心的少數(shù)民族法律保障體系中,少數(shù)民族是一個(gè)具有法定權(quán)利義務(wù)的法律概念。《中國(guó)法學(xué)大辭典·法理學(xué)卷》認(rèn)為:一個(gè)權(quán)利主體在法律上所處的位置即是其的法律地位,這一地位的含義主要指其在相關(guān)法律中的狀態(tài)以及因之而產(chǎn)生的相應(yīng)的權(quán)利和義務(wù)關(guān)系。 所以,作為一個(gè)法律概念,少數(shù)民族的法律地位即指少數(shù)民族在法律上的地位以及相應(yīng)的權(quán)利義務(wù)關(guān)系。少數(shù)民族的法律確認(rèn),也就是指少數(shù)民族法律地位的取得。在法律和相關(guān)政策的執(zhí)行過(guò)程中對(duì)少數(shù)民族的法律確認(rèn),是少數(shù)民族公民取得國(guó)家法律規(guī)定的法律地位并且得以享有相應(yīng)法定權(quán)利的前提。
我國(guó)少數(shù)民族的法律確認(rèn)有兩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是對(duì)少數(shù)民族族稱的法律確認(rèn),第二種類型是對(duì)公民個(gè)人民族成分的法律確認(rèn)。根據(jù)2016年開始施行的《中國(guó)公民民族成分登記管理辦法》第3條對(duì)相關(guān)內(nèi)容的規(guī)定,公民個(gè)人民族成分的登記確認(rèn)必須填寫“經(jīng)國(guó)家正式確認(rèn)的民族名稱”。所以要確認(rèn)少數(shù)民族公民個(gè)人的民族成分,必須是以對(duì)其所屬少數(shù)民族群體的族稱進(jìn)行確認(rèn)作為前提條件。
由于我國(guó)對(duì)少數(shù)民族族稱的法律確認(rèn)并無(wú)相關(guān)的法律或規(guī)范性規(guī)定,筆者將在本節(jié)中根據(jù)我國(guó)政府實(shí)踐中確認(rèn)少數(shù)民族族稱的方式對(duì)其進(jìn)行梳理總結(jié)。對(duì)于少數(shù)民族公民個(gè)人民族成分的法律確認(rèn),我國(guó)的《憲法》、法律和行政法規(guī)中并無(wú)與少數(shù)民族公民民族成分和入籍外國(guó)人的民族成分確定問(wèn)題的確認(rèn)主體、確認(rèn)程序、確認(rèn)效力等相關(guān)的內(nèi)容。至今為止,與少數(shù)民族公民民族成分確認(rèn)相關(guān)的規(guī)定共有六份份規(guī)范性文件(其中一份為規(guī)章)。規(guī)章即2015年6月16日由國(guó)家民委、公安部第2號(hào)令頒布的《中國(guó)公民民族成分登記管理辦法》(以下簡(jiǎn)稱為2015年規(guī)章),該規(guī)章從2016年1月1日起施行。五份規(guī)范性文件按照時(shí)間順序排列則依次是第一份1981年11月28日由國(guó)務(wù)院第三次人口普查領(lǐng)導(dǎo)小組、公安部、國(guó)家民委共同公布的《新恢復(fù)或改正民族成分的處理原則的通知》(以下簡(jiǎn)稱為1981年通知);第二份1986年2月8日由國(guó)家民委單獨(dú)公布的《關(guān)于恢復(fù)或改正民族成分問(wèn)題的補(bǔ)充通知》(以下簡(jiǎn)稱為1986年補(bǔ)充通知);第三份1986年2月1日由公安部、國(guó)家民委共同公布的《關(guān)于居民身份證使用民族文字和民族成分填寫問(wèn)題的通知》(以下簡(jiǎn)稱為1986年身份證通知);第四份1989年11月15日由國(guó)家民委、公安部共同公布的《關(guān)于暫停更改民族成分工作的通知》(以下簡(jiǎn)稱為1989年暫停通知);第五份1990年5月10日由國(guó)務(wù)院第四次人口普查領(lǐng)導(dǎo)小組、國(guó)家民委、公安部共同公布的《關(guān)于中國(guó)公民確定民族成分的規(guī)定》(以下簡(jiǎn)稱為1990年規(guī)定)。
筆者將首先以上述的規(guī)章和規(guī)范性文件為基礎(chǔ),從時(shí)間順序梳理我國(guó)少數(shù)民族公民民族成分確認(rèn)(以下簡(jiǎn)稱少數(shù)民族成分)的管理主體、確認(rèn)原則和確認(rèn)程序,進(jìn)而在此基礎(chǔ)上對(duì)入籍外國(guó)人民族成分法律確認(rèn)的特殊性進(jìn)行分析。
第一,從對(duì)相關(guān)規(guī)范性文件的公布主體和其中關(guān)于少數(shù)民族成分確認(rèn)的內(nèi)容進(jìn)行分析后,筆者認(rèn)為我國(guó)少數(shù)民族成分確認(rèn)的管理主體是國(guó)家民委和公安部門。理由如下:
其一,相關(guān)的規(guī)范性文件和規(guī)章的公布主體主要是國(guó)家民委和公安部門。從1981年公布第一份規(guī)范民族成分問(wèn)題的文件開始,到2015年共同公布迄今關(guān)于少數(shù)民族確認(rèn)問(wèn)題法律效力最高的《規(guī)章》為止,相關(guān)的所有規(guī)定都是由國(guó)家民委和公安部所公布。雖然1981年發(fā)布的《新恢復(fù)或改正民族成分的處理原則的通知》和1990年所發(fā)布的《關(guān)于中國(guó)公民確定民族成分的規(guī)定》的這兩份規(guī)范性文件是由國(guó)家民委、公安部和國(guó)務(wù)院人口普查領(lǐng)導(dǎo)小組共同署名公布的,但這是因?yàn)樯贁?shù)民族成分法律確認(rèn)和這兩次的人口普查工作相關(guān),并不能僅僅據(jù)此將人口普查領(lǐng)導(dǎo)小組也視為確認(rèn)主體。所以,從相關(guān)規(guī)章和規(guī)范性文件的公布主體可以清晰反應(yīng)我國(guó)少數(shù)民族法律確認(rèn)事項(xiàng)的主管機(jī)關(guān)是民族部門和公安戶籍部門。
其二,國(guó)家民委和公安部二者之間的分工配合自1986年補(bǔ)充通知明確后,直至今日始終是由各級(jí)民族部門負(fù)責(zé)審批民族成分恢復(fù)、變更,各級(jí)公安戶籍部門負(fù)責(zé)相關(guān)的戶口登記和身份證辦理。在1981年通知中,由于時(shí)代背景的原因,對(duì)于民族成分工作的管理主體并沒(méi)有明確的劃分。只是在第七段中規(guī)定了需要到戶籍部門辦理手續(xù)。在1986年補(bǔ)充通知中,則規(guī)定了“恢復(fù)或改正民族成分的”根據(jù)人數(shù)和范圍由各級(jí)民族工作部門審批,戶籍管理部門憑縣審批證明辦理手續(xù)。在1990年規(guī)定中第七段對(duì)主管部門的敘述只是對(duì)1986年通知的確認(rèn),并無(wú)變動(dòng)。2015年規(guī)章則規(guī)定的較為詳盡明確。規(guī)章在第四條明確了有關(guān)公民的民族成分的登記工作和管理工作由國(guó)務(wù)院的民族事務(wù)部門和國(guó)務(wù)院的公安部門負(fù)責(zé)指導(dǎo)和監(jiān)管。在第11條規(guī)定了辦理民族成分變更各個(gè)環(huán)節(jié)中,公安部門負(fù)責(zé)戶口登記,民族事務(wù)部門負(fù)責(zé)審批。
第二,我國(guó)規(guī)范性文件對(duì)少數(shù)民族成分的確認(rèn)始終奉行的是血統(tǒng)原則,即依據(jù)父或者母的民族成分確認(rèn)子女的民族成分。在1981年通知中雖未直接規(guī)定子女的民族成分依據(jù)父或母的民族成分確認(rèn),但在第三段中規(guī)定了隔代恢復(fù)或改變民族成分要求:如果是隔代要更改或者恢復(fù)自己的民族成分的,不能直接進(jìn)行更改。在父母健在的情況下,需要先行對(duì)父或者母的相應(yīng)民族成分進(jìn)行恢復(fù)或更改,進(jìn)而才可以在此基礎(chǔ)上對(duì)自己的民族成分進(jìn)行恢復(fù)或更改。如果父母已然去世的,則也需要對(duì)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相關(guān)的民族成份進(jìn)行恢復(fù)或更改,才能在此基礎(chǔ)上對(duì)自己的民族成分進(jìn)行恢復(fù)或更改。這一規(guī)定內(nèi)容從側(cè)面體現(xiàn)了我國(guó)公民的民族成分確認(rèn)采取的是血統(tǒng)原則。在人類整體的歷史進(jìn)程中,血統(tǒng)一直是民族和族群認(rèn)定其成員的主導(dǎo)標(biāo)準(zhǔn)。雖然有其他類型的民族和族群認(rèn)定標(biāo)準(zhǔn),但依據(jù)父系、母系的血脈延續(xù)對(duì)是否為共同體的成員進(jìn)行認(rèn)定一直是最直接、最明顯的方法。我國(guó)的少數(shù)民族群體成員的身份認(rèn)定也采取了這一原則,即依據(jù)父系、母系的血脈延續(xù)對(duì)公民是否屬于少數(shù)民族群體成員進(jìn)行確認(rèn)(即公民的民族成分確認(rèn))。這一原則在具體的規(guī)定中是這樣表述的:1986年補(bǔ)充通知中的第二段則直接提出了公民自己的民族成分,應(yīng)該根據(jù)其父一方或母一方的民族成分進(jìn)行相應(yīng)的確定。1990年規(guī)定亦是在第二段中規(guī)定了公民自己的民族成分,應(yīng)該從其父或母其中一方的民族成分里進(jìn)行選擇并予以確定。2015年規(guī)章則在第5條中再次明確了血統(tǒng)原則:“公民的民族成分,只能依據(jù)其父親或者母親的民族成分確認(rèn)、登記。”并且在此條中將父母的定義明確化:即在2015年規(guī)章中,但凡其條文所涉及內(nèi)容用到父、母一詞的,其范圍包括親生的父母、法律上撫養(yǎng)的父母和合法過(guò)繼的父母三種情形。如此便將依據(jù)養(yǎng)父母、繼父母確認(rèn)民族成分的情形涵蓋至本原則的外延之中,由于此類情況較為特殊并涉及民族成分的更改,筆者將在下一節(jié)中詳述。
第三,我國(guó)對(duì)于少數(shù)民族公民確認(rèn)的程序只在2015年規(guī)章的第6條中有所規(guī)定:負(fù)責(zé)辦理戶口登記的相應(yīng)級(jí)別公安部門在進(jìn)行該業(yè)務(wù)辦理時(shí),要依據(jù)新增人口的父親或者母親的民族成分進(jìn)行確認(rèn)和登記。如果其父親或者母親的民族成分并不相同,則應(yīng)該讓其父母先行共同簽署新增人口的民族成分填報(bào)申請(qǐng)書,再根據(jù)申請(qǐng)書所確認(rèn)的少數(shù)民族成分為新增人口進(jìn)行戶口辦理。依據(jù)條文推理,則辦理新增人口的戶口登記時(shí),只要符合辦理戶口登記的條件即可依據(jù)父或母的民族成分確認(rèn)其民族成分。
下文將根據(jù)上述的規(guī)章和規(guī)范性文件,對(duì)于入籍外國(guó)人者的民族成分管理問(wèn)題進(jìn)行分析。
對(duì)于入籍外國(guó)人者的民族成分管理,最初是在1986年通知第三段中規(guī)定為兩種情形。第一種是當(dāng)入籍外國(guó)人者原本的民族名稱與中國(guó)的某個(gè)定稱民族名稱相同的,則可以填寫為此民族。第二種是沒(méi)有相同民族的情況,則處理如下:按照其本人所稱的原本民族填寫其民族成分,但是需要在填寫的民族成分之后注明為是入籍的特殊情況處理,比如說(shuō)“烏克蘭(入籍)”。
1990年規(guī)定的第八段則不僅細(xì)化了1986年的規(guī)定,而且增加了對(duì)入籍外國(guó)人者子女和跨國(guó)婚姻子女的民族成分的規(guī)定。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段規(guī)定當(dāng)加入中國(guó)籍的外國(guó)人經(jīng)過(guò)符合規(guī)定的程序填報(bào)為屬于我國(guó)的任一少數(shù)民族成分時(shí),對(duì)該加入中國(guó)籍的外國(guó)人參照其填報(bào)的少數(shù)民族所享受的待遇對(duì)待。
首先,入籍外國(guó)人者的民族成分可以申請(qǐng)為相近的我國(guó)現(xiàn)有民族,但是“須在入籍后的兩年內(nèi)申請(qǐng)辦理”。這一年的規(guī)定并無(wú)入籍外國(guó)人之后在原民族名稱上加注的規(guī)定,而是增加了入籍的外國(guó)人個(gè)人要求填報(bào)為中國(guó)國(guó)內(nèi)任一民族成分的,應(yīng)該先從其所屬的部門內(nèi)開具有關(guān)的證明,然后再向省一級(jí)別的民族事務(wù)管理部門提交申請(qǐng)。
其次,在1990年的規(guī)定之中,還增加了對(duì)于入籍外國(guó)人者后裔和中國(guó)人同外國(guó)人結(jié)婚所生的子女的民族成分的規(guī)定。即當(dāng)父母中的任一一方屬于中國(guó)人或者是加入中國(guó)籍者的情況下,并且申請(qǐng)?zhí)顖?bào)為我國(guó)某一民族成分的。作為申請(qǐng)者(即具有中國(guó)國(guó)籍的子女)應(yīng)該填報(bào)父母中屬于中國(guó)一方的民族成分。
2015年的規(guī)章則在第二十條中完善了入籍者民族成分的規(guī)定。增加了當(dāng)中國(guó)公民收養(yǎng)的子女取得中國(guó)籍時(shí),其個(gè)人的民族成分應(yīng)該根據(jù)收養(yǎng)其的中國(guó)公民的民族成分進(jìn)行確定。至于其他的入籍外國(guó)人民族成分問(wèn)題,則在該條中規(guī)定為應(yīng)按照國(guó)家有關(guān)規(guī)定進(jìn)行。
綜合上述內(nèi)容,我國(guó)對(duì)入籍外國(guó)人者的民族成分現(xiàn)行管理辦法為:
其一,對(duì)于入籍外國(guó)人者,有相近的民族成分,則入籍外國(guó)人者可在入籍兩年內(nèi)申請(qǐng)?jiān)撓嘟褡宄煞郑粺o(wú)相近的民族成分,則可以采取在外國(guó)人原民族名稱上加注和申請(qǐng)加入我國(guó)某一民族成分兩個(gè)措施中的任一。
其二,對(duì)于入籍外國(guó)人者的后裔、中國(guó)人同外國(guó)人結(jié)婚所生子女、中國(guó)公民收養(yǎng)子女,其在取得中國(guó)國(guó)籍后才可根據(jù)中國(guó)一方父(母)的民族成分確定其個(gè)人的民族成分。對(duì)于以上兩種入籍外國(guó)人少數(shù)民族成分確認(rèn)方式,可以明確地對(duì)比出是與本章上半部分我國(guó)少數(shù)民族公民民族成分確認(rèn)原則和確認(rèn)程序不一致,乃至相對(duì)突兀的。
三、入籍外國(guó)人確認(rèn)問(wèn)題的國(guó)際經(jīng)驗(yàn)
過(guò)去的幾十年中,人權(quán)已然成為了一個(gè)占主導(dǎo)地位的國(guó)際性話語(yǔ)、一個(gè)全球性的通用語(yǔ)、甚至是“世界性的世俗宗教”。 在國(guó)際人權(quán)領(lǐng)域當(dāng)中,《公民權(quán)利與政治權(quán)利國(guó)際公約》(以下簡(jiǎn)稱為《公約》)是對(duì)于少數(shù)人權(quán)利保護(hù)的主體和內(nèi)容較為權(quán)威的法律文件。《公約》對(duì)于入籍外國(guó)人的分類和確認(rèn)問(wèn)題,筆者認(rèn)為公約中值得注意的有三點(diǎn):
其一,將入籍外國(guó)人在滿足一定條件的情況下分類入少數(shù)人之中,但并不歸類為族群上的少數(shù)人。《公約》對(duì)少數(shù)人的概念進(jìn)行了嚴(yán)格的限制。現(xiàn)在國(guó)際上對(duì)《公約》第27條中關(guān)于少數(shù)人這一概念的主流解釋是卡波托第所做的:“它明確地只限于第27條的適用,并將下面這些群體成為少數(shù)人:第一,在所屬的國(guó)家領(lǐng)域之內(nèi),在人口的總量上要比另外的群體少;第二,這個(gè)群體不能是這個(gè)國(guó)家占統(tǒng)治地位的優(yōu)勢(shì)群體;第三,這個(gè)群體必須具有與所屬的國(guó)家其他的群體在人種、信仰或者語(yǔ)言方面的特征,并且這個(gè)群體的成員至少在顯示出了繼續(xù)保持這種不同特征的希望或努力。” 以上的條件必須全部滿足,否則不能被認(rèn)定為少數(shù)人,比如南非的白人雖然只占十分之一的人口,但因?yàn)榫佑趦?yōu)勢(shì)地位而非少數(shù)人。同時(shí),少數(shù)人群體還必須具備一定程度的穩(wěn)定性,在這一問(wèn)題上智利的修正案用詞更為明確,指“穩(wěn)定的、長(zhǎng)期存在的”少數(shù)人。 所以,《公約》對(duì)少數(shù)人的認(rèn)定是非常謹(jǐn)慎的。在此基礎(chǔ)上,入籍的外國(guó)人只有在同時(shí)滿足居住到一定期限、達(dá)到一定人數(shù)、處于非支配地位并且愿意保留其文化、傳統(tǒng)、宗教、語(yǔ)言特征的前提下,才能在其所居住的國(guó)家之內(nèi)享有國(guó)際人權(quán)中對(duì)少數(shù)人權(quán)利的保護(hù)規(guī)定。同時(shí),由于入籍的外國(guó)人并非居住在本國(guó)內(nèi)的世居族群,所以只被歸類為語(yǔ)言或宗教上的少數(shù)人。
其二,《公約》將少數(shù)人群體的存在視作一個(gè)無(wú)需確認(rèn)的客觀問(wèn)題,在具體個(gè)案的處理上留下了足夠的彈性空間。但這也和《公約》將少數(shù)人的權(quán)利定位為消極權(quán)利有關(guān),需要辯證的看待。《公約》關(guān)于第27條的討論,達(dá)成了對(duì)于少數(shù)人是否存在是一個(gè)實(shí)際問(wèn)題,而非取決于其他主體的承認(rèn)。在當(dāng)時(shí)的會(huì)議記錄中是這樣表述的:“在任何情況下,對(duì)于一國(guó)人口之中的某一群體是否可以被看作是少數(shù)人是一個(gè)涉及實(shí)際經(jīng)驗(yàn)的問(wèn)題,而不是取決于有關(guān)的國(guó)家在法律上對(duì)相關(guān)群體的承認(rèn)。 ”但是,對(duì)于實(shí)際操作中的如何憑實(shí)際經(jīng)驗(yàn)認(rèn)定,公約采取了模糊化的處理,為實(shí)踐留下了足夠的彈性空間。
其三,在《公約》之中,將少數(shù)人的權(quán)利定義為一種帶有集體性質(zhì)的個(gè)人權(quán)利。這種做法既保護(hù)了少數(shù)人的權(quán)利、避免了政治上的分裂可能性,又使上文中的對(duì)少數(shù)人群體確認(rèn)的彈性處理具有了合理性。所以該條之中的少數(shù)人權(quán)利在性質(zhì)分類上是消極權(quán)利和帶有集體性質(zhì)的個(gè)人權(quán)利。第27條是《公約》中唯一一個(gè)具有典型的消極表述的規(guī)定,即“不得否認(rèn)個(gè)人享有”公約中的權(quán)利。 換言之,這一條款僅僅強(qiáng)調(diào)了國(guó)家不去侵犯少數(shù)人個(gè)體的文化、語(yǔ)言、宗教權(quán)利的消極義務(wù),對(duì)于少數(shù)人而言這是一項(xiàng)明確的消極權(quán)利。同時(shí),國(guó)際上公認(rèn)這一條中的權(quán)利是帶有集體性質(zhì)的個(gè)人權(quán)利。雖然只有在集體有意識(shí)的情況下能夠一起行使相應(yīng)權(quán)利,但其本身的性質(zhì)就是一種個(gè)人權(quán)利。這一條款只是用于“屬于少數(shù)人群體的個(gè)人”。卡波托第在其編寫的評(píng)注中詳細(xì)列舉為什么如此表述的具體考量:“首先,少數(shù)人保護(hù)這一權(quán)利最初便是以個(gè)人權(quán)利的形式出現(xiàn)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第二,除了帶有政治性的民族自決權(quán)之外,《公約》之中所規(guī)定的其他所有權(quán)利在性質(zhì)上都屬于個(gè)人的權(quán)利;第三,從政治的角度考慮,讓少數(shù)人的身份成為利益劃分的一個(gè)標(biāo)準(zhǔn)會(huì)讓少數(shù)人群體的政治性加強(qiáng),甚至?xí)鰪?qiáng)其分裂的可能性。” 《公約》將少數(shù)人權(quán)利定義為帶有集體性質(zhì)的個(gè)人權(quán)利,從而在實(shí)踐中將少數(shù)人群體視作一個(gè)實(shí)際問(wèn)題來(lái)處理。所以《公約》對(duì)少數(shù)人權(quán)利的保護(hù)并不需要對(duì)少數(shù)人群體進(jìn)行確認(rèn),這樣做的好處是不僅保護(hù)了少數(shù)人的權(quán)益,更避免了政治上的分離傾向。但是,這和公約將少數(shù)人的權(quán)利視為消極權(quán)利,僅僅限于國(guó)家有消極義務(wù)不得侵犯少數(shù)人權(quán)利亦有關(guān)系。
四、入籍外國(guó)人的民族確認(rèn)問(wèn)題思考
筆者認(rèn)為入籍外國(guó)人的民族成分問(wèn)題主要矛盾在于現(xiàn)行管理辦法提供入籍外國(guó)人獲得民族成分的途徑并參照少數(shù)民族待遇對(duì)待,這一做法從我國(guó)制定少數(shù)民族相關(guān)法律和政策的出發(fā)點(diǎn)和原則進(jìn)行考量,并不具備充分的合法性。并且簡(jiǎn)單的將入籍外國(guó)人的民族身份管理參照少數(shù)民族進(jìn)行,是不符合入籍外國(guó)人所屬群體性質(zhì)歸類的。即使在國(guó)際上也未把入籍外國(guó)人簡(jiǎn)單的歸類入少數(shù)族群之中或是讓其在個(gè)人身份上加入入籍國(guó)的少數(shù)民族群體之中。對(duì)于入籍外國(guó)人的民族成分問(wèn)題,筆者認(rèn)為應(yīng)該分為兩個(gè)階段處理。
首先,在一個(gè)較長(zhǎng)的時(shí)間內(nèi),我國(guó)的入籍外國(guó)人并不符合國(guó)際上少數(shù)人的標(biāo)準(zhǔn)和我國(guó)的少數(shù)民族標(biāo)準(zhǔn),不應(yīng)按照我國(guó)現(xiàn)有族稱對(duì)其劃定成分。筆者在上一章中已詳細(xì)論述了入籍外國(guó)人在國(guó)際人權(quán)領(lǐng)域被列為少數(shù)人進(jìn)行權(quán)利保護(hù)的條件和限制,在本節(jié)中就不再累述。
其次,當(dāng)未來(lái)我國(guó)的入籍外國(guó)人達(dá)到國(guó)際上對(duì)少數(shù)人的標(biāo)準(zhǔn)時(shí),則應(yīng)參照少數(shù)人權(quán)利保護(hù)辦法對(duì)其進(jìn)行管理。但是,入籍外國(guó)人在性質(zhì)上自始至終并不屬于少數(shù)民族范疇,不能簡(jiǎn)單的套用我國(guó)的少數(shù)民族成分并參照少數(shù)民族待遇進(jìn)行相應(yīng)的對(duì)待。
綜上所述,筆者的具體建議為:
首先,筆者認(rèn)為要取消外國(guó)人加入我國(guó)民族成分(無(wú)論是相近民族成分還是入籍兩年內(nèi)自愿申請(qǐng)加入)并參照少數(shù)民族對(duì)待的規(guī)定,一方面,從少數(shù)民族成分管理的角度講,對(duì)入籍外國(guó)人參照少數(shù)民族對(duì)待,并不符合我國(guó)的民族政策的精神;另一方面,從國(guó)際上對(duì)待的入籍少數(shù)人的經(jīng)驗(yàn)來(lái)看,如果直接對(duì)入籍的少數(shù)人進(jìn)行認(rèn)定并制定優(yōu)惠政策,是不符合國(guó)際上的少數(shù)人標(biāo)準(zhǔn)和立法取向的。
其次,在當(dāng)下我國(guó)入籍外國(guó)人較少的這一時(shí)期,可以繼續(xù)執(zhí)行入籍外國(guó)人在民族一欄統(tǒng)一加注的管理辦法,但不能按照少數(shù)民族對(duì)待。即使在未來(lái)入籍外國(guó)人增多的情況下也不能提供其加入我國(guó)民族成分或按照少數(shù)民族待遇處理的法律途徑。因?yàn)槿爰鈬?guó)人既不屬于少數(shù)民族又非我國(guó)少數(shù)民族政策的照顧對(duì)象,對(duì)其的管理政策應(yīng)參考國(guó)際上少數(shù)人的標(biāo)準(zhǔn)來(lái)對(duì)待。
最后,在有實(shí)際需要的情況下,我國(guó)應(yīng)實(shí)事求是制定針對(duì)入籍外國(guó)人群體的管理辦法。即使需要制定對(duì)入籍外國(guó)人群體的優(yōu)惠政策,也不能簡(jiǎn)單的套用我國(guó)的少數(shù)民族政策。并且,筆者認(rèn)為,我國(guó)如果要制定對(duì)入籍外國(guó)人群體的優(yōu)惠政策,必須是在其滿足國(guó)際上對(duì)少數(shù)人定義的前提下才能制定。即對(duì)于以下標(biāo)準(zhǔn)全部能夠滿足:第一,在所屬的國(guó)家領(lǐng)域之內(nèi),在人口的總量上要比另外的群體少;第二,這個(gè)群體不能是這個(gè)國(guó)家占統(tǒng)治地位的優(yōu)勢(shì)群體;第三,這個(gè)群體必須具有與所屬的國(guó)家其他的群體在人種、信仰或者語(yǔ)言方面的特征,并且這個(gè)群體的成員至少在顯示出了繼續(xù)保持這種不同特征的希望或努力。 只有加入中國(guó)籍的外國(guó)人群體滿足了上述的所有條件,才能對(duì)其參照少數(shù)人的國(guó)際經(jīng)驗(yàn)進(jìn)行照顧和優(yōu)惠。否則只應(yīng)制定針對(duì)外國(guó)人群體的管理辦法,而不應(yīng)制定相關(guān)的優(yōu)惠政策。
注釋:
朱維群.關(guān)于當(dāng)前民族工作幾個(gè)問(wèn)題的思考.中國(guó)統(tǒng)一戰(zhàn)線.2011(1).15.
孫國(guó)華主編.中華法學(xué)大辭典.中國(guó)檢察出版社.1997.246.
[英]馬爾科姆·郎芳.人權(quán)與千年計(jì)劃.劍橋大學(xué)出版社.2013.20.
[奧]曼弗雷德·諾瓦克著.上孫世彥、畢小青譯.公民權(quán)利與政治權(quán)利國(guó)際公約評(píng)注.三聯(lián)書店.2005.670,672,685,665.
參考文獻(xiàn):
[1][英]安東尼·史密斯著. 葉江譯.民族主義:理論,意識(shí)形態(tài).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2]戴小明.中國(guó)民族區(qū)域自治的憲政分析.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8.
[3]杜玉亭.民族田野五十年.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
[4]費(fèi)孝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學(xué)院出版社.1989.
[5]黃光學(xué).中國(guó)的民族識(shí)別: 56 個(gè)民族的來(lái)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6]沈壽文.中國(guó)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的性質(zhì).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7]周勇.少數(shù)人權(quán)利的法理.北京: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12.
[8]陳興貴.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與中國(guó)民族識(shí)別.云南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8,25(3).
[9]杜玉亭.基諾族識(shí)別四十年回識(shí)——中國(guó)民族識(shí)別的宏觀思考.云南社會(huì)科學(xué).1997(6).
[10]戴小明、盛義龍、劉木球.民族識(shí)別與法律認(rèn)定——以(亻革)家人認(rèn)定個(gè)案為研究樣本.中央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1(5).
[11]戴小明、盛義龍.未識(shí)別民族法律地位探微——以民族平等為研究視角.中南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bào):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2,32(5).
[12]費(fèi)孝通.關(guān)于我國(guó)民族的識(shí)別問(wèn)題.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1980(l).
[13]黃澤.云南未識(shí)別群體研究的族群理論意義.廣西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1(2).
[14]郝時(shí)遠(yuǎn).中文語(yǔ)境中的“族群”及其應(yīng)用泛化的檢討.思想戰(zhàn)線.2002, 28(5).
[15]蔣立松.略論“族群”概念的西方文化背景.黑龍江民族叢刊. 2002(1).
[16]金炳鎬、畢躍光、韓艷偉.民族與族群:是概念的互補(bǔ)還是顛覆?——民族理論前沿研究系列論文之二.黑龍江民族叢刊.2012(2).
[17]林耀華.中國(guó)西南地區(qū)的民族識(shí)別.云南社會(huì)科學(xué).1984(2).
[18]馬戎.論民族意識(shí)的產(chǎn)生.云南民族學(xué)院學(xué)報(bào):哲社版.2000,17(2).
[19]馬戎.理解民族關(guān)系的新思路——少數(shù)族群?jiǎn)栴}的“去政治化”.北京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4(6).
[20]馬戎.全球化與民族關(guān)系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07(4).
[21]馬俊毅、席隆乾.關(guān)于當(dāng)今中國(guó)亞國(guó)家層次民族概念及其英譯的新思考(二)——National ethnic unit:我國(guó)亞國(guó)家層次民族英譯的新探索.廣西民族研究. 2013(2).
[22]聶文晶.新中國(guó)成立以來(lái)西南地區(qū)民族識(shí)別研究概述.民族學(xué)刊.2013(5).
[23]潘蛟.“族群”及其相關(guān)概念在西方的流變.廣西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 2003,25(5).
[24]沈壽文、董迎軒.對(duì)現(xiàn)行《憲法》與《民族區(qū)域自治法》文本之解讀——基于維護(hù)國(guó)家統(tǒng)一、保障中央統(tǒng)一領(lǐng)導(dǎo)的取向.云南社會(huì)科學(xué).2012(1).
[25]沈壽文.憲法文本中“民族”不同內(nèi)涵的知識(shí)根源.云南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3(3).
[26]沈壽文.撤自治縣(州)改設(shè)“市”異議之商榷——兼駁增設(shè)“自治市”主張.黑龍江民族叢刊.2013(4).
[27]唐建兵.也議“民族識(shí)別”與中國(guó)民族問(wèn)題——與馬戎教授商榷.西南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bào):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4(1).
[28]汪堂家.沿用“我國(guó)有56個(gè)民族”的提法有待商榷.社會(huì)觀察.2004(10).
[29]王希恩.中國(guó)民族識(shí)別的依據(jù).民族研究.2010(5).
[30]王文光、段紅云、尤偉瓊.當(dāng)代云南民族識(shí)別的學(xué)術(shù)回顧.思想戰(zhàn)線.2011, 37(1).
[31]徐杰舜.論族群與民族.民族研究.2002(1).
[32]周剛志.論“消極權(quán)利”與“積極權(quán)利”——中國(guó)憲法權(quán)利性質(zhì)之實(shí)證分析.法學(xué)評(píng)論.2015(3).
[33]朱倫.西方的“族體”概念系統(tǒng)——從“族群”概念在中國(guó)的應(yīng)用錯(cuò)位說(shuō)起.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