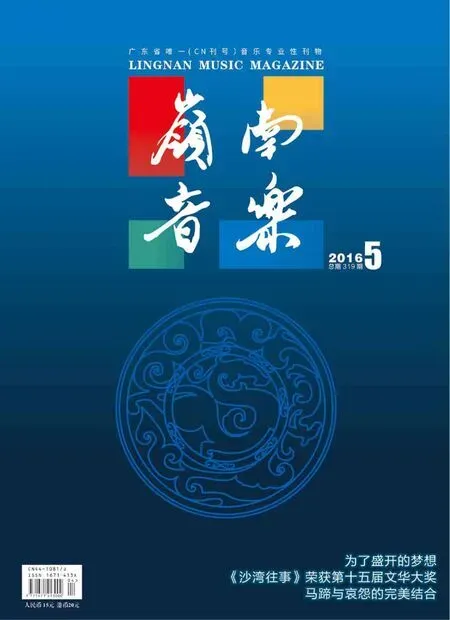冼星海,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的旗幟性人物
文|劉倩 華南理工大學
冼星海,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的旗幟性人物
文|劉倩 華南理工大學

抗戰(zhàn)時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與實踐發(fā)展的重要時期。這一時期的救亡歌曲創(chuàng)作,尤顯冼星海(1905-1945)為突出。在全民抗戰(zhàn)的形勢下,社會民眾的民族意識得到空前激發(fā),加濃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社會思潮,并使馬克思主義迅速影響到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客觀上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
在社會各階層中,知識分子是較為主動的思考者與行動者,這在哲學、經濟、歷史、藝術等各個領域都有著非常突出的表現。在文學藝術領域,對“中國精神”、“中國作風”、“中國氣派”、“民族形式”、“大眾化”等的思考與實踐也相當活躍,特別在音樂界,眾多音樂家更是將音樂與抗戰(zhàn)實踐和群眾生活緊密相連,搜集各地民歌、運用民族形式積極進行創(chuàng)作。作為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冼星海懷著“為人民”的情感,將現代西方作曲技法與中國傳統民間曲調相融合,創(chuàng)作了大量廣為流傳的革命性群眾歌曲,在音樂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中,冼星海可謂是音樂界的旗幟性人物。
冼星海的作品蘊含著豐富的人民因素,有著突出的“為人民”的價值取向,這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價值要求完全一致。回國后的他,當看到祖國的滿目蒼痍,看到人民大眾正遭受的苦難,根源于內心愛國愛民情感的創(chuàng)作力量被猛烈激發(fā)。據他回憶,“尤其覺得高興的,是我的作品那時已找到了一條路,吸收被壓迫人們的情感。對于如何用我的力量挽救祖國危亡的問題,是有了把握了。我的作品已前進了一步。我的寫作和實踐初步地聯系起來了”。①這一時期,在抗戰(zhàn)救亡的時代主題下,冼星海創(chuàng)作了大量音樂作品,且?guī)缀趺恳徊孔髌范寂c祖國人民有著深刻的聯系。
初期,在上海、武漢,他譜曲創(chuàng)作了大量充滿戰(zhàn)斗激情的抗日救亡愛國歌曲,用音樂的形式實現著激發(fā)全民族抗戰(zhàn)精神的歷史責任。《運動會》、《黃河之戀》、《救國軍歌》、《在太行山上》等都是這一方面的代表作品,作品充滿了一致抗戰(zhàn)的現實性,也充滿了革命浪漫主義的氣魄。對于自己不遺余力地創(chuàng)作大量救亡歌曲,冼星海認為,“中華民族在現今的處境,正是一個謀解放的掙扎期間。救亡歌曲正是為了需要而產生的時代性的藝術,是富有建設大眾國際責任的,它的呼聲愈強大,影響也就愈大;換言之,它就是我們民族的唯一精神安慰者,更可以說是我們的國魂。所以一個被壓迫的民族缺少不了救亡的歌詠”。②而這種具有戰(zhàn)斗性的群眾歌曲對于抗戰(zhàn)宣傳來說必不可少,最重要最直接的意義就在于其蘊含的巨大的精神性,發(fā)揮了民眾統一認識、動員戰(zhàn)斗的作用。對于抗戰(zhàn)所要采取的適當形式,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張聞天曾舉例談及,“比如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的方針,開始時不是大多數中國人都能了解與擁護的。當時我們用什么口號使群眾根據自身的經驗來了解我們的方針的正確呢?這就是‘停止內戰(zhàn),一致抗日’的口號。每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對于中國內戰(zhàn)的痛苦都是切身感受到的,他們都能夠懂得日寇的無限制的侵掠同內戰(zhàn)是不能分離的。因此他們也許還不了解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的方針,然而對于停止內戰(zhàn)、一致抗日的口號是熱烈擁護的。結果,內戰(zhàn)停止了,中國開始統一了,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得到了初步的成功”。③在這里,冼星海創(chuàng)作的抗日戰(zhàn)歌就是一種具有力量的“口號”,通過挺拔矯健的旋律、鏗鏘有力的節(jié)奏凸顯了民族抗日救亡的使命,并且,一定程度上,他創(chuàng)作的一些歌曲還實現了黨對抗戰(zhàn)方針策略的宣傳,如《游擊軍》、《到敵人后方去》等。及至后期在延安,冼星海更是進入到了創(chuàng)作的巔峰期,譜寫出了《黃河大合唱》、《生產大合唱》等時代經典。
可以說,抗戰(zhàn)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要求最直接地體現在馬克思主義大眾化之中,也就是將抗戰(zhàn)的思想、文化、理論普及于廣大群眾,而這也是冼星海這一時期創(chuàng)作的價值追求。冼星海曾說,“在巴黎七年,親自感受過勞動的生活,并參加過國際的工黨會議,當時思想突變,堅決同情共產黨。回國后,參加救亡運動,提倡大眾化歌詠,鼓吹民族解放的偉大戰(zhàn)爭,使歌詠運動能夠配合現在的抗日、反侵掠、反漢奸的政治趨向,來完成民族解放,達到日本帝國主義”。④
冼星海的歌曲作品由于易記易唱,易于被群眾接受,因此帶有典型的大眾化特征。更為深刻的是,冼星海同時又認識到,“過去救亡歌曲雖然發(fā)生很大效果和得到廣大群眾的愛護,但不久又為群眾所唾棄。因此,‘量’與‘質’的不平衡,就使很多歌曲在短期間消滅或全失效用。”⑤因而,他的創(chuàng)作十分注重藝術性,有意識的將西方現代作曲技巧與中國傳統民族風格相融合,創(chuàng)造出極富個性的藝術作品,而這種獨具風格的藝術性恰恰又奠定了其作品大眾化的堅實基礎,促成了作品在更大范圍的傳播與傳唱,也使之成為音樂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與實踐的有力推動者。
民族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本質要求,冼星海的創(chuàng)作就帶有鮮明的民族風格。對于民歌的認識,他認為,“‘民歌不一定是偉大的音樂,卻一定是人情的音樂。’我們是人民,不能脫離民族、國家的關系,也不能脫離階級、黨派立場。所謂人民,也是有他的國際性的,不是狹小的。我們研究民歌的出發(fā)點,必須著眼于民族,因為民歌是人民的歌”。⑥ 為此,他積極吸收利用民間音樂,從中尋找創(chuàng)作素材。《黃河大合唱》中的《河邊對口曲》就明顯借鑒了陜北、山西的民歌旋律,顯現出濃郁鄉(xiāng)土氣息。《生產大合唱》中的《二月里來》也是一個“江南風味很重的曲子”,充滿了民族的風情。同時,中國傳統的五聲性旋律也常被冼星海作為主題旋律創(chuàng)作,以五聲音階為主,接近民族調式。如《保衛(wèi)黃河》中,作曲家采用了十分民族化的下行小六度音程,頗具個性化。
當然,冼星海對作品的藝術追求非常自覺,他曾提出,“我還是堅持這樣的作風,這就是吸取歐美進步技巧,利用中國固有喜見樂聞的旋律,用簡單和聲配以中國和西洋樂器,尤其多用打擊樂器,使作品本身成為大眾化、民族化、藝術化的統一藝術”。⑦他的作品正是通過對西方現代作曲技法主動、巧妙的借鑒,并使之與中國本土的旋律曲調相融合,而創(chuàng)造出了一種新的表現形式。
在《黃河大合唱》等多聲音樂中,冼星海運用了較多復雜的復調技巧,如雙調性、對位寫作、卡農運用等,產生了十分動人的效果,而這在當時的延安乃至全中國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意義。如《河邊對口曲》中,人們能感受到兩個主題縱向交織所形成的雙調性的色彩對比,它們既協和,又獨立,形成歌曲發(fā)展的新動力。《保衛(wèi)黃河》則是典型的聲樂卡農曲,作曲家通過安排與主題旋律適宜的輪唱,將抗戰(zhàn)的濃重的油畫般的色調表現無疑。類似的較為新穎的曲式安排,如《黃河船夫曲》其一領眾和的呼應形式,構成了聽眾對我國傳統民歌中多聲部勞動號子的回想,既展現了勞動人民的形象,也成為中華民族不畏艱險、頑強斗爭的精神寫照。
不僅如此,在歌曲創(chuàng)作傳播過程中,冼星海更有著實踐層面的自覺。他曾對自己提出要求:“首先要加強理論修養(yǎng),尤其是馬列主義藝術理論的修養(yǎng)。其次,要加強技巧的鍛煉,利用完整的技巧,發(fā)揚和實現音樂的理論基礎。再其次我們要從理論和技巧的基礎去創(chuàng)作,大量的去創(chuàng)作以適應大眾的需要。最后我們要利用歌詠的宣傳力量,在抗戰(zhàn)期中發(fā)揚高度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激發(fā)全國同胞的愛國熱忱”。⑧為此,在抗戰(zhàn)期間,冼星海一方面積極組織演出,一方面親自教唱,舉辦歌詠大會,組織歌詠游行,深入到學校、農村、廠礦、部隊去推廣、輔導群眾歌詠,有力地推動了當時的救亡歌詠運動。當然,冼星海還十分注重對宣傳干部的培養(yǎng)鍛煉,這些無疑都是音樂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大眾化的實踐主張。
由此,我們不妨可以這樣認為,冼星海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音樂領域的旗幟性人物,他的作品無論是人民性的精神內涵還是以其藝術性為基礎的大眾化特征,都表現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價值內容與要求,又開創(chuàng)性地與社會主義音樂藝術的創(chuàng)作原則與方法相貼近,對未來馬克思主義音樂美學觀也有著直接的影響。而對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fā)展認識,我們既不能忽視音樂藝術的作用,更不能忽視冼星海音樂藝術作品的貢獻。

注釋:
①周巍峙,《冼星海全集》(第1卷),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103
②同上:22
③張聞天,《張聞天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80
④周巍峙,《冼星海全集》(第1卷),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379
⑤同上,1989:37
⑥周巍峙,《冼星海全集》(第1卷),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53
⑦同上:144
⑧同上: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