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倫堡大審判》
——法律的正義真諦
文/趙磊
《紐倫堡大審判》
——法律的正義真諦
文/趙磊

劇情簡介:電影講述了一場紐倫堡大審判的始末。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一位美國法官來到紐倫堡審判一件案子。案子的被告是納粹德國時期的司法部部長及其相關同事,一共四個人。原德國司法部部長詹寧,為人有口皆碑,正義、善良,同時有著豐富的法律理論知識。很多人都認為他不應該成為被告,或即使成為被告也不應該被判有罪。因此,電影用了相當多的篇幅來展現法庭上的激烈辯論。同時,電影還描述了戰斗后德國人的生活,以及德國人對于戰爭、審判的看法。最終,審判結果出來了,卻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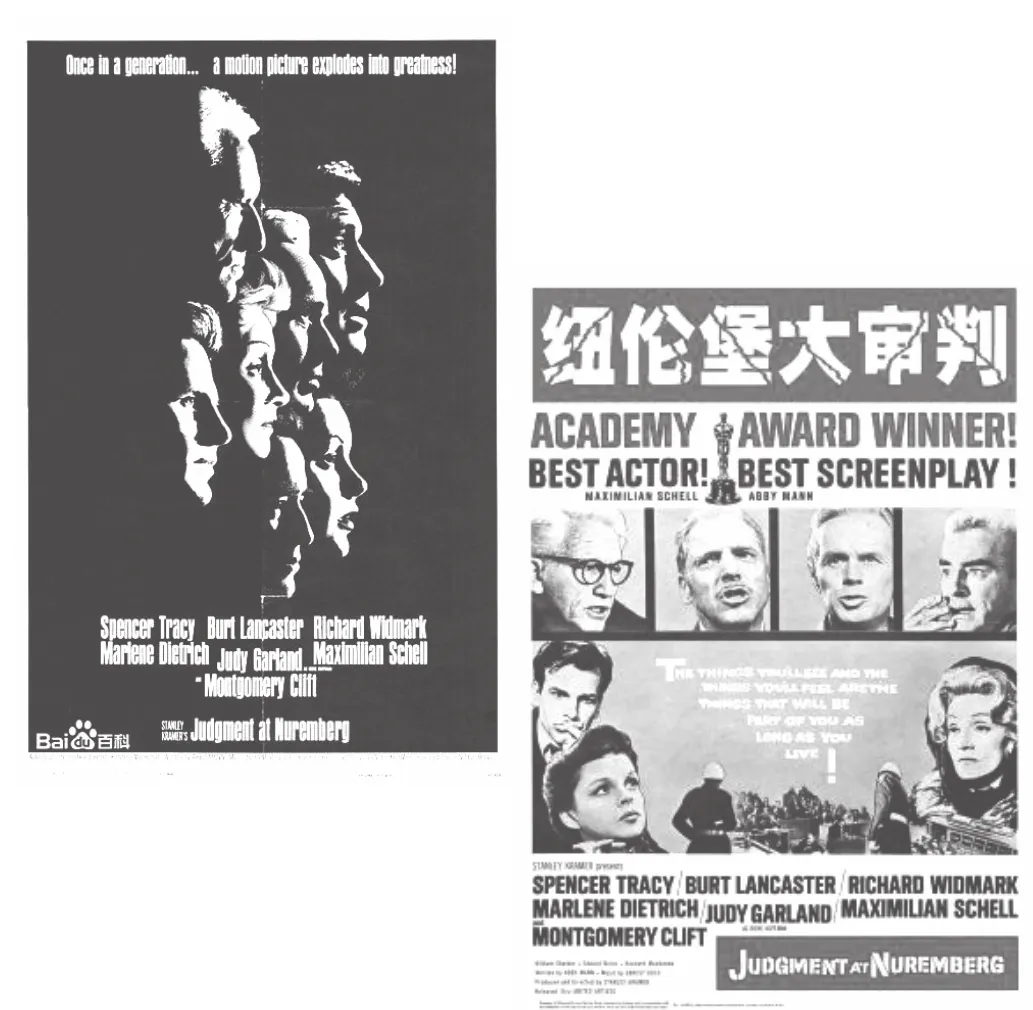
電影與法律似乎是兩個毫不相關的概念或詞語。電影代表了藝術,意味著感性與靈感;法律代表了規則,象征著理性與正義。在社會大眾或以法律和電影為業者的眼里,兩者即使不是有天壤之別,也必定是涇渭分明。但是,這僅僅是表征的現象,讓你的雙眼迷失、判斷失誤。電影作為藝術的一種表現形式,記載著人類情感的表達,承載著價值觀念的傳送。除通過電影內蘊的主題與線索來展現社會的生活現象、人物的經歷與內心情感之外,還可以以法律為主題,通過情節與言語的設置來表達對法律之正義和理性的訴求與追尋。因此,法律與電影這兩個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領域天然具有暗合性。但要發現電影與法律的契合點,需要有敏銳的洞察力與嚴謹的邏輯力。透過電影觀看人世間的千姿百態、世態炎涼與嬉笑怒罵,而其中所蘊含的法律現象也必須要體察與感受。總之,我認為每一部電影都精彩紛呈,其中不乏發人深省、回腸蕩氣的閃光點。而以法律為題材的電影則更多在感性中加入了嚴謹的理性,對社會公眾更具吸引力。通過電影使人們感受與體察法律與正義,發現法律的精神與真諦。
美國電影《紐倫堡大審判》便是這樣一部有關法庭審判的史詩性的電影。影片根據美國法官的回憶錄改編,是“一部以紐倫堡戰犯法庭為題材的電影作品,集中探討了在二戰期間執行納粹法律的德國法官的道義責任問題”。法律與倫理是貫穿影片的核心問題。該片為美國導演斯坦利·克萊默的代表作,由斯賓塞·屈塞、伯特·蘭卡斯特、理查德·威德馬克、瑪琳·黛德麗等人主演,可謂星光熠熠。最終,該片獲得奧斯卡最佳男主角、最佳改編劇本兩項電影大獎。
影片以布局嚴謹、唇槍舌劍的法律辯護來吸引觀眾,展現了1948年的紐倫堡,歐洲國際軍事法庭審判以曾擔任過德國司法部部長的詹寧為首的四名納粹德國法官的全過程以及相關人等與擔任主審判長的美國老法官的交流。四名被告被控“謀殺、殘忍、虐待、殘暴”,“破壞了德國的正義和法律”。導演選取了審判法官這一司法過程,力圖將紐倫堡審判這一宏大的歷史畫卷濃縮進一場審判過程中。“司法、事實以及人類的價值”,被強權政治強奸的法律以及社會暴行中的個人責任,黑白醒目,辯論精彩。這是一場拷問人性、蕩滌靈魂的審判,在其最本質上是對人類內在本性的法律的審判與道德的拷問,展現了一幅正義審判的圖景,一個法官神圣的裁判,一絲道德良心的拯救,一種關于法律未來的沉重思考。
我們從該片所表現的主題所處的背景來尋找法律的意義。紐倫堡審判是指1945年至1949年之間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盟國在紐倫堡所組建的國際法庭對戰敗國戰爭責任人進行的13輪審判,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對侵略戰爭的組織者、陰謀者、煽動者和計劃執行者進行的國際審判,開啟了將戰犯押上國際法庭接受法律懲處的先河。這次對戰犯的指控是以指導戰爭行為的公認的國際法和國際慣例為依據的,它作為國際刑法史上第一案例將永載史冊。紐倫堡審判清算了納粹的非人性的法律體制,但紐倫堡法庭最理想的目標——使戰爭成為非法,為審判侵略戰爭提供一個國際法庭——引起了持續至今的爭論。然而,無論如何,紐倫堡是國際關系法上的一個里程碑,它為當代世界留下了一套處理戰爭問題的行為準則。美國軍事法庭在紐倫堡城對在納粹德國政治、經濟和軍事機構與組織中身居要職的177名被告進行了12項后續審判。而電影《紐倫堡大審判》所演繹的就是其中的第三項——法官審判,這是針對利用法律迫害猶太人和納粹黨反對派的高級司法官員的專項審判。
事實上,當時美國的公眾和政府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沒有太大熱情了,法官海伍德自己也很清楚:“我是美國唯一有資格做這份差使的人。你知道,我不是第一人選,甚至不在考慮范圍內……希特勒走了,戈伯茲走了,戈林在被毒死之前自盡了,現在我們要審判剩下的醫生、商人和法官,都是些不該被審判的人。這樣就使得做這份工作的人寥寥無幾。你們跑到偏僻的緬因州找到我這個土老帽……我希望審判能繼續進行,特別是對德國法官的審判,我希望我能勝任。”可以說,這也是一場“法官對法官”的審判。
整部影片就圍繞著這場審判展開,片中充滿了貴族氣質和優雅風度。雖然影片長達三個小時,但它就像庭審辯論的示范會,精彩的法庭辯論中充滿了諸如“溯及既往的法律”、“自然法”、“法律實證主義”等名詞。控辯雙方激情對抗,尤其是詹寧在140分鐘后那段長達7分鐘的當事人陳述,令人印象深刻。他安然、平靜,從根本上否認這個法庭審判的合理性和權威性,利用沉默給自己澆鑄了一堵城墻。盡管城墻之外的辯論甚是激烈,但他不聽,也不看,他的眼睛里充滿著不動聲色的蔑視。他曾是德國著名的法學家、30本法律著作的作者、《魏瑪憲法》的起草者、德國司法部部長,可以說,他“洞悉法律的規則、精神和本質——法律的本質是虛無?人類自己劃下界限,又被這些界限圍困。世界本是充滿矛盾的,法律妄想理清一切頭緒,結果陷入更混沌的糾葛之中,作繭自縛”。
當然,跟大多數影片的結局一樣,正義最終戰勝了邪惡。然而,法庭上雙方據理力爭,真的都是在維護正義嗎?假定正義是一個能夠得到人們共同認知的東西,那么,他們共同探討正義就好了,何必針鋒相對,甚至不共戴天呢?是否有一條中間道路可以走呢?被告在掩飾下所作的合乎實證法律的“無理辯詞”,還是在維護人類最基本的道德正義嗎?法律是調整社會關系形成秩序,體現正義、保障自由的行為規則。但是,不同的西方法學流派,包括自然法學、實證法學、社會法學、功利法學等對什么是法與法的本質這一古老而又永恒的話題做出了不同的回答,形成了神意論、正義論、理性論、權利論等不同的學說。而對于西方法學流派思想的肇始人物柏拉圖來說,法律就是一種社會行為準則,它是公道與正義的標志。法律正義與道德正義不完全相同。法律正義是“訴訟正義”,是指通過法律機器的正常運轉而獲得的后果或判決。因此,法律正義是為道德正義與自然正義服務的。
該片的焦點集中于四個方面,第一,法庭審理的合法性。第二,所做裁決法律的正當性。第三,被審判戰犯的現實困境。第四,法律的自然正義性與實證規則性。詹寧法官的選擇一方面是基于對實證法律的理解,另一方面是基于對實在法的道德判斷。在某種程度上,他是認同當時實在法的價值取向的:國家本位,為了達到所謂的國家共同利益,不惜犧牲個人的基本權利與自由,個體在這樣的視野中是缺位的。這不僅是詹寧的倫理選擇,也是所有被告的倫理選擇,甚至是整個德國上層社會的倫理選擇。影片中出現的那位俏麗高雅的貝托太太,無疑代表了德國上層社會的形象。她為詹寧辯護的理由是:“詹寧法官舉止紳士、高貴,敢于捍衛自己的尊嚴和榮譽。這樣一個正派的人,怎么會犯錯呢?”這些高貴的人沒有經受過苦難,因而也就沒有對受難者的同情、憐憫之心。他們不是不可能知道執行法律的后果,而是不想知道,不愿去想。因而海伍德法官在最后與詹寧的會談中,在詹寧稱自己確實不知道他們的判決會帶來如此多的殺戮、死亡時,他回應道:“當你判第一個人死刑的時候,你就應該明白這一點了。”沒有個人的自由與權利這個概念的時候,一個人和許多人在你的意識中雖然都是等同的,但卻是虛無的。這種價值判斷在紐倫堡審判中,由海伍德法官給予了最強烈的譴責。他宣判道:“被告的行為違反文明社會的共同原則。國家不是石頭,而是人的延伸——正義、真理、個人的價值,是國家的基本價值。”
納粹法官被指控是因為他們執行了當時有效但現在被認為是惡的法律,如防止種族污染、剝奪生育權等。這就引發了一系列的問題:在德國,法官的地位如何?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外在壓力?法官是否有選擇權,如果不服從將會怎樣?由此又引發出即使法官有選擇的可能,那么他應不應該進行選擇?他的職責是執行法律,還是可以凌駕于法律之上對法律進行判斷?從而產生的進一步的問題是:如果可以,他應該遵循什么法則?這樣的詰問涉及了關于法律效力與適用的永恒爭論:“有沒有比實在法效力更高的規則,可以對實在法進行判斷?”不同的法學流派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不同,“自然法學派認為神法、自然法的效力高于實在法,而歷史法學派則不承認自然法的效力。”
這部影片與其說是關乎法律的,不如說是有關人性與道德的。紐倫堡審判,審問的是所有經歷過這一切的人的心靈。以自然法來看,納粹德國制定的實定法違反了自然法上的正義、公正、自由等價值,作為一個理性與充滿道德正義感的人,應堅決拒絕這些惡法的執行與適用,否則這就是不正義。既然自然法是永恒存在的,就不存在所謂法律不溯及既往以及管轄權的問題了。相反,以法律實證主義的觀點,除了實定法本身之外,并不存在符合所謂正義價值的自然法,正義就代表著忠實地履行實定法。因此,不同的法律理念會導致截然相反的兩種法庭判決。
“執行自己國家的法律而受到國際法庭的審判,還是拒絕適用它們而淪為德國法制下的罪人?是或不是成了問題,孰是孰非,誰能斷清?對法官形而上的苛求是否公允?這又回歸到‘惡法是否是法’的爭辯之中。在戰爭的背景下,像詹寧這樣的法官們,在德國納粹的統治下應該拒絕適用違背正義的法律嗎?他們應該不顧自身可能遭受迫害的危險嗎?而那時又有誰來告誡他們,這樣的法律是不正義的呢?我們在要求法官具備高素養的同時,是否又提供給了足以使其義無反顧進行公正審判的保障呢?是否又要因為這些法官們現實困境的存在而拋開自然法所代表的正義公平呢?現在看來,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也許,紐倫堡審判本身就是矛盾的。歷史中審判者都自覺回避著這些問題。但是,紐倫堡審判中通過正當的司法程序審判戰爭機器下的每一個劊子手,審判中所反映的、更值得我們深思的不是審判,而是人性的終極歸宿。法律的真諦是平等地保障每一個人的自由,自然正義將是永恒的主題。
(本文作者系東北師范大學憲法學與行政法學碩士)
參考書籍:
1.[美]保羅·伯格曼、邁克爾·艾斯默:《影像中的正義》,朱靖江譯,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
2.廖溢愛:《紐倫堡的天問——評〈紐倫堡大審判〉》,載徐昕主編:《影像中的司法》,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book=54,ebook=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