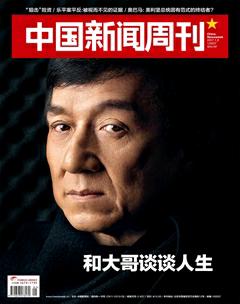從社會建構論視角看“校園欺凌”
鄺海炎
中國很多壞現象都是通過建構才被認識,被改變的,比如“家暴”和“霧霾”。
命名是對事物有一種親,命名也是一種實踐行為,是要宣示面對的勇氣和
改變的決心
資深媒體人,
著有《快刀文章可下酒》
近年來,校園欺凌事件層出不窮。所以,自從女兒前年上了幼兒園,我心里就盤算如何保護她。想來想去只有一招最實用,就是在女兒上下學的路上,像丐幫弟子一樣拿根棍子偷偷跟著,以防有人欺負她……
可我畢竟沒實踐這夸張的點子,因為我相信社會問題可以改良。12月9日,北京中關村二小一位家長發文,稱兒子明明常受同學欺負,最近還被扣廁所垃圾筐,兒子因此失眠、易怒,經診斷為急性應激反應。她向學校反映此事,學校卻只說是“過分的玩笑”,還讓她“大事化小”。
十幾天過去了,這事不了了之。但我探尋孩子保護方式的渴念卻沒有熄滅。
很顯然,在這次事件中,涉事學生行為是否構成“校園欺凌”是各方最大分歧所在。根據國務院《關于開展校園欺凌專項治理的通知》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制止校園暴力:教師手冊》,“校園欺凌”具備三要素,即“重復發生性、傷害性和力量不均衡性”。明明被傷害是事實,但要證明其具有“重復發生性”就很困難,因為學校說第二天這兩個學生還互動玩鬧了。
輿論也因此打結:挺家長的認為,校園欺凌愈演愈烈,就因為學校總當“玩笑”輕描淡寫。挺學校的則認為,這種事應讓孩子自己處理,過分關注反使孩子受傷,以后也不好跟同學相處。
但這個“結”其實不難解。按照建構社會學的觀點,認識是積極主動的“建構”, 而不是被動的“反映”。事實像原料,要經過話語、文本、行動的轉化,公共目光的關注,才能作為“社會問題”存在。(見林聚任《西方社會建構論思潮研究》)所以,明明被傷害這事,可以建構成“玩笑”,也可以建構成“欺凌”。
照這意思,全世界沒理可說,隨意建構嘍?非也,建構社會學還主張,語言不止于命名功能,它還具有規范作用,規定了人們思維和實踐的方向。比如說,把農民工群體類型化為城市的“越軌群體”還是“弱勢群體”,是政策排斥還是政策支持,就體現了不同的建構途徑。
再回看中關二小事件。如果建構成“玩笑”,大事化小,可能縱容欺凌。臺灣學生葉永鋕因為像女的,常遭同學羞辱,校方對葉在廁所內被強行脫褲的羞辱淡然處之,認為“只是好奇”。結果葉永鋕受不了欺凌而自殺。
有些家長也許會說,必要時鼓勵孩子打回去。可被欺學生多乖巧弱小,打回去可能遭到對方更大報復,亦非良策。
建構成“欺凌”就不同了。對“欺凌”的社會討論會對欺凌者形成道德壓力。更關鍵的是,我們可交由家長、學生、學校、社會人士各方代表組成的學生事務委員會來處理欺凌事件,以程序公正避免糾紛。比如,明明父母要求批評肇事學生,合情合理。但要求把這事寫進學生操評,讓該學生背負一生的污點,估計就不會被委員會通過。
傳統“大事化小”方式可行,是因為以前的學生多在村里或單位小學,處于熟人社會,發現欺凌苗頭,家長可“上門討說法”,用“道德共識”規范孩子行為。現在不同了,社會流動性加強,一個班里天南海北的學生都有,家長互不相識,校園欺凌又借助社交媒體成天轟炸家長神經,焦慮的家長也就更喜歡通過抽象化的法律規則解決問題。
中國很多壞現象都是通過建構才被認識,被改變的,比如“家暴”。還有就是,2005年前,國人基本沒有“霧霾”概念。2008 年,幾個外國運動員戴著口罩到北京參加奧運會,還激怒了國人,說他們“侮辱中國公眾”“居心叵測”。最后他們向北京奧組委遞交了道歉信。可在霧霾肆虐的當下,想起那幾個外國運動員,我們難道不臉紅嗎?
有詩人說:“在一個春天的早上,第一件美好的事是,一朵小花告訴我它的名字。”在這個急速變革的時代,能坦然接受新事物的命名,又何嘗不美好?命名是對事物有一種親,命名也是一種實踐行為,是要宣示面對的勇氣和改變的決心。